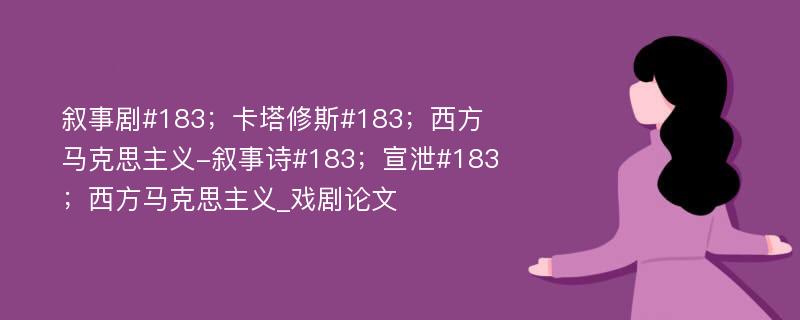
叙事剧#183;卡塔西斯#183;西方马克思主义——Narrative Poem#183;Catharsis#183;Western Marxism,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西斯论文,Narrative论文,Western论文,Marxis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形式主义者用“陌生化”理论总结了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面对一种文学史上新的艺术形式,接受者首先会因为其形式“陌生”而加以欣赏玩味;随后,该种艺术形式又会因为逐渐被熟悉而变得平庸习常,缺乏美感。在对美感的渴望中,一种更新的艺术形式又出现了。这样周而复始,艺术遵循着“陌生—熟悉—陌生”的形式规律推进。
从现象描述来说,“陌生化”理论的概括是与西方文学发展相适应的。我们知道,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指出,史诗、戏剧和抒情诗这三种摹仿的艺术存在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摹仿的对象不同,摹仿的方式不同。如果单就史诗(叙事文学的萌芽形态)和戏剧的摹仿方式来说,西方艺术家们一直在寻求超越各自固定的文化规范。从叙事文学的叙事人、视角等要素的不断实验,到戏剧领域内多种演剧体系的并存,都可视为“陌生化”的进程。但是叙述(narrative)还是模仿(imitate)始终是不可逾越的文体标志线。直到布菜希特的“叙事剧”出现,才最终突破了叙述与摹仿的对立,使戏剧艺术再次走向“陌生化”,将20世纪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起点。
布莱希特的“叙事剧”,简而言之,就是要用叙事方法来表演戏剧内容,人为地打破“戏剧舞台是个真实世界”的幻觉,令观众时刻意识到是在观看表演并要求对剧中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作出理性的思考判断。布莱希特强烈反对把观众融入剧情并产生情感共鸣和感性认同的传统戏剧形式。
布莱希特指出,演员的表演应当象一次交通事故的目击者向一群人说明这次事故是怎样发生的。“他只需要模仿人物的几个动作,使人们能够得出一幅画面就够了。”[①]具体说来,布莱希特要求剧作家应把剧作结构成插曲式的,在每场前面要有一个文字标题。插曲式的结构和文字标题,使事件之间的联结、过渡十分显明突出,情节被打断,故事呈现支离破碎的开放性状态。这显然对立于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有头有尾有身”的有机整体的情节观。在布莱希特看来,亚氏封闭的结构势必迷醉观众,使他们无法批判性地思考。而且,布莱希特还主张剧作家采用古老陈旧的题材进行再创作,有意拉开剧情与现实生活的距离,避免观众产生认同。对演员,布莱希特要求他们放弃所学过的一切能够把观众的共鸣引到创造形象过程中来的方法,客观地进行表演,带一定的保留态度或保持一定距离地说话、慢慢地重复一个动作,甚至可以停下来向观众解释他正在做的事。布莱希特尤其强调,演员不能失去自我意识,完全被角色的意识所取代,演员必须既是角色,又是他自己;既是角色的表演者,又是角色的“裁判者”,这就是著名的演员“双重形象”理论。布莱希特还提倡去除舞台的幻觉性和象征性,除了必不可少的道具外,舞台应是空荡荡的,只提供一个讲述故事的空间。在他的《三角钱歌剧》中,大幕不过是挂在横跨舞台的一条绳子上的一块脏布。舞台换景是在观众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灯光装置也故意让人完全看到,在观众席上有时还挂着诸如“别这么浪漫地发愣”之类的标语。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观众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剧院之中。布莱希特对作曲者的要求更是与众不同,作曲者可以独立地表现对戏剧主题的想法,作出自己的音乐和歌曲“评论”,甚至可以和舞台人物的行动发生冲突,比如在其名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四个乐师坐在舞台旁边的厢房里,在安静的场次演奏有威胁感的乐曲。独立的乐曲和歌曲一方面可以打破舞台幻觉,引导观众采用理智的眼光看戏,另一方面对舞台上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价,“……向观众示范性地表明一种正确态度,使他们凭自己的经验来鉴别,并形成自己的见解。”[②]可见,诉诸理智是布莱希特的旨归。
这种种新颖的戏剧手段,就是要达到“布莱希特所谓的“间离效果”,亦即演员与所扮演角色、观众与舞台形象、舞台世界与现实生活统统拉开距离,从而产生“陌生化”的美学效果。
布莱希特的戏剧美学显然与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戏剧大异其趣。追求“真实性”的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戏剧,从推重“三一律”的古典主义戏剧开始,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体系终于登峰造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倡所谓“第四堵墙”的戏剧美学,要求演员与角色最大可能地认同,体验角色的喜怒哀乐,融入角色的内心世界;舞台也要被最大程度地改扮成现实的生活场景,布景道具写实求真,最终让观众产生自己就是舞台人物,舞台就是生活本身的幻觉。在观众、演员、角色三者的关系中,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戏剧要求的是“我与笑者同笑,我与哭者同哭”,而布莱希特叙事剧追求的是“我笑哭者,我哭笑者”。
写实主义戏剧的美学理想,是亚里士多德“卡塔西斯”(Katharsis)理论的延续和发展。亚氏“卡塔西斯”作用主要是通过悲剧所产生的恐惧和怜悯的效果,使观众的情绪得到宣泄、净化,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以避免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过激行动,发生“悲剧”。亚里士多德是奴隶社会的贵族思想家,他的“卡塔西斯”的潜台词是维护奴隶主统治制度的合理性与稳定性。我们知道,当时戏剧的观众主要是贵族和平民阶层,他们是奴隶社会的统治阶层,观看演出是为了娱乐和消遣,或者得到一些道德训诫和为人处世的学问。因此“卡塔西斯”论的形成显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跨入资本主义社会,市民阶层成为戏剧艺术的主要观众,市民趣味极大地影响了戏剧美学观念的变化。但“卡塔西斯”的作用依然强大,它试图置换现实与艺术的领地,模糊人生与戏剧的界限,力求使大众认同于舞台人物和舞台场景,沉醉于理想的王国或神奇的异邦,偷欢片刻。有时他们化身为“英雄主人公”,纵横驰骋,无往而不利,实现了在委琐的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变得心满意足;有时他们又化身为“悲剧主人公”,感同身受,承受磨难乃至死亡,释发了对“异化”世界、对“异化”自我的不满,变得心平气和。所以,这些或明或暗地以“卡塔西斯”理论作为支持的戏剧,成了灵魂的节日和大众的超脱,它们最终不是激发大众变革社会和改变自身境遇的愿望,而是力图消除这种愿望。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戏剧(毋宁说是自然主义戏剧更为恰当),实际上成了统治集团的同谋,成了现存秩序的掩体。它并不借助赤裸裸的说教和宣传,而是间接地诉诸观众的意识、欲望和情感,有效地削弱和剥夺了大众反抗现实世界的力量。
自然主义戏剧的迷误在于对“摹仿自然”的偏见。任何一种真诚的艺术都是对现实的某种变形和重塑,这是一个形式化的过程。现实只是作为素材的存在,在这层意义上,艺术是对现实的背离,是对现实经验的否定。艺术展现的是一个疏离于现实的新现实,在这里,我们领悟到美和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这个新现实是个自律的、自主的独立世界,在这里,主体摆脱了现实中的各种束缚,走向审美的纯粹的无功利性,获得了彻底解放。而偏执于对自然的如实摹仿,妄想使艺术形式成为生活的直接表现,必然混淆艺术形式与现实之间的根本差异,与现实的联盟意味着艺术本身的丧失,其结果是现实吞没了艺术,对现世欲望的追求取代了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作为人类生存的精神维度消失了,这正是二战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景观。
20世纪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戏剧形式,都是超越了现实具体的生活和经验,重建一个世界并以此对抗于既存的社会。与此不同,写实主义戏剧,愈来愈走向自然主义,追求逼真酷肖,营造真实生活的幻觉。应该承认,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一定意识形态的关联物。资产阶级自然主义戏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言说,它们证明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和稳定性,筑固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井井有条的情节发展,一再重复的道德主题,缺少变化的人物形象,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高度秩序化,造成人性异化的文化表征。而包括布莱希特戏剧在内的现代派戏剧则代表了一种被主流意识形态压制的反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们言说的是现存世界的荒诞和对理性世界观的怀疑,是以反艺术的精神和反艺术的形态来反对现存的非艺术状态。布莱希特曾说:“资产阶级戏剧表演的目的是掩盖矛盾,制造和谐的假象和理想化。舞台上反映的社会状态似乎是不可改变的,人物性格都是‘个性’,而按‘个性’这个词的含意,就是天生不可分割的,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些当然不符合现实生活。所以现实主义的戏剧应该放弃这种表演目的。”[③]因此,从20世纪戏剧艺术的整体背景来理解布莱希特“叙事剧理论”和“间离效果”,就能懂得它的巨大意义在于它不仅打破了叙事与模仿的对立,在艺术领域内对传统戏剧形式发动了革命,而且保持并强化了艺术否定现实的功能,再次唤起了对自然主义的警觉和对自然主义掩盖下的“异化”世界的抗议。
尤值一提的是,布莱希特艺术形式的革新,追求的是“反卡塔西斯”作用,即“领悟现实—否定现实”。他要让观众从对习常生活的麻木中被陌生的形式所惊醒,从而进一步走向思考和行动,而非从震惊走向平静和无为;对主体的激情和意欲,他反对宣泄和压抑,提倡激发和升华,最终成为批判和反抗现实的力量之源。这表明,布莱希特的政治立场同样鲜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布莱希特戏剧观的核心就是:戏剧要通过舞台演出把社会表现为可以改变的,把人表现为可以改变的。对他而言,戏剧的崇高使命是让观众在艺术欣赏中认识社会,投身改革现实的斗争。我们知道,由艺术到生活,由理想到现实,这也正是本文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逻辑和斗争策略。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都着重从文化、艺术和美学入手,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改变人的意识才能真正变革现实,所以他们一致把艺术本质理解为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从本雅明、霍克海默到到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都是现代主义艺术的辩护人。他们认为,艺术上的反叛、文化上的拒绝(反主流文化)源于一种乌托邦的价值追求,既承诺了未来的希望,又表达了对现世的弃绝。艺术的自律性,在他们眼里,绝不是唯形式的,而是具有社会政治潜能。马尔库塞说:“美学形式对于艺术的社会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形式的物质否定了压抑人的社会的物质——它的生活、劳动和爱情的物质。”[④]质言之,艺术借助形式以否定的姿态介入现实。自在自为的艺术世界提供一个理想世界的乌托邦图景,它既脱胎于现实经验,又超越了现实经验,超越不是逃避,而是抗议、造反,以图唤起革命的行动,谋求主体的“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全面解放。
布莱希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用艺术实践补充、佐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但实际上布莱希特“叙事剧”处境似乎很可悲,据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三)介绍,布氏的革新往往只是在同行中得到喝采。一般观众在熟悉了“陌生化”的手段以后,还是把他的戏剧当作传统戏剧来接受,甚至认为“陌生化”是纯形式主义的、华而不实的噱头。这说明,对传统戏剧艺术只作初级的否定,完全抛弃了传统艺术关于“美”的信念,是缺少社会—文化基础的一厢情愿,只会被认为是一种不断缩短周期的形式竞赛。毫无节制的否定只能成为一种时尚表演,终于能量耗尽,向现实投降。
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始终给人一种想揪着自己头发逃离大地的感觉。西方马克思主义声势浩大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在高度一体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具有强大整合作用的资本主义文化面前,依然是一种表演,甚至沦为批判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这一命运,阿多尔诺只能回答说,否定只是永不妥协的否定姿态,就如沉船上发出的绝望呼号;马尔库塞反思后也认为,对审美之境的关注包含了“绝望的因素,即逃避到一个虚构的世界,仅仅在一个想象的王国中,去克服和变革现存条件。”[⑤]乌托邦的价值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无法实现,无法完成其革命任务,这是一个悖论。
但是,无论布莱希特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怎样的理论与实践的困境,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所做出的努力。他们洞悉了资本主义文化结构,解剖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肌理,尤其是对“先锋艺术”和“否定精神”的推重,无疑对处于文化环境下的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帮助,它启示我们面对工具理性的盛行、消费主义的商品崇拜,始终要采取不顺从的态度,维护艺术精神的本性。
注释:
①《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②转引自宋寅展、苏成全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③《戏剧小工具篇补遗》,转引自《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④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⑤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