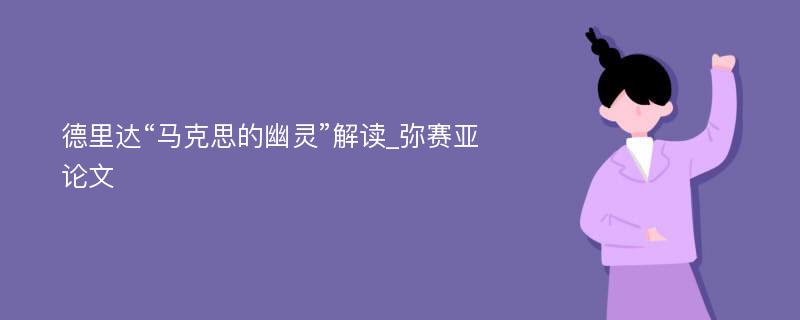
解析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幽灵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据1993年加利福尼亚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其内容庞杂,涉及的问题也较多,但整体观之,其核心内容十分明确:它在论述马克思的精神。表面上看,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精神多种多样,但事实上他正想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马克思精神去表达他对马克思精神的一种完整理解。那么,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的精神是一种批判精神
针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德里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时代仍然呼唤着马克思的精神。他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德里达,第2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他认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第127页)。
在德里达看来,无论当前国际上信仰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马克思的精神”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实际上是在“哀悼”中“召唤”马克思的精神。而那些公开反对马克思的人,事实上他们也离不开马克思的精神,他们受到马克思精神的纠缠,最少他们在分析问题时仍在用马克思的话语说话。他说:“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定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第53页)德里达认为,当前西方社会之所以如此过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因为它们害怕马克思主义,想借某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时”来“驱魔”。因为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已搅得西方社会不得安宁,使许多人感到心惊肉跳,他们恨不得借此能把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棒子打死,立刻开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证书,好让它永远消失于历史舞台。“……驱魔法在于以一种念咒的模式反复说那死者的确已死去”,“灵验的驱魔法故作姿态地宣告那死亡仅仅是为了造成死亡”。但是,德里达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这种句式力图使人们放心,但首先是为了说服自己让自己放心,因为没有什么比期望死者的确已经死了这件事还要不可靠”(第67页)。
既然马克思的精神是时代需要的精神,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的精神呢?在此,德里达指出必须把马克思的精神与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必须从马克思文本的内部去寻找其精神实质。他说:“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且同作为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第98页)至于什么是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德里达认为,“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这样一种自觉自愿的批判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它内在于一种还不是批判性的土壤中……”(第124-125页)
其次,马克思的精神也是一种实现解放的精神
德里达更要向人们展示的是马克思精神的另一向度——“解放”的精神。他说:“如果说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一种内在一致的解构理论必须强调这些方面,尽管它也知道这并非最后的或最初的结论)。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或弥赛亚式的声明,是某种允诺,即人们能够摆脱任何教义,甚至任何形而上学的宗教的规定性和任何弥赛亚主义的经验。”(第126页)“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年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这一希望,而且作为‘有必要’的坚如磐石的保持而坚持到底。”(第106页)
为了论证“解放的马克思的精神”,德里达深入到了马克思的文本内部。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德里达指出马克思在分析意识形态、拜物教和宗教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意识形态和宗教虽然产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中,但它们一经产生后又脱离了生产过程,从而自主化和自动化。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尽管意识形态和宗教产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中,但它们又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立性,并且认为宗教的特点和独立性又为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独立性提供了雏形。他说:“宗教并不是其他现象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或其他生产中的一种幻影生产。一方面,它能赋予幽灵生产或意识形态幻象生产以它的原初形式或它的参照范例、它的第一比喻。而另一方面(而且是首要的方面,且无疑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宗教也能通过弥赛亚降临说和末世学宣告我们在此以必然地不确定的、空洞的、抽象的和枯燥的形式特地赋予它的东西”。(第228页)德里达认为,宗教所宣告的“弥赛亚降临”和“末世学”正是他要指出的“解放的马克思的精神”,尽管“这一精神显得多么的神秘和矛盾”。(同上)在他看来,没有这种精神,所有的物和物质生产就失去了意义,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希望和历史事件。他说:“若是没有那种幸存,若是没有头脑外部的这种自主性和这种自动性的可能幸存,就没有什么是可能的,就没有什么能从批判开始。人们可能会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安身之所在”。(第234-235页)
为了防止人们把他所提出的“弥赛亚”和“末世学”的思想与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德里达一再强调他所说的“弥赛亚”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是想借“弥赛亚”一词去表达一切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他说:“该如何将我们在此在同一名称下谈论的两种弥赛亚空间联系起来呢,又该如何将它们分割开来呢?如果说弥赛亚的召唤真正属于一种普遍结构,属于通向未来的历史开放的不可简约的运动,因此也属于经验本身和它的语言(对即将到来的、紧迫的、急切的事件的期待、承诺和应诺,对超出法之外的拯救和正义的需求,对不在场死了的他或她一类的他者作出保证,等等),那么人们该如何用亚伯拉罕的弥赛亚主义的形象来思考弥赛亚的召唤呢?它能够说明抽象的遗弃和一般的条件吗?亚伯拉罕的弥赛亚主义难道不只是一个例证式的预想,一个以我们在此正试图命名的可能性为背景给出的曾用名吗?但这样一来,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个名字,或者至少保留那个形容词(我们宁愿说弥赛亚的召唤而不愿意说弥赛亚主义,为的是指明一种经验结构而不是一种宗教),在那里没有一个临到者的形象——即便在他或她被预告要来临的时候——是事先确定的、可以预想的甚至可事先命名的?”(第229-230页)在德里达看来,任何宗教和意识形态都要以一定的理想形式出现,都要给人们描绘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当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想“尽力把马克思主义从任何一种目的论或任何一种弥赛亚式的末世学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德里达则明确指出他所关心的“恰恰是要把后者从前者中区分出来”。(第126页)
德里达如此注重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和正义性,是否说他所讲的“解放的马克思精神”只是指一种解放的理念?显然不是。在他的理论中,“解放的马克思精神”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更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在他看来,如果“解放”的思想只表现在思想中,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就没有根本区别。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施蒂纳及其各种“幽灵”的批判之所以显得如此深刻,是因为马克思并不像施蒂纳那样仅仅在意识形态内部兜圈子(在德里达看来,仅仅从思想上去批判“幽灵”是不可能达到毁灭它的目的的),而是揭示了各种“幽灵”产生的现实条件,并提出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摧毁去达到最终毁灭各种幽灵的目的。他说:“马克思似乎是在提醒施蒂纳:如果你想要驱除这些幽灵,那请相信我,我恳求你,自我学的转变是不够的,一种注视方向的改变是不够的,还有加入插入语以及现象学的简约也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工作——实际地,真正地。人们必须思考工作并为此而努力。工作是必要的,把现实性看做是实际的实在性也是必要的。通过驱逐和驱除他们身体的独一无二的幽灵般的形式,人们并没有一下子就赶走现实中的皇帝或教皇。马克思是十分坚决的:当人们摧毁了一个怪影般的躯体时,留下的是一个真实的躯体。当皇帝幽灵般的形式消失时,这不是形体本身的消失,而只是它的形象性、它的怪影性的消失。这时皇帝比过去还更为真实,而且人们还可以比过去更好地领教他们的实际权力。当人们否定或摧毁祖国的幻影或怪影般的形式时,人们还没有触及构成它们的‘实际关系’。”(第184-185页)而摧毁现实中存在的一切,就必须借助于革命行动。他说:“弥赛亚的召唤,包括它的革命性的形式(弥赛亚的召唤通常都是革命性的,也应当是革命性的),当然是急迫的、紧迫的”。(第230页)
再次,马克思的精神是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的统一
从表面上看,德里达提出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是孤立的,是两种不同的马克思的精神,实际上它们在德里达的思想中是根本统一的,是一种精神的两个方面。德里达曾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似乎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之间来回摆动,那就是其遗产对我们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两个公理。但是,这是一个有着双重联系的遗产,而且它还能向任何遗产的双重联系,因而也能向任何负责的决定的双重联系示意。矛盾与秘密就存在于指令中(如果人们愿意说的话,那指令就是父亲的精神)。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要把理想的原创性和真正效验性、自主化和自动化看做是延异(幽灵的、幻影的、拜物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以及在延异中不单单是想像的幻影的无限暨有限的过程。……另一方面,甚至在马克思还是一位第一流的工艺思想家的时候,或者说,甚至在他在遥远的将来还是一位最有名的通信技术思想家——不论是从长远还是从最近来看,都永远是如此——的时候,马克思就一直想在一种本体论中建立他的对幽灵的幻影的批判或驱魔术。”(第232-233页)也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思想的自主性和理想性(即他所谓的“解放”精神),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思想的批判性(即他所谓的“批判”精神),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联系。
那么,德里达究竟是如何建立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呢?关键在于他抓住了联系两种精神的中介——“现实”和形成思想的主体——“自我”。在他看来,现实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有生命的自我具有自动免疫力”。“为了保护自我的生命,为了把它自己造就为独一无二的有生命的自我,为了一如既往地自我关联,自我必然会被引去欢迎自身内的他者(有如此多死亡的形象:技术装备、可重复性、非独立性、补形术、综合图象、幻想等的延异,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语言,且是在语言之前),因此,自我必须为非自我、敌人、对头、对手采取表现上意指着保护的免疫措施,并利用这些措施既保护自己又反对自己。”(第198页)因此,与此相适应,思想也应该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此过程中,新思想不仅要不断批判旧思想,而且也要时刻准备着进行自我批判。不仅如此,德里达认为在批判的同时,也要用新思想对现实实行革命的变革。由此,在他的思想中,“现实”——“批判”——“解放”、再“现实”——“批判”——“解放”等等就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链条。所以,他说,马克思“在为历史号脉。他听到了一种革命的频率。在有规则的跳动中,对幽灵们的恳请和弃绝在革命中交替出现”。(第157页)他激励人们要“在革命的内部拥有革命,拥有将来的革命”(第161页)。
二
《马克思的幽灵》引经据典,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来回穿梭:德里达对马克思文本的熟练掌握令人敬佩。面对这位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思想急转,人们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马克思的幽灵》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首先,德里达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精神
正如德里达所说,马克思的著作中充满了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马克思著作的一些标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历史上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上,还表现在对自己理论的不断超越上。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但是,“批判”绝不是马克思工作的全部,他从事批判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正面的观点——阐述新世界观;也正是因为有了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才最终和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划清了界限。德里达进入马克思,进入马克思的文本,只抓住了马克思精神的一面——批判向度,却避而不谈马克思精神的更为重要的一面——建设向度,甚至声称要把马克思的精神与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这种脱离“建构”的批判精神,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解构主义,是明眼人一眼便能看穿的。
德里达作为一位解构主义大师,的确有高于一般解构主义者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在解构一种理论之后,似乎让人们感觉不到解构的痕迹。为了说明自己与其他解构主义者的不同,他还分析了解构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态度。他说:“在此也许该强调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之间的关系70年代初以来就已经在所有的方面引发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些探讨之间常常是对立的和不可简约的,但也是为数众多的。对我而言,它多得使我在此再也不能公正地对待它们和辨别我对它们所欠的人情。除了直接以此作为它们的题目的那些著作外(如米歇尔·雷恩的《马克思主义与解构学——一种批判的结合》,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2;还有简-玛丽·比努斯特的《已故的马克思》,伽利马尔出版社,1970。后一本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其标题是向马克思致敬,但实际的目的却是解构性的,并且这一标题与其说是否定性的,不如说是死亡证书——是发人深思的;本人的这部著作的标题可以看做是对比努斯特的那本书的标题的回应,不论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或者说还剩下多少时间,它都可以说是对那一不幸的事件的回应——或者说对那亡魂的回应)”。(第134-135页)
德里达对马克思精神的解构性阅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解构主义者,还因为他运用了更加巧妙的解构策略,他更善于利用马克思的言论来解构马克思的精神。一方面,德里达运用了马克思的文字游戏。他肯定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马克思,但同时指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当人们要揭露他自相矛盾的时候,他马上又指出“以前有一个叫马克思的人也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带有“悖论”性的逻辑,保证了德里达在解构性地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时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德里达运用了马克思文本中的内容游戏。他认为马克思的精神不是表现在马克思的文本内容中,而是表现在对此的不断超越之中,即使继承的东西与马克思的文本内容不相一致也不足为惜。对此,德里达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作佐证。他说:“我们不是非得要求得到马克思的同意——他甚至在未死之前就反对这么做——才可以去继承他的观点:继承这样那样的观点,不过这并不是要求继承来自他的观点,而是要求去继承通过他、借助他来到我们面前的观点。我们不是非要假设马克思与他本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似乎对恩格斯吐露过自己的心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确然无疑的。为了说明同样的东西,我们还必须引用马克思作为权威吗)”。(第49页)
其次,德里达所提倡的马克思的解放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精神
不可否认,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出的关于“解放”和“革命”的思想更有价值,更值得人们关注,但其具体内涵也需要作深入的分析。
德里达是结合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来论述马克思的解放精神的,但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误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这里,马克思显然认为意识形态只有相对独立性。德里达不仅把马克思所讲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等同于独立性,而且还混淆了作为一种存在的意识形态和作为一种认识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因以往意识形态的错误而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现实中的作用,但他更没有因以往意识形态有存在的合理性而忘记去揭示其在认识论上的错误。马克思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同上,第72页)正是因为马克思揭示了以往意识形态以“虚假意识”为基础的认识论错误,他才形成了自己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以对现实反映的“真实意识”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科学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确实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带有理想性的特点和实践性的要求,但这种理论之所以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不是因为它的理想性和实践性,而是因为它的科学性。它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而形成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的科学性,是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德里达在分析马克思这一理论时抓住的只是其理想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却避而不谈其科学性,甚至还要否定其科学内容。
另外,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来说,它不只是指一种变革现实的理论要求,更是指一种改造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第15页)为了保证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坚持其唯物主义原则,深入工人实际,认真研究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最终提出了像“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要理论。这些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新的发展(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就曾谈到这一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共产主义实践运动就很难取得成功。德里达始终强调要把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与“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尽管他也提出了“与‘政党形式’或某种国家或工人国际形式决裂,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实际的或有效的组织形式”这样的话语,但由于始终不提这些“实际或有效的组织形式”的内容,因此人们对他所谓的“解放”运动仍然不得要领。事实上,根据德里达的思想,他也是很难提出这些“实际或有效的组织形式”的内容的。因为他把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仅仅归结于经验认识,并且认为这些认识也是因人而易、各不相同的,因而,在这种没有共同认识的前提下,要想建立统一、有效的行动组织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他说:“他(指施蒂纳——引注)既忽视了一定的、因而也是必需的存在,忽视了规定性(指控的主要字眼),同时更确切地说,也忽视了这种规定性的经验性。因此他无法理解在异质的规定性方面决定精神这种规定性的东西。事实上,激发这种批评灵感的表面上公然宣称的经验论,总是会反过来求助于一种相异性的规律。经验论历来负有异质学的使命。人们认识实在的经验是通过它与某个他人的相遇。”(第170页)退一步讲,即使德里达主张的“解放”运动成功了,他仍然不会满意,他还在等下一次乃至下下次“解放”运动的发生。这种无限的“解放”运动究竟能是什么?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口号和毫无限期的等待,只能是对一个永不在场的在场的永久呼唤。对此,德里达本人也是直言不讳。他说:“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幽灵似乎是延宕的精神,是一种赎罪的诺言或打算。这种延异是什么?是一切或什么都不是。”(第191-192页)
总之,德里达走向马克思,不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为了借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完善解构主义,使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而始终未得到系统表达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展开。因为解构主义最得心应手的工作,就是做文本游戏,在文本的穿梭中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值得他利用的东西。)事实上,德里达对马克思的文本早就有所关注,并持某种暧昧态度。1971年,德里达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我的工作中(一个有着自身领域和框架的有限定的工作,它只有在一个被高度决定了的历史的、政治的、理论的等等环境下才是可能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文本及概念性之间的结合不能是‘直接所与’的。要相信这一点,就必须抹去这些领域的特殊性并且限定它们的‘有效’变化。……虽然在该领域中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一个决定性的阐释还未完成”。(见包亚明主编,第107页)但为什么德里达当时没有进入马克思的文本并对其精神进行系统论述呢?这个答案只是等到《马克思的幽灵》发表后才算找到。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曾说:“人们追逐是为了驱赶,人们追捕、着手搜索某人是为了让他逃走,但是人们让他逃走、让他离开、驱赶他是为了再一次追逐他,搜捕他。”(第196页)根据他的“追逐——驱赶、驱赶——追逐”的逻辑,当时他未做这一工作,是因为他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因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方社会还有一定的影响。时过境迁,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已慢慢滑向边缘,当人们都在驱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就要突然站出来为马克思辩护。德里达解构的一贯策略就是: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情况下突然说话,而说最终是为了什么都不说。《马克思的幽灵》抓住的至多只是马克思的“幽灵”,丢失的却是马克思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