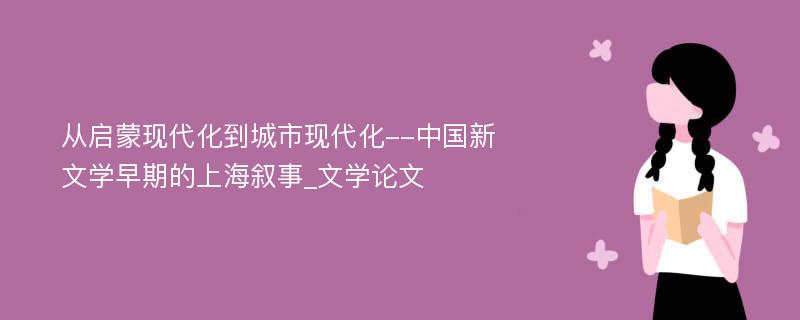
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新文学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4-0023-06
从晚清到五四,是一个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的过程。由于五四进化主义学说与观念的建立,进化论分别以宇宙观与工具论的方式进入文学视野,并逐步转向工具论的实用理性,初步诞生世界主义中心/边缘基本模式,并出现多元现代性向启蒙现代性的过渡。在地域上,则由口岸城市转向北京新文化中心[1],文学中的城市现代性有所减弱。
在五四新文学主导的启蒙表意系统中,新文学的基本形态属于知识者文学范畴。从题材来说,大致分为农民题材与知识分子题材。知识者思想状态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对立构成此期文学的大致框架,也就是说,启蒙的先驱知识分子与旧中国麻木庸众的冲突构成了文学主脉。晚清以城市现代性为“进步”的表意体系遭到压制,而被置换为以知识分子启蒙现代性为“进步”的表意系统,城市与乡村间的形态区别大都被漠视,城市之间的形态区别则更是见不到了。
比如,在鲁迅仅有的数篇城市题材中,城市与乡村在文化形态上并无太多区别。《头发的故事》指出,虽然民国已经建立,但北京市民并没有国民自觉,依旧不过是奴隶而已,与农民无异。作品中的N先生激愤地认为:
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深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尔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在这儿,鲁迅虽然以北京城市见闻为背景,但这个背景并不表现出特定的城市形态,却与保守、闭塞的乡村无异。另外,《示众》中北京人看杀头的场面与《伤逝》中的会馆胡同与机关,也与乡村并无二致,反而与小说中的乡村世界同构。对于上海,虽然作家们以资本文化去看待,但也仍然与新文化启蒙思想构成对立。如陈独秀所说:“什么觉悟,爱国,利群,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2] (P589)或许这可以算做是五四时期的城市想象,城市被赋予了乡村反启蒙的意义。
五四时期文学中,对感受现代文明的表述,从晚清民初时代的上海转向域外。特别是创造社的大部分人,大都在青少年时代负笈东渡,他们比先辈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彼邦现代文明的强烈刺激。在他们笔下,对日本城市文明的羡慕代替了晚清文人对上海的热情。比如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日出》中轮船、烟筒、摩托车的城市文明,显然不是故国能够给予他的。郑伯奇曾指出,早期创造社具有“移民文学倾向”,意思便是说在文明与愚昧对立的大框架中,创造社所采用的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比较角度,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上海与内地之间的对比。对于上海,他们也普遍采用了一种否定性的认知。郭沫若曾在诗中说:“游闲的尸/淫嚣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郭沫若遂感到“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哟”!于是,在创造社作家早期作品中,几乎都出现一个相似的情节模式,即无法忍受在东洋所受屈辱而不忘故土,回国后又无法忍受中国城市特别是上海之肮脏而返回日本,以致知识者漂流于日本城市与上海之间成为主要的情节构架。在郭沫若《月蚀》、《阳春别》、《漂流三部曲》中,作者把爱牟在上海的生活归之于“失败的一页”,因为“上海的烦嚣不利于他的著述生涯”。上海,或者“看不见一株青草,听不见一句鸟声,生下地来便和自然绝了缘,把天真的性灵斫丧”(《圣者》);或者如同坟场,像爱牟感到的“他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他好像埋没在坟墓一样”(《漂流三部曲》)。
最明显的当属陶晶孙。他十岁随父赴日,在日本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在整个大正年间都居留于日本,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远超出其他作家。日本文化对于他来说,不仅是文化认同,还是对各种日本生活细节的接受,因而觉得祖国“百事都不惯”。《到上海去谋事》批评上海的人情淡薄。主人公“想来想去觉得在此地没有我立脚的余地了,这百鬼夜行的上海毕竟不是我可以住的地方,我想立即辞职,马上回日本去研究”。同样的选择也见于郭沫若。爱牟在上海生计无着时,愤然道:“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我们是在国外太久了。”陈翔鹤将上海定性为一个美国式青年的人生方式:满口的商业英语,“经日除食、眠、经营、谋利、娶妻生子,过着本能生活而外完全不知其他”(《不安宁的灵魂》)。
在五四知识文学中,漂泊主题已经成为固定模式。比如成仿吾、郭沫若的人物在东京、上海之间漂泊,郁达夫的人物在上海、东京、北京、安庆、杭州之间漂泊,周全平的人物在上海与沈阳之间漂泊,林如稷、陈翔鹤的人物在上海与北京之间漂泊。在这种模式中,上海仅仅是一个旅行空间,除了与东京在文化上有差别外,与国内其他城市并无区别。林如稷《将过去》中的主人公若水,到北京去是一次失望,而到上海,也觉得在热闹之中的“凄凉冷淡”:“荒岛似的上海与沙漠似的北京有什么区别?”石评梅则将上海径直看做沙漠:“上海地方繁华嚣乱,简直一片闹声的沙漠罢了!……我半分的留恋都没有,对于这闹声的沙漠。”(《一瞥中的上海》)
综上所述,晚清基于城市现代性的城市叙述至五四时代被替换为启蒙现代性之下的新/旧文化的对立模式后,上海现代性想象的传统暂时终止。这一传统的恢复,应该是在20年代末普罗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开端期。
20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新文学发生巨大动荡。简言之,其背景已由五四时期的启蒙革命转向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的社会革命。“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为这时期的中心意识,五四新文学中对知识者个体意义、价值的思考转向对国家、社会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比如,从20年代有关人生观问题的大论战,到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便是这种转向的例证。其背景是30年代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城市日益明显的资本主义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整体变迁,城市开始再次成为国家生活主体。经过10数年的发展,至1930年,上海全市人口已达314万,1933年又增至340万,按国外观察家的话来说,上海达到它由来已久的命运的顶点。作家们也开始以不同形式高度地介入上海城市生活。随着首都南迁,文化中心也从北京转移至上海,以至于30年代接近百分之七十的作家都寓居上海。作家观察社会生活的视角,也与启蒙时代城乡浑然一体构成旧文化环境不同,被置换为城乡的高度对立。所以,在抗战爆发之前,纯粹的乡村社会基本上没有大规模进入作家视野。比如由茅盾、郑振铎向全国征集合编的《中国的一日》文集中,绝大多数是记录城市人特别是上海人的生活的。城市文学已开始占据中心地位。以这一时期三大文学流派——左翼、海派与京派而言,其中两支都是上海城市的产物,并且由于对上海的不同理解,导致其文学中不同的上海图景呈现。
先说左翼。严家炎先生曾谈到普罗与左翼文学的核心问题。他说:“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形势,要求新文学从第一个十年‘混合型的革命文学’(李初梨语,指五四时代的启蒙文学——引者),向前推进到正面倡导‘普罗塔列亚文学’的新阶段。”[3] 也就是说,普罗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基础在于对中国国家革命的认识。30年代初爆发的对中国国家性质大讨论说明了这一时代的中心兴奋点,而城市,特别是上海,在中国国家革命中的地位,便成为多数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上海,如何发动国家革命,成为左翼人士进行想象的绝大空间。
熊月之认为,在对上海城市的认知描述中,30年代前后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上海形象开始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五四、五卅运动之后,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这一形象益发凸现。这大大不同于清末民初国人从“文明”与“堕落”角度对上海的认知。清末民初时期,不管是立足于现代意义上“未来”想象的“维新”题材,还是政治、科幻小说中的国家想象,都基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角度。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的殖民特征被广泛地认知。诚如有的学者所说:“上海在刺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 (P473)除了由沈从文等人发起的京派、海派之争外,另一场较大的对于上海特性的讨论,是由当时的《新中华》杂志发起的。1934年《新中华》杂志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发起了征文,寓居上海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的名流如茅盾、郁达夫、章乃器、王造时、孙本文、李石岑、林语堂、沈志远等纷纷来应征,其中的79篇文章被辑为一书,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文章多半都从国家立场出发,认定上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中心,并大量使用“吸血”、“压榨”、“剥削阶级”、“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畸形”等政治与经济词汇。由此看来,关于国家民族与阶级对立的学说,开始引入上海知识界。这是二三十年代左翼人士表现上海的时代背景。
左翼对上海的认识,当然来源于晚清以来的现代性想象。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这种现代性具有了反对殖民主义与反抗资本主义的双重色彩。由于基于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劳资结构、阶级对立被横向移植为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构建,因此,民族立场又常常被置换为阶级立场,最终成为以城市现代性表述民族国家诉求的混合体。左联成立之后,左翼作家开始抛弃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表现个性主义的传统,在创作题材上,依照1931年11月左联执委通过的决议,开始“注意中国现实社会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左联执委甚至还硬性规定了作家必须表现的五种题材:即“反帝国主义的”、“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抓取苏维埃运动”、“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杀人放火”、“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与变化”。这几乎是国家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全景。在创作方法上,苏联“拉普”于1930年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开始为左翼理论界引进。冯雪峰译介的法捷耶夫《创作方法论》指出:辩证法对社会的把握就是“社会不是个人,而是团体”,“不是一个人,而是阶级”[5]。于是,基于知识者思想存在而产生的城市经验,被替代为阶级对立的城市概念,阶级斗争与产业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构成左翼的城市知识。
其实,早在20年代中期,左翼人士对上海的理解已经开始变化,上海已被指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斗争的集合体。在郭沫若集《前茅》中,阶级论观点代替了早期诗集《女神》、《星空》中对上海的泛化指摘,类似“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一类诗句不再有了,而是接近工人队伍的一种“进入上海”的过程:“我赤着脚,蓬着头,叉着我的两手/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傲慢地行走/赴工的男女工人分外和我相亲。”也由此,上海的图景在劳资对立冲突上展开:“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面的是劳动人的血汗与生命!/血惨的生命呀,血惨的生命,/在富儿的汽车轮下……滚,滚,滚……/兄弟们哟,我相信:/就在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上海的清晨》)郭沫若对上海的空间想象发生于静安寺路,这一想象的依据在于这些地区曾发生的罢工浪潮。而30年代殷夫对上海空间的想象则更具说服力,“五卅呦,立起来,在南京路上走”(《血字》),直接将空间对应于“五卅”意义。由此,从静安寺路到黄浦江口这一段马路,不再是现代中国走向西方文明的时间性想象,而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完成革命的空间意义。上海虽然“腐烂”、“颓败”、“有如恶梦”、“万蛆攒动”,但同时也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母胎”(殷夫《上海礼赞》)。
左翼反对在普遍的现代性意义上建立上海的合法性,首先是在“飞地”意识中建立的口岸城市对于传统中国的“非正统”观念,即上海的异己性,“非中国化”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个巨大障碍。有人曾指出左翼电影《马路天使》与《十字街头》所采用的“传达知性观念”的街景蒙太奇手法:“摄影机角度或是极端偏左,或是极端偏右,使观众产生一种巨大的水泥建筑行将崩塌的感觉。”[6] 因此,它必须在“反抗上海”这一线索中建立上海的现代性意义。左翼的“上海”继承了此前人们对于上海的各种想象,如道德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上海——社会主义思想上的。
在茅盾《虹》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梅有一条对于上海的认识线索,从中我们可以探知,左翼怎样在新的城市空间里形成对上海的认识。初入上海,梅女士对他的引路人——一个革命者——梁刚夫说:“上海当然是文明的都市,但是太市侩气,你又说是文化的中心。不错,大报馆、大书坊,还有无数的大学都在这里,但这些就是文化吗?一百个不相信!这些还不是代表了大洋钱、小角子,拜金主义就是上海的文化。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有点市侩气……不错,上海人所崇拜的就是利。”显然,这与五四时期创造社等人对都市的看法有着共同之处。梅女士目睹了各式各样的上海面貌:这里既有市侩味的都市气,也有浑身国粹味的旧文人、旧式词赋与旧小说、逊清掌故,既有醒狮派国家主义的运动,也有不新不旧的畸形婚姻,更有徐自强式的虽曰革命、其实堕入腐烂生活方式中的革命者。而她却最终认定了一个“上海”,即她所谓“真正的上海”。她对友人徐绮君说:“你没有看见真正的上海的血液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
“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7] (P437)在左翼的空间想象中,大略由以下一些典型的图景构成:杨树浦、闸北、工厂、亭子间、灶披间、监狱、沪北贫民窟、外滩、港口等等。借助这一空间,左翼文学要完成一幅关于国家革命的图景。正如同蒋光慈《短裤党》对上海的判断:“整个的上海完全陷入反动的潮流里,黑暗势力的铁蹄踏得居民如在地狱中过生活,简直难以呼吸。”蒋光慈要以上海三次工人起义为题,以达成这样的雄心:“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从普罗文学到左翼文学,大都进行类似的阶级斗争叙述,如龚冰庐、冯乃超的《阿珍》,左明的《夜之颤动》,楼适夷的《活路》及田汉的《年夜饭》、《梅雨》、《姊妹》、《顾正红之死》、《月光曲》等。一方面,上海的城市生活被置于雇佣劳动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导之下,人物的身份大都为制度所限定,如“包身工”、“包饭作”、“买身工”等。人物命定既然与经济制度相关,因此,城市个体的遭际往往上升为制度问题。以田汉《火之跳舞》为例。田汉偶见刊有浦东大火的报道,此事纯属肇事者性格原因所致,但田汉却深究下去:“工人阿二因失业不名一文,其妻疑有外遇,岂非因他不拿钱回来?阿二不拿钱是失业的结果,无从得钱。再一问阿二为何失业,这问题就与整个社会问题相结合了。”[9] (P2)因此,这一幕性格悲剧,被最终写成了工人因失业与资方收租人之间冲突的社会悲剧,倒与个人性格无关了。在这里,作品的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汉以社会制度为主体的想象方式,也就是说,与阶级、制度无关的社会生活不可能获得左翼叙述上海的合法性。某些作品也只是在这一层面有局限突破,而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一范式,如丁玲的《奔》、魏金枝的《奶妈》等。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国家革命被左翼文学认定为必须带有集团政党性质。殷夫的诗歌经常写到工人运动程序化内容,如《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议决》所写的委员会组织、会议表决等等。其使用的第一人称“我们”是典型的公共主体,表明了左翼文学在国家政治公共空间的存在特性。
在左翼的视野中,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构成上海表述的两个基石,两者都具有世界主义背景。前者是将上海等城市的经济、政治纳入到全球性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背景之下,结论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上海的边缘性,于是,大量表现上海经济破产的作品纷纷出现,并以《子夜》为代表,表明了在中国进入世界后对国家殖民性的思考。后者则最终导向有关民族国家的革命叙述。在这一线索下,晚清民初的民族主义叙述与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叙述,转换为阶级立场,即以无产阶级的国内斗争完成民族国家。这一思维显然也具有当时全球性的无产阶级国家运动背景,例如德国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朝鲜的“高丽无产阶级艺术同盟”与日本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等都有此倾向。
左翼的写作模式在30年代成为一种时尚,对其他各种形态的文学都有影响。早期海派中也有从经济、政治角度对中国国家公共性的写作文本。新感觉派的穆时英曾计划创作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三一》(又名《中国进行》)。该书并未面世,但从其卷首引子《上海的狐步舞》中可以看出“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类路子。赵家璧曾回忆说,穆时英受到帕索斯《美国三部曲》的影响,“准备按多斯·帕索斯的写法写中国”,把时代背景、时代中心人物、作者自身经历和小说故事的叙述,融合在一起写个独特的长篇”[9]。其友人曾谈到他的写作计划:“他雄心勃勃地想描绘一幅1931年中国的横断面:军阀混战、农村破产、水灾、匪患,在都市里,经济萧条、灯红酒绿、失业、抢劫。”[10]《良友》杂志还为其刊登广告,说“写一九三一年大水灾和九一八前夕中国农村的破落,城市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几乎可以说是《子夜》的翻版。“大水灾”也好,“九一八”也好,都是中国国家问题的标志,而“民族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更是《子夜》式的内容。当然,这并非说海派有浓重的国家叙述之倾向,而是说,即使如早期海派这样力图抹去国家内容的派别,也存有以经济、政治主导性表达国家意义的情况。
不过,左翼文学所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唯物史观,即从经济入手,发现社会现象的经济动因与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体结构,以此全面阐释中国城市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的新动向。而无保留地接受马克思建立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析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往往导致在对上海城市的表现上,无可避免地产生以欧洲理论将中国格式化的情形,这种情形反而容易导致对上海城市的资本主义理解,造成城市现代性中心的问题。比如,工业经济以及相应的社会组织(如商会、工会)对城市的主导,城市经济、政治对乡村中国的主导,城市人属性中的经济性对于伦理性的主导,城市阶级关系对多元社会关系的主导,城市现代性对于乡村社会的摧毁等等。即以经济角度来说,其表现形式大多为“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经济形式,而产业工人的斗争也被认为是一种完全集团化的组织活动。无疑,这反而导致对上海已经资本主义化与高度现代性的中心性想象,相应的,上海这座中国城市的非现代性与不发达状态反而被忽略。究其原委,在于左翼的上海叙事是一种非个人、非经验的叙述,不仅以国家叙述代替上海叙述,也以经济的政治中心性叙述代替个人的经验的多元性叙述。
在这里,以经济政治为主导,从而判定城市资本、政权权力关系的“国家性”思维可能是一个妨碍。为了清晰地制造一个现代国家的城市文本,必然要将上海本有的混沌状态格式化为一元主体。有意思的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有一部小说,书名即叫《上海》,其中以1925年的五卅反日、反英运动为中心事件。横光也要突出上海城市的现代性,并认为它主要体现为“东洋对欧洲的最初战斗”。但同时,他没有忘掉上海作为东方城市的地方性,想描写的“只是一个布满尘埃的不可思议的东方城市”。这部小说被认为对上海的定位有三个向度,即“殖民地城市”、“革命城市”,“贫民窟城市”。“甲谷代表了殖民地资本主义的代理人,阿彬代表了都市风俗的阴暗面,宫子代表了都市上层的风俗,高重代表了日本资本主义,芳秋兰代表了工人运动和革命势力,山口代表了东洋的颓废和亚洲主义者,白俄妓女奥尔加代表了流亡者和娼妓中的世界主义者”,因此,《上海》“把上海这个城市的全体当作了主人公”,并“发现了资本主义和大众这两者真正的关系”[11] (P109-110),而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意义上的上海。所以,横光利一“也对广为人知的上海的场所加以想象,一边把无名的里弄编织进去,充分表现了当时上海的复杂和深不可测”[12] (P200)。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出了其与茅盾等人的区别。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许多作家都有游历上海的经历。一开始也有基于上海的西方想象,如岸田吟香、谷崎润一郎等。但是到了20世纪初,上海中西混杂的一面开始成为他们对亚洲性思考的来源,如芥川龙之介、井上红梅、村松梢风、金子光晴、吉行幸助以及横光利一等。虽然他们对上海“不正宗的西洋”的看法不免日本人心态,但却规避了单纯的现代性视野,其经常使用的“魔都”一词,带着对上海新旧莫名复杂状态的地方知识色彩。
至20世纪30年代,自晚清开始的另一种上海城市现代性,即物质与消费现代性前所未有地凸现。美国学者白鲁恂曾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13] 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都市,港口货运量占中国4/5,吞吐量达到40000万吨,外贸总额达到10亿美元。作为金融中心,上海集中了世界40多家银行、170多家保险公司,占西方在华金融投资的79.2%。至1936年,总行设在上海的西方洋行有771家,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的40%,产值占全国一半。其中,上海民族机器工业投资占全国35.3%,产值占全国一半以上。1936年,上海钢铁及其制品输出占全国的78.6%,机器及其零件输出占全国的80.2%[14]。
从城市风貌来说,至30年代,上海城市面貌大致完成。外滩一带建筑的欧化风格尤其突出。从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外滩建筑先后经过晚期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折衷主义等建筑风格,至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进入早期现代派与现代派风格时期,比如外滩的沙逊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百老汇大厦和法国航空公司等。外滩之外,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即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与大新公司相继建成,其风格从折衷主义过渡到早期现代派风格。跑马厅附近的四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储蓄会大楼、国际饭店与大光明戏院业已是现代主义风格。24层的国际饭店在当时与此后数十年间,其高度都居远东首位。而整个法租界,则已建成欧式商业住宅区。自霞飞路迤西迤南广阔区域,由于移植了巴黎拉丁式的风格,不仅引发了欧洲人的“乡愁”,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沉浸在异国生活情致之中。欧洲人的休闲娱乐也开始构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高大建筑、咖啡馆、西式马路、影剧院、跑马场、回力球场、舞厅、公园等,“一面展现了异国风情,一面也在新建的娱乐场所中呈现了想象力”[15] (P281),同时也造就了上海一群有着高度西方素养的文人在消费生活方面现代性想象的空间,并通过众多的杂志、小报以及文学作品将这一异域的空间想象延展开来。
首先是上海消费与文化生活的欧洲情调,造就了一批生活欧化的文人,而这恰恰是30年代海派产生的生活基础。创造社后期的张资平在开设乐群书店期间,曾开了一间咖啡馆。到1929年,创造社后期的小伙计周全平从关外到上海,在南市区西门中华路开办西门书店与咖啡馆,并仿效北四川路上的“上海咖王非”,取名“西门咖王非”,常常聚集一批文艺界人士,其生活方式已经相当欧化。在南京东路的新雅茶室三楼东厅,经常聚集着像李青崖、叶秋原、邵洵美、刘呐鸥、张资平、叶灵凤、杜衡、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不仅在此地闲话,而且构思写作[16] (P121)。当时海派文人经常光顾的咖啡店一类的消闲场所还有沙利文、联邦咖啡馆和霞飞路。据徐迟回忆,下午四点至六点,在新雅有时竟能聚集30多位作家、艺术家[17] (P27)。“现代主义派文化必定在法国城(指法租界——引者)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18] 热衷于法国文化的曾朴与儿子曾虚白于1927年创办“真善真出版社”,效法法国沙龙,成为文学中亲法人士的聚集会所,同仁有徐霞村、张若谷、邵洵美、徐蔚南、田汉、朱应鹏等人。而据施蛰存回忆,后来成为现代派、新感觉派中坚力量的一些人物,其生活也已相当西化:“每天上午大家都耽在家里各人写文章、译书。午饭后睡一觉,三点钟到虹口游泳池去游泳,在四川路底一家日本开的店里饮冰,回家晚餐。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这就是当时一天的生活。”[19] 穆时英个人生活之摩登,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他烫头发,着笔挺的西装,经常出入于舞场或电影院,“是个摩登boy型,衣服穿得很时髦,懂得享受,烟卷、糖果、香水,举凡近代都市中的各种知识他都具备”[20]。他经常出入舞场,并追逐一位舞女,甚至最后在香港娶她为妻。
这一情形导致了文学中另一个上海的出现,即茅盾所说的“百货商店的跳舞场电影院咖啡馆的娱乐的消费上海”[21],而且以前所未有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30年代的海派特别是新感觉派将上海锁定于一个街头、跑马场、夜总会、大戏院、富家别墅、特别快车、新式跑车、游乐场的公共性消费场所,展开他们对于上海国际化、欧洲化的想象,就像张若谷坐在俄商复兴馆喝咖啡的感觉一样:“坐在此地,我又想起从前在法国巴黎的情形来了,此地有些像是香塞丽色路边个露天咖啡摊。”[22] (P17)
基于这种日常消费性的世界主义国际化风格的想象,新感觉派赋予上海以工业的、暴力的、男性的西方都市色彩。应当说,这与晚清以来将上海看做世界性经济中心的现代化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与晚清民初小说中的“维新”叙事不同的是,它建立于物质消费的现代性意义之上,并以某种乌托邦形式展开,将对上海的消费性经验转化为国际资本主义欲望与物质的冒险经历,其大量描写的性征服、竞技、烈酒、恐怖、高大建筑、异国冒险等,带上了西方人的物质经验与冒险经历,一切都在国际性消费生活的意义上符号化。同时,在国际化风格之下,往往采用鸟瞰、漫步、男女聚散、电影蒙太奇与当下的时间状态等手法,并伴有语言暴力。他们将上海生活置于一个平面化的瞬间状态,避免对上海城市历史与东方性深度内容的深究,以造成对上海与巴黎、纽约等国际性都会并无差异的理解。这便是新感觉派的上海叙述。
当然,对于海派来说,虽然它常被看做都市文学中最具现代性的流派,但其实也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矛盾体。海派中有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以现代消费的公共性想象为主导创作倾向的作家,也有40年代张爱玲、苏青这样基于中等阶级或市民阶层个体日常生活经验的创作群体。而且,新感觉派自身也并不统一。施蛰存、杜衡等人立足于乡村立场所表现出的反现代性,又与刘呐鸥、穆时英不同。施蛰存、杜衡等人触及的上海乡土特质的构成,使其作品成为30年代海派非现代性叙述的另一种文学景观。当然,这一种以个人生活经验为主的上海表述在新感觉派中并不占主流。施蛰存对于上海城市自身多元性的表述,应该说开启了另一种非想象性的文学,但由于他将这种表述仅仅以城乡对立来了结,并未触及上海城市东方性文化作为城市史逻辑的一面,更多程度上是将上海的东方性文化外化了,确切地说,是外化为非上海的文化内容了。这种缺陷到了张爱玲的手中得到了克服。张爱玲的文学图景是表述一个东西杂糅、混合、暧昧的所在,她将上海的东方性与西方性看做是一个被糅合后的奇异、混乱的状态。因此,张爱玲将乡土中国的内容化为了上海城市自身的城市史逻辑,并阐释为一种民间形式,终于完成了对上海城市的边缘性表述。张爱玲文学中的上海是非想象的,但在以国家意义与现代化逻辑为主导的上海身份认知的谱系中,张爱玲的小说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作为一个小传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王安忆、程乃珊的作品中才得到了继承。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上海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读书论文; 子夜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