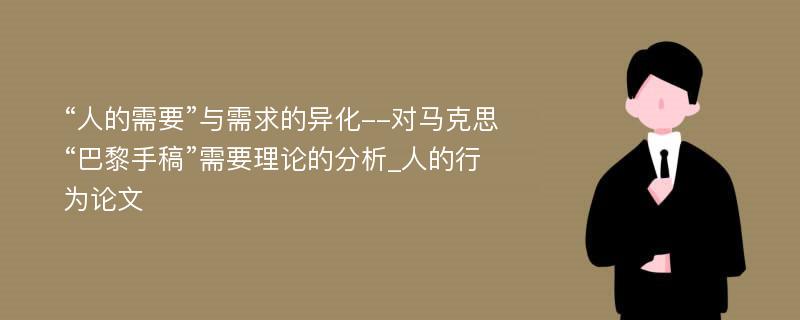
“人的需要”与需要异化——马克思《巴黎手稿》需要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巴黎论文,探析论文,手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6-0029-05
马克思深谙人的需要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就系统阐述了人的需要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异化问题。当前,中国已步入大众消费时代,社会上出现的炫耀性消费、奢靡性消费等现象表明,社会消费已经发生了异化。消费是满足需要的行为,而消费的异化根源于需要的异化。因此,克服消费异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扬弃需要的异化同样也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人的需要”,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术语。它既有别于动物的需要,也有别于人的动物性需要。所以,正确解读马克思“人的需要”概念的关键是把握住两个环节:一是在文本中找到与之对应的概念,通过比较,澄明其内涵;二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实践“应然”观,探寻其真理性的底蕴。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写到:“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行为,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P80)这里,马克思以两性关系作为切入点,立足于人的双重属性预设,运用“人的本质”与“自然的本质”、“人的行为”与“人的自然的行为”、“人的需要”与“人具有的需要”等三对概念,从本质、行为和需要这三个维度阐述了人是从“自然的本质”演进为“人的本质”,从“自然的行为”进化为“人的行为”,从“人具有的需要”提升为“人的需要”的过程。
两性关系是“自然的类关系”,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这种关系因具有自然性而与动物相同,又因具有社会文化性而与动物相异。所以,它能够表明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并把自身理解为人。这里所说的人,当然是指具有“人的本质”的人,亦即真正有别于动物的人。关于这种意义上的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先后两次作了明确界定:“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P56);“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57)。马克思还从人与动物两种不同的生命活动的比较中,对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本质、行为和需要展开阐释。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体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无疑都是属人的,是人的规定,是人的本质及其表现。把妇女当作淫欲的掳获物,是向着动物的“复归”,它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退化,表明人的本质的丧失。所以,人的本质必须建立在对自身自然本性超越的基础上。
两性关系表明了两种行为的差异。吃、喝和性行为等是人秉承的动物性行为,是“人的自然的行为”。人的行为与之有别,它是后天习得的文化和社会的行为。离开了文化和社会的浸润、洗礼与规范,人的自然行为就是动物行为,而不是人的行为。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说过:“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P55)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被文化了的人的自然行为。所以,人的行为也必须建立在超越其自然行为的基础上。
两性关系还表明了两种需要——“人具有的需要”与“人的需要”的区别。从“人的需要”看,“人具有的需要”指与生俱有的自然需要,如吃、喝和性行为等,是人所具有的动物性需要或人作为动物的需要;从“人具有的需要”看,“人的需要”则指人所特有的、标志着与动物相区别的需要,即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文化中生成的需要,如关爱、尊重、自由、发展个性、自我实现以及被文化濡化的人的各种自然需要。显而易见,马克思使用这一对概念,旨在说明,人的需要是从人的自然需要发展而来的,是对其动物性需要的改造和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从“人具有的需要”走向“人的需要”,是人的需要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命就是活动,故而活动的特性就是生命体的本质。这种本质的内在表现是生命体的需求,外在表现则是行为。所以,“人的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决定着“人的行为”,是“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逻辑中介。
什么是“人的需要”呢?凭借“人具有的需要”这个概念,采取用对立面规定自身的辩证方法,就有可靠的根据揭示出马克思“人的需要”的基本内涵。首先,它生成于后天,是人的实践活动因而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的与生俱有的需要,是先天的,是物种遗传的东西,它们肯定的只是“肉体的主体”,因而属于“人具有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是生存性的需要。所以,“人的需要”必须超越生存需要,也就是说,应以人的发展性需要为基本内容。
其次,它由人的本质所派生,且符合人的本性。“人的需要”的本体论根据,是人的应然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有与这种本质相一致的需要,才真正符合人的本性。
再者,它有助于发展人的本质,增进人的本质力量,巩固人的实践主体地位。人的本质发展,就是应然本质不断实然化的过程。由应然本质决定并体现其要求的“人的需要”,其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人的本质发展,必然增进人的主体能力,必然巩固人的主体地位。
“人的需要”是否就是“现实的人”的需要,正是这个问题引发了争议。“现实的人”因其是现实的,故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其需要是不断发生变化并趋向于“人的需要”的过程。把“人的需要”简单等同于“现实的人”的需要,这等于把应然等同于实然,把理想等同于现实,把生成性等同于既成性。“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P90)因此,“人的需要”是“现实的人”的应然性需要,是其实然需要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人的应然需要并不是理性的自由创造物。应然需要的根据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当人们通过实践使最初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2](P79)。这幅人的需要和实践的互动图式,清楚地说明了应然需要是如何根植于人类的实践,又是如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应然需要也并非是软弱无力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人类一般劳动性质时,提出了人的活动的目的律思想,明确肯定了应然需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支配地位和主导作用。他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P202)目的作为应然的典型存在形式,本身就是实践的构成要素。马克思把人类实践看作是受目的控制的过程,将目的律确立为实践活动的规律,这就赋予了应然需要以“必定如此”的特性。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在导致劳动异化的同时,必然导致需要的异化,使“人具有的需要”走向“人的需要”的历史进程发生逆转。依据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有关论述,需要的异化或异化需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需要的粗陋化,即人的需要萎缩、退化,处在维系肉体存在的最低水平上,趋近于动物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当作劳动的动物,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P15)。资本家只考虑工人维持劳动所必需的需求,不考虑“劳动以外的需要”,也就是说,“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他的需求”[1](P14)。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1](P123)。
(二)需要的物化,即人的物质需要成为需要的全部。马克思说,私有制使人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P85)人的需要被异化了的单纯物的需要所代替,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经济动物。“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1](P120),因为它的生产目的是实现物的增值,而不是着眼于人的发展。
(三)需要的工具化,即人的需要被用来作为谋利的手段和支配他人的力量。一种新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与在私有制范围内,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前者确证和充实人的本质力量,后者使人陷入一种新的依赖中,因为新的需要成了一种利己的手段和支配他人的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P120)。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种新的需要,每一种满足这种需要的新产品,都是掠夺的力量。产品的扩大屈从于非人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这种欲望制造了“需要的精致化”或“富人的讲究的需要”[1](P126)。工业充当了“宦官”角色,它想方设法激起人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人的每一个弱点,“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1](P121),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正像工业利用需要的讲究来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来进行投机。”[1][P12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1](P126)
异化了的需要,因其粗陋化、物化和工具化,不仅丧失了属“人”的性质,而且也丧失了维持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功能,成为敌视人、否定人的力量。粗陋化的需要,标志着劳动者的需要直接下降到了动物的水平。这种需要及其满足,肯定的是人作为劳动动物的存在,但不是人的存在。换句话说,这种需要不是源于人的本质,而是人的肉体机能,它迫使劳动者像非洲草原上的动物一样,在“饥饿规律”的支配下整日为肉体生存而奔波。因此,在只有粗陋需要的工人身上,“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P55)。工人的需要的粗陋化,回答了“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问题[1](P122)。
需要的物化,将人的需要囿于物质层面上,把人们追求物质需求满足的相对性,变成了绝对性,并且把物质需要从生存和发展变成了炫耀和奢侈,使其成为人们穷尽毕生精力也永远不可能满足的“黑洞”,其结果必然是将物质需求变成人的唯一需求。诚然,人有物质需要,而且人的物质需要也有别于动物。但是,当人的物质需要脱离了人的其他需要,甚至取代了人的其他需要而成为唯一需要时,人的物质需要就成了动物的物质需要。其区别仅在于前者精细,后者粗糙。
需要的工具化,意味着对需要的满足,不再以需要者本身为目的,而是以利己为目标。能够带来利润的需要,就想方设法满足它。一句话,需要的合理性、价值性甚至包括合法性在内,统统让位于利润。
异化需要的直接根源是异化劳动。劳动产品的异化,意味着“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1](P52)。“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1](P53)对于“肉体的主体”,除了粗陋的动物式的需要之外,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需要。劳动活动的异化,使工人在劳动中“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丧失了对劳动的需要,把劳动当成了“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1](P55)。这种谋生式的劳动必然把人们的需要束缚在物的层面上。人的本质异化,在消解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特性的同时,扼杀了“人的需要”。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必然将他人的需要变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变成支配他人的力量。
进一步思考发现,异化并不是人类劳动固有的属性,而是在劳动发展过程中生成出来的。社会分工使原始共同体发生了分裂,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使个(私)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带来了奴隶制,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零散的奴隶制成为社会的基本制度。随着分工的发展,产生了个人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出了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它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其他一切阶级的工具。分工的发展,还促使产品交换经历了从个别、偶然到大量和经常的发展过程。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后,就已经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者追求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它使人类的生产目的发生了历史性的颠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占了绝对统治地位。显而易见,劳动异化所需的两大基本条件,随着分工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完全成熟了。
必须指出,异化劳动和异化需要,与商品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巴黎手稿》中,被马克思作为分析出发点的“当前的经济事实”,不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发达的商品经济。“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P40-41)马克思曾明确地向商品经济提出了人学质疑:“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1](P14)他在《巴黎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均表明,把私有财产关系和商品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蕴涵着把由分工产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看成是异化劳动,从而也是异化需要之根源的思想。
人的发展是从动物界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因此,扬弃需要的异化,这是人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异化需要的扬弃,意味着以丰富的需要取代粗陋的需要,消除需要的物化现象,将人的需要提升到精神和自我实现的层面,并且使得他人的需要不再成为手段,而是成为目的。
以丰富的需要取代粗陋的需要,这是扬弃异化需要的起始阶段。“需要的精致化”与“需要的野蛮化”,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提到的两种异化现象,它们是背弃丰富的需要的两种极端形式。前者与富有者相联系,以占有超出个人生存与发展正当需求所需的物质资料为基础,肆意挥霍物质财富,其外在表现就是奢靡性消费。后者与贫穷者相联系,以丧失必要的生存资料为前提,缺乏最低的生活保障,其外在表现是必要消费需要的萎缩。“需要的精致化”和“需要的野蛮化”都使人的物质需要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丰富的需要,是真正的人对物质资料的需要,它将物质资料的需要视为实现人的精神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手段,从而将实现高层次需要作为选择物质需要之质与量的标准。显然,这种需要区别于粗陋的需要,因为高层次需要的实现,必须以丰富的物质需要作为基础;同时它也区别于“讲究的需要”,对于高层次需要的实现而言,奢侈的物质需要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将人的需要提升到精神和自我实现的层面,是扬弃异化需要的关键环节。需要是一种关系,而且任何一种需要都是对对象的占有。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分析私有制的“愚蠢”和“片面”时指出,私有制把这种占有只理解为对物的拥有——或作为资本,或直接享用。这是人的需要的“绝对的贫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1](P90)自我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是人的需要摆脱物化需要的根本标志。
将满足他人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目的,这是扬弃异化需要的最高阶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的人类已经结束了把劳动当作谋生手段的历史,进入了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真正的生产”阶段[1](P58)。对这时的生产者而言,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产品,“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1](P82)。简言之,他在满足别人的需要过程中,也满足了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
扬弃异化需要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私有制必然导致需要的两极化,使大多人的需要粗陋化,所以,废除私有制是扬弃异化需要的必要前提。商品经济使人们的生产目的由享用使用价值变为追求交换价值,极大地提升了物的价值,激发了人们强烈的物质占有欲,客观上阻断了人的需要从物质到精神和自我实现的上升过程。因此,废除商品经济,对于扬弃异化需要也是绝对必须的。
私有制和商品经济都与谋生劳动相联系,是人类劳动及其分工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1](P174)谋生劳动以维持肉体的生存作为目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作为目标,是一种在肉体需要强制下进行的利己的劳动。谋生劳动的利己特性,决定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所有权,决定了彼此在相互交换劳动产品中必须恪守等价原则。异化劳动把谋生劳动的这种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劳动者丧失了对其产品的所有权,而资本家获得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在满足乐生需要的劳动中,产品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物的所有权和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都失去了实际意义。所以,实现人类劳动从谋生劳动向乐生劳动的转变,才能彻底扬弃异化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时,人类才有可能使其劳动超越谋生的水平,进而成为乐生的需要。问题在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脱离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在人类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上,亦有其“积极本质”,它们以“恶”的方式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随着这种能力和作用的不断丧失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当代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种分配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格局,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引发了需求异化的现象。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弱势群体在需要上趋于粗陋化;“炫耀性”消费和“奢靡性”消费标志着人们需要的物化程度不断加深;连续发生的食品重大安全事故也说明,需要工具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利”。
需要的异化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相悖。社会主义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宗旨,倘若以发展生产力为借口来默许人的需要异化,无形中也就会消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消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本质规定性。
需要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既是消费的,又是生产的;既是恒定的,又是变化的。因此,扬弃需要的异化,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几方面形成合力,才能有效遏制不断加剧的异化趋势。对于个人而言要加强价值引导和道德约束,摒弃不合理、不健康的需要,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对企业来说,必须树立责任意识,摒弃唯利是图的经营观念,承担起培养“人的需要”的社会责任。社会机制和政府功能的作用是正确引领人的需要,积极创造社会发展条件,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当务之急,一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倡导正确的需要价值观;二是通过法律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从生产的角度遏制奢靡性等病态需求;三是努力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施好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制度,消灭贫困人口,从根源上杜绝需要的粗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