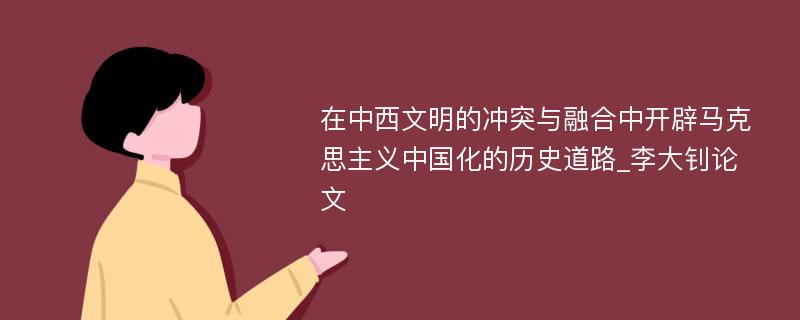
在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西论文,开辟论文,冲突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6-0059-07
从某种意义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扬弃传统文化也是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忽视这一点会使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发展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估价不足。然而, 由此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或者说,传统文化是否注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拖回到历史的阴影中从而把它“封建化”或“儒化”?笔者试图通过对“五四”前后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考察解答这个疑团,并就教于学术界。
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中,李大钊强调的“根本解决”任务和“阶级竞争”手段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性具有强烈否定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绝对排斥的一面。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阶级差别,中国文化主张“调和持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注: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第25、94页。)。西方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历史本身就是抵制共产主义的力量,因为共产主义观念与中国人的财产意识、个人主义和家族观念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特征水火不相容(注:〔美〕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2~23页。)
。他们都是从绝对排斥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最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自身性质,通过穿上传统文化的外衣才走向了成功?还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本性?一般性结论似乎是:中国的文化走向只能在固守或变相复归传统与“全盘西化”之间作出抉择。
人类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若失去自身的文化传统,将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更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文化走在其他民族的前面。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他预言: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吸取西方文明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他们一定能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一生机的成长,一定能产生一种糅合中西文明之长的辉煌业绩。(注:罗素:《中国的问题》,《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
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35页。)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文化同一性维系着古老帝国。外来文化的第一次渗入发生在两汉之际的佛学东来,它一开始便受到唯心主义和有神论者的青睐。魏晋时代盛行的玄学,就是通过所谓“格义”之学,来沟通它与佛学的原理。南北朝至隋唐,佛学大盛,产生了若干著名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华严宗和禅宗,是我国传统唯心主义流派的思想同印度佛教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中国化了的佛学思辨结构,成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理论渊源之一。从形式到内容,佛学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都采取了比较温合的方式,即以渐进、多层的渗透,最终以“中国化”为结果,而且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并未对中国文化的同一性造成破坏。(注:汤一介:《从印度佛教的传入看当今中国发展的若干问题》,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第40页。)
西方“船坚炮利”的直接轰击,使中国在文化上失去了融合的主动性,也危及了固有的同一性。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明显带有以下两方面特征:第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扩张和侵略(注:〔苏〕H.C.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
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68页。)。在这种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化视其他一切民族文化为“落后”与“劣等”,按照“优胜劣汰”法则,一切“落后”文化当被同化并纳入按西方人意志划定的世界“统一”与“进步”的序列中去。第二,虽然基督教文化在本质上讲求和平与仁爱,但由于其经典将世界分为“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两者之间水火不容,因此对“异教世界”的征服就具有了“神圣”性质。基督教文化强烈的侵略性与强制性,对西方的海外扩张具有重要支配作用。(注:克里斯托费·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四川人民出
版社,1989年,第163~172页。)19世纪末来华的美籍传教士明思薄曾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仅是政治上的支配,也是商业、制造业、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上的支配。(注:顾长声:《传教土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第113页。)中国文化面临两难的发展困境:不可能再像同化佛教那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消融西方文化;而中国文化的落伍与中国旧制度的陈腐是同一的,必须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中国文化才可以再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形势下引发的一次大调整,它把我国近代以来渐进的文化批判,引向了空前广泛而自觉的社会文化革新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企望通过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的文化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铺平道路。然而,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差异,使前者面临着更加复杂、艰难的历史环境。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思想界发生深刻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会议的结局,粉碎了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他们顺理成章地吸取对西方文化具有强烈批判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远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东西文化冲突”或“东方落后,西方先进”这类笼统提法所能概括,它不过是世界范围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阵地上的展开和反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意义,既包含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和文化特质,也透射出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先辈们的历史经验教训。从对西学的感性认识开始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上都未能很好解决西学与中国社会改造的关系。就此而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才真正切准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而且也在文化本性上真正利用了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经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具有不同的特征。与俄国相比较,其基本属于欧洲,与欧洲文化具有同源、同构性。从社会性质上看,虽然其经济落后,但基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没有沦为殖民地。所以,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显然比“中国化”更容易解决。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要复杂、艰巨得多,“它是中国面对外力压迫,内部努力挣扎求生的心路历程”(注:徐中约:《现代中国的崛起》,台北虹桥出版社,1971年,第14页。)。因此,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时,既 要关注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本性,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在近、现代所面临的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冲突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创造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个扬弃中西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历史过程。
二
1840年后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入侵,带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变迁。伴随着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连串历史事变而逐渐输入的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尖锐挑战的态势。经受检验首先败下阵来的是儒学一统天下的封建文化。如果说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学在文化价值上还有积极因素和一定的人民性,那么,它在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者手中就成了蔑视人民、仇恨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工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性,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复辟派那里得到了最充分表现。袁世凯提倡祭天祭孔,强令全国恢复“尊孔读经”,宣布以“孔教”为“国教”。另外,鸦片战争以后,伴随中国走向近代的苦难历程,出现了“中体西用,道器常变”的复杂争论,就其主线而盲,主要由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孙家鼐等直到张之洞,逐步自觉地建构起“中体西用”的思想范式。而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除了严复、谭嗣同等少数人有明确批判“中体西用”的言论外,大多数亦曾附和此论。康有为主张:“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粱启超也表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当时,“中体西用”说,“举国以为至言”。辛亥革命后,“中体西用”思潮日趋没落,但它仍以折衷调和论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所以,文化领域的革命任务以中西文化冲突的方式凸显出来,正如民国初年著名记者远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
“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毫不妥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擎起文化革命的旗帜。1915年9月, 《青年杂志》创刊,陈独秀开宗明义论证东西文明势不两立,提出中国文明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的主张。他认为,在中国文明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情形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75页。)。陈独秀列举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反动统治者利用儒学作为复辟封建帝制的舆论工具。儒学的精华是礼教,这“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6页。)。它是中国封建伦理政治之根本。如果“照孔圣人的伦理学说、政治学说,都非立君不可;所以袁世凯要做皇帝之先,便提倡尊孔”(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16页。)。第二,儒学中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道德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3页。)。由此观之,儒家学说中,“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69页。)。
陈独秀对儒家纲常礼教学说的批判,不仅配合了当时反对复辟帝制的政治军事运动,而且掀起了以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二千年来儒学独尊的局面。陈独秀对儒学的批判是客观的,他一再表示,批评儒学不是反对孔子本人,也不是全盘否定儒学,“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7页。),“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2页。)“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11页。)不过陈独秀未能正确解答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一定或一概不适用于现代的问题,因而忽略了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实际存在的延续性,留下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根苗。他认为,文化不分国家、民族,不分“中外古今”,所以“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59页。)。陈独秀认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迁〕就的。”(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0页。)“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86页。)“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0页。)
陈独秀等人所主张的文化革命论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而与此分庭抗礼的文化调和论则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杜亚泉1916年发表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和1917年发表的《战后文明之调和》,打出了“文化调和论”的旗帜。他认为,中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性质之异主要在于:西方是动的社会,中国是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尽管他认为中西文明各有流弊,只能取长补短,不能取而代之,但他的最后结论却是西方动的文明弊害更大,因此,“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西洋文明可以输入,但必须靠中国固有文明的“统整”,以“纳入吾国文明之中。”(注: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他认为,如果中国固有文明“今后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统整世界之文明,则非特吾人之自身得以救济,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此。”(注: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第4号。)由此出发,他把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视为“国是之丧失”,“精神界之破产”,“人心之迷乱”。而章土钊则提出“新旧杂糅”说,试图把文化调和论与社会进化说相结合。他认为新、旧事物不能截然“折疆分界”。社会进化的过程“乃是移行的而非超越的”,“既曰移行,则今日占新面一分,蜕旧面亦只一分”,因此任何“乍占乍蜕”的阶段都处在“新旧杂糅”的状态中。而“新旧杂糅”就是“调和”,“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社会无日不在进化中”,也就是社会“无日不在调和中”。他主张:“一面开新,必当一面复旧”,“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 “国粹不灭,西化亦成。”(注:章士钊:《新时代之新青年》, 《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他由此得出结论:“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注:章士钊:《新思潮与调和》,《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尽管章士钊在方法上抓住了时代发展的连续性这一关键之点,从而高出杜亚泉一筹,但在总体和本质上,他们都不承认西方近代文明比中国文化优越,认为中国当时的首要任务不是变革,而是守旧,因而也就不能超越“中体西用”论的藩篱。所以,他们触到了中西文化融合的重大课题,却没有也不可能正确解决它。
三
“五四”之前,西学在同中国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显露了“只能打上几个回合”的软弱性。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因而“五四”时期的“古今中西”之争就突出地表现为重新估定中西文化价值的“东西文化”论战,先进知识分子在这场论战中把目光转向了另一种新文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以什么样的文化基础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在这里,时代性与民族性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由此而论中西文化,只强调冲突而排斥融合,就会夸大文化的时代性而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只强调融合而排斥冲突,就会夸大文化的民族性而堕入“中体西用”或国粹主义的泥潭。值得注意的是,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的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没有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在文化发展中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这一关键之点上,他们基本上采取了辩证综合的立场,这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李大钊于1918年7月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首先谈到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进而他将人类文明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他认为东西文明的差异是地理环境所致:“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与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与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他从政治、宗教、个人心理与行为、家庭等方面详细探讨了东西文明根本差异的具体表现,但他反对在人类文明上挟持种族偏见,而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他认为东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有调和之日,也可能一方战胜另一方,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他的基本看法是:“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两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所谓本身之觉醒者,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从形式上看,李大钊对杜亚泉关于东西文明的特征为“静的”与“动的”之说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并且也主张东西文明之间的“调和”,然而他们关于两种文明之命运的最终结论则截然相反。李大钊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具体表现为违背宇宙进化法则的厌世人生观、无视个性的权威与势力、严重的等级观念以及惰性深重、专制主义盛行等八大症状。所以,“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反之, “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2页。)由此,李大钊明确指出:“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注:《李大钊文集》(上),第440页。)
李大钊并没有将西方文明的长处和中国文明的短处绝对化,从而拒绝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他认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尽管中华民族在近代处于落后挨打之境,但李大钊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者,其事非他,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愚惟希望为亚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而已。”(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71页。)李大钊逐步由民族性的差异立论,进到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乃是社会发展的迟速不同所产生的时代性差异,因而推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李大钊期望有“第三新文明”的崛起来挽救东西文明所濒临的绝境。他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俄罗斯文明,认为它“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善舍俄罗斯人莫属”(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他得出结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这也正是李大钊主张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注:《李大钊文集》(上),第562页。),主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首开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钊所持的对中西文化辩证综合的立场,既不同于“西化派”与“国粹派”,也有别于杜亚泉、章士钊等人的折衷“调和论”;较之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更富有弹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他批判传统文化替新文化开辟道路,引进西方文化为新文化奠定基础,“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其中一个“变”字,清晰地反映出李大钊中西文化观的核心:即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必须是创造,而不是简单移植或模仿,而这一问题有赖于调和东西文明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实,李大钊的文化调和观念本身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这可以从他反对“伪调和”和“庸俗调和论”(人为调和新旧)中看出来,他认为“时代”是“最有力的调和者”(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而李大钊所言之的“调和”绝不是和稀泥,它的本质是调适,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调适到近代西方文化之高度(注:萧超然:《论五四前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6期。),这与章士钊的新旧杂糅其表、斥新护旧其里的调和论具有本质区别。李大钊形成的“根本解决”思想与对“阶级竞争”手段的肯定,就有这样的文化意识在起作用。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上,李大钊的思想中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中国文化中的社会理想框架来体会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始终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视为一种“天下为公”、“没有阶级竞争”的“互助、博爱的理想”。此外,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上,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精神,在他提出的“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中,的确充盈着创造的光彩。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化”相提并论,后者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上的对西方文化全盘贬斥的文化心态。
四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早期文化观对中西文化采取辩证综合的思想方法非常突出,这对其日后提出并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毛泽东善于汲取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智慧,1914年在《讲堂录》中就写下“天下万事,万事不穹”的话。在继承康有为、梁启超“主变”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9页。)的崭新命题。康梁“主变”,意在“保国、保种、保教”的渐进改良,而毛泽东则坚信:变,不仅是量的变化,而且是质的革命。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1页。)毛泽东正是从“变”的角度去观察和评估中西文化的。
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中,毛泽东坚决反对“中体西用”观点,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他承认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落伍,并主张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找到可以改造中国文化的出路。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非有大力不易摧毁廓清”。毛泽东对中西文化做了比较: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家族主义基础之上,以三纲五常为其根本特征,养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因而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国家主义基础之上,以注重个性的实现和完善为其根本特征,养成了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因而提倡民主与科学精神。他深感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彻底改造,并号召“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5页。)他对中国文化在吸收西方文化中进行改造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为光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4页。)
毛泽东反对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主张融合中西文化的优点,同时改造中西文化的缺点。他坦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他反对盲目的“出国热”,主张在国内脚踏实地研究国情的基础之上,融会中西文化,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认为“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他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个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由此出发,他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页。)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力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强调研究国情和改造现实,是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特色。这样的文化意识,使他保持了思想上的求实性和开放性,从而逐步形成了步子踏实,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突出特点,这就为毛泽东从中西文化的融合及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两个方面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后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以及对待文化应采取“古今中外”、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方针,正是这种对中西文化辩证综合认识的逻辑发展。
中共一大以后,毛泽东着手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其执笔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蔡元培称赞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注: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新教育》第5卷
第1期。)。 自修大学的学员,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兼学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思想及心理学等课程。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指出:“‘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这绝非一个偶然的枝节问题,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做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象征。因为‘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
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后来的许多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他后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就。”(注:〔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对“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有过很精辟的总结性论述:“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而现时的这两种文化“都有危害的病状”,唯有马克思主义,“开辟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由于这种根本分歧的存在,后来在知识分子中就出现了文化运动朝不同路向的分化:“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文化”。而后者,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历史源头。
今天,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全球化,其物质主义影响了整个人类,美国“9·1l”事件后,在国际政治中形成的单一霸权现象也背离了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想。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特别提到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在这个大背景下强调从“精神的高度”把握“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对唤醒我们的“文化自觉”有重要意义。追求“文化自觉”,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说到底,是一个“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素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研究“五四”前后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历史,将为我们提升“文化自觉”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正确把握先进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走向的重大历史课题。
标签:李大钊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明的冲突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