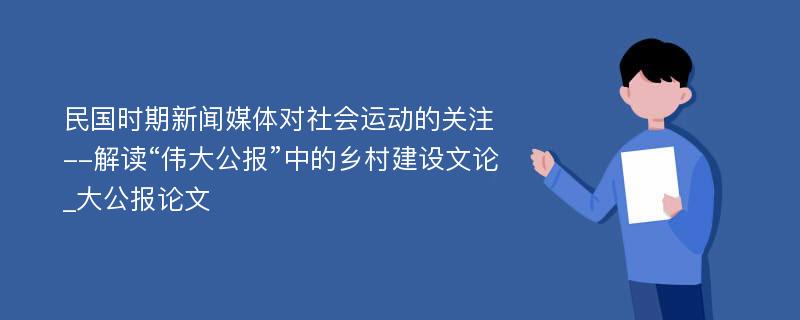
民国时期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关注——对《大公报》乡村建设文论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大公报论文,新闻媒体论文,乡村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9)06-126-04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代以来,如何使农业、农民和农村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对中国乡村现代化道路的一次尝试和探索。运动期间,主张乡村建设的各界人士通过种种媒体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和方案,从多个层面探索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成为了我们今天解读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好窗口。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从萌芽逐渐走向兴盛,报刊杂志等媒体率先透露出乡村建设思想传布社会的信息,反映出社会对乡村现代化问题的普遍关注。当时,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文章在许多著名媒体上大量涌现,人们对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分析、评价纷纷见诸报端,“乡村建设”成为时人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一时期,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章既有乡村建设参与者对自己工作的检查与总结,又有局外人对乡村建设事业的观感与评说。除专门性的学术刊物积极鼓吹乡村运动外,知名度较高的一些综合性报纸杂志,如《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也都曾陆续登载过不少有关乡村改造的文章。报刊媒体敏锐的分析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时期乡村建设思想的传播力度和研究深度,从而也助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繁荣之势,本文即选择民国时期著名报刊之一——《大公报》作为解读乡村建设运动的窗口。《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营报纸。尤其是1926年后的“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社训,努力提倡民主政治,是民国历史上影响十分广泛的媒体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拯救农村危机,乡村建设思想已经非常活跃,并融入当时政治文化的主流,《大公报》以深切的人本关怀精神,对乡村问题做了大量报道,既反映了时人关注的社会焦点,也在无形中为乡村建设推波助澜。相较同期其他报刊,《大公报》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笔论述,形成了自己的报道特色。
一、关注乡村民生
《大公报》认为“中国农村破产,日趋严重,有识之士,亟待复兴农村,以图挽救,故近年乡村建设运动勃兴。”[1]从1930年起,《大公报》开始派记者到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发表具有纪实风格的调查通讯。同时还充分发挥其通信员队伍的优势,发表了大量的旅行通信和写生,并在此基础上以通信的内容为论据,展开评论,这些在当时的报界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报道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问题的进一步关注。1935年,《大公报》发表《中国农民离村及其救济》一文,指出“近年来都市过肥,农村消瘦的病症已普现于我国各地”,文中引用日本人田中直夫所著《中国农民离村问题》分析农民离村的原因,主要有:帝国主义压迫、历年政治变乱、地主富豪的榨取、农业资金缺乏、天灾频仍及买办阶级的操纵等,对中国农村破产环境下的农民离村现象做了深度报道,指出“这样的离村是不得已的、农村崩溃时期的离村。”[2]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大公报》组织了“陕赈周”与“救灾日”两次赈款募集活动,在大公报人看来,赈灾也是推进乡村建设的手段之一,在救济民众生命,给予其物质帮助的时候,教以他们独立谋生的知识与技能,实际是在培植乡村建设的基础,从另一角度讲,乡村建设运动无疑可以被认为是“广义的赈灾”[3]。从《大公报》两次的赈灾活动中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农民命运和农村社会的深切关注。
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大公报》虽不是直接倡导者,但其对于乡村建设事业的关注却是一贯的,对乡村建设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公报人认为:“热心于乡村研究、从事于乡村建设者,……虽是因为环境不同,出发点不同,应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做出各种不同的试验,得出好些不同的成绩,但是他们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就是为乡村谋建设,为中国找出路。”[4]因此,《大公报》不惜版面刊登有关乡村建设的通讯、评论及专家文章。1930年1月8日至12日,《大公报》连续刊登了《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并配发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1933年3月1日至4月19日间,《大公报》每周1期连载了《山东农村观感记——记邹平之行》;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大公报》连载了《定县参观记》;为配合在邹平召开的第一次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大公报》于1933年7月13日发表了社评《乡村建设协进会之成立》,并以连载的方式向读者推出了《乡村的建设——全国乡运状况之一斑》的长篇介绍文章;同年《大公报》刊载有关专家文章,如傅葆琛的《乡村社会人才问题的研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什么》、方显廷的《中国乡村工业与乡村建设》、方方土的《定县平教工作之我见》、董时进的《棉麦借款与农村复兴》等。对于身体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的可贵精神,《大公报》更是予以赞赏并颂扬:“无论什么人,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实际上能帮助农民,使他们得点好处,便是为他们造福;总比唱高调,讲废话,成天鼓吹怎样救济农民,怎样发展农村,却是从来没有到过农村去的人强得多。我们对于抛弃都市生活,深入农村的人们,应当脱帽鞠躬致敬,因为他们是实践者,是力行者,是奋斗者,是肯牺牲服务者。”[5]《大公报》对农民生活的关注,对乡村建设的关注,反映了它对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
二、主张政府参与
在对民生问题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大公报》文论有一个鲜明的主张,即认为应该从政治上着手解决乡村问题,政府应该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政府救济农村,不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从政治立场上讲,都是应该的和必须的;农村问题,根本与行政改良,税制改革,息息相通,如果政府不努力将全国的行政税制彻底刷新,使国家一切税收不再都转嫁到农民身上,根本谈不上救济农村。《大公报》作为舆论工具,曾积极致力于推动当时国民党政府进行的经济建设,并始终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须政府有办法,国民有决心,国难必有解除之日。[6]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大公报》的现代化观中,最关键的要素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廉洁有能政府。”[7]认为国民政府对于乡村建设与改造没有给以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是《大公报》一个大胆的观点,也是其社训“不私”的体现。“中国的政治,虐农特甚,今日则更不可问。政府政策完全与农民利益违背,且直接威胁其生存。”[8]《大公报》以锐利的眼光认识到: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如不注意他们的疾苦,农村破产,中国将急趋灭亡之途。所以,“若夫中国农村破坏,与其谓为经济的关系,毋宁应认政治之原因。”[9]“建设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政治责任者不愿建设或不许建设时,怕是谁也不好建设。”“如果政治责任者谋建设而又愿建设时,以政治力量去推动农村建设即是比较快当的事情。”[10]1933年乡村建设协进会成立时,《大公报》文章认为:“发展乡村运动之总前提,在减除不当之捐税,安定人们之生活。此而不能,则任何理论之乡村运动,皆为徒劳。虽千百热心学者梁漱溟,亦无济于事也。”[11]1934年8月28日《大公报》的《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一文中,更是直接呼吁救济农民“需要政治力量”,文章认为政府救济农村责无旁贷,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也不应该放弃利用政治的希望,“一个社会的改造,尤其是一种大规模的有意识的改造,总须是由上而下的。……现在的农村破产程度已至极点,救济农村实系迫不容缓的急务。但救农岂能不借助政治力量!提高关税,抵制海外农品倾销,需要政治力量;减少棉麦借款,需要政治力量;停止内战,剿除匪患,便利货运,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均需要政治力量;即防止水患,积谷,控制粮价,开渠,修堤,也无不需要政治力量。”[12]
“政府参与”是《大公报》改善乡村社会的主张,具体办法就是“改革县制”:“采取措施,改革县制,提高县长地位,并奖励地方人才,使知识分子回县或乡工作。政府对县级工作人员确定生活保障制度,筹津贴金,并严肃法纪,注重实际成绩。”[13]《大公报》这种舆论正好迎合了国民政府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的“在全国实行县政改革”决议。事实上,从1932年底开始,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趋向,那就是更多的“民间”乡村建设者开始考虑和政府合作搞乡村建设事业的问题。在河北定县的晏阳初提出“政教合一”的主张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乡村建设多年“民间团体”的实验证明,乡村建设事业要有政府的参与才能取得最大限度的成果。《大公报》不仅以深切的人本关怀精神关注乡村民生,而且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新趋向。主张把乡村建设与政治改造有机联系在一起,《大公报》的这种认识和舆论无疑是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三、刊行《乡村建设副刊》
相较上世纪同期的报刊,《大公报》中对乡村建设最具特色的报道当属其在30年代开辟的《乡村建设副刊》。1934年1月4日,《大公报》秉承其创办丰富多彩副刊的一贯特点,与中国乡村建设学会合作,开办了《乡村建设副刊》。该副刊起初每月两期,由燕京大学杨开道主编。一年后,从第25期开始,改为周刊,由平教总会的瞿菊农主编。该副刊一共编辑刊出70期,刊登各地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报告及宣传和讨论乡村建设的理论文章约一百篇左右,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乡村自治、经济、金融、教育、合作、卫生、赈济等诸多方面。副刊中,除乡建各实验区工作情况报告外,占篇幅最多的是有关以下三类主题的文章,即:运动概况、乡村合作事业、乡村建设措施。这些文论既反映了时代主题,也为乡村建设运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首先是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概况介绍。从《乡村建设副刊》中可以看出,早在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就有学者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历史和参加团体的类别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总结研究。徐雍舜在《中国农村运动之总检讨》对乡村建设做了理论上的分析:他首先回顾了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历史:从翟城村治到山西村治、从平教会定县实验和梁漱溟邹平实验到全国大范围的乡村建设活动,指出农村运动已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作者把参加的乡建的团体分为政治机关、教育团体、宗教团体、银行团体、社会团体及地方自治团体。接着又对各种农村运动的特性作出了分析,指出:以政治为主体的乡建,就是要以农民为施政的主要对象,为的是实现全民政治,山西的村治即可做到这一点,全国的自治方案以及国民党的农民工作都可属这一类;以教育为主体的乡建是一切的问题都从教育入手,以平教会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为代表,它们不限于识字教育,而是广义上的教育;邹平的乡建则属于以政教合一为基本理论,以学校为中心实行政治的功用,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村公所,视学校为教育中心,同时也是政治中心;还有一类乡建就是从经济生活入手,以改进技术、增加生产为努力的目标,湖南棉业实验场、各处的合作运动、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等都以改良经济为依归。[14]菊农在《乡村建设之历史的任务》中认为乡村建设有其自然的次序,可分为三阶段:乡村社会服务时期、农民自动建设时期、全国计划建设时期。文章强调了乡村建设的“服务精神”和引发农民自动建设力量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民族的新生命,必须有稳固的组织基础和自动建设的力量才能实现。[15]
《大公报》以政治、教育、经济等为主体来划分民国乡村建设不同派别和特性,抓住了乡村建设各派的不同特征,这种类分办法比较科学,依然为当今学者所沿用。对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次序和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说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作了很好的描述和预见,文章发表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同时,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次是关于合作事业的介绍。据笔者统计,《乡村建设副刊》近100篇文章中有22篇是关于合作运动的,从中可见时人对合作事业的重视。章元善认为“将来以经济的组织——合作社为中心发展村治,这种力量是不可忽视的。”[16]他进一步认为合作运动是人民的运动,应由感觉需要合作的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合作社的呼号是自助互助,农人们与其求天拜地,还不如努力自救。“合作运动得到人们的信仰,全在合作运功的本质,实在能够抓住时代需要的重心。”政府提倡合作有必要,政府应为农民设法,给予此前得不着的种种便利,尤其是金钱的通融。但是,“过分的提倡,拿合作当一种救济事业去办,亦是同样的于合作无益。”[17]这种对合作社事业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对乡村建设运动中合作事业的顺利开展是非常有益的。还有人认为“合作”代表一种民主精神,“合作社虽不能直接领导民众,从事政治活动,但合作社内部组织及经营之程序,颇合近代民主政治之精神,……合作社无形中可以培植民主势力,实现民主政治。”“合作社为乡村建设中心机关最为合适”。[18]副刊除介绍上述国内的合作思想外,也对丹麦、印度、日本等国的先进经验给予介绍,这些探讨促进了当时中国合作事业的成熟,成为《大公报》有关乡村建设报道的重要主题。
最后是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乡村建设副刊》提倡要在消极的控制环境和积极的改进生产两方面并进。既要打破农村建设的障碍,如国际资本的压迫和国内苛政的劫掠;也要从改善农民生计入手,切实做一些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有效工作,如兴修水利设施,改良生产方式、推广先进农技等,而最重要是要解决农村金融危机,保证农民的借贷和合作组织的资金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上,以稳固乡村建设工作的基础。如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卜凯就呼吁“农村金融机关的设立,已成为事实上的需要”,“应该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对于农民的金融需要加以扶住,并从法律上给以保障”[19]。《乡村建设副刊》也反映了乡村建设运动中对教育的一贯重视,认为“如何才能引发农民自动地力量呢,惟一地答案就是教育”[20]。副刊主张教育是造成建设力量的原动力,既要以扫除文盲和提高农民文化程序为目标,训练农民在生计上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培养他们的经济意识和控制经济环境的能力;也要将乡村建设的意义和精神灌输给他们,努力改选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用教育的力量,将青年农民组织起来进行训练,使他们成为乡村建设事业的中坚,被认为是推动乡村建设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副刊所反映的改革农村金融、提高农村教育这两大问题,不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当代中国乡村建设事业中须要花大力气解决好的问题。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乡村建设副刊》发行的时间是1934-1936年,此时正值乡村建设运动高潮时期,所以副刊反映了当时乡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较为成熟的思想。副刊的开设为从事与关心乡村建设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获取信息与交流经验的渠道,正如《发刊辞》所期望的那样:“有这个双周刊,同人随便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彼此交换意见,交换经验。”同时,副刊的开设也拓宽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宣传面,人们不再仅仅知道晏阳初、梁漱溟和定县、邹平,而是了解到更多的热心于乡村研究、从事于乡村建设的人和事,扩大了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的影响。1936年1月1日,时任副刊主编的瞿菊农在《今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对未来的乡村建设作了展望,指出人们应该对乡村建设注意几个问题,对乡村建设的使命要有深刻的认识,最后也实事求是地讲:“现在各地的乡村工作,虽说布满全国,其实大家都知道,实际成就并不多”,“乡村工作不是旦夕可以成功的,需要时间、需要不断努力”。可见,乡村建设事业的任重道远已经为时人所认识。时至今日,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乡村现代化道路仍然是摆在当代乡村建设者面前的艰巨任务。
总之,从《大公报》对乡村建设运动的高度关注和频繁报道中可以看到,上世纪20年代起,以新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力,社会各界已经开始积极探求中国乡村问题的出路并设计乡村现代化的方案。正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对乡村问题深层次的探讨、对建设方案多角度的设计以及向全社会热烈的呼吁,才为乡村建设事业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舆论平台,“乡村建设”才最终得以从少数人区域性的思想主张扩展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要求,汇合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并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大公报》曾有这样的言论:中国经济的出路,“应以增进全国人数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经济能力为主题,须从建设全国面积百分之九十的内地农村社会去努力”,这无疑对我们今天以解决“三农问题”为重心的新乡村建设事业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