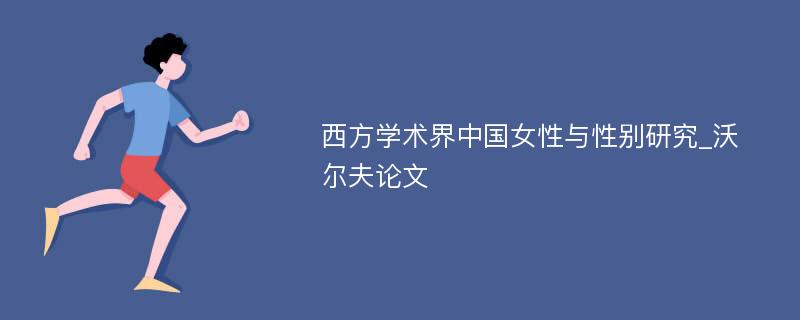
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中国妇女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C913.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07) 06-0097-13
在西方的中国学中,中国妇女与性别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次领域。这方面的著述层出不穷,而相关的会议也经常召开。自上世纪60年代始,一些西方学者就开始将中国妇女作为研究题目,进行跨地域或跨学科的探索。而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也相继成为运动。近二三十年来,西方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在理论与方法论上均有突破,而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的领域也相对受益。尽管多数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近现代中国妇女,但也有一些人探讨古代妇女。各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方法及资料上对中国妇女及性别制度进行调查分析,取长补短,或进行争论,或形成共识,因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妇女及她们所生活时代的了解。本文将从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发展、分析范畴、交叉学科研究、重要问题及观点等方面进行介绍,帮助国内学者更好地了解西方研究中国妇女及性别关系的动向及思维①。
一、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
西方人对中国妇女的关注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到中国的传教士与民族学家记载下他们的所见所闻,阐述儒家经典中的妇道,或者撰写著名妇女的传记。从西方人的优越立场出发,他们把中国妇女描绘成牺牲品或可怜虫。传教士们由于被士绅家庭所排斥,不得不与下层人民接触,而他们对中国妇女的知识也就局限于对这些贫穷家庭的了解[1]。当时的西方人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将人种判分高下,也就难免将妇女的状况看作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那些关于中国妇女悲惨境地的报告,加强了西方人有关中国文化落后的偏见,并给帝国主义的扩张提供证据。比如,缠足、娶妾,或溺婴,就被当成中国人野蛮的象征,从而旁证传教运动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另外,西方学者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其中的三从四德被看成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2]。
当大量著述将中国妇女看成是牺牲品时,也有一些东方学专家对中国上层妇女产生了兴趣。例如,沙拉·康格与凯瑟琳·卡尔曾与慈禧太后及满清贵族接触,因而留下了关于清代贵族妇女生活的记述[3,4]。还有一些传记作家翻译或描写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出色妇女,以体现西方人的猎奇心理[5]。这一趋势的代表作包括南希·斯旺的《班昭传》,以及弗劳伦斯·阿斯考夫的关于中国妇女作家和艺术家的著作[6,7]。无论是将精英妇女理想化或是将下层妇女弱势化的倾向都把妇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一种倾向强调这种文化的正面,而另一种则强调这一文化的负面。当时东西方正在接触,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及西方想了解中国的人往往通过妇女的状况来审视中国文化,从而判断取舍。妇女成了他们研究或改造中国的渠道。
这种为中国妇女作传的情况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了转变,具体体现为下层妇女或革命妇女树碑立传。伊达·普鲁特于1945出版了《汉族的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8],讲述一个山东女佣的生活经历。还有的西方作家受社会主义或进步思潮的影响,对革命妇女情有独钟,大肆描写女革命党或长征妇女[9,10,11]。他们的著述虽然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指导,但开创了中国妇女的研究领域并提供了宝贵资料。
到了70年代,中国问题专家受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将中国妇女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些学者对女性主义运动及第三世界的发展深表同情,开始深入探讨诸如劳工、父权家庭、教育及妇女参政等问题。一些治古代史的学者也关心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及妇女解放根源等问题。但这时的女性主义学者仍然摆脱不了早期传教士的影响,而把中国妇女看作是牺牲品。缠足被说成是父权压迫的象征,贞操则成了中国文化保守性的标志,而父权家庭则特别被当作是妇女的桎梏。不过,这时的女性学者更关心的是妇女受压迫的普遍现象,而非特殊现象。传教士着重批判中国传统,而研究妇女的学者则更注重分析父权制。尽管如此,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优越感使其将西方妇女看得比第三世界妇女高出一筹。她们一般认为,在特殊的中国父权制度的压迫下,妇女的苦难加深了一层。正如有些第三世界的学者所说,西方的女性主义话语(discourse)将第三世界的妇女边缘化[12]。
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在中国妇女研究上进行对话。麦日林·扬于1973年编辑了《中国的妇女:社会变化与女性主义研究》[13],而马格利特·沃尔夫与洛克森·维特克则在1975年编了《妇女在中国社会》一书。扬毫不隐讳她的政治目的。她在前言中说,“美国的妇女运动将我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到中国的解放事业。其实,妇女解放在那里并不新鲜,不过等待我们去发掘”。她的书涉及当时的妇女参政、妇女解放、妇女在台湾的地位等问题。沃尔夫的书是一本会议论文集。与扬的书不同,此书囊括古今、交叉学科,题目包括从16世纪士绅的道德说教,到20世纪女革命家的传记,再到人类学家对台湾香港妇女的研究。编辑者自称要提供妇女在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让政治与学术分家,从而进行真正的学术探讨[14]。
但是,西方学者企图利用中国妇女的研究成果建立一般的关于父权制度或妇女解放的理论。《迹象: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杂志》(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于1976所出的专刊就反映了这一现象。“文化革命”后,西方的左翼思潮衰落,中共的妇女政策又难以落实,许多非中国学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中国妇女失去兴趣。中国妇女的研究任务于是落到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学者的肩上。此后,又出现中国妇女研究是属于中国研究还是属于妇女研究的问题。一般来讲,中国妇女的研究是中国学的一个部分,它在妇女研究的领域中并无重要地位。
到了1981年,理查德·贵梭与斯坦来·约翰森合作编辑了论文集《妇女在中国:史学界的新动向》。她们批判中国妇女的非历史化现象,不满意识形态当道,主张扩大选题,将妇女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为了抵制学术界的非历史主义,该书大张旗鼓地登载历史文章。选题从六朝直到20世纪。许多文章不再讲妇女受压迫,而是强调妇女在历史上的作用。例如,帕利西来·钟( Priscilla Chung)的文章讲北宋朝廷贵妇的权利与影响;帕特立夏·易普莱(Patricia Ebrey)的文章讲南宋血缘关系中的上层妇女;而凯瑟琳·蔡(Kathryn Tsai)的文章则讲尼姑。该书反映了80年代的新动向,即妇女研究突出妇女的历史作用及反抗[15]。当时的一些学者将注意力放到皇族妇女,如皇后、公主及宫廷贵妇,强调她们的政治作用。另一些人则注重研究佛家与道家的性别观念,企图在儒家意识形态之外寻找能够给予妇女力量的思想源泉。
这时,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开始取代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学者们的注意力从历史创造者的妇女转向男女属性(identity)的历史建构与表达。斯蒂文·桑戈兰通过研究台湾的女神揭示出性别特征可以由文化象征所建构[16]。察洛特·福斯通过中医来理解中国人对两性差异的看法[17]。埃米利·马丁则研究中国男女对生死的不同看法,以此解释男女的社会性别并非与生俱来[18]。以性别分析为范畴的方法使学者的兴趣扩大到与妇女研究相关的题目。学者们开始用新方法来探讨在制度、观念及象征等方面两性的不平等关系是怎样形成的。卢比·华森与帕特立夏·易普莱于1991年编辑出版了《中国社会的婚姻与不平等》一书,检讨了婚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所反映的男女不平等关系。华森特别强调性别关系的不平等与其他各项不平等的关系,鼓励人们将性别关系放到特定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19]。
随后,第三世界研究妇女的学者批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西方中心论,引起西方学者对人种、文化与地区差异的重视。1992年由哈佛、麻省理工及威斯里学院联合召开的妇女研究会议邀请各学科人士,进行东西方对话。该会所产生的论文集《性别化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提倡将性别分析当作一般的历史分析范畴,宣称将性别分析带入中国研究将会改变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关系、制度及文化生产的理解。如果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我们可以修改许多解释中国的模式与定论。该论文集特别讨论了性别关系的建构对中国近代化的意义[20]。当然,性别分析在理论领域占上风并非意味着旧的、以妇女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消失。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发掘被忽视的历史上妇女的活动与业绩。帕特立夏·易普莱的《闺阁:宋代的婚姻与中国妇女的生活》一书就提供了了解宋代妇女生活的详细画卷。除探讨婚姻制度的发展之外,易普莱还调查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缠足习俗的形成、男女有别规范的实施及妇女一生的起落。她的研究为我们研究社会史和妇女史树立了典范[21]。下面,本文再进一步探讨不同的方法论及研究焦点。
二、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
妇女研究与性别研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妇女研究着眼于男女的不平等及父权统治。这一方法将生物上两性的区别视为天成,而探讨为什么权利的分配会在两性之间不平等。性别研究则从两性的差异着手,调查性别的社会建构。持这种方法的人一般不将男女的性别差异看成是与生俱来,而认为性别范畴是社会的与文化的。他们还认为,两性的界线是可以超越的。一些学者甚至提出“第三性”,认为有些人不男不女,独立于构成男女的综合因素之外。他们争论说,在各种文化内都存在两性之间行为和属性混淆的现象。比如同性恋和变性人,就证明性别及其属性可以改变。
这两种方法,引导学者去研究不同的课题或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舞台上的女扮男装,对性别研究的人来说是个绝好的题目,但却提不起妇女研究者的兴趣。另一个例子是对最近中国农村溺婴现象的看法。对强调父权-男女不平等的妇女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不过是重男轻女现象的反映,与性别范畴的分析无关。溺婴反映了文化观念上对妇女的歧视,这一现象与父权制下的同姓而居及中国家族制度强调父子传承的习俗有关。但是,在性别研究的学者看来,这一问题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他们注意到在一些文件中农妇如果没有生男孩就不会被称为“全人”。根据妇女有没有男孩儿而将她们分为两类,本身就是性别政治的反映。妇女由于不能为丈夫传宗接代而失去做一个正常女人的资格[22]。
概括来讲,妇女研究或父权-男女不平等的方法包含以下四点:1)通过对历史记载或不同文化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到男人不约而同地垄断了政治权力并且建立起对女人的统治;2)认为男人对女人实施有系统的统治的看法,支持了妇女研究领域的合法存在,也使妇女研究的学者可以批判男权统治,并发掘或肯定被压迫妇女的历史经历;3)这一立场具有道德倾向,谴责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不道德的;4)学者们应该歌颂妇女的反抗,并为消灭父权压迫而做出贡献。根据妇女研究学者们的定义,父权制是指年长的男性作为家长,拥有对家庭成员的最终控制权。在广泛存在两性不平等的社会里,这个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是父权-不平等的方法有一定的缺陷。这一方法忽视性别关系在文化与历史上的变化,也不质疑为何男人的经历使他们成为普遍的主题。他们的研究还容易将女性主义的立场边缘化,使女性主义研究的著作或方法得不到非女性主义学者的重视。此外,这一方法将父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从而忽视它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的环境下会经历再创造或变更形式[23]。
与妇女研究的方法相比,性别研究的方法也有它的问题。过于注重两性差异或性别制度会导致我们脱离男女关系相互作用的政治领域,也使我们看不到在许多方面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会造成男人对女人的统治。结果,女性主义的学术成果会适得其反,得不到主流学术界的承认。一些学者还批评道,一味追求两性关系的形成与变化会使性别研究的学者津津乐道于男人的经历,这正是那些敌视性别主义的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此外,性别研究领域内的一些倾向也令人担忧。一种倾向讨论与一般妇女的经历无关的题目。比如,研究以性别划分的古典诗词领域,却只谈男诗人为男读者所写的诗词。又比如,谈医学著作中的性行为的表达方式。这样的题目与能够改变妇女权利的政治斗争毫无关系。
当然,这两种方法可以取长补短,共同使用。例如,这两种方法可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引向不同的方向。不平等-父权的分析方法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会超越政权的更替,为什么新的统治者会再建父权,而改变这种父权的努力则往往难以奏效。这种方法还可以让学者把无权无势的妇女的经历写进历史。性别分析的方法则可以启发学者探讨,尽管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停的重复,但为什么对两性差异的看法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一方法还可以启发人们思考,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制度下,男女所占有的位置是会改变的。而社会等级的建构,有时与父权统治并不合拍。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受益于新的父权,而有的等级制又会与后者产生矛盾。在这方面,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别研究学者作出了榜样。他们发现,中共所追求的男女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新型的父权。这种父权对旧的儒家等级制度是一种否定,但同时又承认新的男女不平等关系[23]。
三、人类学与妇女研究
人类学与中国妇女的研究息息相关。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历史学家越来越依靠人类学的方法去分析妇女的问题;其二,人类学家对中国妇女的经历或中国的性别关系产生兴趣。当然,这两个群体的学者所受的训练不同,方法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历史学家要靠史料来讲话,而人类学家则靠着实地调查。一个注重过去,另一个则重视现在。一个倾向于研究历史的部分,作微观调查,而另一个则强调人类社区整体的观察并作出结构上的解释。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在人类学领域就出现了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倾向,这是与当时蓬勃兴起的妇女运动相联系的。1974年,米彻里·罗萨多与路易斯·拉姆费尔出版了第一本专讲妇女的论文集。此书起源于斯坦福几名研究生的读书心得,称为《妇女,文化与社会》[24]。来年,又一本宏著诞生,题为《通向妇女人类学》,由瑞纳·芮特编辑[25]。早期阶段的研究被标榜为“妇女人类学”,因为学者们将妇女写进民族学的著作中。
中国人类学似乎一直就存在于西方人类学主流之外,这是由于它与中国学相交叉而造成的。近些年来,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及社会感兴趣,但仍然对人类学领域的新理论敬而远之。结果,中国人类学在中国学之内发展,而人类学的理论对中国的研究影响有限。令人称奇的是,在中国人类学的领域中,对妇女的研究开始甚早。1968年,马格利特·沃尔夫出版了《林的房子》( The House of Lim),这使中国妇女的人类学研究领先了西方妇女人类学的研究数年。从1959年到1961年,沃尔夫与当时的丈夫,人类学家阿瑟·沃尔夫(Arthur Wolf)住在台湾一个中产阶级的农夫家里进行调查。当时,林家正面临分家,矛盾重重。沃尔夫仔细观察林家的人员关系及每日生活,特别是该家妇女的情况,用小说的形式加以描述。沃尔夫没有博士学位,因此不受学术条框的限制。她的研究技巧与写作天才使该书畅销,因而对中国人类学中的妇女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今天,该书仍是研究中国或性别人类学的必要参考书。沃尔夫的第二本书《台湾农村的妇女和家庭》,则更上一层楼,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认为中国妇女在传统家庭内无权无勇的偏见。她提出“母性家庭”(Uterine family)的概念,指出母亲可以通过与子女的感情纽带在父权家庭中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另式家庭。她可以通过儿子来影响丈夫。沃尔夫还谈到妇女的家庭地位会产生变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而婆婆的权力正是拜传统家庭结构之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妇女要维持父权家庭。沃尔夫的著作使我们注意到妇女的关系网以及非正式的影响,改变了旧的、认为妇女是牺牲品的看法[26]。
其实,早在沃尔夫之前,一些中国的人类学家如费孝通和林耀华就认为家庭与婚姻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这些社会科学家特别着眼于血缘关系的研究,以为血缘关系是构成社会的基础。他们还相信,只有了解了男女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异,才可能懂得血缘关系的结构。由于这些学者是男性,又土生土长,他们对妇女生活的描述细致入微并充满洞察力。例如,费孝通留学英国,受布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他在《乡村经济》一书中,对妇女生活作了深入与细致的观察与描述。这些描述虽然简短,但有力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现象,特别是婚姻给她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个例子是民族学家杨马丁。他在《中国乡村》一书里,对妇女的生活及她们与其他大家庭成员的关系作过全面的描写。费孝通与杨马丁比同期的欧美男性学者对中国妇女更加关注,也更加理解。费孝通将他博士论文研究的地点选在他姐姐经营缫丝厂的乡间。当时,他正从一起车祸中复原,而那起车祸使他新婚的妻子丧生。与中国妇女的第一手接触使费孝通与杨马丁一类的中国学者很自然地看到在农村中妇女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沃尔夫一代属于妇女人类学,他们不太在意分析男性与女性的含义。下一个阶段称为性别人类学。新学者们倾向于分析符号、思想、象征等因素,以解释男性与女性作为两个相对的范畴是怎样被社会所构建起来的。这一方法的代表人士是雪利·奥特纳。她的“女人对男人能够相比于自然对文化吗”一文,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解释了把妇女看作低男人一等的文化思维的逻辑。她指出,妇女的低下地位是由于她们与自然相联系,而男人掌权是由于他们与文化相联系[27]。这篇短文提出,并不是所有的思想系统都将自然与文化相对立,因此,妇女与自然的联系也不是天经地义的。她用“文化逻辑”的概念分析生物的性并使其摆脱自然主义的臆想;她把男女两性的差异归因于文化的构建;以及她利用地方的象征及符号来解释两性的范畴,都使她的文章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几年后,奥特纳又与哈利特·华特亥德共同编辑出版了《性的含义:性别与性的文化构建》一书,提出了“第三性别”( the third gender)。华特亥德讨论了印第安人的一种男扮女的群体,认为这就是“第三性别”[28]。她的文章引导人类学家注意性别和性的各种范畴,而非仅仅是男女两个范畴。此后,妇女人类学被性别人类学所取代,大量关于性别是怎样被文化因素所构建的著述相继发表。
在中国人类学领域,研究符号含义的启蒙学者当属埃米利·马丁。马丁的《中国妇女的力量与污染》一文探讨了台湾村民对妇女经血及产后排出物的污染力量的看法。她解释道,这些污物之所以被看成是危险的,是因为她们与妇女的生育能力有关,而生孩子会威胁到父权家庭的权限分配。但是,马丁并不认为妇女有意地利用她们污染的力量去反对男人,而男人也没有用这些污物来诋毁女人[29]。盖里·西门则对马丁的看法持不同观点。她争辩道,男人鼓励对女性的负面看法,是为了使妇女的低下社会地位合法化,并抑制妇女对男性为中心的群体的威胁[30]。察洛特·福斯也研究类似的题目。她的关于晚明的性别异常现象的探讨迄今仍是中国研究领域中关于第三性的最佳论述。她发现,在史书中男变女被看作是异常,而女变男则不是大问题。她还注意到,当一个人被社会定性为男人,他就有一个幅度去演绎性的角色。但是,他不能像宦官一样被人娶为妾。而宦官由于失去生殖器而不再被人们看成是男人。社会的性别在规定男女的属性方面一定程度上比生物的性别更重要。但是在晚明的性别制度中,介于男女之间的第三性似乎并无太多的空间[31]。
到了80年代末,一些人类学家开始研究感情的表达方式。在此以前,沃尔夫在《林的房子》一书中就描写了家庭的拌嘴。她在《中国的妇女与自杀》一文中力图解释失望的根源,并认为不同层次的情绪沮丧导致了台湾男女的自寻短见[32]。步沃尔夫的后尘,威廉·江考维克继续探讨在恋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爱当中的男女不同的感情。他的书和文章揭示了在不同时期围绕着恋爱与父母关爱等问题的复杂矛盾[33]。
四、身体与性
学者们关于妇女的身体与性的著述可以来自民族学、历史学、医学等领域。有的学者称描写女学生、同性恋者,或妓女等群体的文献为“焦虑文献”(anxiety literature),因为这些人常常标新立异,威胁社会上的道德规范。西方史学家们注意到,早在明清时代,医生就告诫孕妇不要乱动,以免伤了胎气。到了民国,社会评论、医学著作及小说也谈生育,但加上了近代健康性行为的内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性的科学研究成了一个新领域,但学者们注意讨论性病及其危害。新的生物学讨论,多由男性发起,加强了对妇女的偏见。当时人们认为,妇女进化程度低,没有男人聪明,她们消极、脆弱,同时又比男人对生育负更大责任。生物医学的作家们大谈胎教,告诫孕妇不要激动,不要胡思乱想,以免影响新生儿的健康。一些知识分子还把优生与民族健康相联系,要求妇女不仅要对传宗接代负责,也要对中国的兴旺发达负责[34,35]。
妓业是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的妓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发现,在 1949年以前的城市里,卖淫行业高度地分化,妓女的工作条件将她们分为三六九等。但是,妓业是民国时期近代化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题目。知识分子将妓业与社会混乱、文化落后与民族衰弱相联系,而通俗读物也将历史上对文化名妓的崇尚变作对20世纪大城市病态妓女的歧视。盖儿·和夏特在研究上海妓业时指出,由于妓业中存在不同的等级,又由于妓业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方式不同,对中国的妓业不可一概而论。其实,对妓业的看法因人而异,即使是文化精英,他们对妓女的态度也在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人将妓女看成是城市文化的体现,漂亮的名妓以及她们与男人的交往是与富足而又发达的城市形象相联系的。但到了三四十年代,妓女被描写成半殖民地社会的牺牲品与性威胁,改革家们大都将妓女看成是剥削妇女的体现与中国落后的标志[36,37]。许多叙述更多的是反映了男人的担忧而非妓女的感受。但这些著述同时又体现出对妓业的安排、规定,以及管理的企图[36,37,38]。城市指南一类的书籍代表了男人的偏见。这些书籍告诉嫖客如何与妓女交往,以便保持体面。在不稳定的城市世界里,男子汉气概对嫖客的信心十分重要。民国的警察与法院把妓业与乞讨、公共卫生、虐待家庭佣人等问题均看成是混乱因素而加以限制或取缔。妓女的街头拉客或一些人的逼良为娼被看成是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国民党的法律并没有取缔妓业,而妓女的捐税则给各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但是,限制及消灭妓业一直被看作是民族振兴的大计,也是近代中国各政府的目标。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无一不为此目标而努力[36,37]。
西方学者看到,到了90年代,妓业再次成为报刊杂志、性医学、社会学、犯罪学及通俗文学的题目。大量关于女青年受骗上当,或受高收入及刺激生活的诱惑而充当妓女的故事出现,妓业甚至成为某些农村的通常生意。国家对妓女的关押及改造成效甚微,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管理与惩罚条例,但有些只是禁止官员嫖娼。一些学者指出,妓业的发展是对政府强权的挑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对正在出现的社会空间不太限制,持容忍态度,这就从侧面上鼓励了妓业。还有一些人看到,在公众的讨论中,缺乏对妓女权利及卖淫作为一种工作的注意。近来,有的学者研究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妓女,他们看到,这些妓女模仿傣族姑娘的性感装束,以吸引汉族做生意的游客[36,39,40,41,42]。
再一个与性有关系的题目,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些研究两性关系的学者,喜欢用汉族的歧视以及他们与少数民族的对比来证明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是斯蒂文·海瑞尔。海瑞尔于1995年编辑了《中国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碰撞》一书。他在书中解释了将少数民族作为女性的性别象征问题。该书的其他作者也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的性感化、苗族的女性形象的产生以及汉族人对蒙古族马背上的男子气的迷恋[43]。此外,德儒·格莱尼与拉夫·利兴格则利用“东方学”( orientalism)的概念,分析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性别关系。据他们所言,“东方学”将西方看作是男子气十足、理性的,并且积极进取的,而将东方社会看成是女性的、神秘的,并且是消极的。当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他们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汉族人倾向于将少数民族描绘成女性味儿的、落后的和迷信的,她们需要有男子气的汉族人指导。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东方的东方学”(oriental orientalism)或“内部的东方学”( internal orientalism )他们还说,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比较,就像女人与男人的比较,或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比较。换句话说,在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形象被概念化了,以一种等级的方式被对立起来,就像在性别或政治关系中一样。西方学者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大众媒介喜欢用性感的女性来表达少数民族的形象。与现代化的汉人相比,少数民族总是代表着落后或原始[23]。还有的学者分析汉族对摩梭人的性的看法。许多汉人对摩梭人的母系社会及开放的性态度感兴趣,但同时又认为摩梭的女人脏、原始,并会勾引男人[44]。
此外,西方人还喜欢讨论同性恋。当代研究中国性的学者大多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他们在考察同性恋时一般将注意力放在男人而非女人身上。福柯在《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一书中认为,欧洲自18世纪以来,在认识论上出现偏颇,结果对同性恋抱有偏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反社会现象。布里特·汉斯则认为,中国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45]。法兰克·狄考特则不同意汉斯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同性恋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反社会的行为范畴。这一现象类似嫖娼、通奸或鸡奸等不正当的婚外性行为,会威胁婚内的合法生育。狄考特的证据主要来自从18世纪至晚清的律例。当时,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微乎其微[34]。另一个研究同性恋与法律的学者是麦素·萨莫。他给中国的同性恋增加了许多细节,认为虽然男性同性恋不被当成不正常,但它显然被看成是对父权的威胁。相比较,女同性恋则不被看作是这样的威胁[23]。还有一些人研究当代的中国同性恋,认为现在关于女同性恋的报道反映了妇女对男人虐待与忽视的回应,也是妇女在缺少男性伴侣时的性补偿方式[46]。
最后,一些西方学者对妇女的“身体文化”(body culture)也作了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男女之气常常通过体育与模特表现出来。苏珊·布朗尼认为,“身体文化”包含日常保健、卫生、锻炼、美容、时装,以及一种通过训练及显示身体所表达出来的生活方式。早在延安和江西时,身体文化就和军事与生产的目的相结合。在毛泽东与改革开放年代,女子体育减少了男女之间的差别,而运动员则要求体现单一的民族主义观念。由于妇女在体育上比男子强,她们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就占有了特殊的地位。女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被媒体说成是能吃苦,讲道德,并且勤奋。同时,一般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又将体育当成是改善自己地位的途径。体育上的成功可以使女孩成为男人喜欢追求的对象,但女孩又怕自己的皮肤晒黑,或者过度的锻炼伤害自己的生育能力[47]。与体育类似,妇女的时装模特也体现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文化。女模特在身高与体重方面要达标,她们的表演既代表西化,又反映东方的传统。从运动员和模特的自我表现,布朗尼看出了性别差异及民族主义的倾向[48,49]。
五、婚姻与家庭
西方人对中国的父权家庭及包办婚姻做过大量的研究。新的相关著述强调地方性差异,认为父权及男女差异在各地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些关系会受到其他关系的制约,也会适应革命与改革的环境而存在下来,革命与改革可以保存或重建家庭制度及性别关系。20世纪中国近代化的定义也是通过政府、知识分子、媒体关于家庭、婚姻、性、男女不同等问题的讨论而反映出来。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自由恋爱在中国的城市中盛行。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家长们还为儿女们介绍对象,但同时又听从后者的选择。改革开放后,介绍对象在城市与农村中仍然流行,而母亲在这一领域最为活跃。合作化曾改变了农村的婚姻选择,但由于农民在地域变动上的限制,血缘群体仍在婚姻双方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威廉·帕历士与马丁·怀特发现在合作化时期,聘礼要比嫁妆重要,因为妇女参加劳动,她们的价值当然就有上升[50]。在合作化时期,年轻人都要找称心如意的对象,但还是要考虑政治与经济的地位。农村妇女在找对象时要考虑户口,嫁到城里是改变现状的一个重要途径[51]。到了80年代,关于男女般配、爱情与亲密关系的题目主导了关于恋爱婚姻的讨论[52]。阎运祥发现,由于农村人进城工作及电视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年轻男女对恋爱婚姻的期望也提高了。女人要求未来的丈夫懂感情,会挣钱;而男人则要求妻子漂亮,会打扮及脾气好。在东北,爱情、亲密接触以及婚前性关系成了谈恋爱的主题[53]。萨拉·福瑞门注意到,政府要求最低结婚年龄,客观上允许年轻人互相了解,甚至婚前同居。她还看到,虽然婚前同居成为普遍现象,但社会上并不喜欢人们谈论性行为及性满足。女青年在找对象方面变得主动,她们可以决定聘礼,及婚后分家的时间[54]。但改革开放后,拥有城市户口仍然是农村人找对象的重要考虑。来自偏僻农村的男人愿意在城里上门结婚,而内地的妇女也愿意嫁到沿海地区,结果导致她们家乡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55,56]。詹姆斯·法瑞发现,在90年代的上海妇女当中,找社会地位高的丈夫的现象十分普遍。因为女工常常首先被工厂辞退,她们不得不考虑经济上的稳定,而男人则面临养妻子的压力。同时,双方也强调通过关系的介绍与感情的表达来建立恋爱关系[57]。
西方学者还注意到,改革开放带来了风俗习惯方面的变化。马里斯·吉莱特指出,90年代西方的婚纱在西安的汉回等民族中盛行,新娘子通过消费为现代化与城市主义定性。在当代中国,聘礼与嫁妆的开销全都直线上升,往往超出结婚伴侣的承受能力。而政府将这一现象看成是旧习俗的卷土重来。有的学者把聘礼与需要家庭劳动力相联系;有的认为婚礼的复杂化反映了在新时代重新建立血缘关系的必要;还有人认为结婚费用的上升,不再是财产在两家之间的转移,或是体现两家的财力与声誉,而是证明财产通过结婚迅速从父母转移到子女[55,58,59,60]。
在婚姻研究方面,西方学者往往对妇女地位的转移及她们对婚姻的态度感兴趣。许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中国的旧式婚姻使妇女脱离了从小生活的社会圈子,成为她们丈夫家的新成员。这样的转变,使她们容易受到其丈夫与婆婆的虐待。在新中国,这种地位的变化还限制了妇女发展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能力,使她们不易上升到领导岗位。卢比·华森证明,在农村,妇女在结婚后即失去她们在娘家的名字,而随夫家的姓,这样,她们即失去了完全的人格[61]。当然,婚姻习俗各地不同。赫尔·盖茨研究从明清到近代的中国婚俗,指出以家庭为中心的小生产方式导致各地区在婚姻形式上的差异。各家庭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妇的劳动价值,有时甚至将妇女商品化[62,63]。阿瑟·沃尔夫则发现在台湾北部及珠江三角洲童养媳的比例很高,这与当地的贫困化有关。他还说,在台湾倒插门的婚姻削弱了夫妻关系,导致离婚率上升。但同时这种婚姻又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当地的习俗允许男人通过婚姻的纽带来扩大影响[64]。
另外,学者们还注意妇女在婚姻方面的反抗方式。例如,玛交热·陶普勒的文章叙述了广东农村年轻妇女由于经济独立而推迟婚姻或不婚的现象。在丝业发达的地区,年轻的劳动妇女组成姐妹伙,发誓不结婚,将她们的收入给自己兄弟,或产生同性恋关系[65]。詹尼斯·斯托克也叙述了广东三角洲的推迟-转让婚姻。据她讲,上个世纪初,当地妇女婚后仍住在娘家,同时出钱帮丈夫找一个妾作为补偿[66]。从各种文献来看,妇女是不愿意离开娘家的。有的学者研究湖南的“女书”,发现年轻妇女可以组成跨村落的并且是非血缘的姐妹关系。但是,婚姻却给她们造成离开自己小圈子的痛苦[67]。女孩的姐妹情使她们对婚姻持消极或抵制的看法。埃兰·乍得在研究北方妇女时发现一种婚后两居处的妇女抵抗方式。年轻妇女在婚后来往于娘家与婆家之间,而在生第一个孩子前基本住在娘家。此后,她们仍然频繁地回娘家,甚至在她们的父母死后。这种方式说明妇女可以通过协商减少父权婚姻给她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回娘家可以使女儿得到父母的支持与关心,即使她们没有自己兄弟那么多责任[68]。
在研究婚姻法方面,西方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他们发现,中共30年代的婚姻改革,承认婚姻自由,废除买卖妻子,规定结婚年龄,及允许妇女的离婚权利。当时,这种法律的制定有利于发动年轻男女参加革命。但是,这一法律在各根据地实施起来颇有困难,男性农民与他们的母亲反对妇女的离婚权利,地方干部也不赞成这种权利。当五四时期的家庭改革方案碰到农民反对时,中共不得不向农民妥协,从而修改妇女政策[69,70] 。50年代的婚姻法进一步废除了封建与买卖婚姻,保障了个人自由恋爱与离婚的权利。这一法律反映政府要把婚姻从长辈的控制及两家交换妇女的所有权变成一种平等的个人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家强调自由婚姻实际上是要将妇女从血缘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这种将婚姻权从老一代转到新一代的做法使年轻妇女受益[53]。许多学者看到,婚姻法带来的变化深远,因而引起的反抗也强烈。一个男人和他的父母花了大钱得到一个女人,当然不愿意由于离婚而蒙受损失。她们指出,50年代的婚姻改革并不彻底。1953年新婚姻法颁布后,地方干部很快从贯彻该法的立场退缩,特别是当该法与土地改革与集体化运动发生矛盾时[69]。近来内尔·戴蒙又提出新观点。她认为,婚姻法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尽管党和国家批评农民的封建意识,农民仍然利用离婚的条文钻空子。他们并不关心妇女地位的提高或个性解放。新法使年轻的农村妇女及高干受益,后者可以利用该法去找年轻和受过教育的女性。同时,年纪大的、穷人及当兵的成了牺牲品[71]。许多学者看到,婚姻法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给妇女带来了解放。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并不是有始有终的。社会上对该法充满了抵制,特别是地方干部与婆婆不支持离婚。更有人指出,国家也非铁板一块。一些聪明的农民利用官员与政策的不同来争取离婚。法律使国家干部难以掌控,而地方利益又使婚姻法或受到执行,或受到拖延。在婚姻法的实施中,妇女个人起到了积极作用[69,70,71]。苏珊·格劳瑟争辩道,婚姻法的目的是要将私领域推向与国家的接触,而非削弱这种联系。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是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72]。
除恋爱婚姻外,西方人对中国的家庭结构及其演变也有研究。他们将旧式的中国大家庭定性为男性聚居的、男性传承的以及数代同堂的,并认为大家庭的理想一直延伸至1949年以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文人认为旧式家庭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他们说,这种家庭压抑个性,支持奴性,传袭老少男女之间的等级,要求家庭成员的效忠,以及阻碍人们关心国家的事务[72,73]。当时,知识分子提倡建立在自由恋爱及感情婚姻基础上的小家庭,认为这种家庭可以产生个人幸福并带来国家强盛。虽然人们对家庭形式的设想随时间发展有所变化,但他们讨论的核心总是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相联系,妇女的平等是家庭改革与强国保种的重要一环。民国时关于家庭的著述多半反映了城市男性知识分子的兴趣[72]。
男性改革派对家庭的设想是与家内的劳动分工密不可分的。他们把女性的家庭作用与近代化相联系。根据他们的论证,小家庭成了近代城市消费的中心、经济健康的基石以及妇女相夫教子并为国家作贡献的地方。当然,对家庭的看法也是新旧并存,居住在上海的宁波人直到40年代还提倡做家庭妇女,认为妇女的位置在家里[74]。
20世纪,小家庭成了城市家庭的主要形式。在农村,革命使贫农可以结婚,因而解决了由战争与阶级分化所造成的家庭危机。自50年代以来,集体化要求家庭作为生产与继承的单位,并保存了以男方为中心的聚居形式。虽然家长失去了一定的经济控制能力,但家庭结构的变化却十分缓慢。合作社由男性亲戚及他们的家庭所构成,重建了旧的血缘关系,因而排斥妇女。妇女总是离开自己生长的社区而嫁到外村[69,70,75]。马丁·怀特发现,近些年,男性为中心的聚居形式在城市地区有所复活。这是因为人们需要家庭纽带来解决工作、住房及照看子女等问题。其他的一些学者则看到在农村地区的生意人中大家庭又兴旺起来。在这种聚族而居的群体内,人们可以利用集体的财富与劳力[59,76,77]。
西方学者看到,分家意味着婆媳不再住在一起,媳妇可以有更多的独立性。分家虽然可给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权,但却不能改变性别上的等级。随着农村一夫一妻家庭的增长,夫妻之间的合作与亲密关系也加强了。有人注意到年轻的农村妇女生活得到了改善,因为小家庭提升了感情的交流,个人的愿望,及个性的发展。他们呼吁学者们不要过于强调家庭的经济作用,而应注重家庭中的个人意愿与夫妻关系,特别是农村中的家庭变化[53]。在城市里,当前的变化也显而易见。老年妇女担心退休金不够用及医疗费用的上涨。1980年的婚姻法要求子女赡养父母,但许多资料显示子女给父母的支持不够。过去的孝道受到新式家庭结构的挑战,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寡妇的处境不利。中共政府推行婚姻与家庭改革,因而降低了家庭的作用。新的官僚与社会体制代替了旧的血缘制度,而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则受到压抑,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传统道德沦丧的现象,即个人只对自己负责而不愿管父母[53,60,78,79]。
此外,西方学者对妇女与立法的关系也有新的见解。国民党的立法承认个人的法人地位,认为妇女是自主积极的法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决定自己的婚姻及离婚,并有财产继承权。父权制的继承方式被认为是封建残余,不再成为产权的基础。凯瑟琳·本哈特发现在城市中新法增加了妇女的离婚机会,但在法律条文与实际执法之间存在差距。离婚的判决建立在双方自愿、虐待、抛弃及通奸的基础上。该法还保护妾的权利,尽管妻子无法阻止丈夫娶妾[80]。黄宗智则认为,虽然民国的法律给了妇女新的权利,但同一法律及习俗,执法均不利于妇女的保护。如当妓女、买卖妇女及嫁寡妇,都被看作是妇女自己的决定,而不管妇女是否出于无奈或被迫。该法还规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这就使妇女无法摆脱不幸的婚姻或丈夫的控制[81]。本哈特也看到,尽管女儿有同等的遗产权,父亲仍然先将财产在儿子之间分配。国民党的法律允许妇女在婚后经营自己的财产,包括个人所有、所受礼物及嫁妆,她们还可以通过工作或副业扩大自己的财富。但是,她们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则是有限的。同时,寡妇则不能为丈夫指定财产继承人,也没有对家庭财产的监护权。她们只是继承人之一,有时与其丈夫的子女争夺财产[82]。在谈到1950年的婚姻法时,学者们指出,虽然妇女享有土地所有权,但在实际上男性家长仍然掌握着家庭财富。理论上妇女有平等的财产权,可是,当时的财产主要是房子家具之类,而妇女又多嫁到丈夫家,所以她们的兄弟也就自然地从父亲手中继承这些财产。当妇女在离婚后要求土地所有权时,她们常常遭受暴力对待[83,84]。相比较,1980年的婚姻法则强调夫妻共同拥有在结婚时所得到的财产。1985年通过的遗产法则保护女儿的遗产权,包括结了婚的女儿。学者们还认为,20世纪的婚姻本身从家庭财产的形式过渡到个人财产的形式,财富属于婚姻双方,但丈夫比妻子拥有更大的权利。1949年之后,私人的财富被社会的财富所取代,而国家拥有最大的掌控权[8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中国妇女感兴趣是从传教士、东方学家及激进派女作家开始的。在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一兴趣转化为学术研究。到了80年代,妇女研究逐渐被性别研究所取代。但是,讲述妇女生活、贡献及反抗的著述仍然层出不穷。在研究中国妇女与两性不平等关系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通力合作,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在理论、方法及资料上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女性主义学者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牺牲品形象,而还原了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他们又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探讨性、性别及两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试图找出中国妇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压迫与受歧视的根源。现在的新倾向是,西方学者开始放弃西方中心论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妇女解放理论,而注重在第三世界内部寻找构成妇女受压迫及两性不平等关系的特殊因素。由于受益于交叉学科的视角,他们的选题广泛并新颖,而对历史上的及现存的制度、政权、法律、习俗、观念、象征、符号、运动及社会关系多持批判的态度。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他们的著述为中国妇女伸张正义,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这些成果已经超越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的领域,对整个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释:
①本文着重参考了以下文献:Jinhua E.Teng,"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an' ,in the Western Academy:A Critical Review",22,11(1996):115-151;Gail Hershatter,"State of the Field: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3,4 (2004):991-1065;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Introduction:Theorizing Femininities and Masculinities",Chinese Femm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A reader,eds.Susan Brownell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标签:沃尔夫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人类学论文; 家庭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