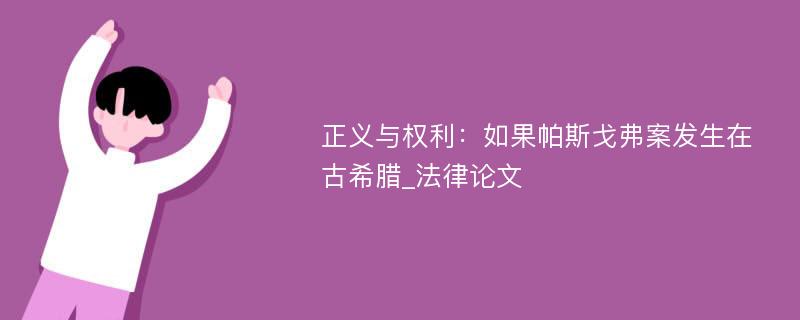
正义与权利:如果帕斯格拉芙案发生在古希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正义论文,帕斯论文,权利论文,格拉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的某一天,帕斯格拉芙(Palsgraf)太太正站在纽约长岛火车站的站台上候车。当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帮一位旅客登上一列业已开动的火车时,不小心碰掉了旅客携带的一个包裹。孰料包裹内竟是危禁的烟花爆竹,掉在铁轨上发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将据称有数英尺远的一杆秤击倒,砸在了帕斯格拉芙头上。受到伤害和惊吓之后,帕斯格拉芙患上了严重的口吃症,而那位旅客去向不明,于是,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要求民事赔偿。不幸的是,纽约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帕斯格拉芙的判决,不仅认为她无权从铁路公司获得赔偿,而且裁定她承担与铁路公司的诉讼费用。
这是阎天怀在《法律救济的界限》(《读书》2005年第9期)一文中介绍的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Palsgraf v.Long Island Railroad)一案的案情。作出如上判决的是著名的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在判决意见中,卡多佐写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正常感知的危险的界限决定应承担责任的界限(The orbit of the danger as disclosed to the eye of reasonable vigilance would be the orbit of the duty)。在此案中,以当时的情形,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包裹的掉落会潜伏着对远在站台另一端的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如果被告的工作人员存在过失的话,该过失也是指向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而不是原告。卡氏的判决为过失侵权行为的认定确立了新标准,即被告只对可预见的原告(foreseeable plaintiff)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处在被告的位置,按当时的情形,能够预见到对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这时,原告就是可预见的,被告对原告负有谨慎从事的义务(duty of care)。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被告的疏忽违反对原告的这一义务,从而造成对原告的伤害,被告才对原告承担责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对其引起的所有伤害都承担法律责任,也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获得法律救济。作者阎天怀特别强调,这不是逻辑,而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一种现实的选择。
于是,在这种不是逻辑的逻辑中,帕斯格拉芙成了“两害相权”的牺牲品。卡多佐的判决奠定了该案在美国侵权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该案的当事人帕斯格拉芙却无辜经受着口吃、眩晕、头疼和愤怒的折磨而无人过问。《纽约时报》在六十五年后的1998年6月16日仍难以释怀:可怜的帕斯格拉芙由于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地方而在美国法学院的教科书中赢得了有限的不朽名声,但她所受的伤害将被遗忘。
卡多佐的同行安德鲁斯法官不容许存在这种无人负责的悬案,他为该案所写的反对意见坚持认为,只要被告的疏忽大意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被告就应当为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责任。安德鲁斯拒绝在法律救济的适用范围上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或者说,让这条界限的划定更多地参照当下的情形、更多地关照情理相容以及司法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对接。在该案中,客观的施害方或许是无辜的,但受害方更无辜——伤害行为的施行者与承受者之间的无辜是不能划等号的,即便是让当事双方共同承担伤害的后果,也已经是对受害方的不公平了;而单以解脱无辜的施害方为考虑,却让更无辜的受害方独自承担伤害的全部后果,则是不公平的二次方,是伤害之外又加侮辱!何况,作为企业的施害方与作为个人的受害方之间还横亘着社会地位与能量的巨大差别,适当的赔偿既能稍稍平复帕斯格拉芙的无辜伤痛,又几乎无损于作为一家有实力公司的被告的利益,何以要把有着正当利益诉求的帕斯格拉芙献祭于一种要为后世立判例的个人冲动呢?
法学家沃伦·谢威(Warren A.Seavey)在一篇研究帕斯格拉芙案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卡多佐从私人感情上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心存挂念,但他并未因被告财大气粗有能力赔偿损失而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保护人。他的天平衡量的是法律正义,而不是情感公正。他的判决不是依据内心无法解释的正义感,而是考虑由判例演绎而成的原则的适用性。对此,一个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要质疑的是:脱离了情感正义的法律正义如何可能?以牺牲原告伸张性的积极权利来划定、强调被告保护性的消极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法律正义”?
何谓正义?正义意味着什么?在崇尚唯理主义和分析主义的今天,法不容情、法理与情感的对峙、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分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被认为是法律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理想的法治状态被理解为:法律挣脱社会肌理的整合性束缚,超越诸如民族性、历史性等局限,而凌空蹈虚为一种普适性的自洽自治的知识体系,在其中法学精英们以一种失重般的自由,操练概念、堆砌符码,靠无所不能的逻辑演绎力量对来自外部现实生活的法律纠纷提供唯一符合法律正义的判决。
而在以整体主义面对生活和世界的古希腊,正义首先是社会正义,或是其对象化的形式——宇宙正义,这种正义不止于实在法意义上的正义,而是高于实在法并赋予实在法以合法性的“天神所重视的天条”(《安提戈涅》语),无论人们用神法、自然法或理性法来称呼它,它在内容上就表现为一些普适性的道德法则。只有与这些普适性的道德准则相对接,只有在这一带有终极关怀意味的观照下,对司法正义的探讨才是有意义的,法律自身的发展也才能不竭于源头活水的滋养,而避免深陷炫技主义的故步自封之中。而情感正义,或曰正义感,正是连接社会正义乃至宇宙正义的必要形式,它在现代司法领域之被有意识地摒弃乃至驱逐,暴露出的是司法活动与其社会环境的制度性裂痕及其合法性的危机。
因此,在古希腊人眼中,现代社会无正义,无论社会正义抑或法律正义,有的只是权利。正义观与权利观作为对个体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秩序的排列与认知,区别在于认知角度的不同:当从社会整体角度考察权利义务划分的原则、尺度或界限时,就是正义观;当站在个体角度考察和强调这个界限的规定时,就是权利观。希腊城邦主义,作为国家与社会合一的强干预主义,其对社会正义的孜孜追求必然衍生对公民义务的强烈预期,“政治动物”的称呼就喻示了希腊公民的义务本位。伯里克利在著名的墓前演说中说:“我们并不认为一个疏远政治的人只是忙于自身的事务,我们认为他根本没有事务。”法律史专家梅因从法学角度指出:“‘古代法律’几乎全然不知‘个人’。”甚至个人的生命也不以出生和死亡为限,“个人生命只是其祖先生存的一种延续,并在其后裔的生存中又延续下去”①。现代权利观则兢兢于对个体利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的守护,崇尚私人领域免于强制的自由,注重多元价值和制度规范。可见,权利与正义存在着反比例的紧张关系,追求整体和谐的正义与个体的低度权利相适应,而现代权利观与契约式的低度义务相联系,天生带有个人主义的胎记。对个人权利天经地义的守护,对多元主义日甚一日的价值化,对消极自由毋庸置疑的圭臬化,正在竖立起在社会范围内达致正义越来越难以逾越的藩篱,事实上使正义成为梦呓。而正义的梦呓化与正义全面退出可经验的社会领域、固守抽象的法律一隅则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法律正义成了社会无正义的遮羞式表达。
以今天的司法理念反观古典希腊,一定可以不费力地指出后者许多的局限性,但这种指出何尝不是世故的中年人对本真儿童的指出。海德格尔认为,当代西方文化已丧失自我反思能力,步入“不思”之境,拯救之道在于回归希腊,思希腊之思。设若帕斯格拉芙案被提交到古希腊、特别是古雅典的法庭上,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
在雅典,履行司法职能的主要是陪审法庭。法庭无职业法官,陪审员的多数意见就是终审判决。每年初公民自愿报名参选,而后抽签从自愿者中选出六千人,作为当年陪审团成员。遇有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大小确定审判所需陪审团规模,从五到两千人不等,然后从六千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陪审员总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方式将这些陪审员分派到不同法庭。这种随机性的组合方式,从制度上杜绝了当事人向陪审员行贿的可能,而不是把反腐败的宝押在个人的自律上。
审判程序的设计也别具匠心。先由法庭两造分别为自己辩护,并进行举证。之后陪审团举行第一轮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可能当时已有“疑罪从无”的审判理念,被告被判有罪的情形仅限于他获得的无罪票数少于半数时,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才需要第二轮投票,从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的判罚方式中选取其一作为最终判罚。否则的话,尤其是当被告的无罪得票占多数时,他不但马上获释,而且取得进而追究原告过失的资格,这时,陪审团再一次投票,以确定原告是否有过失,如果原告获得的无罪票数不到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到处罚。这一设计是为了防范恶意诬告。
对这一审判制度的自以为是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点:首先,雅典有专业法庭,却没有专业的司法和法律理念。人数众多的陪审员没有、也不可能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判决不是根据既有的法律,更多依赖常识和自我体认,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法庭辩护能否打动听众决定着当事人的命运,作为诉讼技巧的演讲术畸形发达的背后却是法律自身发展的停滞。其次,以主观的投票判定客观的事实。无论何种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审判没有调查和取证质证的义务,审判也不需要证据,陪审员们的集体投票才是决定是否犯罪和应受何种处罚的依据。其三,苏格拉底之死,这一雅典民主的悲剧首先是民主审判制度的悲剧。归言之,“虽然希腊人有司法制度,但很难说他们有法律制度。他们没有制定出法典……他们在司法上的一个贡献,民众陪审法庭,采取了最易流于任性的形式,而与任何法律科学根本的不相容”。
显然,这些对雅典司法的否定不过是对现代司法制度迂回的肯定,其独占真理的傲慢妨害了对历史作“了解之同情”。雅典当然有属于自己的成文法,其编纂成文法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立法。陪审法庭的非专业化不仅以城邦生活结构和法律结构的相对粗疏简陋为背景,更与希腊人独到的专业观有关。以牺牲人的全方位潜能而达到的“术业有专攻”,这对于本能抗拒人的工具化和功能化命运的希腊人来说,其狭隘简直近于侮辱:难道这样的人不就是广场上变戏法或走钢索的小丑吗?厄迪斯·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说:“只有我们能够想像出这样的现代社会,即全美的足球运动员同时又是全美最好的诗人、哲人和政治领袖时,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希腊世界的精神。”只要想像一下,雅典这个极盛时全部人口也不过四十万(包括半数以上的奴隶)的蕞尔小邦所开创的全能的精神空间:神话、悲剧、哲学、雕塑、柱式建筑、微积分、民主制度、演讲术、柏拉图、马拉松战役……又怎能不令浅薄的我们汗颜,我们浅薄到仅以身处二十一世纪的原因,就傲视二十世纪、十九世纪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我们浅薄到以消解和否定过去为能事而聊以自慰和苟活。
希腊人不仅拒绝对主体作专业化和功能化的理解,也拒绝对客体作专业化和功能化的理解。事实上,主客体二元对立观的产生,物我一致性观念的消解,目的与手段的分离,本来就是古典世界观崩溃的结果。而在神话式的和诗性的古典世界观中,社会结构关系的有机性和整一性顽强抵制着对它的分析性处理,探讨如何做人(成为公民)的伦理学(就其偏重的角度,或称城邦学、政治学或哲学)通天贯地、包罗万有地成为唯一的知识形态,公共生活的正义和善在城邦社会中具有绝对性和优先性,现代意义上的许多法学命题,在当时却是以哲学或伦理学的话语被讨论,而法律纠纷以政治手段加以解决更是题中应有之义:陪审法庭就是常设的公民大会,重大案件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
至于苏格拉底之死,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储备了探讨这一问题的知识背景和道德境界。把他的死简单地归咎于雅典的司法制度甚或民主本身显然有失公平。单从法律和司法角度讲,他本可以逃脱死刑:他在第一轮投票中以二百八十票对二百二十票被判有罪,从表决结果看,只要他能顺应民众的意愿作忏悔哀怜状,发誓不再敬事新神和腐蚀青年(这是苏格拉底被提起公诉的罪名),以他的口才在第二轮投票中争取较轻的判罚应该不是难事。但苏格拉底的行为匪夷所思:他在随后提出的对自己的处罚建议简直有轻侮法庭之嫌,先是说自己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于城邦,理应受到礼遇,后又提出罚款一百德拉克玛了事。由于这些建议过于荒唐,部分本来同情他的陪审员也倒向公诉人一方,最终以三百六十票对一百四十票被判死刑。
苏格拉底之死,不是公民或被告之死,而是思想家之死。思想家只为思想而活,当社会剥夺了他思想和传播思想的权利时,他宁愿选择死亡。因此,他的死不是一个司法或政治事件,而是一个文化事件,他以赴死的决绝演绎巨大的悖论:他被不公正处死,但他甘愿公正地执行判决。化解如此巨大的张力,需要更大的伦理意志现身。从柏拉图的记载看,苏格拉底也曾在目的-手段内在一致的关系层面上解读自我牺牲的意义:法律的判决或许是不公正的,但你不能以不公正地逃脱制裁相对抗,如果你还以法律公正为信念的话。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法律的公正似乎只是苏格拉底的表面措辞,他一直认为,他的各种活动都是受到神圣声音的指引,其在世的教化活动也是为了将他所倾听到的神圣声音实现在城邦共同体之中。这里的神圣声音其实就是宇宙正义的神秘化表述,但是经由神秘化而形成的对宇宙正义的超越性体验赋予苏格拉底以与现实的不公正作不妥协对抗的道德勇气,支持他以公正执行判决的高贵姿态应对、反衬乃至修正法律自身的不公正。最终,苏格拉底以他堪与耶稣比肩的殉道行为彰显了宇宙正义对于法律正义的价值优先性和本源性。
通观雅典留于后世的法庭辩护辞,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特点,即很少就事论事地举证案件本身,却大谈当事人作为公民甚或客居民的公德表现。一场有关商业欺诈的诉讼,代理人为被告撰写的辩护辞洋洋洒洒万余言,主要的篇幅却是缕述被告对城邦的公益捐助:曾参与赞助了三次公民庆典及两次悲剧演出的费用,独自或合伙捐建了两艘三层桨座的战舰,无数次担负战争期间的紧急开支……上述诸项累计花费达三千五百明那。而与本案直接有关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句:“一个如此热心于公益活动、诚实地履行公民义务的人,又怎么可能在区区五百明那的商业往来中上下其手,玷污当事人的一世英名呢?”
一批非专业的陪审员以非专业的视角进行的审判,自然不会停留于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无罪过”的层次,他们要追问被告人的社会责任:作为公民,你可曾积极参加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工作?可曾忠实履行军役义务?如果被告人是作为社会财富暂时保管者的富人或企业法人,则要承担更大的义务预期:在希腊人的整体世界观里,企业消耗的远不只是“唯一价值创造者”的劳动力,更多的还是本属于全社会的不可再生资源;在企业法人获得巨大收益和巨大享受的同时,却造就了全社会为之承担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具体到长岛火车站,人们在就事论事的判决之前,首先要追问的或许是:作为一家财力雄厚的铁路公司,你曾为铁路沿线因此而丧失土地并身心备受搅扰的农民们做过怎样的补偿?曾修建了多少堵隔音墙以减轻噪音对沿线居民生活的影响?曾在铁路沿线修建了多少座高架桥以帮助人们安全地横穿铁路?而在因横穿铁路而引发的交通事故中制定过怎样的偿付标准?可以想像,身处希腊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长岛火车站在诸如此类的公益事业上也决不会乏善可陈,对这些公益成就的不厌其烦的屡述也将成为辩护辞的主要内容,而不是长篇累牍、技术至上地辨析工作人员的失手与受害者受伤害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这种因果联系在法理上的合理性。当然,如此关注社会正义而不只是法律正义的企业会不会因一桩伤害索赔案而被告上法庭,其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而不是纠缠于所谓的“法理”,它可能早就对受害人给予了补偿,从而加长它赖以自豪并作为社会资本的公益捐助清单。而即便上了法庭,相信陪审员们也不会循着“维护法律神圣性”(“神圣性”的措辞是对唯理主义时代的反讽)的人为原则作出一种只合乎法理、却有悖于人性本身的判决。
雅典法庭设置在与天地神灵直接往来的露天,没有森严的建筑物将法庭内的审判与外在的更广大的世界和更广大的因果网络隔绝。当事人在庭内的表现需与庭外更大时空下的表现相互参照、印证,他在案件中的命运与他在血缘传承中由先祖行为所造就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于是,这种庭外庭内浑然一体的审判方式就不只是对特定案件的审判,更是以城邦社会的名义对当事人一生的审判;不只是旨在明确特定案件的因果链条,还是以“命运”的名义要求对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后果的勇于担当。按照卡多佐式逻辑,俄狄浦斯完全可以不为他的“杀父娶母”负责,这是因祖先的罪过而强加于他的命运,无论如何谨慎从事,他对这样的结局完全不能躲避。但希腊文化仍要求他承担后果,他刺瞎自己的双眼,放弃王位、自我流放以赎罪。与前定的命运作不妥协的抗争,然后在命运分毫不爽地予以兑现并宣告抗争的徒劳之后勇于承担由此带来的毁灭,这正是希腊用以教化公民的悲剧的经典模式。希腊生活世界的特性之一在于其神性空间,这种空间下的人生追求远不能止步于“真相”的层次,这种空间下的审判也拒绝像卡多佐那样被“实验室化”。卡多佐把当事人从无限性的因果链条中剥离出来,使其只对自己可预见的后果承担责任;而安德鲁斯通过要求当事人对后果的无条件承担,事实上引入了“命运”的观念:事件的发生确非你能控制,但既与你有关,你只能自认倒霉。安德鲁斯的判决思路显然更多古希腊整体主义的巫魅色彩,而卡多佐的判决则在司法领域呈示了失去终极关怀和宏大叙事能力之后的现代文明趋于碎片化的症候,是经历祛魅过程之后的失魅时代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号称科学昌明的时代,法庭对卡多佐判决的接纳和对安德鲁斯判决的排斥都同样是必然的。
雅典法庭将当下的审判与人生的审判相统一,消除了技术主义地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在场的陪审员们正是可随时还原于生活的普通民众,而不是与原生态的社会发生疏离的法律精英,他们亲身参与的审判活动同时又是对自身的教育,这样才真正发挥了法律规范日常生活的本真职能,而避免了现代司法忙于事后惩戒的被动与尴尬。事实上,现代技术主义的立法与司法活动所造就的专业对常识的劫持,精英对民意的强暴,已将法律与司法从其本属的生活质地中强行剥离,而异化为与特定的民众、习俗、传统相疏离,背离人们基本正义感、道德感和伦理观的压抑性存在,异化为凌驾于社会生活之上的只能唤起敬畏、躲避和膜拜情绪的所谓“恢恢法网”。人们与法律的关系已失去古典时代的依凭感和亲和感,他们甚至无法靠理性和常识判断自己是否触犯了法律。法律的法网化、法典化,既是法治社会的福音,又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法律的法典化倾向有其不得已的缘由,即与“同调”生活环境的丧失有关。在古代城邦条件下,相对狭隘的物质生活范围、纯一的生活方式和相似的生活境遇,使人们在对共同生活的正当性体验,即社会正义上很容易达致普遍认同,而且这种正义融法律正义、道德正义和伦理正义于一身,又与生活本身不离不弃、水乳交融,抽象的、概括性的专业法律条文对于现实的司法活动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尤其是步入到近现代社会,阶级的、种族的、地域的、职业的各种差别多角度全方位地涌现和呈示,人们在庞大司法共同体内的共性存在趋于抽象化和虚拟化,而个体间的差异则凸现为唯一的经验性存在,为共同体提供底线规范和刚性约束的法律不得不以最大的通约性、唯理性和最合逻辑的方式,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加以提炼,从中找寻基本的法律原则与理念,并通过将这些原则与理念的文本化而向世人宣示。
但问题并没有消失。如果说希腊的法律条文太过就事论事,因而显得琐细、零碎,不具“法律相”,那么,一个深刻的悖论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利益划分的细节化,法律文本的表述却日益凝练、简省了。这一悖论在古典晚期已有萌现,所谓“衡平”概念,正是对它的克服。“衡平”意为弹性可伸缩的东西,与法律的刚性与僵硬相对。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将它认同为有时必须容许的在法律之外的宽容和仁慈(clemency)。亚里士多德认为,衡平并不与正义相左,它本身就是一种正义,只不过不是遵循法律的正义,毋宁说它是法律正义的矫正,因为每部法律都必须作出一般规定,“而精确地作出一般规定是不可能的”,在立法者没有预见到的情况出现,而这种情况又不适用于既有原则或其推衍的时候,衡平就有必要介入了。西塞罗指出,尽管按照物权法的规定,被委托保管的东西应予归还,但把剑归还给已经发疯了的寄存者就是犯罪。
这一悖论甫一出现时,思想者们还能对它保持必要的警惕与纠偏。然而,当这一悖论在历史的惯力下被熟视无睹地积淀为人们意识中的应然状态,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理性主义的膨胀,人们要参透命运秘密、看破造化把戏,进而一劳永逸地为万世万有立法的冲动首先在法律领域寻求释放,法律条文的暧昧性、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肯削足适履地就范于一般性规定的特殊案例,都成了令法学家们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现象。而在东方这个终于寻到“依法治国”宝典的古老国度,缘于“法律永久性滞后”的尴尬和为后世开太平的宏旨,我们目睹了法律文本目不暇接的编纂与出台,耳闻了民法法典化的急迫呼吁。
注释:
①(英)梅因:《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