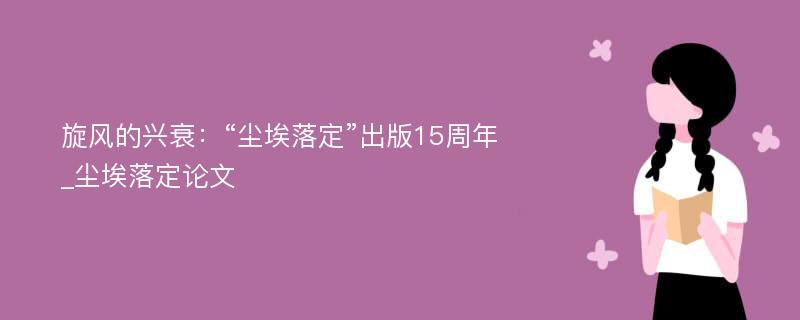
旋风中的升降——《尘埃落定》发表15周年及其经典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尘埃落定论文,旋风论文,周年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5年前,四川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脚印、洪清波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出版,就给了我一种意外的惊喜。在尚未走出惊喜之时,就不得不应约匆忙地为它寻找一种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就是我那时只能找到的作家文化身份视角。从这一作家身份视角出发,我那时把这部小说视为一次新的“跨族别写作”,认为作者着意探索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一种新写法。跨族别写作是一种跨越民族之间界限而寻求某种普遍性的写作方式,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关于少数民族生活的两种写作浪潮的跨越:无族别写作和族别写作。阿来尝试跨越族别之间界限而寻求普遍性,这既有别于不大在意族别差异的“无族别写作”(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着眼于无民族界限的普遍性),也不同于强调族别差异的难以消融的“族别写作”(例如张承志的《心灵史》等作品),而是要跨越上述两重境界,在特定族群生活中去寻求全球各族别生活体验之间的有差异的普遍性。正是这样,这一“跨族别写作”为“我们解读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从而也为整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感人的美学标本”①。
15年后的今天,《尘埃落定》已经通过持续的常销不衰直到突破百万册这一销售业绩,而被一拨又一拨读者实际地奉为一部文学“经典”了,确实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时刻去重读这部“经典”,有意思的是,我的上述看法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改变,只是确实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阅读兴味,包括好奇地去想它为什么会被读者予以“经典化”。这里有两点想法说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②
一 杂糅而多义的人物形象
首先,我的重新阅读视线不得不再次凝聚到小说的绝对主人公傻瓜二少爷身上,发现这一人物形象在内在身份构成上具有一种杂糅而又多义的特性。这部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其独创的这一特色独具而又兴味蕴藉的人物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内涵具有一种奇异的多元杂糅性:他仿佛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形象(《狂人日记》,《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4卷5号),又是与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形象(《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之间一种跨越时空距离的奇异交融和跨越的产物。他一方面具有“狂人”那种超常的历史透视能力,另一方面又有“丙崽”那种反常的憨傻、笨拙。重要的是,他的性格特点在于,看来反常的和否定性的憨傻和笨拙性格,反倒常常体现了一种正面的和积极的建构力量,尽管最终还是落得悲剧结局。再有就是,他的身上明显地还有外来文学影响的因子,其中颇为鲜明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先天性白痴班吉的投影,以及《百年孤独》人物群像中传达的那种四处弥漫的魔幻气息。
从更深层次上着眼,他或许还笼罩在巴尔扎克笔下的鲍赛昂子爵夫人等没落贵族的令人哀婉的身影下。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落实在藏族的民间叙事歌谣的特有曲调及其渲染的悲剧性情调之中。如果这个体会有点道理,那么,阿来笔下的中国川西北藏族傻瓜二少爷,其实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熏陶与西方文学影响及藏族民间叙事传统感召之间的持续涵濡(acculturation)的产物,至少涵濡进了狂人、丙崽、班吉、鲍赛昂子爵夫人以及本地藏族民间叙事曲等多重中外文学形象因子。这些因子(当然不限于此)在这个形象内部形成奇异的杂糅式组合,具有令人回味无穷的功效。正是由于涵濡了多重中外文学形象因子,傻瓜二少爷体现了外表憨傻而其实内在睿智的神奇特点,成就了一位憨而智的艺术形象。这样一个杂糅式及多义性艺术形象的诞生,是此前中国文学画廊和西方文学画廊里都没有出现过的,属于中国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对中国文学传统、从而也是中国文学传统对世界文学的一份新的独特贡献。
由此看,这部小说之被读者经典化,该与这个艺术形象的杂糅与多义性本身有关吧?
二 “旋风”形象与革命世纪
但是,我的问题在于,就是这样一位憨而智的神奇人物,最终也没能逃避那走向毁灭的悲剧性命运。原因在哪里?这就触发了我的另一点新品味:小说中关于“风”或“旋风”的描写。它们在这次重读中竟意外地给了我更加新鲜的印象。小说中每每写到“风”或“旋风”时,似乎都有某种特定的用意在。风的形象在小说中的作用,颇类似于月亮形象在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中的作用,如烘托情境、塑造人物、揭示历史大趋势等。
一翻开《尘埃落定》第一章第一节野画眉,就可以读到下面的描写:“所有的地方都是有天气的。起雾了。吹风了。风热了,雪变成了雨。风冷了,雨又变成了雪。天气使一切东西发生变化,当你眼鼓鼓地看着它就要变成另一种东西时,却又不得不眨一下眼睛了。就在这一瞬间,一切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第4页)风类似这样在小说里多次出现,起到与主人公命运相关联的作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风、特别是旋风,绝不是无缘无故地刮起来的,而总是带有一种隐喻意味——它似乎就是现代中国的彻底决裂式的、摧枯拉朽般的革命世纪或革命时代的隐喻。在这样一股股强劲的革命之风吹拂下,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样。
第37节当翁波意西失去了舌头、傻瓜二少爷决定不再说话时,有这样的描写:“太阳下山了,风吹在山野里嚯嚯作响,好多归鸟在风中飞舞像是片片破布。”(第292页)这风显然正是历史的变化的风,风中的破布恰是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暗喻。又写道:“风在厚厚的石墙外面吹着,风里翻飞着落叶与枯草。”这里的风以及风中的“落叶与枯草”,产生的修辞作用是一样的。“风吹在河上,河是温暖的。风把水花从温暖的母体里刮起来,水花立即就变得冰凉了。水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凉的。直到有一天晚上,它们飞起来时还是一滴水,落下去就是一粒冰,那就是冬天来到了。”(第293页)这里的风绝不是人们通常用来烘托积极的、肯定性的或上升意味的风,而是相反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或下降的风,它指向的是生物界的枯败的冬季而非欣欣向荣的春季。
小说中更有意味的毕竟还是“旋风”。第46节“有颜色的人”写道:“一柱寂寞的小旋风从很远的地方卷了过来,一路上,在明亮的阳光下,把街道上的尘土、纸片、草屑都旋到了空中,发出旗帜招展一样的噼啪声。好多人一面躲开它,一面向它吐着口水。都说,旋风里有鬼魅。都说,人的口水是最毒的,鬼魅都要逃避。但旋风越来越大,最后,还是从大房子里冲出了几个姑娘,对着旋风撩起了裙子,现出了胯下叫做梅毒的花朵,旋风便倒在地上,不见了。”(第372页)这股携带着“鬼魅”的而又需要“梅毒”才能抵挡的旋风,似乎正是历史的无常命运的绝妙隐喻。
最后一节第49节“尘埃落定”这样写道:“一小股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带起了许多的尘埃,在废墟上旋转。在土司们统治的河谷,在天气晴朗,阳光强烈的正午,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陡然而起的小小旋风,裹挟着尘埃和枯枝败叶在晴空下舞蹈。”这样的旋风的意义已经显而易见了。“今天,我认为,那是麦其土司和太太的灵魂要上天去了。”这不正是横扫土司制度的革命的旋风吗?“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只要联系小说的整个语境来体会,这股旋风的意义就更清晰了:它并非一般的笼统的历史宿命隐喻,而是仿佛与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兴亡大势——革命的世纪紧密相连。你看,它竟具有区分两种不同物质的神奇力量:让看不见的轻灵的物质上升,而让看得见的尘埃降落,从而给予这个世界的走向及其结局以支配。
也正是这股旋风,最终有力地推动傻子二少爷走向仿佛是前世命定的毁灭的归宿:“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旋风具有神奇的区分精灵与尘埃的效果。“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这里一再出现的旋风,正是历史兴亡大势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旋风代表的是全球历史兴亡大势,简称历史大势,其主旋律则是革命。置身于这种可以决定一切的历史大势中,无论如何灵异的憨而智的智者如傻瓜二少爷,都无法逃脱被历史潮流“裹挟”的命运。
读到这里,我想就可以进一步回答这部小说之被经典化的疑问了。无论个人如何憨而智,都无法逃避被遍及全球的革命“旋风”所无情摧毁的命运。正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鲍赛昂子爵夫人等没落贵族一样,在无情的历史大势的“旋风”般“裹挟”下,他们难道有更好的命运吗?
三 “旋风”中的现代中国
说到历史大势,《三国演义》早就诠释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古代历史兴亡感慨,而《尘埃落定》也可以被视为一则足以穿越古今历史迷雾的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演义,当然是在更加蕴藉深沉的寓言故事意义上。可以看到,在这个寓言故事中,这个傻瓜对于包括土司制度在内的一切旧制度及自我的毁灭命运,都有清醒的觉察或洞见,从而传达了一种历史智者清醒的现代革命历史的反思意识,同时又不失对于个体的悲剧性命运深切的悲悯情怀。
不过,有趣的是,这部小说或许具有一种难得的双重阅读价值和兴味:你既可以直接阅读它的表层意识文本意味本身,为藏族土司制度和傻子二少爷的悲剧性命运而发出理智式分析和同情式感叹;同时,你也可以更深入地品味它的深层无意识文本意蕴:从傻子形象联想到那些被身不由己地“裹挟”入现代革命“旋风”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千千万万儿女的命运,他们身上不都有着这个傻子的某种影子吗?由此,不难发现这部小说具有深厚蕴藉的双重文本性,可以视为一部明确直露而又深沉蕴藉的带有寓言性的文本。读者在此可以各擅其长,既可以直读其明说的兴味,又可以品评其潜藏的兴味,都会有所得,可谓各显神通。当然,从中国美学的兴味蕴藉传统来说,越是高明的或优秀的小说文本,越善于让自身具有多重阅读兴味和可供再度回味的可能性。《红楼梦》、《阿Q正传》等古今经典小说莫不如此;而相应地,饱受这种兴味蕴藉传统熏陶的古今中国读者也善于品鉴这类兴味深厚的文本。这种来自中国艺术传统的兴味蕴藉特质的打造,可能正是这部小说之被读者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在这个意义上,《尘埃落定》的出现,堪称被迫纳入世界文学进程的地方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结出的一枚硕果,或者说是这种全球化进程在其地方化意义上的一块显眼的里程碑。
更进一步看,《尘埃落定》独特的兴味蕴藉意义在于,它所叙述的藏族土司制度在现代中国革命洪流冲刷下衰败的故事及其中傻瓜的个人悲剧命运,都是属于现代中国革命语境下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族群的独特体验,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不可能有的独一无二的故事,也就是高度地方性的生活体验。但是,与此同时,这个高度地方性的生活体验中所缠绕的革命、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话题,却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现代的或全球的普遍意义。因为,生活在20世纪全球各国的人,都曾经历过同一现代性进程中的革命洪流及其中种种关联事件的不同而又相通的困扰。正是在这一现代革命的巨大平台上,土司家族二少爷的故事一方面呈现出全球化时代地方生活状况即中国四川西北部藏族土司家庭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却又透露出一种跨越地方性的全球普遍性或普世性。正是这种植根于地方化族群生活而又透露全球普世意味的文学体验,突出展现了当今时代中国与外来他者之间的相互涵濡特点,既是地方的又具备普世性,代表了中国作家对全球化时代地方性与全球性相互交融趋势的艺术敏感和反响,可以作为来自中国族群的独特的地方性声音而加入到当前全球各民族文学的普世性对话中。由此看,如果将来有一天,阿来的这部小说及其它作品能够在世界文坛释放出更加强劲的影响力,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再次读完《尘埃落定》,感觉就像沐浴在一股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融的文化“旋风”之中,真切地领略了“文化如风”的意味。但这里的文化之风既非送别寒冬的春风,也非催化成熟果实的夏风,而是专门“裹挟”枯枝败叶和尘埃的“旋风”,显然属于冷酷的秋风或寒风。这“旋风”不也正是指那无情地横扫一切旧制度或旧世界的革命历史大势的隐喻吗?革命一词,在英文中为revolution,其原初意义正是旋转(revolve)啊!正像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处在现代世界的革命“旋风”季候中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学,注定了会遭遇全球历史大势的持续“裹挟”,导致有些东西上升,有些东西下降,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注释:
①王一川:《跨族别写作与现代性新景观——读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四川文学》1998年第9期。
②本文根据2013年4月11日在“向经典致敬——《尘埃落定》出版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