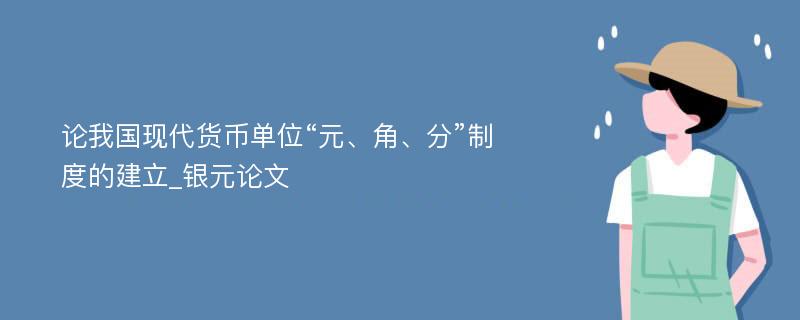
论我国现代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体系论文,单位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5)02-0043-06
“元、角、分”体系(简称“元”体系)形成于清代乾隆时期,20世纪上半叶成为我国的法定货币单位。其由来如何?至今缺少研究。(注:根据笔者的了解,一些综合性的货币史著作虽涉及“元”的出现,因其不是重点,皆一带而过,未曾深究。日本学者百濑弘的《清代西班牙银元的流通》一文曾提到“元”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迄今为止,只有金德平《论我国主币单位“圆(元)”之由来》一文对这一问题做了初步探讨。但金文的史料太少,仅限于粗略的描述,关于角和分则无史料,全凭语言学的分析。)本文拟结合我国币制的近代化过程,论述这一体系形成的背景和确立过程,同时涉及“块”、“毛”等货币单位俗称的出现。
一 “元”体系的形成
“元”体系是中外货币制度碰撞、交流的产物。
明代中叶起,中国的货币制度进入银两、铜钱并用阶段。铜钱为国家铸币(明清两代称本朝官铸钱为“制钱”),计数单位是“文”,辅助单位百、千(或串、吊、贯);贵金属货币白银由民间自由铸造,称量单位是“两”,辅助单位有钱、分、厘……故称“银两”。“银两”属于落后的称量货币,重量、成色不统一,“用之于市肆,则耗损颇多,有加耗,有贴费,有减水,有折色,有库平、湘平之异,漕平、规平之殊,但凭市侩把持垄断,隐受其亏”[1](p691)。因此亟需一种重量、成色统一的计数银币。舶来的外国银币正好填补这一空白,从中孕育出新的货币单位——“元、角、分”。
明清两代,我国所需白银基本来自海外。明代,西属美洲的里亚尔(Real)银币即从吕宋(菲律宾)输入。它是手工铸币,形状不规则,大小、轻重、厚薄不一,只能凭重量、不能凭个数流通[2]。1661年,英国率先用螺旋滚压机铸币,很快推广开来。17世纪末,欧洲人将新式银元输入中国。此后的一个多世纪内,数以亿两计的白银流入我国,大都是机制银币(俗称番银、番钱、洋钱)。18世纪中叶,西班牙银元中的加罗拉币(俗称本洋、佛头)在各种洋钱中占据上风,到世纪末已是中外贸易的标准货币了。它的主产地是墨西哥总督造币厂,主币(Peso,相当于8个Real)重417英厘(公制27.02克),约合中国的库平7钱2分,成色90%。另有几等成色较低的银辅币。从(英)东印度公司的记载看,输入我国的绝大多数是Peso,辅币很少。
洋钱来到中国,先被当作银两称量使用,或被改铸。在洋钱流通较多的地区,经过一段时期的试验,人们觉得机制银币重量和成色标准化,形制统一,不必“较成色之高低,称分量之轻重”,凭个数计值即可。洋钱遂成为中国货币制度的新因素:异于称量货币银两的计数银币。因其圆形,人称圆(简写为员、元),并将这作为洋钱的计算单位。
“元”的称呼可能出现于18世纪初期。雍正六年(1728)泉州黄氏家族的一份契约即有“员银一百八十两九城驼足”的写法,但计值还是用“两”[3](p82)。此后,以“元”计值首先在闽台和广东一带流行开来。在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雄《新建明伦堂碑记》的35条捐银记录内中有13条用“两”,其余22条皆用“员(圆)”[4](p68)。无独有偶,当年刊印的《台湾府志》卷十三《风俗一》中也能看到作婚礼聘钱用的“番银……圆”。在福建沿海,乾隆三十三年(1768)晋江刘暹一案中,刘父“许给黄氏番银一百大圆”,“向蔡耀银店借出番银一百大圆,先交黄氏十大圆”[5](p686)。看来当地早就通行“番银”计元定值了。此时,“元”也在福建内地通行。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德化县因“地处山僻,纹银难觅”,规定契税征收“照收钱粮之例,每番银一员,折纹银六钱二分”[6](p358)。可见此前这里已经计“员”纳税。在广东,“岭南一大都会”佛山的房地契约最晚从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开始大量地用“元”为货币单位[7](p487~504)。1779年,(英)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的文件提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银币变成通货;由于方便之故,而获得虚拟的价值。”[8](p363)所谓“虚拟的价值”,指洋钱的市价超过实际含银量。这只有在计枚定值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乾隆后期,新货币单位“圆”在闽广地区普遍使用。“福建、广东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钱。……凡荷兰、佛郎机诸国所载,每岁数千万圆计”[9]。外贸记账单位也受到影响。1786年2月24日,(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训令说:“不赞成近来流行付给商人的银元按个数计算,而不以重量计算的办法。”[8](p593)过了6年,它最后一个服从潮流,承认“按个数计值是优越的,因为它的方法简单,能力最平常的人也可以做到”[8](p627)。“圆”替代“两”,成为外贸记账单位。后来,《南京条约》规定的赔款额正是以“圆”计算。
闽广是洋钱的直接输入地,海外白银输华的目的是购买中国土产,很大一部分将继续向北流动。因而,长江下游地区的货币流通格局也逐渐被洋钱改变。
18世纪五六十年代,洋钱在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算新生事物,“有商人自闽粤携回者,号称洋钱,市中不甚行也”[10]。在经济中心苏州、杭州,乾隆四十年(1775)后“乃渐用洋钱”。一二十年内,这一新的流通媒介便压倒了银两,“番银之用广于库银”[11](p54)。江浙成为洋钱的新基地,“非特通都大邑人人能办,即乡僻小村亦多有认识洋钱之人。不如纹银,必俟有钱铺始能办其成色,权其轻重。是以民间即有纹银,亦皆兑易洋钱使用。不独市廛交易用之,闾阎收藏用之,即州县收纳地丁、漕粮亦无不用之”。[11](p193)“江南全省,通商大贾,皆以银换洋钱,零星贸易,始以银易换制钱”。[11](p133)“浙江征收钱粮惟此是索,故市肆弥重之”。[11](p195)江、浙、闽、广之外,“圆”又随洋钱进入广西(西江上游)、安徽(茶产区和沿江)以及湖南的南部和东部[11](p57)。
由于洋钱流行,“元”得到了许多原属“两”、“文”的价值尺度职能。在鸦片战争前的江南金融中心苏州,洋钱在乾隆五十年(1785)后“相率通用”,“苏城一切货物渐以洋钱定价矣(按:以元定价)”。[11](p54)上海对外开放时,外商惊讶地发现,“上海同宁波、苏州、杭州一样,早已通行西班牙银元了,大多数做小买卖的店铺都按银元交易”[11](p57)。
随着“圆(元)”流行,产生了辅助计算单位——角、分。嘉庆二十四年(1819)包世臣在《已卯岁朝松江即事》诗中说:“石米块八价在市,官漕石折六块四”。前一句加注曰:“吴市用洋钱以块计,每块十角,每角十分。”[12](p87)“块”是元的别称,至今留在口语中。(注:苏州府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的书价记录也提供了关于洋钱货币单位名称的珍贵资料。121条书价的38条以“番饼”、“番钱”计价,集中在后期。所用的单位名称有圆、元、块、饼,或直称若干番钱、番、洋,其中一部书的价格是“六洋四角”(参见黄寿成:《外国银圆在中国的流通》,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可与包世臣的记载相互印证。)新货币单位的使用范围很广,如陈盛韶《问俗录》记载台湾“每担折银一圆三角”[13](p133)。陈氏在台为官的时间是道光十三年(1833)。圆是因形得名,角、分的情况不同。从语意而言,“割圆则得弧角”,这大概是以角辅元的原因。至于“分”,广泛用于旧式度量衡制度。用于长度,是一尺的百分之一;用于面积,是一亩的十分之一;用于重量,是一两的百分之一。民间也用它辅助圆,作为圆的百分之一。角和分的出现,基本上是计价的需要。因为商品的价格很少刚好是整圆,常有畸零,必须引进辅助单位。当然,随着外国银辅币更多地流入我国,人们也以“角”称之。“分”进入元体系时,可能将另一个货币单位“厘”也带入。这里只能提供一则稍晚的史料,即咸丰年间重修宁波福建会馆“糜白金二万七千五百九十八元三角四分六厘”[3](p85)。因旧式度量衡制度一向分、厘并用,论面积则曰亩、分、厘,论重量则曰两、钱、分、厘,论长度则曰尺、寸、分、厘。故而有理由推测,厘应该是跟随分一起进入元体系,作为“圆”的千分之一。
鸦片战争前,洋钱已成为华东、华南地区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如直隶、山、陕、河南、两湖、四川、云贵等省,概不行使”[11](p47)。在洋钱流通区,“元”体系不断侵蚀“两”、“文”体系的地盘。不过,这一民间的创造得不到政府支持。道光年间,清政府怀疑洋商用而低成色的洋钱换走高成色的白银,规定“行使洋钱,必以成色分两为凭,不得计枚定价”[11](p42~50)。这个禁令没能执行,但“元”体系的生存和发展完全系于一种外国货币,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的困境。一方面,它的发展受到对外贸易的限制。外贸拓展到哪里,洋钱大规模流入哪里,它才能跟随到那里;另一方面,它的生存依赖本洋。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本洋停铸,来源渐少,存量货币又因戳印、剪凿、磨损、刮削不断消耗。“光板”本洋不断流向价格更高的江浙,广东、福建沿海只好大量使用烂板(Chopped Dollar)。烂板需秤称,是另一种称量货币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人们的囤积,本洋在江浙也愈加短缺。1856年9月,它在上海的升水超过50%,而且有价无市。次年初,贸易记账单位不得不从本洋的“元”改为上海两(即规元,一种虚拟的银两单位),“元”体系遭受沉重打击[14](p525)。规元从此独占上海的重要经济活动,而且凭借着上海的金融地位逐渐变成国内、国际贸易和国内、国际汇兑的基准记账单位。
二 “元”体系的多元化发展
本洋虽然衰落,它的灵魂依旧是统治者。近代史上,所有在中国流通的银元(西藏、新疆地区除外)都继承了本洋的重量和成色标准。相应地,本洋的计算单位也被它们继承下来。“元”体系附着在各种本洋系统的银元、以及新兴的银元纸币身上,继续发展。
1823年,墨西哥银元开铸(因鹰徽标志被称为“鹰洋”),五口通商后流入中国。它完全继承了本洋的成色和重量,但在十多年里“非常缓慢地为人使用——而且只是折价使用”。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本洋,“有时认其它银币皆系荒洋,拒绝接受,只能按分量计算”[11](p56)。1856年之后,鹰洋才打开市场,逐步继承了本洋的“领地”。它的大本营是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安徽沿江地区、皖南、江西、两广、福建和台湾是主要势力范围。香港总督卡利斯·鲁宾逊1863年谈到,鹰洋不仅是香港惟一的法偿货币,也在中国广泛流通。它们当时既在广州也在上海大量通行,而且“在中国中部的产丝区付款,必须用没有磨损的墨西哥银元,它有很高的升水”[15](p44)。直到民国初年,鹰洋都是中国流通量最大、流通最广的银元。据彭信威先生估计,输入中国的鹰洋“不下于三亿元”,主要是七钱二分的大银元[16](p885)。
作为本洋的继承者,鹰洋也继承了货币单位——“元、角、分”。由于“元”的长期使用,外国银币的俗称起了变化,番银、洋银、洋钱之外,又有“银元”。1887年,张之洞请许试铸银元的奏折内就称机制银币为“银元”[11](p672)。外国小银币都称“角”,1883年翰林院侍讲龙应霖上的一个折子里提到“(洋钱)又有一角、二角者数种,便于零用”[11](p633)。
19世纪70年代,鹰洋在东亚独步一时,是中国东南沿海、日本、南洋、安南、香港等地最好的硬通货。各国(殖民地)政府先后自铸银元以谋抵制,如香港银元(1866~1868)、日本龙洋(1871~1897)、西贡银元(1895~1903,俗称法光)、香港银元(1895~1903,印度造币厂出品,俗称杖洋或站人),美国也发行过一种贸易银元(1873~1877)出口远东。为与鹰洋抗衡,它们的重量、成色皆仿鹰洋,仅些许出入,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因而都流入中国,也使用“元”体系作为货币单位[17](p140~150)。早期的香港大银元背面即镌有“香港壹圆”,是最早铸有“圆”字的银币。后来的杖洋背面同样镌有“壹圆”二字。大概是受了中国的影响,日本龙洋也镌“一圆”以纪值[18](p39~40)。上述本洋系统的外币仅法光和站人有一定势力。清末民初,前者约二三千万元流入广西、云南,后者约八千万元流入华北、西北。这已是中国自铸银元之后了。在19世纪80年代,银元世界还是鹰洋一枝独秀。但依靠外国货币,“元”体系发展相当缓慢,大体上是固守从前本洋的领地,仅少量进入长江上、中游和北方沿海的通商口岸。
银元之外,“元”体系又找到一个新载体——纸币。很难判断银元纸币何时出现,据外商记载,鸦片战争前后的上海,“市上流通的钞券大部分是指明为银元的”[11](p57)。这些“钞券”未必是钞票,也许是庄票(一种短期信贷工具)。稍晚,有确切史料表明银元纸币在福建的流通。咸丰二年(1852),福建巡抚王懿德说:“自上年十月行抵福建,半年以来,体察省城以及外府州县,所用或钱票、或银票、或番票(按:即番银票,不是外钞)。”[11](p322)钱币学材料可为佐证,现存的一张福建“享利镐记番银票”,面值“一员”,发行时间在道光三十年(1850)[19](p150)。因为银元钞票逐渐流行,外国金融机构也加入发行。起初用英文“DOLLAR”计值,后来直接用“圆”,如1881年(英)有利银行面值“壹圆”的钞票[19](p569)。
从1890年开始,“元”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是年,广东当局开铸机制银币(因背面有龙纹,俗称龙洋或龙元),至清末有12个省及中央政府的造币总厂相继仿效。这种银元还有某些银两的痕迹,正面中央镌“光绪元宝”,边缘标明重量。但它属于本洋系统,大、小银币的重量、成色都“与向有洋钱一律,便于交易”[11](p677)。故此,民间也以元、角称之。受香港银元影响(其一角、二角币称“香港一毫”、“香港二毫”),广东一带“称小银元皆以毫计,如一毫、二毫(按:或曰单毫、双毫)之类。市肆记账,又往往减笔写作‘毛’字”。[20](p85)这一俗称逐渐流传开来,1910年度支部的一个咨文就称小银元为“毛银”[11](p1089)。
民间习惯影响到官方货币。1897至1899年北洋机器局发行的龙洋正面直书“一圆、五角、二角、一角、半角”,完全摒弃两、钱的计重体系,在币制改革中迈出新的一步。与银元相比,银元纸币就彻底摆脱了银两痕迹。清末,省属的官银钱号和户部银行(后改为大清银行)发行的银元票一概是票面直书若干“元(圆)”。
中国自铸银元的一二十年间,“元”体系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华中、西南、东北内地和华北的京师。直隶、山东,有力地排挤着“两”体系和“文”体系。其一,龙洋大都由银锭改铸而成。清末的大小龙洋合记不下3.5亿元,这意味着至少2.5亿两的银两退出流通,由银元取而代之。其二,由于铜钱荒以及铜元(机制铜币,是铜钱的替代品,面值“当制钱×文”,属“文”体系)贬值,银元、尤其是银角大受欢迎,得以侵入铜钱的传统领地。1905年以后,沿海沿江地区的城镇中多数以钱计价的商品逐渐改用银洋(银角)计价,“各业渐改钱码为洋码。惟南货、槽坊、烟纸等业,其所售均系零星小物,故仍以钱计。”[11](p975)如华北商业中心天津的总商会决定自1908年1月起,“凡出售各货均改银价,拟银洋十角为一元,如给铜元随银洋市价核收”。4月又建议“所有京津两地一切官商交易,均以银元为本位”[21]。
至此,“元”体系的势力已经达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它尚未获得法律上的独占地位。同时,“元”体系囊括数种外国银元和十几种“产地”不同的龙洋,它们的重量、成色难免稍有差异。同为一元、一角,因产地和各地习惯而生出价格的差别。这严重妨碍了银元执行价格标准和流通媒介的职能,客观上延长了银两的寿命,特别是巩固了虚银两(某种平砝和某种成色结合而成的记帐银两,并无实银)的地位。在一些大商埠,虚银两长期占据着大宗贸易、埠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价格标准,如上海规元、天津行化银和汉口洋例银。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以“元”为本位,重建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
三 “两”、“元”之争
20世纪初年,在经济发展和中外交往的推动下,全面改革币制提上议事日程。应列强的要求,1902~1903年,清政府在中英、中美、中日“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内首次承诺“中国允愿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22](p85)。确定本位货币和辅助货币成为改革的当务之急,简便的办法是沿用经济发达地区流行的“元”体系。可是部分朝廷重臣坚持铸造重库平一两的主币和一钱至数钱重的辅币,由此引发“两、元之争”。
早在19世纪80年代,御史陈启泰等人曾呼吁开铸银钱(自一两至一钱不等)[11](p632~634)。受此影响,吉林当局在光绪十年(1884)铸造过“厂平”一两至一钱的五等银钱,为我国机制银币之始。
龙洋流通后,就有人反对模仿洋钱的“权宜之计”,要求“自为制度”。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品京堂盛宣怀请铸京平一两的银元,引起重视。军机处允许他开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后附铸十万枚,此事未成[11](p691~692)。光绪二十五年(1899),军机处又电询各省督抚,银元应否改铸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四种,多数主张不必改铸。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意见可为代表,他承认“此论未尝无见”,却又担心新银元“与洋银数目参差”,商埠不肯行用,不如龙洋“尚可依傍洋银而行”[23]。
“商约”谈判期间,铸造一两银币的旧事重提。英方谈判代表马凯赞同中方代表盛宣怀的看法,即未来的国币“以银两为单位比以银元为单位更便利”[22](p32)。这一意见虽未写入条约,但得到奕劻,张之洞、袁世凯等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宣布“著铸造一两银币为本位币”。不料,度支部认为一两币“不便行用”,坚持七钱二分的标准。于是,在奕劻主持的政务处和载泽主持的度支部之间展开一场拉锯战。双方背后各有一批督抚支持,上海商务总会为代表的沿海商界站在度支部一边[11](p734~738)。
“两”派的理由有二:一为“主权说”。各国国币“彼此未尝沿袭”,国币效仿鹰洋是“亵国体而损主权”;二为“习惯说”。中国用“两”之处多于用“元”,国家财政、大宗贸易和进出口也用银两。所以一两国币顺乎“民俗”,并可减少两、元之间折算的烦难[11](p747~750)。
对此,“圆”派都予以驳斥:其一,货币的主权标志是“花纹字样之不同”,与成色、重量无关[11](p736);其二,习俗所用之“两”,各地的平、色不同,即使政府的库平、漕平、关平,也不能处处一致。铸造库平一两银币,此“两”与彼“两”之间、“两”与“圆”之间皆须折算,同样要改变各地“习俗”,并不能减少“折算之烦难”[11](p758)。
显然,“圆”派的批驳正中要害。但留恋“习俗”的大有人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就货币单位征询各省督抚意见,有12人主张用“两”,超过主张用“元”的9人[11](p746~747)。翌年,清廷再度诏告“定一两重银元为本位币”。不料,度支部竟不退让,坚持“一两重币制仍有窒碍请再行妥议”。双方妥协,宣统元年(1909)由度支部设立币制调查局,“宽予限期,详加考察”[11](p763~765)。
“两、圆之争”持续七、八年之久,币制改革因之久拖不决。其实,银币重一两也无妨其计数货币的本质。只是“元”体系银币的重量、成色有一定之规,新币一旦流通,民间不会呼为元、角,以免混淆。或许称“库平一两(几钱)”或“大清一两(几钱)”。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属于称量单位的“两、钱”就被改造为计数单位。诚如梁启超所言,“九钱与六钱四分八厘(按:指拟议的两、元银币的实际含银量),有何优劣之可言?而论者乃视为一大事而攘臂争之,真大惑不解也”。[24](p5)不过,在中央政府财窘力弱、币制又亟待刷新之际,取舍的关键应当是何种方案推广易而风险小。相形之下,“元”币符合经济发达地区的使用习惯,显然更胜一筹。
扭转局势的又是盛宣怀。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任邮传部右待郎的盛氏就医日本,顺道考察财政。他了解到日本“从前开铸一元亦照墨银重量……揆诸人情顺而且易,故不数年而墨元尽矣”。于是上疏支持用“圆”,同时建议辅币单位也要“从俗”,可用“妇孺皆知”的“角”[11](p769~778)。
盛宣怀阵前倒戈,加之袁世凯去职、张之洞去世,“两”派顿时失势。宣统二年(1910)颁布的《币制则例》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曰圆”,“由圆十析则曰角,由角十析则曰分,由分十析则曰厘”[11](p784)。《则例》虽然没有实施,但它弃旧图新,遵从经济发达地区的习惯,确定“元”体系为惟一合法的货币单位,开创了币制变革的新局面。
四 “元”体系的沿用
清王朝灭亡后,“元”体系的法律地位由《币制条例》(1912年)和《国币条例》(1914年)继承下来[25](p88)。“元”体系得以继续扩张。
民初,财政赋税都改用“元”计算,给了“两”体系致命一击,各地铸造银锭的炉房纷纷改行歇业。中央政府又大力推广国币(袁大头),并辅以中国、交通两行的银元纸币。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它们在全国大多数城市占到统治地位。据192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19省48个重要城市的调查,袁大头在44个城市“最通用”、“极为通用”,中、交两行钞票在40个城市“流通最广”、“最为通用”。银两则逐步退出流通界,11个城市完全弃两用元,其余城市的“两”大多是记帐用的虚本位,并无实银[25](p392~400)。不过,关、盐两税还是按“两”征收,偿还外债亦按银两折合。银两的根据地在金融中心上海,全国银两体系的核心——规元是外贸和国内、国际汇兑的标准。
这一时期,铜钱日渐稀少。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文”体系附着铜元,在下层人民的生活中保留了一定地盘。《国币条例》规定辅币以分、厘计价,可新式辅币数量稀少,各省造币厂照旧发行“当×”铜元以牟利,都以“文”计价,如“沪上铜元兑价……已由一千五百文增至一千八百文”[25](p733),“合肥铜元兑价每大洋一元已降至一千六百四十文,而芜湖仍在一千七百三十文以外”[25](p737)。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先后实施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币制初步统一。经过一百几十年的竞争,“两”、“文”体系退出历史舞台,“元”体系统一了中国的货币单位。同时,经由银元兑换券这一中间环节,“元”体系从最初的金属货币单位过渡到法币(不兑换纸币)单位。1933年的《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一元,等于百分,一分等于十厘”[26](p92)。其中没有了“角”,但中央银行照旧发行“壹角”、“贰角”两种小额钞票[27](p107)。官方文件也继续使用“角”,1940年11月中央造币厂与北极公司签订的代铸铝币合同内即有“折合国币十六万三千二百六十五元三角一分”的写法[26](p324)。这个“表里不一”的问题在1948年《金圆券发行办法》中得到解决,它规定本位币单位是“圆”,“辅币为角及分,各以十进”,“厘”被取消[26](p574~575)。
由于长期使用,“元”体系深入人心,顺理成章地被新中国采纳。早在1932年,苏维埃国家银行就曾发行1元、5角、1角、5分面额的纸币和布质货币。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因通货膨胀严重,这套人民币从1元到50000元,没有辅币[28](p4~5)。1955年2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宣布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币面额,主币分为一元、二元、三元、五元、十元五种,辅币分为一分、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六种”[28](p8)。从此,元、角、分成为人民币的货币单位,沿用至今。
标签:银元论文; 袁世凯银元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墨西哥鹰洋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重量单位论文; 钱币收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