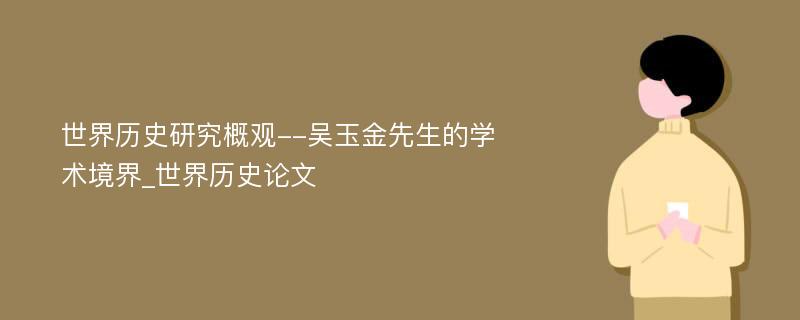
世界历史研究的“通观”——吴于廑先生的学术境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历史论文,境界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当代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吴于廑先生无疑是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通观”,以其博大深邃的学术思想彰显出崇高的学术境界,多年来一直滋养着诸多后辈学者和莘莘学子。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日益拓展的今天,重温吴先生的这一巨大学术贡献,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笔者仅在此拿出个人的体会与学界同仁分享。
一
云南昆明的滇池西山,在通往龙门途中有一幅石刻对联:“置身须向极高处,举首还多在上人”。这一寓含着山势险峻和人生哲理的对联,给致力于史学研究的吴于廑先生带来的是崇高学术境界的遐想。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在昆明参加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年会期间游历西山,于攀登途中看到这一对联,旋即将之与治学的学术境界联系起来。他感悟到当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可映射此景,于是将此联改为“置身须向极高处,放眼通观大世间”。他解释说:
这里说的极高处,是指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极高处。把自己置身于这一理论的极高处当然不容易,但我们可以有志于此,所以说是“须向”,就是应当向极高处努力。能够站得高一点,就便于放开眼界,开阔视野,对这个广大世界的历史加以通观,进行全局的考察。①
先生这里所云的“通观”,从字面意义上看,似是一种对历史的整体、综合的考察,属于理路(认识论)、方法(方法论)的范畴,但仔细考量先生的著述,其间却包含着求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这一宏大学术理想。因此,在数年后,先生在其授课讲稿中谈到历史的综合考察时指出:
这里所说的历史综合,实即是对历史全局的通观。若按中国传统史学的说法,近似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通观在时间上可以为断代,在空间上可以为局部地区、为国别。不限断代、不限地区国别的通观,则是以世界为全局,自远古以迄当代,作历史的全局综合,通观全人类的古今之变。②
由上观之,吴于廑先生所提倡的“通观”是以一种整体、综合的研究去考量历史发展的状况,求得对其中历史变动趋势的理解与认知。这既可以是应用于对某个局部地区、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研讨,也可以是打破断代、国别的界限去通盘探索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而对吴先生自身来说,他所追求的则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通观”,是一种包纳了整体、综合考察的宏大学术视野与路径。他指出,在世界历史的编撰学中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中心论。在近代以前,受各种局限,东西方的史学家在撰写自己已知的世界的历史时,都有其独特的中心论,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和伊斯兰国家中心论即是如此。到了近代,兰克等人建构的西欧中心论更是一度盛行,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受到质疑:
因此,世界客观形势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可能:以世界为一全局,而不是以主观规定的某一地区或某一种族为中心,来考察、研究、著作世界的历史。我曾经称此为“世界观点”,这个观点既排斥西欧中心论,也排斥其它中心论,包括带有某些历史感情色彩的亚洲中心论。③
吴先生说的“世界观点”,就是他上述所强调的整体、综合研究世界历史的视野和路径意义上的“通观”。如果再深入探究,吴先生这一“通观”或“世界观点”更含蕴着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的追问与探求。这一宏大学术理想的学术要旨,就是要突破长期以来盛行于西方史学界并对东方学者深有影响的“西方中心”论,打破世界史研究中所存在的条块分割的碎片化的格局,探索并勾勒出“历史怎样发展成为世界的历史”这一“主题”,并揭示这一主题中所包蕴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④并建构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科学体系。
在世界史研究学科发端最早、学术积淀最深的西方史学界,强调整体、全局地研究世界史之理路甚至是欲以此探求某种趋势、法则的学者不乏其人,而在中国史学界则寥寥可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充分地借鉴西方的史学成果和中国本土的历史资源来系统地阐发“通观”理路、并以此对世界历史进行诸多研究实践的史学家,非吴于廑先生莫属。
二
吴于廑先生的“通观”学术思想,源于他广博的知识结构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吴先生求学时代曾在西南联合大学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诸多名家的著述多有涉猎,并萌发了历史比较的想法,曾撰写过有关士与古代中国统一运动的历史论文。后来留学哈佛,浸淫西方学术时也仍然用中西比较的眼光去审视一些问题,如中古前期西欧封建诸国与中国古代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在君权、法律方面的比较。留学回国到武汉大学从事世界史的教学后,先生对西方史学史、希腊古典城邦、中古前期西欧政治史、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中的不少问题曾进行过个案研究,尤其对从兰克史学的客观主义、斯宾格勒、汤因比、丹尼尔夫斯基等“形态学派”的历史理论乃至巴勒克拉夫的史学学说,都有深刻的解读与体悟。他既洞见这些史学家的某些唯心主义理论与缺陷,如汤因比的保守思想及其对中国文明乃至希腊文明的误读、对文明承续的谬释,同时也看到了其中有价值的要素,如整体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挑战与反应的研究、特别是对启蒙主义以来“西方中心”论的质疑与否定。这些都为吴先生日后在发掘本土资源特别是批判地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世界史的“通观”探索作了深厚的铺垫。
吴于廑先生世界历史研究之“通观”的酝酿,更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他在编撰四卷本《世界通史》的过程中发现以往编著和译述的世界史,因为受某种中心论的影响,“较流行的体系是按社会发展分期,以‘先进’地区或国家进入某一新阶段为断,逐一叙述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的历史”。由这样的理路来编撰,“对列于‘先进’之外的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是强其削足适履”,如此撰写出来的则是各地区、各国或各民族历史的堆积而非全局彰显的世界历史。为了寻找新的路径,吴先生积极从唯物史观中发掘教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世界历史”的理论对他大有启迪。在唯物史观看来,“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是各民族的生产与交往方式突破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相互间的分工差别愈益消失的进程中逐渐凸显的。吴先生认为,这一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世界历史并非“自始就是世界性的,其自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应该作为其以“通观”来编撰与探究历史的理论依据:
以此为据,很显然,考察和研究世界历史,不能以逐个考察世界的各个局部为已足。更为重要的,是应当考察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怎样打开彼此的闭塞,怎样在愈来愈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最后怎样汇合为紧密联系的世界历史。⑤
正是依据宏阔解读与把握历史的“通观”,吴于廑先生放宽视域,打破历史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历史如何发展与融汇成为“世界历史”作了诸多睿智独显、见解精深的探索。
对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之冲击的探讨,是吴先生在以“通观”审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他认为,在近代以前,农耕时节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因此,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出自农耕世界,本能地把以战车、骑兵征讨、蹂躏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看做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样的歧视甚至影响到近代的西方人。不破除这种偏见,“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⑥在吴先生看来,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形成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并发生各种内部、外部的矛盾,由此形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⑦由此,吴先生对欧亚大陆自古代到公元13、14世纪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三次大冲击浪潮,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与解读,并阐述了这些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的积极意义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这些冲击,“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如农耕民族学到了游牧民族的战车与骑射之术。后者从前者学到的东西更多,如金属冶炼和器物制造等方面的知识,从而产生巨大的客观影响。他指出,蒙古人、突厥人和帖木儿的战争征服带走了很多工匠,本为供应生活和战争需要,但是:
发展着的历史却通过这一点,当事者的他们所无从意识到这一点,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⑧
在吴先生看来,游牧民族的军事征服,对农业民族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摧残,但随着他们在被征服地区的定居,都必然要被农业民族的文明与文化所同化。因此,他们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各民族之间封闭自守的状态,“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⑨
不过,吴于廑先生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相关的学术思考中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与“归化”是世界历史酝酿的一个重要进程,但“农本经济”本身带有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属性,要让建立在其上的各地区、各国的历史摆脱孤立发展演进的状态,逐渐演绎起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世界历史”,还有一段必须跨进的历程。这一历程是在16世纪前后的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西端率先发轫的,主要表现为封建的“农本经济”转向商业和航海的高涨并由此开辟出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而突破农耕世界的闭塞,逐渐将整个世界联结起来。基于这样的认知,吴先生又对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作一宏阔的辨析,着重从西欧的变动来说明由农本到重商的历史转折。在他看来,在封建时代,东西方盛行的是以农为本的根本经济准则,“封建的欧洲各国也都建立在农本经济的基础上”。⑩中国古代有儒家的“重本抑末”主张、士农工商之阶层的划分,而中古西欧基督教对工商业活动的鄙视与教士、贵族、城乡劳动者的阶层划分,都足以说明,“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可谓概莫能外,是无间东方和西方的通则”。(11)同时,吴先生指出,中西封建农本经济都具有自足性质,具有持久的韧性,这是因为两者大体上都是为了满足衣食需要的耕织结合。不过,吴先生敏锐地看到了中西农本经济的差异。其中之一,就是对牲畜饲养的需要不同。牲畜饲养在农本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中国,因而农村的家庭纺织主要是毛织,养羊业由此在英国等地勃兴,埋下由农本向重商转变的种子。此外,西方封建农本经济远不如东方的那么有韧性,因而能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发展起商业和城市。商品经济最初并非是与农本经济对立的,城市也不是封建制度的对立物,但它们的发展逐渐对封建社会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侵蚀和分解作用,由“非对立的关系变为对立的关系”。(12)最终,在15、16世纪毛织业日益发达的英国和尼德兰,完成了“对封建欧洲农本经济的最初突破”。(13)他指出:
尼德兰和英国发生的上述变化,是沉沉农耕世界打破自足经济闭塞状态的起点,是资本主义进入世界历史的起点,在海道大通条件下开辟世界市场的起点。有了这个起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将逐一遭到突破。(14)
这个突破的过程虽然还需要两三个世纪的时间与物质生产方面的新的飞跃,但尼德兰和英国的变化,则是这个重大转折的开始。在新航路开辟和世界海道大通的最初两个世纪,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业的发展、殖民地的掠夺与开发,就构成了尼德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确立,人类的历史开始彰显出“世界历史”整体架构。由此吴先生强调:
这个变化是与西欧封建农本经济转向重商的过程,也是旧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过程相伴随的。这个变化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15)
在论述西欧从农本向重商的经济模式转型中,吴于廑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实际上是“农耕世界开始转向工业世界的行程”,(16)毕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重商主义的推行,是以工业的发育与成长过程为前提的,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个进程的拓展。因此,他进一步切入到西方的农耕世界中,去探究工业世界的孕育。吴先生认为,农业是商业和工业的基础,西方的重商主义研究者常常将两者对立起来,“看不到新旧时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农业是社会生产的基础,“没有农耕世界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前提,重商主义为之前奏的近代工业世界,就不可能出现”。(17)他通过对英国、尼德兰的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和生产剩余量的增长,论述了商品交换尤其是毛纺织业和采矿、冶金等其他乡村工业逐渐萌生与勃发的状况,进而论述了以此为端绪的不断向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及其最终对工业革命的促成。由此而建构的工业世界,既“是生产节奏紧密、时间感很强的世界”,同时“是技术的世界”,更是一个“不断机械化、不断追求工效的世界”,这就使它带有最大限度地追求收益、无止境的膨胀扩张、不断地驾驭和改造自然的鲜明趋向,使得它不仅最终从生产生活节奏缓慢、自给自足、不求时效、顺应甚至是崇拜自然的农业世界脱颖而出,而且势必对仍然处于这种状态的非西方的农耕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18)这样的冲击是一个“对外扩张的世界”对一个“固守闭塞的世界”的冲击,是两种文明层次的世界的碰撞。先进的工业文明拥有历史上的游牧文明所没有的强大的经济与技术的扩张力量,农耕世界无法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
接下来,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如何应对西方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呢?这自然也被吴于廑先生纳入其“通观”的考量之中。他不仅阐述了英国工业革命促使法、德、俄三大国告别传统农本经济而跨入西方工业世界的历程,而且对奥斯曼土耳其、萨菲伊朗、莫卧尔帝国、中华帝国在冲击下的经济变动、政治改革和民众起义都逐一审视。他认为,直到19世纪末,尽管这些国家的农本经济遭到摧残而发生变异,近代工业开始萌发,观念层面也多有变化,且发生了程度不一的政治改革,但对西方挑战的回应,“都还没有找到一个切合自身历史的途径”。(19)唯有日本主动地迎接挑战,“作出成功的、合乎历史趋向的反应”,通过明治维新而变革政制、兵制和传统的农本经济迅速进入起于西方的新兴工业世界。(20)
通过探讨,吴先生在总结时指出:
能从根本上变革传统农业体制者,反应多有成效,否则反是。这里说的成效,就短期而言,是适应近代工业化的需求,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世界拓宽道路;就长期而言,是推动农业自身的工业化。……
历史上孕育了工业世界的传统农耕世界,不仅在工业世界的冲击下发生根本的变革,而且最后也要融入工业世界。这一前景已不在远。(21)
这一论述不仅是对亚欧农本国家对西方工业世界冲击之反应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也是对人类世界终重建构起完整的“世界历史”的一个前瞻。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出如此前瞻时,吴先生也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予以了揭露和批判,并在其中寄寓了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走向的人文关切:
兴起于西方的近代工业世界,是资本主义制度支配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利润追求,决定近代工业世界的无限扩张,也决定进入工业世界各国之间的无尽无终的争夺。近代工业世界是一个少和平、多暴力、少公正、多凌夺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在期待着历史的根本变革。(22)
吴于廑先生的上述一系列研究,总计不过十万字,但却以其博大的历史视野,聚焦于欧亚大陆各地区、各民族、各国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它们之间挑战与回应的交往方式的演进,勾勒出人类从史前时代到当代的社会文明的演进、发展与更新。这一探求“世界历史”建构及其内在逻辑与客观规律的“通观”,集中彰显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崇高宏阔的学术境界:从整体全局的角度,来全景式地梳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与大趋势。
吴于廑先生依据其“通观”所作出的这一颇具建树性的研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的研究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众所周知,在建国后开始起步的我国世界史研究,由于前苏联史学界理论僵化的影响,一直处在“五种生产方式”论的束缚之中而难以拓展。此外,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路线的干扰,特别是在“文革”动乱的摧残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积累被湮没殆尽,出现“花果飘零”的惨景。改革开放后,虽说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为史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春天,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和以革命话语编纂世界历史的做法,开始遭到史学界的反思和质疑。但是,在当时,国门才刚刚开启,我们与国外的学术联系与交流不多,对有关西方历史文献资料学术信息与动态尚掌握不够,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路径仍待探索与开拓。同时,原来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僵化的理解、甚至是将之教条化、语录化的做法依然存在,史学界仍旧面临着思想解放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新旧学术转型的境况下,一批前辈前驱先路,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斩棘拓荒,破冰起航,以其卓越的建树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启了不断拓展的宽广路径。吴于廑先生无愧为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以历史“通观”所作提出来的学术创见,在当时的史学界可谓振聋发聩,启人心智,对于史学界破除传统的理论桎梏,了解西方的最新学术走向,从而全局性地思考历史研究的路径与要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事实上,由于吴先生试图用“通观”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来梳理与考量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与横向联系,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及其中所蕴含的学术境界对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也是普遍性和全局性的。尽管各领域的学者在自己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并非都直接从他的学术建树中获取借鉴与营养,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都明显地或潜在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受到了熏陶。而他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力图贯穿其历史“通观”的世界通史教材,更为培养世界史研究的后辈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
经过史学界同仁三十多年的努力进取,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有了明显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上,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接续涌现,人才培养体系日益完善。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将世界历史升格为历史学的一级学科,更为这一学术领域拓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重温吴于廑先生历史研究的“通观”,领悟其对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这些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苗头:其一就是宏观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这在经济形态史、现代化史、全球史、文明史、生态史等领域尤为凸显;其二就是微观史学的盛行,这主要表现在众多领域中个案研究的不断精致与深入。这样的学术态势,无疑是我国世界史研究日益深化的凸显标志。不过,究竟如何研判这两种旨趣不同、路径相异的研究范式的价值,如何将两者有机地整合起来开拓出更为合理的研究路向,还有待于史学界去作进一步的探讨。
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目的和功用,就是要通过对人类社会过去所发生的各种历史现象之深层因果联系的探讨,揭示其中所寓含的历史的统一性和必然性,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客观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为人们把握现实与前瞻未来服务。一般将对历史的研究划分为宏观与微观(或许还可加上两者之间的中观)两种。宏观研究也可以叫做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依据史事对某种历史进程、脉络进行全面阐述与把握。而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的区别,虽然这两者的学术范式不同,但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能将之机械地割裂开来,否则不仅难以作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且常常会误入歧途。
微观研究无疑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基础,也是宏观研究的必要前提。这是由历史研究的“求实”、“求真”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只有依据翔实的史料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解读乃至细节上的精确辨析,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对诸历史现象获得接近于历史实际的认识。也只有在厘清若干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某一领域作出比较准确的宏观审视与演绎,进而从中揭示出某种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微观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宏观考察,历史研究也必然会失去学科存在的特性与学科发展的基础。因此,严谨扎实的个案“求真”乃至细节“还原”应该是历史学家的分内职责和研究起点。
但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微观研究绝对不是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对历史规律性的求索,必须在若干的历史个案乃至细节中去梳理深层的历史经验,透视历史事态的内在机理。要做这样的研讨,就必须突破局部、点面的微观探究层次,升华到宏观研究的台阶,进行远阔的比较、归纳与总体性抽象。如果仅仅停留在微观研究的层次,历史将失去其应有的丰富含义而成为若干互相无关之事物的简单组合、若干缺乏连接的细节的堆积。这犹如一堆打造好的门梁、门窗和砖石,如果缺乏高屋建瓴的设计与错落有致的建构,绝对成不了一座宏大规整的楼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的不少著名史家如W.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I.沃勒斯坦等都十分重视宏观历史研究的重大意义,更有人形象地强调:“建筑历史学的大厦不仅需要优秀的砌砖工人,也需要设计师。”(23)也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的史学家在对史学趋势流变进行反思时,指责当下的“新史学”已经违背了费弗尔与布洛赫等当初探求“总体史”或“长时段”历史的主旨,而片面陷入该学派末流琐碎化的歧路。有人就批评说,“总体历史这一概念在今天成了问题……我们的史学到了碎化、多元、膨胀,直至追求新奇的时代”。(24)这种历史研究琐碎化的趋向,在当下更因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流行而愈为明显。倡导“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不仅力图以所谓的“语言的转向”来解构历史存在的真实性,而以质疑“宏大叙事”、鼓吹“小叙事”的路径来贬抑探求规律的整体综合的研究。由此,“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均变成过眼烟云”,历史甚至“变成符号的游戏”。(25)
这些年来,随着史学理念的不断更新与文献资料的愈发增多,微观研究在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成就,精于某一断代、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专家逐渐增多,一些探讨具体问题的著述也因其精审的实证运用乃至细节钩沉而饮誉学界。然而遗憾的是,在相当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进行整体综合之宏观历史研究,并未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微观研究常常因胸襟狭窄、目光短浅而满足于史实的机械罗列和现象的简单叙事,疏于对历史事实之内在机理的深层解读、难以从现象观照升华到对某种规则乃至规律的认知,最终难免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样看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在研究范式上,既需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来审视若干的“个案”问题,不断深化和夯实微观研究;也需要打破条块分割、相互孤立的研究格局,从宏观的整体综合考察中探求各地区、民族、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事实上,吴于廑先生以“不限断代、不限地区国别的通观”来考察“世界历史”,已经为我国世界史研究标明了这一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术前辈,也以自己的精湛研究,应和了吴先生在断代、局部地区和国别的“通观”,同样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标明了这一方向,如林志纯先生以“古典城邦”为聚焦的世界上古史研究,罗荣渠先生以“现代化”为主线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马克垚先生以“封建经济形态”为轴心的世界中古史研究等等,都是旨在比较与综合考量若干“个案”的研究上,揭示某一段大历史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老一辈史学家所建构起的学术典范,对于我们清醒地认识世界史研究的主旨和路径,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人类历史既是一个社会运动前后接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数现象存废兴替的过程。史海无涯而生有涯,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即便是穷毕生之力而勤奋为之,也常常难以妥帖地认知和把握整体的人类历史。即使是从总体上把握某个时代、某个地区和某个大国的历史,也有着很大的难度。中国史的研究既有着悠久的本土史学传统的支撑,也最先在近代新史学中发轫,在资料与信息占有与个案、细节的诠释上乃至整个学术积淀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但中国史的同仁们,也常常对宏观研究“敬而远之”,以至于史家对之多有忧虑。(26)而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要在起步较晚的中国的世界史领域做宏观历史研究,难度则可想而知。但是,能否把两种研究范式有机地整合起来,将微观研究升华至宏观研究,毕竟是历史研究的主旨与方向,决定着历史学的未来发展前景,需要有人来尝试践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于廑先生“通观”研究所彰显的学术勇气尤为令人钦佩。更为可贵的是,吴先生始终提倡立足于微观史学的“通观”考察,反对那种假象臆断、空泛荒疏的历史模式归纳与建构。为此他强调:
通观必须以对一个一个的关键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我们自己要研究,还要熟悉别人专门研究的成果和著述,尽管他们不一定是从较为宽阔的广度来考察的。没有这个前提,通观就会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会是一种比较透彻的、在大小轻重之间能够取舍得当的通观。要做到这点,还必须付出认真的、艰苦的努力。(27)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吴先生在他所作的上述一系列研究中注意文献征引、史实辨析和域外学术成果的批判借鉴。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注重微观研究,认定“历史的专精和综合”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因为在历史研究中:
分目愈细,所作的研究愈益专精。专精的成果愈多,成果的总触及面就愈广,作比较完整的综合考察,也就愈有条件。专精和综合是相辅而行的。没有专精,即使为一个细目作理论概括都会有困难,更不论作广泛的合符科学的综合。同样,不作综合,就不易确定一项专题细目在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更不会由综合概括中发现某些专精的不足从而引发更专、更深入的研究。(28)
在提倡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时,吴于廑先生尤其强调分目专精的研究虽然是历史研究的基石,但绝对不是历史研究的终点。只有将其升华至综合考察,才能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进而推动历史学的不断进步:
专门研究的积累,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就构成历史某一局部、某一阶段乃至更广泛范围的全貌……为专门而专门,以专门为极致,确实,不一定能产生好的历史。历史学应当在不断的专门研究和不断的综合考察中前进。一些好的历史著作,由之提出的一些已获公众接受并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是概括综合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广搜史料、就一人一事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29)
同时,吴先生也理性地认识到,既然综合的宏观研究是以专精的微观考察为基础的,就不可能奢求一蹴而就地完成某种探讨而建构起永续性的终极成果,而需依据的微观研究的拓展与诸多新的专精成果来对之进行审视与参照。这是因为在时间、空间上大跨度的宏观研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疏漏与不足,必须有一个不断修正与完善的过程。他指出:
在专门史的研究中作出共性与一般的概括,是有条件的,条件在于史料实证的充分。一旦条件改变,例如发现新史料,新实证,不论这种新的发现是在加强还是削弱以至否定已作的概括,都要据新的发现作新的探讨,再据探讨的新的结果,对已作的概括作相应的补充、修改以至更正。这种改变是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概括的完善化。不能因概括不完善而放弃概括。(30)
整体综合的研究在专门史中尚且需要依据新的实证研究来做进一步的参照与完善,那么想要在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中单凭个别史学大家的探讨很快就能做出科学的诠释,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吴于廑先生对其世界历史的“通观”研究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指出:“世界史所要求的历史全局的综合,比之断代或国别,更难一举而尽善。不能尽善,则唯有求其逐步接近于尽善。”因此,吴先生提倡宏观与微观研究密切合作,认定“两者分工,不可分道”。(31)同时,他逐渐将视野聚焦在15-16世纪的世界史领域,组合学术团队展开协作研讨。由此可见,吴先生的世界历史研究的“通观”,与其说是建构了一种科学的学理模式,不如说是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学术路径。他所孜孜求索的崇高学术境界,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标立出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不断鼓舞和鞭策着后辈学者向着这个宏伟的目标奋进!
注释:
①《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6页。
②《吴于廑文选》,第276页。
③《自传》,《吴于廑文选》,第454页。
④《世界史前景杂说》,《吴于廑文选》,第35页。
⑤《自传》,《吴于廑文选》,第455页。
⑥《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第81页。
⑦《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第82页。
⑧《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第82页。
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第83页。
⑩《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89页。
(11)《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91页。
(12)《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91页。
(13)《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109页。
(14)《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110页。
(15)《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吴于廑文选》,第116-117页。
(16)《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吴于廑文选》,第119页。
(17)《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吴于廑文选》,第121页。
(18)《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吴于廑文选》,第139-147页。
(19)《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吴于廑文选》,第173页。
(20)《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吴于廑文选》,第176页。
(21)《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吴于廑文选》,第177页。
(22)《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吴于廑文选》,第177页。
(23)[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24)参见陈彦:《法国的“新史学”现象》,《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
(25)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3页。
(26)李卫民:《深入钻研马列主义,提高宏观史学研究水平——张海鹏研究员访谈录》,《晋阳学刊》,2011年第4期;章开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7)《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吴于廑文选》,第86页。
(28)《朗克史学一文后论》,《吴于廑文选》,第274页。
(29)《朗克史学一文后论》,《吴于廑文选》,第275页。
(30)《朗克史学一文后论》,《吴于廑文选》,第274页。
(31)《朗克史学一文后论》,《吴于廑文选》,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