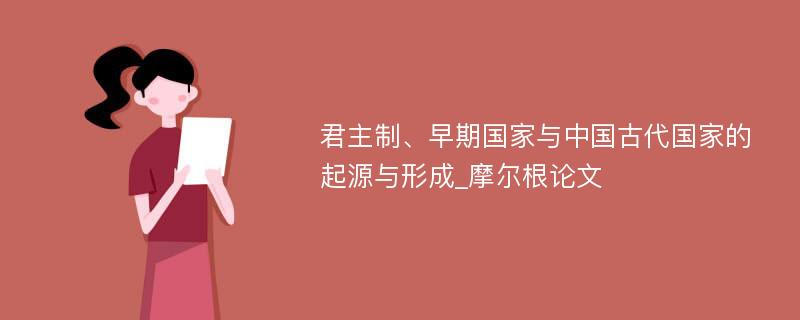
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起源论文,酋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2;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1-0005-07
近年来,在人们十分关注的对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采用了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等人的酋邦学说及其他一些人类进化新说。这对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在此问题上的解释系统造成了一种冲击。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这套理论尚存在着不少争议,但采用这类说法的学者越来越多,并逐渐蔚成一种风气,也是明显的事实。为了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有必要对于在此问题的研究中采用人类进化新说的情况进行分析与评估,同时借以发表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希望学术界同仁关注并予以批评指正。
一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我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所采取的一套理论主要来自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众所周知,恩格斯这部著作有关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基本观点及论证材料又大多来自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期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起源》的副标题即是《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古代社会》一书在解放以后也介绍到了中国,可以看出,恩格斯有关人类社会几个时代及其下面的几个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包括作为这些发展阶段标志的各种制度与技术发明的认定,氏族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根本区别,以及对国家产生的标志、军事民主制度和希腊罗马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等问题的论述,都与摩尔根的叙述相同或类似,只是恩格斯更加强调了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应当说,摩尔根与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理论在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其所构建的由原始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化体系在大的格局上,也基本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们的理论至今在国际人类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包括我国学者所进行的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讨论的深入开展,学者们也感到他们理论中某些环节或个别结论有不够严谨或不够周全之处。其中为不少中外学者共同指出的一点是,对于原始社会所有的氏族组织,在摩尔根的笔下,都基本上是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结构,处于“无差别、无矛盾的和谐的境界”,这同一百年来人类学所观察到的大量个案所显示的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等级、特权、物质资料占有的不均,不同集团乃至个人之间政治影响力和权力的不平等,在前国家社会的许多实例中都明显地存在着。[1] (p260),[2] (p35)“摩尔根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将易洛魁的氏族与早期希腊和罗马的氏族等同了起来(易建平引塞维斯语)。”[3] (p139)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起源》中作为国家产生的例证而列举的古希腊、古罗马和日耳曼国家的产生,对于人类最早产生的国家来说,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由这几个国家产生而归纳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即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是否对于所有国家的形成都一概适用。这里,有关论述无疑更直接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对于此,不久前发表的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明确表示,《起源》中提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之一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一条,“对于古希腊罗马来说也许是适用的,而对于其它更为古老的许多民族则有一定的局限性”[4] (p7)。
为了克服摩尔根对于原始氏族社会这个长时段历史时期笼统而过于简单化的描述造成的缺陷,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主要是一些美国人类学者,如埃尔曼·塞维斯(E·Service)和莫顿·弗里德(M·Fried)等在总结摩尔根以后世界各地的一些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结果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早期人类社会进化新说。这套新说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摩尔根的进化理论,却对之做了重要修正,修正的要点,即是在摩尔根认为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加进了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在各个具体的人类进化新说中,尤以塞维斯的主张最为引人注目,其将人类社会自发生至国家产生所经历的社会组织共分为四种类型,亦即四个连续发展的进化阶段,它们是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其中游团是人类处在狩猎与采集经济时期的社会组织,是一种最简单的、小规模且人数不固定的流动性的社会组织;部落即平等的氏族社会组织,已经进化到种植作物与驯养家畜的阶段,由父系或母系的世系群组成,实行外婚制,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平等的;酋邦即上面提到的不平等的氏族社会,其最大的特点是各地方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尖锥形的分层的社会系统,处在尖椎顶端的酋长通常被认为是与整个系统人们的共同祖先血缘关系最近之人,职位世袭,其他社会阶层人们的地位则依其与酋长亲属关系的远近而定。凭借这种集中的权威,酋长领导着一个常设机构,负责组织整个酋邦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由于社会各成员在政治上已分别出不同的阶等,他们在经济生活中充当的角色亦显示出很大的差异,部分上层人物占有更多的消费品已是司空见惯之事。这样的社会无疑已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了,虽然这个社会还维持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
以上三个阶段都属于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这样设计的社会发展序列,使得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密,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也显得比以往的说明更加合理而易于为人接受。以此缘故,塞维斯的理论,尤其是他的酋邦理论得以在学术界很快地风靡开来,被认为是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及其进化的一种较为准确的概括而被广泛应用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之中。
二
塞维斯的理论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而更臻于成熟。其被介绍到我国的时间亦不算晚,198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的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便向国内读者比较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塞维斯的这一理论。张先生并根据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及考古发掘工作的了解,将塞维斯的四个社会进化阶段与中国考古学者习用的社会分期加以对照,列为下表:
文化名称
新进化论
中国常用的分期
旧石器时代
游 团
中石器时代原始社会
仰韶文化
部 落
龙山文化
酋 邦
三代(到春秋) 国 家
奴隶社会
晚周、秦、汉
封建社会(之始)
张光直认为:“由上表看来,中国考古学在一般社会进化程序的研究上,提供了一些新的有力的资料。”[5] (p52)
稍后,我国人类学暨民族学者童恩正在其所著《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更将塞维斯的上述社会组织划分,作为其所认定的人类社会经历的四种政治组织正面介绍给读者。不过本书对这几种政治组织归属的认识显得与塞维斯有些差距,其称“人类社会可以区分为四种类型的组织,即游群组织、部落组织、酋邦和国家,前二者属于原始社会范畴,后二者属于阶级社会”[6] (p216)。我们知道,包括童恩正本人亦承认,塞维斯是将酋邦划入原始社会的。这或许只是童氏最初的看法,其以后的著作似乎对之已有所纠正(见本文后面有关酋邦的讨论)。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结合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也开始了。谢维扬教授1987年发表的《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大概是应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第一篇论文。文章表示不同意按照摩尔根所描述的国家经由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路子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问题,认为中国传说时代人们共同体的政治组织与摩尔根所描述的易洛魁和雅典、罗马的部落联盟有很大的不同,是属于非部落联盟类型(作者称之为“部落联合体”),可名为“酋邦”。文章比较了中国传说时代的部落联合体(亦即酋邦)与部落联盟之间的区别,讨论了夏代早期国家通过对酋邦制度的改造而形成的过程。文章最后强调,由于中国早期国家经由酋邦而不是经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事实,决定了中国早期国家从一开始就较欧洲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而缺乏民主的传统。[7]
之后,谢维扬继续从事酋邦及中国早期政治组织问题的研究,于1995年写成《中国早期国家》一书出版。这部著作可看作是《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一文有关论点的进一步申论。除此之外,该书尚有以下值得注意之处:一是强调了理论更新对于国内学者的重要性。作者批评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理论语言上呈现‘老化’的现象”[2] (p15),指出国际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在早期国家理论的研究中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讨论摩尔根之后在早期国家理论中出现的各种新的构思。二是在酋邦理论之外,继续引进国际学术界有关早期国家的概念并对其中一些问题,如早期国家的定义、早期国家形成的原因、早期国家的类型及早期国家演进的几个阶段等进行了讨论。作者引用前苏联学者哈赞罗夫(khazanov)的说法,认为“早期国家是指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国家,是原始社会解体后的直接继承者”[2] (p44),同时按照国际学术界组织《早期国家》一书编写的克烈逊(h.claessen)和斯卡尔尼克(p.skalnik)有关早期国家阶段划分的意见,相应地将我国自夏至春秋战国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夏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发生期,商周为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春秋战国为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型期。其三,认为征服活动对于早期国家,特别是专制主义类型国家的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酋邦和酋邦转化而来的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征服与吞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家形成的酋邦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2] (p211)
谢维杨之外,尚有不少学者,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表示了对塞维斯进化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酋邦理论的兴趣。他们或是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或是从考古学与历史学角度,甚至从政治学与法学的角度援引塞维斯等人的理论对各自学科所涉及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涉及我国前国家时期社会形态及其向国家社会演进一类问题的作者及他们所撰写的文章可以举出龚缨晏的《略论中国史前酋邦》[8]、叶文宪的《略论良渚酋邦》[9] 和《部落冲突与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国家的契机》[10]、戴尔俭的《从聚落中心到良渚酋邦》[11]、刘莉的《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12]、陈淳的《酋邦的考古学观察》[13] 及《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14]、何国强与曾国华的《从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看中国国家的起源》[15] 等。这些文章大多将我国夏以前一段历史时期的各种考古文化,包括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乃至北方更早一些时候的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视为酋邦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个别学者(如陈淳)更将夏代亦视为酋邦。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文明产生前的关键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国家孕育的时期。谈到由酋邦向国家社会的演进,多数学者又都强调了征服战争或各酋邦集团的冲突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曾较早将塞维斯社会进化理论介绍给国内读者的童恩正先生亦有意识地将酋邦理论运用于自己对中国早期文明及西南古代民族等问题的研究中,先后发表了《中国北方与南方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16]、《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17]、《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18] 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从这些文章的题目看,它们并不是专门讲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的,但却包含了不少这方面的学术见解。如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一文中,作者指出,约当公元前3000纪的后半,中原龙山文化的总体状况已经可以与文献记载的五帝时期的历史相印证,其时居民逐渐以部落为主体,以“城”为核心,发展成古史中所谓的“国”或“邦”,这应该就是指国家最早的形式——酋邦。其后,以黄帝为首的酋邦逐渐屯兵周围的异姓部落或酋邦,构成更大的实体,到禹时,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而同时期的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虽也进入到文明的前夜,创造了酋邦组织,却因人们居处的分散及生活方式的差异等原因,未能走出酋邦社会组织的阶段而向国家发展。此外,作者还谈到了中原国家的发生与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及组织大规模治水而导致的对集体劳动控制有关。在《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中,作者借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再次提到摩尔根在上个世纪所提出的原始社会的发展模式,即所谓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部落联盟、国家的直线发展序列,目前已基本为西方学术界所摒弃,比较流行的是由塞维斯等人提出的另一个方案,即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发展模式。由此,作者继续概括性地阐释了“酋邦”这一新进化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指出:“我国学术界是否应当接受这一概念,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一些学者设想有这么一个过渡阶段存在,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理论、事实依据的。”
当然,也应当看到,上述学者十分感兴趣的人类进化新说及酋邦理论,目前还未能在我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相当部分学者对之还感到陌生,或者认为酋邦制只是某些民族在国家形成前夕实际存在过的一种制度,“是通过对一些特定的民族和地区考察后归纳提出的”,“从多线进化的观点看,很难认为古代诸文明古国都是通过酋邦这种形式,由史前走向文明的”[4] (p13)。更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在中国使用酋邦这个名词,认为不符合中国考古的情况。[19] 看来,这种主张多来自中国考古学界。
三
要使学界就是否采用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及四阶段人类进化新说达成一致意见,目前似乎还很难做到。好在现在已经有了一种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这使学者能够对这种来自西方的学术观点采取较为平和乃至兼收并蓄的态度,也使我们有可能对这种理论及应用这种理论进行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探研的学者们的主张进行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我们认为,以酋邦理论为核心的人类进化新说对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其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的学说不是对立,而是补充说明与部分修正的关系。从前面的叙述看,恩格斯据摩尔根提出的人类早期社会发展的模式确实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首先是原始社会阶段的划分。如有学者所说:“虽然,原始社会在摩尔根那里被划分为六个‘民族学时期’,从低级蒙昧阶段、中级蒙昧阶段、高级蒙昧阶段到低级野蛮阶段、中级野蛮阶段、高级野蛮阶段,然而,从平等的‘氏族’(‘gentil’或者‘clan’)社会向一个权力更为集中、不平等(世袭阶等制)、出现新的财产形式等等社会现象社会发展的这一过程,在他那里却没有相应的阶段划分。”[3] (p151)这就难免给人一个“从原始社会到政治社会的政治变迁,相对而言是突然发生的”[3] (p151)(易建平引塞维斯语)这样的感觉。或许有人会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在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野蛮高级阶段,除了存在着自由人和奴隶主的差别外,还存在着富人和穷人的差别,存在着“各个家庭首长间的财产差别”,这不也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吗?这与现代人类学者提出的不平等的氏族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还要另外提出一套酋邦理论呢?几年前笔者在向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2001年11月)提交的论文提纲里也有类似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到的野蛮高级阶段,包括他们认为处于这一阶段的古希腊、罗马的前国家社会阶段的社会组织,已明显具有了社会分层(分阶级)的现象……这个阶段,实际同所谓酋邦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实不必为着一些时兴的名词概念抹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真实内涵。”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应当说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是,恩格斯所说的野蛮高级阶段出现的那些社会不平等或社会分层现象,仅仅出现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并且是伴随着氏族组织结构的崩溃而产生的,即如恩格斯所说:“由于生产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同它对立的”。[2] (p168)而现代人类学者所说的酋邦或曰不平等的氏族社会本身即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氏族制度乃是一种稳定的社会存在,只是这种氏族由内部平等变作了不平等,变成了一种“尖锥形的分层的”氏族结构。现代人类学者根据这种氏族结构的社会在各地被广泛发现的事实,推论它应是早期人类社会经历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显然是对包括摩尔根和恩格斯在内的早期人类进化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
谈到酋邦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实践意义,我们也可以对之做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使用酋邦理论较之使用“军事民主制”、“英雄时代”等概念,确实更有利于解决我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疑难问题。事实上,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对于我国古代前国家社会是否存在着“军事民主制”,是否可以称得上是“英雄时代”本身就存在着争议,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国家由所谓“军事民主制”或“英雄时代”过渡而来的解释也并不给人以十分贴切的感觉。我们倒是强烈地感到,上述人类学者所勾勒的一幅酋邦社会的基本图景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我国早期国家产生以前那样一种“天下万邦”的政治格局十分类似。近年各地不断发掘出的考古资料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所谓“酋邦”对应于我国古代“天下万邦”的“邦”,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普遍提到的“族邦”,是完全讲得通的。童恩正先生指出这一点是十分有见地的。这十分有利于认识文献记载的我国夏代以前的一些“古国”的性质。进一步的研究则可以发现,我国早期国家即是通过众邦(众多族邦或酋邦)的不平等联合而实现的,这样一种国家形成的路子及国家组织形式也与当代人类学者提供的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由酋邦联合而成的早期国家的实例十分类似。总之,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国际人类学这一新的研究成果,为了更卓有成效地探索我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的路径,我们应当自觉地更新理论,调整自己的思路。
当然,我们主张采纳塞维斯等新人类社会进化论者的酋邦理论,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提出的所有其他有关人类进化的主张全盘接收,他们的主张并非全部正确,更非都全部适用于古代中国。另外,对于目前国内学者运用酋邦理论对我国古代社会作出的解释,包括他们对酋邦理论本身的理解,我们也不都是全部认可的。我们发现,由于国内利用酋邦理论尚属起步阶段,学者们对于酋邦理论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很大差距。按照塞维斯等人的本意,酋邦不过是一种不平等的或有阶等的氏族组织,可是不少人却将它归入部落联盟的范畴。也有人认为这种解释不对,说酋邦只能叫做“部落联合体”,其与部落联盟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酋邦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童恩正认为,塞维斯指出的酋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阶段”[1] (p344);可是,也有学者认为在由前国家社会向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只有部分地区经历过酋邦的社会组织,另一些地区经历的则是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在将中国古代的情况与酋邦理论相对应时,学者的理解更显分歧,有称古文献提到的“天下万邦”或“天下万国”中的邦、国为酋邦的,有称黄帝或尧、舜、禹部落联盟(或部落联合体)为酋邦的,还有称先周时期周后稷与羌人(有邰氏)的部落联合体为酋邦的(宋镇豪执笔的有关酋邦的学术见解,与本书前面部分不尽相同)。[4] (p488)在酋邦(及由之过渡到早期国家)是否具有个人独裁即专制的性质上,学者间也存在着不同认识。所有这些,都需要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才能缩小分歧,求得理论与实际的更好的统一。
四
我们赞同塞维斯的酋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种理论能够解决我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的全部问题。就我们自己的感觉,目前研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酋邦是指一种不平等的氏族结构的话,那么这种氏族结构在我国古代国家形成以后却继续被保存下来,至少我国夏商周三代都还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氏族组织,都仍然是一种“天下万邦”的局面,它们与三代国家相互依存,或者干脆就是三代国家的下属单位,一直到春秋战国以后才趋于消泯,这种现象如何把握?过去,一些学者往往因为这个问题难于把握而对三代国家的性质产生模糊认识,甚至有学者提出三代并非“真正意义的国家”的看法。[21] 在将酋邦理论介绍给国内读者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张光直先生虽然在自己所拟就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分期表中将夏商周三代划入了“国家”的范畴,却又同时表示,这个分期事实上还存在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也就是“三代,尤其是夏商两代和西周的前期,究竟应当是分入酋邦还是分入国家的问题”。他以商代为例说,按照国外一些学者的意见,国家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血缘关系在国家组织上为地缘关系所取代,二是合法的武力,然而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商代文明,则“前者不适用而后者适用”。也就是说,按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取代这一条说,商代还够不上国家的水平,而按“合法武力、分级统制、阶级”这些条件来说,商代又显然合乎国家的定义。这样,就不免“使上举社会进化分类里酋邦与国家之间的分别产生了定义上的问题”。张先生不愧为大家,他提出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把殷商社会认为是常规以外的变态,如Jonathan Friedman把基政权分配于血缘关系的古代国家归入特殊的一类,叫‘亚细亚式的国家’(Asiatic State);另一种方式是在给国家下定义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考虑为分类基础的一部分,亦即把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作重新的安排。”[5] (p54)
张先生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方式,我们基本赞同。一则,把中国古代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国家形式归入特殊的“亚细亚式的国家”范畴,等于主张不必按上述国外学者提出的两个条件作为国家形式的标准,古代中国这样拥有合法武力但未破除氏族结构的政治组织也可以是国家。对此,我们举双手赞成。不过张先生谓这样的国家为“特殊”类型,即认为所谓“亚细亚式的国家”只能被视作“特殊”,此看法则有待商榷。二则,从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出发重新考虑给“国家”下一个新的包容性更广泛的定义,这个主张也是讨论中的应有之义。像上古中国这样的国家,完全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原生类型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与组织形式应更具有普遍意义,而古希腊罗马乃非原生类型或次生的国家,它的产生应不具有典型的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根据古代中国及其他一些文明古国的实际情况对国家的概念做出更新的界定。只有在这一步工作做好的基础上,再来考虑酋邦理论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才能给予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更好的说明。
我们了解到,现在国际人类学界对于中国这样一些最早进入文明的古国有一个新的归类,叫作“早期国家”。这种称呼和归类应当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遗憾的是,他们并未能很好地将上古中国历史的特点充分考虑进去。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较早地将国际人类学者有关“早期国家”的概念介绍给国内读者,其积极引进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同样遗憾的是,他也没有很好地虑及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没有根据上举张光直先生及其他许多中国学者一再强调的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氏族血缘组织这一特点来对国外学者提出的早期国家的概念进行补充和匡正。其实在谢书发表之前,已有赵世超教授更早地将西方及前苏联学者使用的这一概念应用于自己对西周国家的研究中。他称西周为早期国家,是因为认识到它的“旧血缘关系不仅依然保留,有时还对政治起支配作用”[22]。这个看法无疑更接近于实际。除赵世超外,还有相当部分学者在论及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时自发地使用了“早期国家”的术语。他们使用的这一术语并非从国外人类学者那里借鉴而来,然而却更贴近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如何兹全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使用了“早期国家”的提法,其后,又在《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阐述:“早期国家的特征是,社会已有了阶级分化,氏族部落内部已出现贵族显贵家族,也有了奴隶和依附民,王的地位已经突出,有了王廷和群僚,但氏族部落组织及血缘关系仍是社会的组织单位。”[21] 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将中国早期国家的上限仅设置到商王盘庚时期,并且称早期国家非“真正意义的国家”,这一看法固然不能令我们接受,但他明确将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分作两步,一步为早期国家,一步为成熟国家的论点,还是具有很大启发性的。
最后,与酋邦理论及早期国家理论都有关系的一个问题是,酋邦是如何过渡到早期国家的?上举谢维扬及好几位主张采取酋邦理论的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各酋邦之间的征服战争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谢维扬教授出于将中国这类早期国家政体区别于古希腊罗马国家的考虑,更着力强调由酋邦转化而来的国家的形成同征服与吞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这样一种“以社会本身向外部扩张为主要动因”的国家的形成,同“以社会内部的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的形成,是两种不同的国家产生的模式[2] (p211~212)。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也是有待商榷的。应当说,任何一种形式的国家的产生,其根本的动因都来自社会内部,来自社会内部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对立。中国古代国家也不例外。战争,包括对外征服战争,只是促使国家产生的外部原因之一,有的国家的产生受战争影响的成份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则是其他一些因素起着主要作用。就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而言,文献并不止谈到战争一途,更没有将战争归为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主要原因。人们熟悉的大禹治水与夏代国家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关记载即是对上述说法的一种否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是认为过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的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两种途径的论述,更有利于解决酋邦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的问题。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过去已做过一些论述[23],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标签:摩尔根论文; 起源论文; 氏族社会论文; 文化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汉朝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人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