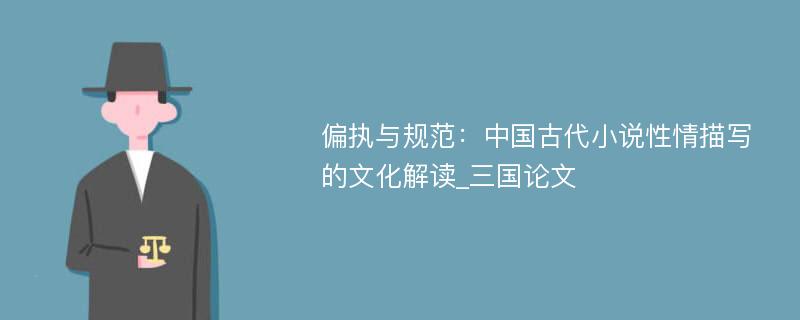
偏执与规范:中国古代小说脾气描写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执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脾气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8)02-0097-06
人们通常所说的“脾气”、“秉性”或“性情”,是个性心理特征的组成要素之一,在心理学上属于“气质”范畴。脾气的论定一方面依据情绪产生的速度,另一方面依据情绪变化的幅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遵从儒家“中庸”行为规范,提倡“中行”型的所谓“好脾气”做人行事;而在小说创作中,为确立并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过”与“不及”等人物偏执脾性的描写上。巴人在谈到“描写人物的手法”时指出:“习惯脾气的描写,也是映现人物性格的一种方法。”[1](P489)在小说写人过程中,脾气描写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然而,在长期以来的小说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脾性描写这一角度。中国古代小说关于人物脾气的描写既热衷于偏执性,又大体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规范,需要不断地进行阐释和解读。
一、偏执脾气描写的“五性”规范
中国人最喜欢用“五行”统筹下的“五性”思维来为人物的脾性归类。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卷九之《阴阳二十五人》即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把人的某些心理上的个别差异与生理解剖特点联系起来。这部文化典籍按照强弱,将阴阳分解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和平五种类型,每种类型具有各自不同的体质形态和气质。同时,该书还根据五行法则,把人分为“金形”、“木形”、“水形”、“火形”和“土形”,以其与不同的肤色、体形和气质特点对应。根据这种思想意识,人们将人物的脾性一分为五,是为“五性”。大致是,水性柔媚,土性厚重,金性骄纵,木性憨直,火性暴躁。按照“五行”与“五色”、“五方”、“五性”等“五数”范畴的对应关系,我们不妨对《三国志演义》的“五虎上将”的脾性作一大致的“五行”归属巡礼。关羽佩以“青龙偃月刀”及其“绿袍”,当属“木”,因木色青;张飞“性急如烈火”,自然属“火”;黄忠被认定属“土”,不仅是因其姓为“黄”,合于“土”分属“五色”之黄,而且还是因为“土”对应“性重”、“情厚”;判马超属“金”,主要是因为“金”对应于“五方”之“西”,而这位天威将军自西凉起身,同时,“金”色白,而这位英雄年少又常常身着“白袍银铠”;赵云之属“水”,首先是因为它来自常山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北),自然合于北方之“水”,同时大体上合乎“水”之“其性聪明,其情良善”德性。按照五行生克原理,他们之间的分工合作自然属于“相生”的一面,不必多言;而关于他们之间“相克”的一面倒需要作一寻绎。按照“五行”相克的逻辑次序,五虎将之间应当是关羽克黄忠,黄忠克赵云,赵云克张飞,张飞克马超,马超克关羽。虽然《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并不着意于依照“五行生克”原理来图解“五虎将”的所作所为,但我们却不妨按照“五行”视角来阐释其中的人物关系。关羽之克黄忠,主要表现在他瞧不起老将黄忠,小说嘉靖本第七十三回写他接到费诗送来的封赐印信,并问:“哪五虎将?”当来者告知他具体人物时,关羽生气地说:“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并表示不肯受印,经费诗一番劝说才肯接受。关羽之所以不愿与老将黄忠为伍,按照“五行”学说,就是因为他们属性相克。作者精心安排这一情节,意在有力地表现关羽的傲气和刚愎自用等人格缺陷。关于张飞克马超,可从第六十五回所写的“葭萌关张飞夜战马超”这件事来加以说明。本来,马超在张鲁幕下受人陷害,早就秘密写信给刘备希望投降他,不可能再发生两员虎将厮杀的故事。而小说为了强化两人的性格,却不顾这些历史事实,特意杜撰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闪眼夜战。小说写两人一开始斗智斗勇,“约战百余合,不分胜负”,张飞“不用头盔,只裹包巾上马”,又斗百余合,“两个精神倍加”。时近天黑,张飞不肯罢休,要安排夜战,马超也跃跃不相让,于是,他们“点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再战二十余合,仍不分胜负。于是,马超暗掣铜锤,回身便打,试图出奇制胜;而张飞则能敏捷地闪过。两军收兵,照样是输赢难决。最后经诸葛亮谋划授计,马超才被逼迫投降。通过这场漂亮仗的巧意安排,作者将两位虎将的神通和血性强化出来。另外,在第四十一回和第五十二回,张飞与赵云的敌对两度白热化,再说,张飞古城会与关羽的误会性冲突也多多少少地体现出“五行”彼此“相克”的一面,这一笔墨对表现张飞粗豪爽直的个性十分有力。如此看来,在人物脾性描写上,《三国志演义》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五行生克”的印记,另一方面,它又不生搬硬套“五行生克”的清规戒律。
将人物脾气归并入“五性”,最经典的小说当数《西游记》。台湾学者吴璧雍曾经指出:从类型人物的观点而言,五位取经人可说各自象征了一种气质:唐僧怯懦好哭,沙僧忧郁沉默,悟空善变好动,八戒懒散幽默,龙马则坚毅负责。作者并以五行之名分别代表取经人的性质:悟空属金属火,八戒属木,沙僧属土,唐僧属水。这种附会似的关系看似无稽,却成为各个人物的表征,造成了特殊的示意作用。[2](P443)
事实上,若按“五行”与“五性”对应学说,唐僧应属“土”,憺漪子(黄周星)谓其处在“中心”地位,而陆续收的三徒一骑“南火、北水、东木、西金”只能发挥“总以卫此中土”的作用。只要敦厚脾气的唐僧这位皇权授予的领头人作为一面旗帜在,取经队伍就会具有向心力,取经事业就能够顽强地坚持下去。但从唐僧怯懦爱哭而论,他又的确带有女性化的“水性”。相对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属“火”的孙悟空和属“木”的猪八戒之间最能体现相生相克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老孙动辄采取各种手段使“呆子”出尽洋相,呆子则把“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当作“耍子”,使得取经队伍内部充满了好戏连台般的热闹。另一方面,孙悟空通过戏弄呆子将其身上的“火”气轻轻松松释放出来,猪八戒则通过应付师兄的捉弄消解自身的“木”性。正是通过这打打闹闹的角色设计,作者给读者带来无穷诙谐幽默、轻松愉快的风趣。如果没有这一“火”一“木”的打打闹闹,《西游记》的意味将会变得索然许多。沙僧理应属于“五行”之“金”,有时又有“土”的特性,作者不时地有意以“金”“土”喻之,将其性情写成像“金”一样晶莹,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特点;又像“土”一样厚重,显示出厚德载物的本性。在取经路上,沙僧一方面帮助师兄除妖伏魔,另一方面又以一片丹心维系着取经群体的内部团结。面对师父的刚愎自用,沙僧能够凭其“木”性做到顺其自然,言听计从;他尊重孙悟空,经常苦谏唐僧不要咒念紧箍折腾师兄,又经常对师兄的“暴躁”施之以柔克刚,用“打虎还得亲兄弟”等古话劝其息怒;他理解体谅二哥猪八戒,经常接过行李担来替他挑一程,还经常婉言劝说八戒不要动不动闹“散伙”。对两个师兄闹矛盾,他更是不偏不倚地扮演起和事佬。在稳定取经队伍方面,沙僧这一角色不可或缺。另外,小白龙原本身居水渊,自然属“水”,他不仅任劳任怨地充当唐僧的坐骑,加快了取经队伍的行程,而且还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宝象国的“垂缰救助人”就是突出的例子。无“水”不足以成“五行”,无小白龙,取经队伍也不健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小说在为人物起“绰号”时,就赋予了其“五行”中的某一脾性。如,在《水浒传》中,作者通过给水浒英雄以“豹子头”、“青面兽”、“锦毛虎”、“扑天雕”以及“霹雳火”、“黑旋风”、“拼命三郎”、“独火星”等绰号,赋予他们以“猛兽”脾气、“烈火”脾性。又如,在《红楼梦》中,作者也善于通过人物之间互相起诨号,来概括人物的脾气特点,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如晴雯性情刚直,属于“火性”,第五十二回写平儿评价说:“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上来,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又如,在第六十五回,作者别具匠心地假借兴儿这个小厮之口,形象地写出了一系列人物复杂的脾气,其中,“二姑娘诨名儿叫‘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哎哟’一声。”显然属于“木性”;而“三姑娘的诨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则属于“火性”,等等。中国古代小说关于人物脾气的概括,在很多情况下符合传统“五性”规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二、脾气速度描写的“刚柔缓急”规范
中国人常常以“缓急”、“快慢”、“好坏”等观念来谈论人的脾性。如《韩非子·观行》载:“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过犹不及,古人特别注意调控自己的偏执脾性。宋代哲学家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也说:“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这就是说,人之“气”若发生偏离,便容易形成“刚柔缓急”等偏执脾性。清末王国维在《古剧脚色考·余说一》中,谈到角色所表达的涵义时指出:夫气质之为物,较品性为著。品性必观其人之言行而后见,气质则于容貌举止声音之间可一览而得者也。盖人之应事接物也,有刚柔之分焉,有缓急之殊焉,有轻重强弱之别焉。……自气质言之,则亿兆人非有亿兆人之气质,而可以数种该之。此数种者,虽视为亿兆人气质之标本可也。[9](P196-197)
这里所谓的“气质”相当于脾气。可见,“刚柔缓急”是中国古代脾气理论的核心范畴,脾性决定行动,中国古代小说常常按照“刚柔缓急”观念,把人物性急与性慢等脾性规范当作故事发生的逻辑前提。
首先,《世说新语》在采取道德评价的眼光将人物分类推出的过程中,不仅从社会属性方面对人物的总体风貌予以评判,而且还注意写出人物后天形成的两极对反个性。该书《忿狷第三十一》有两则写王蓝田之性,其一曰: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纳)口中,啮破即吐之。
另一则曰:
谢无奕性粗强,以事不相得,自往数王蓝田,肆言极骂。王正色面壁不敢动。半日谢去,良久,转头问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后复坐。时人叹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前一则通过几个连续的动作描写,突出了官位高至侯爵的王蓝田急躁脾气。这是脾性肆张下的脾性表演。而同样一个王蓝田,后一则写他面对谢无奕的无理责骂,竟又能“正色面壁”,装聋作哑,这是自控情境下的脾气表现,真可谓能屈能伸。这种写作观念本自“刚柔缓急”规范。
众所周知,脾气的快慢直接决定了人物的行为方式、办事效率以及后果。一方面,“性急者”容易招惹是非,因而有利于小说的叙事运动;另一方面,“性缓者”则经常误事,露面的机会也不少,因而也常常被小说家当作情节因子植入小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国志演义》这部宏大的小说多以“性急”、“性缓”来比照性地托出人物,并借此推演人物的故事及生存处境与命运。关于脾性的“快”“慢”这一理论问题,毛宗岗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谈到《三国》所具有的“奇峰对插,锦屏对峙”妙笔时说:“张飞则一味性快,何进则一味性慢。”这里所谓的“性”,意思就是脾性。小说第二回回评又说:“写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写何进十分性慢。性急不曾误事,性慢误事不小。”故事的原委是,性子快的张飞见督邮对刘备傲慢,气愤不过,不管三七二十一,果断地实施了“怒鞭督邮”的行动。尽管事后不得不避祸而走,但终归消解了心头之恨;而同回至第三回则写何进脾性慢,面对袁绍、曹操等人的良言劝告,不是不认真听取,就是拿“吾意已决,汝勿多言”、“且容商议”等话搪塞,因此,作者给他的定性是“本是没决断之人”,终于贻误时机,遭到张让等十常侍谋害。在《三国志演义》中,因“性急”而致败者还可列举许多。如第二十九回着力写出了孙策性急带来的生存危机:
孙策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将息到二十余日,忽闻张纮有使者自许昌回,策唤问之。使者曰:“曹操甚惧主公;其帐下谋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策曰:“郭嘉曾有何说?”使者不敢言。策怒,固问之。使者只得从实告曰:“郭嘉曾对曹操言主公不足惧也: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策闻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许昌!”
这段文字先点出孙策的“性急”特点,尔后写他接见使者的表现,通过他不断被激怒的言行描写,将其“性急”的特点以及暴怒的情形逐步坐实下来。在作者的叙事操纵下,“性急”成为其不久横遭亡故的逻辑前提。又如,第五十三回写道:“却说长沙太守韩玄,平生性急,轻于杀戮,众皆恶之。”强调韩玄性急,遭到众人厌恶,就为最终写其被魏延追刺至死埋下了伏笔。第六十三回写张飞攻打严颜,就有人给严颜出主意说:“更兼张飞性如烈火,专要鞭挞士卒;如不与战,必怒;怒则必以暴厉之气待其军士:军心一变,乘势击之,张飞可擒也。”此外,刘表优柔寡断的慢脾气造成家庭争端,也属脾气决定故事进程的个案。这表明,作者也善于通过夹带笔墨来不断地提起主要人物的“性急”、“性缓”等偏执脾气,并为写其命运结局设置了逻辑前提。对同是脾气慢或脾气快,小说家也会写出其同中有异,做到特犯而不犯。如第二十二回先后写出了袁绍和刘备这两个脾气慢面对曹操军队的表现。对此,毛宗岗父子在回评中指出:“玄德获岱、忠二人而不杀,尚欲留为讲和之地;其与袁绍之顿兵河朔、迁延不进,毋乃同耶?曰:否。绍之力足以战而不战;备之力不足以战故不欲战。袁绍性慢是无主意;刘备性慢是有斟酌。”袁绍与刘表被写成“性缓”或“性迟”,他们都曾因为这种脾性上的致命弱点而坏了大事,可见关于人物的“性缓”描写有其独特的叙事意义。另外,如果按照中国古代的脾气学说,那么,曹操属于“狂”者一类,刘备则似乎是“中行”而偏于“狷”者之流。关于二者的对照,人们较为熟悉。第六十回写刘备对庞统自我标榜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作者通过刘备的这一番表白,集中点明了曹操的“急”、“暴”与刘备“宽”、“仁”等两极对反的脾性,为写二人的人生道路作了铺垫。
在《水浒传》中,“性急”人物的塑造被当作重头戏。容与堂本第三回总评所列出的“急性”人物名单就有“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当然,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大致写出了他们的“同而不同处有辨”,突出了他们相同脾气中的不同特点,使之“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由于这些人物是“急性”的,因此,他们经常在快节奏的行动中犯一些“冒失性”的错误。我们经常读到作者关于他们“性急”的穿插评论,如第十回写李小二既有正义感,也有报恩思想,但他之所以不敢及时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林冲,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以免受到连累。又如,第十三回写急先锋索超获名之由说:“为是他性急,撮盐入火,为国家面上只要争气,当先厮杀: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锋。”第六十四回写“宋公明雪天擒索超”,正是利用了索超的脾性缺陷:“索超是个性急的。那里照顾?……索超听了,不顾身体,飞马撞过阵来。山背后一声炮响,索超连人和马跌将下去。”全传本第一百一十五回再一次写索超“性急”支配下的行动:“宋军阵上,急先锋索超平生性急,挥起大斧,也不打话,飞奔出来,便斗石宝。”另外,小说第四十五回写道:“杨雄是个性急人,便问道:‘兄弟心中有些不乐,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作者写出了杨雄对石秀的直来直去,为后文写他怒杀其妻作了铺垫。总体说来,在《水浒传》中,秦明应当是“性急”的头号,第三十四回介绍他出场时就说:“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姓秦,讳个明字;因他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随后,小说接二连三地强调秦明这一性格弱点:“秦明是个性急的人,心头火起,那里按捺得住,带领军马,绕下山来,寻路上山。”围绕这种性格逻辑,小说让他走进宋江等人设下的圈套,一而再,再而三地动怒:“秦明怒坏,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秦明气满胸脯,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秦明怒气冲天,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秦明怒不可当,便叫军士点起火把,烧那树木。”“秦明此时怒得脑门都粉碎了。”宋江、花荣等人正是抓住秦明的这种脾气弱点,让他吃尽了苦头。后来,为赚取他上山,梁山英雄又设下圈套让他去钻。小说又不断地点染道:“秦明急性的人,便要下山。”“秦明是个性急的人,看了浑家首级,气破胸脯,分说不得,只叫得苦屈。”归顺梁山后,秦明仍然以这种脾气伴随了他的整个战斗历程。如第四十七回写道:“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正好没气,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第五十五回写道:“秦明本是性急的人,听了也不打话,便指马舞起狼牙棍,直取韩滔。”在作者笔下,秦明的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在“性急”的驱动下进行的。再如,鲁达也是个有名的急性子,且疾恶如仇,因此,他决不会耐着性子采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长远战略,而是追求遇到问题即时解决。如金批本第二回写他在酒楼上遇到金老父女,听了他们哭诉被地方恶霸郑屠欺压的遭遇,马上就要去找郑屠算账,被史进等劝住后,当晚“回到经略隅的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对于这段描写,金圣叹于夹批中说:“写鲁达写出性情来,妙笔!”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脾气的快慢以及大小、好坏等情绪变化的幅度决定着人物的行为方式和言语态度。换句话说,人物描写常常被置于预定的“刚柔缓急”等脾性框架内进行。
三、脾气幅度描写的“狂狷”规范
从情绪幅度审察,中国古代小说关于人物脾气的描写还依照了另一套规范性原理。《论语·子路第十三》载孔子之言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曾把人分为三类:富有进取精神的“狂者”,为人拘谨的“狷者”,以及“依中庸而行”的“中行者”。这是中国较早的气质或脾气理论。对应于情绪速度而言,大致可以说,狂者性急,狷者性缓。
中国古代文人小说对表现“狂人”脾气情有独钟。唐人传奇注重赋予其主人公以某种偏执个性。如《柳氏传》写韩翊“有诗名,性颇落拓”,《任氏传》写韦崟“少落拓,好饮酒”。两篇小说的人物虽然在人生表演上所具体呈现出的品味又不同,“有诗名”的韩翊的故事是风流的、浪漫的;而“好饮酒”的韦崟的行为则不免显得有点放荡,同时又不失为豪爽,但他们同被各自的作者概述为颇有狂放之气的“落拓”,故而笼统地属于“狂者”之流。这种脾性描写倾向一脉相承地延续到到蒲松龄那里,《聊斋志异》往往在开篇即开宗明义为人物的偏执性格、气质、禀赋人物情性定案,这些定案大致可以纳入“狂”与“狷”两类。“狂者”纷纷登场,占了很大比例,如《鲁公女》所写张于旦“性疏狂不羁”;《青梅》所写程生“性磊落”;《花姑子》所写安幼舆“为人挥霍好义,喜放生,见猎者获禽,辄不惜重直(值)买释之”,等等。“狷者”也复不少,如《娇娜》所写的孔雪笠“为人蕴藉”,脾气偏于狷。在这篇小说中,不仅孔生蕴藉,狐公子蕴藉,狐女娇娜、松娘也无不蕴藉。正如另一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所评:“蕴藉人而得蕴藉之妻,蕴藉之友,与蕴藉之女友。写以蕴藉之笔,人蕴藉,语蕴藉,事蕴藉,文亦蕴藉。”就蒲松龄所塑造的“狂者”而言,如《辛十四娘》入笔便先写冯生“少洒脱,纵酒”。对此,但明伦评曰:“四字定案。”这种定案很自然地为人物的所作所为预设了一个逻辑起点,因而“但评”又说:“轻脱已非修身保身之道,况又纵酒乎?冯生一声跳不出此四字外。得美妻以此,遘奇祸亦以此。”人物的所作所为乃至人生命运都取决于这种篇首的性情定案。但明伦更指出了《聂小倩》创作的“先断后叙法”:“廉隅自重,则财不能迷;生平无二色,则色无可惑;性又康爽,则剑客之御患,女鬼之倾心,皆从此出。”关于人物情性的开篇定案,也为后文的故事叙述提供了逻辑前提,而后文叙述则是这种定案的“佐证”。相对而言,《阿宝》所写孙子楚大致属于“狷者”,他“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他的一连串的事情皆因此而发生:他向阿宝求婚,导源于“有戏之者,劝其通媒”;他剁掉枝指,是由于阿宝那句“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那句戏言;就连最后考中功名,也是因为“人诳之,辄信为真”所致。
在白话长篇小说中,“狂者”一开始就受到青睐。若按照中国性情学说,那么,《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属于“狂”者一类,刘备则似乎是“中行”而偏于“狷”者之流。《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大都属于“狂者”。金圣叹在提出“性格”理论的基础上,几度夸赞狂放型的偏执人物塑造。如第二回总评指出: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剀直,接手便写鲁达剀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金氏虽然主要是在说人物个性的同中有异,但已经提出了“气质”问题。该回又有眉批说:“写鲁达,便又有鲁达一段性情气概。”这里的“性情气概”意思就是习性、脾气。从小说的回目,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气息:在水浒世界里,人物的行为方式大都极其豪壮,不是“醉打”,便是“大闹”,如武松“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醉打孔亮”,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大闹桃花村”、“大闹野猪林”,李逵“大闹江州”,花荣“大闹清封寨”,杨雄“大闹翠屏山”等,其行为大胆坦荡,其心地光明磊落,其“醉打”、“大闹”等等都是“狂者”行为。另外,《说岳全传》中的牛皋,《杨家府演义》中的焦赞、孟良,《说唐》中的程咬金等生性粗鲁爽直,脾气暴躁,疾恶如仇,也深受读者喜爱。他们也都可以被纳入“狂者”行列。
相对而言,先行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古代小说多以“超值”型的人物偏执脾性为主,后起的《金瓶梅》、《红楼梦》等世情小说则多注重描写人物“庸常”性的偏执脾性,尽管其描述术语已经步入多元化,但也可用传统脾性范畴来概括分析。《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脾气大体上可归属“狂者”框架,作者一开始就赋予其“行为偏僻性乖张”的特点。在行文中,作者不仅时时随笔点明他以“呆”为主调的性情,而且还借助别人的评论来强化他这种性情的偏执性,如第十九回写道:“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弛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第三十六回又写道:“袭人深知宝玉性情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话,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些近情的实话,又生悲感。”在关于人物脾气的描写中,《红楼梦》常常直接用“脾气”二字挑明,并强调欺偏执性,如第六十五回写道:“这尤三姐天生脾气,和人异样诡僻。”而第八十二回写道:“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来看。”她们的脾气也大致都属于外向型的“狂”。当然,林黛玉、史湘云与薛宝钗尤其属于不同的脾气类型。林语堂《中国人》曾经说过:“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易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更喜欢哪个。”[4](P268-269)大致说来,林黛玉属于敢想敢做的“狂者”,而不嗜张扬、甘愿守拙的薛宝钗却是一个厚重雍容的闺秀淑女,也是“中行”而偏于谨慎持重的“狷”者之流。同样是孤儿的林黛玉与史湘云虽然长相迥异,黛玉“娇袭一身之病”,外形“弱柳扶风”,而湘云却生得“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但她们都一样文采横溢,不愧为大观园中的狂放之士。
中国古代小说关于人物脾气的描写,既是社会现实人生角色扮演的投影,人们不妨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小说人物对号入座,借此镜照现实社会人们的脾性;又大致符合传统文化脾性范畴,为评判现实人物的脾性提供了某种值得参照的规范性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