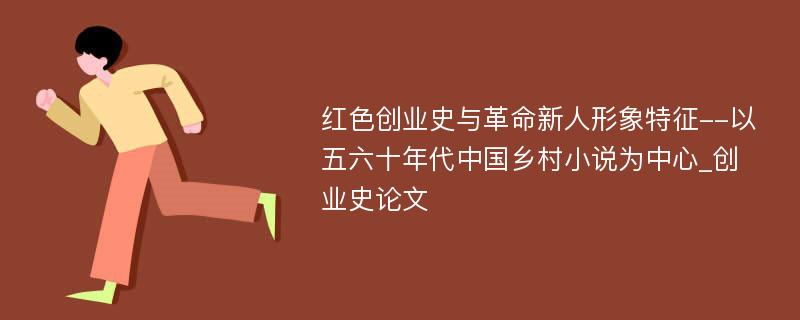
“红色创业史”与革命新人的形象特征——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史论文,五六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农村论文,题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红色创业史”的小主题与大主题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红色小说中,许多农民英雄身上都流淌着纯正的革命血液, 柳青《创业史》曾经是土改时期民兵队长的共产党员梁生宝;浩然《艳阳天》中退伍军 人、坚定的共产党员萧长春,都是战争年代的红色武装人员,接受过革命战争的熏陶和 考验。这种出身对于表现这些农民革命新人的政治坚定性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不过 ,另一批出身于战争、土改年代的“老干部”则相反,他们在农村新的革命过程中并不 能保持足够的革命干劲,而是“退坡”了。赵树理《三里湾》中的农村干部范登高、柳 青《创业史》中的代表主任郭振山,在土改后,由于缺乏政治热情,享受了土改的成果 ,却走发家道路,竟蜕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立面。这一历史时期的红色小说中,这 一系列的“退坡”人物,与中间分子、敌对分子一道,被塑造为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 的重要障碍。这是一个有趣的角色转变,意味着在革命战争和土改小说中一些出色的革 命干部,到了表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红色小说系列中,已经从进步走向反动。而到 了“文革文艺”,这些人物则演变成了“走资派”人物系列。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已经 提示了两种红色系列小说间(一个系列是革命战争小说和土改小说,另一系列是合作化 题材小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其一致性是,二者都针对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军人英雄 为中心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土改作品,其叙述动力来自于以暴力反抗阶级压迫,而反映集 体化的红色农村小说的最主要的主题是防止在土地改革后发生新的阶级压迫,二者说的 都是阶级斗争;其差异性在于,革命战争小说和土改小说其起始情感多是阶级仇恨,多 以复仇为发端,但这种仇恨多是对阶级压迫的仇恨,并全部是针对私有制观念的仇恨, 保家保田甚至是许多农民战士参加革命战争的决定性动机。其次,“取而代之”的斗争 模式更是红色土改小说的鲜明特征,红色土改小说中农民对地主的清算既有解除压迫的 翻身自豪感,更有重新分配土地和财物的无比喜悦。然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化、 集体化题材的红色作品则用审美的方式告诉读者,私有观念如今已经成为革命最可怕的 敌人。
革命战争和土改题材红色小说中,叙述者对农民们对土地和财产的渴望是宽容的,周 立波《暴风骤雨》的叙述者是以善意的眼光来看老孙头的自私,老孙头心里的小算盘也 被赋予轻微的喜剧色彩,小人物老孙头的自私行为是被笼罩在受压迫者获得土改果实的 狂喜情绪之下的。然而,发展到《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类似老孙头的自私 ,则成为被叙述者进行“强聚光”的叙述焦点,《创业史》《艳阳天》的叙述者对农民 们迷恋土地粮食的情感是持必须“改造”的态度的。
事实上,毛泽东在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前夕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 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 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的工 业化的问题。”①(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7页, 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老孙头的私有观念,如今已经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而 改造农民、埋葬私有制亦成为红色农村题材作品的重要的叙事主题。毛泽东所指出的“ 教育农民”的严峻性,在于“农业社会化”关系到农业能否为国家工业化创造财富,从 而实现在较短时间内建立现代强大国家的革命理想。而实施这一步骤,其主要的困难便 在于如何瓦解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使农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 金积累。在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环境压力之下,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的红色作品中革 命势力的斗争对象多是农民的私有观念,这便不难理解。红色战争小说中农民出身的战 士们为获得土地、解除经济压迫而表现出来的革命激情与革命斗志,已经悄然转变方向 。一次针对农民私有观念的声势浩大的审美攻势已经展开。
当然,红色文本中“改造”农民只是一个“潜在主题”,红色小说从未以“改造农民 ”作为其直接的审美命题。红色小说更愿意在积极、正面的“创业”主题之下构造关于 “改造农民”的潜在主题。革命文本,从来不止于对农民的“落后思想”的批判,若如 此表现合作化运动,则未免太“消极”了。所以,即使在以改造农民为主要叙述环节的 合作化集体化题材的中国红色文本中,革命战争文本培育出的饱满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 依然贯穿始终——以集体创业的崭新面貌来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建立新的精神 高地,吸引徘徊观望的农民们加入新的神圣事业之中。所以,展现革命精神的优越性并 显示社会主义力量的逐步强大,这才是社会主义“创业”类型的红色文本最通用的情感 脉络。
此类型小说当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柳青的《创业史》一开篇便叙述了发家力量 在农村的恣意蔓延。农民们被自由竞争、发家致富的念头深深地吸引着。这在《三里湾 》《山乡巨变》中是见不到的。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并没有将 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描述得如此强大、自信并形成占精神优势的“势力”。《创业史 》叙述如此“明目张胆”的自发势力,其目的之一在于凸现一种“危险”:土地改革后 农民们的自由竞争使土改的游戏规则被推翻了,农村也不再可能再来一次以阶级成分重 新分配劳动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土地改革,部分个体农民凭借劳力和能力发家致富,另一 部分农民再次沦落到赤贫的地步,而这种分化势必将使历史倒退。所有的这些描述都指 向一个“现实”:土改中的阶级关系已经开始松散,在土改中获得利益的“新阶级”产 生了,而“新阶级”的成员竟然与富农坐到了一块。在富裕中农郭世富大瓦房架梁的日 子里,共产党员郭振山和富农姚世杰这土改中的“两个仇人一同在郭世富家做客了,而 且都等着第二轮坐席”。蛤蟆滩四处是喜庆的氛围,活跃着羡慕富裕中农发家致富的心 思。在这快活的背景下,乡场上的人物虽然议论着互助组和梁生宝,然而他们显然都不 认为梁生宝互助组能够成功,且都误读了梁生宝互助组的历史意义。《创业史》在小说 的开始部分便让农村中的“自发势力”特别是“自发思想”充分亮相,勾画了一个情势 严峻的阶级斗争形态分布图:农村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势力是弱的,土改后的许多农民 的思想依然是落后的,他们为富裕中农为代表的个体发家的思想所陶醉了,而这其中竟 然有老共产党员郭振山。这一严峻的意识形态态势是《三里湾》《山乡巨变》所没有的 ,就连较早叙述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的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其发家势力也是躲躲 闪闪、扭扭捏捏,显得极其单薄。而《创业史》却将富裕农民的发家欲望书写得酣畅淋 漓。由此,《创业史》构造了一个迫在眉睫、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重大矛盾:要么走社 会主义合作化生产道路,贫困农民因此不再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长工,要么走发家道路( 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重新回到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老路上,农民之间再 次分化为贫富悬殊的阶级。《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山乡巨变》显然没有达到如 此紧张的“高度”,五十年代初期的《不能走那条路》中贫农宋老定老汉最终将准备买 地的钱借给要卖地的农民,老汉的发家私欲很快转化为对濒临破产的农民的同情,问题 解决得轻而易举。《三里湾》仅仅以温和的落后/进步分野和家庭纠纷来完成不同农民 们对合作化事业的认识,结尾更以三对青年皆大欢喜的姻缘传达着农村集体劳动生活的 勃勃生机。《山乡巨变》中出现了个体劳动与集体劳动的“竞争”,目的在于叙述合作 生产的优越性,更有特点的是,整部小说中太多乡村田园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描绘,部分 消解了合作化运动的内在紧张和紧迫感。这些合作化作品中的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 与《创业史》比较,要弱得多。特别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农民们对土地的迷恋、以及加入 农业合作社的内心矛盾远不如《创业史》那么突出。《创业史》中农民对互助合作的对 立和冷淡颇似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情形,这部苏联反映集体化运动的名著, 其主人公达维多夫在推动农村集体农庄化的过程中,同样遭遇到农民们普遍的抵抗和嘲 弄。而《创业史》第一部中梁生宝的互助组亦从孤立起始,许多农民排斥梁生宝对互助 生产的热情。不过,在小说中,农民们的不安,在小说中被归结为落后和自私。这就显 示出梁生宝的“创业”,已经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活动,其重要意义在于,农业合作化运 动将以根除农民的私有观念为第一目标:
生宝回到庄稼人拥挤的前街上了。他心里恍恍惚惚:这难道是种地吗?这难道是跑山吗 ?啊呀!这形式上是种地、跑山,这实质上是革命嘛!这是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 产制度哩嘛!整党学习中所说的许多话,现在一步一步地在实行。只有伟大的共产党才 搞这个事,庄稼人自己绝不会这样搞法!②(注:柳青《创业史》第235页,中国青年出 版社1960年5月北京第一版。)
这段心理活动,可以看出梁生宝对农村日常生活的“政治意义”非常敏感。梁生宝的 原型王家斌就是位善于将经济生活联系于政治意义的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③(注:柳 青在他的散文《王家斌》中叙述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他开会讲话、批评人、和人谈话 、商量事,开口闭口‘政治意义’,常引起人们善意的笑”。见《柳青文集》第681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作为艺术形象,梁生宝对日常生活的政治意义更 加敏锐。梁生宝成为国家巨型话语的一位积极的承载者。严家炎先生对此颇有异议,认 为“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 明快地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这种本 领,我看,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 ④(注: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柳青对此做了正面 回答:“许多农村青年干部把会议上学来的政治名词和政治术语带到日常生活中去,使 人听起来感到和农民口语不相协调,这个现象不是普遍的吗?……农村党员和农村积极 分子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自发由批评者所谓的‘萌芽’生长 起来的。此外,在艺术上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如果不涉及 他们的政治学习生活和阶级觉悟程度,怎么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描写他们的行动呢? ”⑤(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月号。)这表明,严家炎所 认定的那位梁生宝是以买稻种那样的实际行动去贯彻党的政策的,以朴实的阶级感情去 从事社会主义实践的青年农民,是一位应该从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的“先进分子”。这 样的人物应该以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以传达政治“理念”的心理活动来保持其“先进性” ,一位青年农民英雄并不见得要以政治远见来表现其英雄特性。而柳青却认为,所谓“ 理念活动”正是梁生宝这一先进人物形象的重要特征,巨型的国家话语与梁生宝日常口 语表面上虽然“不协调”,但却反映了党的“教育”和“阶级觉悟程度”。柳青更愿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而不仅仅是一位农民先进分子。在 柳青的认识里,梁生宝形象应该类似于小说中县委杨书记所说的那种人物:“一个工厂 里的工人,一个连队里的战士,一个村子里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 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 要和要写的话,……。”⑥(注:柳青《创业史》第2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5月 北京第一版。)
在今天看来,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喜欢想“大事”、说“大话”的梁生宝完全是虚假 的政治理念产物。
梁生宝的内心情感可能是单向度的,或是西方小说理论中所谓的“扁平”人物。与不 断发生自我冲突的梁三老汉、郭振山比较,其内心的戏剧性自然不强,然而,这同样不 能成为判定这个人物缺乏艺术特点的理由。梁生宝的特点在于:他在一个相当不利的日 常环境中,对“大意义”充满了执著的追求。梁生宝“雄心勃勃地肩负起改造世界的重 任”,充分意识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历史意义”。梁生宝的自我估价,和梁生宝以斤 斤计较的态度从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之间的形成的有些可笑的“落差”,正是梁生宝这 个新人英雄最有特点之处。《创业史》的作者正是抓住这个看来有些可笑的“落差”、 “错位”告诉读者:梁生宝的农民身份和他“小打小闹”的经营活动,实际上联系着中 国历史的巨大变革,我们完全有理由从梁生宝买稻种或搞密植水稻的经济活动中发现其 革命性的历史意义。
如此,梁生宝买新稻种、搞密植水稻、进山搞副业便不是简单的“科技兴农”和“创 收”了,而是与转变中国革命的历史,与转变中国农民的意识形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是一位踏踏实实的基层革命新人。小说《创业史》中,若要细究起来,梁生宝在激烈 的阶级斗争过程中确实没有办什么“大事”,他整天“拘泥”于经济生产的每一个细节 。他的互助组规模很小,工作琐碎,甚至有些婆婆妈妈,以致于让他的政治对手代表主 任郭振山乘机奚落其政治上的“落后”。但由于梁生宝内心里不断反省互助组的每一步 工作的历史意义,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又在关键时刻从政治大方向上对梁生宝的互助组 进行指导和帮助,加上一位政治眼光非常敏锐的叙述者从旁点评,这就在叙述效果上造 成了梁生宝互助组经济行为的政治意义之“叠加效应”。梁生宝互助组的生产活动每行 进一步,就被巨型的政治诠释话语不断追逐,不断放大,从而堆积了繁复的政治意义。 柳青叙述梁生宝在经济活动上的“创业”的起步过程,其用意不仅在农业生产活动和生 产方式的改变本身,这只是《创业史》的小主题,其大主题则是,梁生宝通过组织互助 组的创业活动,教育、带动农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琐碎、日常性的经济活动过程中 ,逐渐构筑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厦。实际上,小说要读者认识到:正是像梁生宝互 助组这样微小的单位,组成推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新的革命力量。也只有如 此,写梁生宝的互助生产,这才真正符合“创业史”这样一个气势宏大、意义非凡的革 命主题。
下篇:革命新人:冷静的“磨难”
《创业史》这样的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本,创造了梁生宝这样的革命新人形象。主人 公梁生宝形象的时代意义在于:在郭振山之流的“老革命”们参加革命的动力已经衰竭 的时候,梁生宝这样的新人英雄却找到了继续革命的起点和支点,走到了时代的前面。
柳青的《创业史》将文学的红色教化作用推到极致,堪称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在当时,这样的文学作品的功能已经不是单纯用来描述已 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它已成为构筑继续革命意识形态 的文艺先锋。
革命新人的形象裹挟着强大的政治示范功能。因此,人性的细腻刻画和矛盾形态的展 现对于革命新人形象虽然重要,但与突出新人身上的继续革命主题比较,则成为次要的 审美要求。柳青毫不掩饰他创作梁生宝形象的政治功利目的,他的理由是政治特征突出 ,甚至达到“天真的程度”,正是梁生宝这样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最突出的形象特 征。⑦(注: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8月号。)
从政治实用角度看,梁生宝这样的新人英雄无疑是党的政治理念的形象化身。不过, 奇怪的是,柳青创作这样的审美形象,并没有将其构造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锋芒毕 露的超级英雄。与梁生宝形象的延续——萧长春比较,梁生宝显然比较羞涩,比较收敛 。在小说前半部,梁生宝甚至颇为孤立。其实,这正是熟悉西方经典现实主义创作规则 的柳青的过人之处,在具体生存环境中,柳青要让梁生宝接受“磨难”,使人物的“精 神成长”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逐步扩展同步。
梁生宝对私人生活需求的漠然不顾,他的天真、和气、迂谨,他令人放心亲近的道德 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都构成了这个人物形象设置的主要元素。然而,就是这样的一 个在道德方面上近乎完美的人物,却受到了环境的挤压:继父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责难 ,郭振山对梁生宝的嘲弄,改霞对梁生宝的抛弃,都构成了梁生宝成长道路上最直接的 冲突。小说要展现的,就是作为一个社会先进分子的梁生宝,为实现他的高尚的社会创 业目标,要承受的来自亲人、同志和敌人给予他的多方面的心灵磨难,这种人物成长模 式与西方成长小说如狄更斯、巴尔扎克的某些作品中的人物经历模式相像,更与俄国的 民粹主义小说如《怎么办》的人物成长过程接近。可以说,对梁生宝的塑造,柳青所采 用的小说叙述类型吸收了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叙事传统,更承继了中国“五四”以来以鲁 迅、茅盾为代表的作家对社会心态的剖析和对典型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的密切追踪。这是 柳青这一类型的作家与赵树理的重要区别,赵树理仅仅以同情的视角从发现农村问题、 解决农村问题的角度来书写农村集体化过程中的故事。如果梁生宝与《三里湾》中的青 年干部王金生、《山乡巨变》中的年轻共产党员刘雨生,甚至与其后的《艳阳天》中比 较强硬干练的共产党员萧长春比较,其形象的社会主义新人特征,则最为突出。或者说 ,也正是由于梁生宝形象多少带点“天真汉”的特征,使他并没有“降格”为王金生、 刘雨生那样的集体化过程中的事务工作分子,但也不像萧长春那样“成熟”。
梁生宝略有些“夹生”却不断自我放大的政治热情与他勤劳谦逊淳厚的个性,构成了 革命新人形象常有的意义超越性与生存活动的日常性琐碎性本身的矛盾。
但是,在《创业史》中这种矛盾是隐匿的,而不是刻意强调的,甚至让这种矛盾笼罩 在一种诗意的叙述氛围之中,远未达到迫使革命者的精神世界发生内在分裂的程度。其 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红色小说的主人公都拥有冷静的、理性的性格核心。五六十年代的 红色叙事几乎都对革命者做了“非狂热”的叙述处理,以突出革命者高度的自控能力。 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叙事修辞,即阶级革命的具体措施越是激进,越是越出渐进革命的 轨迹,其革命者的形象反而越务实、理性、冷静,越有正剧意识。
激进的阶级革命行为表现为审慎的、细致的工作,从而获得理性的“自然化”的表述 ,这是中国五六十年代“继续革命”文学中的审美特征之一。而且,小说作者们若让革 命新人去思考阶级革命的意义,还常常引入一个诗意抒情的叙述背景。这是非常“中国 化”的革命新人的塑造方式:革命新人首先在道德上没有瑕疵,在性格方面更具有一种 “儒将”风范,在不利于己的环境中保持完整的甚至是诗意的人格形态,这才有利于表 现革命者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同样是以集体化运动为主题,苏联虽然也出现了像《金星英雄》这样完全以粉饰、“ 美化”生活为能事的小说,但在苏联最有艺术个性的反映集体化运动的名著中,我们却 能发现灵魂世界高度紧张的集体化运动的英雄新人形象。苏联的大师级作家肖洛霍夫《 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革命者饱受灵魂劫难,爆发种种道德危机。革命经常将共产党人 推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其典型人物如集体化运动极端激进的推动者共产党干部达维多夫 、拉古尔洛夫,都在不断地忍受着革命理想/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的重重矛盾的折磨。乡 村书记拉古尔洛夫挑灯夜读英语,真诚地幻想着有朝一日到英国发动工人,进行阶级革 命。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激进的革命者,却因为对落后分子开枪被开除了党籍。而一 个乡村荡妇则让两个最真诚的革命者无法逃避情欲的强烈诱惑,彼此发生了裂隙。《被 开垦的处女地》中革命者的种种遭遇似乎都在构筑着这样的革命意象:过于急切的和理 想化的革命运动中,革命者将首先承当最直接和最矛盾的痛苦。革命者既可能因为富农 一家被驱逐出村庄而情不自禁地掩面而泣,也可能被暴怒的妇女群众痛打一顿还得委屈 周旋。激进革命中的一切似乎都在走向极端后转向革命理想的反面,所以,这也使得《 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激进革命者的革命理念革命设计常常在其实施过程中不断构成具有 反讽意味的情节:革命者的美好社会蓝图和无私的革命动机与革命过程中革命者自身的 难以克服的难堪、狼狈、委屈、自我放纵或自我陶醉、自我麻痹不可思议地形成怪异扭 曲的心灵图案。《被开垦的处女地》这种独特奇异的革命与人性的无法调和的冲突,充 分展示了革命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冲击的强度和力度并不仅仅在经济层面,而是对旧的精 神秩序的全面摧毁和重组(首当其冲的是革命者的精神世界),而这种冲击是一个充满了 心灵疼痛感的过程。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比较,这种精神深处的强烈冲击力量在中国反映 集体化的革命文本中即使有所表现,也显得太皮相了。
中国集体化小说的人性深度与萧氏的俄国集体化名著比较,即使是在《创业史》这样 的中国集体化题材中的重量级革命文本中,也很难发现主人公痛苦的精神“蜕变”。一 位年轻的学者指出:“梁生宝几乎是天生地具有一种新农民的本质。”⑧(注:李扬《 抗争宿命之路》第12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确实如此,梁生宝这个 新农民的见解、个性与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是每一项政策步骤皆水乳交融,特别是中国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冲击力”与梁生宝几乎没有形成正面的、成规模的冲突。这种 冲突不是不可能发生,事实上,梁三老汉、郭振山、郭富仁、姚士杰甚至梁生宝的恋人 改霞已经具备了与梁生宝发生正面的强烈冲突的政治和个性条件,但梁生宝过分理智、 冷静的性格完全消解了迎面而来的矛盾,“有理有节”消磨了梁生宝作为一个活生生的 革命者可能有的个性深度,也许只有在他与改霞的爱情方面梁生宝尚能发挥些许个性锋 芒。不管这种中国式的革命偶像走向更温和(如《山乡巨变》的主要干部刘雨生、李月 辉)或更激进(如《艳阳天》的萧长春)的两个极点,其主人公的心灵基本上都是“完整 ”的、和谐的,缺乏萧氏笔下苏联革命者那种天翻地覆的心灵震动感。
中国合作化题材的红色文本中,最和风细雨的作品当推《山乡巨变》,小说中农村基 层干部李月辉、刘雨生这些主要人物亲切朴实,几乎难以见到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叱 咤风云的气派。小说以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来描述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这在美 学上并非没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我从小说中感觉不到那么一种轰轰烈烈蓬蓬勃勃的 气象”。“在小说中感觉不到那种农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出的‘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 出路’的迫切要求”。⑨(注:肖云《对<山乡巨变>的意见》,1958年8月27日《读书》 。)的确,《山乡巨变》中的许多农民,多以迫于形势压力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政策变 化,许多农民们处在被说服的位置。这样的合作化文本,显然如批评者所言没有很好地 表现出农民们对“改天换地”如饥似渴的革命要求。而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山乡巨变 》这样的美学风格勾勒出一幅喜气洋洋的农村新风俗画,“它们不仅给予读者以丰富的 美感享受,而且在他们心里唤起对农村新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这些描写不仅富有诗情画 意,同时也是有思想性的”。⑩(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2 月26日。)在世纪末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也认为,“人情美、乡情 美和自然美,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主要画面”,并认为周立波的这种叙事方式,“在丰 厚的民间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唯一要表达的东 西”。(11)(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3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第一版。)这种解读途径虽然颇为别致地注意到民间的人缘亲情对紧张的合作化运动的 某种缓冲力,但显然忽略了“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的民间缓冲力已被利用为主流 叙事“护法”。《山乡巨变》一幅幅弥漫着泥土芬芳的乡村风俗速写画,传达出这样一 种信息:合作化运动在谨慎、亲切的农民干部们的推动过程中,是一种非常富有美感的 田园诗意生活,背着封建思想包袱的农民们即使是被动的,也同样能够在颇有耐心的善 良的农村干部们的政策执行过程中,以讲人情而非讲政治的方式,获得妥善的甚至是快 乐的“大团圆”结局。这种将革命写作进行趣味化与诗意化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对自 然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尊重,不如说是充分提炼了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乐感文化”的成分 ,为革命叙事创造出一种不发生强烈抵触情绪的“革命幸福”之氛围。在此,土改小说 《暴风骤雨》中“革命恐怖”已经转变为充满生气的快乐气氛和弥漫着民间美感的幸福 感。应该承认,建立在幸福感之上的革命美学并不见得比建立在仇恨之上的革命美学无 力,它所创造的农村新生活的崭新气象与“唤起对农村新生活的热爱和向往”是和谐一 致的。或者说,革命的仇恨美学与革命的幸福美学,本来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式的 叙事图式,革命的幸福美学,往往借助于仇恨美学作为叙事的过渡。但回避了人物心灵 世界自我搏斗历程的革命幸福感是否过于肤浅呢?依恃于民间美感的集体化小说是否太 拘泥于革命运动中“幸福的一面”?其实,《山乡巨变》最大的失败还不是将合作化运 动书写得过于美好,而是在这种过于幸福美好过于平缓的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几乎见不 到革命者的革命理想与现实社会种种关系的冲突,从而回避了革命者精神世界可能掀起 的惊涛骇浪。我认为,《山乡巨变》进入这样的叙述盲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部小说缺 乏梁生宝那样为革命理念而奋斗的新人形象,而多是些缺乏自觉的革命理想的事务工作 者和政策执行者。当然,仇恨感与幸福感并没有绝对的分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情感与 生活在新时代的自豪感与幸福感常常结合在一处。革命的“红色”,即是阶级仇恨的象 征,亦是革命幸福的标志。事实上,继续革命是以社会主义优越性作为承诺,以长远的 幸福感作为情感支撑的。复仇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建立 一个富足平等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才是继续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即使在《艳阳天》这 样完全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小说中,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文本中也是放置在叙事 的突出位置。《创业史》中的一句话:“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 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这句话乃全部集体化红色小说的“文眼”,特别是在革命建设 时期,旧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打倒,新兴的剥削阶级尚在一个假想的范畴中,革命锁定的 目标多是富裕中农,甚至是梁三老汉这样的贫农,阶级仇恨几乎无从谈起。而靠发挥社 会主义“优越性”,最终创造更多的幸福成为继续革命题材小说中一个重要的叙事趋向 。梁生宝等革命新人形象的创造,最终必须为革命幸福的政治意图作出审美的保证,所 有历史重负、人性弱点和革命现实的纠葛,在中国式的继续革命审美文本中,皆交给梁 三老汉这一系列的“中间人物”去完成,从而让革命新人获得人格的完整和形象的“正 面化”“高大化”,让革命者成为幸福承诺的一个具体符号而不是人格分裂的承当者是 中国式集体化作品的一大特色。这从柳青对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的审美“加工”过程中 亦可略知一二。(12)(注:参见《王家斌》,《柳青文集》第67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 91年5月第一版。)
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战士的刘雨生、梁生宝、萧长春们,为新社会提供了比较新颖的审 美形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式的革命新人,在审美领域中只接受冷静的、正面的“磨难 ”,在这些新人英雄身上,不带有道德瑕疵,从未发生道德危机,如果发生个人情感矛 盾,在革命压倒一切的思维走势面前或者获得花好月圆的解决,或是以革命的名义将爱 情矛盾自我判定为无意义。总之,与苏联大师级的集体化红色小说比较,中国的革命新 人心灵结构过于稳定,从而导致了其心灵深度和丰富性的相对匮乏。中国继续革命新人 的成长,其标志多是纯正的阶级血统,鲜明的阶级意识,坚定的革命信念,冷静的工作 态度,身先士卒的革命干劲,深刻的政治洞察力,谦逊忍让的人格魅力,但缺乏与自我 性格的多个侧面搏斗而带来的复合多重的情感景观。在这样的革命新人审美模式之中, 传统的“圣者”形象依然是其塑造革命队伍中先进分子的一个关键性的构成元素。在这 种新人模式的内涵中,暴躁、幼稚、走极端、沉溺私人情感、偏听偏信等等人性弱点都 为革命新人的形象所排斥,从而保障了中国五六十年代革命者形象的“纯正性”和革命 叙事的“幸福感”。从这点上说,这一时期的革命英雄形象为六七十年代以样板戏为中 心的革命文艺提供了直接摹本,当然,这种完整感和幸福感又与完全抹除革命的世俗幸 福感,过分强调阶级仇恨的样板戏文艺有着明显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