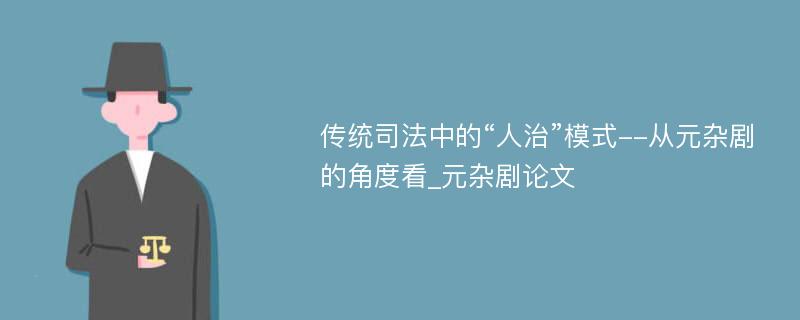
传统司法中“人治”模式——从元杂剧中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视论文,司法论文,传统论文,模式论文,元杂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08(2005)01-049-14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一些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有强烈的“清官”情节,民间有相当数量的清官戏,表现了一种司法上的“人治”模式。在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元剧选》中以及明代的公案剧《十五贯》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尽管这些剧作都赞美清官司法,但同时也展示了更多的值得今天学者分析思考的问题。
一、审判中的清官
在元杂剧中,有两类公案剧。一类有关执法。在这种公案剧中,所谓的清官和贪官的冲突实际主要是一个政治力量或权力对比问题。当面临权势时,你是否敢公正审判并依据明确的规则严格执法?你是为虎作伥,还是为民作主?是乡愿妥协,还是刚直不阿?在这个领域内,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无疑是起作用的,甚至常常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还有另一类公案剧,即所谓的“决疑平反”的公案剧。剧中的主要问题是疑难案件的审判或昭雪。在这后一类戏剧中也会出现了恶人、坏人、无赖,剧本中也常常提及“滥官污吏”,同时剧中的清官也是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勤政爱民、智慧非凡。看起来,似乎官员的个人道德很重要。清官之所以成功审理了疑难案件,在受众的印象中,往往是因为他的这种正义感。但真的如此吗?
有时印象是靠不住的,因为,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往往会模糊一些重要的差别,并因此强化人们的某种既定的印象。我们需要对元杂剧中清官(吏)形象作更细致的分析。
我首先假定,任何好的审判都需要裁判者具有两个最基本维度的个人素质,道德和能力。(公正、正直、刚直不阿以及基于负责任的爱民勤政等)(智慧、敏感、犀利、在某些情况下善于周旋等)依据这两个维度排列组合,构成了一个矩阵。根据元杂剧以及明代公案剧《十五贯》中诸官吏的事迹,把这些官吏分门别类,就构成下面一个表:
表1: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分类
清廉贪婪
包拯(《灰阑记》等) 赵令史(《灰阑记》)
张鼎(《魔合罗》、《勘头巾》)萧令史(《魔合罗》)
精明 王然(《不认尸》)宋了人(《神奴儿》)
钱可(《绯衣梦》)无名令史(《不认尸》)
况钟(《十五贯》)赵仲先(《勘头巾》)
桃杌、窦天章(《窦娥冤》)
完颜(《魔合罗》、《勘头巾》)
苏顺(《灰阑记》)
贾虚(《绯衣梦》)
平庸 巩德中(《不认尸》)
河南府县令(《魔合罗》)
河南府大尹(《勘头巾》)
汴梁县官(《神奴儿》)
过于执、周忱(《十五贯》)
这个分类是高度形式化的,人们对其中某些官吏的分类会有不同意见。估计以包拯为代表的清廉且精明以及以赵令史为代表的贪婪但精明这两栏都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以《窦娥冤》中处死窦娥的太守桃杌为代表的清廉但平庸这一栏会有比较多的争议。(注:在我所了解的文献中,只有黄克曾经犀利地指出,在一定层面上看,窦天章与桃杌的差别并不大(黄克:《关汉卿戏剧人物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70页),但遭到了批评(华世忠:“《窦娥冤》第四折析疑”,《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窦天章在《窦娥冤》中是以清官形象出场的,类似的人物还有《勘头巾》和《魔合罗》中的府尹完颜。而《窦娥冤》中的楚州太守桃杌、《灰阑记》中的郑州太守苏顺、《绯衣梦》中的县官贾虚等明显是作为昏官来表现的,属于反派人物。(注:注意,这不是我的概括,而在剧本角色分类中已经显露出来了。在剧中,这些人物都注明是“净”,但不可能是那种刚正英武的“花脸”,而属于“丑角”。这一点也可以用于窦天章和完颜等。)此外,由于剧中桃杌、苏顺等人都把告状者作衣食父母,急于收取“诉讼费”,在当代中国观众或读者心目中,这些至少是有道德缺失的官员。因此,把处死窦娥的楚州太守桃杌同为窦娥平反的提刑肃政廉访使窦天章归为一类,似乎没有道理。
不错,在戏剧中,窦天章和完颜确实是作为清官出现的,但这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审理案件的结果正确。而他们之所以没有作出错误的判断,相反成为平反冤错案的“清官”,如同我在其他地方分析的,(注:参见苏力:“窦娥之冤”,《中国社会科学》(即出);“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法商研究》(即出)。)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清正廉洁,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智识卓越,而是因为一系列条件。窦天章能够为窦娥平反冤案主要依靠了窦娥冤魂提供的信息(包括窦娥死后的超自然证据),以及窦娥与他有父女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他更容易相信窦娥的言辞,并将之作为案件处理的证据)。而所谓的昏官桃杌在决定窦娥案件之际不可能拥有这些信息和条件;如果有,桃杌也肯定不会作出错误判决(桃杌会那么匆忙地把自己的女儿作为罪犯处死?!如果处死了,即使是错案,也可能更会被视为大义灭亲的“清官”了)。完颜在《勘头巾》和《魔合罗》两剧中的成功则依仗了能吏张鼎的过人智识和才能。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条件,窦天章和完颜都肯定会重复下级官员或前任官员的错误判决。因此将窦天章和完颜归为清廉但平庸的官员是有道理的。
而另一方面,尽管在戏剧中是作为“反派人物”出场,但《窦娥冤》中的桃杌以及《十五贯》中的过于执在剧中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道德上的缺失,只是有些普通人的特点(弱点)。确实,他们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但这一错误,从剧情看,与贪污腐败无关,不属于有意制造冤案,而主要是因为证据缺乏、审判能力不足以及过于自信。《灰阑记》中郑州太守苏顺严格说来也应当属于这一范畴,因为他没有徇私枉法的行为,甚至他在场“监督”了赵令史的审判,他的问题出在对审判一窍不通,任用并信赖了污吏。
因此,如果严格按照这两个维度来看,我的这种合并同类项可以成立。
据此,除了印证了我先前的一些发现外,我们还有了一系列与流行的观点或我们对传统戏剧之印象不同甚至相反的发现。首先,在审判上,造成冤错案件的虽然有污吏的因素(例如《灰阑记》中赵令史、《魔合罗》中的萧令史),但戏剧中反映出来的,却更多是由于审判官员的平庸,智力和能力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胥吏弄权。
其次,尽管常常被概括为清官与贪官或滥官之间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但这些戏剧真正反映的是,冤错案件基本与作为裁判者的官员本人的道德品质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官员的智识、能力则有更直接的关系。如果仍然要用“清官”这个词,那么这里的“清”不能仅仅,甚至主要不能,理解为道德上“清廉”或“清正”,而应理解为包括了智识能力上的“清楚”或“清醒”。
第三,这就表明,尽管元杂剧作者习惯于用清官和贪官或其他道德术语来讨论分析审判中的问题,但至少从这些戏剧所展示的格局来看,元杂剧的作者们实际上更关注官员的施政、审判能力,尽管他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命题或表达。这些戏剧中的艺术形象其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清官和贪官两重划分;实际上拒绝了用道德(即当时的政治)维度作为划分“好”、“坏”官吏的尺度。从剧情来看,在案件审理问题上,正确的判断当然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道德人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审判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从后果的维度对清廉但平庸这一范畴的官吏作出更细致的区分。如表2:
表2:清廉但平庸之官吏的分类
清廉但平庸
后果好 后果糟
窦天章、完颜桃杌、苏顺、巩德中、贾虚、河南府县令、
河南府大尹、汴梁县官、过于执、周忱等
第四,若是以这些传统戏剧作为测度中国民间观念的标识,(注:关于传统戏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般民众的观念,我在《德主刑辅的政法制度》(未刊稿)中另有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的道德意义上的清官情结主要集中在执法上,在司法上这种道德情结并不非常强烈。若是从总体格局上看,这些戏剧还反映出,剧作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真正关心的实际是审判的结果,而不是审判者的个人人品,他们只是为了审判结果才看重审判者的人品;同样,如同他们不反对清官搞刑讯逼供所显示的,他们也不关心所谓的“程序”本身的“正义”,而是程序的普遍适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传统公案剧的表达有强烈且浓厚的道德主义和意图主义倾向,但内容透露的却是一种后果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司法哲学倾向。(注:这一点与波斯纳在《法理学研究》中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新译本),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特别是最后一章。不同点在于,波斯纳是从司法者的角度切入得出这一结论的,而中国传统戏剧反映的是剧作者和民众对司法审判的愿望和要求。)
第五,在这些戏剧中,官员的审判能力问题仍然是作为一般的道德问题提出来的。尽管按照今天的社会舆论,我认为把能力问题简单转化为一般的道德问题可能是一种认识论上的错误,或者是一种表达的错误,但这种转化还是可能具有这样一种寓意,即对于公职人员来说,由于其职务行为的后果严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履行公务的能力往往关涉一种特别的政治的伦理责任;据此,把官员履行公务的能力视为一种“道德”,从社会功能上看,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也是有正当性的。(注:这也许就是行政官员“引咎辞职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心理基础。可参看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37页。)
或者,这种转化体现了一种对官员的超乎对一般人的道德要求。虽然一些官员没有收受贿赂,没有舞弊,但戏剧中还是予以某种道德上的鞭挞;这不仅因为案件审判的后果糟糕,而且这些案件中的主要官员至少是道德上还不够高尚——表现为关心诉讼费的收取(例如桃杌)或个人的升迁(例如过于执)或不勤政而把“司法”大权旁落于胥吏手中(例如苏顺)。这些对于一般人来说可以宽容的不认为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一旦涉及司法,涉及人命,就具有了强烈的道德意味。
上述分析再次凸现了:在疑难案件审理问题上,在古代社会中,官员的道德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而能力和判断力更为重要。或者,更准确一些说,元杂剧中的材料显示了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司法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于民众对司法的需求而言,当时的官员司法审判能力太弱;而当时的民众(通过剧作家的表达)希望通过提高官员的个人的道德水准——或者是选拔出更多的清官或者是通过官员的个人努力——来提升他们的审判能力,履行官员的政治治理上的责任。
社会期待总是正当的,关键是官员有无可能达到这种社会期待。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分析一下官员的审判能力之构成,这种分析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相应的制度措施的缺陷。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官员的审判疑难案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官员本人的主观因素决定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构成因素是社会的和制度的,例如前两章论及的社会分工、职业化、科技和专业知识的积累。但在给定的社会、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个人因素——例如个人的智慧、勤政——仍然起很大作用,在个别案件上甚至起决定作用。包拯、况钟这样的杰出的人物就是例证。
当然,这种杰出人物很少;但我还不能仅仅用(尽管可以用)社会中这种精英很少作出强有力的反驳。人们会说,一个好的官员制度或法官遴选制度就应当把这些很少的人挑出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因此,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就必须或者展示,即使是包拯和况钟这种高度智慧的清官,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疑难案件的审判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或者是论证,即使社会中有这种能力的清官很多,一个可靠且有效的制度也只能接受(容纳得下)极少数这样的人。
因此,我转向对具体戏剧文本的分析,希望从分析中进一步展示司法中“清官”的局限性。具体的戏剧是《灰阑记》和《十五贯》。(注:张燕瑾、弥松颐(校注),《十五贯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956年,浙江省昆苏剧团进京演出了改编的《十五贯》,引起轰动,当代中国人对《十五贯》的了解主要是这个本子,朱素臣(原著),陈静等(整理):《昆曲十五贯》,香港三联书店1956年版。)我选择这两个戏剧还不仅仅因为两剧都讲了清官平反冤案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个形象分别展示了智识(能力)的限度,以及勤政(道德+能力)的限度。因此,可以从不同侧面强化本章的主题。
二、智识的限度
为达到与奸夫赵令史结婚并谋取丈夫马员外家产的目的,马员外的大老婆与赵令史合谋毒死了马员外,反诬陷是小老婆张海棠下的毒,同时又谎称张海棠的孩子是自己生的(出于怕张的孩子分享马的遗产),并贿赂了邻居和接生婆等为自己作证。张海棠被屈打成招。案件上诉到包拯那里。敏感且富有洞察力的包拯认为“药死丈夫,恶妇人也,常有这事;只是强夺正妻所生之子,是儿子怎么好强夺的?况奸夫又无指实,恐其中或有冤枉”。包拯认为此案首先应查清谁是孩子的真正生母。他命令用石灰撒了一个圈(故有灰阑之说),让孩子呆在里面;又命令张海棠和大老婆各执孩子一臂用力拉,看谁能把孩子拉出来。张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据这一人之常情判明张海棠是孩子生母,明察秋毫,进一步调查终于发现并严惩了真正的罪犯。
在这个故事中,包拯确实展示了一种基于常识的睿智和洞察力,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注:据学者考证,这个故事本土的最早原型来自东汉时应劭的《风俗通义》中黄霸的故事,此后元魏时期慧觉等翻译的《贤愚经》(卷12)中故事也曾出现。吴晓铃:“试就《高加索灰阑记》探索三题”,集于《名家解读元曲》,吕微芬编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类似的故事在《圣经》中也有记载,(注:《圣经·旧约·列王纪上》第3章,第16-27节。)同样在西方广为流传,成为历史上智慧裁判者的标志性故事。故事的广泛流传一方面反映出此案件处理确实很好:不仅裁判者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结果获得了人们一致认同,而且审判的费用也很低;此外,这种审理还有其他优点,例如,它的非专业性,其逻辑和推理是普通人都可以理解的,但在结果开示之前却很难预测,它没有丝毫神秘,出其不意但又尽在情理之中,它不是宗教奇迹,却令人赞叹不已,因此它非常具有戏剧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首先,这种“司法”如果作为一种理想和规范,那么其必定导致一种非专业化甚至是反专业化的“司法”,至少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利于司法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司法知识的积累。当然,这其实不算是一个问题,只有对于今天强调司法专业化的人(法官、律师和法学教授)这才是一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他们在社会中存在和收费的正当性。对于更广大的民众来说,专业化还是非专业化解决都不是问题,他们关心的是纠纷怎样才能顺利、公平、有效和便利地解决,并且是普遍的(作为制度),而不是作为特例。
这类故事的广泛流传的另一面反映的更可能是,这种结果很罕见。只有罕见,才能成为人们的谈话资料,才可能为人们惊叹和赞赏。试想,如果是今天遇到类似《灰阑记》式的案件,法官或其他类型的审判者只需下令做一个亲子鉴定,或DNA检验,100%不会错误;人们绝不会对这种决定赞叹不已,更不会广泛流传。稀缺赋予了其价值。因此,即使《灰阑记》不是受圣经故事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启发,在人类历史数千年中,又有几个案件是用这种方式或类似方式解决的,又有几个案件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的?我们能记得的,大约也就这两件(实际是一件)经典佳作了。因此,在我看来,《灰阑记》或《圣经》所罗门国王的故事的广泛流传更多反映的是,在传统社会中,在一个没有出生登记制度、没有现代生物化验技术的社会中,人们在亲子鉴定问题上以及推广开来在其他疑难问题上作出正确判断之困难。这一点,在另一部中国传统戏剧秦腔《三滴血》(注:秦剧《三滴血》取材于清人纪昀《阅微堂笔记》。剧情是:山西商人周仁瑞在陕西经商时,娶妻一胎生下二子后病故。周自己抚养长子天佑,次子则卖给李三娘。周经商亏本,带天佑回老家,其弟周仁祥不认侄儿天佑。仁瑞告至官府,县官晋信书以滴血之法将父子断散。李三娘为养子更名李遇春,与己女晚春订婚。后,三娘病故,恶少阮自用假造婚书逼晚春与其成婚。晋信书又以滴血之法断晚春和遇春为亲兄妹。在与阮自用的花烛之夜,晚春逃出。周仁瑞寻找天佑,遇晚春奶娘,奶娘随周仁瑞往县衙对质,晋信书竟然还以滴血之法断周仁祥与其子牛娃非血缘关系……天佑和遇春投军立功并得官,平反冤案,全家团聚。196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曾将此剧摄制为戏曲艺术片。)中又有更深刻的体现。
注意,我说的是困难,而不是说无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审判者有时还是可以运用个人的智慧在某些案件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有人能作出这样一个正确的判断并不能证明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这就像有人可以挺举200公斤,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甚或多数人都可以挺举200公斤一样。作为制度的法律,更多得依赖常人的道德和智力,而不是依赖超常人的道德和智力。毕竟戏曲中的或民间流传的包拯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多少年来,在民间还没有其他替代。事实上,包拯在民间,包括在元杂剧中的形象是一个神话了的形象。《盆儿鬼》中张敝古称包公“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生金阁》中则干脆直接出现了日断阳、夜断阴的表演。(注:无名氏:《叮叮当当盆儿鬼》,《元曲选》(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407页;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元曲选》(第4册),第1716-1736页。)而所罗门国王也是古犹太人少见的“明君”之一。
其次,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案件都无法使用这种方法。这一点在其他一些元代包公戏中就已经显露。在《元曲选》另外9出包公戏中,包拯(可以视为剧作者)在判断事实问题上都没有其他什么类似的精彩之作。事实上,包拯在此案中所使用的这种“方法”只能一次性使用,无法重复,因此是无法制度化的。它更像是猜谜,“抖包袱”,是“招法”,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法。
第三,这种方法的证据力其实也很有限。在《灰阑记》中,如果张海棠求子心切,不遗余力拽夺儿子,加上她年轻有劲,不无可能把孩子拽到自己身边。如果这样,那么她就有可能被确认为罪犯,真正的罪犯反而可能因此逃脱。并且,张海棠求子心切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首先关系到她自己的性命,其次孩子未必在争夺中受伤;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从长远来看,一旦她被处死,她的儿子也迟早会被马氏大老婆害死,因为大老婆争夺孩子并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孩子享有的财产继承权;只要财产到了手,大老婆完全会谋杀张海棠的孩子。张海棠也未必看不到这一点;如果她真正为了孩子的长远,现在争夺,哪怕受了伤,也比将来被谋杀好。包拯使用的这一招风险是非常大的,他的成功仅仅是由于张海棠的错误。(注:相比之下,所罗门国王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似乎更为合理。首先,争议双方是两个女人,除了争孩子之外,并不涉及其他利害关系;其次,所罗门国王的判决是将孩子劈成两半,这种行动不但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而且这个行动具有震撼力,很容易唤起母亲的怜子之情(拽孩子并不直接威胁孩子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放弃孩子的收益(孩子活下来)实际要比争夺孩子的收益(一个死了的半个孩子)更大。《风俗通义》中黄霸的做法也比灰阑记中的包拯更合情合理。)
由于这些原因,哪怕是包拯,在审判上也难免犯错误的时候。甚至元代就有《糊突包待制》的戏剧,(注:臧晋叔在“元曲论”一文中就收录了元代汪泽民的《糊突包待制》一剧的剧目,见臧晋叔编:《元曲选》(卷1),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页。此剧已失传。参见李春祥:《附录:元代包公戏新探》,见《元代包公戏选注》中州书画社1983版,第301页及注16。)尽管该剧本已经失传,我们无从考察错误的类型。但是从元杂剧中其他有关包拯的戏剧中,我们看到在其他一些疑难案件上,包拯除了不畏权势之外,与其他官员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涉及人命案件且没有证据时,他及其他得到元杂剧赞颂的清官同样大量使用或威胁使用刑讯。例如在《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仅仅为确认为父复仇的三个儿子中是谁先打死人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样一个问题,包拯就对三个兄弟都动用刑讯,“麻槌脑箍,六问三推,不住勘问,有甚数目,打的浑身血污。大哥声怨叫屈,官府不由分诉;二哥活受地狱,疼痛如何担负;三哥打的更毒……”。类似的例子还有《救孝子贤母不认尸》和《王翛然断杀狗劝夫》中的清官王翛然,《魔合罗》中的能吏张鼎。当遇到法律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时,包拯就利用各种法律外的手法达到目的。(注:例如,元杂剧《鲁斋郎》、《生金阁》、《陈州粜米》等剧中的包拯。)虽然,这仅仅是戏剧中的事,但这至少表明当时的戏剧家以及民众都不认为这类情节有损包拯及其他“清官”的形象;他们不认为清官就可以不或不应使用刑讯,单凭智慧就可以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事实上,在评论该剧时,今天也有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是“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和措施。这[……]正是人民大众对清官的希望”[1](P.355)。在一个缺乏获得可靠和充分证据的审判技术的社会中,哪怕是“清官”,遇到疑难案件也同样表现出无能为力,只能诉诸刑讯逼供。这种“无能”并不是官员个人的能力的问题,而是社会条件使然,也是民意使然。
智慧的限度的另一个方面是权力。尽管许多观众或读者高度赞扬包拯的智慧,但是必须注意,在审判问题上如同在许多问题上,智慧并不能自动地独立发挥作用,必须有权力的支撑,智慧和知识才可能发挥作用。(注:参看Muchel 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trans.by Colin Gordon et al.,Pantheon Books,1980.)包拯不仅是智慧的,廉洁的,更因为他是“龙图待制天章阁大学士”,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包拯的智慧就无从发挥作用——尽管受众在谈论清官包拯时,总是有意无意省略了,因此也就掩盖了这个权力的维度。事实上,在元杂剧中这一点得到了反复强调。《灰阑记》中包拯登场时,首先提到的就是他“手揽金牌势剑”,“官拜龙图待制天章阁学士,正授南衙开封府府尹之职。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容老夫先斩后奏”。在其他元杂剧的包公戏中几乎也都有类似的说法。(注:未公开提及包拯权势的元杂剧中的包公戏有《合同文字》、《神奴儿》。)但由于包拯形象在中国社会早已符号化,(注:赵景深先生曾把包公故事中与其他清官相似的故事作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包拯就是钱和、黄霸、张咏、周新、刘奕、膝大尹、向敏中、李若水、许进等人,不过是一个吸收传说的人罢了。”转引自段宝林:《关于包公的人类学思考》,《光明日报》1999年5月6日,第7版。)观众也早已预设他有巨大的权力。
必须指出,包拯的权力还不是一般的权力,他的权力远远超过了一般官员的权力,他可以“随意刷卷”处置、乃至可以“先斩后奏”。清官包拯的智慧必须依赖这种权力才能发生作用,看来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更懂得后现代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而这就意味着,一旦遇到一个更大的甚或是同样的权力时,这种智慧的局限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元杂剧的其他一些包公戏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在《鲁斋郎》中,包拯为了处死霸占民女的权豪势要鲁斋郎,他就无法运用他的权势了,他只能先奏请鱼齊即死刑,然后擅自将“鱼齊即”三字改为“鲁齋郎”,才达到了其目的。而这种做法不仅非法,而且令人可怕,令人不可思议。尽管这是戏剧情节,但其中阐明的道理是一般的:智慧的力量是有限度的。
必须把包拯的这种权力的意味说得更清楚一些。包拯握有的这种权力实际是一种合法的(legitimate)超越法律制度的权力:他可以超越当时法定管辖制度(随意刷卷)和程序(先斩后奏)行使权力。鉴于任何社会都可能出现一些制度和程序无法合情合理解决的案件,因此在几乎一切社会内,都赋予社会中的位居特定职位的个人享有这种超越法律的权力,例如在美国,总统和州长的特别赦免权。这是任何制度都必须有的为应付不测事件或特殊情况的紧急出口(太平门)。但是这种权力是极端危险的,因为它是在常规法律制度之外行使的。你可以追求,却无法事先保证只有“好人”才获得这种权力,(注:元杂剧中就有表现贪官利用获得的这种法外的合法权力祸国殃民的。例如,《包待制陈州粜米》中刘衙内儿子小衙内就获得了“敕赐紫金锤”,可以打死人勿论(《元曲选》卷1,第34页)。)也无法保证“好人”的每一次使用都是正确的、智慧的。(注:例如,在《魔合罗》和《勘头巾》中的府尹完颜,尽管也有心“除邪秉正”,有“势剑金牌”,可以“先斩后奏”(《元曲选》卷4,第1376页),但是由于智慧不够,结果都是险些中了污吏的诡计,犯下大错。)甚至,即使在此不考虑、不讨论这些危险性,我还要强调,只有在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权力才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才有可能;并且永远只能作为制度的补充(紧急出口)。只要设想一下,不用说全部官员,哪怕一个社会中有一半甚至更少的官员有这种授权,即使他们都清廉爱民和聪明智慧,但只要他们的意见还会有什么分歧(而这在审判中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并经常发生的),就会有一个谁可以更随意,谁可以更先斩后奏的权力之争。事实上,这种权力一旦多了,制度就必定一片混乱,根本无法运转。这种权力必须是独占(垄断)的,至少在一定的管辖中是独占的。同一管辖中不得有两个以上的这种权力,哪怕是智慧的权力。这也就注定了智慧的限度,注定了没有哪一个制度能够容纳下很多这样的智慧的权力。我们在《魔合罗》中就看到张鼎的智慧、在东海孝妇的故事中就看到了狱吏于公的智慧,都受到了权力的某种制约,甚至完全不起作用。而在下面讨论的《十五贯》中的清官况钟身上,我们可以更明显看到这种制约。
三、勤政的限度
除了不畏权势和智慧外,理想“清官”的另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勤政。勤政一方面既是“清官”爱民的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确实可以补智慧之不足。因此,如果不可能有很多智慧高超的清官,那么智力一般的清官是否可能通过勤政来保证正确的审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得到了许多中国人的赞赏,似乎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判断。明代戏剧《十五贯》中的况钟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勤政(但不仅仅是勤政)因此防止了冤狱发生的典型例证。但是,我们将看到,即使《十五贯》也从另一方面证明勤政对正确审判的贡献是有限的。
因家贫,屠夫游(改编本为尤)葫芦从姐姐那里借来15贯钱,回家后对继女苏戍娟戏称已将苏卖给他人做小老婆了,苏痛苦不堪,天亮前乘父亲熟睡时出走,去姑姑家。当地赌徒娄阿鼠碰巧发现游葫芦家门虚掩,入室行窃,惊醒了游葫芦,搏斗中,娄阿鼠情急杀人,用肉斧(砍肉的斧头)杀死了游葫芦。次日晨,邻居发现游葫芦被杀,追上苏戍娟以及苏在途中遇到并结伴同行的回家书生熊友兰(熊身上同样携带了15贯钱),将他们带回见县官。当地县官过于执“决意要作清官”,认定:苏戍娟与熊友兰通奸,杀死游葫芦,携钱逃跑。大刑之下,苏戍娟和熊友兰屈打成招。此案经“三审六推”,经中央政府批准处死。临刑前,监斩的苏州太守况钟发现了诸多疑点,力劝苏州巡抚、都察御史周忱,终于获准重新调查。经实地调查,况钟不仅确定苏熊确为冤屈,又发现娄阿鼠的可疑。况钟扮作测字先生,四处追捕,发现了娄阿鼠。他揣摩娄阿鼠心理,诱使娄阿鼠说出真情,真相大白人间。(注:这里的简介主要依据1956年昆剧改编的《十五贯》,改编本的最大好处是简化了原本过于复杂的线索,消除了原本中况钟得神明托梦指点的情节。但是1956年版本也有其弱点,受当时的社会政治影响,改编本加重了原本中实际上相当淡化的官员本身的道德色彩,因此把司法问题更多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淹没了该剧的司法理论意义的问题,因此,在分析故事人物性格时,我将仍主要依据原本。)
在这个戏剧的原本中,况钟的形象比任何元杂剧中的包拯都丰满得多,剧中的其他人物以及故事都相当合情合理。但在我看来最有意义的是,该剧并没有着力表现况钟有什么特别的独到的能力,没有过分强调他与其他官吏的道德差别和能力差别。在我阅读的有限传统戏剧中,这可能是最有意义的,它几乎展现了古代社会“司法”合理性中的全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中的合理性。
例如,在这个剧中,没有一个贪官的形象,县官过于执与都察御史周忱都基本是为人正派的官员,尽管在履行职务上是作为况钟的对立面出现的。县官过于执作出的判决尽管错了,然而,这种错误固然有他作为行政官员追求政绩的因素,(注:关于这一点的更细致的分析,请参看苏力:《制度角色和制度能力》,《法商研究》(即出)。)但总体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是难免的,即使是况钟在他的位置上未必不会作出类似的判决。因为各方面的证据对苏戍娟和熊友兰都太不利了:苏戍娟是随母改嫁到游葫芦家的,而且“继父不仁,母亲复怄气而死。现今家道艰难,饥寒不免,[继父]并无好言相慰,反加非打即骂”[2](P.213),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苏戍娟有报复的潜在动力;熊友兰身边携带的钱与游葫芦失窃的钱数量相同;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强调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条件下,很难设想一对陌生男女结伴夜行而没有私情。如果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没有出现其他可疑者的情况下,一般的人都会认为苏熊二人是杀人凶手。事实上,游葫芦的邻居就断定“一定是[游的]女儿与人私通,觑得父亲有钱十五贯,暗下约了汉子,谋财害命,一同脱逃去了”;邻居和公差追上苏熊二人后,也立刻认定熊为奸夫;连借钱给游葫芦的姐姐(也即苏戍娟的姑妈)也当即认定苏戍娟杀死了自己的兄弟,指证熊友兰身上带的钱就是“老身昨日亲手交付我兄弟去的”,并表示“记深仇,食肉寝皮”,最后也作为受害人家属出庭作证。而相反的证据没有,或不能落实。例如,熊友兰提出了借钱给自己的证人,但由于证人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因此官府到了指定地方却查无此人。在这样的人证、物证面前,过于执认为“此事真确无议了”;甚至熊友兰自己都觉得“则么怨着问官?别人的枉事,须有个冤家仇对,装砌而成,偏是[……]我的冤枉,分明是天造地设一般,自家走到死路上去!”并问上苍,“这疑案怎决?这疑案怎决?”
但是在戏剧中,况钟质疑此案,也同样合理和可信。况钟在此案中是监斩官,面对的是苏熊的喊冤叫屈;阅卷后,他发现案件有嫌疑。况钟产生这种怀疑固然可能与况钟的个人气质、性格和敏感程度有关,但更与他同过于执的明显不同的经历有关。况钟“本是吏员出身”,而过于执是“十年窗下揣摩成,早年甲榜荣登”。并且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同过于执的职务位置、责任和追求不同。况钟的责任是监斩,是案件的复审,他的主要职责包括了刀下没有冤魂,因此他要比过于执对行刑的责任更为敏感。从制度上也有根据,因为“《会典》上原载有一款,‘凡死囚临刑叫冤者,许再与勘问陈奏’”,这就是允许监斩官根据新的信息作出新的反应。监斩官的位置使得况钟获得了这种信息,而过于执在初审时不可能获得这种信息。此外,况钟的位置(上诉审)也使得他脱离了当地民众的政治性压力,他可以更平衡地考虑相关的证据和信息;而过于执是相对年轻的行政官员,政治上一路顺风,而且有更大的政治雄心(也可以说是野心)——“河阳春色权支领,伫看万里功名”,因此,急于回应当地民意,着意表现自己的政绩,其中包括他的“爱民犹子,执法如山”。所有这些差别,都使得况钟对哪怕是微小的疑点也更为敏感,尽管这些疑点还不足以推翻判决,但足以使这位“虽以刀笔出身,未尝失于学问”,认为“时人莫谩轻刀笔,千古萧曹相业推”的比较年长的地方长官质疑该判决。
冒着罚俸降级之风险,况钟劝说都察御史周忱复查,双方展开了一场中国传统戏剧中我所仅见的法条主义(周忱)与现实主义(况钟)的争论。周忱以“三推六审”已经结束、判决必须坚决执行的程序主义为根据反对重审;况钟则以案件有疑点、事关人命的政治现实主义、道德主义为基础展开辩论,并以自己的官爵俸禄作担保,最终说服了周忱(这意味着周忱最终也屈服于现实主义,放弃了法条主义),并从周忱那里获得了跨管辖的“司法”特权(令箭,即上一节讨论的权力问题),到案件发生地进行调查。况钟重临凶杀犯罪现场(此后叙述根据改编本),他发现了一系列新的证据。他发现“家无隔夜之粮”的游家地上竟然有不少散落的铜板,使得况钟推测地上的铜板是有人同游葫芦搏斗中散落的;而熊友兰身上携带的15贯钱一文不少;他还发现了娄阿鼠遗忘在游家的赌具骰子,而游葫芦从不赌博,由此引起了况钟对娄阿鼠的关注,开始调查娄阿鼠。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娄阿鼠杀人,甚至无法将之逮捕,更没有理由刑讯逼供(刑讯必须有比较充分的证据才能动用)。况钟因此扮成测字先生,利用老鼠偷油(游)的说法诈取娄阿鼠的真话,终于使得真相大白。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案件,就反映社会现实和“司法”制度现实而言比元杂剧中的任何公案剧都更为深刻,特别是改编本删除了神明托梦,凸现了况钟的智慧,对事实的敏感、细致,对案件当事人的高度责任心,深入实际、注重调查、勤政爱民、不媚上,据理力争等等。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此案中看到在审判问题上勤政的限度。
例如,在此剧中,由于没有专门的职业治安和侦察人员,我们看到,甚至太守况钟都不得不到现场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况钟扮演了现代社会的刑警、法医和检察官的角色。在调查娄阿鼠是否罪犯的过程中,况钟还扮演了现代的卧底侦探的角色,而且他还必须了解犯罪心理学。这些角色不仅与况钟的行政官员身份冲突,而且与现代社会中职业法官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区别。现代法官的主要职责是根据双方提出的证据作出明智审慎的判断,其判断依靠的是一个支持性的制度系统和人员、技术、资金。况钟没有这种制度的依赖,他必须自己独自搜集、发现证据,进而作出判断。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知识,而人的智力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即使从理论上说他可以且应当了解各种知识,但是——且不说当时的社会是否有这些系统的知识——即使有这些知识,他也只会是一个“样样通,样样松”的官员,而不可能在多方面都是一位专家。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可以看到,在《十五贯》中,况钟,就如同其他戏剧中的其他官员一样,所运用的知识都更多是常识,而不是专家的知识和洞察力,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供的信息。《灰阑记》中包拯运用的招数以及这些招数所依赖的知识也都是非司法的知识。这也就是说,在这种制度条件下,作为总揽行政、“司法”的官员很难成为真正审理案件的专家。推展开来,在传统社会中,就很难出现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队伍,很难出现专业化的分工并累积专业化的知识。勤政有可能部分弥补知识的缺陷,但至少在一些需要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些知识。
不仅在专业知识上如此,在人力和财力资源上也是如此。在《十五贯》中我们看到的是深入调查的况钟,但是这毕竟是戏剧,这里涉及到两个人的性命,并且剧中反映出来的也只有这一个案件,所以况钟有可能、也有激励深入调查,并且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来调查娄阿鼠。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案件数量相对比较多一些(比方说一周一件),如果案件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甚至不涉及生命,仅仅涉及财产或伤害案,如果况钟有繁重的行政事务,我们就可以推断,即使是况钟,即使况钟有更大道德责任感和事业心,他也不可能总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苏熊案。况钟可以在个别案件上这样做,但在其他案件上,他可能就不得不如同都察御史周忱一样,尊重地方官过于执的判断,尊重“三推六审”的结果。而这就意味着在其他大多数案件上他不可能扮演清官的角色,不可能明镜高悬。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其他案件所涉及的许多希望官员为民作主的原被告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来说,况钟就会在这些案件上被视为一位庸官或昏官。
还要指出,尽管这种选择性的深入复查要比根本不调查要好,但由于是否复查的决定完全取决于官员自己的意愿,因此,这就不是一种严格的制度,它对官员没有强制性和约束力,而必须且完全取决于官员的个人道德感和责任心。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根本局限——缺乏制度的约束,这是一个无论是智慧还是勤政都无法突破的局限。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员道德进入传统“司法”的必然性,对于这后一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
从理论上看,况钟调查发现的这些信息并不是只有况钟才可能发现,过于执也应当能发现;但是,如同上面分析的,由况钟发现,根据和理由都更充分。不仅由于况钟是“刀笔出身”,有更多的审判经验,也不仅因为况钟与过于执的制度角色和面对的压力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是况钟已经对苏熊二人有罪产生了怀疑,并且由于他请求了刀下留人,如果他不能查清苏熊无辜,就有可能受到一系列处罚。因此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他个人的利益来说,况钟都会更注意那些有利于苏熊二人推翻已定判决的证据。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在过于执的位置上,况钟就不大可能那么勤政,也没有全力为苏熊平反的动力。
四、严格责任——司法“人治”的另一面
指出智慧和勤政的局限并不意味着要否弃它们。当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时,或当想像中有替代(而想像中总是有的),但现实上还不可能实现时,也许惟一的出路也就只能是抱残守缺,维系现状,最多作些微象征性的调整,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很“不道德”,“不正确”,但这是一个也许颠扑不破的生活的真理。因此,重要的不仅是要指出智慧和勤勉的局限,清官的局限,这里面还隐含了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司法”而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当这两者结合时,呈现的实际是一个司法的人治模式,即在当时的社会科学技术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审判的有效运作在更大程度上只能取决于案件裁判者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勤政爱民。(注:但必须注意,我在此讨论的并不是一个社会的人治与法治,而是司法上的人治。)
司法上的“人治”模式当然有很多问题,学者对此也有过不少讨论,例如容易滥用权力、贪污舞弊、以言代法、非专业化等等。鉴于这类分析批判已经很多,我在此不再多言。
我想在此讨论的是人治模式的另一方面,不仅至今没有学者讨论,而且在许多当代中国法学家那里还常常被错误地作为所谓的“值得借鉴的”中国古代社会“法治”的特点,这就是,一旦发现官员“刑名违错”,即使没有贪污和徇私舞弊的行为,案件审理裁判者也会受到相当严厉的制裁。例如,在《窦娥冤》中,已经调任的前任楚州太守桃杌,仅仅因刑名违错,就被“杖一百,永不叙用”[3](P.1517)。这种情况在其他元杂剧中也曾屡屡出现。(注:在《灰阑记》中郑州太守苏顺因“刑名违错,革去官带为民,永不叙用”;在《神奴儿》中“本处官吏,不知法律,错勘平人,各杖一百,永不叙用”;在《救孝子》中“本处官吏,刑名违错,杖一百,永不叙用”;在《魔合罗》中,“本处官吏不才,杖一百,永不叙用”等等。)
这种强调案件审理者个人责任的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通说以及西方现代国家的司法实践相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现代司法制度中,除了发现法官徇私枉法,法官不会因其智力不足或不够勤勉(注:波斯纳法官——基于美国的制度条件——甚至认为,法官应当“懒一点”。请看Richard A.Posner,Overcoming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ed,3。)而出现的“刑名”错误而个人受到制裁,最多是其案件被发回重审。法官判了错案,哪怕是冤案,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法官有舞弊行为,都会受到豁免;其错误会被视为是制度的错误。当然,这样处理司法错误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官的决定确实有其他制度因素的参与,例如陪审团的定罪或检方的指控,或证据的错误,或证人的诚实与否和过失等等。因此,在现代司法制度中,法官的个人责任实际上是大大减轻了,而不是如同当代一些中国法学家的司法改革建议的那样——例如错案追究制——更强调法官的个人责任。(注:近年来,一个最典型的案件就是2002年11月4日,广东省四会县人民法院法官莫兆军因案件当事人喝农药自杀以示清白,被以玩忽职守罪起诉。尽管,2004年6月29日,广东省高院终审裁定莫兆军无罪释放,但是这一结果几乎完全是一种万幸。据广东省的法官称,如果莫兆军曾经与另一方当事人有任何其他交往,就很难被无罪释放。而且尽管无罪释放,莫兆军至今还是“回家养猪”,是否“永不叙用”至少现在还没有结果。请参看,“无罪法官回家养猪,莫兆军的悲剧结束了吗?”《新快报》,2004年8月3日,第A11版。又请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4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强调:中国的传统的哪怕是“司法”制度采用的也是一种人治和德治导向的模式,而不是法治的模式。(注:当然,对我的这种比较必须加以限制。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案件裁判者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而且,尽管使他受罚的事件具有“司法”性质,但他却不是作为法官被惩罚的,而是作为行政官员受到处罚的。其次,现代司法中法官个人责任的减轻是因为制度的发展,其中包括司法作为一个单独的部门从其他政治性机构中分离出来了,减轻法官的个人责任据说是为了维护司法独立;而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不仅司法行政合一,而且没有其他支持司法部门运作的其他部门,因此也就没有理由减轻案件裁判者的责任。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社会强调案件裁判者个人责任的原因之一。)
一定会有很多人会质疑这些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对官员的惩罚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我并不把戏剧所反映的都当作现实,但是在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戏剧与现实差距不会太大。除了有关的实证材料外,我的主要根据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逻辑推论。第一,这实际上是对官员实行一种相当于现代法律制度上的“严格责任制”,而不是“过错责任制”。这是由于在传统社会中(无论中西方),信息获得不易,除了在某些具体的很容易获得相关信息的案件中,在各个法律部门中,一般都采取了严格责任制,(注:参看,Richard A.Posner,Economic of Justi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特别是第6章。)古代的“行政法”自然也不可能远离这一逻辑。事实上,只是到了近代以后,过失责任才在法律理论中,特别是在许多部门中流行起来。从制度上来看,当时在“行政法”上采取严格责任制有一定的道理,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大大降低信息成本。只要发现“刑名违错”,不需要调查审案官员是否贪污受贿,是否徇私舞弊,就可以惩戒官吏,“刑杖一百,永不叙用”。而一旦要求考察官员刑名违错的原因是故意还是过失,是否徇私枉法,是否收受了贿赂,是因为裁判者的知识不足还是因为他的道德缺陷,并要求提出具体证据予以证明,这就势必大大提高传统中国官吏管理的制度成本,甚至会使制度无法运作。因此强调官员的个人责任,采取严格责任原则,这种人治模式在当时社会中是一种比过错责任更有效率的管理和治理制度。
还有一个因素促成了这种责任制不仅严格,而且严厉,这同样与信息成本太高相关联。由于信息费用高,大量过失造成刑名违错的官员和胥吏实际上不可能被发现,如果不是窦天章来刷卷,窦娥之冤实际上无法昭雪,因此就现实而言,官员因刑名违错而受到惩罚的概率相当低。这就意味着,即使是严格责任制,但对官吏的实际威慑力还是偏低。为了保证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威慑力,就势必加重法定的处罚,由此导致了更为严厉的个人责任制。(注:这里的逻辑和刑法惩罚的逻辑是一样的,假定迫使官员勤政廉洁的惩罚是x。X=pS,在这里p为发现官吏不勤政廉洁的概率,S为法定的惩罚。那么当信息成本过高而降低概率p时,要保证足够的X,就势必增大S即法定的惩罚。这一点也是近代以前的刑事惩罚普遍更为严厉的因素之一。)
当然严厉性还表现为对那些有过错但未必道德恶劣的官吏,社会(通过戏剧)往往施加了额外的道德和舆论谴责,而细心的法律人会发现,现代的严格责任制一般不对加害人作道德评价的。为什么古代的和现代的严格责任制之间会有这种差别?而且,我在前面章节中也指出,元杂剧以及许多传统戏剧都表现出许多在今天的分析中被证明更多是由于信息、知识和技术而发生的问题,往往被转化为官员的个人道德问题。为什么?
首先,由于信息费用太高,人们(而不是政府)在来不及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倾向于首先对无法容忍的行为作出道德判断。一个人伤害了我,而我无法判定他的意图,为了更有效保护自己,我会首先判断对方对我有恶意。这种判断是人类在生物进化中形成的一种便利且有效率的自卫机制,它会促使人们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如果一个人受到伤害总是首先推定加害者无心,在社会生活中就太容易受伤害,甚至被毁灭。要注意,说到误解,基本都是善良意图被误解为用心险恶了,而不是邪恶用心被误解为善良用心了。
其次,现代法律上的严格责任制是一种法律的制度,其目的一是为了降低法律制度的运作成本,因此不考虑违法者的主观精神状态;二是强调对伤害的实际救济并可能予以救济,因此一般可以不对侵害行为作道德判断。而本文在此分析的不是政府的正式制裁(“刑杖一百,永不叙用”),而是传统社会民众(通过剧作家)对官吏审判错误的社会评价;社会的评价一般说来只能是道德的和舆论的。此外,官吏的审判错误的后果往往特别严重,通常无法由官吏本人补救(即使可能对这些官吏也不公道),也没有财力通过国家赔偿之类的制度予以救助,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将有过错的官吏撤职往往会显得制裁力度不足。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社会自然会以道德和舆论的制裁来补足和强化法律的制裁。
五、严格责任的有效性
对于这种严厉的严格责任制,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大致说来,当代中国的法学家可能会有这样两类评价,一是从“人道主义”的刑法哲学出发,认为这种惩罚不仅过于严厉,而且不考虑官吏的主观过错,因此对这种严格责任制持批判态度;另一种是从“民主”的政治哲学出发,认为为了保证政治的清廉,审判的公正,防止官吏草菅人命,徇私舞弊,应当实行严格追究官吏责任的严格责任制。但是,我认为这两种进路都是错误的,都是试图从一种先验“正确的”政治理念或信条出发,从原则出发,而不关心这种制度的实际效果。在我看来,法学家更应当探讨的是一个事实问题,即这种严厉的责任制度是否减少了或可能减少刑名违错,增进了社会的福利;换言之,我们应当关心的是,这个制度是否有效。
从理论分析上看,这种严厉的严格责任制也未必能够减少刑名违错,未必能保证有效的审判。因为,尽管奖惩机制对官吏的行为有一定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会促使官吏更为公正和勤勉。但是,就总体而言,在审判中,严格责任制对提升审判质量、防止裁判错误的影响不会很大。
首先,在一般的情况下,影响裁判的正确与否的变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的,例如科学技术和劳动的专业分工(即制度),而在传统社会的条件下,这两个变量基本上是长期稳定的。另一方面是审判者主观方面的,即官员的智慧和勤政。这四个变量中,严格的奖惩对科学技术、专业分工和审判者的个人智慧都不起或几乎不起作用。奖惩不可能促使科技变革,也不可能促成或加快社会的劳动分工,更无法使审判者变得聪明起来。奖惩因此最多只能对官吏的勤奋有某些激励作用。还必须注意,尽管我无法进行精确的计算,但可以肯定,这四个变量对于正确审判的贡献率也不是相等的。从长远来看,在无人偏私或无人有意徇私舞弊的前提下,真正能促成有效且公正审判的主要变量可能是科学技术、劳动分工(制度)。但是这两个因素以及个人智慧又都是长期稳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勤政对减少刑名违错的贡献会非常小。
其次,勤政即使对正确裁判有所贡献,但由于任何投入的收益都会呈边际效用递减,那么到一定限度后,勤政的实际效用甚至会为负。这也就意味着,即使严厉的严格责任制可以促使官员为避免受到惩罚而勤政,但也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善审判。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严格责任制可能促使官吏更不负责任,更不勤政。这个逻辑推论似乎违反直觉。但是,历史上并不缺少这样的例证,严格的吏治并没有导致制度设计者意图的长久的清廉吏治。(注:参见葛健雄:《重读〈明史·海瑞传〉》,http://218.21.62.195/sx/000722/10.html。)当然,这种枚举法的说服力可能不够,因此,必须从理论上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
如果假定减少刑名违错的基本变量是长期稳定的科技、制度和审判者的智慧,并且这些变量都不受严格责任制的影响,受严格责任制影响的勤政变量对正确审判的贡献率又很小,那么官吏就没有太多的勤政动力。因为,由于科技落后、缺乏司法上的劳动分工以及智慧的限度,任何人的审判都难免有一定数量的错案,勤政不勤政就不会对减少错案有多大差别,这也就意味着勤政或不勤政的官吏因错案受追究的概率几乎是相同的。由于严格责任制完全不考虑勤政的因素,这种做法实际上有鼓励官吏不勤政的倾向。因为只有当勤政和不勤政有不同收益,并且这种收益与投入(勤政)相称时,官吏才会勤政。反之,如果勤政者需要有额外的大量投入,却没有额外的或只有少得可怜的收益,久而久之,势必使勤政者也不勤政了。如果一个勤政官吏一生有5%的概率因刑名违错被“杖一百,永不叙用”,而一个不勤政的官吏一生有5.1%的概率甚或完全相同的概率因刑名违错被“杖一百,永不叙用”,官员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勤政了。官吏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对成本进行比较收益之分析的。他们更可能把时间、精力用于建立关系网络甚或休闲而不是用于勤政,因此从前者获得的实际收益(减少自己因刑名违错受到惩罚的概率或获得的享受)——可能要比从后者获得的实际收益(减少的因刑名违错而受惩罚之概率)要大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官员来说,是否愿意勤政的关键是受奖惩的概率,而不是刑名违错发生的概率。由于传统社会中信息费用和监督费用高昂,真正能发现并证实有刑名违错的,概率会很低,几乎是完全随机的。如同我所分析的,即使是窦娥之冤,如果不是窦娥的父亲来“刷卷”,如果没有超自然的证据,如果没有窦娥的冤魂,也就不可能得到昭雪。(注:请看苏力:《窦娥之冤》,《中国社会科学》(即出)。)
这也就意味着,在传统社会的社会历史技术条件下,严格责任制基本起不到激励官员勤政的作用。因此,这也就可以解释,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刑名差错之官吏的制裁要比现代国家对有类似错误之法官的制裁严厉得多,更强调个人责任,但是前者的激励效果却很不明显。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在“司法”制度上的人治模式落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我只是反对法官的严格责任制,特别是认为,在传统社会条件下,严厉的法官严格责任制会起负作用。而且,我的分析是假定科学技术和司法制度这两个制约因素的影响力很大。由于现代的科技条件发展,司法制度的完善,这两个制约因素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也就意味着,勤政的因素对法官作出审判正确判断的贡献有可能增加了。在这种现代条件下,废除严格责任制,采取更为严谨的过失责任制,对法官的激励作用会更大,法官也会更重视个人的荣誉,因为法官的个人努力有可能获得相应的实质性的个人回报了。这也许可以解说,为什么在当代科技发达、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的法官,一般说来,没有采取严格责任制,法官就总体说来却更廉洁自律;而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当代中国的法官,一般说来不那么廉洁自律。
我说的是在现代科技和制度条件下,更严谨的过失责任制对法官的勤政的有效激励更大,这并不是说,所有生活在现代的国家都可以采取更严谨的过失责任制。在这里,现代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概念。因此,当代某个社会是否应采取这种制度,这与上面的分析不同,这不是概念演绎可能完成的,而必须首先关心具体的事实。就中国而言,就必须调查,至少要有一个基于经验研究基础之上的估计,在审判上科学技术以及相关制度对正确审判的贡献率,要了解发现审判过错的概率。甚至要考虑发现审判错误和区分审判错误的成本。但是,即使如此,这一分析也表明,在技术制度条件不完善的条件下,对于审判官员,过于严格的责任制对激励法官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
因此本文也就勾勒了传统“司法”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特点发生和存在的根本逻辑。即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在信息费用,特别发现事实真相的信息费用很高的社会,也就是没有科学技术发现事实真相作出恰当判断的社会或场合),一方面使得刑讯逼供成为必须,另一方面又使得社会过多强调审判者的个人智力,强调个人的勤政,从而构成了案件审理上的人治模式。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信息费用过高,而绝大多数官吏都是普通道德水平和智力能力的人,个人的任何努力,例如勤政,对正确决定案件至多只有边际的影响,不足以较大程度地降低审判上的错误。也是由于信息费用过高,就难以监督和确定官吏是否廉政勤政,也难以发现——至少是——某些官吏腐败。为了保证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政府一方面通过减少“司法”来防止官员扰民,因此“司法”难以发展,司法知识难以积累,有更好出路的社会精英一般也不愿研习司法;而另一方面政府在刑名违错上实行了相当严厉的个人严格责任制。严格责任制固然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激励某些个人因素,有助于裁判的效率和公正,但超过一定限度,至少在某些条件下,甚至有促成官员们懒惰、推卸责任甚至腐败的作用,而不是相反。从比较成本收益的角度,官员们因此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联络上级,建立关系网和保护伞,而不是用于包括审理案件的公务上;而这就留下了一些空间,令至少是部分胥吏可以上下其手。
这不仅再次从另一个侧面重申了本文的主题:“司法”人治模式的限度或弊端,而且从理论上更深刻地批判了,而不单是从道义上谴责了传统中国社会“司法”上的清官模式的德治传统。此外,这一论证甚至对今天的某些制度改革,例如目前在司法界采取的笼统的错案追究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试图重复古代的严格责任制),也不无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