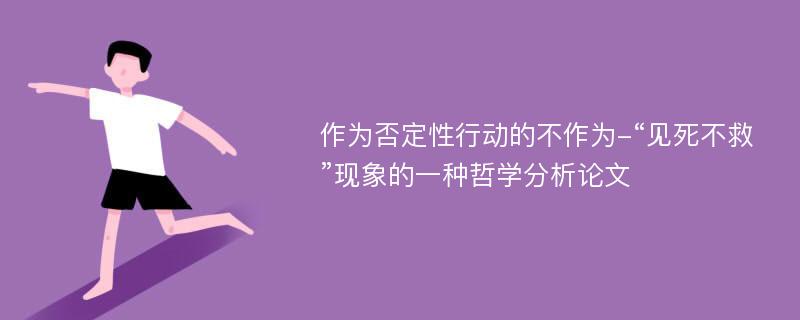
作为否定性行动的不作为
——“见死不救”现象的一种哲学分析
胡中俊1,田 静2
(1.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2.南京中医药大学 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一般认为,“见死不救”是不作为。然而,这种理解却不能充分地展现它的内在机制。按照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对行动的分类,“见死不救”这样一种不作为也可看作为一种特殊的行动。尽管“见死不救”这一现象的发生受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整个社会缺乏信任的一个缩影,但从行动主体的角度来看,未施救事实的发生只有两种可能:其一,能救但没有救;其二,不能救而没有救。“见死不救”行为的特征在于主体“不救意向”和“不救行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它能够被看作行动的一个重要理由。将“见死不救”视为否定性行动是一种更深刻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它将有助于唤醒人们的主体意识,主动成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参与者。
关键词: 见死不救;道德冷漠;不作为;道德建设;否定性行动
一 引言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中道德失范事件时有发生,而“见死不救”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道德冷漠现象之一。例如,2017年4月21日,河南驻马店一名女子在斑马线遭车辆两次碾压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一女子被一辆红色出租车撞倒在斑马线上。62秒后,倒地女子遭到一辆SUV二次碾压。事发后,过往车辆和行人减速绕行,但无人上前移动或者保护该女子。这起交通肇事案件,让不少人想起了2011年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回顾两起交通肇事逃逸事件,虽然肇事司机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但路人的“集体冷漠”仍然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和热议。“见死不救”事件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见死不救”事件的发生,既反映了在公共生活中公共秩序不够良好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现代社会中存在着麻木不仁的旁观现象。
“见死不救”现象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一个关乎公民道德建设的难题。学界对“见死不救”的讨论大概可以分为法律和伦理两个层面。在法律层面,有学者不支持设立“见死不救罪”,理由在于:“(1)入刑缺乏心理基础;(2)入刑是对道德的绑架;(3)入刑的权利资源不足;(4)入刑难以操作;(5)入刑将导致群体性的规避。”[1](P139-140)在伦理层面,有学者认为要超越这一类冷漠的道德旁观现象,需要形成“公正回报机制的全面构建、公民意识教育的深度推进、道德自我的限制与反省”[2](P21-22)这一三维路径;也有学者强调:“陌生人之间之所以不讲道德,是因为目前陌生人的伦理归属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当前所要做的就是构建一种基于中国市场经济现状的伦理体系,并形成具体的道德规范。”[3](P62-63)本文既不从伦理学的角度,也不从法律的角度对“见死不救”进行讨论,而是从行动哲学这一全新的角度对“见死不救”本身做出一种较为全面客观的分析,以期加深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屋顶早趴满了人,我们来得迟,只能趴在屋檐边。还是老婆想得周到,带了床大被子,我们一家四口挤在被子下。有被子也不管用,我们仍冻得直抖。
二 “见死不救”现象涉及的三类命题——认知、事实和规范
“见死不救”这个表达最早出自于元代关汉卿《救风尘》的第二折“你做的今见死不救,羞见这桃园中杀马宰乌牛”。它的意思是,看见别人有急难而不去救援。我们给“见死不救”加上主语和宾语,就可以得到“见死不救”的完整的一般形式,S见到P要死(有急难)而不去救。
S和P可能是存在职务关系或者义务救助关系的主体,比如正在火灾现场的消防员与火灾中的受难者,也可能是不具有上述关系的普通公民,比如旁观的邻居、行人和被车子碾压的受害者。对于第一种情况基本没有争议,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在这种情形下,S应该去救P,因为S有义务去救P;如果S不进行施救,那么,S的行为将是一种放弃职守的渎职行为。而对于第二种情况,S和P可能是熟人,也可能是陌生人,在熟人的情形下,S一般都会救P;而在陌生人的情形下,S很可能就不对P进行施救,而我们通常激烈争论的“见死不救”的情形正属于这一种。
那么,“见死不救”究竟复杂在何处呢?从表面上看,它意味着两个命题的合取:<S知道P有急难>[注] 本文中“< > ”是表达命题的符号,这里的<S知道P有急难> 代表命题S知道P有急难。后同。 并且<S没有救P>。可以看出,前者是个认知命题,而后者是个事实命题。当我们从法律或道德的角度,对“见死不救”进行争论时,实际上,我们是在上述合取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另一个命题<S应该救P>(或者<S不应该救P>)。命题<S应该救P>既不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也不是对S主观的认知状态的一种断定,而是对S如何行动提出某种命令或规定,因而它实际上是一个规范命题或者道义命题。
显然,这一事实的发生是S的表现直接导致的。那么,如何看待S这样的一种表现?一般的理解是把这样的表现看作为一种“不作为”。关于“不作为”,美国哲学家雷斯彻(Nicholas Rescher)曾这样准确地给出两种区分:“一个是克制:当坐在书桌旁写作时,我可能会克制去搔一只蚊子的叮咬而形成的痒痒——那就是‘我克制自己’或‘克制自己’做出某个行动。这种克制某人做出某事不同于接下来要说明的第二种不作为。当我坐在桌旁写作时,会有无数多的事我没有做:读报,和朋友聊天,驾驶一辆车等等。但是,这些‘不行动’并不是任何活动。我不会以某种方式来克制自己不做它们。因而,不像克制,它们根本就不是行动。”[6](P248)
当然,“见死不救”的行为如果是不作为,那肯定是第一种不作为。事实上,按照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的看法,第一种不作为还可以称作为消极的行动(即否定性行动)。在边沁看来,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与目的来划分出人类行动的类型:“首先,它们可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的指动作或发力,消极的指坚持不动,即在这样那样的状况中克制自己,避不动作或发力。”[7](P125)因而,打击是积极行动,而不打击在某一确定的场合是消极行动。换言之,在边沁看来,上述S“见死不救”的行为就是一种否定性行动。
在这里,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对于OIC,传统的阐释是,如果S在t时刻应该做A,那么,S在t时刻能够做A。举例来说,根据规定,小明应该在星期天付账单,可以推知小明能够在星期天付账单。然而,这样的理解会面临问题,很可能小明在星期六把钱花光了,因而他并不能够在星期天付账单。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阐释来避免这种情形。斯奈德(D Howard-Snyder)修正了传统的阐释,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OIC*:“如果S在T’应该做A,那么,有一个时刻T*,S能够在T*做T’时刻的A。”[4](P235)按照OIC*,如果小明应该在星期天付账单,那么,有一个时刻T*,小明能够在T*做出星期天的付账单的行动。显然,T*指的就是星期六。因而,“应该蕴涵能够”仍然是成立的。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将“S见到P死而不救”简单理解为<S知道P有急难>并且<S没有救P>这两个命题的合取是不够的,因为尽管<S没有救P>确实表征了一个发生了的事实,但这个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却存在着两种可能:其一,S能够救P并且最终没有去救P;其二,S不能救P并且最终没有去救P。对于第一种可能,还应满足三个条件:(1)施救者S有条件有能力提供安全救助却不提供;(2)S的施救行为不会给自身的生命带来伤害;(3)因为施救者未救助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对于第二种可能,根据逆否律,前面的OIC原则等价于“不能够蕴涵不应该”。因而理性地看,这种情况下的“见死不救”并没有任何道德责任。
当然,在上面的分析模式中,理想的情况是,S对自己能不能做出施救行为除了做出准确的预判以外,还需要对自己能不能做出施救行为具备一种诚信的态度。然而,在现实的一些情形中,采取施救行为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并没有人站出来,这一方面反映了路人缺乏道德勇气,另一方面还反映了一些人对自己能否采取施救行为持有一种自欺或者不诚信的态度。也就是说,某人即使实际上有能力进行施救,却有可能辩解说自己没有能力施救。
逝者如斯,一晃轮到柳知客家带孙媳妇了。正在大家欢欣鼓舞前往合家欢时,却被柳知客家门前贴的一张启示(“事”被柳知客误写为“示”)拦住了——
此外,S是否身处人群之中,也同样对S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群体中的个人往往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由于互相都不认识对方,不知道对方是谁,自我往往处于隐遁的状态。若在群体中,S作为群体中的一员,个人责任感的约束作用难以发挥。没有了责任感的约束,加之人数上的优势,S很容易做出与他道德水平不一致的事情。换言之,如果S身边的人都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那么,S即使有想施救的想法,也可能会被同化。若S不在群体中,即S是单独一人,那么,S是否对P采取施救行为则直接取决于S的道德水平。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当我们看到有人落水时,不是立刻冲下去救人,而是想想自己能不能救人,如果不能救人,可以推知自己不应该去救人,这在道德上并无问题。如果是自己不能救人,由于感情上的冲动,反而跳下去救人,这往往导致更多的悲剧。但是,如果不秉持诚信的态度,明明有能力救人却不采取施救行为,这在道德上当然是有问题的。以上的讨论表明,第一种可能才是真正的“见死不救”。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去解读第一种可能,去分析S这种特殊的行为(能够救P但却不去救P),并尝试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
三 否定性行动视角下的“见死不救”行为
仍然在上面的情形中继续讨论,S看见P掉入水中(P不会游泳),S能够救P,但是,S什么都没做,因而一个“见死不救”的事实(S没有去救P)发生了。按照某些哲学家比如罗素的观点,带有否定联结词的真陈述或者真命题如果对应着事实,那么,它所对应的事实是否定性事实。若认可这些哲学家的看法,S没有去救P不仅是事实,还是一个否定性事实[5](P55-59)。
预制光缆余长控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室外至室内或预制舱之间的预制光缆长度控制,解决方案如下:首先,确定预制光缆长度计算原则,精准控制预制光缆长度;其次,通过预制光缆余长分散至各自屏柜或设置迂回井放置,实现预制光缆余长收纳。
在赖尔(G.Ryle)看来:“否定性行动并不具有行动的属性,比如熟练的或者笨拙的、可观察的、借助工具的等等,而这些属性肯定性行动都具有,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将否定性行动看作为行动。”[13](P107-109)梅莱(A.Mele)更是直接指出:“所谓的否定性行动要么就是肯定性行动要么就不是行动,只有这两种可能。”[14](P146-154)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赛德决定不去投票来反对候选人,她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吃饭等等,但当她下班离开时,投票站却已经关闭。可以确定的是,赛德并没有去尝试不投票。梅莱反问,在赛德的行动中有“不投票”这个行动么?
在小悦悦事件中,S代指那些知道小悦悦有危难却没有施救的路人,而在河南驻马店事件中,S则代指看到有人被碾压仍然减速绕行的路人或者驾驶车辆的人。那么,问题接着就产生了,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增加规范命题<S应该救P>,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又会增加规范命题<S不应该救P>?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对于“见死不救”行为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把它解决,那么,进一步从道德层面甚至法律层面去讨论绝无可能。
例如:《黄河怨》(光未然词,洗星河曲)这首著名女高音独唱曲,恨与悲痛之情控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这样的一种历史画意,让歌唱者想象她此时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所以由声乐教育家郭淑珍演唱了《黄河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试想出现这样的情形,S看见不会游泳的P掉入水中,最终S没有救P。根据常识,在增加规范命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确认S本人能不能(can or can not)一边游泳一边救P。如果S能够救P,那么,我们此时当然会选择<S应该救P>;如果S不能够救P,那么,我们不会选择<S应该救P>,而会选择<S不应该救P>。其中的缘由并不难理解,我们知道,某个人应该做某事的前提是某个人能够做某事。如果某个人不能够做某事时,那么,他当然也就不应该去做某事。从学理上说,它正是康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所强调的“应该蕴涵能够”(ought implies can,通常缩写为OIC)原则。
然而,边沁对否定性行动的界定仅仅限于“克制做某事”这一种模式。在其之后,哲学家布兰德(M.Brand)将“忽略做某事”扩充为否定性行动的一种。同时,布兰德把“克制做某事”严格界定为:能动者S克制实施行动a,当且仅当:“(1)S没有实施行动a;(2)S实施了一个行动b,且S实施b的目的是为克制实施a。”[8](P45-53)对于“忽略”,布兰德用“克制”和“义务”共同来进行界定,即S忽略实施行动a,当且仅当:“(1)S克制实施a;(2)S有义务实施a”[8](P45-53)。
莫塞尔进一步指出,在t时刻,P克制住不去做Q,当且仅当P没有做出Q,同时满足以下八个条件[10](P309):(1)去做Q是一个行动;(2)曾经或现在,P有能力去做Q;(3)P相信在某个时刻努力做出Q会给他做出Q的预期;(4)P的意向是不去做Q;(5)P不做出Q的意向阻止了他在t时刻去做Q;(6)P意识到他没有在t时刻去做Q;(7)P可以选择在t时刻去做Q;(8)P克制住不做出Q,也就是通过P的不做出Q的意向而引起P没去做Q。
莫塞尔(Benjamin Mossel)对否定性行动概念的界定对理解“见死不救”行为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莫塞尔说:“有意地不去做某个肯定性行动构成了否定性行动;而肯定性行动是包含努力、尝试或者活动的行动,不管它们多小。”[10](P309)有一点值得注意,表达否定性行动不一定使用否定词的。英文的“He starves the dog”(有意地不去喂狗)和中文的“他在戒烟”(有意地不抽烟)都是对否定性行动的表达,但在这两种表达中,我们都找不到否定词。这样的反例意味着,否定性行动的表达在语法上并不是固定的,它既可能包含否定词,也可能不包含否定词。那么,我们该如何用语言去恰当地描述否定性行动呢?莫塞尔给出的建议是使用“克制住不去做”(refrain from doing)这样的短语。因为在使用“克制住不去做”这样的表达后,我们就很难将其理解为和主体意向无关的情形了。这一点,只需对比一下<小明克制住不去参加晚宴>和<小明没有去参加晚宴>这两种表达,便可了解。
1.样本选择。本文选取2014年-2016年沪深股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经过数据处理,本研究最终获得1606份有效的样本数据,3年的观测值共有4818份。有关企业存在财务重述行为的数据来自于迪博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不同于布兰德,沃尔顿(D.N.Walton)进一步强调了“克制”和“忽略”的差异[9](P305-324)。对于“忽略做某事”,沃尔顿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规范性更强的概念,因为“忽略做某事”往往意味着“应该做某事”。举例来说,一个开车的人在倒车之前,疏忽大意没有看后视镜或者没有看倒车影像,在因为这个疏忽出现相关事故的时候,这个开车的人就需要承担责任,因为他本应该看后视镜或者看倒车影像,本应该确保车后没人。
莫塞尔对否定性行动的解读的核心正是行动主体的否定意向(intend not to)。但需要注意的是,莫塞尔强调了一种特殊情况,即在层级生成(level-generate)的情况下,否定性行动可能是非意向性的。否定性行动可以层级生成其它的否定性行动,高层级(high-level)的否定性行动可能和主体的意向无关。既然否定性行动之间会存在层级生成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基本的否定性行动呢?在莫塞尔看来,如果P没有做出R,以致R层级生成了Q,那么,我们便可以认为Q是基本行动。简单地说,一个行动(肯定性的或者是否定性的)是基本的,当且仅当它不是由主体的另一个行动所层次生成的。克制(refrainings)、弃权(abstainings)和有意疏忽(intentional omissions)被认为是基本的否定性行动。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高层级的否定性行动和主体的意向无关。彼得没有关掉煤气,这导致室内的鹦鹉中毒死亡,而彼得并不知道鹦鹉在室内。根据莫塞尔的主张,“彼得没有关掉煤气”这个否定性行动生成了“彼得使得鹦鹉死亡”的高层次的否定性活动。又因为,彼得并不知道在室内有只鹦鹉,所以,彼得使得鹦鹉死亡是和他的意向无关的。
现在,我们来对莫塞尔的观点进行一个总结,否定性行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意地不去做某事;二是由基本的否定性行动所层级生成。第一种形式的否定性行动一定和主体意向相关,第二种形式的否定性行动可能和主体意向无关。实际上,我们在对“见死不救”分析时,往往忽视了意向性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回到S和P的情形中,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其中出现的见死不救。在t时刻,S的见死不救是一种否定性行动。具体地说,该否定性行动是指S克制住而不去救P,并满足:(1)去救P是一个行动;(2)S能够去救P;(3)S相信在某个时刻努力救P会给他救P的预期;(4)S的意向是不去救P;(5)S不救P的意向阻止了S在t时刻救P;(6)S意识到自己没有在t时刻救P;(7)S在t时刻可以选择救P;(8)S克制住不救P就是通过S不救P的意向而引起S没有救P。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个更为极端的情况,那就是S和P是同一人的时候,这也就是说,S见到S(也就是自己)有急难而不救。根据上面的分析,这意味着S克制住而不去救自己,它其实正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杀。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自杀是一种特殊的“见死不救”,因此,自杀同样是一种否定性行动。
本研究还对CEACAM1在食管腺癌不同病理参数中的表达方式进行了检测分析,结果发现CEACAM1在食管腺癌中表达分为三种:细胞膜表达、细胞质表达和混合表达。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食管腺癌组织中尤其是分化程度越低、分期越晚、生存越短的食管腺癌组织中,细胞质表达显著增加,这说明细胞质表达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呈正相关,间接表明CEACAM1的细胞质表达参与了肿瘤的进展与转移。提示细胞质表达不是早期肿瘤发生标志,而是进展期的关键标志物。
四 “见死不救”行为的特征——不救意向与不救行为的一致性
然而,将“见死不救”看作为一种否定性行动很有争议[11](P102-108),那就是“有意地不去做什么”和行动概念本身之间的矛盾。因为不管是物理意义上的行动(比如搬东西)或心智意义上的行动(比如计算),它们都是指“有意地去做什么”,而并非指“有意地不去做什么”。巴赫(K.Bach)就认为:“克制做某事不过是行动失败的某种形式。”[12](P50-57)
不难看出,雷斯彻是想说明,“不作为”的出现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和主体的克制相关,而第二种则并不牵涉到主体的克制。第一种可被认为是行动,而第二种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行动。主体的克制实际上反映了人类心智独特的意向性特征,某个行动主体没有做什么,既可能和主体的意向无关,也可能和主体的意向有关。小明不知道要去参加晚宴,而去听了讲座,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所以,他没有去参加晚宴。在这个情形下,小明没有去参加晚宴是和小明的意向无关的。小明知道要去参加晚宴,同时能够去参加晚宴,但却有意不去,而去听了讲座,在这种情形下,小明没有去参加晚宴是和小明的意向分不开的。行动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主体具有去行动的意向性,尽管蚂蚁在沙滩上可能会偶然地爬出一个美丽的图形,但是,谁都不会认为蚂蚁做出了一个画画的行动。
“身临其境”。这话,是不是依然适用于东蒙草原之行的今日?只不过,比起33年前,我们是不是少了很多的“多年以后”?
此外,船宽还受制于闸宽约束,目前京杭运河全线共有19座主要通航船闸(见表5),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的山东段和苏北段,浙江段仅1座三堡船闸,位于最南端连通钱塘江,不是影响运河全线通航能力的关键要素。同时分析尺度,山东和江苏船闸最大闸宽为23 m,明显大于船宽值,船舶过闸可通过合理的排闸调度方案提高闸室利用率,因此闸宽不作为最大船宽取值的限制条件。
面对否定性行动和传统行动概念之间的矛盾以及赖尔的质疑,莫塞尔的基本策略是拒绝接受用肯定性行动的标准来衡量否定性行动。他认为,只要行动不必然是实质的和具体的,我们就不能够证明否定性行动不是行动。而对于梅莱的反例,莫塞尔认为并非所有的行动中都包含着尝试,赛德有意不去投票,最终她也没有投票,因而赛德不去投票的行为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否定性行动。
尽管莫塞尔给出了回应,但这种回应仍然是不够彻底的。要想真正地让否定性行动成为行动中的一类,有必要去厘清行动概念的本义。在哲学史上,对行动概念的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区分出了两类行动:“有两类行动,一类是某种强制性的东西引起的行动,其特征是不自由的、非随意的,引起和决定它的东西不是行动者自己的意志,而是外在的力量。因此,行动者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二是自由的、有意的行动,它不同于第一类行动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行动者深思熟虑、谨慎选择的结果,其动力是愿望和引起的思想,过程包括思考、形成愿望、做出选择,最后做出身体的动作。”[15](P374)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家们讨论的主要就是第二类行动,因为第一类行动(比如人受重力而下落)和人的主体意向不相关,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它们甚至都不能被看作为行动。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行动概念包括了主体的内部意向性(目的、动机)以及主体的外部行为(身体的动作),这里的外部行为可以认为是做了什么。比如“想房间通风”的意向和“用手推开窗”的行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行动。我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否定性行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行动是否定的(克制住自己而不去开窗),我们观察不到外部的具体行为表现。托马森(J.Thomson)就认为:“克制做某事不能够导致相应的事件,无法体现出行动主体的活动性。”[16](P212-218)
因而,现在的问题便是,主体的外部行为真的是构成一个行动的必要条件么?并不尽然,按照行动的内在论说明:“行动的本质特征是由内在过程决定的。行动与简单的身体动作,从外在的表现上说没有太大的不同,其差别主要取决于内在的因素。”[17](P6)此外,我们不应该忘了冯·赖特对行动一个更为广义的界定:“行动就是有意识地造成世界或者阻止世界中的变化,行动的特征就在于它的意向性。”[18](P13)
为研究PRB利用率等网络性能指标与用户感知指标的相关性,在项目实践过程中,采用三个网络性能指标作为样本属性(即自变量),由于丢包率对于用户感知影响最大,采用丢包率作为样本标签(即因变量),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算法研究相关性。AAC采集数据与训练出算法模型之后,采用模型估算出丢包率,在4G移动互联网的实时应用中,业务丢包率2%是门限值,大于等于2%被视为影响用户感知,将拒绝本次调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模型见公式(1)。
“有意地不去开窗”当然会带来世界中的变化,比如室内变得暖和,它同时也具有主体的意向——希望让室内暖和。在驻马店的交通事故或者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见死不救”行为当然造成了或者阻止了世界中的变化即缩短了受伤者救命的宝贵时间。这个现实的例子表明,尽管“有意不去做某事”这样的行为与“有意去做某事”有很大差别,但是,“有意不去做某事”也是具有因果效应和影响的。这一点正如卡梅伦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部分地创造着一个‘认为人们应该负责的行为’的范畴。因此,人类行动的类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客观存在的范畴,而至少部分地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它反映了我们关于行动的思维方式。”[19](P67)实际上,对比分析否定性行动(意向性地不去做Q,确实不去做Q)和肯定性行动(意向性地去做Q,确实去做Q),我们还将发现这二者所具有的一个重要共同点,那就是主体的内部意向和外部行为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有理由认为“见死不救”不仅仅是一种不作为,它更是一种行动。它之所以被看作为一种否定性行动,正是在于主体具有不去救的意向,同时,主体最终没有做出救援的行为。正如冯·赖特所说:“克制做某事(有能力做但事实上没有做)与做某事都是行动的模式。”[20](P41-43)
五 结语
本文将“见死不救”这一社会现象理解为一个认知命题<S知道P有急难>和一个事实命题<S没有救P>的合取(假定S和P没有利益上的直接冲突,最常见的就是路人与受伤者的关系)。同时,S没有救P的这一事实是由S的不作为导致的,而S的不作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否定性行动,即S克制住自己不去救P。
事实上,“见死不救”一类事件频繁发生的背后隐藏着人们“不作为就不用负责任”和“不作为是明哲保身”的错误信念。但是,如果我们把“见死不救”理解为否定性行动,那么,我们就会更加明确自己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意识,因为否定性行动是会处于因果链条中的,它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从根本上说,只有当人们对“见死不救”拥有足够准确和深刻的认识,才可能真正地成为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
增加与“见死不救”现象的相关法律条款,并非一定是要将“见死不救”入刑或者将“见死不救”的行为定罪。可以换一种角度,尝试去运用法律的鼓励倡导功能,将及时施救这一正面的行为明确化、制度化,如对救助人进行奖励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使及时做出施救行为的人不再限于一小部分道德高尚者,从而使得处于危急状况下的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救助可能性。这样将会使人们更积极地出手相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尽可能减少冷漠的社会画面,使我们的心灵变得温暖。对于“见死不救”这一行为,也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注] 实际上,西方的一些国家已经做到这一点。比如《德国刑法典》第330 条C项规定:“发生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并有可能进行救助且对自己无显著危险,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并处罚金。” 《法国刑法典》第223-6 条第二款规定:“对危险之中的他人,能采取行动,或能唤起救助行为,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无危险,而故意放弃救助者,处五年监禁并处五十万法郎罚金。” ,在法律层面做出更详细更有利于保护生命的规定。只有法律上“问责—激励”两方面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够有效降低“见死不救”这一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乐观地看,在深刻理解“见死不救”行为的基础上,借助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律的硬约束,最终能够使“见死不救”这样的“无义无利”销声匿迹,而使得及时施救这样的“有义有利”大行其道。
参考文献:
[1]周安平.对“见死不救”事件的道德和法律追问[J].江西社会科学,2013(1).
[2]黄岩.“旁观者”的现代生产及其超越[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3]韩建磊,赵庆杰.道德失范与陌生人伦理缺失[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4]Howard-Snyder F.Cannot“IMplies”Not Ought[J].Philosophical Studies,2006,130(2).
[5]胡中俊.如何认识否定性事实?[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6).
[6]Rescher N.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Actions[G]//Brand M,Eds.The Nature of Human Action.Scott,Foresman and Company,1970.
[7]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Brand M.The Language of Not Doing[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71,8(1).
[9]Walton D N.Omissions and Other Negative Actions[J].Metamedicine,1980(1).
[10]Mossel B.Negative Actions[J].Philosophia,2009(37).
[11]王淑庆,程和祥.“否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之争[J].哲学动态,2018(3).
[12]Bach K.Refraining,Omitting,and Negative Acts[G]//Th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Action。O’Connor T,Sandis C[M].Oxford:Wiley-Blackwell,2010.
[13]Ryle G.On Thinking[M].Oxford:Basil Blackwell,1979.
[14]Mele A R.Motivation and Agenc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5]高新民.现代西方心灵哲学[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16]Thomson J.Acts and Other Event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
[17]高新民.行动的本质特征与心理的因果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
[18]冯·赖特.知识之树[M].陈波,胡泽洪,周祯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
[19]卡梅伦.行动的本质[J].张志林,译.哲学译丛,1992(6).
[20]Von Wright.Norm and Action: A Logical Enquiry[M].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3.
Omission as Negative Action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Doing Nothing to Save Somebody ”
HU Zhong-jun1,TIAN Jing2
(1.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94,China ; 2.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S did nothing to save P” is some kind of omission.However,this understanding begs the question since it cannot show the mental status of the subject who is doing nothing to somebody.On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ification of actions proposed by Bentham,“S did nothing to save P” can be recognized as a special kind of action.As the fact that S did nothing to save P ,there are two possible causes:S could save P but did not or S could not save P and did not.The first one is truly “doing nothing to save somebody”.It is a negative action in which the intention of“not to save”and the behavior of subject is consistent.On the one hand,this understanding is more profound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governed by law and morality.On the other hand,this understanding will help to awak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and will make them become participator rather than bystander.
Key words :doing nothing to save somebody;moral indifference;omission;moral construction;negative action
收稿日期: 2018-10-12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莫尔纳问题’研究”(17ZXD004)。
作者简介: 胡中俊(1988-),男,江苏兴化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西方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田静(1988-),女,贵州贵阳人,讲师,哲学博士,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9)02-0083-07
(责任编辑王能昌 )
标签:见死不救论文; 道德冷漠论文; 不作为论文; 道德建设论文; 否定性行动论文;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与政治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