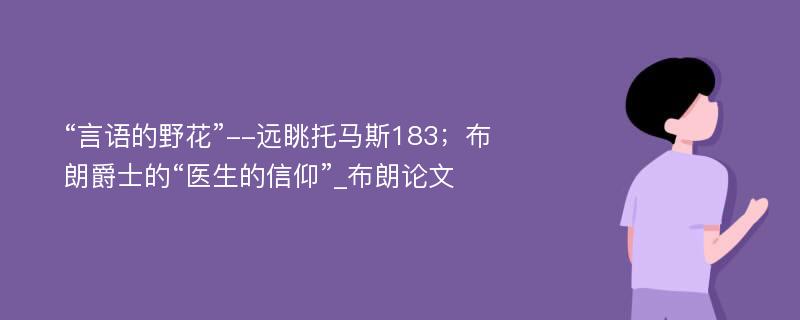
“言语的野花”——远观托马斯#183;布朗爵士的《一位医生的信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布朗论文,野花论文,爵士论文,言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1-0003-12 在其所著《一位医生的信仰》(Religio Medici,1643)一书中,英国17世纪博识家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说道:“至于这个[外部的]世界,我不把它视作客栈,而是当作一处收容站,一个我来此不是为了生存而是要死去的地方”(Browne 89)。 现世生命之旅仅被视作人生旅程的一个时段,而且被限定在“死”的形态中。若隔着遥远的时空对说此话者给予关注,或可先行做此一评:其所言具有在程度上罕见于英国思想史的超然意味。具体被超越的对象,除了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外界或基督教概念中的俗界,更有17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思想纷争。自然科学与神学、天主教与新教、英国国教内部的高教派与低教派或王党与清教徒、上流人士与街头民众等,诸种矛盾冲突一同构成一个现代化发展早期阶段的奇特的社会景观,布朗身在此中,却在他处寻找其作为一位个体的精神立足点。不过,其超然的思路一旦开启,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政治与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大到如此,亦可小到衣食住行等琐事,都可成为被他看得开的对象,也都会失去其原本毋庸置疑的正当性。有鉴于此,我们阅读《一位医生的信仰》这样的书,多半会体验到极端的状况。读者不仅会见识一种迥异于其时流行观点的思想维度,也会面对自己日常价值理念被颠覆掉的危险。当然,这只是阅读经历的一半,另一种需面对的“风险”是,读者在失落中或成为获益者,获赠一种终极而实在的安全感、一个最终让现代个体可以立足的而且并不超然却触手可及的疆域。姑且以布朗本人不喜欢的概括方式定义他,我们所面对的是广义上英国自由保守派思想传统的一个高峰,它至少有两个侧面:一是极度的个人自由观,二是对天理国法和社群精神等价值理念的敬畏,两者均体现出很高的思想烈度,却凭借信念和才智而奇妙地融在一起。 有关布朗生平的文献相对零散,国际学界大致知道其年轻时曾在欧洲大陆多地学医,后长期潜居英格兰乡间一隅,约三十岁时写出《一位医生的信仰》,以“信仰”、“希望”和“仁爱”这三个概念为支撑,与现时纷争对话,表达了介乎天主教信条与极端清教理念之间较和缓的立场。该书最初只以手稿形式在朋友间流传,1642年有盗版出现后布朗才将其整理好正式付梓,后成为其代表作。总的说来,英国内外布朗的读者群规模有限。1923年,有英国出版商认为人们对布朗的兴趣大增,由此引出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那篇著名书评,其中有此两句:“何必罔顾事实?没多少人喜爱托马斯·布朗爵士的作品,但喜欢者都属于世上的盐(the salt of the earth)”(436)。不过,若只考虑重要作家或思想家中的喜爱者,则世盐之多或出人意料。评论家芬奇(Jeremiah S.Finch)曾说:若将历史上传播布朗美名的文人列举出来,“几乎就是一份英语文学史上的优等作家名册”(5)。我们不求尽述这份名册,但英美作家中的约翰逊(Samuel Johnson)、英国浪漫主义主要作家、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主要作家、马尔维尔、狄金森、佩特(Walter Pater)、乔伊斯、伍尔夫以及南美作家博尔赫斯等,都是研究者通常提及的例子。 好作家喜欢他的理由不一而足,伍尔夫在上述书评中认为,最终是一种“想要沉浸在想象之中的渴望”让大家转向布朗的文字。单看此语,伍尔夫似把才思或文笔因素放在了较高位置。但先避开思想,非避重就轻,因为布朗的文风的确奇特,而文风关乎思想。对伍尔夫有重要影响的英国维多利亚后期文人佩特早已说过,尽管人们不可能忽略布朗的内容,但仅赏其文采就足够了(158)。佩特本人讲究文笔,他并非不知布朗的文字“失于松散”,但他也看见了里面的“真诚”;他说布朗不需要时时考虑如何面对今人所说的“公众”,因而其文更易生出鲜见于“更正式的文学”的“言语的野花”(125-28)。 仅以我们一开始引用的有关死亡的一句为例,布朗更说到他不只死一次。在《一位医生的信仰》第一部分第41节中,他说他已经活得够久,“超过了我的寿限”;血气方刚时交朋结友,生活已经享受完了, ……而若继而活入余年,我确能预见到,此后我生命的角色或丑或恶了。说角色,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此人间,不过一场梦,或一出模仿秀,若严肃审视之,则我们不过都是剧中的笑料或小丑。我生命之轨迹或时序,即成为死而复死的历程。我历尽各种饮食、情绪、表情、饥饿、饥渴、寒冷、炎热、贫困、富足、危难、危险。如今再感寒冷,我不再取热而自暖;遇上病痛,也不会取药而求愈。当下知我如何生活者,或可无误地讲,这个人并不看重寿命,也不惧怕死亡。(50) 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说他早早经历过死亡,在出生之前,更在“人间世被创立之前”;因为涉及“救赎”之说,他不奢求日后的救赎,对此不怀疑,更不确定,所能确定的是自己所依赖的救赎方式并非具体的场所或教派,而是上帝一向有之的“仁慈”;于是自己既能出生,那一定是曾经被救赎过,“在我出生之前,我曾死过”:“虽说我的坟墓将在英格兰,但我死去的地方曾经在乐园,夏娃怀上该隐之前已曾流产了我”(69)。 不依赖具体场所或教派,此态度已饶有意味了;此外,赴死云云也映射耶稣的类似姿态,还间接指向柏拉图有关灵魂的“前在”和“后生”不受世间旅程限制的哲思。但我们不深究这些,仅在此展示其能把诸如死亡等主题穷尽到如此程度的笔力。阅读《一位医生的信仰》,即是见证许多不同因素的共存。在思想层面,哲学与神学、辩思与笃信、自然与超自然、智识与迷信、个人理性与宏大真理、肉体存在与精神实在,以及细微洞观与人间揽视等等,共同定义了布朗式的兴趣点和包容能力。而落实到文字表述层面,读者则可领略源源不断培根式常识性格言和诗性奇语之间的有机融合。直陈与宛示、论说与比喻、交谈与自语、散文与诗文等,共同促成了一部篇幅不大但令人观止的文学瑰宝。 至于说意义不止于文笔,我们先可谈及布朗与现今学界的相关性。至少相对于包括浪漫主义诗歌在内的英国19世纪文学研究者而言,他们或可在所研究对象的背后找到一个可能的灵感源泉。英国17世纪文学本身即是英美现代文学的源头之一,而布朗的作用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一位医生的信仰》的许多局部文字都内含日后浪漫文学的基因。这位被佩特称作“如此热爱室外生活的人”(158)说他自己会从宗教圣像转向一种游荡于世间的无形精神。该书第一部分第32节说道,除了各种具体的神灵,“全世界还有一种普在的共同的精神”。尽管他将此直称为“上帝的精神”,但他也延用柏拉图或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些意象或辞语,对此中所可能指向的上帝之具象进行了稀释。他把这种普在的精神比作创世时“盘旋于水域上空的轻柔的热流”,也说道:“它也是那种四射的光耀,能赶走地狱的迷雾,能将惊恐、畏惧、悲伤及绝望的阴云驱散,能让人保持心域的静谧。任何人,即使我能摸到他的脉搏,但只要他感觉不到这种精神的暖风、它的轻柔的流动,我就不敢说他还活着”(38)。“轻柔的流动”、“精神的暖风”、心灵的平静以及辐射的光耀驱散恐惧情绪等说法所代表的思想成分,尤其其表达方式,立即能让人联想到日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雪莱等人的诗性表述。具体到布朗所谓普在的暖风,他还在此节中专门提到它既外在于我们,也“活跃于”我们自身之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的精神因素可以被它唤起,这与浪漫诗人有关“精神的轻风”(intellectual breeze)连结内外世界的说法相似。 以下我们还会呼应这个局部的话题,在此仅指出,此前国外有若干评论家都从各自的角度谈及布朗对神性的虚化。比如但恩(William P.Dunn)就说过,布朗应该被称作“宗教浪漫派”,因为他“主要被宗教中富有想象力的一侧所吸引”,而不是倚赖被某种教条限定住的精神支点。但恩此言出自其有关布朗宗教哲学的专著,其中他多次使用“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者”等概念。他解释道,对于布朗这样的人来说,宗教教义和机构的任务不是去界定信仰的对象,而是“为那些不能界定的信仰对象提供某个象征符号”;他进而认为:“之所以说[布朗]是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是因为对他来说,《圣经》的价值高于其他一切,但《圣经》本身也并不等于那道白光;用托马斯·布朗所喜欢的比喻讲,它也不过是上帝的影子”(54,56-57)。把辉光当作神性的符号,此类做法在柯尔律治、雪莱和丁尼生那里会成为常态,尽管但恩本人并未提及这个脉络。当然,由于担心人们将布朗的上帝完全等同为自然,但恩把布朗的信仰与英国19世纪诗坛见上帝于自然的泛神论区分开,认为他不会与寓于大地或空中的神灵灵交。不过但恩也补充说,“倘若我们不得不给他那个‘自然是上帝之匠艺’的美妙说法加上一个哲学标签,那么最贴切的字眼就是‘上帝之无所不在’(immanence)”(105)。无所不在的确与泛神有微妙差别,大致上后者略靠近无神,而前者不想把神格淡化掉。不过,过分强调不同,反倒难以精确勾勒思想活动的方式和形态。而且,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丁尼生等人本身也经历过这两种认识之间的演化,“泛神”也并不能完全涵盖他们本身的文思。即便说到“无所不在”,后来的哈代和霍普金斯(G.M.Hopkins)等人将上帝内在于万物的理念寓于其作品中,也体现了现代作家对布朗式不同思想侧面的传承。 倘若我们扩展眼界,扩展到与上述学界兴趣点相关联的文化和思想传统领域,尤其从今人角度绎英国人文思想环节,则对于布朗的关注就增加了一分意义。或者说,至少有三个相互叠接或互成侧面的意义。首先,《一位医生的信仰》这样的书在西方现代化早期阶段把个人的内部空间变大了,把跨越横向竖向各种界线的无个性变成了个性。上述有关死亡的文字调整了内外世界的比例,布朗另说道:“至于那个[外部世界],我就像对待我的星仪那样使唤它,偶尔转之一转,聊以自娱。”他说他真正“看重”的是自我内部世界,因为“地球只是一个小点,这不仅因为我们之上有层层天体,也因为我们身内也有圣域或天际”,它大于肉体和地球(89-90)。大于地球,当然也就大于具体的外部自然疆域和文化体,如他在该书第一部分较早的第15节中说道:“我们自身携带着我们在外部世界中所寻找的奇迹:整个非洲以及她的奇观都存在于我们身体中”(18)。 说到疆域或界标,《一位医生的信仰》对人世间过多的思想流派和分支也有抱怨,说基督教本应众脉同宗,却变出许多“不伦的和相悖的形态”(31)。芬奇在老一代学人中较早把布朗放在时代语境中,其《一位医生的科学与信仰的一生》一书说到当时的不列颠正处在变成最强大国家的前夜,一些富含独立思考与睿智的个人声音也会在诸类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应运而生。芬奇认为布朗即是代表。从我们的角度看,所谓睿智,也在于布朗以为不必在行为层面陷入时下的偏见,个人的小世界可兼收并蓄,最终助其抵御任何人以精神救赎或地区利益等为借口,把私己信条强加于人从而使人的精神和能力反被限制住的做法。布朗说他懂多地方言,会讲“不少于六国语言”(84)。虽然他自戒说不必因此而自赏,虽然其游历欧洲诸国的观感也并非都属正面,但若仅挖掘此中态度,则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位允许其自我内部容纳多于单一价值理念或政治信仰的人。“六国”必然要涉及信奉不同教派或秉持不同文化观念的国家,在这些不同区域之间跨界、对它们分表敬意,这都体现了所谓早期世界公民所拥有的轩豁而自由的精神。以下文字值得大段移译过来: 我的机体构造太过一般,能让我与所有事物共处,相投;无论涉及哪种饮食、气质、神情,乃至任何东西,我都不会与之相逆,或更确切地说,哪种都不为我个人所独有。我不会讶异于法国人吃青蛙、蜗牛和蘑菇,也不会因犹太人吃蝗虫和蚱蜢而感到怪异。和他们相处时,这些倒成为我的日常佳肴,而且我发现这些不仅合他们的胃口,也合我的。无论何处采来的生菜沙拉,从花园里也好,从教堂庭院中也罢,我都能消化。我做不到因近旁出现了巨蟒、蝎子、蜥蜴或蝾螈而吓一跳,也感觉不到因看见一只蛤蟆或毒蛇而就想捡起石头灭掉它的冲动。种种厌恶为世间常有,而我只发现于别人身上,我自己身上没有。国家间也多有相互的鄙夷,却都影响不到我,我也不会带着某种偏见去对待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荷兰人。正相反,若见其行为与国人所为相当,我亦会一视同仁地给予他们敬重、爱、拥抱。我生于北半球的第八区①,但我的躯体和命相之如此,似能让我适应所有地带,不会像某种植物,移出了先前的园子就长不活。对我来说,所有的世界、所有的气候最终都成为一个国家的地界与气候;无论何处,无论在哪道子午线,我都如身在英格兰。我曾遇海难,但并不与海洋或海风为敌;即便身处暴风雨中,我也照样能研读、玩耍或睡去。简言之,无物能让我嫌弃它,无论植物、动物还是神灵。(71) 若尚有为布朗所包容不了的事物,人类群氓行为应是主要一项。他认为一些“低下”或“无教养的”人会与他人聚到一起,所结成的并非其眼中体现传承与秩序的良性社群,而是“乌合之众”(the multitude),乌合者不再体现人格,而是共有一个被他称之为“怪兽”的群格(72)。布朗的仁爱和包容都延伸不到这个“理性的敌人”,其态度近似于此前培根和同期霍布斯等人对相同对象的警惕。 再看上面这段引语。到处都是英格兰,竟不限于一地。虽然表此意者反倒比某些爱国人士更不厌乡居,但精神(和胃口)如此普适,不可能不担风险。1972年,美国批评家费什(Stanley Fish)在其有关英国17世纪文学的专著中专辟一章谈论布朗的《一位医生的信仰》,将其与班扬的《天路历程》等“好书”进行对比,称布朗是“坏医生”,缺乏责任心。费什的观点折射史上清教派思想家对布朗式思维的诟病,也解释了为何在英美等地布朗受欢迎的程度较一般,但这正好可帮助我们从相反角度结识布朗。按照费什式的认识,阶进的精神历程应好于散漫的思想环游;个性需维系于信仰之上,因此对某种教义的信守应更利于个人的自我认知,助其发挥内部潜能,而过于活跃的想象力、过于耀眼的文采,都可能瓦解信仰。费什有自己的上下文,所及道理用在对弥尔顿等人的研究上,自是恰切而深刻。但先不管弥尔顿自己是否反倒有宽容的一面,仅就费什对布朗的评价而言,其之所以感到不安,似过多倚赖那种以为需给个人主观世界限定疆域的理念;无方向或路线,无具体认同感,不辨教堂与花园,都会导致迷失。沿此再往前引申一步,其认识中亦具体指向一种以为笃信大于才思或宗教大于文学的价值观。至于此间比例该如何认定,观点应有所异,但至少此观念从相反方面证实了跨域的才思有可能会威胁到信仰;才思真的会变得很活跃,而且确有那种借其而生的精神移游。后来的柯尔律治以及卡莱尔、阿诺德等都就相似的问题做过思考。当然,这种出于不安而对于不同思维方式之间孰轻孰重的排序也并非没有问题。比如,仅就我们所说的才思和信仰而言,它可能会让人过多以宗教尺度评价文学,似乎一本书不管多么可读,只要信仰上不正确,或可被人从多种立场接受,那它就不是好书。如此评价难免导致宗教观念和文学作品之间圆凿方枘的情况。而且,评论家一方若求宗教正确,似乎也得先行遏制自己的思想和情趣,从而忽略包容性想象力中反倒可能含有的虔信成分。 费什并非首位质疑者,学界的不安先前已有。1962年,美国评论家亨特利(Frank Livingstone Huntley)发表《托马斯·布朗爵士:传记与批评性研究》一书、一本博学而清晰的著作,确立了文笔与精神活动的不可分割性。在逐项梳理布朗表意手段的过程中,亨特利提到此前一些学者曾担心生花妙笔会乱人心性,他认为这不得要领。他说,虽然“布朗享有有史以来写出最美英语散文的作家的声誉”,但“美”并非其声誉全部,美文亦可以有思想,思想亦可以含信念:“我们需要让布朗既以一个人也以一位思想家的面目再现于世,因为所谓散文写作,无思想即无散文,无一例外”(104-05)。除非我们的思想有别于他的思想,我们的信念有别于他的信念。当代学者奎伯里(Achsah Guibbory)在其所著《从赫伯特到弥尔顿的礼仪与社群》一书中说,英美世界之所以忽略布朗,主要是今人多以体现改革、进取、积极社会行为和清教教义等理念为道德指南,但她认为这种指南不该是排他的;她不满于费什所言,认为他片面强调个性,反倒把布朗的长处当成缺陷(126,129)。 粗略看,西方的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中自然而然被布朗吸引者较多,而教会人士、政治家和某些理论家等相对多持保留态度。2008年墨菲(Kathryn Murphy)与人合编了一本体现文化唯物主义手法的文集,展示布朗所处历史语境的多个侧面,其中她说道,虽然费什“因[《一位医生的信仰》的]文笔压倒内容而沮丧”,但当时剑桥大学以极高的热度将这本书选作教材,“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它的神学内涵]”(280)。这个历史信息提醒我们,严肃的神学亦可以寄寓于才思。或可说,批评者不必要求布朗少一点思绪或文采,倒不妨让自己多一点意趣。但恩说,布朗的玄学思考力不算很强,“但他的想象力所及实在宽广,需要评论家一方具备最高等级的创造性思维”(90)。文学评论亦需想象力,即可借此更有效地探索作家的精神空间,甚至可让我们意识到,布朗所言对于广义的新教信仰并无实质伤害。 更何况文思即便能维系或建构信念,其功效也不限于此,亦可以反过来制约它,或对极端宗教和政治理念产生解构的效果,此中也会体现责任心。在《一位医生的信仰》第一部分第55节,布朗说他以慈悲胸怀希望所有人都能体验到救赎,但现状却令其悲哀:“桥很窄——那个通向生的甬道;而那些把上帝的教堂局限于某些具体国家、教会或家族之内的人却把它变得更窄了,有违我们救世主之本意”;他更借《马太福音》中穿行针眼的比喻来表达其对于人多路窄的感味(66-67,68)。似乎多一点对个人意识的宽容,即可助世人拓展被救赎的方式。《一位医生的信仰》这本书始于信仰,止于仁爱,即便在表面上似乎都是在说仁爱虽在概念上不等于信仰,但最终无异于信仰的一种形态,而仁爱所及还会漫过信仰的疆域。仁爱部分第11节中,布朗在强调个人内部世界的“圆周”如何“超过了三百六十度”的文脉,谈起人类的睡梦,从又一个侧面对个人心理和思想活动可能达到的丰富程度表达了认知和尊重。肉体休眠时,梦幻活跃起来,理性或理念都松懈了,自我变得大于自我,只可惜我们醒来后都忘记了这个更大的自我,因此布朗认为我们的记忆若能把梦中情节都记录下来,人类其他的钻研都可放弃,只研究梦就够了(90-91)。就像是梦幻对于日常生活内容之边缘的虚化,文学思想有时也会虚化宗教或政治理念的疆界,进而开启空间之外的空间。 关注布朗的第二个意义与上述意义相关联,涉及英国等地人类阅读行为的转化。既然非洲等处的奇观可以存在于自我内部空间,那么自我就成了自然的一部分,亦值得探观。对于这个意思的表述,布朗借用了阅读的意象:“我们是自然万物中鲜明而活分的那一件,善于研读的人面对它,只读其梗概即可比那些埋头于无尽长卷或零散书籍的人了解更多。”自我成了一本书,可作为阅读的对象。除此之外,布朗紧接着又补上了另外两本:“阅读之如此,有两本书供我采集我的神性:除了上帝的那本成文之作,另一本出其仆人——自然——的笔下,即那部铺展于所有人眼前的普在而公开的书稿。未见之于前者的人,曾见之于后者”(18)。接通神格的阅读行为不一而足,即便在基督教之前,如古希腊人之所遇,亦有见神性于自然的例证。《一位医生的信仰》后面第二部分第11节与此处相呼应,再提人类这个小宇宙,尤其说道:“自然告诉我,我就像那部原典,也体现上帝的形象”(90)。这里直接将自我的身体比拟上帝的身形,更微妙的是将自我与原典并提,亦视其为一部典籍,再加上自然的概念,把上帝之下的三个重要成分浓缩在一个短句中,而且更将自我这部书定义为诗书,非史书,自然而又高于自然。 《圣经》、自然、自我,这三本书依次排开,若借此触摸一个很粗的线条,姑且说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张力恰好体现西方文化认知和宗教信仰演化过程的几个重要形态,贯穿于新教兴起后直至现代社会这段历史时期内。再加上此前的天主教教会,四大形态就凑齐了,尽管如此概观会失于简单。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教会却不是阅读的对象,至少有鉴于“阅读”的字面意思是这样。作为文化产业意义上的英国现代印刷业的兴起,大致与亨利八世(1491-1547)和马丁·路德(1483-1546)的生卒时间同步,或者说现代个体读者的出现并行于新教阵营与罗马之间的交恶。此前的信徒行为较多局限于集体的倾听,社群大于个人,教堂大于私室,听讲大于自修,机构大于上天。书多了之后,个人通过读原典而自省,无需中间环节却能与终极因素直接神交的机会就增加了。此所谓新教产生的物质条件一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后班扬写他的《天路历程》这本所谓清教通俗版《圣经》时,一上来就确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焦点画面:一位个体,手捧一本书。这既是精神影像,也是文化符号。弥尔顿在其有关出版自由的国会演说(Areopagitica)中更明确提到,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崛起都有赖于读者人数的增长。在这一点上,布朗与广义的新教阵营无分歧。 不过,如但恩所说,新教改革派以原典为权威,尽管意在颠覆天主教将教会这个天人之间的中介机构视为权威的传统,但其本身也会蜕变为另一种教条,甚至“更危险”,“新教式的经院主义比此前任何一种都更贫乏”;而且改革的阀门一旦开启,其所含个人主义倾向会超越改革者之本意,或向前再行一步,对《圣经》的阐释因派而异,最终亦导致终极权威的解消(46)。布朗不可能完全认同于诸种极端倾向,他像英国17世纪其他一些文人一样,不甘蜗居于局促空间,而是将可读之书变多,放大,自然而然转向其他的权威符号。亨特利提到另一个侧面,说基督教式新柏拉图主义理念也促使布朗连续调整其思想焦点:上帝的“影响”降临,体现于繁复万物,“从宇宙到自然的和人类的历史,再到布朗本人这个地心点上一个更小的点”(109)。的确,布朗本人几乎是徜徉于不同坐标之间,像是兼有新拍拉图主义者的宽豁和真诚,甚至他也把教会当作可读之书,以新教的话语方式表达了对任何文本的宽容。他说:“原典若失声,教会即是我的文本;其声可闻之处,后者即成为可供我阅读的批注;若遇两者同喑,我则既不会向罗马也不会向日内瓦那里来给我自己的宗教信仰借取具体的规章,而是借自我自己理性的指令”(6)。教会和原典、罗马和日内瓦,这些无非都是象征天主教和新教(含卡尔文教派)的常用指代,布朗似将大事化小,转辗其间,虽又补上自我这个第三维,反倒更体现道德完整性。布朗之后,随现代化进程的展开,阅读自然和自我的英国文人渐多,但至少仅就文字表述而言,迄今尚未有人能让布朗显得暗淡。 说到阅读自然这部“公开的手稿”,下面谈及第三个意义时还会再提。此处需指出,布朗是一位耐心的读者,表现出面对自然文本的敬畏,其有关文字很容易将人引向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等人的一些文思。在《一位医生的信仰》的第一部分第13节中,他加入一段致意上帝的诗文,其中说道:“请教会我如何着力阅读你的作品,/让我在读懂它之后进而阅读你自己”(16)。此书该版本编者温尼(James Winny)注释道,通过自然界而认识上帝,这是“老科学之目的所在,而老科学无意为人类提供实用或实际的知识”(Browne 104)。回到我们自己的上下文,所谓新科学,其世代一始,纸版小书多取代宏文大书,耐心的静观也变成埋头的探究。而布朗等人相信,书籍不限于纸版,尚有一些知识为积极的追求所不及,倒可能垂临那些被动领受的观者。“坐下来”一语他在此书中不仅用过一次,表达了老科学时代读者面对自然时的谦恭。在第二部分第8节中,他质疑那些不假思索就把“追求知识”当成绝对信条的人们,质疑此中智识的“自负”。他说,若尚有某种自以为是的毛病他不愿戒除,那是一种与此不同的笃信,它 有时会让我合上书本,因为[另一种自负]告诉我,将生命耗费在对知识的盲目追求中是一种虚荣。只需延长一点耐心的旁侍,我们即可凭借心知和心浸(instinct and infusion)而享有我们此刻试图通过苦读和考据而寻获的东西。最好还是带着一点适度的无知坐下来,安于我们自身理性之天然资质,而不必以汗水和苦楚去购置有关此生的不确的知识,尤其考虑到死神可以给每个人免费提供之,而获此之后它也不过是我们声名的赘物。(85) “合上书本”、“适度的无知”、附属的“赘物”,此类概念将会有人几乎是直接复用于英美文坛。 第三个意义来自于我们从另一个邻近的刻面对布朗整体思维的观察,具体体现在布朗类思想家既属意新兴自然科学又保有宗教情怀这个佯谬状况之上。“情怀”概念佩特曾用在布朗身上,他说,科学怀疑论虽兴起,但“超自然的世界观”并未失效,体现于布朗式的情怀(religious mood)或“虔诚”(159)。布朗的书名指向“信仰”,佩特却不认之,是因为他断言“《一位医生的信仰》所扶植的,并非信仰,而是虔诚”,前者为信徒所持,而后者让俗人“在各种现世投入中同时保持宗教情怀”(138)。他认为布朗与华兹华斯一样,都凭借超越教派信条的方式悟见灵魂的“不朽性”,而维系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契机即在于有此一悟。不过,我们谈论所谓悖谬状况,需首先指出,英国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确让布朗等人感受到了真实的磁力。上面我们提到温尼概念中的老科学,而布朗所示即便真属老科学,其中也掺杂着无以抵御的新科学成分。英国老一辈学者威利(Basil Willey)曾直接把布朗放在新兴自然科学话语体系内,认为他与哥白尼和培根等人的追随者一样,也放弃或否定了中世纪经院哲人有关天与地的正统观念,人间流行的迷信与盲点成为他们都欲捅破的纸靶(372,374)。似乎布朗拥有了启蒙运动先驱的质素。墨菲在她的新式研究中提到布朗稍后的心路走向,说尤其17世纪50年代之后,他不仅潜心研读有关自然的文献,体会培根的哲思,更亲自动手,“用昆虫和动物做实验”,“培育果园和花园”(Murphy and Todd 277)。国外新近发表的一本专著即以好奇心和广泛兴趣等为主要内容,称布朗是整个“17世纪最具探询精神的人”。 当然,我们阅读《一位医生的信仰》的总体印象会有别于威利所言。书中确有对威利观点的支撑,但亦有对立的文字相映成趣。概念上,威利的新兴科学与温尼所指未必一致,或许我们可借今人眼光折衷一下,姑且说布朗是用所谓老科学的态度处理着新科学的内容。因此,即便温尼的解读也未必周至,但其编者导言中所揭示的思想侧面仍值得我们温习。他认为,那时候的科学和神学尚能做到相安无事,只是在本质上,布朗虽涉猎自然科学,但其内在而基本的保守信仰并未动摇,反而更坚定了对培根等人所质疑的终因(final cause)和终极秩序的笃信;布朗反对“进步思想”,并不反对经院思想,倒是给后者原有的一些信条重新注入了活力(Browne xi-xiii)。考虑到布朗的医生身份,温尼所见就更添意味。芬奇在其谈论科学与信仰的专论中告诉我们:“在[布朗]所受过的训练中,他见识了思想重点的转移:从中世纪经院派的‘何以’(why)或终因,到伽里略和哈维(William Harvey)的‘如何’(how)”(19)。或者说,从对绝对因素的思考,到具体的观察。芬奇认为《一位医生的信仰》融合了新与旧两类知识,既向前看,也向后看;既重视理性,又知晓理性的局限:“其医学上的训练让他以怀疑态度看待人们有关物质世界的传统认识,尽管这并未让其发展到宗教上的不信”(10)。日后奎伯里就像是给芬奇的观点作补充说:不管布朗对经验式观察方式如何感兴趣,他“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培根式科学家,这是因为他缺乏培根那种改革派或清教徒式的对于事物间各种差异的确信”(129)。另有布朗最新传记的作者巴布尔(Reid Barbour)在其此前发表的著作中延续了奎伯里对于差异化的审视,尤其着力勾勒培根之后布朗等人所表现出的焦虑,或他们如何面对自然与神性之间“被解除互文性”之后其所必须面对的挑战。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复杂,但面对的方式够简单,就是带着一定的退让与和解姿态,给自然“重建互文性”,以此缓和或修正天地之间、神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以及教会内部等领域的分化、差异化或“碎裂化”(atomization)倾向。他说:“布朗乐于将自然哲学神学化——此乐无人能及。桑蚕、点金石和水银都可成为事证,让他见识那些有如大自然之文字的物形如何经历种种化朽为奇的蜕变,从而丰富并加深其对宗教神秘因素的钟爱和信奉”(190-93)。 桑蚕等当然不是被观察的全部。英国18世纪文人约翰逊早就说过,伟大作家往往“在卑微的事物上施展其学识和才华”,他们有此“抱负”,我们就有了“荷马的青蛙、维吉尔的蚊虫和蜜蜂、斯宾塞的蝴蝶、沃维鲁斯(Wowerus)的影子和布朗的五点阵(quincunx)”(436-37)。五点阵概念主要出现在布朗后来所写的《居鲁士的花园》(Garden of Cyrus,1658)一书中,指遍布于宇宙间由五个点构成的形状,地上者如古波斯人的园艺或花朵等自然小物所呈。对此感兴趣之人所具有的秉性不可能一时偶成,因此此意象或是布朗固有思维习惯的观照。或者说,这些或大或小的阵形在布朗眼中多是意味浓烈的符号,它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但同时又拥有诗性的神圣;它既是外在图案,又展现内在秩序;既属新科学,又是老科学;它或许也连接着日后华兹华斯和丁尼生等人都端详过的那朵小花。我们前面提到作为读者的布朗所具有的耐心,但恩另外引申说,布朗对自然的关注可被追溯到但丁及之前中世纪经院哲人阿奎纳有关“自然体现上帝之匠艺”的理念,因此他面对这个世界时,就不可能只察看次因,必然也会企望初因(the first cause);他是一位“真正的观察者”,也必然会从包括卑微事物在内的各种自然奇迹“转向‘我体内的宇宙图景(cosmography)’”,最终都是要证明终极意义或目的论(89,96)。这样的观察者虽也有科学上的抱负,却有别于其时其他科学家的自傲,当然也不同于同样注目初因的室内型信徒。 英美论家会把布朗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神学家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联系起来,主要为厘清布朗亦表现出来的兼具保守立场和开明气度的自由派宗教哲思。等到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阅读《一位医生的信仰》时,我们又看到布朗与后代思想家的关联,似乎后人的所见略同也强化着类似的思想血脉。柯尔律治在不同著述中数次提到布朗,有关该书的阅读随笔是较明显一例。涉及第一部分第15节布朗有关非洲奇迹内在于自我等说法,柯尔律治叹曰:“这正是天才的特征。”因为这样的人“能洞见所有事物的谜语和奥秘,即使最普通者,因此他无需借任何陌生或稀奇的说道或景物来激发其奇妙感和深入兴趣”(301)。更需我们注意的是,他在布朗身上看到了斯宾诺莎的影子,认为布朗身上“强烈的情感与活跃的思考交合在一起”,正体现斯宾诺莎主义:“托马斯·布朗爵士是个不自觉的斯宾诺莎派。”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比布朗小了一代,柯尔律治的联想中应该是直觉多于分析,似主要指向同样为布朗思想所拥有的泛神论倾向,以及情感与智识、笃信与思辨、上帝与自然等所谓对立因素之间不能被割裂的交融性。在一定程度上,柯氏未必不是在顺势推介其自身内部的那个斯宾诺莎:“在我所读过的书中,从未有哪本更能让我觉得贴近我自己的秉性——积极探询,倾意信仰”(299)。 在所谓第三个意义的脉络内,布朗本人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喜欢听音乐,尤其是教堂音乐,因为灵魂亲近和声,能让他进而转向内含音乐的所有和谐事物,并借此认识背后那位“最初的作曲家”;有了这位作曲家,有了普遍而内在的旋律,人类的终极认知和所谓上天堂都成为可能(86-87)。喜欢教堂音乐,这在当时是对一些新教分子的冒犯,但未及圣餐等倚赖实物的教堂圣礼,又未必会取悦天主教派。两派中敏感者应能意识到,布朗其实是有意择取并综合了天主教仪典中较抽象者和新教理念中的模糊性,既抽身于狭隘,又不失虔敬。此外,首位作曲家和上天堂等概念也表明布朗仍秉持那种尤见于文艺复兴鼎盛期有关灵魂竖向移动的惯常思路,有时他直接将此背后的理论支架摆上前台,如新柏拉图主义或有关生物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的思想成分。他直称人类是个“中间环节”,“一个两栖的东西”或人与兽“复合”的“怪物”,兼有理性和感知(42,66),其追求善即可上移而近天使,而无信仰则会下滑而同畜类。信守这个竖向巨链的人由于保有对上端第一环节的意识而不大可能滑向新科学类的无神论,同时他又抱有对自然之动态、广大或万物之丰富的感认。《一位医生的信仰》第一部分第15节始,布朗谈起自然格局中的所谓无用东西之用,暗示其对自然界和人世间偶发因素的否认,进而强调“预先安排”等概念,甚至还沿用旧时的星象说,以连结天人。无偶发,但很丰富;有终因,但可抽象;因自然而不很唯心,因模糊也不大唯物。这样的思维如今似显得陌生了。 布朗说:“我渴望在最难的难点上行使我的信仰,因为对于平常和可见物体的确信并不属于信仰,而是教规。”“物体”如圣墓、圣物或诸如红海等圣区,难点则包括有关“三位一体的奥秘以及道成肉身和复活”等无以物证的概念。他直言,对实物的触弄或对实证的追求都体现较低级的思维方式或信仰行为,“是一种省事的和不得已的信仰”,而“优秀的人”则能在头脑中积极容纳“神秘领域中那些飘忽的谜团或宗教中那些空灵而微妙的因素”,这后一种能力是“福分”(11)。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第10节,他说:“我以为,信仰之所及,虽可能超出理性,甚至与之相悖,得不到我们诸感官的相应证实,但这样的信仰并不因此而变得庸俗”(12)。此类认识已经超越宗教疆界,也是在与文化环境和哲学思潮对话,而讲话者此刻显然与所谓启蒙先驱的身份有出入,不大像新式思想家。布朗更以有逆俗见的口吻自我“祝福”,说“我庆幸自己未曾生活在神迹(Miracles of Jesus)的时代,庆幸自己既未见过基督,也不识其门徒。我无意加入那群途经红海的以色列人,也不愿成为见证[降生]奇迹的基督的父母”。将常人求之不得的幸事视作不幸,这里面似有对于陷入事实的抵触或对于陷入暗淡的恐惧,是对更大意趣的守护。继续用布朗本人的话讲,不想围观,关乎“主动信仰”和被动信仰之别,后者热衷于俯窥“棺椁”,而前者更愿仰望耶稣复活后于空中的“辉光”(11)。柯尔律治读到这段自我庆幸的话时说道:“我也这样认为”(300)。 的确,布朗的这些表白既折射中世纪后期乔叟等人对某些不怕劳顿的天主教朝圣者的暗讽,又预示后来布莱克和柯尔律治再到丁尼生等人贬对应性喻比(allegory)而扬诗性象征(symbol)的文思。柯尔律治的思想依托之一就是17世纪布朗式文人对于三位一体等神秘因素的热衷,尤其是布朗那种以有机的视角平等看待肉身和圣灵的做法。丁尼生更是在长诗《歌唱国王的田园诗丛》(Idylls of the King)中直接写到一些骑士纷纷出去寻找圣杯等物件的机械行为,诟病那种以为凭实物才能宣示和维系信仰的宗教与文化理念,并具体呼应布朗式的以为横向猎奇不如竖向仰视的信念。《一位医生的信仰》第一部分后面的第28节,布朗更具体地说道,他信不过那些从死人身上推导出的奇迹,“这种做法一向让我对圣物的效用产生怀疑,会让我审视那些骨头,质疑圣徒们的甚至基督本人的服饰和配件。”骨头等物会遮挡那个令他真正“崇敬”的“比古物还古的”对象,即“早于世界的”上帝,大于时期的永恒(34-35)。这样的表述几乎直接连结着伍尔夫等人对于某些历史学者或考古爱好者所表现出的思维程式的怀疑,其背后是英国文坛间断出现的对于想象力和“情怀”的救治,或对更大真相的尊崇。 由于有了更早更大的对象,接近它的方式就不该仅仅是为新派思想家所推崇的“验证”或“刻板的定义”,因为“定义”暴露傲慢。我们提到布朗的耐心,耐心不仅关乎态度,更寓于方法。他说,一旦我们遇到某种“模糊性”,一旦其程度之“深”为理性和言辞所不及,我们就不便再对其施用“刻板的定义”了,而应转向“描述、迂说或约喻”(description,periphrasis,or adumbration;12)。“约喻”也可译为“略示”。姑且用今人的话讲,迂、约等几个词确立了“能指”和“所指”之间孰小孰大、孰弱孰强的关系,划定了语言与学识可为和不可为的领域,体现出启蒙之前的谦卑。当然也不失灵活,以description取代definition,这是又一个将活跃的思维和虔敬的情怀融在一起的例子,也是布朗式“言语的野花”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而若不提“野花”,布朗之前之后还有其他文人也以各自的表意方式与他分享着自由而高贵的心绪,诸如多恩(John Donne)、赫伯特(George Herbert)以及同为医生的沃恩(Henry Vaughan)等诗人都看见和维系着自然与所谓圣界之间的亲缘,都从相近的角度先后展示着介乎培根式科学观出现之后和启蒙式极端唯理性思潮出现之前的一种文化敏感性。启蒙运动开始后,这种敏感性渐冷,取而代之者虽并非不重视个性,却也在放大自我的同时,抑制着其内部的活动空间,或导致不大自由的自由。回到布朗,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或可说他通过“野花”而表达出来的信仰不仅是个人主观世界的告示,也代表了浪漫主义等现代文思出现很早之前西方文人曾对危及精神生态的政治、科学及教派等因素的防御。或也间接缓冲了自然科学对自然生态的侵扰。 ①“第八区”:当时对地球气候带所分区域中的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