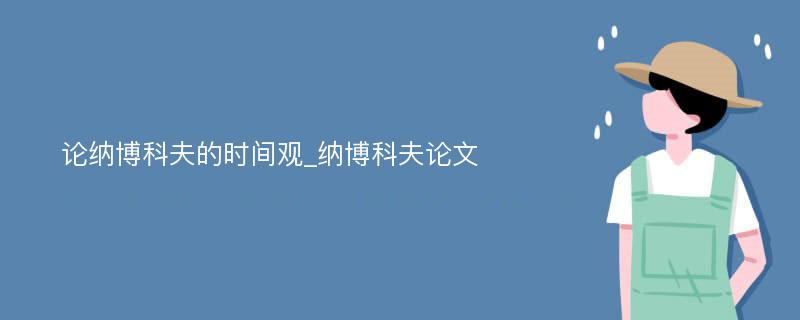
论纳博科夫的时间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博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欧美声名显赫,阿尔弗雷德·卡津称他是“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注: Alfred
Kazin,"Wisdom in Exile",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8(Detroit:G.R.C.Book Tower,1978),p.418.)伊哈布·哈桑认为他是对战后小说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人物。(注:Ihab Hassen,"American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Since 1945,Ivar Ivask and Gero Wilpert eds.(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73),p.3.)1999年纳博科夫诞辰100周年, 美国兰登书屋再版了他的几本重要小说及传记作品。(注:21st Century,9 June 1999.)纳博科夫之所以声名显赫, 与他独特的文体和风格紧密相关,他自己说过,“我既不是说教小说的读者也不是它的作者……对我来说,一部虚构作品的存在仅在于它提供给我一种我坦白地称之为审美狂喜(aesthetic bliss)的东西。 ”(注:Vladimir Nabokov,"On a Book Entitled Lolita",an appendix toLolita(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0),p.313.)然而,纳博科夫并非只关注小说的审美方面,他在展示多姿多彩的文体时,还对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审视,他在作品中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因素之一——时间的探索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观念及缘起
著名的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布莱恩·博伊德认为,时间,而不是空间,是纳博科夫的真正主题。 (注:Brian Boyd.Vladimir
Nabokov:the Russian Years(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248.)约翰·斯达克的认识深了一步:“他(纳博科夫)不接受传统的那种先后顺序的、可用计时仪记录的时间观……他重新定义了时间。”(注:John Stark,"Vladimir Nabokov,"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8,op.cit.,p.409.)纳博科夫到底如何重新定义了时间,他为什么重新定义时间?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认真考察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他受到的影响以及他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
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有过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父亲是法学家,也是政治家,尽管公务繁忙,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孩子的教育,他安排幼年的纳博科夫学习西欧和俄国的语言文化,培养他对大自然的兴趣,引导他健康地成长。纳博科夫的母亲心地善良、受过良好的教育,“用整个灵魂去爱,把其它留给命运”(注:Vladimir Nabokov,Speak,Memory(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51),p.11.)是她的信条。由于纳博科夫幼年多病,他得到了母亲特别的关心和爱。另外,母亲对纳博科夫在艺术方面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鼓励作用。纳博科夫家的一些亲戚朋友对他极其友善,其中卢卡舅舅更是偏爱他,死后将财产和庄园都留给了他。纳博科夫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着,他热爱读书、抓蝴蝶、写诗,还常有机会到西欧各地旅游和度假。但这样的好日子在1919年时到了尽头,十月革命的爆发使纳博科夫这样的贵族家庭不得不举家西迁。刚开始的时候,纳博科夫和他的弟弟靠“一笔与其说是承认智力价值,还不如说是补偿政治灾难而颁发的奖学金”(注:Vladimir Nabokov,Speak,Memory(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51),p.11.)进了剑桥大学。带着羞辱感的纳博科夫遇到了更令人不快的事:人们将他看成“白俄”、不尊重他。大学毕业后,纳博科夫来到德国,“失去”故国的他不得不手持国联颁发给无国籍人士的“南森护照”。为了谋生,纳博科夫教过书和网球,还在电影里跑过龙套。在那里他爱上了维拉并跟她结了婚,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即使这样的日子也没能维持下去。1937年,随着纳粹在德国的兴起,纳博科夫不得不移居巴黎。1940年,在德国人入侵法国之时,纳博科夫又不得不移居美国。此后直到1960年,在纳博科夫享誉美国之后,他才有机会重返欧州,在瑞士的蒙特罗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1970年,在被问及为何选择蒙特罗度过余生时,纳博科夫这样回答:“对一个俄罗斯作家来说,住在这个地区很合适——托尔斯泰年轻时来过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访问过这里,果戈理在这附近开始写作他的《死魂灵》。”(注:Vladimir Nabokov(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1947),p.21.)但出了名的纳博科夫却没有重返俄罗斯,因为他知道,咫尺之遥的俄罗斯不再是他记忆中和幽梦中的俄罗斯,他幸福的早年生活也已消失在时间的巨幕之后。
快乐的早年生活和近60年的流亡生涯所形成的鲜明对照给纳博科夫带来了极深的心灵痛苦。在1919年之后的每一个日子里,纳博科夫都忍受着命运的煎熬: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也不能回归温暖的过去。纳博科夫敏锐地直觉到,在历史事件之后还有某种支配人类生存的根本因素在支配着他。他将这一因素归之于时间:“最初,我没有觉察到,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垠的时间,竟是一个牢狱,”(注:Vladimir Nabokov,Speak,Memory(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51),p.11. )“我曾在思想中返回……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但仅仅发现时间之狱是环形的,而且没有出路。”(注:Vladimir
Nabokov,Speak,Memory(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51),p.11.)在他看来,时间如同牢狱,将他禁锢在每一个特定的“现在”,使他抵达过去、拥抱未来的梦想都变成了幻影。
纳博科夫是极其自信的人,他不仅认为自己是原创性作家,而且认为“艺术的原创性只有它自己可以复制”。(注:Vladimir Nabokov,Strong Opinions(New York:Mc-Graw-Hill,1973),p.95.)然而, 在纳博科夫形成他自己的时间观时,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其间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亨利·柏格森、马赛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
柏格森是作家、哲学家,纳博科夫在20岁左右就开始喜欢读他的作品。柏格森在他的著作中,将时间分成两种,一种是用钟表可以度量的时间,即物理时间,一种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绵延。在柏格森看来,物理时间的概念受到了空间概念的腐蚀,它表现出由年、月、日这些标准单位所构成的、依次延伸的一根同质的长链,它忽视了瞬间与瞬间的区别、忽视了时间的流动性;相反,绵延是不同质的、川流不息的也是不可截然分割的,它的各阶段互相渗透,共同构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柏格森认为只有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柏格森的时间观深刻影响了纳博科夫,使他认识到传统时间观的机械性。同时,纳博科夫发展了柏格森的一些观点,在他看来,既然时间是绵延的,那么过去总在时间的运动变化中消失,人唯一能够把握的、也是人不能超越的,只有“现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意图追回失去的时间,但他最终发现,要想重现往事,就必须有现实的感觉(包括味觉、嗅觉、触觉、听觉)与关于一个过去的感觉的追思和记忆之间的结合。而且他认识到,人们只能在精神上追回失去的时间,艺术作品是人们在精神上重现往事的唯一手段:“通过种种记忆来再造那些业已深埋于它们之中的印象,把它明朗化并转化为相应的精神,这不正是象我所创造的这种艺术作品的精髓吗……?”(注:Quoted by Vladimir Nabokov,Marcel Proust,Lectures on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Inc.,1980),p.249.)纳博科夫接受了普鲁斯特的主要观点,而且从另一个侧面巩固了那些认识。在他看来,人们只能在精神上追回失去的时间意味着他们不能在物质层面上追回失去的时间,一个人如果要从物质层面上追回失去的时间,必然会遇到挫折和失败;艺术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不能帮助一个人从各个层面超越“现在”。乔伊斯是少数几个纳博科夫终生敬重的作家之一,他向20世纪贡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思想,他在《尤利西斯》和其他作品中表达的时间观具有极其独特的一面。马赛尔·布里恩评论说:“《尤利西斯》将《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忒勒马科斯数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个普通人十八小时的生活里——而且是在除了日常烦事别无其它发生的一个普通人生活里,是关于时间相对性的爱因斯坦式奇迹之一。”(注:MarcelBrion,"The Idea of Time in the Work of James Joyce",OurExagminination Round His Factification for Incaminination ofWork in Progress(A New Directions Book,1962),p.30.)在乔伊斯那里,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时间的本质所决定的生命质量。纳博科夫吸收了乔伊斯关于时间相对性的思想,在他看来,人的生命质量受制于一个简单却严酷的事实:没有人能从时间之狱中逃逸,所有人都是时间的囚徒。
如果说柏格森使纳博科夫摆脱了机械时间观的话,普鲁斯特和乔伊斯则启发了纳博科夫深入思考时间的本质并将之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联。接受某种影响对于纳博科夫很多时候并非有意为之,但大师和传统的精神渗透往往无孔不入。
纳博科夫的时间观里还凝聚了他个人独特的理论思考。他首先排除了末来对于人的生存的意义:“未来并不存在, ”(注:
Vladimir Nabokov,Strong Opinions(New York:Mc-Graw-Hill,1973),p.184.)“未来的基本要素……是彻底的虚无,”(注: VladimirNabokov,Bend Sinister(New York:Time,Inc.,1964),p.43.)“未来不具有(如同可勾画的过去和可感知的现在所拥有的)那种现实性;未来只是一种修辞格,一个思想的幽灵。”(注:Vladimir Nabokov,TransparentThings(New.York:Mc-Graw-Hill,1972),p.1.)他认为那些笃信未来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以为过去经验的那种事件延续性可以推广到未来,而事实上未来只是无穷可能性中的一种。为了解释清楚纳博科夫的思想,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1990年一个公司成立了,1995年同一个公司破产了,在一般人看来,1995年这家公司的破产就是1990年这家公司的未来。但纳博科夫不这么看,他认为破产是1990年成立的这家公司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一种,只是因为我们从2000年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所以这种实现了的可能性变成了唯一的可能性,实际上如果我们从1990年的角度来看待这家公司,不难发现这家公司有多种未来,它或许会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公司,或许会保持原有的规模,当然它也有可能会破产。在纳博科夫看来,正因为对于时间中的任何一个点来说,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实际上它并不存在,它只是笃信未来的人心目中的一个“乌托邦”。
纳博科夫通过探讨意识的性质来排除过去。他认为意识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反身性:“(意识)不仅能意识(其它)事物而且能意识自身。”(注:Vladimir Nabokov,Lolita,p.262.)尽管这一特征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时间问题上,意识的另一特征,即意识对现在的依赖性,更为重要。意识对现在的依赖性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意识的客体在变,世界在变,我们意识到的世界只能是眼前的世界、现在的世界,它跟过去的世界不一样,我们的意识会受制于这现在的世界。其次,意识的主体在变,“现在的我”跟“过去的我”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仅表现在外观上,还表现在较深的层面上,而意识只受制于“现在的我”。正因为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主体和客体都受制于现在,意识本身也就不能摆脱现在,过去或许会对意识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相对于现在来说是不重要的、轻微的、可以忽略的。纳博科夫通过他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这种现在性(nowness )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现实;它承继着过去的多彩虚无和引领着未来的绝对虚无。因此,从原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意识的人类生活常常只延续那么一瞬。”(注:Vladimir Nabokov,Ada or Ardor:A Family Chronicle( NewYork:McGraw-Hill,1969),pp.549—550.)
纳博科夫的理论思考进一步证明了他那种时间观的合法性,它起到了一种巩固作用,加强了纳博科夫在生命体验和读书中产生的对时间本质的认识。生命体验、读书和理论思考使纳博科夫坚信,时间如同牢狱,它将人们禁锢在现在,使他们不能回归过去,也不能拥抱未来。
二、作品和实践
纳博科夫将他的时间观融汇在他的小说之中。或许是纳博科夫本人对未来的彻底绝望,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未来的影子。他的小说人物总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挣扎,过去总是很美好,现在总是很糟糕,他们于是想借助某种东西,以使他们超越现在、回归过去。不同小说中的人物寻找到的借助物不一样,《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亨伯特借助于记忆,《普宁》的同名主人公借助于幻觉,《微暗的火》中的查尔斯·金伯特借助于艺术,但这些借助物都没能使他们战胜时间,他们最终都以悲剧告终:亨伯特死了,普宁被迫出走,金伯特发了疯。
因为描写了一个中年男人对一个12岁小姑娘的情与欲,《洛丽塔》是纳博科夫最有名也最富争议的小说,笔者在下文中将从时间和记忆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
亨伯特是美国大学里的一个中年学者,在出生地法国度过的美好童年和少年时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过去的一切中,最不能让亨伯特忘怀的,是他与小女孩安娜贝尔·蕾的“恋爱事件”。起初他们只是常在一起的玩伴,但后来他们“疯狂地、笨拙地、毫不羞怯地、痛苦难忍地相爱了”。(注:Vladimir Nabokov,Lolita,p.12.)不可忽视的是,在他们的“爱”中还交杂着早熟的性欲。按照常理,在12岁的孩子身上,不可能有强烈的性欲,但纳博科夫从来就认为现实是“很主观的事情”,(注:Vladimir Nabokov,Strong Opinions( New York:Mc-Graw-Hill,1973),p.9.)他按照自己的意图描写了他主观中的“现实”。很多文字被用来叙述少年亨伯特和安娜贝尔的相互性吸引和冲动。然而亨伯特终子没能“占有”他的爱,他与安娜贝尔精心策划的一次海滨行动被两个洗澡人打搅了。数月后,安娜贝尔死于伤寒。
多年后已生活在美国的亨伯特继续保留着那些记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洛丽塔——与安娜贝尔一样,她有着“同样柔嫩的蜂蜜样的肩膀, 同样绸子般温软的脊背, 同样的一头栗色头发”。 (注:Vladimir Nabokov,Lolita,p.39.)亨伯特一下子被打动了。 他产生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意图。一方面,他想让洛丽塔成为安娜贝尔的化身,使少年时代的“恋爱事件”在美国背景下重演。另一方面,他还想实现他少年时代未能成功实现的占有欲,弥补他少年时代的某种“缺陷”。然而,从根本上说,亨伯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记忆或者说通过复制记忆来超越现在、回归业已消浙的过去。他为此不惜代价。为了接近洛丽塔,他与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结了婚。夏洛特死后,亨伯特又冒风险带着洛丽塔周游美国。但是,亨伯特想通过记忆回归过去的愿望注定了不可能实现。
夏洛特是第一个阻止亨伯特实现梦想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可以看作是现在的一个象征。夏洛特三十几岁,丈夫早死,亨伯特并不喜欢她却跟她结了婚。她在无意中成了亨伯特的“绊脚石”,使亨伯特不能轻易接近洛丽塔,这似乎预示着现在有种极自然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它箍制着人们,使之不能穿越时间之狱。奎尔第是第二个阻止亨伯特实现梦想的人,同样,他也可以看作是现在的一个象征,但是,奎尔第与夏洛特的作用有点不一样,他刻意勾引了洛丽塔,使亨伯特不能一直占有她。亨伯特恨透了勾引走洛丽塔的人,但他起初不清楚是谁勾引了她,后来终于知道是奎尔第,便作了一个精心安排杀死了他。然而杀死奎尔第是容易的,消除他的影响却是艰难的,因为他也代表了现实或现在的某一方面。
在洛丽塔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小说的戏剧性冲突。从表面上看,亨伯特将她看作了安娜贝尔的化身,他承认,“事实上,可能从来也没有什么洛丽塔,要不是我在一个夏天曾爱上了一个女童。”(注:Vladimir Nabokov,Lolita,p.1.)从深层上分析,亨伯特是将洛丽塔看成了一种时间象征,更准确他说,是将洛丽塔看成了他记忆中少年时代最激动人心、最令人难忘的那一刻的象征。这中间有种过度,在亨伯特眼里,洛丽塔是安娜贝尔的化身,而安娜贝尔代表了那难忘一刻。正因为亨伯特如此看待洛丽塔,他内心时时涌出的超越时间、回归过去的冲动化成了占有洛丽塔的力量。但是,亨伯特的所有努力最终只能遭遇失败。洛丽塔就是洛丽塔,她不可能是安娜贝尔的化身,从而也不可能成为过去那难忘一刻的象征。她是现实中的女孩、是粗鄙化的美国女孩,她并不象安娜贝尔那样“爱”亨伯特,她“愿意”被亨伯特所占有,如果说是出于“爱”,不如说是出于好玩的天性和母亲死后的现实考虑。她有自己的想法,在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说迟早要回到奎尔第身边去。亨伯特意图通过复制记忆中激动人心的一幕来超越时间的梦想最后落了空。
《普宁》是纳博科夫继《洛丽塔》之后的第二部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小说起始于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俄国老教授普宁的一次出门旅行,他乘错了车,不得已在中途换车。在颠簸之中,疲劳“像一股浪潮那样突然淹没了他头重脚轻的身体,把他同现实隔离开来”。 (注:Vladimir Nabokov,Pnin,in The Portable Nabokov,Page Stegner ed.(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2),p.372.)这是普宁特有的一种怪异感觉,他曾经感受过多次,而且每当这种感觉来临,普宁的眼前都会栩栩如生地出现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些情形。事实上,不难看出,当这种现象产生时,普宁正处于一种幻觉之中。常人的幻觉应该是这样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心理状态中,不在眼前的事物出现在眼前。普宁的幻觉与常人的幻觉稍有不同,他幻觉中的事物都来自于他过去的生活,或者与他过去的生活紧密相关。
普宁的幻觉中常出现他在圣·彼得堡度过的早年生活。他出身于名医之家,父亲母亲都疼爱他。他有很多好朋友,后来他们有些人在革命中被杀害了。米拉在普宁的早年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她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的女儿,是普宁的初恋对象,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相亲相爱。很多年以后,普宁“在鲜明的幻觉中”,“重新又成了当年那个笨拙、羞怯而又固执的18岁男孩,在黑暗中等待米拉……(他)觉得米拉正偷偷从那里溜到花园向他走来,在高高的烟草丛里,她白色的上衣和烟草暗白的花混杂在一起。”(注:Vladimir Nabokov,Pnin,in ThePortable Nabokov,Page Stegner ed.(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2),p.464.)普宁在幻觉中感受到的不仅有往事的甜蜜, 也有往事的忧伤。米拉后来被德国人杀害于大爱特斯堡,因为她是犹太人。
普宁的幻觉中还有他过去的婚姻生活。那时普宁在巴黎,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他爱上了同是俄国流亡者的丽莎。丽莎自私、浅薄、好卖弄,但普宁偏偏爱上了她,而且非常珍惜自己的感情,后来他们结了婚。他们的婚姻未能维持长久,丽莎很快就移情别恋,喜欢上一个叫埃里克·温德的大夫。普宁很爽快地与丽莎离了婚。然而,在普宁准备移民美国之前,丽莎带着七个月的身孕回到了普宁身边。事实上,丽莎并非真地想回到普宁身边,她不过是想借助普宁前往美国。这一切在驶往美国的轮船上得到了公开,普宁知道了丽莎的“阴谋”。尽管如此,普宁并没有产生对丽莎的恨意,在洞察她的那些行为动因之时,普宁仍对丽莎怀有某种说不清楚的感情。
普宁的幻觉中还有那些他一日活着就一日割舍不开的事物,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俄罗斯语言和文化。对于他来说,“如果说他的俄语是音乐,他的英语就是谋杀。”(注:Vladimir Nabokov,Pnin,in ThePortable Nabokov,Page Stegner ed.(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82),pp.409—410.)普宁在给美国学生讲授俄罗斯文学的时候,往往忘了他授课的对象——那些既不熟悉俄罗斯方言土语,也不具备丰富的文学见识的年轻人,自己陶醉在他曾经体验过的美妙境地里。普宁的一个美国女学生喜欢他,但他对她的感情很特别,他似乎并不喜欢她本人,只是因为她喜欢俄罗斯语言文学,普宁才有点喜欢她。普宁对俄罗斯语言文化的深入了解也促成了原先看不起他的克里门茨教授与他的友谊。
普宁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总出现那些幻觉,但读者却并不难发现普宁潜意识里的那些想法。尽管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普宁却未能真正适应美国的生活,他始终留恋着过去的日子。过去并不完全美好,但在那种生活里普宁是“主角”之一,他有自己的痛苦和欢愉。然而,在美国背景下,普宁是一个外来者,只有少数人对他友善,大多数人都看不起他,他的情感是虚茫的,他宁可溜进那保留着过去影踪的幻觉,而不愿意直面现实。他根本的目的还在于通过幻觉来战胜时间,以便超越现在、回归过去的世界。
普宁当然不能成功,因为时间之狱不可突破,美国背景下的现实生活在按照它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米拉不可能重现,现在的丽莎比过去的丽莎更自私,很少有人能体会到他对俄罗斯语言文化的热爱。更重要的是,普宁沉缅于幻想、不去面对现实的做法危及到了他在温代尔的生存,最终他不得不卷铺盖走人。从根本上说,他不可能冲破现在的重围、实现他的梦想,因为他脚下还是现实的土壤,他受到了时间的束缚。
《微暗的火》是纳博科夫又一部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在它1962年出版之初,玛丽·麦卡锡曾称它是“本世纪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
《微暗的火》结构很特别,它由一首999 行的题为“微暗的火”的长诗和编注者的前言、注解以及索引组成,形式上很像是一种学术研究成果,但事实上是很有创新意义的小说。那首长诗的作者约翰·谢德是纽卫镇华兹史密斯学院的教师,著名美国诗人,他在那首长诗里记述了他的生平及其对人生、死亡等的思考,整首诗完整、质朴、诗意贯通。编注者是谢德的同事查尔斯·金伯特,尽管他与谢德交往不长,但他认为自己已经与谢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谢德死后,他接手编辑和出版“微暗的火”。
两个角色,一个诗人,一个编注者,似乎由两个不同的人完好地扮演着,但事实并非如此。编注者金伯特实际上对谢德的诗本身不感兴趣,他在前言里拉扯了许多与诗歌不相关的事,他的注解和索引也与诗歌本身风牛马不相及。金伯特的工作与其说是编注谢德的诗歌,不如说是将一个名叫赞巴拉的国家及其前国王的故事硬塞进谢德的诗歌。小说和谢德诗歌的那个相同题目“微暗的火”暗示了这一点。这个短语出典于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在原文中,莎士比亚用它指称自然界中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利用、相互“借光”。在小说里,它暗指金伯特借助谢德的诗歌艺术来记述赞巴拉故事的意图。金伯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细读小说可以看出,事情本身比较复杂。
先说金伯特的身份。按照小说第一人称的自述,金伯特实际就是赞巴拉的前国王,他在国内革命中被囚禁,后来历经磨难,在拥戴者的帮助下逃到美国,在华兹史密斯学院里掩身埋名,以学者身份讲授赞巴拉语。但小说里的一些细节又显示,金伯特很可能只是华兹史密斯学院里的一个流亡学者,他书呆子气十足,想象自己是一个名叫赞巴拉的国家的国王。金伯特还可能具有另外的身份,此处姑且讨论两种。再说金伯特的意图。他到底为什么要那样注解谢德的诗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两种身份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国王”金伯特一方面怀念他过去在赞巴拉的生活,那些熟悉的场景、鲜活的人物时常在他眼前出现,另一方面带着极大的恐惧在美国生活,尽管美国与赞巴拉相隔万里,他却时时刻刻担心着来自赞巴拉的杀手的出现。作为“国王”的金伯特需要找到一种东西能帮助他逃避现实、躲进过去的温暖巢穴。“学者”金伯特有同性恋嗜好,同事们对他极不友善,他过看孤独的生活。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快乐可言,金伯特虑构了一个国家赞巴拉,并设想那个国家的国王也喜好同性恋。他又将自己等同于该国王,以此使他生活中的同性恋嗜好合法化。书呆子气的“学者”金伯特有时候并不傻,他知道人们的想象只能维持一瞬,他象“国王”金伯特一样,需要借助一种东西来保留住想象中过去的一切、从而走出时间的深渊。身份不明确的金伯特找到的是一个明确的借助物,即谢德的诗歌,他千方百计将自己的过去(对于“国王”金伯特,是事实上的过去;对于“学者”金伯特,是想象中的过去)融进谢德的诗歌,意图借助艺术的力量超越现在、战胜时间。
与亨伯特和普宁一样,金伯特也不可能成功,他被人们视作为疯子,事实上他的行为确有颠狂之处。艺术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超越性,它来自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它吸收了生活的养分却更多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某些普遍经验。谢德的诗歌同样如此。颠狂的金伯特却想方设法要使谢德的诗歌变成对赞巴拉及其国王生活的一个简单记录,这本身就违反了艺术的本质和规律。金伯特实际上已经使谢德原来意味深长的诗歌变成了不堪细读的次品、已经破坏了谢德原诗宏大的气象和完好的整体性。因而,金伯特想借助艺术的力量回归过去、战胜时间的意图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得到实现的。
纳博科夫的小说实践使他的时间观有了具体的落脚点,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时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