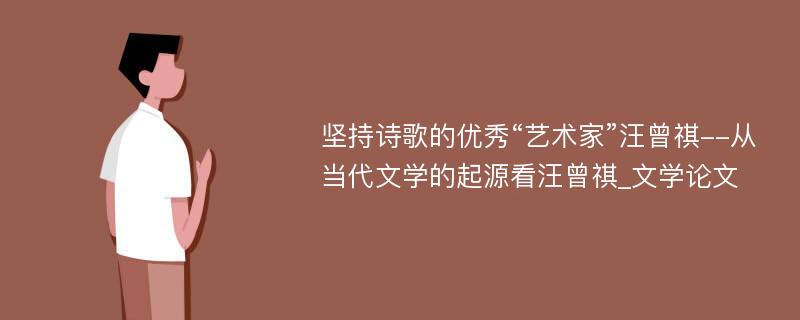
一位信守诗意的卓越“艺人”——当代文学源流中的汪曾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当代文学论文,诗意论文,艺人论文,汪曾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文学的生发源流和话语境遇的纵横比照中,汪曾祺是怎样一种定位、一种形象、角色,这是一个最终依待时间去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结合他的审美意识,把他置于文学史的渊源、背景中进行考察比较依然是有意义的。本文试图将汪曾祺的创作和文论结合起来,在当代文学的整体语境中对汪曾祺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识的话语特征、渊源及其意义做一初步认读和描述。
一、坚守行业立场的卓越“艺人”
汪曾祺的作品和文论在以不同的表意与言说方式,向读者传递着他自己对广大的民间和无边的自然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某些深刻的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认同与阐扬。他在人生和艺术方面所怀抱持守的民间的立场和浓厚的自然色彩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他在写作上所信守的民间艺人式的职业立场以及对于自己行业的技巧的崇拜和精益求精、不断探索的精神。他像一位质朴虔诚的乡下艺人一样,始终自觉清醒地坚守了自己行业的纯洁品性,始终坚守了作家的本分。说到底,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历史、哲学等等,有赖于它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心灵过程,正是这种方式和过程保证了它特殊的品性,汪曾祺出类拔萃地领悟到了,尤其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坚持了自己所体悟的这种人学和艺术的本分与真谛。
在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上,他品尝、领悟、默守,继而清醒、自觉、坚韧地捍卫了文学的审美独立性。他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缄默中以行业独立意识拒斥政治功利的外在影响,维护文学的审美独立,抵抗图解化、概念化。如对一段时间统治文坛的那种政治性极强的说法,即所谓的“两结合”,他说道:“怎么结合?我在当了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期间,忽然悟通了。有一位老作家说了一句话:有没有浪漫主义是立场问题。我琢磨了一下,是这么一个理儿。你不能写你看到的那样的生活,不能照那样写,你得‘浪漫主义’起来,就是写得比实际生活更美一些,更理想一些。”[1]他还说过,“其实我看浪漫主义只有‘为政治的’和‘为人的’两种”[2](P145)。他正是这样以其职业的敏悟,能够识破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套语,而持守职业的真理,并在特殊年代不为所惑,宁愿搁笔也不去写那种虚假的政治宣传品、附庸品。
在文学的品性把握中,汪曾祺领悟了文学的独特性,始终注意到了它独特的心灵特质。他强调思维上的直觉性,即紧紧地把握住了审美感性的本质。他并非拒斥思想、拒斥深刻,恰恰相反,他只是拒绝生硬的概念化和图解化的非文学,拒斥迎合潮流、赶时髦的浅薄做法。作为一个艺人,他懂得自己的本分;作为优秀的艺人,他有自己严格以求的理想、标准。他的理想来自深厚的文学熏陶和修养,表现为与他的民间情怀相一致的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理想的卓越继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于世界文学养分的吸收。
他的理想和标准,他的“民间性”所在,从大的笼统的理论上来说,可以借用他自己的口号来概括:“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2](P213)他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来涵养自己的文学才能,历练自己的文学悟性,丰富自己的艺术技巧,形成自己的美学标准和审美判断力。创作作为一项具体的心灵体验和创造活动,情感的积蓄,文思的涌动,布局谋篇的顿悟运畴,作品孕成以出、诉诸文字的整个过程,每一步的时机火候都必须有一种内在的审美把握,正是于此,汪曾祺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文气论,这就从创作的基本环节、过程上保证了作品可能的审美性。这一点与上文刚刚说及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文学审美品质的纯洁性密切相关,即一切深刻的思想和观点都必须如气在胸般化解在作品字里行间的血肉之躯中,并能如气浩然地感动人、震撼人,而不是成为生硬的说教,或苍白乏力的图解,肤浅的时髦装点。
在作品整体的鉴赏、把握即作品论的价值标准上,他继承发扬传统的境界说,在语言——这一文学产品具体构成、存在的载体——机体上,他赞同韩愈等关于言气的卓越见解,朴素明确地指出,语言的一个标准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2](P30)。作为一个精于行业艺术的“艺人”,他特别重视创作的具体操作的工艺技巧。他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艺术的完成,小说的出品,如同胸中之竹最后成为纸上之竹,在这个具体过程中,小说总是通过语言、出之语言,又成于语言、存于语言。因此,他的“写小说即是写语言”并不是玩弄技巧或形式的空话,而是将一切技巧和讲究都质朴地含蕴于作品之中,含蓄作用于读者的审美感觉,而决不使之在作品中以任何生硬或突出的情况出现,必使它们浑然天成,使作品自然质朴的风貌得以保持。这是因为他就像民间艺人一样把着审美直觉的一关,丝毫不放弃自然一样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审美立场和审美原则。
因此,汪曾祺一方面在创作技巧方面做了极为广泛的尝试,把握了很好的写作技能,发表了很多富有启迪的真知灼见,但他的作品从来都是本色的、朴实无华的,一切精雕细琢的汗水和用心如同养分之于蔬菜,只会促使作品更加自然,更加鲜活、和谐、朴茂;他的作品的自然本色与在技巧上多方面的磨练、探索、迷恋,既相对比又恰恰充分地印证了他作为一个作家如同民间艺人一样对自己行业技艺的崇拜,以及作为一个作家如同民间艺人一样的审美理想的民间色彩、传统色彩。就像他的小说除净一切外在功利、一时的偶然因素,通过风俗抓住了一般普通人的生活本质和常态一样,作为一个作家他透过了激烈多变的政治话语而抓住了实在、本然的文学。他始终是一个纯文学的作家,一个既民间又精英、狷介的作家。
二、汪曾祺的文学际遇
汪曾祺文学的这种民间情怀、自然美学和审美自立的立场态度,可以说,从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具体、真实的成长经历来看,也是渊源有自。在汪曾祺认同并受到其影响的作家中,间接如西班牙现代的阿左林、中国明代的归有光,直接如沈从文、废名,而最有代表性的该属沈从文和阿左林,他们同中有异地佐证、显示了汪曾祺的基本美学构成。
“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2](P184)这是《阿左林是古怪的》一文开篇即抑制不住表明的话。可见汪曾祺对他由衷的认同和心仪神往。“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善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察觉不出来的戏剧性。”[2](P56)这是汪曾祺对阿左林的评价,可这个评价不也正是对他自己的主张——小说即是回忆、审视生活要除净火气,以及他的小说艺术的笔记化、散文化特点的一种注解吗?“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2](P56)的阿左林,其心境、人格、态度深深打动、影响了汪曾祺,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那一半老年性的悲悯情怀。他的作品把一切心思、力量、思想、主题等等都化为了那种心境和人格态度,用这种心境和态度去阅历人生,出之笔下,即含蕴了作者的心境和态度的风俗画:西班牙的风景、西班牙的生活常态、西班牙的人生。阿左林的作品介乎散文诗、随笔和小说之间,如同汪曾祺先生说的,他尽量地淡化了故事。因此,单说作品的规模、体式,对待“情节”和故事的态度,无疑,和沈从文相比,汪曾祺与阿左林有更多相近之处。甚至从心境的主要倾向上说,阿左林式悲悯淡凉的情怀在汪曾祺这里更重一些。有一个深刻的靶心被击中了,这个靶心实际上是把他们串在一起的。“……夜来临了,阿左林想起了在黄昏时分,在忧郁的平原间,那位讽刺家对他的爱人所说的话——简单的话,平凡的话,比他书中一切的话更伟大的话。这就是塞万提斯,真正的塞万提斯……阿左林笔下的塞万提斯才是真正的塞万提斯。”[2](P185),——这个靶心击中了塞万提斯、阿左林、汪曾祺,不知道还要击中多少人。在这里我们其实看到了一幅特别的造像:作家在世界和他人中的姿态。
汪曾祺直接的文学渊源来自沈从文的熏陶,他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京派在文学观念上有很深的认同。如果说,阿左林、废名、归有光等和汪曾祺的共同之处多表现在人生的态度方面,表现在世情、人性等人际之侧于“悲情”的方面,而沈从文所给的影响和启示则更多地在“欣悦”的一面,生命的美的一面。沈从文更多地展示给他的是生命如自然的清新、健康的力量和清新自然的人性人情之美。作家唐敏评论沈从文说,“他不是留过洋的博士或书香门第的传人,他对美的情感是他从故乡山水中呼吸到的,是他的直觉的积淀,所以也是大自然通过一个纯朴忠厚的老实人传递的信息。沈从文是人与自然间的一个媒介体,通过他,我们感觉到什么是‘美’”[3]。这句话是论到了沈从文美学的深刻独特之处的, 依此正可进一步理解沈从文给汪曾祺的影响的民间色彩和自然亮美色彩的一面,并可又一次印证汪曾祺在他对文学社会功能的看法和在审美选择上所采取的“宗教式”策略方面与沈从文先生的继承关系。
这里我们还想进一步申说的是沈从文和京派作家们的纯文学的姿态与汪曾祺的渊源。
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参照系中来看,京派有一种共同的艺术独立的纯文学“唯美”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与直接的政治功利保有一定距离,在艺术上持一种成熟的自觉态度。某种意义上作为京派领袖的周作人,主张用“一种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文明”。他采取一种宽容而中庸的态度,在中西方古代朴质明净、高远清雅的文化中发现“自我”,并认识到这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既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又是孔孟“本来的礼与本来的中庸的复兴”,提倡“人的文学”,推崇英国作家清澈博雅的美文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晚明小品。这种“朴质明净、高远清新”的旨趣与沈从文和汪曾祺是很一致的。[4]特别是考虑到激烈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黑暗与希望、灾难与光明相混杂纠葛的历史时期,京派在艺术上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信守一种内在的自持和自律,既不如郭沫若、郁达夫们来得激情宣泄一般,也不同于鲁迅、茅盾们对黑暗现实采取深痛解剖和诅咒批判。他们的自信自为来自哪里?显然,这是一群在文学上、艺术上、学理上有“学究气”的一群,是很执着于行业的一群,是在文学、美学上朴实而又成熟的一群。因此,废名把自己写文章看成是纯艺术的。女作家苏雪林很明确很现代地在观念上确认:“文学最大的作用是表现情感的,它的职能是感(to move)而不在教的。”[5]而沈从文也始终以一个“对政治无信心,对生命极关心”[4]的乡下人自居;同样,作为京派理论家的朱光潜,崇尚的是与直接的政治保持距离的独立的美学态度,主张艺术的独立性,宣传克罗齐的“直觉说”和布洛的“距离说”等美学理论。一言以蔽之,尽管作为社会的一员,这些作家都有自己清醒的或不清醒的、犹豫的或坚定的政治主张、态度、理想,但在文学上,他们共同持有一种独立、超然、唯美的行业意识,有一种自律性的文学主张和态度。这种态度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难免会受到逃避现实的指责,但无疑,这些人又并非逃避者,而且无疑,文学与政治相区别的鲜明理念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成就了中国现代最清醒、最成熟自持的文学流派之一。沈从文的创作曾遭到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文学要求的批评,并被迫放下了笔。汪曾祺说,针对这样的批评,沈从文作了挑战性的答复:“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办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2](P98)作家唐敏也说, “沈从文恰恰是少数的注意到在美学上重建中国文学的作家之一”[3]。他们说的恐怕也都有这个意思。于此,京派和沈从文、 汪曾祺之间潜在的文学史的意义也可见出一斑了。而于此我们也可略知沈从文、汪曾祺们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何以重放光彩、引人瞩目了。如果我们借用美国批评家杰姆逊的文学观的宏观理论来看,[6]处身第三世界的沈从文、汪曾祺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奇迹般地超越了所谓第三世界文学难以挣脱的“民族寓言”的历史性外在硬壳,在艺术魅力和美学品性上突破了它所产生的那个特定历史——政治时空和民族国家限制,而在更深湛更广博的层面上实现了一种完美的中国传统文明和人类共同理想的重造和表达。汪曾祺说:“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2](P100)而这个“太深太远”正是其超越性、穿透性所在吧。
有的评论家说汪曾祺是接受了“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的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7]。还有一些评论家把汪曾祺当作是技巧派的作家,甚至他自己也说自己大概是个文体家。今天看来,这两种说法也是未免要让人遗憾其局限于表面和局部了。因为汪曾祺的意义还远不是某一支派的传统、香火延续的问题,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外在的某种现象描述。而汪曾祺、沈从文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见热,更根本的原因和意义在于其代表和预示了纯文学的真正重新被时代领悟,他们的作品显示了文学的真正的纯洁完美的生命力和魅力的难以磨灭和不可掩藏。尽管他们所代表的具体风格不必占据未来文学的主流或中心,但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态度、文学理想必然要成为纯文学的主流。他们的文学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特殊的历史需要突现了出来。同样在技巧方面之被瞩目并被冠之以“技巧派”作家,恰恰也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方法热、文体热、语言热的历史偏好,显露一段时期人们看待汪曾祺的普遍眼光、取向。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认读取舍吧。
三、“民间性”“自然性”的限度与小说之“能事”
汪曾祺的创作和文论实际上也表现出了“民间性”和“自然性”对他的艺术思维、技巧和作品风格的制约。这特别表现在他的创作和文论取向的“朴素性”、“自然性”方面。汪曾祺在理论上尽管也曾批评过纪昀批评《聊斋》的一些迂腐的话,[1]但在实际的创作上,他并没有超出纪昀的审美看法多远。而正是在虚构性上,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倒与纪昀的理念现出明显的亲和性、一致性。汪曾祺的作品大部分话语构成都极朴素、真实,让人感到它的形态完全是普通的,大众日常生活化的;另一方面,汪曾祺的作品,远距离、远镜头、历史回顾性文字片段在作品的构成中占了较大的比重,而人物的正在进行时的具体性的、栩栩如生、逼真无遗的正面、细致的工笔描写、刻画、分析、叙述,相对大部分小说来说总是少的、简约的。汪曾祺是以最经济的情节性作成了小说。这也是他作品的笔记性、散文化以及取材的高度回忆性、纪实性所在。有人曾举《复仇》一篇以说明汪曾祺拥有高超的虚构才能,而实际上以《复仇》那样构思奇巧的结构却写成那样一篇哲理、寓言交织的散文诗式的作品,恰恰不足以说明汪曾祺的虚构能力,却正显示了他的“民间故事”倾向的短小性、简约化的审美心理定势和创作定势。至少这篇作品没有显露出汪曾祺有足够的与生活同比例的细致、生动、逼真、丰满的细节和情节以及能够持续推动作品伸展的气势、动力。它毕竟只是一篇短小的制作品。
汪曾祺作品在组成成分上,“民间故事”性的质朴、简短、总括性成分较多,而“故事性”、“情节性”、“虚构性”,近在眼前、步步紧挨的“小说性”因素较弱。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显露出了他与阿左林的亲近,而与自己的老师沈从文以及新一代的小说家王安忆们的分歧。汪曾祺对故事、情节、虚构是淡化、简化、抑制的取向,而沈从文总是清醒、在意于那些成分,给叙事性和情节铺排演绎予以突出的关注,并对五四小说传统有所反思地说,“我只写了些故事,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来写故事”[8]。 从这里我们也可进一步回头反思汪曾祺小说在规模体式上与沈从文的区别。如果说,沈从文在小说观念反思上,是一位深有体悟的先驱,[9]但还没有达到较充分、系统的理论表述的地步,那么,新一代的小说家王安忆在此方面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较为深刻、系统的理论地步。当王安忆充分领悟到虚构(fiction)的要义时,她说, “自我倾诉便无法满足创造的需要了”[10]。恰成对比,汪曾祺总是以回忆日常现实的朴素形态还原生活。王安忆确认了“小说要创造一个存在物,自己个人的经验便成了很大的限止。要突破限止,仅仅依靠个人经验的积累和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人的经验与认识都是有限的,还应当依靠一种逻辑的推动力量,这部分力量,我就称之为小说的物质部分”[10]。相应,当王安忆以宏大的气势如同女娲炼石一般以具体可感的情节、结实有力的“物质”来构筑小说的实体性存在的时候,汪曾祺用心于以巧妙的文字如泉涌出一样抒写自己的回忆、情感、情趣,并且,一切坚固、结实的“物质”都被以“气”揉化,并以文本中的空白含蓄地折射、暗示出一片主体的精神境界。王安忆一再强调以坚实可感的物质去正面构筑作品,而汪曾祺却一再强调“含蓄”、“暗示”、“只画一枝风有声”地以少胜多,以形传神,寻求一种以“巧”和“无”取胜的“无为”式策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汪曾祺在几篇文章中一再以同样的事例来津津乐道于“避实就虚”的技巧策略,如《传神》[2](P46)、《美在众人反映中》[2](P69)、《小说技巧常谈》[2](P38)、《使这个世界更加诗化》[11]。一个作家对一个话题的一再重申,是反映了他在运思、创作上的基本定势、倾向的。如同样面对“美貌”这一难题,托尔斯泰盛赞了荷马,他说:“还记得荷马怎样描写海伦的美丽吗?‘海伦走了进来,她的美丽使老人们肃然起敬’。……用不着去描写她的眼睛、嘴巴、头发等。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想像海伦的形象。”[12]荷马是简洁的,但依然直接,单刀直入地写出人物心理,有力,震撼人心。同样,汪曾祺先生盛赞的《陌上桑》对罗敷的美的间接侧写,[2](P69)给人以无比巧妙的智趣和想像空白,但是它们却不具有直接描写的震撼力。对于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13]这组小说的评论,充分地展示了汪曾祺、王安忆小说观念上的分歧。这组小说以简洁、精致、含蓄巧妙取胜,汪曾祺先生盛称其:“好!”[13]而王安忆却认为这组含蓄精简到极处的小说也便暴露了其窘况,带给人莫大的遗憾,“因它的暗示,我们知道,在那五篇美文之后,其实都可能有着一个‘呼啸山庄’,而我们却只得到一些风声鹤唳,我们等待了很久,却一直不曾获得一个‘呼啸山庄’……许多创造的机会和可能,则全部略去,尽管略去得极为漂亮,可是一桩存在就此全然改变了命运”[10]。同样对语言,两人都极为重视,但汪曾祺赞赏的是风格化的、表现性的语言,而王安忆则清洗这种个人风格,不要任何独特性,[10]她要把语言变成物质性矿石。因此,我们认为,汪曾祺的创作和主张是传统式的,如同中国建筑,以现实的、天然的自然材料构筑,并与自然环境虚实相衬;而王安忆的主张则类似现代建筑,以人工材料,钢筋、水泥、玻璃构筑,前者小巧、朴素、自然,以虚衬实,以小见大,后者宏伟、现代,震慑人心。因此,汪曾祺和王安忆实际上代表了小说艺术上的两种方向,汪曾祺做成了最经济的情节性、虚构性的小说,它们以作家的广泛深厚的生活经历和艺术修养取胜,而王安忆则代表了小说艺术的“虚构性”方向,代表了中国小说家在小说(特别是指向中、长篇的大制作的小说)艺术观念上的新突破。关于汪曾祺和王安忆、沈从文于小说艺术上的分歧是一个极富挑战性和理论价值的命题,它需要另文展开,在此,我们并非要对作为具体风格的汪曾祺、王安忆的创作和美学风格——它们无疑都是优秀的、成功的——作价值评价,在此,我们只是为了进一步理解汪曾祺作品的艺术特点,进一步确认汪曾祺艺术的民间性、朴素性、自然性所在,于此,并可见出这种特色就作为小说之“能事”的“虚构性、情节性、故事性”来说显示出了它的弱点、局限。
在对外国文学的吸收上,理智、理论的层面上,汪曾祺也是抱有较开放的态度,但实际上依然受到自己风格的内在的隐性的选择、制约,如意识流,他所吸收的依然只是这个流派中与其美学观念相吻合的微妙自然、清澈见底的成分。好在每一种风格都是有选择、有取舍的,完美的风格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汪曾祺的创作形态、艺术风格、理论主张与他整个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些信仰,他选择了这种现实的、朴素的、自然的形态。他创造了席勒所说的朴素的诗和相关的美学理论。席勒用“素朴”这个术语所表达的状态,是日神文化的最高境界,完全沉浸于外观美的素朴境界。[14]而这正是汪曾祺选择的、倾向儒家的、民间自然的审美文化境界。那么,汪曾祺缺乏虚构的庞大气度吗?纵然,他的创作和理论圆融自足于一种自然朴素的形态,而宽宏大度的汪曾祺先生是允许人们做各种设想的,他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思维的方式”[2](P206),“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像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样烟云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2](P198)。 理论和创作总是有差距的,作为风格型的创作总与作家的气质有关,而气质是因人而异的,而理论,从其自身的内在要求来说,是要求克服和超越个人的、气质的、境遇的东西的,因此,对汪曾祺这样风格化的作家来说,其创作理念和经验的某些特点往往即意味着其在理论层面的言说可能会自然带有某些“天然的”局限,正像人们常说的,特点即是局限,长处即是意味了缺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