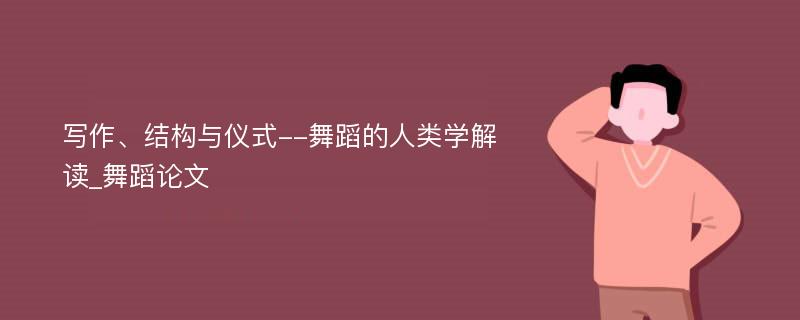
书写、结构与仪式——舞蹈的人类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仪式论文,舞蹈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02(2012)04—0078—06
毋庸置疑,舞蹈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类学家眼里却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人类学家普遍把舞蹈看作一种社会现象①,喜欢把对舞蹈的漠视归结为它的“晦涩难懂”,并发现论证舞蹈比解释舞蹈要简单得多②。他们关注舞蹈一般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然而,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眼中的舞蹈稍有不同。一般来讲,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把舞蹈看作一种文化,而社会人类学中则把舞蹈看作一种社会行为③。总体来看,他们的分析方式一般采取对不同文化中动作模式进行分析并把这些动作模式作为区别文化特征的方式,如此,对舞蹈人类学和舞蹈学研究均带来极大影响,“使他们把焦点集中在舞蹈的社会和公共属性上以及舞蹈制造意义的方式上”④。虽然对舞蹈的人类学分析多种多样,但从进化论学派至今人类学对舞蹈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只是这种关注多了些“功利目的”而少了些“审美特征”。无论如何,舞蹈实体从没有从人类学文化概念中分离出来过。
从整体来看,似乎把舞蹈人类学看做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比看做一门学科更为合理,因为它没有独有的研究范式,现有研究方法也基本由人类学而来。相反,舞蹈民族志却异常的丰富多彩。舞蹈民族志并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或研究模式。舞蹈民族志研究并不仅仅属于舞蹈人类学学科范围,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或民俗学家撰写的关于人体运动的民族志作品,都可以称为舞蹈民族志。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关于舞蹈的人类学研究似乎遭遇着“工具”的命运,成为人类学家眼里有效的分析工具。人类学家关注舞蹈是因为舞蹈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社会,阐明文化价值;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舞蹈人类学研究的起步,为数不多的有舞蹈教育背景的并受过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学者的出现,使得这一学科名称开始跃入人们视野。关于舞蹈的人类学研究开始脱离附属地位,而有了独立意义上的研究。这时研究舞蹈是为了舞蹈,而不再是为了其他目的。此外,舞蹈人类学的兴起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滥觞不无关系。一些哲学家、美学家使用田野调查方法记录和研究人体运动与舞蹈,比如威尔士大学哲学系教授戴维·贝斯特(David Best)等,他们对舞蹈的田野调查的讨论为舞蹈人类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的力量。
我们似乎可以把舞蹈的历史看做“失去舞蹈”的历史,这是因为舞蹈不能像绘画、手稿和乐谱一样,以一种具体客观的形式留下“痕迹”。近年来,由于现代媒体和舞蹈记录法的发展,复排那些“逝去的舞蹈”似乎成为可能。当然这种行为也与近年来旅游产业的繁荣不无关系。从舞蹈创作角度来看,复排舞蹈的目的包括了填补舞蹈历史空白并呈现传统的连续性特征,然而,对这些“可恢复的过去”的探索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对“历史真实性”的探讨。本文关注点之一就是对复排舞蹈中“真实性”和“解释性”问题的讨论。迈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认为:“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去探究历史的精确性得以形成的那些准则,然后运用这些准则来理解一个社会成员通过何种方式将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⑤在人类学家看来,所谓的历史“事实”是永远无法追溯的,这一点从福柯根据权力关系对事实的质疑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从传统人类学的两个转变开始,逐步引起学者对历史表述的瞩目。舞蹈和人体语言成为同样可以表述历史的“无声的言语”,而个体能动性成为这种表述的最大特征。情境使我们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来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使我们的研究更为微观,更为具体,也相对客观。情境也让我们关注到个体之间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在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看来才是文化真正的寓所⑥。
一 “书写”舞蹈
人类学对舞蹈的漠视除了因为舞蹈本体的“晦涩难懂”外,与舞蹈的“转瞬即逝”性特征有很大关系,这无疑给舞蹈的传播和留存带来极大障碍。舞谱使舞蹈的瞬间得以留存,使动态的人体运动得以静态呈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统人类学家对舞蹈的文字描述也可以看做一种舞谱,是人类学家对舞蹈的解读和书写,是对舞蹈的表述。
我们追溯舞蹈的历史时总会陷入“逝去”的舞蹈中,在各种推测中转而借助壁画、雕塑这些静态的艺术形式。舞谱就是用文字、符号或图形等把舞蹈动作、方位和造型变化记录下来的工具。在舞蹈人类学家这里,一般把对舞谱的研究称为“民族舞谱学”(ethnochoreology)。在西方,从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到皮埃尔·博尚(Pierre Beauchamp)的舞谱再到拉乌尔·弗耶(Raoul Feuillet)的曲线舞谱,舞谱的发明从没有间断过,但没有一种舞谱被普遍认可。1928年,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on Laban)创立了“拉班舞谱”(Labanotation),由此被作为记录人体运动的有效工具而普遍使用。拉班是德国现代舞的理论家和教育家,是人体动律学和拉班舞谱的发明者,还是德国表现派舞蹈的创始人之一,他撰写并出版了《编舞》(1926)、《舞谱》(1928)、《现代教育舞蹈》(1948)、《把握舞台动作》(1950)等专著多部以及自传《为舞蹈而生》(德语原版1935/英语译本1975)等。“拉班舞谱以数学、力学、人体解剖学为基础,运用各种形象的符号,精确、灵便地分析并记录舞蹈及各种人体动作的姿态、空间运行路线、动作节奏和所用力量。”⑦在《拉班舞谱》中,拉班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舞蹈理论,并确立了“拉班舞谱”体系,为世界舞蹈艺术向着科学的轨道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拉班所创立的“人体动律学”堪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媲美,被认为是对人体小宇宙的运动规律的发掘。拉班舞谱的出现使舞蹈的科学记录成为可能,也使对舞蹈的书面分析成为可能。Labanotation在美国被认为是“拉班动作分析和记录体系”,而在德国则被称为“拉班动态记录法”(Kinetographie Laban)。在中国,Labanotation被仅仅看做舞谱,从不同的称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Labanotation理解的差异。
舞蹈界之外的部分学者不关心拉班舞谱(拉班动作记录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拉班舞谱专为舞蹈而设计。比如雷勒·伯德惠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在对人体动作学(Kinesics)的研究中提出,拉班舞谱虽然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它专为舞蹈而设计,因此他拒绝使用拉班舞谱来记录人体运动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有些过于绝对化了。拉班创立拉班舞谱源于科学的人体运动这一理念,在拉班看来,拉班舞谱并非仅仅适用于舞蹈,也适用于一切有关人体运动的研究,甚至有关人体行为疾病的治疗也曾尝试用拉班舞谱来分析其日常生活中的肢体运动。由此说,对拉班舞谱的分析使得对人体运动的科学分析成为可能。(以往就有人类学家认为拉班舞谱是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与传统的人类学家对拉班舞谱的认识不同,反思的人类学家认为,拉班舞谱是科学主义的反映,这与人类学结构主义方法一样,需要用反思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舞蹈的直观动态性与舞谱的静态凝固性“二元对立”的困局难以解释,同时也存在着对动作记录的准确性和滞后性的质疑,使得拉班舞谱并未取得同音乐界乐谱等同的普及范围。尽管如此,因为有了拉班舞谱,舞蹈就有了可以阅读的文本,我们对艺术本体的分析就有了依据。对于舞蹈来说,拉班舞谱在细致分析时空中每个人体动作时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从拉班舞谱记录的舞蹈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舞蹈的运动规律,可以洞察记录者或书写者是如何思考舞蹈的,记录者或书写者是如何理解舞谱与舞蹈关系的以及他们为什么如此书写,依据是什么。更进一步则可以思考,依据拉班舞谱来排练的人是如何理解拉班舞谱记录的人体动作的。不同书写者所书写的拉班舞谱是有差异的,同样,不同时期所强调的舞谱也是有差异的,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同时代的情境。书写者所强调的一定是在他看来有意义的内容,由此,对舞谱的解读源于人的当代需求。如果想知道构建舞蹈“真实”的准则是什么,就应该把对舞谱的分析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探讨舞谱形成的历史原因、撰写舞谱的人以及书写的特定舞姿之间的关系,因为“文本与情境相生相成”⑨。在书写的情境中,我们要去了解书写者强调的是什么,什么对他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些也唯有情境才能给我们提供答案。把对舞谱的分析构筑在整体之上才有可能接近了解舞谱形成的准则。舞谱书写的对象是舞蹈作品,但是舞谱和书写这一行为是一种规范化的、整理过的思维逻辑的体现。由此,从一定程度上讲,舞谱是文化的书写,是对社会文化的书写方式之一。
在中国,拉班舞谱于20世纪80年代在戴爱莲先生的推行下逐渐传播开来,但与世界拉班体系发展程度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舞谱,从文字谱到人舞谱,从中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即从敦煌舞谱(残卷)到东巴舞谱,再到定位法舞谱,这些为我们对“逝去的舞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文本。就像乐谱一样,书写者通过书写动作文本看到的是表演的重要成分和因素,而读谱者和书写者看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两者有意无意寻找的,而这取决于他们舞蹈知识的储藏量。由此,对解读舞谱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与解读者的知识资本相关。对于舞谱来说,动作书写者和读动作文本的人对舞蹈的理解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但“被书写的人体运动(舞蹈)”是研究的前提也是最有利的证据。如果我们把舞谱看做文本,也许能打开舞蹈研究的另一条思路。
“写文化”让我们了解到,“人类学写作远非客观性的叙述,而是通过文学性的描述、创造和虚构建立起来的。”⑩舞谱中的文字描述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社会环境,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个体理解,不可避免地在使用修辞的同时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舞谱也是一种创造,是以舞蹈的符号来传达书写者的思想、观念及对舞蹈感觉的综合体,从而形成一套意义以供读谱者解读。由此,舞谱的书写本身就暗含着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知识交织在一起。抽离舞谱,这些符号(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本身并没有意义,是人给了这些符号以意义,而这些意义在书写者和阅读者那里是不能完全重合的。书写也是一条认知途径,而认知是主观的、独有的,它赋予无序的动作符号以意义。由此,舞谱的书写成为“一种用符号反应经验,并赋予其意义的实践”(11)。
那么,如果把舞谱看做文本,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
首先,舞谱的书写并非简单的描述人体运动,并非就是舞蹈动作的客观呈现,而是一种创作,它体现着记录者对舞蹈的认知、经验以及对舞蹈的想象;其次,舞谱是一种认知符号,从对它的解读中我们可以读出它的历史感,它所体现出的社会文化;再次,舞谱是书写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书写者把自己头脑中对舞蹈的想象转化成文字或图像,通过自己的表述把自己对舞蹈的经验理解传达出来。这种表述因为修辞的使用不免充满了记录者的主观想法,叙述(表述)必然会表现出“解释充分”这一特征。因此,它必然具有深度、细节、情感、差异以及连贯性(12)。那么,解读舞谱时所解读的也只是书写者对舞蹈的认知,对“历史真实性”就要存疑,因为“文献记载中哪些是‘事实’或‘非事实’并非是研究要点,更重要的是文献作者在何种情境(社会情境与叙事文化情景)下作如此书写;而诠释,并非只是在既有社会与知识体系中弥补其缺漏,而是反思我们整个社会与知识体系以及两者间的关系。”(13)此外,我们谈论舞谱的时间、空间时,实际上是在谈论人,对舞谱的解读也就成了对人的解读,人即指人体也指舞谱的书写者。舞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历时性“对话”得以形成,后人对舞谱这一文本进行解读,就可以产生新的话语。对舞谱的分析如果只停留在静态的文字和一个个独立动作姿态的分析上,就忽略了舞蹈的动态特征。由此,我们还要继续关注舞蹈从静态的文本到动态的舞台呈现的过渡阶段。
二 结构·多重能动性
人类学对艺术中的能动性的研究似乎尚未引起太过的关注,然而,在艺术创作和表演中,能动性的发挥却无处不在。人作为能动者,是舞谱的书写者和阅读者,是人的创造性行为使得从舞谱到舞蹈的转化成为可能,这种转化过程也是创造性的实践过程。对舞谱的进一步分析就牵涉到对作为能动者的个体的分析。在阿尔弗雷德·吉尔(Alfred Gell)眼里,能动者就是我们每个人,因为“任何人都必须被视为一个社会能动者。”(14)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曾把人的身体看做“艺术品”,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舞蹈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艺术品。舞蹈的艺术成果是写在身体上的,身体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它写在了日常生活或舞台空间中。它书写出来的文本,在格尔茨看来就成为文化,这种呈现方式就成为“表征”。
在舞蹈人类学中,对作为能动者的舞者的分析目前仅仅局限在肢体语言和内心情感的描述上。例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的模式》一书中对夸扣特尔人的舞蹈进行了描述:“在他们舞蹈时,所有男人齐声合唱,当他们移动着在其整个舞蹈那轻柔而沉重的鸟步时,身体向前微倾,肩、头松弛而沉重下垂,脚步有力而柔和,踏着节奏进入场中……他们跳舞,希望玉米破土而出;或用踏脚呼唤狩猎的动物;或集体舞蹈来求雨。”(15)就像本尼迪克特一样,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中对舞蹈的描述较多地集中在肢体的外部呈现上。抛开动作描述的准确性不说,这种描述方式虽然显得平铺直叙,却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舞蹈在人类学家理论思考中的位置。舞蹈语言的难解使得民族志描述充满神秘感,但这样的描述最终只是一种装饰,并未对作为能动者的人的身体和内心做过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囿于舞蹈身体语言之中,并未突破舞蹈外在的身体呈现这一视野。由此,我们应该通过对舞蹈中身体的分析,了解身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了解舞蹈作为一种非语言艺术,是如何通过身体来构建文化、隐喻社会、传承与创造传统的;通过对舞蹈中作为能动者的人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到舞者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创造和想象来认识客观世界的;通过对能动者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实践的桥梁作用。
能动者是行动的主体,这种行动是主体的一种创造性行为,具有理性特征。能动性则是附着在能动者身上的一种实践的能力和权利。“实践即是策略性的个人行动,也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16)在实践行为中,能动性在舞者肢体运动中体现出来,但对于舞蹈来说,这种能动性是附着在舞者和编导双重主体上。演员既是能动者也是编导能动性的实践者。一部舞蹈作品从构思到成型,编导和演员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编导和演员的双重能动性的发挥使得舞蹈作品成型,但是这种双重能动性也使得舞蹈作品的形成中充满了创造性。我们也应该关注到编导的权力,权力是力量,是人与人之间功过控制形成的支配关系(17),正是这种权力使得知识和人的身体产生变化。此外,演员和编导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非一个实施一个执行,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舞蹈作品得以产生,正是在这种互动中舞蹈创作才变得有意义。
吉尔在《艺术与能动性:一种人类学的理论》一书中把作为物的艺术品也视为能动者,认为艺术品是次要的能动者,并不能自给自足。事物也只有在称为艺术品时才能被看做能动者,因为人们已经把自己的情感注入艺术品中。实际上,吉尔是把能动性看做依托于人的能力,因为能动性只能是发自人,而非外部事物所能给的。在舞蹈作品中不存在这种能动者的划分,因为舞蹈的存在依托于人体而非其它。
编导的“创造”在个体能动性发挥中起到重要作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把个体比作“能量源和能动的世界参与者和创造者”,这种个体的创造性行为在编导这里体现的尤为突出;个体的创造中又充满了想象,“正是通过想象,个体生产并再生产他们存在的本质”。(18)而想象与现存惯例之间的张力对创作来说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我们可以把编导的创造看做是个体能动性的最佳体现。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编导和演员毕竟是社会结构下的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他们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的时候会受到约束。但是,也正是这种社会结构与能动性的冲突使得舞蹈作品体现出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相互对立和整合中寻求一种妥协。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和关于艺术研究的民族志研究,似乎在关于结构与能动性的讨论中忽略了作为研究对象一员的人类学者的参与和体验在其中的作用,而这将是笔者在本文中所强调的。此外,在笔者看来,能动者可以从多重意义上加以理解,他不仅是仪式的施行者也可以是作为表演者的能动者。依附于能动者身上的能动性也不仅仅是人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文化展演过程存在。
三 仪式·文化展演·舞蹈
在许多人类学家眼里,仪式有着特殊的魅力,但是仪式中的舞蹈(或人体运动)却并未成为关注焦点。在小规模社会中,舞蹈是仪式的主要构成部分,由此,传统人类学对舞蹈的描述总是和仪式捆绑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仪式中的人体运动和舞蹈的界限并不能明确划分。仪式中的舞蹈动作是从祖先那里学来的,而并非完全的创造。仪式与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不同,前者以“转化”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展现”为主要特征。从仪式到文化展演的演变中我们也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变迁。
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出生到死亡都会经历不同的仪式。仪式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即通过仪式和巩固仪式。通过仪式又称“转换仪式”(19),是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仪式理论上发展而成。通过仪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分离阶段、边缘阶段(阈限阶段)、聚合阶段。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是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是这两个阶段的人的身份不同,已经发生了戏剧性转化。中间阶段是过渡期,这一阶段的人的特征是不清晰的,人的身份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这就是所说的阈限阶段了。特纳的公共域概念成为人们研究宗教仪式甚至社会戏剧的重要理论,从而确立了仪式对社会存在的支持。不管社会地位有何差异,正是公共域使人们连结在一起,在这里,人们都只是普通人(20)。
特纳对非洲恩登布人的研究中也涉及到对舞蹈的描述。特纳曾描述了恩丹布人为有生殖问题的女人举行的四种仪式中的舞蹈(21):恩库拉(NKula)乌布万古(Wubwang'u)、伊索玛(Isoma)、奇哈姆巴(Chihamba)。这些仪式都有三个标示分明的阶段(1)伊雷姆比(Ilembi)或者库雷姆贝卡(Kulembeka),人们通过治疗和跳舞,使治疗对象“变得神圣”;(2)隔离期,这期间她们完全地或部分地与日常生活隔离,并遵守一些饮食禁忌(3)库-图姆布卡(Kutumbuka),人们采取进一步的治疗措施、跳舞庆贺隔离期结束,准备让病人再次进入日常生活。从恩丹布人的仪式性舞蹈中我们可以看到,舞蹈对疾病的治疗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功能。在为双胞胎举行的乌布万古仪式中舞蹈是仪式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仪式性舞蹈象征性的表达了双胞胎给社区所带来的负担。双胞胎现象是恩丹布人心理矛盾的体现——福分和不幸。“在跳这一舞蹈的时候,双胞胎的母亲身上只披一块树皮所制成的布,前面遮上一块皮子或麻布,手拿一个又圆又扁的筛子,在不远的地方环村而行,整个村子都绕遍。她一边跳舞,一边撩起挡在前面的那块布,为众人展示她过度生育的源头。在观看的人面前,她围着筛子转圈,恳求他们提供一些食物、衣服和钱。”(22)在仪式中,“生病”的妇女通常坐在祭坛前,有时也会加入跳舞行列甚至会跳起独舞。此外,在一种为妇女举办的卡雷姆巴仪式中,巫医兼具舞者身份,表演一种挎篮独舞。由此我们看到,舞蹈不仅构成了仪式的主体,更通过舞蹈来庆贺通过仪式中的稳定阶段的到来。但在特纳的手里,人类学对舞蹈研究的惯习并未得到改善。
与特纳的通过仪式不同,巩固仪式(加强仪式)更关注群体之间团结意识的构建。巩固仪式(23)是雪波·艾略特和科·卡里特融合“互动理论”和“过渡理论”,来指称与群体危机相关的仪式活动,并着重指出,加强仪式的意图在于通过团结群体成员,协调群体成员之间、群体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这方面来看,与杜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对祭祀仪式的分析有些相似,两者都指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保持与更新,由此加强群体间的团结。其实,早期宗教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便是指出仪式的角色之一便是确认、维持一个宗教依附所产生的凝聚性(24)。因此,年节期间仪式中的舞蹈为加强仪式的表现提供了媒介,通过舞蹈人们能更好的调节相互间的关系,巩固和维系甚至促进了整体的团结。在保罗·斯潘塞(Paul Spencer)看来,舞蹈并不仅仅是使人们聚在一起,团结一致的高度社会的和等级化的行为,舞蹈自身也常常处于边缘和反常中。它与日常生活形成对比,把舞者带离结构化的常规,并进入一种无休止的吸引力中(25)。
文化展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了仪式,它通过呈现来体现社会秩序,但两者共同处之一就是所体现出的文化和传统都隐含着“社会真实性”。正是展演唤起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观众对展演内容的独特解读使得展演的内容被当作历史事实。也许文化展演与仪式的差异之一就在于前者的呈现过程中充满了想象的创造,而后者多是从祖先那里习得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相对来说,仪式的“宗教性”比文化展演更为浓厚,而文化展演并不以宗教为其展演的主要意图。仪式的不断重复性特征使得信息得以通过文化成员传达出来。文化展演是一种对社会事实的呈现,“它使社会成员得以反思自己,明确自己的本质,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我们的集体神话,为自己展示其他选择,最终在某些方面改变自己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自己的特色。”(26)文化展演关注到展演过程各个因素的作用,把展演看做一个整体。文化展演呈现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能够再现官僚体制的行为,为我们理解展演背后的运行机制提供借鉴。
对于舞蹈来说,观众的作用在文化展演中得到提升。表演者与观众是一个连续体,对文化展演中两者的分析不能截然分开。表演需要观众,但是观众看到什么并知道了什么我们并不能准确表述,因为作为个体的观众解读舞蹈的“能力”是不同的,表演者和观众对动作的理解也并不相同。观众观看舞蹈需要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和语言一样是要习得的。而实际上,表演过程比动作本身可能更重要。因此,“人类学家研究舞蹈就不能仅仅记录和描述舞蹈动作,还要关心舞蹈表演者、观众的经历和感受,了解舞蹈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对舞蹈的影响,研究舞蹈表达的族群认同和政治诉求、舞蹈体现的社会文化及艺术家个人风格、舞蹈创作和表演中的社会文化理念等内容,甚至在舞蹈训练中对身体形态及身体观念的改变等等。”(27)
如果仅仅把对仪式中舞蹈的描述停留在传统人类学的描述方法中,那么对于舞蹈的人类学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应看到舞蹈在仪式中对洞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起到的作用,甚至推进仪式进程的影响。仪式中的诸因素,如器物、音乐、场地安排等与舞蹈的关系是什么,舞蹈与其它因素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也可能是与整体社会的一种互动,互动本身也会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促进社会整合,而这些可能是我们缺乏深入分析的地方。文化展演让我们更加注意到传统的发明与传承的关系问题。文化展演中充满了创造性因素,舞蹈是其中之一。文化展演中的舞蹈说明了与过去的联系,但并不是“过去的舞蹈”,这又引起关于“历史真实性”问题的思考。但是按照福柯的理解方式,历史客观性并不重要,他更关注把历史理解为文化。那么历史真实性在这里也就成了文化真实性的讨论。
上述人类学研究舞蹈的三种视角和方法,似乎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舞蹈的人类学解读可以让我们从一种更为多元的、存异的角度来理解“舞蹈文化”这一概念。它强调舞蹈产生的场景如何,而非舞蹈历史的真实性是什么;它反思舞蹈的多重维度(舞蹈观念、舞蹈作品、舞者、观众……)而非局限于舞蹈本体。它把舞蹈看做是一个时代文化特征的外在表征,它在表征文化意义的同时还储藏着记忆,构建起肢体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桥梁。它可以通过“阅读”来实现由舞蹈语言和舞蹈主体构成的整体的文化表达。
注释:
①Royce,Anya Peterson,The Anthropology of Dance,Alton:Dance Books Ltd.2002.12.
②③(20)(25)Spencer,Paul,Society and the Dance:Social Anthropology of Process and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 Preface; 28; 28.
④Novack,Cynthia Jean,Sharing the Dance:Contact Improvis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13.
⑤(26)[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石毅、李昌银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第288页。
⑥⑩(11)(18)[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第204页,第355页,第3页。
⑦王建民:《舞蹈人类学》,北京:内部资料未出版,第37页。
⑧Thomas,Helen,Body,Dance and Cultural Theo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3.78.
⑨(13)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9页,第37页。
(12)(17)[美]诺曼·K·邓金:《解释性交往行动主义——个人经历的叙事、倾听与理解》,周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第54页。
(14)Gell,Alfred,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16.
(15)[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2-75页。
(16)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9)(22)[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第44页。
(21)[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页。
(23)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4)王嵩山:《仪式、文化展演与社会真确性——阿里山鄒人的例子》,陈中民、王秋桂等主编:《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1年版,第295页。
(27)王建民:《田野工作与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学科建设》,《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