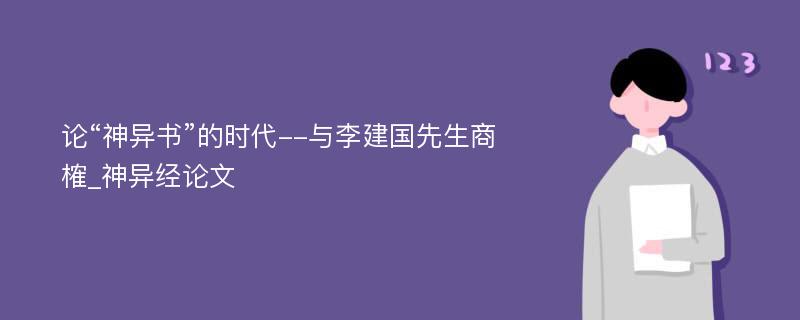
也谈《神异经》之成书年代——兼与李剑国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异论文,成书论文,也谈论文,年代论文,李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9)10-0017-05
有关《神异经》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颇多,诸如版本、撰者、注者、成书年代等等,学界均歧见纷出,现但就其成书年代问题,略作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关于《神异经》成书年代的几种看法
历来对《神异经》成书年代的看法,大抵有三派:其一,以《神异经》乃西汉东方朔所撰,故认为《神异经》当成书于东方朔时;其二,认为《神异经》成书于六朝时期;其三,认为《神异经》乃汉末作品。
认为《神异经》当成书于朔时,这种意见多见于书目类记载:《隋书·经籍志》、《日本国见在书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通志·艺文略》、《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持此论,皆题《神异经》为汉东方朔撰。且《隋书·经籍志》以前,此书已列之东方朔名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齐王纪》引《神异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一《河水注》引《神异经》,皆曰撰者为东方朔,可见最迟在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以前① 已将《神异经》之撰者归之东方曼倩。然此说并不可信,最先对著者产生疑问的当推南宋陈振孙,其《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云:
二书(《神异经》、《十洲记》)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解,末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谈谐,其事浮浅,行于众庶,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1](页315)
据陈氏所言,考《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仅列《东方朔》二十篇,无东方朔著录《神异经》之记载,可见是书不为曼倩所著者明矣。此书既非朔撰,成书朔时自是无稽之谈。
“六朝说”亦非。明人胡应麟首倡此说,其《四部正讹》卷下《神异经》、《十洲记》条下有云:
《神异经》、《十洲记》俱题东方朔撰,悉假托也。其事实诡诞亡论,即西汉人文章,有此类乎?《汉志》有《东方朔》二十篇,列《杂家》,今不传,而二书传,甚矣,世好奇者,众也。[2](页62)
后胡氏之说又为四库馆臣所采。《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四二《神异经》条云:
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则其为依托,更无疑义。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3](页1872-1873)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六《神异经》亦持此说,大抵承袭前论:
《汉志》及本《传》皆不载朔有是书,即《晋书·华传》亦不言其注是书,则其均为后人所依托矣。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故辞采过干缛丽,颇便词章家所取资。[4](页1302)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山海经》稍显于汉而盛行于晋,则此书(《神异经》)当为晋以后人作。[5](页19)
此外,今台湾学者周次吉亦倡六朝说,并指出《神异经》之撰者身份当为方士:
从《山海经》以来,就有许多怪异的传说,而后慢慢酝酿,直至佛教传入,更加上许多想像,到了东晋末年,由某个方术之士写下来的。说本经东晋末年成书是不错的。[6](页81)
显然,从上述所列举的意见来看,主“六朝说”之人,多据志怪小说流行时代及此书的风格特征判定其为六朝作品,见解陈陈相因,缺乏有力证据,多为臆断猜测之论,不足取信。
近世学界多认为此书乃汉末作品,几成定论。段玉裁最先指出此书乃汉末作品,其《古文尚书撰异》卷一《尧典·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条云:
(《神异经》)此等书疑皆是伪作,未必东方朔所为、张华所注也。而服氏注《左氏》“梼杌”、“饕餮”亦引《神异经》,则自汉有之矣。学者阙疑可也。[7](页24-25)
段氏所论乃东汉末年服虔注《左传》卷二○曾引用《神异经》,服虔案:“《神异经》云:梼杌状似虎,毫长三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服虔既为汉末大儒②,此乃其《春秋左氏传解谊》之遗文,服氏注书既引《神异经》为说,则《神异经》成书当在汉末以前。后陶宪曾③、胡玉缙④、余嘉锡⑤ 皆以服虔征引《神异经》考订其为汉末作品。
然“汉末说”遭到周次吉和王国良的反对,其反对的焦点集中在服虔征引《神异经》可靠性问题上。周次吉以《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载服虔曾得到郑玄之《左传注》稿本,服虔引《神异经》注《左传正义》,则郑玄亦应看到过此书,而考之郑玄、许慎以至许冲《进说文解字表》均不见引用此书,同时,杨慎《六书索隐》备举《说文》所引诸家说凡二十八家,也无此“东方朔说”,加上杜宇多引用服虔义,而杜氏之注亦无见此经。故周次吉认为服虔引此经不大可能,故仍主张“六朝说”。周次吉此说实不足信,不能以郑玄、许慎、许冲、杨慎等注书不引用《神异经》,就否定《神异经》之存在。王国良也以许慎未见此书否定“汉末”说,并以“四凶”中独“梼杌”引自《神异经》而怀疑服虔征引的可信度:
所提“四凶”中的浑敦、穷奇、饕餮,也分别见于《神异经》的《西方经》、《西北荒经》、《西南荒经》,服氏却不引,乃转而援用《山海经》。这种作法,颇令人不解。服虔到底有否看过《神异经》,并引用之以解释《左氏传》,单由唐代学者转引的孤证就下论断,似嫌轻率。[8](页7)
考察王国良的说法,存在两个问题:(1)服虔案语很清楚,饕餮亦引自《神异经》,非独“梼杌”一条。(2)“四凶”中浑敦、穷奇均可见于《山海经》,梼杌、饕餮不见于《山海经》而见于《神异经》,故服虔要向《神异经》征引,因《山海经》无有之故,这是客观情况。这样看来,王氏的诘难也显得很苍白。
其实,服虔征引《神异经》不当有疑。服虔所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虽已亡佚,但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转引服虔案语,证据确凿,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二、李剑国“成、哀帝前后”说质疑
对于《神异经》的成书年代,李剑国在“汉末说”基础上又提了出新的看法。李先生说:
我们尚要补充的是汉末许慎《说文》六上木部“枭”字注为“不孝鸟也”,“不孝鸟”的名称出《神异经》,似亦可证书出汉人。而且《神异经》出于西汉末,因为东汉初郭宪《洞冥记》卷二有云:“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此正本于《神异经》;再者《汉书》朔传谓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刘歆《上山海经表》云宣帝后文学大儒皆读学《山海经》,《神异经》刻意模仿《山海经》,又托名东方朔,看来其成书于西汉成、哀帝前后,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9](页147)
显然,李先生在承袭前论的基础上,已基本上将神异经的成书年代上推至西汉成、哀帝前后,我认为李先生此说亦值得商榷:
李先生证据有三:其一,“不孝鸟”本《神异经》;其二,《洞冥记》之“东王公”条必出《神异经》,《洞冥记》必出东汉初郭宪之手;其三,刘氏云宣帝后有学《山海经》之风,而《神异经》体例与之相类。考李先生三条证据,第一条为辅证,亦可据此证明《神异经》成书在汉末以前;第二条至为关键,将成书年代上溯到东汉初以前:第三条为臆测,认为其成书当在成、哀帝时最为可能。下面,我逐一进行分析。
(一)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枭”字条注“枭”为“不孝鸟”,认为“不孝鸟”出自《神异经》,这是很武断的看法。枭鸟食母,其不孝,名出甚早,传说黄帝欲灭此恶鸟,此不必定出《神异经》。《史记·孝武本纪》:“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裴骃集解引孟康曰:“袅,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10](页456-457)《汉书·郊祀志上》亦有类似记载:“后人复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11](页1218)可见,枭鸟食母之事在西汉武帝时已广为流传,不足为奇,后为《神异经》所采,夸诞其物,已属情理之中。是以许慎释枭字以此鸟食母,故释其为不孝鸟,乃自然为之,非必出《神异经》矣。后清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亦指出许慎释枭为不孝鸟之因,段玉裁曰:“《汉义》,夏至,赐百官鸟羹。《汉书音义》:‘孟康曰:枭,鸟名,食母。……黄帝欲灭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12](页271)另,或有可能的情况是,许慎之《说文》注枭鸟为不孝鸟,后《神异经》撰者先见许慎注,然后有不孝鸟条也未为可知,断不可认为不孝鸟必出自《神异经》。
(二)以《洞冥记》“东王公”条必出《神异经》,又以《洞冥记》为东汉初郭宪所作,是以《神异经》成书当在东汉初以前,此说亦属臆断。
首先,《洞冥记》之“东王公”条并非定出《神异经》。《洞冥记》全记东方朔与汉武帝之事,此种特征其序已言明:
汉武帝明俊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今籍旧史之所不载者,聊以闻见,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庶明博君子该而异焉。[13]
是以此书保留了诸多武帝与朔事,很多记录皆他书所不载,更不见之于《神异经》。所记东王公事仅一条,尚且与《神异经》所记之东王公迥然有别,只有其中一句即“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与《神异经·中荒经》所载“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约略相关。《洞冥记》卷二云:
东方朔游吉云之地,得神马一匹,高九尺。帝问朔是何兽也,朔曰:“昔西王母乘灵光辇以适东王公之舍,税此马游于芝田,乃食芝田之草,东王公怒,弃马于清津天岸。”[13]
然则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中荒经》云: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稀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8]
显然,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两则所记并非同一事件,若以《洞冥记》“东王公”条有“朔云”二字,并《神异经》托名东方朔,便断定此条出神异经,也全然不可信,因《汉书》朔本传所言甚明:“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洞冥记》既为志怪之书,大谈怪异并全附之朔与武帝,其言神马事附之朔,亦属常情。
其次,《洞冥记》亦不能确定为郭宪所作。⑥ 考《洞冥记》,前人多有疑《洞冥记》非郭宪作。《洞冥记》是否出自郭宪之手,尚无定论。李剑国认为“郭宪作《洞冥记》不应有疑”[9](页154-155),只是个人之见。诚然,即使《洞冥记》确实为郭宪所作,情况也有以下三种:其一,《洞冥记》之东王公条引自《神异经》;其二,《神异经》之东王公条引自《洞冥记》;其三,两书所记东王公条互不关联,各有出处。这样,李先生据《洞冥记》之有东王公条,便认为其必出《神异经》,是难以成立的。
(三)以《神异经》体例近《山海经》,又以自刘歆《上山海经表》后有仿《山海经》之潮流,说明此时《神异经》确有成书可能,但亦只能算作揣测而已,并不能证明《神异经》成书就在此时。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李先生将《神异经》的成书年代上推到西汉末年的成帝、哀帝之时,存在诸多问题,故其说法也值得怀疑。如韩国学者郑在书即认为此书不会成于西汉时期,郑先生的证据是《南荒经》有“食如何树果实者可以为地仙”条,“而这种以地仙为主的神仙观,直到东汉后期或魏晋时期,才被一般化。因此,推测这本书的成书年代,至少不会是西汉时期”[14](页305)。显然,对于《神异经》的成书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三、从“东王公”条看《神异经》的成书年代
实际上,对于《神异经》成书年代的考察,我们或许还可以从“东王公”条找到另外一个线索。《神异经·东荒经》云: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8]
从上述记载的情况来看,东王公在《神异经》中不但已经出现,而且也拥有了较为具体的形貌体征,这表明东王公的形象早在《神异经》的记载以前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而且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形象特征已经趋于成熟。这样,如果能够考证出东王公何时被创造出来,那么,很明显《神异经》的成书年代至少不会早于此时,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东王公,学术界普遍认为其是作为西王母的配偶神而创设的,他出现的时间要比西王母晚很多,所以考察东王公被创造出来的时间必须与西王母结合起来看。其一,迄今为止,最早的西王母绘画形象发现于洛阳郊区的卜千秋墓中⑦,墓葬年代约当西汉昭帝、宣帝时期(前86—前49),此时东王公并未出现。而汉代极盛的“阴阳理论”则由伏羲、女娲两尊神灵来表示。其二,到了公元1世纪左右,作为阴性化身的女娲逐渐被西王母替代,阳性象征则更换为神人同形的箕星。这种组合的早期典范出现在著名的孝堂山祠⑧:西王母描绘在西山墙上,陪侍她的是人形仆从和一只正在捣制长生不老药的兔子。对面东山墙上相对应的位置上呈现着一幅奇特的景象,描绘的是一个跃入空中的巨人正用一种不知名的器物吹开一幢建筑物的屋顶。这位巨人被认定为箕星,或称之风伯。汉人普遍相信“箕主八风”、“箕为天口,主出气”。就此而言,这颗星是风伯的对应物。东汉蔡邕解释说“风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兴风”⑨,应劭的《风俗通义》和郑玄《周礼》注中都有类似的见解。又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记载,箕星位于天之东宫,是天龙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与东方以及龙的相互关联关系解释了箕星被视为阳性象征并被用于表示东方方位,从而与表示阴性、西方方位的西王母相对,揭示了箕星在东王公尚未创造出来之时与西王母相对的合理性。其三,兴建于公元151年以后⑩ 的山东武梁祠两面山墙刻像则代表了以图画形式显示阴阳对立的又一阶段,其特征为箕星被一位新神——东王公取而代之,东王公于此时已经出现。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难查证。巫鸿认为:“汉宇宙哲学以阴与阳为两股极端对立的力量,它们在无数成双成对的力量平衡中来显示自身,如东与西、男与女、兽与禽、天与地、日与月等等。他们热衷于把‘阴阳理论’应用于一切社会和自然现象。为了便于阐释这种抽象的模式,他们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具体象征物。例如,伏羲和女娲本来是两尊丝毫不相关的神仙,但在汉代神话传说中他们却成了一对夫妻。东王公形象的塑造也同样出自这样的考虑,作为阴阳两方面的象征,雕刻在东汉初期祠堂内的西王母和箕星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并不完美。这两尊神除了与西和东两个方位有关之外,彼此之间既无内在联系也不对应。于是一尊新神——东王公登场亮相。甚至他的称谓都与西王母构成完美的平衡对应,从而揭示他存在的合理性。”[15]
显见,汉代阴阳观念的呈示,由女娲、伏羲到西王母、箕星再到西王母、东王公,展示了东王公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和契机,也大致向我们显示了其被创造出来的时间。于是巫鸿明确指出:“西王母,她在古代中国神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和悠久的历史。而东王公仅仅是西王母的一个镜像,他被创造出来的时间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16]对于这一点,汉画学者信立祥也持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大约东汉章、和帝之间,另一个与西王母相对应的男仙东王公也被创造出来”[17]。
巫鸿和信立祥的看法是令人信服的,从整个汉代出土的实物来看,东王公的出现的确很晚,“目前见于画像砖、画像石、壁画、铜镜中的东王公均出现于东汉中晚期”[18]。东汉中后期有东王公、乐舞庖厨画像石刻|19](页7),有刻有东王公西王母铭文或图文的元兴镜、龙氏神人龙虎画像镜、延熹三年神兽镜、中平镜(11),亦有镂雕有东王公西王母纹的玉座屏(12) 等等。正如夏超雄所说:“有关东王公的情况,两汉以前各书未见,仅从东汉纪年铜镜中见到他的简单图象和铭文。年代早的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环状乳神兽镜上有‘寿如东王公西王母’,其他几面铜镜均是桓、灵之物,镜铭不超出前者。”[20]同时,从祭祀来看,东汉末已开始并祭西王母、东王公二神:“立东郊以祭阳,名曰东皇公;立西郊以祭阴,名曰西王母。”(13) 可见,东王公神话基本都出现在东汉中期以后,而且以东汉末更为普遍,不然不会见之日常器皿与祭祀活动。因此东王公在公元2世纪以后才被创造出来应该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汉末服虔征引《神异经》证据确凿,东王公被创造出来的时间又在公元2世纪以后,所以《神异经》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2世纪到3世纪的这段时间之中,当为可信。而《神异经》成书的确切年代尚需我们进一步考证。
收稿日期:2009-07-10
注释:
① 《三国志》附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言裴注《三国志》当在宋文帝元嘉六年即公元429年完成。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云:“(服虔)中平末(公元182年左右),拜九江太守。”“中平”乃汉末灵帝年号。参见(刘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9月,第2583页。
③ 参见陶宪曾:《神异经辑校》,载《船山学刊》,1933年第1期。
④ 参见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上海:中华书局,1964年1月,第1128页。
⑤ 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122—1128页。
⑥ 宋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云《洞冥记》为梁元帝时期所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则认为此书乃梁元帝作也,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以《洞冥记》当为六朝人依托为之,王国良亦认为《洞冥记》非出郭宪之手(见《汉武洞冥记研究》第3—4页)。
⑦ 参见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7年6期。
⑧ 参见夏超雄:《孝堂山石祠画像、年代及墓主试探》,载《文物》,1984年8期。
⑨ 《独断》卷上。
⑩ 武梁死于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从《武梁碑》可见武梁祠系其子孙所建,石室年代应晚于武梁卒年,故曰武梁祠兴建年代当在151年以后。参见夏超雄:《汉墓壁画、画像石题材内容试探》,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11) 见林素清《汉代镜铭集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帛金石资料库(电子版)。
(12) 定州市博物馆藏,此器由四片镂雕玉片插嵌而成,通高16.5厘米,国家一级文物。
(13)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