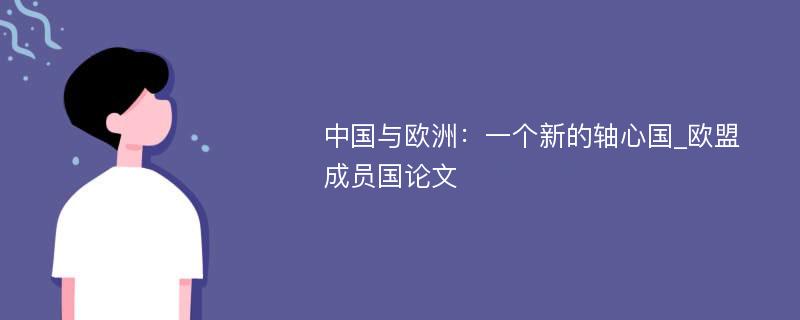
中国与欧洲:新兴的轴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轴心论文,欧洲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来,世界事务中最重要、但最少受到赏识的发展是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的惊人增长。不仅所有欧洲国家各自不断地深化与中国的联系,而且欧盟自身以集体形式与这个人民共和国交往。在构想并实施一种基础广泛的战略以促进范围广泛的领域的联系和合作方面,欧盟已走在前面。欧中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关系的全球重要性使之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新兴的轴心。虽然这个轴心在亚洲和欧洲得到赏识,但美国对欧中关系的变化及其在新兴全球秩序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是迟钝的。
走向战略伙伴关系
欧中关系的急速发展在许多领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最近几年来,这种关系已发展成一种全面的和多维的关系——甚至是战略伙伴关系。
如果目前的贸易增长在今年下半年得以继续,欧盟与中国将在2004年成为彼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04年上半年44%的贸易增长率惊人地超过了2003年实现的给人深刻印象的25%的增长率。2003年,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贸易总额达到1250亿美元,而欧盟的统计数据高于1350亿欧元(或者按年终汇率计算高于1650亿美元)。自经济改革在中国开始的1978年以来,中欧贸易增长了40倍。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欧盟也是中国所获得的技术和设备的最大外国提供者及中国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者之一。欧盟估计,欧洲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迄今累计超过350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也参与大量技术合作计划,包括欧洲伽利略卫星定位计划和世界最大的科技合作研究计划——欧中框架计划。
在政治领域,中国领导人经常与欧洲国家首脑和欧盟官员会面,就在2004年前6个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访问了欧洲(胡和温在2003年秋季也访问过欧洲)。在同一时期,中国作为东道主接待了许多欧洲和欧盟的领导人,包括欧洲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自1997年以来,欧盟与中国的高峰年会在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轮流举行。双方之间的这种高层交往导致大量实质性协定的签订。
在军事和战略领域,每一方都将对方称作“战略伙伴”(许多欧洲国家各自也与中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这种关系)。虽然在欧盟与中国之间迄今没有军事交流,正在制定的计划将开始这种交流,以补充个别欧洲国家正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交流。
法国和英国的海军舰艇今年已经与中国海军进行过联合搜救演习,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一次与中国进行军队对军队的交流。英国为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执行过一个培训计划,中国对国际维和行动的参与正在日益增多。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每年都与中国文职的和军队的安全专家进行“战略对话”,而中国军官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参谋学院接受训练。东欧10个新成员加入欧盟使与这些国家进行更多军事交流有了可能。去年,中国悄悄地发起了与北约的对话
武器禁运的纠葛
中国也显得渴望从欧洲购买武器和防务技术,但自1989年以来,武器和服务技术是被禁止向中国出口的。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向欧盟施加了解除禁运的强大压力,而美国也施加了维持禁运的同等压力。因此,欧洲被夹在日益敏感的外交纠葛中间。
解除禁运将需要欧盟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欧盟官员估计,25个成员国中的16个目前赞同解除禁运(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为首),而丹麦、瑞典、挪威、爱尔兰、葡萄牙以及或许一两个其他新的东欧成员国反对解除禁运。英国和荷兰迄今对这个问题谨慎地持中立态度,但这两国将是使平衡发生倾斜的关键——鉴于英国的威望以及荷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因此能够推动和影响辩论的事实。所有欧洲国家似乎一致认为,鉴于中欧关系总体健康以及有关“战略伙伴”的协议,禁运是过时的,但它们也受到三类担忧的影响。
第一类担忧是人权。欧洲于1989年实行禁运是对中国军队杀害平民以及随后严厉镇压异议者作出反应,目前仍然反对解除禁运的欧盟成员国(主要是爱尔兰和北欧国家)认为,即使形势自1989年以来已得到重大改善,人权仍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担忧。它们希望在禁运被解除之前出现切实改善。欧盟去年也在高层会晤中一再提醒中国人,欧盟寻求“现实的”实质性进步,尤其在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包括西藏的宗教权利)等领域。欧盟列出中国监禁政治和宗教异议人士以及中国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批准联合国《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第二类担忧是中国军队与台湾地区相比日趋增强的能力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力量平衡。欧洲不希望为中国的兵力投送能力以及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恐吓出力。事实上,只有法国似乎对真的向中国出售武器感兴趣。其他欧盟成员国都没有显示出这么做的愿望。它们断然声称,解除武器禁运将是一个政治上的象征性行动,并不表明欧洲国家寻求确实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售武器或者防务技术(禁运也包括防务技术)。欧盟认为,如果这种出售被认为不符合欧洲的总体利益,它需要一种阻止这种出售的机制。为实现这个目的,欧洲官员提到于1998年生效的一个“行为守则”,它为欧盟在世界各地出售武器确立了标准。然而,这个守则是自愿遵守的,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并且容易产生不同的解释。
最后一类担忧是,解除禁运,更不用提确实向中国出售武器和防卫技术,将进一步恶化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已经十分紧张的关系。美国众议院已经讨论过,对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或者技术的欧洲公司实行制裁。
因为这些担忧,欧盟正在制定若干保障措施。一旦禁运被解除(最早或许于12月在海牙举行的下一次欧盟一中国高峰会议上),这些保障措施将生效。它们有可能包括三个同时进行的步骤。首先,发表一个“政治声明”,说明解除禁运是与欧中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总的健康状况相一致的,但这并不表明对武装中国的渴望。其次,公布一个强化的“行为守则”(这个守则正在修改之中),以便更有效地限制出售最终用于军事的项目和基础设施。第三,在欧盟成员国中间颁布“内部标准”,以便更清楚地说明“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武器和基础设施的类别。根据这种标准,诸如雷达和某些通信技术等“防御性”项目将适于出售。
显然,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引起争议的问题——引起中国与欧洲之间、欧洲与美国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争议。仍然有待于观察的是,欧盟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它是否能抚慰有关各方。
“一种非常认真的婚约”
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也在其他领域不断增强。2003年10月,在欧盟与中国的年度高峰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包括一个有关团体旅游的协议。欧盟官员认为,到2005年,多达60万中国游客将根据协议访问欧洲大陆(和英国)。中国旅游机构以人民币1万元(1220美元)的价格提供为期10天的欧洲包价旅游。如今在大多数较大的欧洲城市,遇到中国旅游团体并不罕见。
欧盟官员也估计,在2003~2004学年,多达10万名中国学生在欧洲的大学和技术学院注册,其中或许一半在英国。这个数字大大超过在美国注册的大约6万名中国学生。因为美国政府严格的签证限制,2004~2005年美国校园内外国学生的数量预期至少下降大约10万人,其中许多人,包括中国学生,将改往欧洲求学。在2003~2004学年,近5000名欧洲学生在中国的大学注册。德国提供了最大的份额——1280名学生。另一个交流领域涉及中国共产党与一系列欧洲政党之间的交流。在许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只与其他共产党或者社会党进行交流,但自19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首先,中国共产党选定右翼欧洲政党作为交流对象,以增强欧洲反对苏联的舆论;然后,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将注意力转向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过去10年里,与欧洲大陆各国大大小小社会民主党的交流名副其实地达到数百次。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其自己的发展和内部改革方面,它能从社会民主党人那儿学习很多东西。这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目前正处于推倒社会民主党的福利国家模式的进程中,即使中国共产党指望借鉴这种模式,并使之适用于中国。
对这种交流以及其他交流的始终如一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年不充分的和被忽视的交往,中国与欧洲正在享受漫长的蜜月和欢乐(欧洲委员会主席罗马诺·普罗迪最近评论说,“如果这不是一桩婚姻,这至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婚约”)。法国政府宣布2004年是“中国年”,纪念“中国年”的展览和事件不少于378起。这反映出席卷欧洲的喜气洋洋的“中国热”。
诚然,欧洲与中国的新婚姻并非不存在摩擦。中国的主要抱怨集中于欧盟的禁运,即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或者防务技术,以及欧盟拒绝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将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向欧洲市场倾销若干类别商品的指控)。欧盟的抱怨清单更长。它不仅包括人权,而且包括“倾销”出口品、中国所谓的未能充分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非法移民和限制遣返非法移民、日趋上升的贸易赤字(2003年为550亿欧元,2004年有望达到800亿欧元)、以及对中国最近处理香港事务的担忧。然而,欧盟与中国正在讨论这些存在问题的领域,具有其自己的担忧的个别欧盟成员国也在致力于双向地解决这些问题。
浪漫背后
若干因素有助于解释欧中关系最近引人注目的发展,第一个因素是冷战的历史余波。在1990年代之前,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反之亦然——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每一方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每一方都不把发展与另一方的关系本身看作一种值得的追求;看待欧中关系的出发点是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因此,欧中关系从未形成其自己的独立的动力,而是对美苏关系变化的反应。虽然大多数西欧国家于1970年代建立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北欧国家和英国与中国建交更早,在1950年,而法国在1964年),外交接触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也始终受到限制。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于1975年正式与中国建立联系。中国与东欧的联系在1980年中苏分裂以后实际上并不存在。可是,1989年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为北京建立遍及欧洲大陆的商业联系和政治联系开辟了道路。自那时以来,尤其自欧盟于1994年开始形成一种中国战略以来,欧中关系已开始迅速发展。虽然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发展与中国的联系的速度较慢,但现在它们同样显示出积极交往的迹象。
推动中国与欧洲之间联系的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没有使中欧关系复杂化的台湾问题。所有欧洲国家严格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避免向台湾出售武器,或者接待台湾“总统”陈水扁的“私人”访问(欧洲议会曾邀请陈水扁在2003年3月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讲,但来自北京的强大压力使这次邀请和访问搁浅)。欧洲政府也严格控制台湾的代表处,除了允许它们促进贸易,很少允许它们干别的事情,而欧洲驻台北的对等代表处同样限制自己的活动。自法国于1992年向台湾出售武器以来,任何欧洲国家都不敢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或者防务技术——以免北京勃然大怒、断绝外交关系或者失去有利可图的合同的风险。与美国不同,欧洲不存在政治性质的“台湾游说团体”,但企业界和某些学者与这个岛屿维持着强有力的联系。总的说来,“台湾因素”的不存在排除了欧中联系方面一个潜在的重大刺激因素。
第三个相关因素是,欧洲(再次与美国不同)在东亚不具有实际的军事利益或者战略利益。没有欧洲军事力量被部署在东亚地区,也不存在可能使无论哪一方把对方视作一种潜在威胁的安全同盟或者其他义务。这使中国和欧洲能够自由地锻造一种不受两个因素妨碍的关系,这两个使美中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的因素是台湾和战略利益的潜在冲突。诚然,欧洲在对华关系中存在人权和贸易的担忧,但大体上不存在安全担忧排除了摩擦的固有根源。这种摩擦是中美关系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的特征。
第四,中国和欧洲对美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的全球行为的看法不谋而合。这种观点的趋同在乔治·W·布什总统的政府执政之前已经存在,但自2001年以来变得更一致得多。中国和欧洲都寻求限制美国的权力和霸权,无论是通过创造一个多极世界,还是通过多边地实行对美国的制度约束。法国站在这两种战略的最前沿,但法国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并非孤军作战。德国、西班牙、北欧国家以及欧盟本身也持有这种观点。正如欧洲委员会一名官员最近在布鲁塞尔向我描述的,“不是就压力而言,而是就我们对发展多边主义以及抑制美国[霸权]行为的共同兴趣而言,在欧盟与中国所有会晤的桌子上,美国是不说话的一方。”事实上,欧中多边合作远远超过了约束美国的共同渴望,因为布鲁塞尔和北京对全球和平、安全和环境所面对的范围广泛的挑战越来越持相同的观点。
第五,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在一些重要方面是互补的。虽然欧洲不能帮助中国缓和对能源供应和原材料的不能满足的渴望,欧洲公司能够满足中国的许多技术需要,也比美国公司更愿意转让敏感技术。对欧洲来说,中国能提供一个重要的低成本制造基地、一个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出口和内销的市场(大众、沃尔沃、标致和其他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的经营尤其成功)、一个投资和经营的吸引人的目的地、以及一个技术创新的源泉。
解释中欧关系和谐而迅速的发展的第六个因素是欧盟通过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提出的指导欧中关系发展的战略框架。欧洲委员会从1995年开始发布一系列政策文件,以引导欧盟与中国的联系。中国也于2003年10月发表了一份有关与欧盟的关系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阐述欧盟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采取的战略,也阐述正在实行的各种计划和交往。
欧盟的战略
欧盟对待中国的战略似乎以三个层次为目标:在全球多边机构中使中国负起责任,并帮助中国在承担其在这种机构中的适当角色和责任方面获得信心;强化双边交往(在欧盟一级);改进中国的“国内能力”以应对一系列管理挑战和改善生活质量。
欧盟在每一个层次都作出了各种努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具有同样的目标,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分道扬镳。欧洲长期以来是增强政府间机构以应对全球和地区的管理挑战的倡导者。尽管欧洲大陆存在“现实主义”的过去,自由主义的社会公共机构体系是在欧洲发明的,欧盟本身也是欧洲国家和社会多么相信对国内和国际问题作出协同一致的规范性反应的一个范例。尤其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处于努力建立并增强国际机构以应对一系列人道主义挑战的最前线(即使欧盟显然未能共同处理在其自己的后院——前南斯拉夫的危机)。中国的崛起符合欧洲的这种思路。
欧洲人不仅长期以来认为,如果中国加入所有国际机构,它将更容易被“控制”——它成为“修正主义强国”的可能性随之大大减少;他们也认为,中国必须承担应对全球挑战的责任的适当份额。欧洲人把中国看作一个负有重大的全球责任的伟大的全球强国。某些更热衷于现实主义均势模式的欧洲人也把中国看作一种希望实现的多极世界秩序中有用的一极。正如欧盟最近有关中国的政策文件简洁地提出的,“欧盟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全球活动家,与中国一样关心一种基于有效的多边主义的更平衡的国际秩序,并希望使中国成为处理全球问题的一个负责任的强国。”
因此,欧盟和欧洲成员国努力使中国加入许多国际组织。欧盟为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出了艰苦努力,并在致力于与核扩散、导弹扩散、武器交易、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贩毒和其他许多问题进行斗争的机构中与中国合作。欧盟和中国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也都是活跃的。正如中国外交部一份出版物最近所说的:“中国和欧盟不存在基本利益的冲突,对许多意义重大的国际问题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看法。”
欧盟通过双边会谈就范围广泛的事务交换意见。20个单独的对话机构和工作小组所涵盖的问题从人权到纺织品贸易,从科学技术到知识产权。欧中合作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话。每一次会晤都促使各自的官僚机构提出建议,并且商讨与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关的务实计划——从而使各自的官方机构彼此合作,并赋予它们共同的目标。许多成员国也在类似领域与中国进行其自己的对话。例如,人权在欧洲的社会和议会中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而德国、法国、英国、丹麦和瑞典都与中国进行单独的人权对话,欧盟和中国的官员也在其他论坛上经常会晤。而且,除了这一切,还有个别欧洲成员国的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会晤。2003年,不少于7个欧洲国家元首访问了中国。
欧洲官员与中国官员之间交往的密度因此是相当大的。这种官方交往的结构是重叠的,往往也是混乱的,但交流的总数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坦率和信任的程度据说也是很深的,而分歧以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得到讨论和磋商。与中国官员和学者的面谈表明,中国特别能接受欧洲官员所采用的公事公办和平等主义的方式。中国接受采访者往往把美国官员有时所采取的更傲慢、更专横和更盛气凌人的态度与欧洲官员的态度进行对照(否定的对照)。
欧盟对待中国的战略的关键方面或许涉及这个人民共和国国内“能力”的改善。能力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多方面的,涉及中国国内相当大的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分配。在2002~2004年期间,正在执行的这种国内计划包括40个项目,总价值接近2.6亿欧元(3.38亿美元)。这些计划分成三大类。它们支持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过程(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改革社会保障和开发人力资源)。它们支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保护水资源和生态多样化)。它们也支持有效管理和法治(减少非法移民和促进市民社会)。
这种国内主动行动的例子包括一个全国范围的环境治理计划、一个甘肃省的高等教育项目、一个乡村管理倡议、一个企业改革计划、一个天然森林管理项目和一个金融服务项目。这些例子表明,欧盟的支持目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开发援助和扶贫计划的范围,包括范围更广泛的一系列促进中国的变革的活动。市民社会和传媒改革是未来两件优先考虑的事。
这些正在进行的计划正在获得切实的回报,也正在改善中国应对范围日趋扩大的公共政策挑战的国内能力。欧盟的努力在中国国内赢得了广泛赞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最近指出的,“美国和其他国家靠空谈博得中国的好感,但欧洲人正在切实地这么做。”
世界事务中的新轴心
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的前景是非常积极的,中欧关系的强大动力、日趋增强的彼此信任和认识、障碍和摩擦的不存在、对世界事务互补的观点以及相互依存的经济利益促进了这种前景。欧洲与中国交往的两个层面——双边的国家层面和多边的欧盟层面——是彼此增强的。在中国进行的贯穿一系列计划范围的切实合作以及欧盟和许多成员国(尤其是英国和北欧国家)为这些计划投入的大量资金使合作的口头承诺具有实质性内容。
欧洲和中国正在享受其新的浪漫感情。这种激情是否会消散,这种新的亲密结合是否会解体?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鉴于不存在系统的或者战略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始终潜伏在中美关系背后——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中欧关系将继续不断地增强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延,中欧关系将成为世界事务中一个新的轴心,并将充当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上的一个稳定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