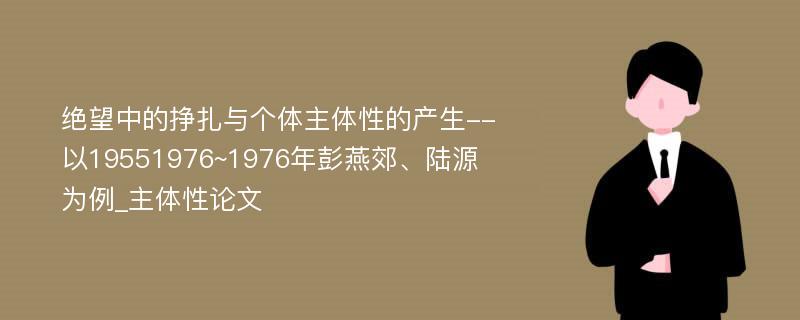
绝望中的抗争与个人主体性的出现——以彭燕郊与绿原1955~1976年的写作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为例论文,绝望论文,彭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254(2007)04-0038-07
彭燕郊与绿原标明写于1955~1976年期间的作品,在胡风冤案受害者这时期的写作中,比较直接地表达了他们对案件的精神反应。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作品文本,不少在以后的时间里经过或可能经过修改加工,但它们都有当年亲历的不可替代的具体情景作为作品的基础,修改加工多半是在艺术表达的完善方面。这也使得即使经过修改加工,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当事者的精神线索。① 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案件的发生是利用暴力对他们的社会身份乃至主体人格的剥夺,那么,他们是怎样在逆境之中重建自己的主体性的?由此出发的主体性的写作又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也构成了本文关注的中心。
一、心灵濒临抽空时的颤栗:彭燕郊的无声语
彭燕郊此时期的部分作品,收入他的散文诗集《夜行》中,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55~1957年受审讯期间形成腹稿的八篇。在这些文本中,抒写人内心的声音表现为非常复杂的状态:身份与人格被剥夺之后的耻辱感、生命的空白、疯狂的臆想、臆想中惊人清醒地揭示出的时代的荒谬以及与之相伴的批判精神等等,以一种辩驳、冲撞、矛盾的状态夹杂在一起。然而,这样复杂的声音,其存在方式却往往只能是“无声语”。冤案审讯常见的一种形式,乃是要求“鹿”自己承认为“马”。所谓“无声”,即是因为权力者要求被划为另类的人按照事先的定性发声,凡是不符合这种定性的声音,必须被压抑,处于“无声”的状态。这实际上等于企图以权力机器的力量,取消后者的主体性,使之处于一种空白状态:
……我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符号,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和这个符号相吻合,充实它所代表的内容,适应它所提出的要求。(《无声语》)
让活生生的个人向一种不应为之所有的“罪”的符号认同,并迫使其向虚假认同,混淆真假的界限,使得后者的生命处于一种被抽空的过程之中。对这种生命的被抽空的过程的片断记录,是彭燕郊的这些文本最摄人心魄的地方。它们记录的被冤屈的知识者内心的屈辱感与空白感,真实得让人悚然。它最有文学价值与精神价值的部分,也正在于这种真诚的、无所顾忌的对陷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濒临崩溃时的精神状态的描写——无疑,这也是他当时内心最深处的体验。
首先是隔离之后社会身份被抽空:
没有恨,没有爱,感情的真空。爱已没有人敢接受,恨,恨谁?恨这渺茫的罪名吗?(同上)
这里陈述了个体生命被彻底排除在社会与人群之外的一种悲哀,个人被贴上一个被社会彻底排除的标签,此生此世,休想再融入社会,“只能过着永远、永远生锈的,发霉的日子,在歧视,蔑视,仇视的眼光里”过活。更严重的结果在于,个人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以后将永远被迫成为一个对社会无用的废物,如同被审讯者由审讯者的套话“废物利用”,联想到自己是“一只被踩烂的斗笠,只剩下一圈笠边的”、“一只被敲掉壶嘴、壶把的烂茶壶”乃至“剪下来的指甲”、“挖出来的耳垢、鼻屎痂”、“头发根上掉下来的头皮屑”……当“废物”这个词完全被实体化后,抒写者的屈辱、辛酸、愤激通过这种自我屈辱、自我作践表现得特别强烈。他清醒地感觉到自己在新的社会秩序中不再有容身之地,他也不再要求被荒谬的社会秩序所承认。当人被置于一种剥夺得一干二净的状态时,这种自暴自弃的心理也算得上一种没有办法反抗时的反抗办法吧?
然而,“罪人”还要蒙受更为惨重的“心灵的苛刑”与“意识的惩罚”——“耻辱”。在《耻辱》里,彭燕郊用了一个触目的意象,将耻辱形象化为“耻辱蚂蝗”,粘乎乎软腻腻地布满全身,像吞噬人血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人的尊严,使之成为“不要脸的东西”,而人的羞愧感与自卫意识更加激起它们的兴致:
你能想象,不用好久,你就将只剩一具残骸,发着既不是香气也不是臭气,不像烧糊的焦味也不像变质的霉味,馊味,而是辛酸的泪和懊悔的叹息能够发出的气味,一种非味觉所能接受的气味以上的气味,一般气味不可能有的那种气味。(《耻辱》)
耻辱之所以能够作为一种精神苛刑,正在于它不但使人从社会中隔离出来,更时时刻刻向别人也向被排除者自己提醒这种“异质性”,从而使他即使在没有他人的时候也处于自我意识的惩罚之中——仿佛是一个可以自己运转的惩罚机器,而蚂蝗咬啮的意象生动地传达了耻辱所能给人的深层的心理体验,使得这种体验具象化,仿佛可以使人亲眼看得见自己的尊严与自我在耻辱的一口口咬啮中瓦解。
进而,自我被抽空的状态在最极端的时候被表现为整体性的,成为一种精神病的表现,哭笑无常,生命处于意识失控的空白状态,仿佛切身经历着主体的消解:
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喷射力使已经失去知觉的我爆发出这一连串没有任何内容的哭和笑。但在哭和笑的时候却还能感到残余的生命在蠕动,在不自禁地往外滴,滴,滴……滴出既不是悲哀又不是欢喜的情绪以外的不知什么东西,还能感觉到生命在蠕动之后没有重量的飘浮,下坠,下坠,飘浮,向着上下四方无穷尽的大空白。忽然,又把自己悬挂起来,搁浅起来,在无比深,无比宽之上,之下的大空白中,失控了的生命的残余由于得不到控制而彷徨,而茫然,而惊慌,而找寻不存在的,或虽然存在的一大部分、一小部分不像自己的自己,而在自以为找到那生命的侧影,生命的碎片时,庆幸自己竟已不认识自己,“那不是我”,而得到片刻的缓解;但立刻又翻悔,为这多余的蠕动、寻找和发现所激怒,所羞辱,于是又爆发出一连串无内容的哭和笑,以及哭和笑的混合。
……(《空白》)
《空白》中的文字虽然是出狱以后凭借记忆记录的,但却生动地再现了抒写者神经濒临崩溃时的心态,生动得让人头皮发麻。首先是生命内容的失控,失控之后,整个生命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从而接触到茫然的大空白,在这大空白之中,生命失去了意义,找不到自我,只有在有意识的自我之外的生理反应。寻找任何主体性的表现在这里立刻引起一种生理性的震颤,因为,可以为强权势力所合法地承认的自我表现实际上即等于抹煞自我的存在,任何被外界认为合法性的自我属性却都被真正的自我所拒斥,人的躯体在自我的矛盾之中只能爆发出悖谬的外在表征:表达悲哀的哭与表达欢乐的笑都失去了内容而毫无逻辑地夹杂在一起。生命的内容进入一个被淘空的过程,生命变成了“不能算是生命的生命”,失去了一切感觉,甚至失去了表达自我存在的必要。在这里,任何显示生命、自我仍然存在的迹象,实际上都必然被打倒,似乎其出现即是“企图以此证明其绝对的极端不稳定”。整个生命的存在都处于一种似梦似幻的状态,它充满了生命存在的迹象,然而实际上又等同于主体性的“空虚”——因为有一个固定的过去的“我”存在,我无法理解我之外的“我”是什么,只能感到生命被压榨、消耗一空……
就此而言,彭燕郊的散文诗为这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到的最为酷烈的精神炼狱做了非常具有心理深度的见证。也许在所有的胡风冤案受难者的潜在写作中,彭燕郊的《空白》在记叙的详尽方面最为触目惊心——在这里,生理性的失控直接体现着精神上的空白,而精神上的绝望即直接表现为生理上的狂悖——它直接让人们接触到当事人精神上所感受到的高压的质地,其表现力绝不比沈从文的“呓语狂言”差。②
二、个人对绝望的抗战:绿原的精神历程
与彭燕郊一样,绿原在审讯中也经历了痛苦的“认罪”过程,从1955年5月17日到1962年6月5日,绿原总共被隔离了七年之久,其中头五年多是单身监禁,接着又被送到秦城监狱,在集体中改造了一年多。这中间的心理体验,虽然没有像彭燕郊那样在当年就笔之于书,但也是极为惨酷的。
在狱中,失去表达自由的感觉是一样的,像彭燕郊的《无声语》一样,绿原也有一首诗,叫《手语诗》。不过,他虽然也表现那种极端的疏离感,却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个人在荒谬之中重新面对自我的精神历程。《手语诗》显示出一种被取消了表达的权利之后、自我表达已经极度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表达自我心灵的努力。如果连表达“不想表达”都只能用“无声语”或“手语诗”的形式,这种表达实际上是一种对自己的表达。这也显示它们的意义首先是指向诗人自身的,然而,也许我们不该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过分作界限清楚的区别——人的存在总是社会化的存在。至少,困难之中对自我心灵的表达,显示了个体心灵的独异性,即使在权力控制最极端的状况下也不能完全被扼杀。在《童话》时期与90年代之外,因冤案隔离及“文革”时期是绿原另一个个人写作时期,大概与此有关。这些诗属于他最为感人的诗篇,因为环境逼迫人不得不以生命来反抗历史的荒谬与个人心中滋生的黑暗。
这种个人反抗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给我们标示了一种主体性出现的方式。绿原的名诗《又一个哥伦布》直接描述了这种心态。在这首诗中抒写者将自己比作20世纪的“又一个哥伦布”,他们都面对着无限的洪荒,不过,前者面对的是无限的空间,而后者面对的是无限的时间。绿原是著名的追求诗歌意象的奇特、醒目与构思的深度的诗人,这在他这一时期那些最初只有几句或几行但后来经过修改、锤炼才得以定稿的作品中也不例外。这些诗篇一般都是以叙述来代替抒情,但由于意象尖锐且极具张力、构思奇特因而达到很深的思想深度与精神深度。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很明显。空间与时间的对比与转喻,构成了该诗构思的核心:老哥伦布面对的是“空间的海洋”,“四周一望无涯/没有陆地,没有岛屿/没有房屋,没有船只/没有走兽,没有飞鸟/只有海/只有海的波涛/只有海的波涛的炮弹/在追赶,在拍击,在围剿”;而新的哥伦布则“航行在时间的海洋上”,前后也是“一望无涯”,“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没有年月/只有海——时间的海/只有海的波涛——时间的海的波涛/只有海的波涛的炮弹——/时间的海的波涛的炮弹/在追赶,在拍击,在围剿/他的孤独的‘圣玛丽亚’”。两段诗句是对称的,共同有力地传达出题词中巴斯噶(Pascal)的“无限空间之永恒沉默使我颤栗”所包含的内容,洪荒广大的沉默的空间、时间,失去了任何生命运动的迹象,也失去了所有衡量这种运动的标志,构成了一种对希望的无边的威胁:因为其广阔无垠,所以着陆的希望非常之渺茫,而海的意象所传达的这种“空间”与“时间”的绵延性、均质性与广垠性使得这种希望渺茫的航行更加显得枯燥、沉闷、无望,难怪那“永恒沉默使我颤栗”。
在无尽的时间与无垠的大海的对比与转喻中,绿原也揭示出自己狱中处境中有限与无限、动与静的强烈矛盾,从而使得“时间的海洋”、“航行”、“圣玛丽亚”号等意象充满了张力。他将自己狱中的漫长岁月比作“时间的海洋”,航行在这个海洋中的“圣玛丽亚”是他的囚室,然而,哥伦布的“圣玛丽亚”面对的无垠的大海是真实的,它本身是运动的,也是开放的,而20世纪的“又一个哥伦布”,它的“圣玛丽亚”却是封闭的,也是静止的,那在无垠的时间里的航行也只是一种玄想,其无望与寂寥实际上比老哥伦布还要严重:
他的“圣玛丽亚”不是一只船
而是四堵苍黄的粉墙
加上一抹夕阳和半轮灯光
一株马樱花悄然探窗
一块没有指针的夜明表咔咔作响
再没有声音,再没有颜色
再没有变化,再没有运动
一切都很遥远,一切都很朦胧
就像月亮,天安门,石牌胡同……
这在时间中的航行实际上是一种寂寞而单调的静止不动,就像绿原事后描述的:“外面的生活在沸腾,接着发生肃反,鸣放,反右,三面红旗,庐山会议,反右倾,三年困难,反修防修等等,这一切都与我不相干。”[7] (P140)这时间中的航行仿佛被抽空了任何历史的内容,面对的是个人的茫茫苦海。但是面对这茫茫苦海与人生的炼狱,像老哥伦布一样,这“又一个哥伦布”仍然有自己的信念,而且只有这种信念才成为他坚持这苍凉的航行的心理支撑:“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这个哥伦布坚信的也许是自己的无辜,他的印度也许是无罪释放后重新获得自由,也许是后来的《重读〈圣经〉》中所说的“对我开恩的只有人民”,这些都可以不管,我们所关心的是:他最后达到的是怎样一个“新大陆”。我倾向于把这个“新大陆”理解为以往被遮蔽的个人的主体性的出现,但在阐释这一点以前,我们不妨检视一下达到“新大陆”以前的旅程。
虽然绿原处身的囚室是一种封闭静止的环境,但他的航行的比喻确实不无道理。表面上看,这种航行被抽空了历史的内容,但在个人的心理中,却确实有一个在精神炼狱中煎熬的历程。对于描述这个历程来说,可以参考的诗篇真是少得可怜,除《手语诗》、《又一个哥伦布》以外,仅有《面壁而立》、《自己救自己》、《好不容易》几篇,所幸这些诗篇,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一些颇具深度的精神片断。
《面壁而立》通过幻觉,简洁地表现了抒写者在灾难中的精神历程。从题记中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表达的是“1960年8月单身囚禁五年后将转集体监狱在交接室被命面壁而立达二时许”时的心理体验。在幻觉中,“一堵手舞足蹈的白墙”像猛兽一样向抒写者扑来,两者“面面相觑”,离得太近,“近得简直看不见但听得见它”,于是在幻听中抒写者的各种各样的意念像油彩一样向白墙泼去,使之成为“五颜六色”的“一幅可怕的交响乐式的大壁画”:在幻觉的第一个层次,抒写者首先听到“风声雨声枪声以及逃窜者惊慌而凌乱的脚步声”,那逃窜者似乎逃出了壁画,与抒写者并排站立,艰难地喘息着;在第二个层次,抒写者听见自己“一脚跨进了壁画”,“正和逃窜者一起在刺丛中间爬行还在喘息”,前面有路,又似乎没有路,“在有路和没有路之间”逃窜者们奔跑着,“在希望之中奔跑着”;进而,抒写者从幻觉之中苏醒过来,然而感觉自己一个人还在奔跑,匆匆奔向了永恒——“什么也没有”的永恒,也许就是没有绝望与希望的虚无吧,它至少使得抒写者从纷乱中清醒——然而,这种虚无中的清醒没有机会延续多长时间,交接手续完成,新的“宽敞而嘈杂的监狱”“像一头巨兽”把抒写者吞没。他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与肉体的炼狱。
这里,幻觉的过程表现为一个“逃亡”的历程,他似乎逃向“希望”,最后得到的竟是虚无,而连这虚无竟然也不能持有,只有再经历一次炼狱的磨炼。这仿佛是一个简洁的蒙太奇,概括了胡风冤案受难者们的生命姿态:那刺丛之中的爬行与喘息使人联想起在刺丛中求索的鲁迅的精神传统,即使在绝望之中他们仍然在“爬行”、“喘息”、“奔跑”着追寻,虽然前面的永恒也许竟是虚无。诗的最后写道:
你——
这支紫色的灵魂浑身颤抖着
让它的嶙峋的骨骼
把自己搡着喂了进去
而它则迸成飞灰
漂泊在狱门外的沼泽地带——
如果联系到后面的意象——“巨兽”般的狱门、狱门外的沼泽地带等实际上都将监狱隐喻为地狱,那你不能不想到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题词:进入这里的人,把一切希望都放弃吧。那进入地狱的灵魂将经历怎样的煎熬呢?它最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正是在这种绝境中,绿原的诗歌显示出其最有力的地方,它告诉人们,当一切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才会发现唯有自己的心灵与精神才是真正可以凭借的支撑,在面对最深刻的绝望时,人的主体性才真正彰显与建立起来。在《自己救自己》中,绿原借用了那个非常有名的所罗门的瓶子的阿拉伯传说,而对之作了小小的改动。这首诗是以“精灵”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的,头三段实际上是改写原故事中精灵的三个愿望,但绿原有意识地用复沓的方法强调了精灵的极端压抑无望的处境——因为是第一人称,便很自然地将精灵的独白转换成了抒写者的自况:“头一百年我被关在一只铅瓶里沉到了海底周围有沉默的鱼虾在咆哮”、“二一百年我仍被关在一只瓶里沉在了海底,周围仍是沉默的第几代鱼虾在咆哮”、“三一百年我还被关在一只铅瓶里还沉在海底还有沉默的第十几代鱼虾在咆哮”,复沓的句子很强烈地传达了瓶子中的狭窄、憋闷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的情形,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绿原在前面描述的单人囚室的可怕的单调孤独。而精灵的心理也越来越焦躁、愤怒,由发誓让救它的人变得“富足”、“长寿”到最后发誓让他“马上死”。在原来的故事中,精灵的做法是很蛮横霸道的,绿原的描述却因为采用了精灵的视点、强调了它极端压抑无望的处境转而引起读者对它的同情与理解。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段,精灵在被渔夫略施小计仍然沉在海底之后的独白:
我不再发誓不再受任何誓言的约束不再沉溺于赌徒的谬误不再相信任何概率不再指望任何救世主不再期待被救出去于是——大海是我的——时间是我的——我自己是我的于是——我自由了!
这段独白使得整个故事的主题转换成为对绝境中精神自由与自主的真谛的揭示。一个人的心灵自由与否,与他外在的处境并没有决定性的关系。一个为所欲为的人仍然可能是不自由的,因为他很有可能是自身欲望的奴隶。相反,身居囚室的囚徒,却有可能保持心灵的自主与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主与精神的自由取决于对外界权威与自身妄念的断然舍弃,只有这样,才能在绝望之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精灵之所以一次次感受着痛苦的折磨,是因为它完全将获救的希望寄托于外界,为了外界降临的莫须有的得救而期待、焦躁甚至愤怒。当它一次次碰壁之后,放弃了对外界的救主的企盼时,它也就终于从希望与诅咒中平静下来,从“施恩图报”的循环中解脱出来,直接面对自己必须面对的命运,在绝望之中从自身内部吸取力量,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变成真正的强者。心灵的自由在对外在希望与妄念的舍弃中出现,个人的自主性在对荒谬的承担与反抗中出现。在这时候,正如希望是虚妄的一样,绝望也成为虚妄,从而带上了一种尼采的悲剧人生观式的崇高精神。
三、个人主体性出现的困难及其意义
然而,这种个人的主体性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以绿原为例,从50年代初开始,面对文艺界某些人针对阿陇、路翎的专横与仇恨的批评,他已经开始陷入“一种长期无从解脱的二律悖反式的深刻矛盾之中”,他写到:“一方面,我作为党员在言行上必须服从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决定;另一方面,我认识到或者说我相信,文艺界的那些现象、事态和做法明明不利于人民文艺事业,明明违背党的基本政策,明明解决不了有关的思想问题,而任何盲从行为终归只能招致政治良心和艺术良心的谴责。”[7] (P112~113)组织行为和个人良心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入狱之后,不过这时他已经失去了沉默的权利,在极端状态之下,在真理与权力之间必须做出自己或此或彼的选择——正如伽利略在真理与宗教审判所之间一样。也恰恰是在这里,绿原做了与伽利略一样的认罪的选择。他后来反思胡案时说,从中可以看到“当年广义的个人迷信如何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人身依附和思想僵化”、如何使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与真理认同的勇气”,[7] (P134~145)显然将自己也包含了进去。由矛盾彷徨到承认自己有罪,除过外界环境与权力的压力以及个人现实上的考虑之外,思想上的诱因显然是更为重要的,绿原自己说:“由于长期为二律悖反所折磨,一旦发现党和胡风不可能‘调和’,我在神光的炫耀下立即就产生了负罪感。”尤其是发现“编者按”是谁写的以后,就更不敢对之否定,而是感觉“作为党员,我必须向党交待一切”。[7] (P135)这里的价值天平上,集体的因素显然要大于个人的因素,而慑于权威的因素也远远超过了维护真理的因素——显然,之所以会“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与真理认同的勇气”,既是“广义的个人迷信”的结果,也是因为在价值判断上集体立场与庙堂权威在个人心目中占的地位太过重要。
对于后人来说,理解这一代人的集体主义思想的利弊确实需要费些心思,因为这里造成了许多现实的与理论的悲剧与误区。在真实与良心面前,最朴素也是最为诚实的立场如《新约·马太福音》第37节所言:“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便是出于那邪恶者。”然而,对于曾经的一代人来说,求真的考虑在集体利益与最终目的面前必须让路。英籍匈牙利作家库斯勒在40年代所写的《中午的黑暗》对这一心态有惊人的描绘。这是一部直接受30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刺激的作品,在那次大审判中,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称雄一时的老革命家,在公开的法庭上,个个成了泄气的皮球一般,或者痛哭流涕,或者垂头丧气,承认了自己在外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罪行”。这些人物在小说中以虚构人物鲁巴肖夫的形象出现。“究竟是什么力量打垮了鲁巴肖夫的精神,摧毁了他的意志?不是单独禁闭和疲劳轰炸般的审讯,更不是肉体的苦刑。而是鲁巴肖夫陷在其中而无法自拔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诡辩的逻辑。崇高目的的大前提,使鲁巴肖夫这个20世纪的革命家像喝了‘迷魂汤’一样那么愚昧和盲目,不敢和权术政治公开决裂,更不用说挑战了,深恐这样会对最终的目标产生不利的分裂……”为什么会“默默地、顺从地接受了种种横加的莫须有的荒谬罪名”,“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对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产生了怀疑,但是始终摆脱不了这个恶圈,因而认为自己是在为了最终的崇高目的,作出最后的贡献和必要的牺牲,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在内。”[8] (P294~295)这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党、集体、国家、事业、最终目的等等作贡献,似乎是一种崇高的悲剧性的牺牲,然而现实的发展对之却构成尖锐的讽刺——他们的“克己”的行为不但没有为“历史的进步”做出一点贡献,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了罪恶的同谋。最朴素的立场其实也是最不应该放弃的。虽说库斯勒的小说是一种虚构,但这种思想在中国也很普遍。比如《中午的黑暗》的译者董乐山注意到的老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因吸烟不慎引起火灾时说的话:“火,我确实没有放。但如果党要我承认是我放的,如果承认了对工作有利,我可以承认。”[8] (P295)又如牛汉在听到被开除党籍的决定时说:“牺牲个人完成党。”[9] (P451)曾卓也发出这样的呼喊:“不要遗弃我呵,/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10] (P113)对于这一代人来说,集体的理想确实比个人的利益要远为重要,但当以集体理想的名义要求个人歪曲真实、背弃良心时,如果依然向集体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就不但是对个人本己的立场的遮蔽,而且是对知识分子最应珍视的品质的背弃。正因为这一点,绿原多少年后深切自责,不是没有理由的。虽说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良知未泯——他们和“鲁巴肖夫”式的完全自欺有非常大的距离,并没有完全被虚妄的“历史进步”所彻底欺骗,他们虽然可以认罪——但并不为这种认罪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构辉煌的结果来欺骗自己。像绿原虽然迫于权力压力与自己精神上的罪感承认了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但交代问题还是在事实的范围——他的认罪仅仅是对自己立场的否定,虽然这样的代价也已是很惨痛的。
可以说,与狱中诗篇体现出来的相反,此前的认罪过程正说明了对外界的庙堂权威与广场理想的忠诚恰恰是导致个人失去自己的主体性的诱因。对于绿原这样在40年代为了新社会的理想而奋战的知识分子来说,就更是如此。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个人只能凭借自己的良心来裁判别人与裁判自己,而不能倒向不无可疑的集体权威,而对于自己选择的后果,也没有别的权威可以推卸责任。正如鲁迅在世纪初年就发现的那样,民族、国家的本根实系于个人的本根,主体性的建立要依据个人的内心而非多数或外来权威。在这方面,彭燕郊的文本具有更为彻底的批判与反省精神,他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外界的批判,如果是那样,不免有些缺乏说服力。那随意可以向别人分派耻辱的作为价值标准的权威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人格》中,诗人描述了一个在“把一切交给最高”的年代大家排队上交“人格”、换取一个随时可以被取消的“民格”的场面,答案在这个场面中不难找出。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场面不仅是为了批判庸众,抒写者“我”自己也是那上交“人格”的队列中的一员——当批判的精神指向我们自己内部可能存在与曾经存在的奴性与黑暗时,真正的无所依附的主体性才能在这种“扪心自问”的反思中开始建立。绿原在多少年之后深切省思“神光”的力量“如何使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如何使人丧失了敢于与真理认同的勇气”,其实是经过多少年的灾难之后对这一观点的另一个明晰的表达。
而正是在这一方面,保留不多对狱中经历进行描述的诗篇显出其真实的意义来。概览彭燕郊与绿原的这些赤裸裸的心灵书写的诗篇,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他们所代表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延续,但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延续已经失去了其现实目标、现实力量的支撑和社会功利主义——而在40年代与50年代初,这些都是存在着的而且对他们构成巨大影响与制约的。在狱中的环境下,被集体与外界彻底排除,尤其是短时间内通过认罪释放的希望彻底破灭后,个人真正面对存在的虚空,除过自己的信念之外,一无依傍,因而只能是一种对来自外界与自身内部的荒谬与绝望的个人抗战。然而,真正的个人的主体性,恰恰是在发现外界的宏大的叙事——不管是庙堂的还是广场的——都不足为据、甚至充满了荒谬性因而不得不对之舍弃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与那些被迫的、迷失的认罪相对比,正是这些袒露个人心灵的诗篇显出其真实的意义来,那赤裸裸的精神空白的嚎叫,那在时间的空白之中凭借信念航行的20世纪的哥伦布,那在荆棘之中奋力爬行的逃亡者,那对外界不再抱希望不再指望救世主而是自己救自己的精灵,其艺术感染力与心灵的力度正显现出个人主体性出现以后的巨大作用。个人从虚妄的集体中分离出来的,造就了一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诗篇——讽刺的是,这样的诗篇恰恰是在被社会彻底排除之后出现的。
也正是个人主体性的出现,成为承担荒谬的命运的力量。几十年后,绿原描述自己狱中的心理体验时,不自觉地提到希腊神话里两个著名角色西绪弗斯和坦特勒斯。[7] (P134)当联想到西绪弗斯时,绿原自己心目中未必意识到这个形象在法国作家加谬笔下成为代表对生存荒谬抗战的重要原型,但他的描述却直接接触到这种反抗荒谬的核心思想。面对狱中的漫长岁月,绿原显出很强的忍耐力,“像斯特凡·茨威格的主人公在狱中自学象棋一样”,他“通过自学德语排遣无穷的岁月和无垠的忧伤”[7] (P140),以后德语程度竟然到了能够翻译卢卡契与里尔克的程度。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荒谬的命运的西绪弗斯一样,“他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就是对诸神的蔑视”。这是50~70年代公开文学中从未出现的精神力量。
注释:
①彭燕郊的潜在写作及写作过程曾前后分别收入《夜行》、《野史无文》,绿原已发表的潜在写作曾分别收入《人之诗》、《人之诗续编》、《绿原自选诗》,后全部收入刘志荣编《春泥里的白色花》,本文对二人原诗引用均依据《夜行》及《春泥里的白色花》,以下仅在括号内注明篇名,不再一一注明页码。彭燕郊有关写作情况可参考《〈夜行〉后记》及《野史无文》前言;绿原有关写作情况参见《野史无文》附录绿原致刘志荣信。
②根据《空白》前记,彭燕郊患的是“心原性精神病,心脏有毛病的人受强烈刺激即得此病”,显然,同一般精神病不一样,这里既有心理的原因,也有生理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