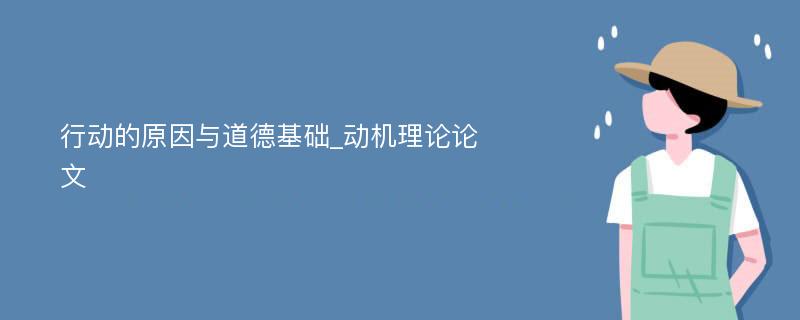
行动的理由与道德的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理由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5-0048-07
“行动的理由”(reasons for action)是当代西方元伦理学界兴起的一个重要话语体系,目的是通过追溯道德的实践性问题最终为道德建构起“证成”(justified)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说,行动的理由是将行动与理由加以有机连接的一种理论企图,其基本思想逻辑是:每当我们践行行动A的时候,我们必然先前具有引起行动A的理由R。换言之,我们的行动是有理由的行动,行动必然出自于理由。然而,实现理由与行动的契合面临一个困境,即两者之间似乎缺乏最基本的概念联系:理由是“认知性”(cognitive)的,理由的产生、选择与运用过程归根结底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过程;而行动本质上却是“意动性”(intentional)的。认知与意动的二元对立性使“行动的理由”似乎成为一个概念悖论。①除此之外,行动的理由理论还必须回答理由对行动的规范性约束问题,即理由如何成为行动价值(“善”)的裁决者。休谟主义的兴起主要源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应对,而康德主义则更多地给予行动道德价值规范性的关怀。本文分别对行动理由的这两大主流理论作了考察,并对它们各自的缺陷作了指摘与批评。
一、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动机
在试图建立起理由与行动之间桥梁的各种努力中,休谟主义依赖“动机”(motivation)概念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洞见,并迅速成为一种主流的理论。其方法是在理由与行动之间“嵌入”动机概念,并借此刻画了从理由至行动的传导机制。②休谟主义的理论是,每当我们具有行动A的理由时,我们必然具有践行A的动机M,动机M促使我们将A现实化,从而产生了我们所观察到的行动。然而,行动的理由为什么能够产生行动的动机,是休谟主义者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对此,他们的观点是,动机的产生实质上来自于主体的“欲求”(desire),而非来自于纯粹的信念。当主体具有某一欲求时,主体自身拥有的理性将生成满足欲求的行动理由,即认知性的信念。
在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 1981)那里,理性信念是发端于“主观动机集合”(subjective motivational set)、经过“完满思维路径”(sound deliberative route)而形成的理由。某一行动的理由产生了践行该行动的动机,但动机归根结底却是欲求的产物。所以,对威廉姆斯来说,欲求本身可以成为行动的理由。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当同事问张三为什么明天要去河北的时候,这实际上是在索取张三去河北这一行动的理由。张三的回答是:“我想去探望我的母亲。”这里,探望母亲的欲求就是张三奔赴河北的理由。休谟主义的核心是所谓的“休谟主义动机理论”,即行动的动机必须来源于行动主体的欲求。其背后的理论假设是欲求与信念的二元对立性。张三去河北的理由还可以有多种语言表述,比如,“母亲生病需要我探望”、“我认为(或相信)我的探望将会使母亲感到欣慰”等等。然而,休谟主义者辩称,这些表述性的“理由”并不能提供张三奔赴河北的现实动机,除非他具有关切母亲的欲求。母亲的身体境况需要他前往探望、照料,甚至这种需要是一个客观性的事实,但如果他不想去满足母亲的这种需要,他就不会具有去那儿的动机。
所以,威廉姆斯认为,行动的理由要成为激励行动发生的理由,就必然发端于行动主体的某一欲求。同时,每当主体拥有某一欲求之后,也必然能够生成为满足欲求而采取行动的理由。他把这一机制下的理由称为“内在理由”(internal reasons),而把超越于该机制的“理由”叙述称为“外在理由”。他强调,真正的理由都是内在性的,不存在所谓的“外在理由”,从而反对外在理由论者。按照史密斯(Michael Smith)的术语,威廉姆斯的“理由”仅仅是“动机理由”(motivating reason),而外在理由主义则强调“规范理由”(normative reason)的存在。当某人的房子着火时,虽然他作出了没有逃生的选择,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他应当逃生的“规范理由”。但威廉姆斯的观点是,他选择没有逃生,自然有他自己的“内在理由”,比如说他原本就打算自杀。主体完全是自身欲求的权威,没有任何外在的事物能够裁决主体自我的欲求。外界的任何标准如果不能成为主体如何行动的考量,它也就无法构成主体行动的“理由”。所以,“理由”只能是“第一人称的”(first-personal),仅仅对主体而言才有意义。
相反,外在理由论则否认威廉姆斯的主观理由主义,而强调理由的第三人称性。一个人也许具有彻底除掉其公平竞争对手的“内在理由”,但那仅仅是他的个人理由,事实却存在着他不应当采取这种行动的“规范理由”,即使这个“理由”对他而言是“外部”的。表面看来,内在理由与外在理由之争是一个本体上的争论,理由外在主义是部分地出于对内在主义主观色彩的担忧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外在理由论者看来,理由内在主义将行动的理由单纯化约为行动主体的主观欲求,排斥了主观之外的规范性权威的可能性,这是无法接受的。具体到道德问题上,如果行动完全取决于主体的主观理由,不存在任何外在的规范性裁决标准,那么我们将无权去评判、指责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不道德的行为很明显是出自个体的“内在理由”。按照内在理由论者的逻辑,只要主体的行动是出自于“内在理由”,他的任何行动都将是合理的。
笔者认为,理由外在主义者对威廉姆斯内在理由论的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威廉姆斯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试图去证明外部应然规范的非存在性,他所强调的是,这种外部应然规范对主体的行动如果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它必须首先成为主体的“内在理由”。只有“理由”得以内部化,才能给主体的行动提供现实的动机。事实上,对威廉姆斯而言,“理由”是针对行动的专有语言,外界标准如果无法解释主体的某一行动,它就不能被称作“理由”。在该意义上,也许存在着外在的规范,但没有外在的“理由”。所以,威廉姆斯并不像许多理由外在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道德虚无论者。他仅是赋予了“理由”以特定的内涵,即理由必须与主体的动机相联系。
在理由、欲求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上,威廉姆斯是一个休谟主义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认为理由在欲求上没有裁决权;其二,他坚持休谟主义动机理论,宣称欲求是产生行动动机的最终源泉。但道德理性主义者反对这两个信条,辩称理由在行动中具有更加根本的作用。理性主义者内格尔(Thomas Nagel 1970)虽然承认信念与欲求的概念二元化,但否认休谟主义的理由怀疑论,认为理由可以对欲求加以考量。他的辩护逻辑是,行动主体往往用“审慎理性”(prudential reasoning)来决定当前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审慎理性”的本质则是将主体当前的欲求搁置一边,让“远期理由”来决定当前行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购买保险的行动决定。一般说来,人们的当前欲求是不想每月支出收入的一部分为将来可能的风险进行投保,但“审慎理性”往往让我们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我们运用“远期理由”来决定当前的行动。其结果是,“审慎理性”决定下的“远期理由”取代了当前的欲求(即不想购买保险)而促使我们购买保险。由此可见,是主体的“远期理由”而非当期欲求为当前行动提供了现实化的动机。
另一位道德理性主义者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 1998)同样强调理由在行动动机中的核心作用。他假定了一个“理想的德性主体”(ideally virtuous agent),该主体拥有两种彼此关联的能力:一是拥有确切概念的能力,二是利用确切概念正确地分析自己所处的情景从而形成道德信念的能力。而对自身处境的理性勘察以及由此形成的信念或理由,构成了行动主体采取合宜行动的动机来源。没有对先前概念的掌握或者缺乏理性对主体自身处境的正确分析,纯粹的欲求将无法给予主体行动的动机。
理性主义者致力于打造一个客观的行动理由理论,强调行动理由的客观性,反对休谟主义理由论中的主观主义。但是,如果把休谟主义的行动理由理论完全视作一个主观主义学说,那是一种曲解。事实上,休谟主义的理论是客观理由论与主观动机论的二重体。对威廉姆斯而言,行动主体通过“完满思维路径”生成行动的理由,以满足来自于“主观动机集合”中的某一欲求。虽然后者是主观性的,但行动主体借助于理性所发现的行动理由是客观的,因为它完全独立于主体的欲求状态。所以,本质上,休谟主义实践理由的客观性来自于工具理性的客观性。比如,休谟主义者德雷尔(James Dreier)承认实践理性对行动主体的客观约束性,但他坚持这种约束仅仅是来自于工具理性的一种约束。工具理性指实现主体欲求所采用手段的有效性与合理性,而主体理性恰恰是由主体的工具理性构成的,主体是否理性,需要诉诸于主体的行动是否是工具理性的加以考量。工具理性决定了主体的理性。所以,意向求生者在房子碰巧失火时选择逃离是理性的,而意欲轻生的人选择不逃离也是理性的。我们可以把休谟主义的工具理性概念作以下阐释:主体欲求D,寻求行动A。如果主体是理性的,那么行动A将有助于D得以现实化。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主体形成行动A的理由而实现的。如果主体通过“内在理由”选择了相反的行动-A,错误地相信-A能够满足欲求D,那么他的这一“内在理由”是非理性的。决定行动理由(即“内在理由”)是否理性的标准是威廉姆斯所提出的“完满思维路径”概念,它是考量工具理性的根本法则。
理性主义者却不认同休谟主义者的工具理性论。相反,他们认为,主体的理性并不仅仅在于工具理性,更重要的在于目的理性。目的理性体现在主体具有对“主观动机集合”里的要素加以审视、反思和选择的能力,从而展现出理性对欲求的裁决权。内格尔的“审慎理性”是目的理性论的版本之一。假设主体的当前欲求集合包括两个要素:投保与不投保。“审慎理性”会让主体在这两个欲求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比如说,主体否定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不投保欲望而选择投保。内格尔辩称,“审慎理性”说明理性不是为欲求服务的工具,而是凌驾于欲求之上的更根本的原则。理性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更是目的性的。对此,休谟主义工具理性论的反应是,欲求分为两个层次:基本欲求与“工具欲求”(instrumental desire)。前者是更根本性的欲求,后者则是实现前者的途径。休谟主义者辩称,内格尔“审慎理性”选择的只是工具欲求,但对于更根本的目的性欲求(比如追求个人的福祉)没有发言权。因此,“审慎理性”不是证明了它具有目的理性的性质,相反恰恰说明了理性是为了满足主体更深层次欲求的一个工具。
史密斯为休谟主义动机理论辩护时提出,实践理性无法为主体的行动提供终结性的解释。如果理性仅仅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为主体的根本欲求服务的手段,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最终要为了理性而去理性。这是一个理性动机的渊源问题。对史密斯来说,理性无法充当理性自我践行的动机,给予主体践行理性要求的只能来自于理性之外的要素——欲求。但不同于其他休谟主义者,史密斯赋予了欲求特殊的内涵。他批判了把欲求视为主观感觉的常识性观点,认为欲求的本质在于其功能性作用,即拥有某些信念的主体按照一定方式进行行动的倾向性。实践理性对主体提出了行动的要求,而主体对该要求的响应却来源于其先验的、遵从实践理性约束的意动倾向或欲求。意动倾向性先于、从而独立于主体对自身应当去遵从实践理性约束的认知,从而为主体响应实践理性的要求提供了原始的动机。所以,实践理性给主体带来了行动理由的信念,但将这一信念转化成现实行动桥梁的,却是主体先前拥有的、功能性的欲求。
功能主义的观点同样贯穿于凡勒曼(David Velleman 1992)的行动理由理论之中。他将行动的动机区分为初级层次与高级层次两种类别。“初级层次动机”(first-order motive)使主体形成具体行动的理由,而“高级层次动机”(higher-order motive)则代表着主体为理由而行动的功能性倾向。作为一个非休谟主义者,凡勒曼拒绝将高级层次动机等同于休谟意义上的欲求,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理性主体所必然具有的意动性功能状态,该状态恰恰“构成”(constitutes)了主体的实践理性。所以,主体依赖低级层次动机生成行动的理由,如果他能够将认知性的理由用行动加以践行,他就是实践性理性的;否则就是实践性非理性的。③
笔者以为,形成行动理由的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取决于主体的认知性理性,认知性理性保证主体发现或生成合宜的行动理由。而实践性理性则保证主体为了理由而行动。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一起才能构成一个理性的主体。因此,对于广受争议的“非道德人”(amoralist),即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但没有践行自身道德判断的任何动机的人,笔者认为他是非理性的,其主体理性因为实践性理性的缺失而无法构建。
二、行动理由的规范性
行动理由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规范性”(normativity)。理由对行动的主体具有规范性的约束。换句话表述,如果主体有理由做行动A,那么他就应当做行动A。所以,理由本身隐含了应然性的要求。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理由能够成为行动的应然性权威,或者说,为什么行动主体应当去响应理由的要求。这个问题涉及到行动理由的本质及其本体论基础。
什么是行动的理由?一种回答是,行动的理由就是“规范性事实”(normative facts or truths)。这是行动理由的实在主义。“规范性事实”本身具有的应然性对行动主体具有自然的约束作用,因此构成了主体行动的理由。“撒谎是恶的”,这样一个“规范性事实”是我们不应当去撒谎的理由。这种定义方法很好地契合了实践理由与“信念理由”(reason for belief)④之间的概念二元化,充分彰显了两者均属于“理由”的同一性。“这是一棵树”的事实成为我们产生对应信念(即相信这是一棵树)的理由,所以信念理由在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外在的“事实”。两者之间唯一不同的是,行动理由对应着“规范性事实”,而信念理由对应着“自然事实”。“规范性事实”中的“规范性”构成了行动理由的规范性。行动理由实在论属于外在理由论者,它主张存在着一个外在的、客观的“应然”(ought),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行动发挥着引导与考量的作用。其优点之一是避免了威廉姆斯内在理由论的主观主义色彩,彻底排除了行动主体有悖于“规范性事实”的“内在理由”的可能合理性。因此,行动理由实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行动价值的外在参照标准,它对应着史密斯所称的“规范理由”,区别于主体所具有的“动机理由”。“规范事实”的存在为行动理由的“真值性”(truth value)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辩护。如果行动的理由与外在客观的“规范事实”相符合,我们就可以宣称该理由为“真”;反之则是“伪”的。这就是斯坎伦(Thomas Scanlon)所坚持的“理由认知主义”(reason cognitivism)。
然而,在笔者看来,行动理由的实在论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一是本体论的困境,二是行动动机方面的难题。在本体论方面,“规范性事实”作为“实体性”(substantive)的价值本体,显然有悖于我们持有的科学的世界观。所以,实体实在论者往往将“应然事实”视为“非自然”的一种属性。在柏拉图那里,它是超自然的“形式”(Forms),一种超越于现实世界,甚至属于彼岸的客观实在。摩尔(G.E.Moore 1903)则将其定义为此岸的、但特殊的一类“非自然属性”(non-natural properties),从而躲避开他所称谓的“自然主义错误”(naturalistic fallacy)。柏拉图与摩尔的“实体实在主义”(substantive realism——Korsgaard语)在麦凯(John Mackie 1977)那里遭到了彻底的颠覆。在其著名的“古怪性论断”(Argument from Queerness)中,他提出,如果存在着价值实体这样的“规范性属性”,那么它们是非常“古怪”的,因此,有理由认为“规范性事实”是不存在的。虽然我们无法接受麦凯最终走向的道德虚无主义,但他对实体实在论本体基础的质疑却是深刻而有说服力的。
实在论的一种可能的回应是诉诸于“随附”(supervenience)与“凸显”(emergence)概念来解决自身本体论的困难。按照这种理论,规范性属性是“随附”于自然属性、“凸显”出来的一种客观事实,但本身又不能化约为自然属性。然而,这种理论必须解释规范性事实“随附”与“凸显”于自然事实的内在机制。虽然在心灵哲学领域对这种机制的描述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但这种理论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用于行动哲学却令人担忧。行动本身并非实体性的自然客体,价值如何“随附”于行动、如何从行动中“凸显”出来是一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至少当前没有一个道德哲学家从这个视角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⑤在行动动机方面,如果外在的“规范性事实”存在着,它充其量可以成为信念的理由,但似乎无法成为给予主体现实动机的行动理由。也正是这种担心导致了休谟主义动机理论的兴起,即我们上一节所探讨的问题。
实体实在主义的理论缺陷导致了考斯佳德(Christine Korsgaard)康德主义实践理由论的提出。不满于行动理由规范性与动机性的二元对立,考斯佳德致力于建构一个“规范动机理由”(normatively motivating reasons)理论,将理由的规范性与动机性有机整合到同一个概念框架之中。在她看来,行动的理由并不是外在的规范性客体,而是行动主体对行动本身“好”(goodness)的属性的一种“反应”(response)。这里的“好”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指行动适配于主体的“合格性”(eligibility),因而具有更普遍的价值意义。但行动的价值本身不能给予主体行动的现实动机与规范性要求,除非行动主体意识到自身所选择的行动是“好”的。考斯佳德批判了道德功利主义“善”的概念,认为最大化效用原则无法成为主体采取道德行动的理由。行动的理由是主体对行动价值的主动性反应,因此首先是“第一人称”的理由,是行动主体内在的理由。行动理由是主体对所选择的行动价值的认可以及作出的“合宜”(appropriate)反应。由此,考斯佳德将主体的主观性与能动性要素注入到行动理由之中,试图摆脱实体外在主义所面临的本体论尴尬。⑥
是什么决定着行动的“好”或者价值?功利主义者认为,它取决于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好”的结果。行动本身是否有价值依赖于行动的结果是否有价值,因此,行动在本质上是一个生产过程,其功能仅仅在于生产出某种价值,或是达到某种目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行动的价值必然化约为行动结果的价值,功能性是行动的本质。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行动与行动产生的结果是不能等同的,行动的价值并非是由行动所产生结果的价值赋予的,而在于行动本身的内在价值性。“德性”(virtuous)的主体必然去选择自身具有价值的行动,因此德性行动付诸于实施不是因为它所能够产生某种结果而得以实施,而是因为自身的缘故得到践行。这使亚里士多德看起来似乎是一位无目的论者,即主张“为了行动而行动”。但事实上,“为了行动而行动”背后更确切的表述是,为了行动自身的价值而行动。然而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正如休谟主义者所质疑的那样,如果脱离了对行动结果的考量,行动自身的价值如何成为可能?答案在于该如何界定“行动”。亚里士多德将行动视为一个包括行动目的与结果在内的完整整体,认为一个有价值的行动在于它内化了这样一个原则:行动在合宜的时间、以合宜的方式、针对合宜的对象、为了合宜的目的得以践行。因此,“行动”是一个统称,是一个包含所有这些要素的有机整体。当我们赞扬一位战斗英雄挽救了整座城市的行动时,他的这一行动价值不仅仅在于该行动的结果是挽救了一座城市,而在于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这座城市、并为此在合宜的时间采取了合宜的方法(比如及时地切断了敌人的供给线)而实现了这一目标的整个过程。设想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拯救城市,但该目的的实现是依靠承诺今后为敌军窃取情报而换得的,他的这一“行动”将没有价值,因为它违背了“合宜时间、合宜方法、合宜对象、合宜目标”的价值原则。
在康德那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行动价值原则被表述为“出于责任”(from duty)。行动是否出于责任是该行动是否具有价值的衡量标准。康德用“格律”(maxim)来解释什么样的行动才是出自责任的行动。出自责任的行动是体现普世化格律的行动,即行动的主体意愿背后的规则成为普世的、一般化的规则。因此,“善意愿”(good will)是决定行动价值的源泉。一方面,主体的意愿必须体现于行动之中,行动的选择是主体意愿被实施的过程,因而行动是一个客体。另一方面,行动同时是行动主体自觉将意愿付诸行动的过程,因此行动又是自身价值的承担者。但行动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实体性“应然事实”,而是来自于行动主体的自觉选择。与此对应,选择有价值行动的规范性要求不是来自于行动主体之外,而是主体自治的结果,即发端于“自治主体性”(autonomous agency)。自治性让行动的主体为自身立法,主体自主地选择了应然性约束,并自觉践行这一约束。
考斯佳德立足于康德范式试图建立一个规范动机行动理由理论。她辩称,在康德的道德哲学架构下,行动的理由对行动主体而言既具有规范性,又具有动机性。这意味着,当主体拥有某一行动的理由时,他将应当并且必然会去践行这一行动。一方面,主体的自主意愿决定了行动的价值。当主体能够将某一行动背后的格律意愿变成为普世化准则的时候,这一行动就是有价值的行动。所以,行动背后的格律说到底是主体意愿的主观原则。另一方面,意愿的理性则保证了主体能够自觉践行有价值的行动。行动理由是关于主体对行动的价值进行认知与反应的刻画,但这种认知与反应并非是先于行动、或是引起行动主体践行某一欲望的前提条件。相反,它本身就包含在行动之中。主体选择行动的过程是他意识到这一行动是否具有内在价值的过程。当主体意识到自己的“善意愿”赋予了某一行动内在价值,因而自觉获取了践行该行动的动机时,第三者会说他具有这一行动的理由。所以,行动理由是对主体意识到并反应于自身动机“合宜”基础的语言描述。行动理由的规范性与动机性是行动者主体性与自治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行动过程就是行动者的动机化与理由化过程。
三、对当代行动理由理论的批判
行动理由的兴起实质上是对道德基础进行探究的当代话语体系,其核心的问题是要回答我们为什么有理由去践行道德的行动,即道德理由的规范性问题。从西方当代哲学家们的回答来看,大致可分成两大类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诉诸于外在“规范性事实”的实体实在主义,坚持“规范性事实”是给予道德行动应然要求的最终源泉。从柏拉图到当代的摩尔,再到当今的部分理由理性主义者,均是这一方法的捍卫者。在本体论上,他们强调“规范性事实”的非自然属性及其不可化约性,认为这种“事实”为主体的道德行动提供了排他性的“规范理由”。在认识论方面,他们则是直觉主义者,声称直觉是架起“规范性事实”与行动主体认知之间的桥梁。
第二种方法则是道德心理学的方法,认为道德理由的规范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道德行动的心理学问题。在他们看来,道德理由的规范性体现在道德主体践行道德行为的动机之中,本质上是对行动主体道德动机的一种语言曲述。因此,道德行动理由的规范性必须化约为道德行动的动机性。在这种方法下既包括行动理由的休谟主义者,又涵盖部分的实践理由理性主义者。威廉姆斯、史密斯等休谟主义者将行动的动机归源于主体的心理状态,强调行动理由的规范性出自于满足主体的目的性欲求。康德理性主义者则将道德理由的规范性诉诸于人们的自治性与主体性。自治的意愿赋予了行动的价值,对行动价值的自我意识则给予主体行动的现实动机。行动的理由无非是对主体意识到动机价值基础的概括与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内格尔认为,伦理学应当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考斯佳德的康德建构主义也分属于这一方法论阵营。
可以看出,实体实在论是一种外在主义的方法,而道德心理学则是一种内在主义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实体实在主义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道德本体学说,才使得道德心理学方法在当今的元伦理学界得以繁荣。然而,笔者认为,时至今日,道德心理学的方法同样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道德理由规范性问题的满意答案。休谟主义动机理论在解释人们非道德的行为方面具有良好的说服力,但在其自身的理论框架内却无法圆满地回答为什么我们会具有道德的欲求;更重要地,我们为什么应当具有道德的欲求。考斯佳德的康德建构主义与休谟主义的欲求动机理论彻底隔绝,试图把道德理由的规范性与动机性建立于康德的主体自治性概念之上,具有进步性,但它的最大缺陷是无法脱离一个实体价值理论基础而成为一个独立、自成体系的道德理由规范性理论。如果“善意愿”是康德主义道德哲学的最高价值范畴,那么这个实体性价值——“善”——将会是外在于主体的一个客观性标准。这个外在标准作为考量主体行动是否具有价值的原始尺度,对主体是否应当选择某种行动发挥着外在的约束作用,与康德主义的主体自治原则相矛盾。如果把“理性的意愿”(rational will)作为道德规范的终结来源,即康德所宣称的“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理性虽然能够保证行动主体去选择那些内置了普世化格律的“好”的行动,但理性将成为超越于主体之上的一种外在规则,同样违背了康德意义的主体自治原则,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实世界会存在如此众多的“薄弱意志”(weak-willed)或“不理性”之人。
所以,笔者赞同考斯佳德的说法,道德理由的规范性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但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背后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更加复杂的价值本体问题。在实践理由的语言体系下探讨道德问题确实使道德哲学取得了不可小觑的进展,但只要价值本体问题得不到解决,史密斯所称的“道德问题”(The Moral Problem)就会一直存在。事实上,行动理由的当代争论从根本上说是发端于古希腊的价值本体争论的一个当代版,一个完满的价值本体理论是道德哲学体系的根本支撑。科学时代的到来否定了超自然的实体与“非自然”的属性作为道德价值本体基础的可能性,造成了当代道德哲学“无根”的“危机”(John Rist 2002)。行动理由视角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道德哲学奠定本体之根基,至目前为止的探索还没有为我们提供答案。但是,如果行动理由哲学能够为道德哲学作出实质性贡献的话,该问题就应当成为它努力的一个方向。
注释:
①对于认知与意动的二元对立性,安斯库姆(Anscombe)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辩护,参阅E.M.Anscombe,Inten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
②这里笔者使用了“传导”这个词汇来概括因果与非因果联系两种类型。有的哲学家强调理由与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理由“导致”(cause)了行动;而其他哲学家持非因果联系的观点。
③Houston Smit,Internalism and The Origin of Rational Motivation.The Journal of Ethics,2003(7),pp.183-231.
④“信念理由”也称作“认知理由”(cognitive reason),正如“行动理由”也被称为“实践理由”一样。
⑤笔者将另文撰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特别地,从该视角出发提出自己的价值本体理论。
⑥以下的论述部分地参考了考斯佳德的文献:Christine M Korsgaard,"Acting for a Reason",Chapter 7,The Constitution of Agency:Essays on Practical Reason and Moral Psych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