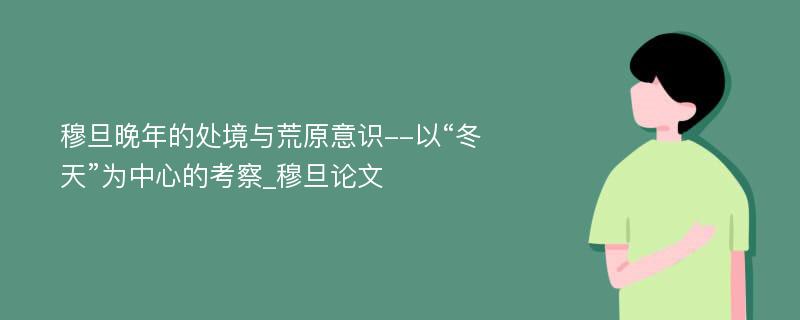
穆旦晚年处境与荒原意识——以《冬》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荒原论文,晚年论文,处境论文,意识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略特的名作《荒原》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荒原》中表达的对于现代世界中精神荒漠化的显示、讽刺和批判,构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诗歌形式理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派的基本信条,冯至、叶公超、孙大雨、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杭约赫、袁可嘉等人,都受过直接的启发。穆旦早年诗歌也明显受到过艾略特的影响,这一点不少人都已谈及,如其同学王佐良、周珏良、赵瑞蕻等,周珏良曾说穆旦“有许多作品就明显的有艾略特的影响。40年代末期,他曾把自己的诗若干首译成英文,当时一位美国诗人看到了,说其中有几首风格像艾略特,这很可说明他给我国新诗引进了新风格。”① 穆旦早年诗歌观念和诗学思维都受到包括艾略特在内(更有奥登、叶芝等)的现代派的影响,如强调诗歌写作的智性特征、玄学化审美趣味、戏剧化情境的创造、寻找客观对应物等,在精神内涵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写现代文明和现代处境中的人性异化,精神荒芜,自我的分裂与破碎等等,在诗歌语言风格上趋于深奥艰涩……不过即使在那时,穆旦也并没有完全接受艾略特的价值观念,艾略特清教徒式的对待欲望的态度,很显然违背穆旦对人的理解,他的《我歌颂肉体》,恐怕就是艾略特决不能容忍的,他把肉体当成大树的根,尽情地歌颂,“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因为它“原是自由的和那远山的花一样,丰富如同蕴藏/的煤一样,把平凡的轮廓露在外面,”(《我歌颂肉体》1947),尽管穆旦也多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有所选择的,而且并不那么虔敬②——他绝没有作为天主教徒的艾略特的那种深厚而执著的宗教体验与宗教感情。在诗歌风格上,穆旦也带有了艾略特的晦涩,却拒绝像艾略特那样刻意大量地使用西方文化的神话、典故——更少使用中国传统典故,因此其晦涩的程度也不相同。我们想要说的是,穆旦的晚年诗作中,有着和艾略特《荒原》更为一致的人生感受,那就是人生处境的荒原感,尽管他的表达方式大为不同,当然,如果细加分析,这种荒原感的真正精神内涵也是有相当大的文化和历史差异的。这种荒原感几乎表现在晚年的大部分诗作中,其中最集中突出的是其绝作——《冬》。我们以此为中心,作出论述。
穆旦的朋友和研究者,在论述他的绝作《冬》时,大都采用了杜运燮所编《穆旦诗选》中的文本,这也是穆旦生前修改过的文本,但这一文本与1980年2月《诗刊》据穆旦手稿刊发的文本,第一章有相当大的差别,尽管有人注意到这种差别,但对两个文本表达的感情与思想的实质性背离却缺乏足够的关注,而这其实是理解穆旦晚年生存状态的文本裂缝③。
当穆旦的人生到了严酷的冬天,他已经走到了幻想的尽头,他的理想已经“流到了现实底冰窟中”(《理想》1976),只能孤寂地站在20世纪中国的荒原上,发出他最后的哀吟——也是20世纪中国的荒原绝唱——《冬》。《冬》充盈着穆旦最后的人生体验,也充盈着他一生诗歌创作、翻译与人生经历的醇厚而又复杂的经验,以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风格,展示了他严冬中的文学生存:
1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这是全诗四章中的第一章,写诗人在平常的冬日,意识到人生残酷的本真实相时,所有微末而平淡的意愿与希望。每节最后一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像是表达出诗人对人生是严酷的冬天的意识,既是产生各种意愿的原因,同时,“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又似在陈述连这微末的愿望也难以实现的现实状况及原因,所以第一章中每一节末尾的这一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的复沓,实在构成这一章的节奏重心和核心象征。这是穆旦对于自己生存状态的清醒意识和自觉反省而酝酿出来的象征,也是他人生的智慧之树所生长成熟的最为沉重的果实,尽管是他要“诅咒”的果实,因为这是以人生苦难为营养,以爱情、友谊、理想的毁灭为代价而成长起来的果实④。但并不是经历了苦难的人都会结出这样的果实,因此,也不见得其他人愿意承受这一智慧树上的果实真正的分量,于是,《冬》中第一章每一节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分别改成了“多么快,人生已到了严酷的冬天”、“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种改动完全改变了第一章的情绪基调和核心象征,然而,对这一文本变异过程与结果的分析,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穆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生存的极好样本。
李方编辑的《穆旦诗全集》中,《冬》有一题注:
本诗第一章,原稿及《诗刊》1980年2月刊出时,每节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其实,诗人曾将此诗抄寄给友人时,经杜运燮提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故改为不同的四行。穆旦家属和杜运燮所编《穆旦诗选》(1986)收入的即为诗人的改定稿。这里选用的是《穆旦诗选》版本。《诗刊》发表的系诗人家属当时提供的最初手稿。⑤
这一题注蕴涵着相当丰富的生存内容,值得关注。杜运燮与穆旦当时已是三十多年的老友,他也是相当有才华的诗人,尽管他同别人一样经历了历史的风雨,但他显然没有像穆旦那样承受超出常人的苦难——抗战时期参加远征军,经历长达八日的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个月,体验过临死的状态,终于幸存归来,却时常面临失业,陷入生活的困顿;当他1953年初,怀着回到生养他的故国可以尽情以诗歌抒写其人生感受的梦想,从他感受到歧视的美国学成归国时,时代却剥夺了他写诗的权利;教学业务的出色,成为受打压的原因,不久又因几乎使他丧生的1942年参加远征军抗日,而成为“肃反对象”;1957年因受鼓励鸣放,发表了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而遭受批判;1958年更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剥夺教学的权利,甚至被判接受监督劳动三年的处罚;然后文化大革命到来,被不断地抄家,不断地批判、检查、劳改;1976年摔伤骨折,但因心理负担甚至耽误治疗,痛苦一直持续到去世……,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中,写了《冬》。还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冬》是在1976年12月完成,当时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大变动,而且穆旦也为当时的政治变动而兴奋,可是我们在诗中读不出因政治变动而带来的浮浅的兴奋,有的是人生体验的深沉。作为生性较为乐观的朋友,才经历困苦就能写出“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啊,/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秋》1979)的诗人杜运燮,显然对智慧的理解,对人生苦难的理解,尤其是对造就苦难的严酷的环境的领会和感受,都与穆旦相去甚远,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强加给人们的价值观,都彻底地否定和压制对苦难的吟味,对人生的悲观,几乎把悲观作为道德污点,人生耻辱,杜运燮显然真诚地接受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所以可能是毫不犹豫地建议穆旦改变《冬》的原稿中那低沉而近于绝望的情绪基调和反复回荡的悲哀旋律。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改写的四行诗,表达的几乎是与原作完全相反的意义与感情。第一节的最后一行,由原来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替换为“多么快,人生已经到了严酷的冬天”,原稿把“严酷的冬天”作为整个人生的象征,这是从绝望的心底涌现出来的笼罩世界的象征,而修改稿,把人生晚年当成了严酷的冬天,年龄特征生理特征成了冬天让人感到严酷的原因,很显然完全扭曲了穆旦本真的生存状态以及穆旦自己对生存状态的领悟⑥。多么致命的文本阉割,其中体现的是权力对文本也是对穆旦文学生存的强制性宫刑,尽管作为朋友的杜运燮是好心地以建议的方式执行这种宫刑的,而且也可以看到穆旦多少有些屈服且屈辱地接受了这种处罚,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第二节末行,把“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易动为“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这样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凭吊曾经有过而显然现在已不再有的火热生命的“我”,就改变了性质。这个“我”本来“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并不是要表现“小河”在严冬中的生命活力,而是表现小河的话语遭受冰封,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正如诗的第二章明确表达的“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而改本中的“我”变成了在严酷冬天中显示出强劲生命力的“我”,这个“我”不再是真诚的诗人穆旦,文本在这里裂变,实际上已经裂变为本真之我和“制造”出来的“自己”(即假面之我)共同创作的文本⑦。
第三节末句修改为“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初看起来,此句似乎和本节前面的四句是和谐一致的,因为“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确乎是“人生的乐趣”,但为什么原作会在这样一种人生乐趣之后,加上一句“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呢?如果把前面四句理解为表达了“我”经常实现这样一种人生乐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最后一句就是原初文本的重大破绽,因为不仅我们的“往年”是“快乐无忧”的,而且“我”现在也享受着人生乐事。笔者现在没有条件去校勘穆旦手稿,如果手稿未曾有其他改动的话,那么穆旦实际上是借助语词本身的含混多义来表达他的思绪的,关键就在“我爱”这个主谓结构中的“爱”字,“我爱”既有表示“经常性地去作”某事的意味,又可表达纯粹的“意愿”,而这意愿并不见得能够实现。在《冬》的第一章中,第一、四两节的“我爱”可能既表达了意愿又更多地表达自己经常性的生活状态,因为这样一种状态几乎是不假外求的。而第二、三两节的“我爱”可能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想象,因为诗人正是在真实的自然季候——1976年的寒冬完成这首诗的,此时右腿股骨骨折未愈,行走仍然艰难,“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当出于想象与意愿,而“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奢望,因为他受打击压制的社会处境,在世态炎凉中,他当时要能“和两三昔日好友”,围炉夜谈,并不是一件易事,更不可能是经常性的乐事,这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与人的书信中即可确定,如写此诗前3个月还在致郭保卫的信中抱怨:“[大地震受重灾之后]开头为了探问安全,还有些朋友来看看,现在是门庭冷清,枯坐家中,抱着一本又一本小说度日,更觉得头脑空洞,乏味得很了。”⑧ 事实上,能够称得上“昔日好友”的,即使当时还有联系,恐怕也大都在异地他乡,围炉夜话只能是严酷冬天中的温暖想象,近乎《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的火柴光焰中幻现的情境。
第四节第五行变易为“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种变易与第一节一样,充分显示了原诗与改作之间的差距。如果把修改后的文本,只理解为承接上一句“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表达诗人对于亲人的爱,即使在严酷的冬天中也不泯灭,从诗意的延续来说是通畅的,也与诗人的深爱不因处境的残酷而消泯这一生存实况并不矛盾,但是原稿表达的是对整个人生的感受,是把整个人生当成严冬的,而改作只不过是把人生老年比喻为一年的冬天,所以实际上完全背离了原作,而这种背离,一方面确实扭曲了穆旦原作显示的生存状况,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可看到,其实这一背离更真实更深刻地显示了穆旦接受杜运燮提议而修改时的生存状态。
穆旦这样一位有着深刻独到的体验与思想,有着独立的人格与艺术品格的诗人,为什么竟然会违背自己的本意,表达出与其原诗本真的情绪体验不相同的人生感受呢?老友杜运燮从交往和友情的角度来看,是对得起穆旦的:不仅在穆旦遭受社会排斥、压抑,生活最为低沉、阴暗的那段历史时期,杜运燮是与穆旦仍然保持交往的极少数老朋友之一,这当给予了穆旦极大的精神安慰,而且在穆旦身后,杜运燮也为其奔走,编辑出版了个人诗集《穆旦诗选》和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争取出版《穆旦全集》,他对穆旦的诗的成就也极力揄扬。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杜运燮是穆旦诗歌尤其是《冬》这首诗的真正知音,其实穆旦生前已经透露,他们对诗的理解有很大的距离,他并不视杜运燮为“诗的知交”:
自古诗人以愁绪为纽带,成了知交。我的朋友运燮原是写诗的,但现在成了100%的乐天派,因此情绪就谈不出来。现在你的来信补了这个空隙。⑨
这是1976年3月8日致其忘年交郭保卫的信中的一小节,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因为穆旦在通信中屡次提到,希望郭保卫看过即毁,不要留存,这意味着穆旦清楚地意识到并惊恐于那个时代的个人言谈可能导致的后果(这就是他的生存状况的真切展现),这也意味着穆旦在说真话。这几句话包含了微妙的多重意义:首先,穆旦认为诗歌的根底是愁苦;其次,诗的知交应具有共同的愁绪即苦难体验以致悲观情绪;再次,杜运燮是朋友,原先是诗人,但在穆旦眼中,现在已不是诗人;再其次,杜运燮是乐观的,所以他不再是我的诗的知交,我与他就诗的交流已经很困难;最后,你已经代替他成了我能在诗歌上交流的诗友。很显然,杜运燮在对《冬》的解读与建议中,再一次印证了穆旦对他的感受,而且正好是在对待诗应该写愁苦还是应该写乐观的这个问题上⑩。恐怕令一般人疑惑不解的是,穆旦既然很清楚这一点,而且实际上对杜运燮的诗歌观念与人生观念不以为然,为什么却又按杜运燮的建议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变诗的核心象征和基本情绪的修改?这其实正是探究穆旦在那个时代那个特定时刻文学生存的机会难得的裂缝,沿着这一裂缝,我们可以发现更为丰富复杂的生存内容。
穆旦是相当看重友情的,像他那样的处境,友谊弥足珍贵,杜运燮、萧珊等人是他被判劳动改造后,还不时有书信联系的少数几个老朋友,虽然穆旦必然有自己的确信,但当这样的朋友建议他改变诗作的悲观情绪基调时,即使仅仅出于情面的考虑,他也是很难拒绝的,何况接受这样的建议并不只是情面的问题,杜运燮的意见表达的其实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读者的意见。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批准的价值观是不容许悲观情绪的存在的——更不容许悲观情绪的表达,对人生的悲观,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审视下,就意味着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也就意味着对社会制度的不满,这不止是一个个人价值观和私人体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穆旦当时以一个“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本来就相当清楚地意识到这首诗有可能给他带来的危险,他在给郭保卫的信中讲到:“同信附一诗是我写的,请看后扔掉,勿传给别人看。”(11) 这时,当朋友杜运燮明确提出“太悲观”的意见时,杜运燮本人是否意识到穆旦的处境我们且不管,但可以肯定穆旦会感到惶恐不安,经历了那样一个不容腹诽、充满诛心之论的时代,经历不断的残酷打击,穆旦实际上早已成为惊弓之雀,这只要读一读穆旦与郭保卫最后一年多时间的通信就会有深刻的感受,他不断要求受信人扔掉自己的信,不要留存,并叮嘱他写东西要小心,而且“任何时候都要小心(12)。然而,对于穆旦这样一位真诚的诗人而言,要改变其最为深入骨髓的人生感受,要让冰封住他的口舌,发不出最本真的声音,他是不可能那么心甘情愿的。《冬》的写作本身就表明,即使“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已经“封住了你的门口”,“使心灵枯瘦”,他仍然想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出心灵的呼号,表达出对严酷的人世间最令人悲哀而愤怒的抗议,所以,他自己是不可能不意识到原稿与改本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他并没有在他的手稿上作出改动,而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就原诗作出改动,甚至可以更为大胆地设想,他只是在给提出修改建议的杜运燮本人以及其他的个别朋友,提供了自己修改的意见,因为当时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要发表的意识,前提是他清晰地知道没有发表的可能。这种设想并不是纯粹的假想,毫无根据,因为穆旦完成此诗三年以后,家属提供给《诗刊》发表的《冬》,就是《冬》的原稿而不是改作。这首先意味着,穆旦可能没有在原稿上作出修改;其次,与他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夫人周与良比朋友杜运燮更能深刻准确地理解原作所包含的人生苦难,更能理解原作的意义和价值,周与良尊重穆旦的意愿而提供了《冬》的原稿。因此,我们应该把《诗刊》上刊发的《冬》作为穆旦本人的最后定稿。杜运燮编辑《穆旦诗选》采用的可能仅仅是穆旦寄给他个人的修改稿,从文学生存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不能看作穆旦本人的定稿(13)。
《冬》的第一章写我的意愿与对于人生冬天的强烈意识。《冬》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才真正写严酷的冬天对于生命的严酷。
2 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了手脚,/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了口舌,/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大地一笔勾销它笑闹的蓬勃。//
谨慎,谨慎,使生命受到挫折,/花呢?绿色呢?血液闭塞住欲望,/经过多日的阴霾和犹疑不决,/才从枯树枝漏下淡淡的阳光。//
奇怪!春天是这样深深隐藏,/哪儿都无消息,都怕峥露头角,/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
3 你大概已停止了分赠爱情,/把书信写了一半就住手,/望望窗外,天气是如此萧杀,/因为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
你把夏季的礼品拿出来,/无论是蜂蜜,是果品,是酒,/然后坐在炉前慢慢品尝,/因为冬天已经使心灵枯瘦。//
你拿一本小说躺在床上,/在另一个幻象世界周游,/它使你感叹,或使你向往,/因为冬天封住了你的门口。//
你疲劳了一天才得休息,/听着树木和草石都在嘶吼,/你虽然睡下,却不能成梦,/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
穆旦晚年诗歌书写的目标是什么?他是要写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写出他对于一个时代的感受:“只不过你要写人与人的关系,而我想替换为自己‘对这一时代的特殊感受。’”(14) 这两章诗从情感状态和诗人对于人生冬天的感受和描述来看,与第一章的修改本是绝不相容的,而是第一章原稿人生象征的具体化,也是对于获得这样一种人生象征的根源的追溯:话语被封杀,欲望被闭塞,生命受挫折,爱情遭扼杀,心灵变得枯瘦,连好梦也做不成,没有任何希望,甚至不能再有幻想。第二、三章延续着、扩展着悲哀的主旋律,这一主旋律确实是从其心底涌出来的,自然流畅,没有文饰,甚至与他其他诗歌竭力追求以奇特的方式,表达对于生活发现的惊异,也有所不同,他如此清晰、平易地表达了他最真切的人生体验,在文字风格上几乎已经脱离了他一直欣赏并执著的现代派诗艺,因为这些都是他感受酝酿已久的情绪和认识,事实上也在他最后一年所写的其他不少诗如《智慧之歌》、《理想》、《友谊》、《问》、《爱情》中均有充分的表现。如果说,穆旦此前或许也相信“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天真预言的话,他这时只能低吟:“春天是这样深深隐藏,哪儿都无消息……”《智慧之歌》是穆旦1976年的第一首诗,也为他最后一年旺盛的诗创作定下了基调,这一基调就是彻悟后的绝望:“我已走到了幻想的尽头,/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是堆积的枯黄落叶。
穆旦对“时代的特殊感受”是什么?我认为最核心的感受是:感觉到那个时代是个精神的荒原,而且是寒冷严酷中的荒原。这是没有了色彩(爱情、友谊)的荒原:“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智慧之歌》1976);这也是理想被毁灭的荒原:“呵,理想,多美好的感情,/但等它流到现实的冰窟中,/你看到的是北方的荒原,/使你的丰满的心倾家荡产。//”(《理想》1976);这也是生命的奔波、劳作、冒险,都失去意义的荒原:“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冥想》1976)。严冬中的荒原可以看作是穆旦生命的最后一年对于时代的最深切的感受,而诗歌中不时出现荒原的象征,可能有来自艾略特的《荒原》(1922)的影响。事实上,在翻译过雪莱、普希金、丘特切夫、拜伦诗歌后,他竟然翻译起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诗,这就令人惊异(15)。前面所提到的诗人是当时还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诗人,而穆旦选择艾略特的《荒原》来翻译,意味着他对此诗有着很深的认同感,以致不顾巨大的压力而奋然命笔,为中国读者又增添了一个《荒原》的杰出译本(16)。只不过穆旦视野中的荒原,其具体内涵与艾略特所书写的荒原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与早年诗中受艾略特诗歌的影响颇不相同。
穆旦晚年的诗作几乎已经完全消除了晦涩,《冬》初看起来,与艾略特的诗风相去甚远,整首诗象征清晰明白,语言纯净透明,用词浅显平易,节奏平缓流畅,没有一点艰涩之感,而且这是典型的抒情诗,几乎可以说是直接抒发着诗人的感叹,与艾略特《荒原》的非个性的戏剧化效果很强的叙事诗相比,属于差别甚大的诗体,艾略特的《荒原》,语言结构多变,场景光怪陆离,用典深奥曲折,有意识造成含混艰涩的效果。在主题上,《荒原》批判现代性处境中欲望的泛滥至于淫荡,而《冬》则感叹欲望被禁锢,生命被抑制,但同样都是表现荒原上的情感的缺失,精神的荒芜,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为什么《冬》与《荒原》差别如此之大,却让人感觉它们之间的联系呢?荒原作为一个整体象征,表达了穆旦与艾略特对于世界的感受,这才是最关键的,而这样一种荒原意识,在穆旦的精神世界中,确实有来自艾略特的启示,不仅有他当时翻译《荒原》的佐证,也还可用荒原的这一象征的根本特征作为保证——都表现了精神的荒漠带给诗人的精神创伤。有人认为穆旦早年诗歌中表现了荒原意识,其实穆旦早年的荒原意识可能还不如晚年强烈,还没有那么铭心刻骨,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的深刻性,是穆旦晚年诗作与包括艾略特在内的现代派的相互呼应的根源,而且也是穆旦本人的自觉追求,他试图在诗歌风格上糅合他晚年最欣赏的普希金和艾略特为一体。穆旦的年轻诗友孙志鸣回忆道:
一次,先生给我讲一首俄文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后,说:帕斯捷尔纳克的风格和普希金不一样,倒可算得上是苏联的艾略特。现代派诗歌流派众多,表现手法尽管不同,但有一点,这些诗人都力图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外在的世界和内心世界。如果以作品的深刻性来衡量,传统的诗歌就显得逊色了。中国的自由体诗,人们不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肤浅,至于形式倒是次要的……但也应该看到欧美现代诗人在追求深刻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晦涩。……从目前来看如何从普希金和艾略特的风格中各取所长,糅合成有机的一体,这未必不能成为今后中国新诗的一条探索之路。(17)
他有意识地学习艾略特的东西,恐怕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与艾略特对世界的感受有着很深的共鸣,那就是强烈的荒原意识。但这时,他已经不想用晦涩的风格来表达这种荒原意识,不管是受到他所处时代的诗学观念的影响,还是主要因为年龄的变化使他的审美趣味也变得纯净透明——或二者兼而有之。当然,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不止是表现在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在精神内涵上,《冬》的第四章就颇有俄罗斯诗歌的意味,甚至有着俄罗斯大地和俄罗斯人的气息,当然,与艾青笔下的中国北方也有着同一的精神根脉:
4 在马房隔壁的小土屋里,/风吹着窗纸沙沙响动,/几只泥脚带着雪走进来,/让马吃料,车子歇在风中。//
高高低低围着火坐下,/有的添木柴,有的在烘干,/有的用他粗而短的指头/把烟丝倒在纸里卷成烟。//
一壶水滚沸,白色的水雾/弥漫在烟气缭绕的小屋,/吃着,哼着小曲,还谈着/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
北风在电线上朝他们呼唤,/原野的道路还一望无际,/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扑进寒冷的空气。//
《冬》的这最后一章,具有场景化的特点,背景和人物如此鲜活生动,几乎像是某部俄罗斯电影中的一组镜头(令人想起电影《日瓦戈医生》),而表现的是对于绝望的反抗,同时也是绝望的反抗,并不是乐观——这也正是承担着鲁迅建立的新的精神传统。处在穆旦的历史情境中,能够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即使是在严酷的冬天中,面临的是寒冷的荒原,也必须生存下去,“原野的道路还一望无际”,唯有行走在路上,才显现出人的价值与尊严。穆旦的诗,从早年起,从来都敢直面真实,但他也从来就没有廉价的乐观,他并不为达到某种虚幻的目标而幻想,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理想是个迷宫,按照它的逻辑/你越走越达不到目的地。//”如果毫无疑问地跟着她走,就会“像追鬼火不知扑到哪一头。”(《理想》1976)所以,《冬》第四章中的泥脚们尽管走出了屋,却是没有目标的,这种没有目标的坚韧行走,是穆旦生存的精神实质,理想作为现实追求的目标是虚幻的,对它的追求与否,却直接构成了生存的现实,穆旦对此有深刻而辨证的理解:“没有理想的人像是草木,/在春天生发,到秋日枯黄,/对于生活它做不出总结,/面对绝望它提不出希望。//没有理想的人像是流水,/为什么听不见它的歌唱?/原来它已被现实的泥沙/逐渐淤塞,变成污浊的池塘。//”(《理想》)《冬》充分而准确地表达了穆旦自己的生存哲学,那是经过苦难磨炼以后的生存哲学,带有了特别深厚的体验,但他又是采用了那个时代容许甚至赞赏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个时代,只有泥脚才能被看作是最坚韧的,知识分子几乎只能以软弱的形象出现——而事实上,表达的却是后者的心声。即使现在,荒原依然如故,只是穆旦已不再哀吟。
甲申冬于乐是幽居
注释:
①周珏良《英国现代诗选序》,第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如《我歌颂肉体》中的末节:“我歌颂肉体:因为光明要从黑暗站出来/你沉默而丰富的刹那,美的真实,/我的上帝。//”这里上帝显然具有戏谑的意味,而这样使用“上帝”一词,也表明了他对上帝的态度。
③按修改文本解读该诗的如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论穆旦的诗》,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程勇真《永不衰败的旗手:试析穆旦的诗〈冬〉》、刘志荣《生命智慧的最后之歌》等,唯宋炳辉等少数人意识到了两种文本间的差别,宋之《新中国的穆旦》且采用了原文本。
④见《智慧之歌》(1976),其最后一节:“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诅咒它每一片页的滋长。”
⑤《穆旦诗全集》,第362页,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本来,以作为一个季节的冬天来比喻人生,往往含有以四季来喻人生各个时期的意味,这已经成了一种诗人的习惯性比喻,如果是这样,那么穆旦的比喻就有陈腐之嫌,但以季节与人生各阶段相比,又很自然吻合,因此冬天的比喻往往也难以跳出陈规,所以《冬》的第二、三章确有与春夏相对照的意思,不过仔细体味第一章,可以发现,穆旦确实以冬来象征整个人生的,这是他的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地方,但冬的两种比喻象征义在《冬》中是交错的。我们还可以看到,穆旦在1976年的诗歌书写中,写了《春》、《夏》、《秋》、《冬》,但每一首诗都落到了写冬的寒冷、严酷。
⑦《诗八首》中第六首有:“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我制造自己在上面旅行。”制造出来的自己就是不同于本真之我的假面之我。不过,对于诗人的文学生存而言,本真之我和假面之我的生存都是其真实的生存内容。
⑧《蛇的诱惑》,第246页,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⑨《蛇的诱惑》,第236页,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
(10)郭保卫在纪念文章《书信今犹在 诗人何处寻》中也回忆起穆旦“当谈到有些人在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里仍安然乐天,渐渐觉得与他们共同语言少了”。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17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蛇的诱惑》,第259页。此信发表未附该诗,但从时间等各方面因素推断,当指《冬》。此信写于1977年1月3日,正值写完《冬》之后,而《冬》是穆旦的绝笔,此前写的最后两首诗《退稿信》、《黑笔杆颂》都已在1976年11月致郭保卫的信中附寄给他。
(12)《蛇的诱惑》,第248页。
(13)穆旦家属尽管参与了《穆旦诗选》的编辑,恐怕出于情面或其他原因,也会尽量尊重诗人杜运燮的意见。《穆旦诗选》以后编辑的穆旦诗集,均采用修改稿,如《穆旦诗全集》、《蛇的诱惑》,前者就修改过程作了说明,后者完全没有说明。我建议此后的穆旦诗集尤其是《穆旦全集》编者,应该以穆旦原稿为正文,再就变动之处以及修改过程作出注释,这样更为适当。
(14)《蛇的诱惑》,第244页。
(15)在1975年11月14日致郭保卫信中说:“最近我在译艾略特的《荒原》,这是现代英诗的古典作品,……”
(16)艾略特《荒原》至今已有至少6个中译本,穆旦翻译之前,已有赵罗蕤1937年出版的译本。
(17)孙志鸣《诗田里的一位辛勤耕耘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第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