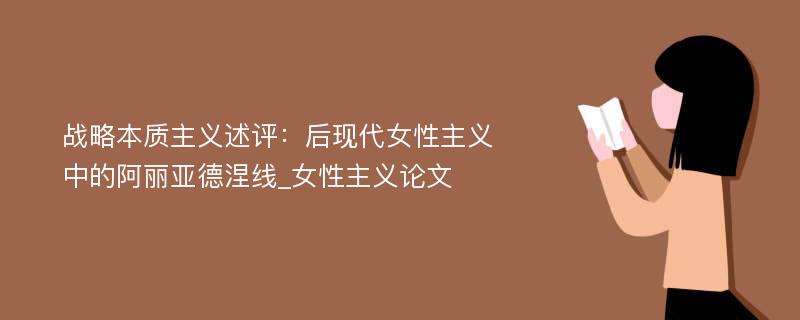
策略本质主义述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阿里论文,后现代论文,阿德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从后现代理论中汲取了多种营养,作为为女性争取权益的新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后现代理论对同一性的消解,对差异的强调,经常被女性主义者用以抵制抹杀女性性别特征的本质主义。然而,后现代理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和对同一性的消解过于极端,有可能威胁到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女性主义的前提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都受到父权制压迫,处于屈从地位;为了实现男女平等,全体女性应该携手同心,建立“姐妹情谊”(sisterhood),为推翻父权制而斗争。根据后现代理论,根本不存在一个同一的女性的本质,超越阶级、肤色、人种的普遍的“姐妹情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理论有使女性主义为之奋斗的目标化为泡影的危险,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性也随之遭人怀疑。于是,有人提出,后现代女性主义是不可能的。
可是,后现代理论和女性主义之间真的不可调和吗?后现代女性主义真的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了吗?斯皮瓦克提出的策略本质主义为走出这种困境提供了希望,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阿里阿德涅之线”①。对此,本文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困境、策略本质主义、斯皮瓦克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运用以及女性主义的前景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困境
后现代女性主义又被称为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综观女性主义的历史,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中,争取选举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是主旋律;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争取平等的工作权利、同工同酬、消除两性差异等是最主要的诉求。这两次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都是为了达到男女平等。基于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女性要求取得跟男性同等的权利,向男性靠拢。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和前两次有较大的区别。受到福柯、拉康和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家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个体差异,认为每个女性都是不同的;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女性本质;男性不是常态,女性不是对常态的偏离,不必要也不可能向男性靠拢。另外,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或者“女性”是本质主义的概念,事实上,性别,无论是生理性别(sex)还是社会性别(gender),都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不存在绝对的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
狭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指的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上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朱利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西苏主张女性写作,伊利格瑞倡导女性话语,克里斯蒂娃强调女性欲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她们颠覆了男女二元对立,从思想上进行了彻底的反性别主义革命。广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指的就是第三波女性主义,即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包括法国女性主义和英美女性主义在内的、受到后现代理论广泛影响的女性主义的总称。本文所说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就是指这种广义的女性主义。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具备统一性,各个流派之间的理论倾向、政治抱负也相差很大,以至于人们常常用“feminisms”这个复数形式来指称后现代女性主义。谈论后现代女性主义时,人们往往会问:“你谈论的是哪一种女性主义?”甚至有人把后现代女性主义称为一种拼盘杂烩(pastiche)。
各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之间常常相互攻诘,彼此诟病,陷入内讧,其社会批判性大打折扣,世界女性主义运动也因之削弱,甚至有分崩离析、把阵地拱手向父权制让出之嫌。女性主义如何才能做到既强调差异又能够有效地进行理论生产和政治斗争呢?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女性主义者找到了斯皮瓦克策略本质主义,作为走出困境、走向对话的药方。对这个困境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女性主义者要清楚地意识到有关女性的各种诉求都是政治上的干涉,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结果的普遍化的说法,而不是对现实的非政治化的描写。
二、策略本质主义
1.什么是策略本质主义
策略本质主义由“策略”和“本质主义”两个关键词构成。对于解构主义来说,本质主义是要解构的对象,然而,解构又依赖本质主义。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斯皮瓦克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她强调“本质主义是个陷阱”[1](P89),但是,当理论在现实情境中表现出局限性时,斯皮瓦克认为需要做出选择。她也提出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采用本质主义的概念有好处:“我认为我们又不得不策略地选择不是普遍主义的而是本质主义的话语。……事实上我得说我不时成为本质主义者。……我认为反对本质主义的话语是对的……但是策略上我们不能够这样做。”[2](P11)换句话说,本质主义是有危害的,又是不可避免的。斯皮瓦克认为,对本质主义的批评就是要承认有些概念我们不能不使用,但是必须警惕其危险性。[3](P15)
策略本质主义者实际上是反本质主义的,但是把“本质主义”当成在具体情境下为了达到斗争目的而采用的策略。“策略”意味着不是长期的、永久的,而是针对具体情境的:“一个策略适合于一个情境;策略不是理论。”[4](P4)不能把为了达到斗争目的而采取的本质主义的策略变成永久的不假思索的真理。斯皮瓦克提醒人们,不要对政治斗争的口号或者形成斗争群体的标签过于迷信。[5](P11)
可以这样理解,在斯皮瓦克看来,本质主义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不好之处在于对本质主义使用不当。策略本质主义中的“策略”可以看成是斗争的动员口号,但是不能被僵化;策略本质主义中的“本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旦僵化就会显示出其局限性。本质主义可以用来作为动员、号召和斗争的口号,如“女性”、“工人”或国家名称等都是口号。在理想的状态下,团体的成员都心知肚明,知道这是一种口号、一种斗争的策略。但是,本质主义的口号不能够被历史化,因为一旦僵化就呈现出了局限性,就会抹杀内部成员之间的差异,从而给斗争带来负面的效应。于是斯皮瓦克提醒人们注意,“当你捡起能够给予你力量来跟对立面斗争的普遍性时,你所抛弃的是理论的纯洁性”[6](P12)。
徐贲曾热情称赞了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指出它对我们理解后殖民批评与其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非常重要,有利于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后殖民”都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状况的一种策略性的描述,并不排斥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性和压迫关系。[7](P185)
2.策略本质主义与女性主义
斯皮瓦克不是第一个提出“策略本质主义”的人,但是把这个策略用于女性主义则是她的首创。在1984年录制的访谈节目“批评、女性主义和体制”(Criticism,Feminism and the Institution,后被收入《后殖民批评家》)中,她表示拥抱策略本质主义。而在她所发表的论文中,最早使用策略本质主义是在《解构历史编纂》(Dis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一文中对印度属下(subaltern)②研究小组探寻属下主体意识的讨论之中。
斯皮瓦克认为,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社会性别本质。她受到德里达和福柯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影响,尊重差异,反对一切的二元论和本质主义。在男性和女性的问题上,她反对二分法,反对所谓的女性本质,反对基于性别的压迫。对于“女性”这个概念,斯皮瓦克是这样定义的:“我对女人的定义十分简单;它取决于在各种文本中使用的‘男人’这个词,这些文本为我身居其中的文学批评机构的这个角落提供基础。也许你们会认为,根据‘男人’一词来界定‘女人’是一种反动的立场,难道身为女人的我,就不该为自己勾画出一个独立的定义吗?……对任何事物下严格的定义最终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想这么做,你尽可以不断地解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对立,最后表明,这是一个自我置换的二元对立。”③
斯皮瓦克认为给女性下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下定义就是创造出一个严格的二元对立,而作为解构主义者,她反对这样做。在她看来,根本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女性本质。尽管她反对把女性本质绝对化、固定化、超历史化,可是从价值立场出发,她认为女性历史的、具体的本质还是存在的,并且可以把它用作斗争的武器。
斯皮瓦克在女性主义的政治性和差异理论之间做出了调和,认为在与男权社会作斗争、争取女性的权益时,我们仍然需要女性的统一,把“女性”作为我们一致对外的斗争口号。而在女性内部要承认女性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尽管女性作为个体千差万别,但是为了争取权利我们还是要统一。策略本质主义有利于女性主义者来应对后现代状况下的矛盾。
三、斯皮瓦克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运用
斯皮瓦克在自己的女性主义研究中采用了策略本质主义的方法,一方面,她把女性主义引向女性内部的文化差异研究,另一方面,她又极力号召女性集体的形成,呼吁女性之间要互相帮助。
1.女性内部的文化差异研究
斯皮瓦克借鉴了德里达的差异理论,并把它用于女性主义研究,用于对以法国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进行批评。对差异和踪迹的兴趣使斯皮瓦克跳出了女性主义关于女性本质的争论,从女性与男性之间差异的探讨走向关于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女性的文化差异的探讨。她聚焦于第三世界属下女性,强调她们与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
斯皮瓦克对第三世界女性差异性的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进行:对印度属下研究小组忽视属下女性差异问题的批评;对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理论以自身经历概括所有女性的总体化倾向的批评;对帝国主义文本再现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他者化的批判。
印度的属下研究小组试图通过重写印度历史来肯定属下阶层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作的贡献。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小组成员们认为属下阶层之所以被排除在正统历史之外(他们的功劳被记在了独立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民族主义者的头上),是因为他们缺乏统一的阶级主体意识。于是,小组成员们费尽心机想要还原出一个属下阶级的主体意识。斯皮瓦克肯定了该小组的做法,指出他们试图还原属下的能动性和主体地位,从而重写属下为独立运动作贡献的历史的做法是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运用。[8](P205)但是,她也批评属下研究历史学家们性别意识不强,对属下女性为独立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她们的悲惨处境视而不见。她认为在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双重遮蔽下,属下女性的声音被剥夺,具有“彻底的不可表现性”(a total unrepresentability)。[9](P209)
利用策略本质主义的思想,斯皮瓦克批判以法国女性主义者为代表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把女性本质化、强调女性主义的普适性原则背后隐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框架之中的法国女性主义》(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一文中,她着重抨击了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一书中对中国户县农民妇女的描写,认为克里斯蒂娃只关心自己的身份,而对中国妇女采取漠视的态度。她还批评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历史厚古薄今,并不关心当今的活生生的中国妇女的利益。她因此指出,西方精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对于第三世界女性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甚至还间接地会起到危害作用。[10](P150)西方女性主义者企图在政治上代表沉默的东方属下女性说话,实际上是把她们当作镜像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西方女性主义者关心的是她们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属下问题。因此,她们实际上与帝国主义话语之间有着共谋关系,结果就使属下女性进一步丧失话语权。
作为一位文学学者,斯皮瓦克认为文学再现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地位也有重要的影响。她既研究宗主国主流文学文本中对属下的再现,又探讨后殖民主义者的文本中与帝国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三个女性主义文本和一种帝国主义批评》(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这篇论文中,她对《简·爱》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中把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罗切斯特夫人描写成为一个野兽,来凸显西方白人简·爱的独立的个人主义女性形象。斯皮瓦克指出,19世纪的许多文学文本借助文学语言为殖民者辩护,把残酷的殖民扩张说成是上帝赋予的使野蛮人文明化的重要使命,从而掩盖其中的血腥和丑恶。她认为《简·爱》这个女性主义文本也不幸成为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工具,本来可歌可泣的女性主义形象被帝国主义叙述大打折扣。[11](P116)
斯皮瓦克对《简·爱》的评论是结合里斯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来谈的。英国裔克里奥④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对女性主义经典著作《简·爱》中对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疯女人——罗切斯特夫人的不公正的描写感到非常愤慨,于是重写了这个可怜的女人的故事。里斯在《藻海无边》中对这个不幸的女人给予了同情和关注,指出导致后者疯狂的是殖民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穷白人,这个女人生活在夹缝之中,既不能进入白人的世界又不能进入黑人的世界;既不属于自己生长的土地,也不属于英国;她既没有家庭的温暖,也没有友谊,结果受害于包办婚姻和财产所有制,成为一个一无所有、任人宰割的“疯子”。
斯皮瓦克指出,虽然里斯竭尽全力要还原出这个女人的生活,试图把这位属下女性当成主角,但是,这个西方女性的“他者”(the other)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成为自我(self)中的一员。这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女人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烧死自己,为作为自己姐妹的简·爱成为一个为世人称道的高大的女性主义形象而让路。因而,《藻海无边》这个试图为属下妇女说话的后殖民文本仍然充斥着帝国主义的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罗切斯特夫人这样的属下女性因具有不可纠正的异质性(unretrievable heterogeneity)而根本无法被公允地再现。通过对《简·爱》和《藻海无边》两个文学文本的分析,斯皮瓦克指出,某些文学作品中对属下女性有失公允的再现妨碍了第一世界女性对属下女性的了解。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斯皮瓦克彰显了第三世界女性的差异性,既把矛头对准了男权主义对女性的视而不见,又批评了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对世界上其他女性的忽视,并通过揭示文学文本对第三世界女性不公正的再现这一事实来控诉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
2.女性集体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斯皮瓦克更加关注女性主义流派之间的合作问题。《国际框架之中的法国女性主义》发表十年之后,她反思了自己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评,认为“宗主国女性主义和解殖女性主义(decolonized feminism)之间可以对话”[12](P144),认为自己先前对法国女性主义的批评只是从单一问题女性主义的主体位置出发,过于偏激。
斯皮瓦克对待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态度的转变,与她自己的策略本质主义的观点分不开。一方面,在女性主义内部,大家应该谈论彼此之间的差异,以此来防止占据主导地位者把自身经验普遍化,从而对其他女性带来损害;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应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来为女性集体争得更多的政治权益。她在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时,号召大家注重差异研究;而当女性主义者过多地谈论差异而威胁到集体的一致对外的政治行动时,她转而提醒大家要注意同心协力,团结作战。
在《一个学科之死》(2003)中,斯皮瓦克重新解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由此提出了女性要成为一个互相帮助的友爱集体的观点。她指出,《一间自己的屋子》一直被解读为女人要成为作家、要想获得解放,就得要得到一间自己的屋子和丰足的年金,即经济上的独立,然而,这是对伍尔夫文本的误读。在文本结尾处,伍尔夫以虚拟式提出了要“为她们努力”的要求:“但是我坚持说假使我们为她努力,她一定会来,所以去努力,哪怕在穷困、落魄中努力呢,总是值得的”[13](P114)。斯皮瓦克认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吁求,伍尔夫要后辈读者关注的是,女性要获得解放,不仅仅限于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所有女性作为一个集体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斯皮瓦克所说的女性集体就是一个策略本质主义的集体,即一个作为政治工具的集体,而在集体之中,要尊重女性之间的差异。
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学者,斯皮瓦克认为在后殖民时代,要建立一个和谐的政治秩序,要让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之间相互沟通,有必要通过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来推动,通过包括翻译交流等方式来逐步实现。她号召女性主义者要“学会向属下学习”,开展田野调查,真正做到了解属下,从而更好地巩固女性主义集体。她重视对属下女性的教育,十几年来,她利用业余时间在孟加拉、印度和中国的边远地区的学校培训教师,为那里的贫困妇女工作。可以说,策略本质主义一直是她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南。
四、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评价
自从斯皮瓦克把策略本质主义作为解决后现代女性主义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提出来之后,在女性主义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反思。这种策略被许多女性主义者接受,基本上成为她们的共识。斯皮瓦克和查拉·提·墨罕提(Chandra T.Mohanty)等许多女性主义者一起,冲破了单一的“女性”概念,走向多元化研究,使女性主义的讨论峰回路转,走向柳暗花明。
策略本质主义使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眼光转向众多社会问题的研究,开始关注女性基于阶级、种族、肤色等形成的不同团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使女性之间走向求同存异,形成一个互相帮助的集体。
然而,对策略本质主义也有不少批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策略本质主义仍然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例如有人质疑斯皮瓦克走向第一世界女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文化差异研究,也就是走向了二元对立,她的观点是建立在“倒转的种族中心主义”之上的。可是,这实际上是对斯皮瓦克的误解,斯皮瓦克对此也作出了回应,说她实际上是对“第三世界女性”这种范畴的策略的使用,并不是说真的存在“第一世界女性”或者“第三世界女性”的本质;使用这类口号只是为了辩论的方便,目的在于回应某些剥削政策。[14](P13)
第二种批评意见针对策略本质主义的适用性。劳拉·阿诺德(Laura Arnold)教授曾高度评价策略本质主义,认为它可以成为被压迫群体的有力的政治武器[15],她的观点遭到了不少批评。保罗·布赖恩斯(Paul Brians)与阿诺德教授的观点相反,指出策略本质主义设想被压迫者可以在内部争论,而在与压迫者公开辩论时则把争论掩盖起来,团结一致对外,这种设想过于理想化,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因此,策略本质主义不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16]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也认为,策略本质主义的问题在于,假设人们能够并且应该辨别出一般所理解的“女性”的各种意义与为了特定的目的政治活动家所提出的意义之间的不同之处,而这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17](P296)尽管事实证明策略本质主义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并且为后现代女性主义走出迷雾作出了贡献,但是这类批评意见有利于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反思应该如何更好地使用策略本质主义。
第三种批评意见来自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及其追随者,这可能是对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的最重要挑战。巴特勒对社会性别的叙述使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显得过分局限于规范化的性别区分,没有考虑到不同性取向者的差异性。这种观点值得借鉴。对策略本质主义,巴特勒经历了一个从赞成到质疑的过程。在她的成名作《重要的身体》(The Body that Matters)和《性别烦恼》(Gender Trouble)中,巴特勒运用了策略本质主义的概念,不遗余力地要取消普遍性,强调特殊性。但是,十年之后,她意识到绝对地取消普遍性不可能做到。她指出,像斯皮瓦克想象的那样仅仅策略性地使用一个概念是不可能的,因为“术语的语义生命会在旅行的过程中超出策略设计者的初衷,而获得一些新的本体论的意义,结果与设计者的初衷大相径庭”[18](P332)。这是在提醒我们需要警惕对术语的僵化使用,实际上是对策略本质主义的进一步深化。
在巴特勒等人对女性主义的新的理解基础之上,艾莉森·斯通(Alison Stone)提出用女性系谱学概念来挑战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19]艾里斯·M·杨(Iris M.Young)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集体”概念来反对斯皮瓦克的策略本质主义。[20](P70-71)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批评斯皮瓦克反对本质主义做得不彻底。然而,笔者认为她们的挑战未必成立。毕竟“在解构实践中,总是要本质化一些东西”[21](P51),没有人能够当一个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者。
策略本质主义基本上是斯皮瓦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观点,后来被一些人滥用来为本质主义辩护。斯皮瓦克曾经愤慨地指出,许多人误解并且滥用了“策略本质主义”这个短语,把它当作仅仅是“一个本质主义的团体票(union ticket)。至于策略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想要知道”[22]。她声称已经放弃这个短语,尽管没有放弃这个概念。她从提倡策略本质主义走向研究他者伦理。
然而,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来说,策略本质主义不会过时。女性主义运动通过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在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女性主义仍然任重道远。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后现代女性主义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和争论也必然持续存在。合理地运用策略本质主义,女性之间可以形成一个求同存异的集体,为共同的目标而斗争。不过,在运用策略本质主义时,除了关注女性之间的基于阶级、种族、肤色等的文化差异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不同性取向者之间的平等,谨防为了提高女性地位而伤害其他弱势群体。策略本质主义将会一直是女性主义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中国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杨莉馨认为本质主义的解构促进了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女性主义的多元化发展[23](P243),而李银河认为与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立场相比,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即中庸之道……是女性主义处理身份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法”[24]。中国的女性主义如果要加强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就不应当完全否定使用本质主义概念,但是,对本质主义的妥协又会伤及已经取得的解构成果,因此,策略本质主义可以是一种好的选择。起码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使我们意识到在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之间,我们可以“策略地”推进女性主义事业。
注释:
①古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特修斯(Theseus)为拯救苍生,入迷宫除掉了半人半牛的怪兽米诺陶(Minotaur)。谁料那迷宫是能工巧匠迪德勒斯奉旨所建,意在困住米诺陶,进去容易出来难。所幸英雄总有美人相助,聪明的公主阿里阿德涅(Ariadne)教特修斯借助一团红线走出了迷宫。后来人们常用“阿里阿德涅之线”喻指脱离困境的妙计。
②Subaltern,又译作“贱民”、“底层”、“非主流”等。
③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he Spivak Reader:Selected Works of Gayatri Charkravorty Spivak.Eds.Donna Landry and Gerald NacLea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6.54.译文参见曹莉:《史碧娃克》,91页,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稍有调整。
④英文是“Creole”,指出生于美洲的欧洲人及其后裔,有时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这里指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