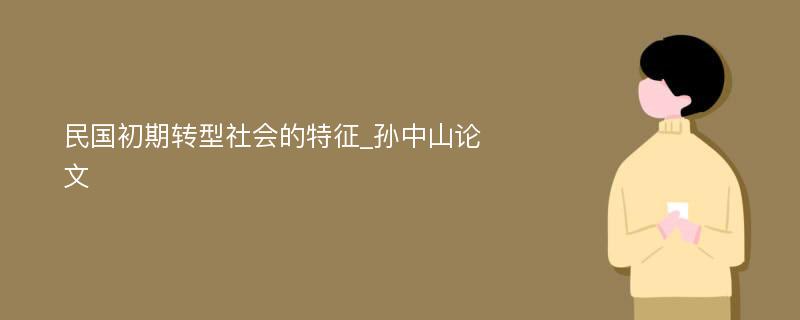
略论民国初年的转型社会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特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初年,虽然共和的旗帜与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西方移植来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并未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在动荡不安和剧烈变化的社会中,中国人民并不都是失去:新经济在发展,新的思想不断传入,全新的力量已走上历史舞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已经飘扬,黑暗的中国已依稀看到光明的曙光。从一个较广阔的历史角度看,民初这一时期是中国两次飞跃之间的一个能量积蓄期,是中国又一次腾飞的前夜。作为这样一个转型社会时期,它的特征如何概括,似为史学界所忽视,其客观原因,可能与我们史学的分工过细有关,就1912—1928年这一时期的研究,我们在北洋军阀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几个研究领域分头进行,还要在经济、思想、政治、政党、社会等等专史中深入探讨,在深入研究的同时,我们或许会因学术分工过细而淡化了对整体和宏观的探讨。笔者参考了广泛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试图对北洋时期的社会特征作一概括,以就教于大家。
一 两种政治体系的结合体和过渡期
清王朝的崩溃,并不意味着传统势力、传统观念及传统价值取向与清王朝一起消失。恰恰相反,这些传统的东西在新的政治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中顽强地生存。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夺得政权而告终,这使旧有政治在新式政权中的烙印更深,新的政权模式重重地打上了旧的痕迹。北洋军阀时期新式政权的结构共和的国体浸透着浓厚的封建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在于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也在于它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政权形式、新的价值判断体系和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资产阶级共和理想未能真正实现,正如革命志士所感叹的:“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革命志士不满旧势力对共和的扭曲,为建立真正共和而一直不懈地奋斗,但他们毕竟未能建成真正的共和国。在革命派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对现实不满的同时,传统势力从相反的角度对现状亦表示极大的不满。民主共和国将西方近代制度文明全盘引入中国,并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精神文化作为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孔子也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而丧失了昔日的风采,引起众多人捶胸顿足的惋惜,昔日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而奔走奋斗过的康有为、严复等对此也大为惊叹。康有为认为共和制度的实行造成礼乐并废,典章皆易,无教可奉,“则举国四万万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康有为政论集》下,第864页)。这种想法代表了封建遗老遗少当时的普遍心态。 严复也极力主张教育复古。在顽固的封建主义者看来,康有为、严复已经是离经叛道者,他们对民国的成见尚且如此,顽固的封建卫道士更是不言而喻。
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及社会动荡,是新旧两种势力斗争呈胶着状况的产物。代表新势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无实力将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十分强大,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和启蒙并不十分广泛的情况下爆发的,中国政治官场一向有随风倒的传统,许多人看到清王朝气数已尽,为了维持自己的权益,纷纷转向革命,使革命阵营一下子膨胀起来。这些人背叛了清王朝,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使革命阵营复杂化,使旧势力、旧思想、旧观念大量带入新式国家政权,使新式国家政权打上旧的烙印。特别是袁世凯对最高权力的控制,更使新式政权与旧政权无法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军阀时代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政治体系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甚至相互依存的时代。从各级政权的形式、社会组织、经济、文化、传播媒介、社会风尚的某些方面来看,有不少是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东西,但从政权控制者的思想、行为及社会广大领域深层次的内涵来看,封建主义的东西还相当顽固地存在着,新与旧在广阔的社会层面并存。
李大钊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对此曾做过精彩的论述:“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合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起,分立对抗的生活。”对新旧并存的现象,李大钊认为,“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李大钊认为,造成新与旧“凑到一处”的原因,“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的过处了”(《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7~99页)。
这种新旧共处的奇观在民国初年随处可见,看似荒唐,实则必然。旧的封建专制在腐朽中崩溃,但旧势力、旧思想观念不会同清王朝一起“退位”。将表面上的旧的东西除去还较容易些,如辛亥革命后剪掉发辫,1924年冯玉祥将清室逐出故宫等,但深层次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却无法在短期内清除,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新旧势力长期较量和僵持,是造成军阀时代混乱与动荡的根本原因。
有人认为,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实行的是假共和,因而并无进步性可言。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假共和与真共和不同,但与真专制也不一样。首先,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虽短,但它以全新的面貌使中国新式政权一展新貌,在中国影响很大。以后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努力使共和国名副其实,他们的努力虽未成功,但也并非无效,他们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限制了军阀的独裁,促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新势力的增强。其次,军阀控制政权的独裁专制比封建君主受到的制约要大得多。除三权分立的分权政权结构外,革命派的存在、军阀分裂争斗、舆论功能增强及人民觉悟提高等都使军阀不可能完全按封建专制时代的方式行事,袁世凯的败亡充分说明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军阀不是利用共和的招牌,而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摘掉这个招牌。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势力在较清末宽松得多的环境下有了较大发展,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或未及实行的总统制、内阁制、国会、地方自治、政党政治等民主与共和的原则和观念广泛传播,已被国人当作衡量一个政权是否是民主制的尺子,谁反对民主共和的原则,谁就会受到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反对。
民初时期处处存在新与旧的矛盾冲突,资产阶级代表中国的新生力量,但其力量弱小,封建主义的影响虽还很大,但已日渐衰落。在这样一种新旧斗争、交叉、共存的时代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它带有两种政治体系的色彩。
二 一元的传统和多元的现实
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变。封建专制制度以封建帝王的意志为中心,以维护皇室、贵族、地主阶级利益及其政权的巩固为目的,以维护一元化的封建皇权为宗旨。就政治思想而言,从汉代“独尊儒术”以降,以孔子思想为主体形成的一套儒家思想体系成为封建统治者用来维护皇权的思想武器,成为维持封建社会秩序的宗教和禁锢人民思想的锁链。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尽管发生过多次社会动荡、战乱及分裂,但还是统一的时期占主流;经济上的小生产和政治上的层层向上负责维护皇权的统治形式使大多数民众处于愚昧状态,只将改良社会的愿望寄托在贤良君主的出现上,中国人已习惯于“定尊于一”的大一统传统,它成为中国“国民性”的特征之一。从政治体制上看,虽然中国早有“民之有愿,天必应之”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在世袭帝制的中央集权下,皇帝是全国的首脑,拥有无限权力,人民很难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长期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并没有代议政治的实践,相反,却长期奉行对皇帝和上级负责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与日俱增,清王朝在被迫做了一些改革的同时,仍顽固维护旧有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民主共和的宣传及其活动只能在海外进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封建皇帝被赶下历史舞台,复辟活动被沉重打击,“君权神授”、“皇权高于一切”被抛进历史垃圾堆,自由、平等、博爱、主权在民、人权神圣等思想开始在中华大地传播,“定尊于一”的传统被打破了。新文化运动呼吁人们独立思考,反思中国的过去与现状,寻找走向中国光明未来的途径。人们普遍在寻求建立一个和平、富强、繁荣的新中国的道路,各种改革中国现状的呐喊和主张此起彼伏,令国人目不暇接。这些不相同或根本对立的主张在国内各抒己见,各有市场,经常争论得沸沸扬扬,形成一种异常热闹的局面。思想文化领域多元的价值判断体系现状使习惯于以儒家思想为是非曲直标准的中国民众一时无所适从,很难适应这种局面。
封建政权是以皇权为中心高度集权式的政权,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官僚都要向皇帝效忠,历史上皇权旁落的情况,也是通过控制傀儡皇帝来实现的。在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中,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一般不采取公开的方式,而是以不公开的相互倾轧和争取上一级官僚权贵直至皇帝的支持为主要方法。而民国成立后引进的新式政权采取分权式的权力结构,大总统、内阁、国会、司法系统相互制约,北洋军阀头目对民主制度的破坏,并未使权力制衡结构完全失灵,因而经常因权力机构之间的矛盾而出现一些政治纷争,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中矛盾公开化的结果,也使政治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民初在传统自然经济仍占有绝对优势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加上外资企业的发展、封建地主向现代实业投资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几种经济各自发展并相互渗透使经济领域中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
民初多元的现实主要还是体现于政治力量的多元并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状况。
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西南军阀在对付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时采取联合抵抗的政策,但实际又分为滇、桂等各路军阀,还有一些较小的军阀控制某一省或某一地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二次革命”后军事实力急剧下降,但政治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清室虽宣布退位,也仍有一定的实力和社会基础。这些政治力量以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出现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政治主张、发展方略、对时局的态度等千差万别,彼此也因时局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分化组合,不断变化着盟友和敌人,形成相对独立的多元政治实体。
民初的混乱局面不仅在于它的多元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多“元”共存中没有形成强弱分明的局面,相反却形成了此伏彼起谁也吃不掉谁的平衡僵持局面。无论是军阀与革命派的斗争,还是军阀间的混战,都无法使自己一方获胜;思想领域里的争论以新文化占了上风,但封建文化的势力仍盘根错节有广大市场,经济领域中新经济的成份增长势停撤猛烈,但封建经济仍为汪洋大海。清王朝的解体是高度集中的一元结构的崩溃,民国的建立并无强有力的权威,大小军阀割据一方,原有一元结构分裂成大大小小封建式的权力中心。特别是持续不断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始终未能出现一个强大派别控制整个中国的情况,使军阀分裂的现象贯穿于民初中国。他们的势力相对均衡,造成整个中国社会被军阀间混战和争夺所困扰。多元及其力量相对平衡是民初社会动荡不安的基本原因之一,也是民初中国社会一个鲜明的特点。
三 社会机制发展的不平衡
1914年,曾留学日、美、英、德等国,又十分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杨昌济曾指出,“吾国近来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不仅是国民的思想,近代和民初中国的许许多多方面都与政治的变革不相适应,严重滞后,因而大大影响了政治变革的实际效果。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要求要有相当比例的国民受过良好教育,有参政能力。而民初的中国,教育远未普及,处于极其落后的状况。 20 世纪30年代,巴克曾对中国22个省的308个县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有30 %的男性和1 %的女性只具备读懂一封简单家信的文化程度(费正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识字者中大部分应划入半文盲的行列, 民初的民众文化水平大体上是这种状况。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不关心政治的传统,有人评论这一点时指出:“每个中国人,假如他有办法做到,决不肯让自己卷入同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事情。”“多数人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宪法,几乎有90%的人民对于政府体制漠不关心。”(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281页)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封建政治观念浸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选择及价值取向。要改造旧的政治传统和民众素质并使之适应民主共和的要求,应对广大民众进行一番长期广泛的启蒙工作。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此也做过努力,但民主宪政的观念在中国还远未普及,距离让广大民众认同和自觉追求还相去甚远。武昌起义后不久,严复曾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和环境将需要30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于建立共和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785页)。 民初尽管有革命派的长期宣传和新文化运动那样大规模的反封建文化运动,但中国大多数人仍未摆脱其不关心政治的状况。所以从国民素质与政治变革不能同步前进这一点看,严复的分析有其一定合理的成份,可以说,中国民众素质严重滞后是民主共和制度不能名副其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报刊上进行了一场长达3年的大论战,论战的焦点是中国社会如何进行变革。 改良派主张采取“渐进论”,梁启超引用19世纪末年德国学者波伦哈克的理论,认为“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梁启超提出,中国人因长期专制造成“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惟知个人主义以营其私”。所以,“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者也;今日中国政治,非可采用共和立宪者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二卷上,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5、182页)。革命派坚持要推翻清政府和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实行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指出,“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 仿而造之者, 岁月之功已足”(《孙中山选集》第73页)。落后国家选择政治体制,当然要选择最先进的,但革命派对改良派提出的顾虑未能进行深刻的思考,忽略了其主张的合理部分,对于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滞后等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这个问题,1906年,他在《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建国三时期设想(《孙中山选集》第78~79页)。辛亥革命后,军阀当政已使共和国体成为虚设而国民对此并无能力制止的现实使孙中山深入思考了中国国民性和改造中国的问题,他指出:“惟民国开创以来,既经非常之破坏而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此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孙中山选集》第168、173页)。他以美法两国为例:“美国一经革命而后,所定之国体,至今百年而不变”,原因在于他们未独立以前已有地方自治基础,“法国则不然,法虽为欧洲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于革命之前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儿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故何也?以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地盘,无自治之基础也”(《孙中山选集》第170页)。从这里看出,有无自治的传统, 共和命运完全不同。孙中山分析中国时指出,“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而予犹欲由革命一跃而儿于共和宪政之治者,其道何由?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为之补救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同上)。这种思想的提出,就是承认共和资格非可短期养成,因而对国民素质滞后的现实采取带有补救性质的措施,这也是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
社会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对立的产物。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阶段,旧有的封建制度严重束缚了它的发展,因而展开了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决战。与西方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很不相同,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远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至1913年,中国产业资本总额只有15.4亿元,其中外国资本占80.3%,中国官僚资本占9.7%,民间资本只有10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华学术论文集》第337页)。 民族资本的现代产业产值只占国内总产值的2.7 %(《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第44页)。 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对抗能力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势力有着种种联系,在政治上更趋向于渐进和改良,不愿接受革命带来的大动荡和大变革。中国也不具备西方典型资产阶级革命时所具有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大批自由劳动力涌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的趋势。以西方典型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衡量,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并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
然而,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下,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列强掠夺的众矢之的。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在巨大社会压力下,仍拒绝实质性的改革,解决国内社会矛盾唯有通过暴力革命。旧式的农民起义已无力领导20世纪的社会革命,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了解世界与中国的差距,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的巨大推进作用,了解清王朝的腐朽,因而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仍成为清末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级反抗清政府斗争中政治纲领水平最高、组织最完备的力量,担当了进行变革的先锋。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
可以认为,辛亥革命是在种种外在因素刺激和民族、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带有某些早产性质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它所带来的种种滞后问题也就是必然的了。历史上的革命,往往没有充分实现原有的革命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这场革命不需要进行。吸收革命的成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种带有早产性质的革命是使中国社会的变化远远落后于政治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既然资产阶级无力使共和国名副其实,无力击溃封建传统势力在各个领域的阵地,新与旧势力就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共存,必然造成社会的冲突、动荡和不安。
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远非仅仅变更政权所能完成。中国在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后,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方面,在提高教育水平和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方面,在政治和军事领域清除旧势力方面虽有进展但仍远远滞后。一句话,整个社会还缺乏现代化因素,即使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它也不能控制政治局面,相反,新政权形式被军阀势力利用、改造成为其手中的工具,完全失去了革命派建立政权时的初衷。这也是社会现代化因素贫乏的必然结果。
在一个封建主义势力占很大优势的国度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革命需要有经济、文化、社会及个人素质的相应变革才能真正完成,任何方面的滞后都会影响政治变革的效果。很明显,民国初年的混乱和无序,就是由发展的非整体化、非协调化这一社会特征造成的。
四 两次飞跃间的积蓄期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是曲折、坎坷的。民国初年,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民主共和并不能真正建立和运行,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能说它完全失败。一个旧的政治制度的解体,不仅包含着其政权的结束,也包含标志旧有忠诚中心和一整套社会准则的让位和一切旧制度基础的瓦解。这就意味着这种更替不会是以短时期暴力活动就能完成的使命,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相当浓厚的国度里,这种转型时期将是相当坎坷的历程,我们不能因新制度没有取得彻底胜利而否定其积极意义。民国的建立是中国从封建专制向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过渡的开始,它虽未完成这一使命,但它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做了准备。政治领域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登上历史舞台,新文化运动和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经济领域里新经济的成长等都是这一时期显而易见的积极成果。
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使人们的希望化为失望。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许多人及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也满怀疑虑。西方许多人士认为西方近代文明已经破产,应由东方的文化来弥补。欧洲的战争创伤和贫富距离拉大等社会问题,使中国许多人对西方文化怀疑起来,有人指出:“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13卷10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评论道:“泰西之文化单趋于物质,而于心灵一方缺陷殊多。此观于西洋文化因欧战破产一事,已甚明显。”(《申报》1924年4 月14日)对于东方文化重新被崇拜的原因,胡适评论道:“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西洋人对近世的科学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自大狂,东方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气焰。”(《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
中国是遭受列强侵侮之后才被迫向西方学习的。向西方学习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饱受其多次侵略的过程,向欺辱自己的人学习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严复集》第2册,第50页)。不过, 由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功利主义色彩很浓厚,他们希望从西方学到某种模式,经过短时间的奋斗便要中国摆脱落后,跻身于强国之林,迅速完成救亡和强国的使命,因此缺乏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一旦引进西方制度未获成效,不少人立即对西方文化或制度失去信心,把强国的希望又寄托于传统文化。
当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受到严重挫折、西方文化本身也因一次大战陷于危机时,中国有识之士仍在冷静的思考,寻找使中国实行真正共和制度的道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呼吁要提高国民意识,实现真正的共和:“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所能主持,更非一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宪政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孙中山认为建设民国应先消除官僚、军阀、政客这三种“陈土”,“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故”,“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25~126页)。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政治、思想界带来一股清风,孙中山在探索中国出路方面有了新的飞跃。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代议政体进行反思:“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十倍”,“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罢了。”所以,有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孙中山选集》第756 ~757页)。1922年1月4日,孙中山在演说中提出:“法、 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孙中山选集》第507页)1924年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 孙中山指出欧美资产阶级代议政体“有很多缺点”,“不是真正的民权”,“人民所得的民权,还是很少”。与此同时,孙中山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制度作了很高的评价:“近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明确表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选集》第692~801页)。
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单方面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模式、马克思主义等更加引起国内人们的注意。五四运动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诞生了共产党,在摸索中国出路和改造中国的实践中,出现了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
北洋时期使中国人经历了磨难,也让中国人在磨难中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黑暗的中华大地已依稀可见光明的曙光。在看到这一时期黑暗和混乱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它也是中国下一次飞跃的孕育期。
标签:孙中山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孙中山选集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