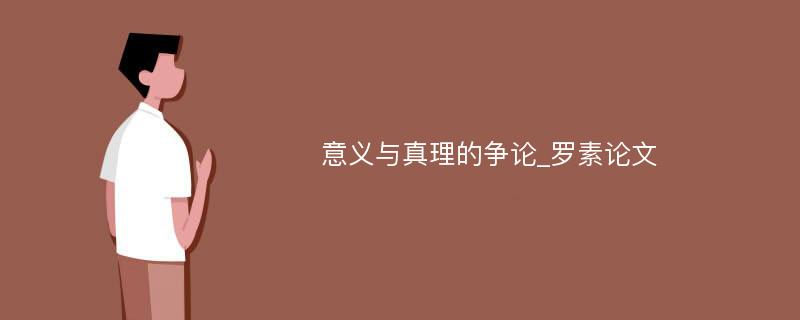
意义与真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1-)03-0020-05
意义和真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语言哲学中碰到的重要问题。由于意义的被给予特性,使得真成为隐蔽在后的东西。而意义作为真的呈现方式,又使意义指向了真。复杂的关系加上哲学家本人的理论背景,导致了这一领域长久的争论。本文打算粗略梳理和分析有关意见的争论,最后试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也许在于对意义通向真的途径的讨论。
一
意义和真的关系明确成为一个可讨论的问题是从19世纪末弗雷格那儿开始的。在弗雷格那儿,这个问题表现为涵义和指称的关系问题。当时,弗雷格在讨论逻辑“恒等”问题时注意到,一个名称的指称和其涵义并不是一样的。在三角形ABC中,中线a、b、c的交点既是中线a与中线b的交点,也是中线b与中线c的交点,它们的指称相同,但涵义不同。“晨星”和“暮星”同有一个指称,却有不同涵义。因此,“和一个指号(名称、词组、表达式)相联系的,不仅有被命名的对象,它也可以称为指号的指称,而且还有这个指号的涵义(内涵)、意义,在其涵义中包含了指号出现的方式和语境。”[1]指号、涵义、指称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一个指号对应于特定的涵义,特定的涵义对应于特定的指称,而与一个指称相对应的可能不只是一个指号。就是同一种涵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也会由不同的表达式来表达。还有的表达式具有涵义,却不具有指称。弗雷格的讨论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引起了人们对意义问题的重视。什么是语词语句的意义、意义是如何确定的、意义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怎样、符号的指称行为是如何实现的等等成为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就弗雷格本人讲,他并没有提出一种有别于传统认识论的意义理论。然而,弗雷格的大量分析足以引得后来哲学家们去得出不同的结论。
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对意义和指称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弗雷格涵义、指称理论的一种延伸。他们的研究旨在创立一套与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图画,以逻辑的人工语言来代替日常的自然语言,以期达到指号与指称、语句与事实、语言与世界的统一。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上述意图的典型表现。他专门研究了那些人们在未能亲知情况下用来表达意思的指谓词组,也就是确定的摹状词。这些摹状词因为兼有专名的功用,就使得带有摹状词的句子在意义和指称上出现了混乱的情况。罗素的思路是改写这样的句子,使其中确定的摹状词只以意义的表达式出现而与所指不直接关联。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符合人们健全实在感的语言逻辑,为实现人工语言的设想树立了典范。
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找到了一条到达意义与真的统一的道路,那就是建立人工语言。而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哲学家戴维森在总结过去几十年人们对语言意义的讨论时看到,语言的意义既不能依靠语句中语词的指称来确定,也不能依靠对语句内涵性的翻译来确定,因为这两种方法都将导致意义的无穷后退。戴维森接纳了蒯因的做法,从外延上着手来研究意义问题。[2]面对着内涵意义的困境,戴维森说:“对于我们陷入处理内涵语词这一困境的忧虑,是由这样一种作法所造成的,即把语词‘意谓(that)’用作填充在对语句的描述与语句之间的连接语词。但是,情况可能是这样,我们这种冒险作法的成功并不依赖于这种用于填充的东西。”“让我们尝试以外延的方式处理由'P'所占据的位置。”[3](134)这样,意义和真就连结在了一起。他十分赞同塔尔斯基在真的语义学定义中构造的真的定义与意义概念之间明显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表述为:塔尔斯基的“定义通过对每个语句的真实性给出充分必要条件而起作用,而给出真值条件也是给出语句意义的一种方式。知道一种语言的关于真理的语义学概念,便是知道一个语句(任何一个语句)为真是怎么一回事,而这就等于理解了这种语言。”[3](135)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起到捍卫塔尔斯基理论的作用。由此,戴维森反对任何企图构筑人工语言的想法,他认为“意义理论的任务并不是改变、改进或改造一种语言,而是描述并理解这种语言”[3](141)。“语言哲学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最终的任务是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可以说出许多理由,将‘语言’一词限制于当前或一直是在实际使用中的符号系统:未经解释的形式系统由于没有意义因而不是语言,得到解释的形式系统最好看成是自然语言的延伸或一部分,它们从自然语言那里获得生命。”[4](103)显然,反对人工语言的态度与主张由外延方面入手研究语言意义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基于对语言意义与真的紧密关系的理解,戴维森逐步引导出了他的意义的真值条件论的公式,这个引导是由三个步骤组成的:
S意谓m;
S意谓P;
S是T当且仅当P。
这三个步骤也可以理解成戴维森对语言意义理论发展的理解,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不断摆脱意义的内涵论理解、走向外延理解、走向真值条件论理解的过程。只有在最后一个公式“S是T当且仅当P”中,戴维森才实现了借助于真理理论来完成以往人们认为要凭借意义概念来完成的任务的目标。“S是真的当且仅当P”是“S意谓P”的最好解释,于是,“雪是白的”这个语句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雪是白的”这个语句有意义,因为雪真的是白的。现在,无穷倒退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就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它也可以通过把它的某些结论同事实进行对比而得到检验。在现在这种情形下,这是易于办到的,因为这个理论被表征为生成无穷多的语句,其中每个语句都给出一个语句的真值条件;在一些样本情形下,我们只需询问,被这种理论断言为语句真值条件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3](136)
二
不过,现代语言哲学中除了主张意义与真的统一的观点以外,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指称论和语言图象说不久就遭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在《哲学研究》这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代表著作中,他指出了意义指称论的不合理性,又回到了弗雷格分别涵义和指称的境地。他批判了自己前期的意义理论,认为错就错在假定我们可以找到语言的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对于统一性的渴望驱使人们力图在形形色色的语言现象中找出共同的东西,并用逻辑的形式固定它,形成某种人工语言。但是这样做是天真的,它只是一个哲学的迷梦。语言现象是多种多样的。现在,维特根斯坦要来说他的语言意义的用法论了。我们不敢说意义的用法论一定是反对意义与真的统一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它确乎是反对语词指称论,反对语言意义与外部实在的绝对同一的。这种理论把语言使用者的生活方式引进语言意义的判定中,形成了语义、语言使用者和语言对象的复杂关系。如果把中间那项的作用夸大,并推向极端,其后果自然是意义与真的分离。这样的观点果然由意义用法论的一个代表人物斯特劳森提出来了。
斯特劳森不同意罗素等人的意义指称论观点,认为他们混淆了语句本身和语句的使用这两件事。斯特劳森认为,语词本身不起指称的作用,但我们可以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语词去指称不同的对象。指称事物是语词使用的特征,是一种言语行为。“‘提到’或‘指称’并不是语词本身所作的事情,而是人们能够使用语词去作的事情。提到某个东西或指称某个东西,是语词的使用的特征。”[5](93)语句本身也不论述特定对象,因为同一个语句可以在不同的场合下被用来论述各种不同的对象,因此语句本身无所谓真假,只有在特定场合下把某个语句用于论述某个特定事实时,语句才有真假之分。真和假也是一种言语行为。“显然,我们都不可能谈到语句本身的真或假,而只能谈到使用语句做了一个真论断或假论断,或者说(如果这种说法更可取的话)使用语句表示了一个真命题或假命题。”[5](92)这样,斯特劳森就把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指称及真假作了区分,“意义是语句或语词的一种功能;而提到和指称,真或假则是语句的使用或语词的使用的功能。”[5](94)
差不多同时,斯特劳森又对“真”这个概念作了分析,得出了一种真理冗余论的观点。斯特劳森借用兰姆赛的观点,后者认为真理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产生于语言混乱,“真的”和“假的”这两个谓词只是起到强调或增添文采的作用,它们不具有任何描述内容,不表示任何性质或关系,我们可以把它们从任何语境中删去,而不引起语义上的损失。斯特劳森从言语行为论角度推进了这种冗余论。按照斯特劳森的观点,“真”这个词不是用来描述任何特性的谓词,它首先是用作行动的语词。我们使用行动语词不是作出一个陈述,而是作出一种行动。我们往往用“真”这个词表示赞同、承认、许可、保证等等,它表示我们接受别人的某一说法。比如,“‘天在下雨’是真的。”这句话中的“真”只不过表示我同意“天在下雨”这个陈述,我说这句话是用来完成“同意”这一行为的。于是,斯特劳森就彻底堵死了从语言到实在的道路。
在意义和真的关系问题上,上述声音还可以从达梅特那儿听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语言哲学家达梅特对戴维森的意义的真值条件论,从反实在论的角度提出了批评。达梅特认为,“主张语句的意义要由它的真值条件来说明,即要陈述若语句为真世界上的情况是怎么回事,这暗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即这种真值条件是不言而喻地可以得到的,而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识到这种条件无关。”[4](103)确实,戴维森借助于塔尔斯基“T约定”建立起来的“S是T当且仅当P”,从逻辑形式上解决了以往传统真理符合论无法解决的问题,回答了语言的意义在于其真的形式条件。但是,戴维森没有讨论如何衡量一个具体语句的真,也就是说,没有从内容上来讨论真的问题。用达梅特的话说,意义的真值条件论不能说明它的基本概念(即“真”这个概念)和语言实际用法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中,语句的真值条件是超验的,这即是说,反正世界上的情况决定了语句的真和假,至于我们有没有能力知道这一点,能否表现出我们把握了这一点,则不在考虑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显示出我们具有关于语句真值条件的知识,我们的意义理论就不能表明句子的意义和用法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意义理论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达梅特认为,意义理论就是理解理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和理解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理解A’与‘知道A的意义’之间真觉上的等值表明了这一点,不管是否严格地看待后一个短语中‘知道’这个动词。意义与理解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可以说,意义是理解的对象(或内容)。如果理解与知识的关系不成问题,我们就能说,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某人理解该表达式时所知道的东西。”[6]不过,达梅特并不赞同从心理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心理主义的“理解”将使意义逃离公共领域,变成为私人的、非一目了然的东西,进而成为同样超验的东西。达梅特吸取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把“理解”与语言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理解某一语言并不是在脑子里理解、懂得一套规则,重要的是看其语言实践。说明一种语言的实践与说明何谓理解那种语言必定是同时进行的,而这同时也就是理解那种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达梅特又一次突出了使用语言的人,把“真”排斥到意义之外去了。
三
意义和真之争看来难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对立意见的分歧似乎从来就不是纯粹而泾渭分明的。一方阵营中出现对方的声音并不见怪。这种现象既反映了意义和真的关系的复杂性,也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契机。
(一)罗素关于专名指称问题的疑义
罗素当初灵机突现,将摹状词与专名区别待之,为的就是专名可以根据人的亲知来指称某物,而摹状词不能。因而后者不能是句子的逻辑主语。不过在罗素的进一步探讨中,沿着亲知原则来寻求专名,发现绝大多数原以为是专名的语词却原来并非真正的专名,它们只是一个或一组摹状词,是改头换面的摹状词。罗素把真正的专名叫做逻辑专名,它们能够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因此,它们是主谓语句中真正的主词。也就是说,一个语词要确定其是否为逻辑专名,看就看它是否指示某个实际存在的对象。按照这种标准,逻辑专名真是贵如金银了。在罗素看来,逻辑专名其实只有两个:“这个”和“那个”。他说:“只有象‘这个’或‘那个’这样的词,才是可以在逻辑意义上作为名称使用的词。人们可以把‘这个’用作名称,以代表人们在一定时刻所亲知的某个特殊之物。”[7]
对于大家通常以为是专名的语词,罗素把它们叫做普通专名。普通专名在指称方式上有所不同,它不是依据我们的亲知来指称对象的。比如:“苏格拉底”,当我们在使用“苏格拉底”这个名称的时候,心里想的其实是一组描述性的语词,诸如“其貌不扬”、“柏拉图的老师”、“饮鸩而死”、“会用精神助产术”等等。这些描述语即便在苏格拉底本人离开我们远去之后仍旧可以通过别人的描述而清晰地在我们头脑中呈现,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摹状词来用“苏格拉底”这个名称指称苏格拉底这个人的。这样的指称是否可靠呢?也许历史上真有苏格拉底这个人,有人曾亲知过他,并用“这个”人或“那个”人指称过他。但对于象“柏伽索斯”这个希腊神话中有翅膀的飞马的名称怎么办呢?所以,那些通过摹状词来指称对象的专名从逻辑上说来不能作为真正的专名,它们是普通专名而不是逻辑专名,只是缩略的摹状词罢了。
然而这么一来,罗素在意义和真的关系问题上必将陷入困境。罗素原先意图建立人工语言,以达到语句与事实、语言与世界的同一。而此同一的基础是指称关系的存在。语句的真取决于构成语句成分的真。而一旦专名在细细过筛后只剩下“这个”和“那个”以后,上述同一的基础就受到极大的威胁。而事实上人们在语言使用中,虽然“这个”、“那个”有确凿的指称,但它们却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名称,因为名称之所以必要,在于其能够区分对象,而“这个”、“那个”只是代名词,无法拥有真正的名称的功用。因此,专名和指称在这里发生了分离。通常所谓的专名,其指称不可靠,而具有指称的所谓“逻辑专名”又不是名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语句与事实、语言与世界的同一形式已经不可能由专名与其指称对象的统一来确定了,语言和语句似乎永远将成为真值函项式,那个变项永远要空着了。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只能拥有意义,而无法到达意义的彼岸——真。
无独有偶,罗素分析普通专名指称问题的结论,得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塞尔的赞同,弗雷格也持有这样的主张,认为专名相当于一个摹状词,有人称这是一个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传统。普特南更把这个传统读解为名称的意义通过对于性质的全部说出而给出。[4](151-153)
如果我们接受罗素分析的结论,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在接近斯特劳森的观点。在罗素这儿,名称(普通专名)和对象的指称关系已经不是一种本质关系,名称所指称的与其说是某某东西,倒不如说是如此这般的东西。而“如此这般”表明了它们与使用名称的人的指称行为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斯特劳森所讲语词本身无所谓指称,有的只是人们用语词去指称不同的对象的观点,我们在罗素这儿也隐隐有所发现。不过,与斯特劳森不同的是,罗素并不得出真理冗余论的结论,指称对象的存在始终可以通过亲知而肯定,摹状层面的指称行为,除了意味着指称“如此这般”以外,还意味着指称“东西”。罗素始终是实在论的。
(二)达梅特对于真的“仁慈”态度
应该说,达梅特的反实在论态度是一贯而坚决的,也就是说,他始终坚持认为不能从真的角度去确立语言意义。然而他对于真,也是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为意义和真的连接设想了种种合情合理的出路,可谓“仁至义尽”。要不是他一定要坚持逻辑统一性的原则,他本该接纳真的。其实,我们从达梅特这些对真的分析中,已经感到了某种正面的说服力。
一个句子的意义在于其真之条件,达梅特认为,这是一种流行的看法。这种看法在直观上显而易见,很多人倾向于接受它。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心中的等价原则,“亦即这一原则:任何句子A在内容方面等价于‘那个A是真的’这一句子。”“等价原则提供了一个基础,据之可对‘真的’这个词在语言中的作用作出一种可令人接受的解释。”[8](77)这种解释满足了人们心中对语言扩展功能的要求,人们希望通过“真”这一谓词,使一种语言的内容扩展到另一种语言的内容,通过理解一种语言而肯定自己能够理解另一种语言。[8](78-79)如果我们把一种语言确定为对象语言,另一种确定为元语言,那么,达梅特所说的情况就很清楚了。套用到戴维森纲领上去,能够理解“雪是白的”,就能够理解“‘雪是白的’为真”是怎么回事。两者对等,扩展成为可能。达梅特当然不同意这里的等价原则,认为它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假设。然而他没有否认这是人的一个心理需求和心理趋向,只是这个需求和趋向无法纳入到他的思路的逻辑统一性中去,他说:这个原则“从心理方面确切地说明了:我们为什么最终很容易以为,对于属于我们语言中不是很基本的部分的那些句子,我们具有某种诸如知道它们必然为真会是什么情况的能力;但它并没有提供有关这种假设的证明。”[8](100)既然如此,我们不由得想到,要是人心确有实在论倾向(等价原则)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承认它,然后再设法说明它吗?如果我们无法用“证明”的方式给予它存在的地位,难道不能通过其他途径来确立它存在的地位吗?
除了等价原则以外,达梅特还从人的断定行为来讨论“真”。“真这个概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显然,它与语言的断定行为的联系是基本的,正如下面这个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自然而然地把断定称做‘真的’或‘假的’,而不把询问、命令、打赌等等称做‘真的’或‘假的’。”[8](83)按照达梅特的分析,断定行为只是人们用语言来做事的一种,语言还能做其他的事。如果断定中的真和假能够说明用语言所做的其他事,则吸纳“真”作为意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可以的。不过,在断定问题上,他并没有过多地讨论这一方面的关系。他注意较多的是断定行为与真的关系。达梅特认为,人们往往把真与断定的正确性联系在一起,但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重合的。我们说一个断定行为正确,包含了这个断定所说的东西的正确,还包含了这个断定被认为是正确的理由。前者属于断定所说的内容,后者属于断定这种行为,“这样,真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断定的语义方面和语用方面的差异;真乃是说话者所说内容的一种客观的性质,它的确立与他说话时的知识、他这么说的理由或动机是无关的。”[8](87)而断定不仅包含了前者,而且还包含了后者。两者非重合。因此,“解释我们为什么出于语义学的目的需要真这个概念,这本身并不能解释怎样使用这个概念。”[8](87)真与断定行为相关,但断定并不等于真。达梅特的态度是鲜明的,不过我们从这鲜明的态度中,也看到了他对真“仁慈”的宽容。至少他在断定行为中没有完全否定真,人们希望通过断定来达到真,毕竟断定的内容与虚构的内容在人们眼里是有区别的。达梅特只是强调了断定与真的非重合性,依据他的逻辑统一性的思路,既然是不重合,真就不等于意义的全部,因而真不可以成为意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我们的看法是,就从达梅特的分析出发,恰恰可以得出与他不同(不一定是相反)的结论:既然真与断定相关,那么,两者的相关而非重合正是引起讨论的前提。应该说,不相关或完全重合的前提是不会产生任何意见分歧的。现在我们要问,我们如何解释人们想通过断定来达到真这种希望呢?如果这种希望的合理性无法在断定行为中得到解释,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其他的途径来说明它吗?达梅特说,从真之条件来确立意义理论的做法,在原则上存在着困难。现在我们要说,根据他对真的分析,把两者分开,恐怕在原则上也会存在困难。
在意义和真的关系问题上,各种观点各自据理力争,期间也有融合的迹象,然而各方的声音却并不因此消失,这就说明,意义和真的关系的确非常复杂。各方在原则上都有一些在理之处,这就意味着对方在原则上会有困难,这是一盘下不完的棋。如果各方都坚持自己的原则(逻辑),争论的情形可想而知。那么,如果承认各方的原则呢?也许,我们可以把问题转换为:意义通向真的途径。
收稿日期:2001-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