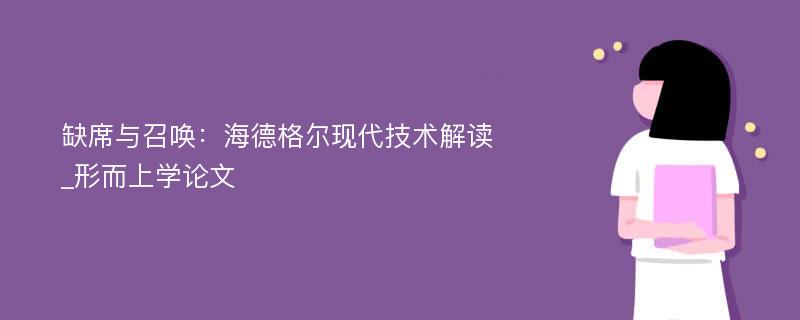
缺席与召唤——对海德格尔现代技术之问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0)04—0057—06
一、座架(Ge—stell)
50年代前后,海德格尔集中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对现代技术的追问。为此,就相关话题,他作了多次演讲,并修改成文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953年11月18日,他在巴伐利亚艺术协会所作的演讲后扩充成文的《技术的追问》,从中可以发现海氏对现代技术问题的基本看法。
海德格尔是从现代技术的流行观点开始分析的。对现代技术本质的思考,最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技术是合目的工具和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者又彼此相通。因为设计、创造和利用合目的的工具,当然是人的活动。海德格尔把这种观点称为工具性的技术规定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凡是流行的,总有其流行的道理。海氏也说,他不想否认其正确性。确实,谁能否认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的说法呢?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似乎也在证明这种流行观点的正确性。我们不是乘坐高速飞机这一运输工具去实现观光旅游的目的吗?我们不是利用电站为人类生活提供着能源吗?而设计和制造飞机、电站,当然是人的行为。既然如此,海氏还有必要去追问如此明白的事情?仿佛是在回应黑格尔的“熟知非真知”,海氏出乎常理地说:“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唯有真实的东西才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与那种从其本质来看关涉于我们的关系中。照此看来,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注: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6页。 )海氏试图区分正确与真实。在他看来,正确只表述了一种不错的判断。说流行观点正确,就如说“诗是词的堆积”在陈述上不错一样,但这种不错的判断远远没有触及到真实的东西。若按照流行观点,现代技术和手工技术甚至古代工艺就没有质的差别,现代技术只不过仅仅在速度和效率上有所提高罢了。正如海氏所分析的:“即便是带有涡轮机和发电机的发电厂,也是人所制作的一件工具,合乎人所设定的某个目的。即便是火箭飞机,即便是高频机器,也还是合目的的工具。”(注: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 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5页。)看来, 在工具层面上我们无法穿透现代技术的本质。
现代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海德格尔那里,问题本身常常是引导追问的指南。先看“本质”。海氏认为“本质”的原本含义并不是与现象相对的一般概念,而是“现身方式”。因为“即便我们说‘家政(Hauswesen)’、‘国体(StAAtswesen)’时,我们也不是指一个种类的普遍性,而指家庭和国家运行、管理、发展和哀落的方式。”(注: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8页。 )这意味着“本质”就是如何展示自身的方式。照此说来,技术的本质就是技术的显现自身的方式。再说“技术”。海氏通过对因果关系的词源学分析,指出技术的原初的含义不只是表示手工行为和技能,它作为某种创作归于更本源的“产出”,昭示为一切生产制作(包括后来的技术、艺术等)过程的可能性都基于存在之解蔽之中。即技术是属于开启世界,去除遮蔽的存在方式。因此,技术之本质是存在之解蔽与遮蔽过程中某种现身方式,不能简单地看作手段的工具。
比如,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拒绝使用钢犁。这并不能简单地归于拒绝使用一种工具,而是根本上拒绝与他们生存方式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在印第安人眼里,大地是养育人的母亲,自然而然,钢犁就不可能在大地作为母亲的世界构造方式下,实施耕作的功能。反过来,也只有当大地非神化,被降为加工、获取财富的对象时,才有可能采用发动机作动力的钢犁来耕作。
由此,追问现代技术的本质,实际上在问现代技术所开启的存在世界是以何种方式显现。
海德格尔以一个词来描述现代技术的本质, 那就是“座架(Ge —stell)”。这个词本来是相当常见的日常用语,一般指书架、 骨架等。但海氏赋予它新的内涵:带有前缀的“Ge—”,意指把许多产生同属性的东西聚集起来,“Stellen”意指“摆置”(或译“限定”), “座架”就成为把存在者强制性地限定为具有单一功能的解蔽活动。现代技术展示为促逼(Heransfordern)着的摆置。在这里, 对象被促逼成为功能化的东西,使物在某一方面被限定。因此,现代技术展示为“座架”的现身方式。比如,在农耕时期,耕作意味着:关心和照料。农夫把种子交给大地,任其守护并发育。但以“座架”为展示方式的农业耕作已经成为机械化的食物工业。耕作成为在促逼意义上摆置自然。空气被促逼着摆置为氮气,土地被促逼着摆置为可通过化学分析的营养提供者。现代农业让大地和空气缩减为单一的营养功能。“座架”所开启的世界,物已失去了丰富性,被强制、限定为可利用、可耗尽、可预测的对象。“座架”成了现代技术世界现身方式的形象、深刻的表述,它不是认识论含义上的抽象概念,而是开启现代技术化社会的本质显现。
二、思之缺席
如果现代技术的本质是“座架”,那么这种现身方式怎样才有可能?它仅仅是一种独立的现代社会的顽症或者有其历史的渊源?如果有的话,“座架”产生的源头在哪里?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说:“决定着现代的作为座架的存在乃源出于西方的存在之命运,它并不是哲学家凭空臆想出来的”。(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5页。 )海氏想说明其现代技术的思考并不是突发奇想的故作怪论或热闹应景的时髦评论,他试图从传统存在论的分析背景下去探索现代技术之本质,凸现现代技术是思之缺席的结果,也是思之缺席的典型。
首先,传统存在论遗忘存在的对象性思考方式,显示了西方存在之命运,成为“座架”产生之源。
海氏分析西方哲学的产生时,指出哲学是希腊式的。在柏拉图那里开始以“这是什么?”的方式提问。这种方式意味着存在被设定为存在着的某种根据(本源),这种根据(本源)则成为为人所把握的某种对象性的东西。因此,柏拉图规定了西方思想的基本基调。但是,毕竟古代的存在者从存在的发生过程中还能显示其丰富的特征;中世纪的存在者作为上帝的受造物还带有神性的灵光。只是到了近代,笛卡尔确立了主体以理性的认知方式对象性地处置其它存在者的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以论证性的表象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为现代技术及其先锋近代科学确立了思想方式。
从存在论角度看,这种对象性思想方式造就了遗忘存在,不思存在的历史命运。传统存在论始终只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而言,形而上学并不思存在本身。这里有必要弄清海氏所说的思与传统认知方式上的“思”的差别。传统认知方式上的“思”,是与行动相对立,并为行为与目的服务的思考,这种“思”在传统存在论乃至现代技术中特别发达,它所展示的惟一标准就是“正确”。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认知含义上的思考是在主客二元框架内的筹划,故还不是真正的思。在海氏看来“一种思想越是采取激进的态度,越是深入根本(radix), 深入一切存在者的根源,那么这种思想就越是具有思想的特性”,(注: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078页。)而一切存在者的根源就是存在之运作。因而,真正的思保持着存在的基本成分,让存在显现其自身的本源性的展示过程。可以说,思属于存在,或者说存在使思发生——发生为存在之显现。以柏拉图奠基的笛卡尔发展了的传统存在论,只是追逐着存在者的存在,遗忘或遮蔽了使存在之存在成为可能的存在本身,而且把存在者的存在仅仅在对象性思维中加以规定。因此,传统存在论就是蕴造不思存在的“存在论”。
现代技术的开路先锋近代科学在传统存在论对象性思考方式下才有可能产生。因为,不思存在成了科学产生的前提,进而成为其特色。海氏就认为:“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方式及其手段规定了它不能思,亦即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科学不能思,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长处。正是这一长处确保它有可能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其对象的领域,并在其中安居乐业。”(注:海德格尔:《什么召唤思?》,《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09页。)这表明现代技术是在存在之遮蔽而对象性的存在者显现的过程中运作的。
可以说,思之缺席造就了现代技术的产生,遗忘存在的西方思想的命运成为孕育现代技术的渊源。只有在传统存在论的树枝上才能结出现代技术之果。
其次,现代技术就其本质而言,仅仅是形而上学之树上的一个普通果子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海氏对现代技术批判将仅仅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一个例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海德格尔曾把西方哲学史勾勒为形而上学产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其中,柏拉图奠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调,笛卡尔确立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黑格称尔则建构起绝对精神的形而上学体系,尼采以其“强力意志”为本体作为倒转了的柏拉图主义而终结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这并不表示形而上学消声匿迹。因为,在海氏那里,形而上学的终结从来不是完结、消极意义上的终结。“我们太容易在消极意义上把某物的终结了解为单纯的中止,理解为没有继续发展,甚或理解为颓败和无能。相反地,关于哲学之终结的谈论却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完成。”(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43页。)完成意味着结束,表明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的结束。但这并不表示对象性思考方式的结束。正如海氏所说:“‘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从此一终结到彼一终结’,意思即是从此一位置到彼一位置。”(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44页。)那么,哲学终结是何种位置上的转换呢?
最先表现为各科学从哲学中分离。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考方式就是对存在者作对象化领域的设定,而各科学则在这种对象化设定领域中探索相关对象的某一侧面的性质。因此“它看似哲学的纯粹解体,其实恰恰是哲学之完成”。(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44页。)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在各学科中生根和发展。这是现代技术的序幕。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现代技术的随之兴起,凸现了传统存在论的深刻影响。现代技术化社会的出现,西方传统存在论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对象性思考方式进一步采取“座架”的促逼着摆置的形式来运作,从而使传统存在论所塑造的思之缺席达到了危险的地步。
具体说来,在对象性认知方式下,“甚至上帝也可能对表象而言丧失了一切神圣性和崇高性,也可能丧失了它的遥远的神秘性。”(注: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44页。)当这种方式在科学中渗透、 发展,让作为对象的存在者在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展时,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人自然就成了认知主体。如果说对象之为对象还具有作为对象的自身性、反抗性和相异性、不可捉摸性;那么以“座架”为运作方式的现代技术通过计算、评估、预测,使对象甚至不再是传统意义下的认知对象了,而是进一步退化为以“持存物(Bestand)”的方式在场。 持存物只让一切东西抹平为材料的提供者和储存者。与之相对应的是持存物的订造者——人,他必须依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对一切东西加以物质化和功能化并实施统治。在这过程中,他丧失了他自己,异化为功能化的人即技术人员,从而人本身只被看作持存物。
更何况在“座架”起支配作用的运作过程中,当物作为单一特性的持存物开启为存在之解蔽形式时,已是对存在的遮蔽,而且,这种遮蔽不再显现为一种遮蔽。即人作为持存物本身无法觉知到以“座架”方式开启的存在者是对存在者本身的极端遮蔽。
因此,现代技术的本质建立在“思之缺席”的基础上并且以“座架”方式把现实的丰富性存在者限定为持存物,从而,现代技术成为思之缺席的典型的极端形式,成为传统形而上学具有现实性的终结。
三、思之召唤
既然现代技术危机的根源是思之缺席、存在之遗忘,那么克服这种危机就在于思之召唤。召唤根本上就是追问。追问并不期待着对问题的回答,而需要一种响应。响应的方式恰恰是对思之缺席作更为本源的追问,这是思的尝试。在这思的尝试过程中解构传统存在论。“解构意味:开启我们的耳朵,净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之存在向我们劝说的东西,通过倾听这种劝说(Zuspruch),我们便得以响应了。”(注: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600页。 )但当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主宰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现代技术大行于市时,存在之思已经变得越来越生疏了。因此,思需要训练。海氏很有意思地认为思也是一项手工活(Handwerk)。就如其它手工活要不断训练一样,思这一活儿不能一朝完成,作为最简单而又最艰难的手工活,需要不断训练。从广义上说,海氏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揭示就是思的过程,当然,那是否定性地揭示现代技术不思的过程。作为肯定性的思的追问,不可能列出某种存在的本真状态,然后说:“喏,这是思的本真之处,请享用吧!”追问本身只是促使人注意被传统形而上学所遮蔽的问题,让人通过被问及的东西去倾听、去体验。海氏正是在让人思、让人学会倾听的层面开展现代技术之问的。
值得注意的是,海氏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又作了《物》《筑·居·思》《什么召唤思?》等演讲,它们构成了对思之缺席的尝试性召唤。海氏的演讲《物》可以说是他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思的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对“壶”的分析。壶若按制作技术或者按照壶底和壶壁所用材料来分析,不可能领会壶之壶性。因为对象性思考方式只能指出制作所用壶的材料和壶里所盛的是气体还是液体。海氏以生动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极赋召唤力的思之视野:壶之虚空以承受和保持的双重方式来容纳注入和承受的东西。无论注入和承受都是一种聚集。壶之为壶的本质就是显示在聚集活动中。聚集起来成为赠品,如水或酒。水中有泉,泉中有岩石,岩石中有大地的蛰伏,而大地又承受天空的雨露。因此水中融和着天与地,酒由葡萄酿成,葡萄由大地的滋养与天空的阳光所玉成。同时它们作为赠品是终有一死的人的饮料,让人解渴提神。若用于敬神献祭,则在倾注中作为祭品对诸神的敬仰。由此,在壶中逗留着大地、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如此描述,壶作为一物,本真地敞开了自身。
海氏试图更为本原地来思物,从而让人领悟到克服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更加虔诚地追问思,倾听存在者在不同在场状态下作出的反应。海氏在给一位青年学生的信中说到:“我常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形,而且恰恰是在我周围亲近的人那里碰到这样一种情形:人们非常乐意而且专心地听我讲壶之本质,但当我谈到对象性、被置造状态的站出和来源时,当我谈到座架时,他们便立刻充耳不闻了。”(注:海德格尔:《物》,《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86页。)他抱怨人们只对壶的生动描写感兴趣,而不再深究这种描写与“座架”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不再去思考壶的描述实际上是思之召唤的某种尝试。其目的就在于让人对描述之事有所触动,能学着去思,从而不再以对象性的探索路子去看物。比如,我们看花,不再问“玫瑰花是由什么组成的”,从而避免把花看作一定频率和波长的高速运动着的微粒。海氏认为他是在培养让人如何才能更好地看的能力。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他就坦露,其思考试图协助人们看生活时,能看到生活第一次被经历的原样。(注: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2页。)
我们能否更好地去看?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更好地召唤思。海氏认为在技术发源处与技术处于近临关系的诗与艺术,是训练思之召唤的最佳方式,“诗人经验到:唯有词语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显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anwesen)。”(注: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071页。)诗几乎摆脱了对象性的表述物件的倾向,它让人们经验到物之显现自身的存在境域。海氏重视荷尔德林,根本上不是说荷尔德林那里藏着存在的本真境域,而是表明荷尔德林的语词是诗的语词,具有更大的感召力,激发我们去思。同样,艺术不能简单地看作美学的一个部分,它以保持物之为物性的方式,凸现了存在者的本原性存在,昭示着人们去领悟这种存在的丰富性。米开朗基罗以其创造性的眼光,经他那漂亮的手工活塑造的雕像,保持和凸现了被石匠作为对象消耗掉的石头之存在性。伟大的艺术家成为保持物之为物性的大家,其作品促使人们学习本源性地去追问,召唤缺席之思,具有引导和启发性。
四、海氏技术之问的定位
描述甚至评论技术问题是容易的。我们不缺少对技术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作精彩描述的作品;也不缺少对技术问题作一翻评论,抓住某个方面,急切地开出一大堆“药方”的作品。难的是对技术问题作深层次的思考。
社会上流行的技术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有三种。一种对技术持肯定态度,认为现代技术给人带来种种好处和便利。另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种种害处,破坏了生态平衡等等。第三种则认为技术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只是人们利用它来达到的目的不同,才显出好坏来。但无论那一种都没有超出把技术作为工具的流行观点的范围,都在肯定技术是工具的前提下,对行使这一工具的结果、目的的分析,此种描述本身都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框架中运转,无法揭示现代技术发生的渊源,更谈不上去克服现代技术的弊端。
当然,也有人试图从深层次上思考现代技术问题。如德国文学家弗里德里希·荣格在1953年出版的《技术的完善》一书中论述到技术不再仅仅是帮助现代人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与“工具”。他认为技术使人发生内在变化,人所设定的目的本身就已经由技术决定好了的。荣格的看法显然比流行的观点来得深刻。但有人以为“由于有荣格的影响,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看法并没有原来所认为的那样具独创性。”(注:E·舒尔曼:《科学时代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 李小兵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这种看法根本上没有弄清海氏现代技术之问的根本意义。如果说荣格直观地认识到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生存方式;那么海氏以思之缺席揭示了这种生存方式之本质及其产生渊源,以思之召唤来唤起此在对“座架”之危险的警觉,显示了海氏对现代技术之追问的深刻性和独创性。
大致说来,海德格尔的思想经历了由现象学存在论到追溯希腊思想之源,通达存在之真理,探索艺术、语言乃至技术之本质,从而归于大道(Eerignis)之言说(Sage)。这一过程所涉及的题材极为广泛,但贯穿其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对存在追问,从中显现本源性思的过程。但在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表达方式下,作为被抛入此世的此在,“一方面我们要从对对象的表象方式中摆脱出来,而同时却必须使用那些被理解为对象的,而且只有在对象领域我们才能熟知的语言,”(注:比梅尔:《海德格尔》,刘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4页。)由此, 克服形而上学意味着对意义问题的原始追问,在这种追问中,显示为与传统形而上学及其表述方式的艰难对话、澄清与超越的过程。这构成了海氏探索存在之路的思想张力。随着探索的不断发展,其主导词在变化中深化着本源性思之运作:从此在之本真与非本真生存之境,昭示“存在之意义”,到从存在之遮蔽与去蔽来构筑“存在之真理”,最后达到本有居有的“大道之言说”。在这些称为路标的先导词中,后一路标是前一路标的进一步深化,前一路标成为后一路标的暂先展示。相对在后的路标更为本源地通达存在之境。海氏现代技术之问以其思之缺席与思之召唤的思想张力,成为从存在之真理向大道之言说的过渡与桥梁,成为海氏本源性思的重要阶段。
具体说来,现代技术之追问,揭示为传统形而上学思之缺席的典型形式—“座架”与天地神人“映射游戏”的思之召唤的强烈对称。“座架(Gestell)”与壶之聚集为“赠品(Geschenk )”两者皆有“聚集(Ge—)”之义,但聚集的方式不同。前者是以强制着限定存在者的方式聚集,后者以天、地、神、人四元以各自的方式相互映射,并以各自方式反映自身而进入本己之中的聚集。这种聚集还直接构成了“大道(Ereignis)”这一后期主导词的非形而上学化的内涵。这两者以极其强烈的对照,凸现了思之缺席与思之召唤之间的张力。考虑到海氏对其思考的理解:思的事物只是为了带来震惊。思想家不是提供一套思的规则和原理,相反地只是蕴造情境,让人去思。海氏对现代技术的思考,形成了他本源性思之过程极为紧张、精彩的华章。
从海氏的运思方式看,其技术之问是其本源性思的重要阶段;从其探索的内容看又是特赋现实性的追问。真正的思想家总是思考其具有时代特征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在随便谈论现实问题时,就具有现实性。只有其思想触及到现实问题的根本,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海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根本上是对现实问题的本质的关注。当他揭示现代技术是具有天命性质的座架所显现的思之缺席的极端形式时,我们才会体会到现实性的真正分量。
因此,那种认为海氏早期是现象学存在论分析,后期转向现实问题的谈论,实际上是人为地割裂了海氏的运思方式与现实问题的关系。其实,海氏贯穿全过程的本源性思与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内在合一的显现。在最现实的世俗的问题中蕴涵着思的张力,现代技术之问又是思之现实性探索的典型。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之追问给我们带来了震惊,但是对于能否通达思之本真状态克服技术之危机,海氏的彷徨、犹豫、矛盾显示出思之无奈和忧虑。
在《技术之追问》中,海德格尔认为“座架”具有二义性。“座架”以其强制性,控制着人与物的功能性展示方式。同时,“座架”毕竟是“大道(Ereignis)”的遮蔽性发生方式,遮蔽就意味着去蔽的可能,因此,在对“大道”的呼求中通达一种可能性:它把座架的纯粹支配作用克服到原初的居有中,从而使技术对世界的统治关系转变为服务关系。于是,那里有危机,那里就有挽救的希望,似乎救渡就植根于技术之本质中。但是,随后在《什么召唤思?》中,海氏又认为他只能召唤他人去思,虽然最激发思的是我们还没有思,但能否真正通达思之本真状态,那就事随人缘了。况且从思的缺席到思的在场所经过的不是逻辑的推论而是“跳越”,跳向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境界。而这种跳越境界之开启只有个人体验了。那么“跳越”如何可能呢?接着,海德格尔在《泰然任之》的演讲中, 给出了一种跳越的方式, 那就是“泰然任之(Gelassenheit)”。但考虑到海氏认为“座架”为西方历史的命运,“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委员会,没有任何举足轻重的政治家,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没有任何经济及工业首脑的协商会议,能够刹住或者控制核时代的历史进程。没有一个单纯的人类组织有能力夺得对时代的统治地位。”(注:海德格尔:《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38页。)也就是说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控制不了的一种东西。由此,海德格尔对克服现代技术的危机所作的最激进的现实可能性阐述:“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对象,却在所有切合实际的利用的同时,保留自身独立于技术对象的位置,我们时刻可以摆脱它们。”(注:海德格尔:《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39页。)实际上成为不可能。如果一定要说可能的话,至多只能理解为“泰然任之”心态的改变。但是这种仅仅改变看世界的眼光的禅宗式的顿悟,能保证现实技术问题的解决吗?当海氏认为我们可以把技术限定在一定范围,并对其越权加以拒斥时,海氏似乎忘记了我们正生活于被他称谓座架所构成的技术世界中。
当晚年他在接受《明镜》记者访问时,干脆把这种“跳越”的奇迹给予上帝:“哲学将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任何直接变化,不仅哲学不能,而且所有一切只要是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做到。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注:海德格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30页。 )他又悲壮地认为思考至多可以唤醒大家准备期待上帝,这充分说明海氏现代技术之问在改造现实技术世界时所昭示的思的无奈。当然,即使在这种无奈中,也显示出他对现代技术世界的深刻忧虑和关注。海氏去世前两天,他在一封写给其同乡弗赖堡大学神学教授贝斯哈德·韦尔特的信中,还念念不忘对思之缺席的忧虑和思之召唤的急迫:“因为急需深思,在技术化了、形式化了的世界文明时代,是否以及如何还能有故乡。”(注: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6页。)
因此,严格地说,海氏的探索只是给我们带来震惊,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并以其思的尝试,召唤人们虔诚地追问、认真地思考现代技术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