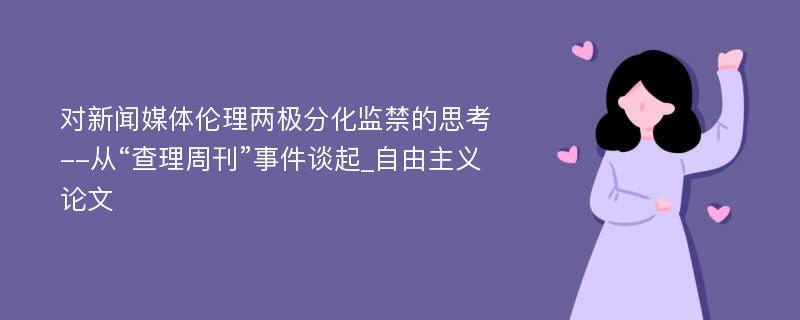
期刊所涉媒介伦理极化的嵌顿现象思考——由《查理周刊》事件所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媒介论文,伦理论文,查理论文,周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因刊登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造成包括主编在内的12人死亡,此次事件以其血腥性震动世界。这是自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12幅将穆罕默德描述为恐怖分子的漫画,从而引起伊斯兰世界抗议怒潮以来,又一次因一份期刊所引起的超国界、超常规震动。此次事件除了说明在网络时代,作为传统媒体的期刊,其社会文化地位并没有因网络的勃兴而消失殆尽以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亦可以引发更为深刻的伦理学与传播理念方面的思考。 一、西方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去和谐趋向 和谐是多数宗教主张的理念,但是在现代传播语境下,西方式的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去和谐趋向在世界范围呈现。《查理周刊》事件所涉及的双方,都有各自的固有理念:以人权为基础的新闻自由和以信仰权为基础的宗教信仰。2006年《查理周刊》转载《日德兰邮报》所载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由此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结怨。《查理周刊》对伊斯兰的辛辣讽刺让其主编斯德凡·沙博尼耶屡次受到死亡威胁,但沙博尼耶认为只有人类和言论自由是神圣的,因此他始终坚持“自由又争议的漫画”。沙博尼耶对自由言论的信念根植于法国式的新闻自由传统。1789年8月法国颁布了《人权宣言》,赋予公民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新闻自由被视为法国民主的根基而被法国人所珍视。和新闻自由一样,讽刺漫画在法国同样具有久远的历史,以至于《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这些记者,他们的所有作品都是对言论自由的捍卫。”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也撰文指出:“那些人之所以被杀,仅仅因为他们是记者,仅仅因为他们捍卫自由,仅仅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理念。”[1]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主要宗教之一,为了避免偶像崇拜,禁止安拉的绘画和雕像;同样任何绘制和雕刻穆罕默德“圣像”的行为都被看做对先知的不尊。因此即使《日德兰邮报》刊载的部分穆罕默德漫画“无伤大雅”,但当代以研究媒体伦理著称的学者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Clifford Christians)在分析时指出:“对逊尼派来说,即便制作穆罕默德画像的行为也是亵渎,所以并不奇怪,很多穆斯林只因为这一个原因就被激怒了。”[2]和《日德兰邮报》一样,《查理周刊》不仅刊登了穆罕默德的漫画,而且这些漫画是讽刺性的,正如《纽约时报》发表《我不是查理》一文认为,讽刺和侮辱有着明确的界限,但《查理周刊》对穆罕默德的讽刺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侮辱。因此罗马教皇方济各在评论《查理周刊》事件时指出:“如果我朋友Gasparri博士说了诅咒我母亲的言语,他会吃到一拳……一个人不能挑衅,一个人不能侮辱别人的信仰,一个人不能取笑别人的信仰。”[3] 《查理周刊》所坚持的西方式新闻自由以及伊斯兰教所坚守的宗教信仰理念都有深厚的传统,以至于两者发生碰撞并产生冲突的时候,传统成为两者身上的包袱,沉重的包袱压制了两者向彼此走近一步进行对话和和解的努力,成为横亘在西方式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沟壑,使得两者在去和谐的轨迹上加速运行,成为西方与中东地缘相近而理念相背的一个矛盾场域。 二、以期刊为节点产生恶性嵌顿的文化新现象 《查理周刊》和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去和谐态势,集中于一个文化平台——期刊,因之走向激化,这是一个传播效果严重外溢、值得关注的新现象。矛盾双方在“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两种理念互不相让的极端情况下,形成一种类似于生物肌体的恶性嵌顿(incarceration)现象。 嵌顿是一种突变的肌体卡位反应,即两边的肌腱都有神经,只因相关神经极度痉挛而造成环形绞榨,最终致死肌体。社会嵌顿(social incarceration),则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它产自于信息不对称和网络的放大功能,使得经传媒中介的事实(mediated reality)在某种情况下形成失控的信息痉挛,恶性绞榨社会肌体,造成社会坏死性嵌顿,并形成神经链式传导,深度损伤社会远端与文化深层。 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在当今社会是一种广泛现象。文化嵌入宗教,或宗教嵌入文化;文化嵌入冲突,文化嵌入暴力等等,综合显示为文化衍生为广泛的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查理周刊》和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具有文化嵌入性,又显示为社会嵌入性。《查理周刊》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涉世宽泛性和从容性,从某种深刻的角度影响着社会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期刊,它具有文化聚合性作用、延续性功能以及累积性价值,这些桀骜特征的叠加在网络传播中被放大,使得作为社会器官之一的《查理周刊》由诱发隐性的文化痉挛,发展为诱发恶性的社会绞榨性嵌顿。同时,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将深植于文化传统中的宗教信仰作为袭击事件的道德盾牌,力图将自身的行为“神圣化”和“合理化”。《查理周刊》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宗教信仰的坚守都嵌入到文化的深层肌理,试图从文化土壤中找到自身行事的依据,从而让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媒介伦理的极化和宗教信仰的极化,都是对文化和文明的嵌顿。宗教信仰的极化在此搁置不论,学界一般认为,从媒介伦理的角度来看,在此事件中,《查理周刊》对西方式新闻自由的坚持达到偏执的程度,成为绝对自由主义的表现,以至于有学者在评析此事件时认为,“西方‘泛言论自由主义’似乎又在作祟”。[4]《查理周刊》对新闻自由的偏执性的坚持导致媒介伦理的极化,而这种偏执型的新闻自由反映在一个非主流的期刊平台上,进而引发世界性后果,这需要引起对媒介伦理极化现象的重视,并且对其历史根源和哲学传统进行某种学理厘清。 三、媒介伦理极化的若干哲学根基溯源 如上所述,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法律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国家,《人权宣言》第十一条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5]这种“新闻自由”被传播学奠基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称之为“传媒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任何理论都不是经由理论家的头脑凭空产生的,“自由至上主义与其他有关大众传媒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的理论一样,也是哲学原则的产物。这些哲学原则为传媒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了基础”。[6]而孕育法国新闻自由思想的哲学原则主要是当时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同时也受到世界其他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 据施拉姆的历史分析,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阔了人们的思想、撼动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同时宗教改革进一步瓦解了教会的权威,培育了人们自由思考的意识,而中产阶级的出现提出限制王权和贵族特权的要求,因此它强调自由契约的重要性,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为自由至上主义“积累了经验”。17世纪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哲学以强调人民意志的人民主权理论为核心,对后世的自由至上主义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他(洛克)用过的很多词汇都可以在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中找到”。[7]而其影响最大的则是启蒙运动。人类理性成为启蒙运动运行的动力,亦是启蒙运动进行的目的,“启蒙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外界束缚,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解决宗教、政治和社会问题”。[8]在施拉姆等人看来,正是16世纪以及17世纪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依据这些经验生发出来的原则最终又指导了人们的实践,以至于“到了18世纪末,各国基本法都将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奉为圭臬,并以宪法条文的形式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9]法国《人权宣言》正是在依据这些经验所产生的原则指导下实践的产物。 自由主义哲学以及自由主义至上理论都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认识上,“人是理性的动物”以及“人本身就是目的”被认为是自由的根基,这种看法强调了人的理性和人本身的重要性,使其摆脱了上帝的束缚以及强权的压制,推动人类走向康德所谓的“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启蒙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笛卡尔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施拉姆等人认为,“他坚持理性至高无上,向权利和权威的整个信仰体系发起挑战”。[10]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提出“普遍怀疑”的主张,强调了人类的理性,开创了“欧洲理性主义”哲学。 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哲学在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的推动下,建立了欧洲大陆自由主义传统,哈耶克(Hayek)称之为“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或建构论型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有别于被哈耶克称为“进化论的自由主义”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进化论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首要性,强调要用法律来保护个人,使其免受任何专断强制,因此,继承和发展了源自古希腊的‘法律下的自由’和‘法律下的政府’的政治原则”,[11]它推崇和承认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但“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则拒绝承认理性的有限性,因此“导致把所有的文化现象都看做是可以由人的理性来刻意设计,并宣称可以根据一个预先确定的计划对所有自我生成的制度进行重构”。[12] “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人的思想,因此法国主流社会固执地主张新闻自由并褒扬讽刺漫画。《查理周刊》正是生长于“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的土壤上,其对新闻自由的偏执以及所导致的媒介伦理极化,无不是受到这种自由主义的浸染,以至于其主编沙博尼耶曾认为,“如果我们能嘲讽法国的一切,如果我们能谈论法国的一切,但伊斯兰或伊斯兰主义的影响除外,那很讨厌”。主编的认识以及《查理周刊》的所为深刻地反映了“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所熏陶出的蔑视一切权威、重估一切价值的信念。《查理周刊》不仅仅只是蔑视和重估伊斯兰教,其更进一步地将评价推动为执行,试图对周围的世界进行重构,沙博尼耶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到底,直到伊斯兰教像天主教一样被庸俗化”。用讽刺漫画的力量使伊斯兰教庸俗化,在《查理周刊》以及法国人看来,是对法国社会的一种“设计”,是人类理性的最大彰显。因此,可以看出,《查理周刊》对绝对新闻自由的坚守,根植于“欧洲大陆型自由”哲学传统,对理性的绝对推崇导致了媒介伦理的极化,最终致使文明的嵌顿。而纾缓文明的嵌顿,则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方面西方伦理界不乏有之,法国伦理哲学家伊曼纽尔·勒维纳斯(E.Levinas)和他提出的“他者”伦理就是其中有影响者。 四、“他者”伦理对媒介伦理极化的纾缓 与“建构”和“消除”两个极端相共存的,是“纾缓”理念,它可以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中庸”(Moderate)理论中找到源头,而勒维纳斯则进一步从西方哲学坚守的本体论角度作了思考。他认为,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是一”的观点奠定了本体论的哲学基础,而柏拉图(Plato)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是在“存在是一”的观念上的具体走向,甚至到黑格尔(Hegel)的逻辑学以及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基础本体论”,西方哲学都没能跨越本体论的固有轨道。而本体论以“同一性”为追求,在勒维纳斯看来,本体论对“同一性”的追求是以牺牲“他异性”为代价,同一性像炼丹术一样将他异性“融合”为自我。“本体论哲学的同一性就是把存在者的自由和同一性等同起来,他者就是进行同一的障碍,他者的存在使我的自由出现了问题,因此,必须征服他者,整合他者,在征服和整合之后,真理获得了胜利”。[13]这种同一性思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此会导致暴力冲突等人类困境和危机。 在勒维纳斯看来,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本体论的轨道,因此《查理周刊》所坚持的新闻自由,以及新闻自由所根植的“欧洲理性主义”和“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都是本体论哲学的产物,导致“欧洲理性主义”对理性的绝对推崇以及“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绝对坚守。而不能嘲讽的伊斯兰教成为站在对立面的他者,阻碍了《查理周刊》所坚守的绝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实施,因此受到同一性思维趋势的《查理周刊》必须要征服伊斯兰教,让伊斯兰教和法国一样世俗化以达到伊斯兰教和《查理周刊》以及法国的同一性。 具体分析来看,按照勒维纳斯的观点,《查理周刊》刊载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是以自我的身份,试图对作为他者的伊斯兰教的同一化。本体论哲学对理性的绝对推崇以及“欧洲理性主义”哺育的“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建构了《查理周刊》的绝对自我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将不同于普遍世俗化欧洲的伊斯兰教置于他者的地位。而拒绝世俗化的伊斯兰教通过让自己成为禁忌话题的方式,展现出对《查理周刊》所坚持的新闻自由的不合作和反同化,因此沙博尼耶认为,《查理周刊》有讽刺我们自身的自由,也有讽刺基督教的自由,自然也要有讽刺伊斯兰教的自由。当期刊讽刺伊斯兰教而后者没有反抗,那么则实现了前者对后者的同化。而“将他者同化和排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是地地道道的暴力,目的在于消灭他异性的他者要么据为己有,要么进行贬低,使之驯服,最终消灭掉”,[14]《查理周刊》刊登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正是为追求同一性而产生的某种文化“暴力”。 《查理周刊》事件和勒维纳斯所观察的众多人类困境和危机一样,在勒维纳斯看来,其症结在于西方的本体论哲学传统,因此要克服人类的危机和困境,就必须清除本体论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清除这一思维方式的关键在于构建“绝对的他者”。勒维纳斯在具体的论述中认为,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就是探究世界的本质和本源,同一性思维排除了他者,将他者融入到“自我”之中,从而压抑他者或消灭他者,清除差异之后宣称同一性和整体性。即使胡塞尔(Husserl)和海德格尔努力论证他者的存在,但这种存在还是被勒维纳斯看做是“第二我”,而不是存在于“自我”意识之外的独立存在。 因此,勒维纳斯将“他者”分为传统意义上受到“同一性”迫使而被还原为“自我”的他者,以及不可还原的“彻底”的他者。勒维纳斯认为,前一个他者是自我的他者,在和自我的关系中被消解并还原为自我;而后者则是“无限的、彻底的和绝对的他者”,具有绝对他异性而不可被还原,从而绝对地独立于自我而存在。在勒维纳斯看来,“伦理产生于他者的显现,或者正如他在第一本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年出版)——中说的那样,伦理产生于他者‘面貌’的显现”。[15]因此他将其建立的“他者”伦理学定义为:“我们把这种由他人的在场而对我的自发性提出质疑称之为伦理学”。[16]“他者”伦理学有别于以自我的主体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学,而是将他人看作是对自我的限制,自我必须回应他者的呼唤,因此自我是被动的,必须为他人负责。 勒维纳斯所提出的“他者”伦理学思想将“我”对他者的责任提到了无限的高度,强调他者对“我”的要求是“命令性的”,“我”必须服从,因此“这种(他者对我的)意义先于我的自由,超出本质”。[17]笔者认为,为了纾缓媒介伦理极化以及宗教信仰极化所造成的对文明的嵌顿,《查理周刊》和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他者”伦理的合理要素。《查理周刊》和伊斯兰极端势力都有承认并尊重对方的“绝对的他者”地位的必要。《查理周刊》应该走出传统西方哲学所造就的本体论窠臼,放弃将伊斯兰教同一化的思想,不能以讽刺漫画的方式强迫他者接受“自我”所坚守的西方新闻自由理念;同样,伊斯兰极端势力也须意识到作为他者的《查理周刊》的世俗化现实,而不是以暴力制服他者接受“自我”的宗教信仰。《查理周刊》和伊斯兰极端势力都应该以他者的需求和召唤作为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而不应当作有条件的假言律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应该承担起自我对他者的责任,而不是以讽刺漫画和恐怖袭击将对方置于敌对位置。综合以上两点考虑,借鉴和适用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不失为纾缓伦理极化现象以及文明嵌顿症状的一个思路。 勒维纳斯作为法国著名的伦理哲学家,吸收了希伯来思想中的精髓,将他者和责任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按照他的观点来看,西方本体论哲学(包括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孕育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使得新闻自由和宗教信仰将对方置于必须被自我同化的他者地位,从而导致两者矛盾的不可调和。由法国哲学(主要是笛卡尔“唯理主义”)所孵育的“欧洲大陆型自由主义”孕育了绝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查理周刊》秉承这种新闻理念走向了媒介伦理的极化,最终导致《查理周刊》事件。蕴含走向暴力因素的法国哲学,同样也孕育了防止暴力事件的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走向现代化路径的清醒者可以择善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