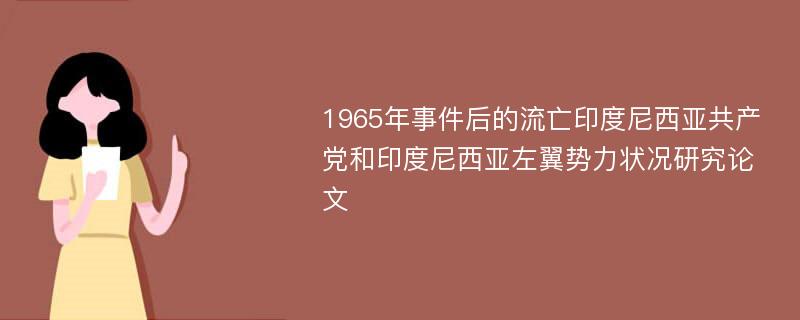
1965年事件后的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状况研究
张猷※
摘要: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暴力事件的毁灭性打击后自行解散,幸存党员流亡国外。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分散在世界各地,主要以文学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形成了成果丰富的“流亡文学”。1998年以后,1965年事件的幸存者和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日渐活跃,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影响从国外发展到印度尼西亚国内,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目前,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社会已具备一定的影响力,1965年事件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印度尼西亚国内极端右翼组织的存在仍使印度尼西亚左翼的活动面临不小困难。
关键词: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左翼;流亡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于1920年建党,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1965年“九·三〇”事件发生前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数量达到350万,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1965年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陷入混乱,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印度尼西亚极右军方势力在混乱中迅速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并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从此一蹶不振。苏哈托政府此后修改了印度尼西亚历史,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进行污蔑性宣传,颁布了禁止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传播的法令。直到1998年苏哈托宣布辞职,意识形态的束缚才逐渐松绑,但禁令仍未废除。
两下总算是谈妥了,冯一余每天出20块钱,周一到周五,大爷负责帮他占住车位。冯一余怕夜长梦多,提出先付一个月的钱。大爷却不要,说,占一天算一天,而且要先占后付钱。冯一余坚持先付钱后占位,左说右说,大爷才收下了头一次的20块钱,揣到口袋里,走了。
目前,福建省聋人高等院校仅面向省内招生,但是省内的聋人可以选择报考全国其他省市的的高等院校,因此,每年的生源有限。但省内仅有一所院校招收聋人大学生,且专业有限,与专业较多且面向全国招生的其他本科院校或专科院校相比,竞争优势不明显,优秀的聋人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省外规模较大的本科院校。除此之外,全国的聋人高等院校采用的都是单独招考的方式,每个院校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都不一样,考生可同时选择多所院校报考。福建省的现行招生规定是一次录取,无补录机会。这就会出现优秀的考生同时被多所院校录取,一旦其放弃省内的录取资格,就会挤占原先可递补考生的入学机会,显失教育公平。
1965年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活动大体可分为3个时期:即1998年以前的国外流亡时期、1998—2010年左右的左翼政治在印度尼西亚恢复时期以及2010年至今的左翼政治形成一定影响时期。首先,1965年以后,在迫害中幸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大部分流亡国外并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发挥着微弱的影响;其次,1998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国内左翼势力的活动渐渐活跃,被关押的1965年事件受害者逐渐被释放,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声音也传回印度尼西亚国内;再次,2010年以来,迫害幸存者开始为1965年被迫害的遭遇要求人道主义说法,而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则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印度尼西亚政治中的自由和民主变革。
因此,当差分隐私保护参数为ε′(由算法的7~13行计算而得)的相邻评分矩阵上的Laplace噪声之比为
尽管当前印度尼西亚左翼政治已形成一定气候,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印度尼西亚公众领域仍受压制。虽然从2015年印度尼西亚“1965年事件50周年纪念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以来,“共产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恐惧症”“共产主义东山再起”等词汇就不断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公众视域中,然而,作为组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早已消失。一方面,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情况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描述的状况相似——“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印度尼西亚游荡,印度尼西亚极右组织指责自己的政治对手为共产党;然而,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幽灵”又是一个无法向世人宣告自身存在、甚至无力有效组织起自身话语的“虚假幽灵”。因此,1965年事件幸存者以及左翼势力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活动仍面临着不小压力。
本文拟按时间线条梳理1965年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左翼政党的活动情况,包括:第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的流亡情况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第二,1998年苏哈托政府倒台后,幸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和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的活动及其影响;第三,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反共”势力的情况,印度尼西亚左翼面临的主要困境,并展望印度尼西亚未来的政治趋向。
一、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的军政府迫害中毫无抵抗之力,在短时间内便失去了绝大部分有生力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党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二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组建起独立的军队力量。1965年政变的发生,只有少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层牵涉其中,主要是总书记艾地和以其心腹夏姆(Sjam)为核心的秘密局① John Roosa.Pretext for Mass Murder: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New Perspective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6,p.117. 。一方面,大部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对政变并不知情,情报的脱节造成了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共产党员以及相关“亲共”人士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就被抓捕和杀害;另一方面,尽管政变发生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民众中有极高威望,能够有效地发动群众运动,但其几乎没有能够依赖的独立军事力量。于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迫害中几乎处于等着被杀害的状态,在艾地被处死之后更是群龙无首。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由于具有机器人手术执照的低年资医师较少,本研究仅 3 名医师受训,且在临床实践阶段完成膀胱尿道吻合仅 9例,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倚,需加大样本量进一步证实。此外,据研究报道,机器人辅助前列腺癌根治术中膀胱吻合的步骤需要至少 17例手术才能达到平台期[13],本研究中每位医师仅完成 3例膀胱尿道吻合,尚无法明确虚拟培训对学习曲线的影响,需增加实战例数后再进行分析。
苏哈托刚下台时,被压抑已久的印度尼西亚社会迅速反扑,被长期压抑的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少数派(如华人)成为印度尼西亚新政府上台执政的主要支持力量。改革力度最大的是瓦希德政府,他在任期间积极推进民族和解和国家民主建设进程,取消了部分歧视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瓦希德甚至承诺印度尼西亚官方将对1965年的受害者公开道歉,并重新修订被苏哈托“抹黑”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历史、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是,瓦希德的改革进程受到了来自印度尼西亚政治上层的强大阻力。在苏哈托时期,有大量的受保护的精英阶层遗留到了新时代,他们掌控了能源、交通、对外贸易和金融等部门的大部分资源。由于政治斗争中污蔑和丑闻的骚扰,瓦希德最终在2001年被弹劾。继任的梅加瓦蒂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著名的“反美亲中”、亲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左翼政治家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所属的民主斗争党虽然也是印度尼西亚世俗政治力量的重要代表,但是,面对政治上层的巨大压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幸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在印度尼西亚的处境在梅加瓦蒂在任时期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总归来讲,从苏哈托下台以来,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和幸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的活动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愈来愈显示出影响力,不过,当代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在国内仍面临不小的困境。虽然印度尼西亚国内顶层的政治势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民众中的左翼力量来对抗其极右的保守主义对手,但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亲共”左翼仍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出声音。
在流亡人员中,影响最大的是孙达尼和艾地兄弟。孙达尼从中国北京开始流亡,后移民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教授印度尼西亚语和文学,直至1979年去世。在流亡期间,他写成4部小说和3部自传,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俄语、爱沙尼亚语、中文、捷克语、德语、越南语、荷兰语和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有一定的世界性影响,是印度尼西亚流亡文学的重要代表④ Dived T.Hill.“Knowing Idonesia from afar:Indonesia Exiles and Australian Academics”,in Review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ffairs,Vol.43,No.1,2009,p.154,p.154,p.158. 。艾地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沙汉在1965年事件期间正在莫斯科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得以逃过一劫。硕士毕业后,他到越南渡过了长达17年的避难生活,并在此期间完成了越南语和越南文学的博士学位。1984年,他移民荷兰定居,直到2007年去世。1998年后,他有4部短篇作品集和诗歌集流传回印度尼西亚,并在雅加达出版,即1998年的《越池为23个名字哭泣》、2001年的《战争与花》以及最后出版的2006年的《从莫斯科到河内间的爱、战争和幻觉》和《感谢真主浪漫回忆录》⑤ Asahan Aidit.23 Sajak Menangisi Viet Tri,Pustaka Jaya,Jakarta,1998;Perang dan kembang,Pustaka Jaya,Jakarta,2001;Cinta,Perang dan Ilusi Antara Moskow-Hanoi,Lembaga Humaniora,Depok,2006;and Roman Memoar Alhamdulillah,Lembaga Sastra Pembebasan,Jakarta,2006. 。这些文艺作品的出版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重新回到印度尼西亚公众的视野中,推动着印度尼西亚国内对1965年创伤记忆的反思。梭伦的活动更为频繁,他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更大。梭伦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迫害期间正在中国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教授印度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文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辞职到农村避难,并最终获得了到法国的政治避难授权。在避难期间,他曾用25个假名在印度尼西亚报刊媒体上发表各类文章,在印度尼西亚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自传等7部作品⑥ Dived T.Hill.“Knowing Idonesia from afar:Indonesia Exiles and Australian Academics”,in Review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ffairs,Vol.43,No.1,2009,p.154,p.154,p.158. ,这些作品还流传到苏联、中国、英国、保加利亚、荷兰、德国和法国。印度尼西亚著名艺术家丁丁·乌利亚(Tintin Wulia)还根据梭伦的生平拍摄了一部名为《归家》的纪录电影,记载了他的流亡足迹,并对他进行了采访。
由于流亡生活的恶劣环境以及党内遗留的分裂问题,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无法形成政治上统一的声音,也无法进一步扩大影响。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主要依赖国外政府或同情、支持共产主义的地方组织的援助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会受到援助中断、避难时间到期、护照到期、苏哈托政府的海外政治施压以及海外政治迫害等系列问题,大多数流亡人员都没有固定居所。这些困难都使他们无法有效开展政治活动。
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流亡活动影响最大的是其内部存在的政治分裂问题。1965年事件发生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内部就没有形成政治上的统一,一直存在“亲中派”与“亲苏派”之间的争执,两派间的斗争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处于一种相对分裂的状态⑦ John Roosa.Pretext for Mass Murder: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 (New Perspective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6,p.98. 。“亲中”与“亲苏”之间的分裂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的流亡生活中,中苏关系的破裂不仅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产生了差异,还使得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在流亡路线上也产生了差异,在中国、苏联和欧洲各国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之间没有有效沟通,无法集结起有生力量。正如黑尔(David Hill)所言:“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分裂的群体,它始终存在有政治上的分歧,即便在寻求避难和保护时,它也无法以统一的声音发言。”① Dived T.Hill.“Knowing Idonesia from afar:Indonesia Exiles and Australian Academics”,in Review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ffairs,Vol.43,No.1,2009,p.153.
包括孙达尼和艾地兄弟在内的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尽管他们写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成为国际流亡文学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影响,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化方面。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由于苏哈托政权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高压政策以及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内部的不团结,他们无法发挥更多影响。在苏哈托政权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持续抹黑宣传之下,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通过文学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1998年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流亡文学、1965年事件以及印度尼西亚左翼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幸存者才逐渐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受到关注。当然,左翼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幸存者的活动大多都聚焦在1965年事件上。正如流亡文学研究学者尚伯特—卢瓦尔(Henri Chambert-Loir)所言:“流亡的书籍出版了,证词是有声音的,但它能被听见吗?不完全能,因为流亡的问题,以及囚犯(tapol)的问题还远未解决;这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问题,而非文学的问题。”② Henri Chambert-Loir.“Lock Out:Literature of the Indonesian Exiles Post-1965”,in Archipel,Vol,91,2016,p.145.
二、后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的活动
质疑与建构:著作权法创作激励目的之二重奏............................................................................................司 明 02.77
苏哈托政权倒台后的前10年,被禁止出版和传播的关于1965年事件的研究书籍在印度尼西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外学者的著作均由左翼出版社引入印度尼西亚,其中包括在美国加州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知名学校的知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包括克里普(Robert Crrib)、罗宾森(Geoffrey Robinson)、鲁萨和戴尔—斯科特(Dale-Scott)等。除此之外,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也出版了大量作品,主要包括1965年事件受害者的证词和传记。比如,2006年,索德乔诺(Soedjono)在日惹反抗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反面”:摘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虚假面纱》③ Soedjono.“Yang berlawan”:Membongkar tabir permalsuan sejarah PKI,Yogyakarta:Resist Book,2006. 等。除了这些直接探讨1965年事件的出版物,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还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艾地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的著作。比如,2004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哈斯塔·米特拉出版社在雅加达出版④ Karl Marx.Kapital:Sebuah Kritik Ekonomi Politik,Jakarta:Hasta Mitra,2004. ;2002年,艾地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它的历史背景和前途》在日惹出版⑤ Aidit D.N..Revolusi Indonesia:Latar Belakang Sejarah dan Hari Depannya,Yogyakarta:Radja Minjak,2002. ;2000年,印度尼西亚早期共产主义者陈·马卡拉(Tan Malaka)的著作《从监狱到监狱》也在日惹出版⑥ Malaka T..Dari Penjara ke Penjara,Yogyakarta:Teplok Press,2000. 。当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流亡情况也在此期间受到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关注。赫斯里·塞蒂亚万(Hersri Setiawan)是著名的研究流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作家,他从荷兰开始流亡,游历欧洲各国,收集欧洲流亡的印度尼西亚左翼资料,撰写了大量关于印度尼西亚左翼人员的流亡传记,出版了选集《在沉默的声音中找寻:印度尼西亚流亡左翼》,并被收入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网站① IISG.“In Search of Silenced Voices”,see from http://www.iisg.nl/collections/silencedvoices/index.php. 。
对采购人员应制定监管制度。在制度中明确采购纪律,对相关违规行为制订相应的惩罚措施。同时对采购人员设定奖励制度,通过对采购工作中成本控制、品质控制、执行效率等方面设定相应权重进行考核,考核成绩突出的给予相应奖励。另外平时应定期对采购人员进行培训,加强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的提升。
印度尼西亚左翼女性活动家苏拉米(Sulami Djoyoprawiro)与小说家托尔(Pramoedya Anata Toer)结合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于1999年成立了谋杀受害者研究基金会(Yayasan Pemerhati Kesehatan Publik,YPYK)。该基金会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全岛范围内对1965年事件进行了调查访问性的研究,对屠杀幸存者进行实地采访,收集了第一手口述史料。2000年,基金会开始在印度尼西亚全境范围内调查大屠杀的受害死亡人数,根据访谈以及相关资料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寻找埋葬受害死者的地点,进行挖掘调查。2016年7月,基金会与国际人民法庭(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一同提交了关于大屠杀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修正了2012年对1965年事件死亡人数的估计,并指出在1965年事件中只有部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高层人员参与其中,大多数受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对于事件的发生并不知情,而且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均以间接方式牵涉其中① John Gittings.“Fin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n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Indonesia 1965(Extracts)”,http://www.spokesmanbooks.com/Spokesman/PDF/134Indonesia.pdf. 。苏拉米也于同年将该报告提交海牙国际法庭,海牙国际法庭随后对印度尼西亚政府做出了有罪判决,并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出面进行道歉、赔偿。虽然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是印度尼西亚进入改革时期以来第一位平民出身的总统,并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民主与改革运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65年的遭遇抱同情态度,但是,迫于印度尼西亚保守派在政府中的庞大势力,佐科也未能对1965年事件的幸存者发表官方道歉、进行赔偿。苏拉米遭到印度尼西亚保守组织的攻击和骚扰,她的住宅曾被印度尼西亚极端伊斯兰组织烧毁。基金会挖掘受害者的工作最终也因为内部意见不统一、且时常处于极端右翼组织的威胁中等一系列原因而终止。
印度尼西亚许多左翼活动组织或活动家还开通了自己的脸书或个人主页来宣传1965年事件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印度尼西亚著名左翼活动家温杜·尤素夫(Windu Jusuf)的脸书主页“雅加达孤独者协会(Dewan Kesepian Jakarta)”将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尼西亚的流行元素融合起来。他修改印度尼西亚经典流行歌曲“Angka Satu(第一)”的歌词,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他也通过改编其他流行歌曲来支持印度尼西亚各项人权运动和左翼运动,比如支持印度尼西亚左翼组织针对1965年事件发动的“拒绝遗忘”运动等。2013年,日惹的一群艺术家组织了一个名为“勤劳的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团体,该团体的印度尼西亚语名称为“Pekerja Keras Indonesia”,其缩写形式(PKI)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缩写形式一样。该艺术团体还以镰刀和锤子的经典共产主义符号作为团体标志,这个标志作为反抗官方意识形态的符号迅速在印度尼西亚流传开来,出现在各大博客和推特中,甚至流传到线下,成为T恤、笔记本、提包和水杯等日常物品上的装饰③ Stephen Miller.“Zombie Anti-Communism?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mons of Suharto-Era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 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92. ,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引发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反响。有人认为,该符号标志着共产主义势力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再次兴起;有人则认为,该符号无非是一种对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影响的再消费。迫于舆论压力,印度尼西亚现任总统佐科(Joko Widodo)下令限制与查处该符号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流传。
另外,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也以艺术形式传播1965年事件的影响。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木偶艺术家玛丽亚·莉亚(Maria Ria)和伊万·埃芬迪(Iwan Effendi)对印度尼西亚传统木偶戏进行改造,变成“纸月亮木偶戏剧”(Papermoon Puppet Theatre),并依据1965年受害者和流亡者的遭遇创作了两部戏剧,分别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和雅加达以及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巡回演出④ Marianna Lis.“The History of Loss and The Loss of History:Papermoon Theatre Examines the Legacies of the 1965 Violence in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 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 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62. 。
当然,出版物、虚拟空间以及艺术途径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在印度尼西亚左翼作家维尼马托尼奥(Bagoes Wiryomartono)看来,虽然“在面对历史的问题上,当前的政府仍未准备好”,但是,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的政治活动仍是“测试印度尼西亚民主界限的好方法”⑤ Bagoes Wiryomartono.“The 1965-1966Affairs and Communist-Phobia in Post Suharto Indonesia”,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6995844_The_1965-1966_Affairs_and_Communist-Phobia_in_Post_Suharto_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诸多左翼组织围绕1965年事件的真相、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事件中的遭遇、印度尼西亚军方和相关势力在事件中的作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死亡人数和受害者的身份等展开调查,并尝试找寻流亡和幸存的左翼人员进行口述调研,呼吁印度尼西亚官方对受害者道歉,希望官方与受害者达成和解,并恢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合法地位。
随着21世纪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的活动不再局限在书籍出版上。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公开政治活动仍然缺失,但是,借助信息化媒体,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仍在虚拟介质中以符号的形式间接地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量的左翼网站在印度尼西亚涌现,这些网站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历史进行宣传,反驳苏哈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进行辩护。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创办了著名的流亡文学网络期刊《创作》(Kreasi),该网站定期发表流亡文学作品,对印度尼西亚文学和印度尼西亚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该网站现已停止更新)② David T.Hill&Krishna Sen.The Internet in Indonesia’s New Democracy,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5,p.57. 。希德(Umar Ssid)、库斯尼(J.J.Kusni)和伊布拉希姆(A.Kohar Ibrahim)等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各自创办了个人网站。其中,最活跃及最著名的是“印度尼西亚进步”网站(网址为https://indoprogress.com),该网站至今仍然活跃在印度尼西亚的大众媒体中,有许多左翼活动家和左翼团体在该网站中参与讨论新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中的地位等问题。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工作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开展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健全全国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测体系,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和水平,是强化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监管的有效手段,是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具体举措,对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苏哈托政府倒台后,印度尼西亚不再处于高压统治之下,而是进入民主化改革进程中。虽然旧有右翼军方势力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存在使得印度尼西亚官方仍然没有废除禁止宣传和信仰共产主义的禁令,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束缚的放松,从国内外大量引进的关于1965年事件的各类作品仍然极大地冲击了苏哈托时期建立起来的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抹黑”的历史叙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虽然已经不再能作为一个党派活动,但幸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和“亲共”左翼人员一同构成了印度尼西亚左翼政治活动的主要力量。当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已经失去了政治身份,并融入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中。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试图恢复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合法性,并呼吁印度尼西亚官方重新审视1965年事件。
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外,围绕1965年事件的政治性或学术性会议也周期性地举行,这些会议汇集了诸多国际知名学者以及印度尼西亚左翼成员,还包括许多印度尼西亚军方内部或印度尼西亚诸多伊斯兰组织中支持民主、同情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人士。2016年4月,一次关于1965年事件的纪念讨论会议在雅加达举行,该会议由英国广播公司(BBC)集中报道② Affan H.&BBC-Indonesia.“Simposium 1965:Negara terlibat dalam peristiwa 1965”,http://www.bbc.com/indonesia/berita_indonesia/2016/04/160419_indonesia_hasil_simposium1965.shtml. 。该会议的主持人维德乔沃(Agus Widjojo)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军方成员,其父亲是在“九·三〇”政变中被杀死的将军的后代③ Jakarta Globe.“Indonesia Should Heed Verdict From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ver 1965-1966 Mass Killings”,https://jakartaglobe.id/news/indonesia-heed-verdict-international-peoples-tribunal-1965-1966-mass-killings/. ,会议的发起人是瓦希德在任时期被提拔任用的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前部长、退休将军、左翼政治家潘德贾凯(Luhut Binsar Pandjaitan)。除了两位前将军,会议还包括了印度尼西亚警察前总长、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dhlatul Ulama)和穆罕默德雅迪协会(Muhammadyah)的部分领导人,会议的主体人员是1965年事件的受害者。参会人员交换了揭露1965年事件真相的有利证据,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解决1965年历史事件中疑团的声明。此外,在日惹、东爪哇和西爪哇等地,也有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士聚集在一起举行类似的会议。由此可见,虽然在印度尼西亚上层政治精英中,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的宗教团体中,右翼势力的力量仍然很大并占据着社会主流,但是,左翼势力的政治力量已经渗透到印度尼西亚社会的各个方面,1965年事件以及共产主义成为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挥之不去的“幽灵”,也成为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集结起来共同向社会发出呼声、共同对抗极端保守主义的重要手段。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都在1965年的大规模迫害中遇害或被捕,仍有不少在外访问、留学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以及极少数的逃亡人员躲过了这一劫难。在1965年之前,约有2000名知识分子和学生在苏加诺“亲共”政策的支持下到苏联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学习① Alex Supartono and Lisabona Rachman.“Studi Indonesia di Russia:Sebuah Rumah Sejarah yang Alpa Disinggahi”,in Kompas,6 July 2001. ,部分人到中国访问、学习,还有部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到北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② Dived T.Hill.“Knowing Idonesia from afar:Indonesia Exiles and Australian Academics”,in Review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ffairs,Vol.43,No.1,2009,p.154,p.154,p.158. 。另外,欧美也有一些机构组织甚至“反共”机构——比如在法国巴黎的由美国资助的“文化自由计划”(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也支持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左翼和右翼人员出国,其中便包括部分“亲共”人士③ Dived T.Hill.Journalism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A Critical Biography of Mochtar Lubis(1922-2004)as Editor and Author,London:Routledge,2009,p.150. 。这些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躲过了迫害,在中国、苏联、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开始流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迁往瑞典、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家。著名的流亡人员包括:孙达尼(Ungy Tatang Sontani),著名流亡作家;梭伦·艾地(Sobron Aidit)和沙汉·艾地(Asahan Aidit),两人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迪帕·努桑塔拉·艾地的弟弟;诗人韦斯比(Agam Wispi);散文家舒朗(Kusni Sulang);印度尼西亚著名画家里索博沃(Basuki Resobowo);记者赛德(A.Umar Said),等等。
三、“反共”政治与当代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活动的困境
按照维尼马托尼奥的梳理,印度尼西亚左翼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即从1998年以来到第六任总统苏西洛上台时的恢复时期(1998—2004年)、苏西洛在任的相对放缓时期(2004—2014年)以及佐科担任总统以来的在困境中前行时期(2014年至今)① Stephen Miller.“Zombie Anti-Communism?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mons of Suharto-Era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95,p.295,p.296. 。在1998年即将到来之际,印度尼西亚政治经济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苏哈托政府丑闻频出,苏哈托不得不主动辞职下台,副总统哈比比组成临时过渡政府,开始推进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改革进程。哈比比之后的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均继续推进印度尼西亚的民主改革,两人也面临着不小的阻力。
1966年,幸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开展了最后的活动,苏迪斯曼(Sudisman)接替艾地担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并试图重建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组织。但是,他在做出实质性推进前便被捕并于1967年被处死② 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227. ,剩余的少量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干部逃到东爪哇的南勿立达地区避难。1968年3月,勿立达地区爆发“反共”暴力事件,当地人杀害了60名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相关的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atul Ulama)成员。澳大利亚学者克劳奇(Harold Crouch)认为,这些被杀害的60名教士联合会成员实际上就是残留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印度尼西亚军政府也就此发现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存在,对当地残留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展开围剿③ 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227. 。至此,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销声匿迹。
在当代,随着印度尼西亚左翼政治力量的发展以及印度尼西亚幸存共产党员影响的扩大,印度尼西亚右翼势力也获得了一种新的在民众中发动的政治斗争形式,即“反共运动”的斗争形式。“共产主义的幽灵”“共产主义恐惧症”“共产主义东山再起”等词语近几年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出现频率极高。根据米勒(Stephen Miller)的研究,“反共活动兴起的准确时间已很难找到,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种类型的活动在苏西洛总统第二任期时日渐增多”② Stephen Miller.“Zombie Anti-Communism?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mons of Suharto-Era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95,p.295,p.296. 。经历了苏哈托下台后的动荡时期,2004年,印度尼西亚社会在苏西洛上任后又趋于稳定,激进的左翼政治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影响逐渐减小,右翼保守势力经历短暂的蛰伏后又逐渐抬头。苏西洛是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以来第一位任职期满并在第二期选举中连任的总统,他有着“清白之身”(clean skin)——在印度尼西亚即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权滥用的记录,没有卷入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迫害事件、东帝汶事件等暴力事件中,同时又是军方出身。因此,在米勒看来,苏西洛“代表着印度尼西亚改革时期的两极:他既是改革者,是从1998年以来的新自由民主政治潮流的代表,又是新时期的组织和势力网络的代表。不过,他第二个身份的影响似乎要远大于第一个③ Stephen Miller.“Zombie Anti-Communism?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mons of Suharto-Era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95,p.295,p.296. 。苏西洛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并没有明显的反共性的政治活动,没有在最近几年出现的对1965年事件幸存者的持续性攻击和骚扰,没有公开举行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游行,也没有通过指责政治对手具有共产党员身份而获取政治支持的行动。这种情况是从2014年苏西洛任期满、佐科上台执政后才出现的。不过,佐科的执政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苏西洛时期的右翼政治活力的恢复才是主要因素。米勒认为,右翼势力在苏西洛时期缓慢地恢复了力量,并且通过将“稳定”“发展”作为“自由”的对立面来进行宣传,为日后反共性的政治活动留下了巨大空间① Stephen Miller.“Zombie Anti-Communism?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mons of Suharto-Era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 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 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96. 。平民出身的佐科的上台则是诱导性因素。
印度尼西亚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87%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在后苏哈托时代,其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就是在以世俗政治为基本取向的左翼政治与以伊斯兰教神教政治为基本取向的右翼政治之间摇摆。印度尼西亚世俗政治与神教政治之间的对立又体现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众多流派之间的对立,即支持伊斯兰教教义与世俗生活相对分离的新现代主义派和支持伊斯兰教教义的普世性的理想主义派之间的对立。前者主要以伊斯兰教教师联合会以及穆罕默德雅迪协会等较大的伊斯兰教党派为代表,而后者则分为温和的理想主义派和激进的理想主义派,激进的理想主义派的代表为印度尼西亚反共阵线(Indonesia Anti-Communist Front,FAKI)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Islamic Defenders’Front,FPI),它们是印度尼西亚极端的反世俗政治力量,也是进行“反共运动”的主要力量。由于苏哈托政府的宣传,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被普遍地视为反动宗教的极端势力,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往往被当作危险的、有污点的身份——不过这是与历史不符的,因为早期伊斯兰教教士联合会以及一些较小的伊斯兰教党派都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亲密关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是非宗教世俗政治力量的最大代表② Vannessa Hearman.“The 1965-1966 Violence,Religious Conversions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ft and Indonesia’s Churches”,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181. 。
最近两次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政治力量的对立,即平民出身的佐科与精英出身的普拉博沃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两种伊斯兰教政治教义之间的竞争。军方出身的、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有着人权践踏的政治污点,曾卷入过东帝汶暴力事件和1998年的“排华”事件,从未加入过任何“亲民主的政治活动”,是印度尼西亚右翼选出来的代表③ Edward Aspinall.“Oligarchic Populism:Prabowo Subianto’s Challenge to Indonesian Democracy”,in Indonesia,Vol.99,No.4,2015,p.2. ,印度尼西亚政坛中两大核心“反共”组织即印度尼西亚反共阵线和伊斯兰教捍卫者阵线也公开宣布支持其参选。
2010年,印度尼西亚反共阵线在其网站上宣称自己是由“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队(Indonesia Defence Froces)和国家警察部队(National Police Force)组成”,并“有责任从共产主义或新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中保护印度尼西亚的统一”④ Stephen Miller,“Zombie Anti-Communism?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emons of Suharto-Era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in The Indonesian Genocide of 1965,Causes,Dynamics and Legacies, Edited by Katharine Mcgregor, Jess Melvin and Annie Pohlman,Palgrave Macmillan,2017,p.297. 。在总统竞选期间,印度尼西亚反共阵线还组成了普拉博沃竞选支持社团(Masyarakat Pendukung Prabowo Presiden,MP3)来干预普拉博沃的政治对手。另外,伊斯兰教捍卫者阵线也是印度尼西亚众多伊斯兰教极端右翼团体中的一员。在1998年的“排华”运动中,伊斯兰教捍卫者阵线便在军方和警察的支持下开展了多项活动⑤ Woodward M.,Coleman D.,Yahya M.,Rohmaniyah I.,Lundry C.&Amin A,“The Islamic defenders front:Demonization,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Indonesia”,in Contemporary Islam,No.8,2014,p.154. ,也因多次为政治对手贴上“共产主义”标签、进行暴力攻击而出名,曾经攻击过苏拉米的住宅,也攻击过中爪哇地区为1965年事件幸存者进行健康服务的自发团体。印度尼西亚自由穆斯林知识分子色亚克尤素马(Julia Suryakusuma)曾将伊斯兰捍卫者阵线称为“伊斯兰教的法西斯(Islamofascist)”,许多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也认为伊斯兰捍卫者阵线的活动应该被禁止。虽然以印度尼西亚反共阵线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为首的“反共”组织在印度尼西亚经常性地组织“反共”活动,但是,其活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专门针对共产主义(尤其是在总统竞选期间),其政治目标实际上是维护印度尼西亚极端右翼政治势力。
2)桥吊远程监控系统的完成,使得桥吊的整个运行过程都在掌控之中,实现过程监管,为生产设备实现全系统、全效率的管理奠定了基础,既提高了设备的综合效率,又降低了设备寿命周期的费用。
在2014年佐科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前夕以及2019年印度尼西亚大选前夕,印度尼西亚的“反共”组织多次发动相关活动来误导民情、阻扰选举,比如散布佐科是秘密共产党员的谣言等。伊斯兰教捍卫者阵线也公开指责佐科为“新共产主义”;雅加达市前市长、佐科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印度尼西亚华裔政治家钟万学也被指“有共产主义血统”“亵渎伊斯兰教”从而被弹劾。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时描述的场景:反动的政治势力都为它的对手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仿佛是一个“幽灵”,在沉默中触动着这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温杜总结指出,印度尼西亚“反共”组织的逻辑就是,“自由主义反对伊斯兰法规;共产主义拒绝伊斯兰法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① Windu.“Pengkhianatan G30S PKI,menurut FPI”,https://cinemapoetica.com/pengkhianatan-g30s-pki-menurut-fpi/. 。
由于在当代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原本就有“反共”意识形态存在,所以,极端右翼势力的“反共”宣传策略产生了相应的效果。佐科为了政治选票也不得不公开出面撇清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关系。支持佐科的印度尼西亚左翼组织在其受到极端右翼势力攻击、选票下降时也组织了相关活动来进行反抗,比如2015年举行的“1965年事件50周年纪念会议”等。
我们必须看到,“共产主义的幽灵”甚至是印度尼西亚左翼势力在当代印度尼西亚的影响也非常有限。正如阿斯皮那所讲,“在印度尼西亚,左翼似乎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② Edward Aspinall.“Still An Age of Activism”,in Inside Indonesia,https://www.insideindonesia.org/still-an-age-of-activism. 。印度尼西亚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左翼政党,存在的只是政党倾向民众或倾向精英的政治偏向。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表面上看起来激进的左翼政党最终会在保守政治势力面前妥协。佐科在这种政治处境中的基本做法与苏加诺相似,即在冲突的中心尽量维系两边的平衡来保证自己的政治地位。2015年,印度尼西亚军方举行“1965年事件纪念会议”时,佐科同时公开表明自己没有任何正式的对1965年事件道歉的计划,并声称任何散布他将道歉的谣言是“不负责任的”③ Tempo Co.“1965 Symposium:Gov’t Will Not Apologize,Luhut Says”,https://nasional.tempo.co/read/763592/1965-symposium-govt-will-not-apologize-luhut-says. 。随着2019年印度尼西亚总统选举的结束,“共产主义的幽灵”作为手段也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被禁止的状态仍然不会改变。
A Study on Exile PKI and the Indonesia Lefts after the 1965 Event
Zhang You
Abstract: By the devastating blow of the 1965 violence,PKI was dissolved,and the surviving members went into exile.The exiled Indonesian communist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ontinued to exerted its influence mainly in a literary way,forming the fruits of a wealth of“exiled literature”.After 1998,survivors of the 1965 events and related Indonesian lefts became increasingly active,and the influence of exiles was transmitted abroad to the country,until they had a certain political impact.Currently,the Indonesian lefts have certain influence in Indonesian society,and the 1965 event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However,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domestic extreme rights organization,the activities of the Indonesian lefts still face considerable difficulties.
Key Words: PKI;Indonesian Lefts;Exile
[中图分类号] D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9)04-0086-09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周中坚)
标签: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论文; 印度尼西亚左翼论文; 流亡论文;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