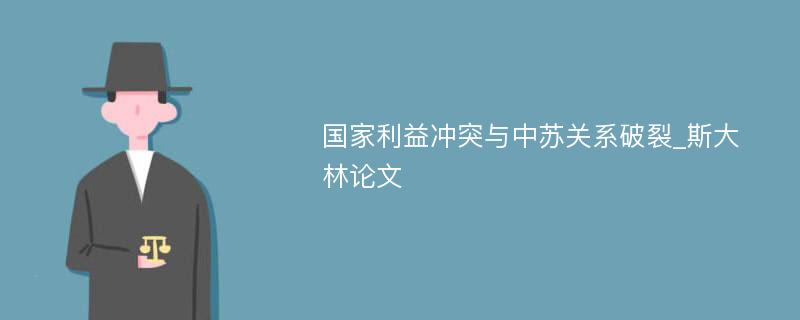
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益冲突论文,中苏论文,关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致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意识形态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对于意识形态分歧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注:参见拙文:《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本文将着重论述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双方关系破裂的因果关系,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行们。
(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刚刚宣告成立,苏联政府便宣布承认新中国。自此,中苏两国便正式建立起一种新关系,并迅速地开展广泛的合作,使双方的关系进入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当时,两国的国家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双方又都基本上采取了互相支持、互谅互让、友好合作的政策,因而关系处得相当好。然而,即使是在“蜜月时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差别,既有互利的一面,又有矛盾,并由此而引发过一些虽然不大,但也不是无关紧要的“磨擦”。
新中国成立伊始,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彻底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毛泽东与国家领导人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希望在废除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妥善地解决中苏两国在1945年签订的实际上也是不平等性质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相关协定。为此,毛泽东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于1949年12月首次访问苏联,以便就这一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商谈。不料,当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中国希望“废旧约”、“订新约”的意见后,斯大林却以必须遵守《雅尔塔协定》为由予以拒绝。实际上,斯大林是不愿轻易地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中方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苏方却不愿放弃有损于中国独立和主权的旧条约旧协定,维护苏联的特权和利益,这就不能不产生矛盾和“磨擦”;斯大林由此而一度冷落毛泽东,毛泽东则因在莫斯科无事可做而牢骚满腹。尽管此事由于毛泽东的力争,加之国际舆论的影响,斯大林后来改变了主意,最终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但它毕竟表明了一个事实,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别和矛盾的,并非“完全一致”。
除这件事外,中苏两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还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来。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要恢复经济、开展经济建设又缺乏经验、资金和技术,因而需要苏联的援助,且援助得越多越好,苏联虽然愿意援助中国,但因受财力、物力所限,不可能完全满足中国的要求。毛泽东、周恩来首次访苏,苏联仅同意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这对中国无异于杯水车薪。后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展开,苏联虽然增加了各种援助,但也很难完全满足中国的需要,致使中苏之间在经济援助问题上不时地发生一些小磨擦,中国抱怨苏联不够大方,苏联则觉得中国要得太多等等。又如,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形势发生逆转之后,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遭受重创,请求中苏两国采取紧急措施援助朝鲜。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反复磋商后,决定组织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同时保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由于中国军队的武器相对落后,当时尚未组建起有作战能力的空军。故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国出兵前要求斯大林出动苏联空军,以掩护中朝两国的地面部队,并与美军争夺制空权。但斯大林却因害怕出动苏联空军会将苏联拖进战争,以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为由予以拒绝,致使中国的志愿军不得不在缺乏空军掩护,而美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开始入朝作战,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再如,中苏建交后,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当时两国都缺乏硬通货,不得不采取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从而为结算带来了困难。由于结算办法不合理,中方吃亏很大。(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页。)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因限于篇幅笔者不一一列举。总之,即使是在中苏关系最好的几年里,双方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别和矛盾的。
其实,出现上述情况很正常。在国际交往中,不同的国家之间,总会有不同的国家利益,中苏两国也不例外。由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加之其他种种因素,双方的国家利益出现差别和矛盾,这并不奇怪。一般说来,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也会对彼此的国家关系产生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则取决于矛盾的性质及双方处理这种矛盾的态度和方法,如果矛盾并不严重,而双方又处理得好,这种差别和矛盾就不会造成彼此间的严重冲突,不会导致双方关系出现大的变化;反之,则有可能使关系恶化。如果其中一方搞民族利己主义或大国沙文主义的话,则对双方关系造成冲击的可能性就更大。就中苏关系而言,毋庸讳言,即使是在“蜜月时期”,苏联对新中国,就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斯大林晚年,如前所述,苏联对中国不够尊重,处理对华事务时主要考虑苏联本国的利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重视不够,且常有损害。
不过,在1957年以前,中苏之间虽不断地发生一些“磨擦”,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导致“蜜月关系”的根本改变,双方的友好合作未受大的冲击。
这当然是有一定原因的。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由于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战略等方面的一致,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基本的、主要的,而差别和矛盾则是次要的、非根本的。中苏两国都是由共产党执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指导,以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立国之本,以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因而在重大的、基本的国家利益上有许多共同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对苏联是很大的支持,有利于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利于苏联反对西方国家的斗争,而苏联的存在和壮大,对中国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开展,也是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中苏双方在国家利益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冲突。这一点,正是两国最初之所以能结成同盟,建立“蜜月式”友好合作关系的扎实基础。诚然,由于民族、历史、地域和文化等方面的种种不同,中苏两国的需要也不会完全一样,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和“磨擦”,但与巨大的“共同利益”相比,只是次要的、局部的、非根本性质的,一般不会影响大局。二是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苏两国基本上都能遵守共同的国际关系准则,且强调和实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求同存异。在1957年以前,双方基本上做到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也做到了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朝鲜战争形势出现逆转后,中国不考虑自身的困难,毅然出兵抗美援朝,主动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责任,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苏联则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堪称慷慨的援助,在国防、外交等方面也给予中国较大的支持。中苏双方基本上都能从大局着眼,以维护大局,即双方的共同利益为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强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避免因为局部性的矛盾而影响大局的事情发生。三是出现国家利益的差别和矛盾时,中苏双方基本上都能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并尽可能做到互谅互让,以避免矛盾的激化。诚然,在处理矛盾和摩擦的过程中,苏方也产生过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中方对此亦有不满和抱怨。即便如此,由于中方从大局出发,或进行适当的抗争,或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而苏方在意识到不当之后,或有所改变,或采取了补救措施,使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如斯大林后来就改变了不愿废除1945年的中苏旧约、另签新约的态度,满足了新中国的要求。又如,在中苏非贸易支付中,苏方多算了中方的钱,后来又退还给了中方。(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页。)再如,苏方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几个实际上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中苏合资企业,赫鲁晓夫上台后,也主动取消了。四是中苏双方都十分注意不把与国家利益无关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开始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中苏两党在涉及斯大林的评价、和平过渡等理论和政策问题时,看法有了不同,双方出现了分歧。但双方在处理这些分歧时,都比较注意不要把与国家利益无涉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是就事论事。因而尽管双方对上述理论、政策上有不同意见,也在内部争论,有批评和反批评,但分歧并没有影响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两年里,中苏之间的“蜜月关系”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所发展。特别是在1957年10月,中苏两国还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方答应帮助中国发展导弹核武器,并允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此举使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因此第二次亲自到莫斯科访问,作为对苏联“慷慨援助”的一种回报。
总之,事实表明,“蜜月时期”的中苏之间虽然在国家利益方面也有差别和矛盾,但因矛盾的性质并不严重,双方又处理得比较好,它并不一定,也没有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
(二)
然而,从1958年春夏开始,上述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部队保持联络,苏联希望和中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共同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并提议,该电台的建设费用由苏中两国分担,苏方出大部分,中方出小部分,电台建成后归两国共同所有,共同使用。对此建议,中方首先考虑的不是经费,而是国家的主权问题。毛泽东与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在中国领土上建设长波电台,只能归中国所有,否则就会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因此,中方答复说,电台可以建,钱由中国出,苏联给予技术帮助,电台建成后归中国所有,但苏联可以使用。苏方却坚持电台建成后归两国共有。双方为此磋商了好几个月,不仅未能就此达成协议,而且双方都因此而感到不满。(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12-113页。)这一风波尚未平息,中苏两国又在所谓“联合潜艇舰队”问题上发生了新的风波。可能是由于中国不久前曾向苏联提出,希望苏联在海军建设,特别是在核潜艇的建设方面,提供技术援助,苏方也乘机于1958年7月向中方提出,希望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苏方的理由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难以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如发生战争,黑海和波罗的海会被敌人封锁,苏联东、北面的领海既不宽阔又不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也好,在中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对两国都有好处。但毛泽东听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转达的这一建议后却认为,苏联关于在中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的要求不仅有损于中国的主权,而且企图以“军事合作”为名控制中国。因此,他的反应非常强烈,不仅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而且对尤金大发雷霆,严厉地批评苏方是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向中国提出政治条件,是想控制中国,是要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等等。毛泽东愤怒而激烈的态度震动了莫斯科,赫鲁晓夫不得不于几天后急匆匆地亲自飞到北京,为苏方辩解。尽管经过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都得到“解决”,苏联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要求,但发生过的争执却使已经出现巨大裂痕的中苏关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13-114页。)更糟糕的是,此后不久,中苏之间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争执。同年8月下旬,为了打击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的蒋介石集团和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炮轰金门、马祖两个近海岛屿。由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内政,故事前并未与苏方磋商。未料,美国对炮击金、马之事反应十分强烈,迅速介入。华盛顿的强硬态度又惹得莫斯科心神不安,赫鲁晓夫一方面对中国擅自行动不满,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此举可能将苏联拖下水,甚至有可能导致苏美大战。因为美国已宣布援助蒋介石集团,苏联是中国的盟国,也不能不表态支持中国。苏联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台湾海峡的战火就有可能引发新的世界战争,导致苏美冲突。尽管由于中国的一再解释和克制,事态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赫鲁晓夫也在公开场合表态坚决与中国站在一起,并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但在私下里,却一再对中国表示不满,并在几个月后单方面中止了1957年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允诺,给了中国沉重的一击。1959年8月,由于印度方面的挑衅,中国不得不在中印边界进行自卫。但当时赫鲁晓夫正积极准备访问美国,他认为,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破坏了苏美会谈前的和平气氛,因此而迁怒于中国。同年9月,苏联不顾中国的一再说明和反对,以塔斯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声明,对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表示“遗憾”。中国认为,这篇表面上表示“中立”的声明实际上是偏袒印度的,并将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因而对苏联的立场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正是从此时开始,中苏围绕着中印边界冲突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与此同时,中苏还围绕赫鲁晓夫访美的问题,争吵得很厉害。苏联出于本国的战略需要,希望同美国缓和关系,并希望通过苏美缓和达到苏美共同主宰国际事务的目的。经过努力,赫鲁晓夫实现了访美。访美之后,赫鲁晓夫不仅宣传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有和平的意愿,而且在访问中国时为美国作说客,也要中国作出努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苏联及其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做法却十分反感。由于美国在台湾驻兵,又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并长期敌视新中国,中国当时不能不把美帝国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不能不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中国认为,赫鲁晓夫热衷于美苏缓和、美苏合作是违背中苏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赫鲁晓夫要求中国缓和对美关系,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放弃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中苏双方关于对美战略的争吵一直持续到中苏破裂之后的60年代末。中国后来甚至把苏联的做法说成是联美反华,公开予以严厉的批判。
除上述各条外,1958-1959年间,中苏之间还发生过其他一些涉及国家利益的争执,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笔者认为,已经例举的事实已足以说明,这两年两国间涉及国家利益的矛盾和争执与中苏此前蜜月时期的七、八年相比,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性质也严重得多了,矛盾和争执已发展为严重的冲突,内部的争论已演变成公开的争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关系不可能不受影响。事实也是如此,到1959年底,彼此间的恶感已大大加深,对立情绪亦日趋严重,两国领导人已很难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
更加糟糕的是,中苏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争执和冲突不仅促使双方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和升级,而且和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致使中苏关系雪上加霜。
尽管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早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已产生,但最初双方都没有把它与彼此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搅在一起,而是就事论事,因而当时未对双方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1958年以后的情况则不同了,由于两国在国家利益方面的争执造成了彼此间的不满和恶感,加剧了彼此间的不信任,各方均开始怀疑对方的动机和目的,甚至认为对方居心叵测。尤其是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问题越来越多时,各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上寻找原因,从理论、路线和政策上挖根子。正因为上述争执的出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把它和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起考虑,开始怀疑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分析以后,毛泽东等人又进而作出判断认为,赫鲁晓夫等人显然已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已发生变化了。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如果不是在理论、路线上出了问题,赫鲁晓夫等人怎么会干出如此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呢?在苏联方面,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实际上也在运用同样的逻辑推理,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违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犯了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等等,于是,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大大升级了,从某一具体问题的观点之争发展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或教条主义之间的根本原则之争,根本路线之争,双方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方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认为真理在自己一方。必须指出,在双方的争执中,尤其是涉及国家利益的争执中,确实存在着“是非”,存在着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作分析;但是,双方都把争执上纲上线,使分歧升级,显然是夸大其辞了,结果反而掩盖了具体问题上的“是”和“非”,不仅分不清是非,反而徒增恶感。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将国家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争执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即一方面,国家利益的争执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和升级,而另一方面,反过来,意识形态分歧的尖锐又加剧了国家利益的冲突,1960年以后中苏争执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既然双方都认为对方的理论、路线错了,意识形态之争不可避免地尖锐化。从1960年初开始,中方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帮助赫鲁晓夫改正错误,决定公开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以所谓“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为靶子,系统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些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虽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所批判的错误观点都是赫鲁晓夫的。苏方当然看得出来,也十分恼火。为对中国进行反击,6月间赫鲁晓夫策划召开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企图对中国进行压服,但中方并不买帐,中共代表团毫不客气地顶了他。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占不了上风,便决定在经济上施加压力。会后不久,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援助中国的所有合同和协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此举进一步将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了巨大损失。尽管中国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但出于对苏联做法的痛恨,便更加严厉地在意识形态方面批判“苏修”。而随着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尖锐化,特别是公开论战的开展,苏联为了进一步打击中国,再次采取行动。1963年,苏联改变过去一贯坚持的立场,毅然同意和美、英两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此举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伤害更大,也比1960年的撤专家、毁协议更使中国恼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终于下决心与苏联分道扬镳,下决心与赫鲁晓夫撕破脸皮,进行更大规模的公开论战,而不再顾及中苏关系会不会完全破裂了。
上述分析表明,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都对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相比之下,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起的作用更重要,更带有根本的性质。不过,国家利益的冲突之所以如此,也和它同意识形态的分歧、争论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有关。这正是中苏关系不同于其他双边关系的地方。
(三)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中苏之间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关系破裂,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本文虽然不可能对此作全面的分析,但有几点则是必须指出的:
第一,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甚至要求中国牺牲本国利益服从苏联,或企图控制中国,因此,中国当时对此进行适当的抵制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如上所述,与一般国际上正常的双边关系不同的是,中苏在国家利益上发生矛盾的争执,不仅仅是因为国情和需要的不同,而是苏联方面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中国,斯大林时期就是如此。赫鲁晓夫上台之初,虽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使中苏关系一度变得平等了,但后来又故态复萌,从1958年开始,依仗其国家实力方面的优势,再次以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企图迫使中国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到60年代,莫斯科则更进一步,不断地在经济上、军事上、外交上向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国力相对簿弱的中国屈服。应当说,这既是造成国家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因,也是这种冲突的实质所在,正如80年代末邓小平所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破裂了,“这不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4-295页。)既然如此,中国就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抵制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这不仅在当时是对的,即使在今天看来,对任何形式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都必须进行适当的抵制和斗争。特别是小国、弱国,因为最容易受到大国、强国的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危害,更应当进行斗争,以维护自身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
第二,中国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虽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所采取的斗争方法并非完满无缺,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应当考虑:一是将国家利益的争执、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同意识形态的争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不仅使问题复杂化,而且使思想发生混乱,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诚然,这并非都是中方的过错,苏方也是这样做的。但毋庸讳言,中方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对意识形态争论更主动、更积极、调子更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应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位,尽量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无疑是应当汲取的重要教训。二是由于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中方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中,态度过于生硬,缺少灵活性,方法也过于简单化。一般说来,不管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发生怎样严重的矛盾和冲突,除了它激化到必须诉之于战争外,都只能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而要进行谈判并使谈判获得成果,双方都要在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同时,作出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妥协。如果一方或双方都采取毫不妥协针锋相对的态度,矛盾和冲突不但得不到解决,而且会越来越尖锐。中苏之间在60年代就常常陷于如此困境之中。今天来看,苏方当然对此有责任,中方也不能辞其咎。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更强调“斗争”,不大愿意作必要的“妥协”,且采取了所谓“大批判”开路的斗争策略,误以为只有彻底批判批臭所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问题才能解决,但其结果却与批判者的愿望相反,越批越对立,越批越不解决问题。历史证明,不仅在解决国家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时不能如此绝对化,而且在解决意识形态分歧时,这样做也是不成功的。三是在处理国际关系、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时,缺乏透明度,内部外交的成份极浓,加之宣传上有很大的片面性,故常常给民众造成错觉,也给对外关系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对中苏关系尤是如此。5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确实比较好,但也不是没有矛盾和磨擦,但由于对苏外交缺乏透明度,宣传又片面,民众看到的只是“一片光明”。甚至1958年以后争执日趋严重,政府仍秘而不宣,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直到关系相当恶化了,民众虽然有所了解,却感到十分突然,无法理解。其实,对外关系的发展时好时坏,本不奇怪,应当让民众及时了解事实真象,这样才能有思想准备,正确对待,否则容易造成思想混乱。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作一点历史反思,却无疑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