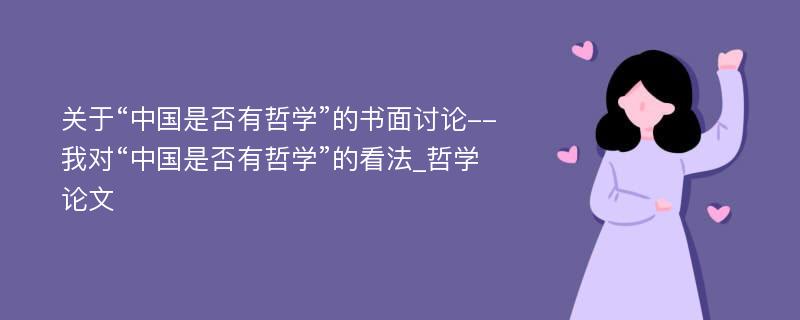
“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笔谈——“中国有无哲学”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有无论文,哲学论文,笔谈论文,我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2]04-0060-012
1.“中国有无哲学”问题的提出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在“哲学”这一舶来词传入中国之前,我们有自己的经学、子学、儒学、道学、心学、佛家的义学,却惟独没有西方所谓的“哲学”。哲学(philosophy)和科学(Science)、宗教(Religion)、文学(Literature)一样都是外来词。“哲学”一词本是日本学者西周在1837年译西语Philosophy而使用的,然而他的本意是要表达“哲学即欧洲儒学”的意思,以“别之于东方儒学也”。后来该词传人中国后却背离了西周的初衷,中国学者使用“哲学”一词恰恰是用来指称中国古代研究“形而上者”的学问。当时正值西学东渐的时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强国梦驱使他们放眼西方,仿照欧美和日本的模式建学立制。中国的传统开始失去制度的依傍,新的知识秩序得以重建。“哲学”这一学科门类的诞生就是新教育制度确立的标志之一。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这标志着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
时至今日,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已存在发展了一百多年。当西方学界提出“中国有无哲学”的质疑后,中国学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受到震撼,长久以来未清醒意识到的西方话语霸权问题凸现了出来。在我看来,“中国有无哲学”的质疑可看作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彰显。自“哲学”传入中国之日起,“中国哲学”就隐含着二者矛盾的基因。如果说“中国”意味着传统,“哲学”意味着现代,那么二者能很好地结合吗?是用中国的范畴讲西方的思想,还是用西方的范畴讲中国的思想?中西方哲学可通约吗?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然不会在20世纪30、40年代就有胡适、傅斯年等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
从20世纪30、40年代至今,“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一直遭到质疑。西方学人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信心十足地宣称:哲学自始至终是为西方所特有的,“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注:德里达语,转引自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载《文史哲》2002年第2期。)。如果中国有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有严密的理论思辨体系吗?有完备的逻辑论证吗?面对西方学人的诘难,中国学者发生无限的感慨,焦虑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一位外国教授戴卡琳(Carine Defoort)所说的:“……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祖先只是一个被收养的孩子,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还是经常不认同他们属于这个大家庭时,我们的中国同行在更敏感的处境中寻找他们自己,他们的学术研究也从他们的结构内部获得意义,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拒绝被哲学‘收养’并拒绝‘哲学’这一‘命名’”(注: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舍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与儒教定义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然而历史的发展不可逆转,中国学人不可能单凭一个拒绝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也大可不必焦虑,藉此机会,我们恰好可对中国学问作一番反思。
2.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岌岌可危,中国学人当然有为自己辩护的需要。然而在论证“中国有哲学”时,却存在着两种应当避免的倾向:
一种倾向是极力找出中国哲学中逻辑、思辨的成分,以期符合西方哲学的模式和标准,得到西方的承认。这种倾向常使中国哲学处于更尴尬的境地。本意是要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为中国哲学争得一席位置,结果却又陷入了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衡量中国哲学的窠臼,以至于使中国哲学沦落到既没有西方哲学鲜明的逻辑、思辨特征,又丧失了中国哲学本色的“两不像”境地。当然,中国哲学确有逻辑、思辨的成分,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中国人不只是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征的阶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0-121页。)虽然黑格尔这段话总体是在表达中国哲学处在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然而却对中国哲学的逻辑思辨特征作了某种肯定。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也说过,中国先秦虽有名学,但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日后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所以名学不是中国哲学的重点,当然不可以此来了解中国之传统思想(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如果硬要以中国哲学具有思辨性作为中国哲学合法地位的根基,显然既不能说服西方也不能说服国人。
另一种倾向则是力求把哲学的定义放宽,一直宽到中国思想可以无拘无束地进入哲学之门。这种倾向的来源可能是由于中国学人苦于中国思想无家可归的焦虑之情的折磨,急于让哲学这个大家庭接纳它,从此褪去“孤儿”的名份,结束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于是拼命地打造一个宽阔的哲学之门,放宽作为哲学大家庭成员的资格。可问题在于:哲学本就是哲学,它有自己的特定规定性。如果执意扩大它的外延只会造成哲学本身的边界模糊,最终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相当普遍的意见即放宽定义的原来尺寸,使它符合中国历史上的思想与学说,就像戴卡琳教授说的让西方哲学大家庭敞开大门,容纳这些无家可归的弃儿,使这个大家庭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家庭’,可问题是,这个原来就拖了长长的历史背影,又一提起来让人浮现出明确边界的词语,如何可能不分彼此地由单门独户扩张而变成大杂院?如果把各自的房屋院墙拆掉,变成天当被地当床,用容纳一切的方法放大边界,是否会反而等于消解了家与家的界限而使人们实际上没有‘家’?”(注: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与儒教定义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所以这种倾向也是不能证明中国有哲学的。
其实,我们不妨转换一下思维方式,既无需极力挖掘相似于西方哲学的中国思想以符和西方哲学,也无需放宽哲学的定义。哲学的本义就是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根据。从词源学上讲,“哲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由Phileo(爱)和sophia(智慧)两字构成,意即爱智慧。中国人也早已认识到:“哲学者,本于希腊语之费罗索费。费罗者,爱也,索费者,智也,合而言之,则爱智之义也。”(注:葛兆光:《穿一件尺寸不合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与儒教定义的争论》,载《开放时代》2001年11月号。)虽然日后关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人们却无法给哲学下一个明确、严格的定义。因为斯宾诺莎说过“一切肯定都是否定”。人们惟恐陷入片面肯定的偏执之中,遮蔽哲学的其他方面的含义,所以在哲学的定义问题上慎之又慎。这也是为什么使一个哲学家最为尴尬的事情就是问他“什么是哲学”的原因所在了。然而尽管人们无法在“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有一点却无法否认,那就是无论在日后的发展中哲学又负载了多少内涵,“爱智慧”的基本含义肯定始终寓于其中。既然哲学为爱智之学,那么岂能说中国元哲学?而且,既然人们用“哲学”来指称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思想,二者就必然存在某种相契合之处。其中道理正如佛教之传入中国,虽然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有很强的融摄力,然外来之物终需有与中国文化相契合之处,方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似乎佛学天生就与中国文化具有一种亲和力,佛学中所宣讲的心、性、命与儒道两家的学问似殊途同归,甚为相投,以至最终形成了儒、释、道共存互补的学术局面。反例也有。基督教虽然也很早就传入了中国,终因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鲜有与中国文化可通约之处,所以至今也难以融入中国文化之中。以上举佛教、基督教之于中国文化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既然国人用“哲学”来指称中国古代的思想,就说明中国思想中有符合哲学基本含义的因子,即“爱智慧”。
3.承认了中国存在爱智之学,也就意味着承认了中国有哲学。当然,同是爱智的学问,中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概而言之,西方哲学的智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思维中的思维,即“纯粹的思”;而中国哲学是一种心性之学,是生命哲学,是关于人格提升、道德践履、生命伦常的智慧。二者在致思取向上存在分歧。中西方哲学同为爱智之学,它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逻辑知识论和超越的心性论成为哲学智慧的两个方面,二者并不存在以一方否定另一方,以一方存在为根据取缔另一方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否则就必然会像《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而“得一察焉以自好”。
那么具体地说,中国哲学究竟有哪些特质呢?梁启超先生说过,“中国先哲虽不看轻知识,但不以求知识为出发点,亦不以求知识为归宿点……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个人?人与人相互有什么关系?”(注:梁启超:《儒家哲学是什么》,载《粱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8页。)冯友兰先生也说过,“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贺麟先生说过类似的意思,他指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注: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0页。)按照牟宗三先生的概括,“‘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Subjectivity)与‘内在道德性’(Inner--morality)”(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总之,中国哲学是关心人、重视人,关乎人的人格提升的智慧。与中国哲学重人格提升、道德修养不同,西方哲学的特征突出体现在它的逻辑性、实证性、知识性追求之中。尤其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主——客二元的认识论框架愈发明显。这种特征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渊源。在西方,哲学与科学有—个由混沌不分到逐渐分野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科学都是以未分化的状态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科学和哲学两个概念常被模糊地使用。随着社会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知识也日益精确化、系统化。—个研究领域一旦形成了精确的系统知识,就立即成为一门“科学”。就这样,当各门具体科学在哲学的胎胞里成熟之后,便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去,确定了各自具体的研究领域,从而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科学似乎总是在征服、占领、前进,而哲学似乎总是在丧失自己的阵地。然而哲学不是“李尔王”,那看起来的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它把胜利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女儿”——科学,而它本身则怀着神圣的永不满足的情愫又继续向前,去开辟新的领地了。科学和哲学生而具有的亲密关系,就成为西方哲学逻辑知识论色彩的历史根据。翻开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常常体会到强大的纯粹理性的逻辑力量,哲学仿佛成了理性、逻辑的化身,哲学家们融铸一生的经历构造出来的庞大体系只不过是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构成的板块式组合,伟大的哲思变成一个个苍白、冰冷的理性符号。黑格尔就曾说过,“哲学家越少将个人感情注入哲学之中,则他的哲学也就越好。”(注:转引自何中华:《超越逻辑:哲学的另一面》,载《临沂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然而,西方哲学的这种纯而又纯的理性思辨却难以安顿人的情感。
当然,中西哲学在心性学、逻辑知识论上的分野,只是就其主要方面和总体意义而言的。中国哲学固然也有逻辑思辨的成分,然而只是昙花一现;西方哲学作为爱智之学,同样不是逻辑、理性一统天下,它也并不存在—个“人的空场”。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也关心人、关心人的心灵的安顿,也追求“诗意地栖居”。读尼采、海德格尔、马克思等哲人的著作不难发现其间渗透着的浓浓的人文情怀。
正是由于中国哲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是以“生命”为中心而展开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所以在表达方式上,它不会也不能采取精确、科学的逻辑语言。隐喻、寓言、诗化的表达成为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中国古代的圣人先哲用含蓄、朴素的寓言、故事,将宇宙、人生之理讲得十分深刻而透彻。老子的《道德经》短短五千言便将天地不可言说之道言尽了;庄子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天地之大美、万物之至理;而孔子的一部《论语》足以让人体悟一生了。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确有其区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质,以西方哲学的标准去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必然得出“中国无哲学”的结论。然同为爱智之学,二者却很好地体现了圆而神与方以智、知与悟、逻辑与超越逻辑的互补统一。不必也不可端着西方的架势,握着西方的话语霸权审视中国哲学。中国学人也不可为追求民族学术的独立而将“哲学”拒之门外。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应该在历史时间轴上超越二元对立的心态,实现中西文化的融汇贯通,让人类乐章中凸显每一个民族的声部,实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