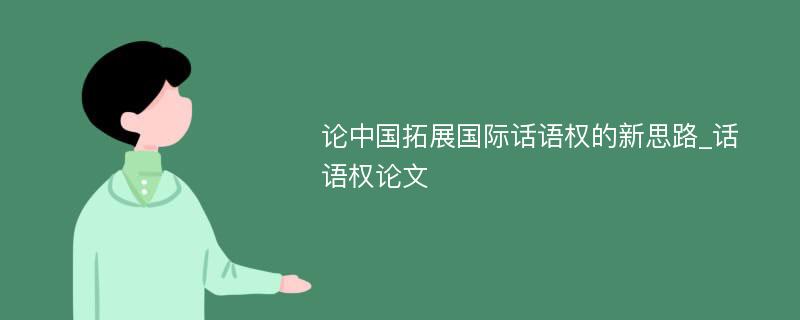
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思路论文,话语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9-03-19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3-0043-4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关系变化中各种新的挑战和机遇。这包括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责任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而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也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的。如何正确地定义国际话语权,提出拓展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要靠自身的力量承担“责任中国”的角色,可以做出的选择是:追求一个比较民主的和多元化的国际体系,调整和发展中国的国际话语,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和其国际地位相一致。
一、国际话语权的定义
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国际话语权”中的“话语”(Discourse)并不完全等同于或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声音”(Voice)。国际话语权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家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些事务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连的,并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就其内涵而言,这一话语权就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如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有人提出新总统上台后的国际战略应是在不确定的未来的发展轨迹上重新确立美国的道德权威。①这就涉及了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和裁判权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以及按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事务、事件,制订国际游戏规则,并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按自己的利益和逻辑作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
国际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具体立场和主张。国际话语权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
第一,话语施行者(或传播者)可以是主权国家的官方机构,也可以是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其所用符号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第二,话语内容是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利益相关或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可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但从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说,话语内容往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拥有的影响所决定。
第三,话语对象是一个“有话对谁说”并涉及如何选择听众以争取或扩大话语效果的问题,而这与话题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听众所在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话语对象可以是外国政府和国际官方组织(如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也可以是国际非官方组织(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国民间组织(如所在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意力量(如议员或议会)等。
第四,话语平台是指话语凭借何种载体或渠道被表达,从而实现话语施行者的权利。就国际环境而言,现代社会中可以使用多种话语平台来凸显国际话语权。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话语平台主要表现有:一是公众媒介,包括传播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如电视、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络等;二是国际会议,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三是主权国家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援助计划,包括政府和民间项目;四是国际的正式和非正式官方互访活动;五是民意机构,主要是相关国家的议会,可通过电话、传真、传统邮件和电子信箱等及时与这些相关国家的议员进行沟通,或面对面探讨相互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六是民间特别活动,可以是因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主体利益问题与国际环境相关所引发的公众集会或游行等活动。
第五,话语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这种反馈可以表现为:一是话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上的反应,毫无效果;二是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被关注或得到相应互动,这涉及话语最终起到了什么作用的问题。前者是与话语权能否实现相关,而后者则是和话语权的增强与否相连。从话语反馈的结果上可以看到,没有作用或结果的话语,就等于是没有话语权。“说话权”和“话语权”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说话权可以体现为寻找发出声音的权利,而话语权要追求其所表达的话语能被确认。如2008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诞生了一个被认同的新集体(“五国”集团),而中国被认为在其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经济规模,中国的声音是自然更大。②然而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靠恩赐得来的,而主要是靠有效和灵活的中国政府决策与行动,还要靠中国非官方组织的努力以及中国公民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运用多种话语平台作为入口,让世界通过这些平台了解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意见。
二、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
中国作为责任大国在当前国际事务中正面临着一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中国所处的地位有些被动。如由于缺乏国际话语权,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价值观念就不被西方所接受,当西方攻击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中国就不得不设法解释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改善;西方攻击中国政治上不民主,中国就不得不设法证明中国是正在向“民主”方向前进等。当前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和外部世界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经济上已发展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惟一和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不折腾”而继续改革开放,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美国奥巴马选举演讲中强调“两场战争”:地球处于危险之中和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包括中国的建设性贡献。③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和发展”的问题,而在这些方面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被削弱,那么中国走向世界就缺乏支撑力。在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中国要充分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争取主动,而这与科学发展中国的国际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轨迹看,改革开放所倡导的思想解放精神,使得这一学科进入了真正的理论发展阶段,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和国际观的更大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国际体系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和决策系统有着重要影响,其具体涉及外部环境和中国政策的协调及决策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④党的十七大提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和具有远见的。当然中国首先要关注和思考的是国内问题,但在中国的决策方面“国际”这个大局也要有足够的表现。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来看,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永不当头”理论,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及胡锦涛、温家宝的“和谐世界”,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中国的国际观。⑤总体上说,这些大多是针对西方所确立的国际秩序而言的,要表达的是中国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所持的态度。现在,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中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国际观,其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的外部事务层面上来说,这种国际观所要回答的问题主要包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而这种国际秩序所体现的价值原则是什么、如何构建这样一种国际秩序、如何处理新的国际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支持和接受这种新的国际新秩序等;二是从中国的内部事务层面上来说,中国在实践中首先要解决好与这种国际观相联的内部问题,如中国怎样才能扩大对外交往的空间、如何在现存国际秩序中与不同国家和社会打交道、如何保护走出去的自身利益、如何来建立国际新秩序等。如果中国没有发展好自己的国际观,对上述所有问题缺乏明晰的解答,那么在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中就会处于极大的被动境地。
随着中国的成长与发展,中国正面临着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对国际事务的贡献度远不及世界的1/5。如在联合国大系统中的维和系统、世界货币组织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面,几乎没有一个是由中国主导的。中国有时被认为其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外援)不仅很少,而且还被认为这类外援多半是“战略外援”,通常与中国的利益和战略目标相关。在制定全球公共产品的规则,如极地、外空、公海规则等的会议上,中国的代表几乎常被安排在后排座位,而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家则坐前排。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与其责任大国的地位还有距离。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除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重要的还是中国未能充分发展与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所处责任大国地位相应的国际观。这也就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时表现出严重不足或含金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凭借出色的经济表现和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积极态度,在这场全球危机中有了不同以往的话语权。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华盛顿出席G20会议上强调,中国愿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能力,加大对受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⑥中国愿意积极参与解决金融危机的态度与行动赢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赞誉和期待,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欧盟近来一直奉行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对华政策,但和美国一样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在世界政治中潜在的关键角色”。⑦中国有理由得到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和谐世界”提供更大贡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临各种挫折,但中国可以从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得到有些被自己认可的经验并做出正确地选择。国际观是确立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基础。有了健全的国际观,中国才能有充分的国际话语权。否则中国只能跟在国际形势后面,被动地对国际局势做出反应,而且中国和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还会永无休止地陷于一些具体利益之争而找不到有效的根本解决方法。很显然,发展一种能够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的国际观,并且把这种国际观体现在中国“国际大局”的决策中,对中国在和平崛起中扩大国际话语权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扩大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
学术界有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认为,有实力才有话语权,有话语权就有了参与权和决定权。如何让世界听得懂中国人的话语,是作为责任大国的中国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就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来看,要完全而有效地维护和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还必须要对话语的施行者中的非官方组织或群体、话语对象中的民意力量和话语平台中的特殊渠道等予以足够重视。
第一,增强中国对外传媒力度,支持海外华人话语
当今世界公众媒体仍然是国际关系发展中极为流行的公开而重要的信息通道,而中国在争取国际公众媒介的话语权上面临着严重挑战。在如何增强中国对外传媒力度的问题上,除涉及硬性因素之外令人更为迫切关注的是软性因素。中国对外传媒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话语对象”,避免以“套话”、“空话”或“官话”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2008年1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会上以平民化的语言提出“不折腾”一说,引起国际社会媒体的热烈反响和叫好,这应成为公众传媒用语的楷模。同时,还要注重“话语的施行者”(或传播者)中的非官方组织或群体就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性事件的反应。民间意愿的表达往往也是一种重要的话语权的表现,而且其作用不可忽视,如2008年美国总统布什坚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美国不想让“中国老百姓反感”。因此,中国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这个领域里会有很多的发挥空间。
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也离不开海外华人话语的有力支持,中国应加大力度对他们提供切实和有效的支持。海外华人及其媒体的话语与中国官方、在中国的非官方组织和群体相比具有不同凡响的作用。2008年对全球华人来说,是与祖国贴得更近的、有特别意义的一年。为声援北京奥运会和抗议“藏独”势力,海外华人积极诠释并维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此外,遍布世界各地的华语媒体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上述这些事实为中国拓宽话语平台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机会。海外华人争取中国话语权的有利条件包括:一是中华文化早已成为共同认可的凝聚力,这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血脉、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二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快速地、跳跃式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靠近,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实力首先或更多的是表现为中华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充分张扬。世界关注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在这种环境下,世界华人发出的话语,不仅是在弘扬祖国的中华文化,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展示理性中国、责任中国的形象。中国应从多方面、多形式和多渠道运用并发挥海外华人在争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方面的影响与作用。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拓展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
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具体实践上,开辟和建设以“和谐世界”为特色的国际话语平台来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问题上的话语权。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批判吸收,以人为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扬人的价值上有相同性,同时两者都认为相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人是目的。⑧当中国把“人”字放大到足够大时,西方大多数普通民众就开始理解中国,接受中国。2008年的四川救灾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救灾过程中,“以人为本”成为从中国政府到普通百姓的行为准则,从而赢得了世界民众的普遍赞誉。因此,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话语平台方面,除了走“官方渠道”(国家间政府)外,还要特别注意“民意渠道”(中国外部和内部的民意力量)。
具体来说,一是多做和尽可能做好有关国家的议会(包括议员)工作,如西方国家的议会不仅在制约政府的决策方面,而且还在社会的民意动向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二是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接触和沟通,如环保、节能、慈善事业、乡村教育和卫生、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都是这类组织所高度关注的,通过彼此交流提升国家形象并扩大国际话语权。三是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公众外交应有的作用。“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舆论间接进行,但其行为主体仍然是政府。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对公众外交明显重视,如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现在已遍及66个国家和地区,共有227所;2008年10月,中国政府决定,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必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需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这些都推动了公众外交的发展。四是要重视来自中国内部的民意力量的作用。有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自发地关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在2008年“拉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民间对西方的一些带有偏见和成见的媒体报道所做出的强烈反应,体现了中国民间国际话语权意识的启蒙。这意味着中国民间正在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主权观念已经远非物质边疆那么简单,而在捍卫国家利益的过程中,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发言权。这种从民间开始的话语权启蒙,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将辅以强大的推动力。
在如何开拓话语平台的问题上,中国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关注非官方的民间管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争取国际公众媒介的话语权上正面临着严重挑战。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新闻舆论和控制世界传媒市场,⑩从而形成了这一平台的话语霸权。其结果可能是,世界最终只能听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逐渐地发现自己被封闭在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设的“国际化话语”的围墙中。
世界只有一种话语是很危险的,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以话语多元化为基础的公众媒体格局的改变不能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善意”的让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一份有关国际传播领域问题的重要报告认为,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世界统治权力,而在这一信息的单向流动过程中深受其害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11)这份报告主张国际社会应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以实现话语多样化和公平的话语权。中国发表的一份有关对信息时代的国家进行分类的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信息霸权国家”,十几个“信息主权国家”和大多数“信息殖民地国家”的非正常关系。(12)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只能靠自己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让世界听懂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话语。
第三,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
中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国际社会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上拥有更多话语权,是顺理成章的。随着中国以经济力量为主的综合国力愈加强大,其话语权也必将得到不断扩展。与此同时,中国必然也会面临主要是来自一些西方国家的对自己的和平崛起所进行的“骨头挑刺”或“百般挑剔”,而这些冲突表明了“整个世界都会欢迎中国的崛起”的想法实在是无异于天真。(13)身处这种国际环境,中国一方面要以继续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进行坚定而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形象。
改革开放三十年表明了中国通过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为原则与外部世界整合而和平崛起,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努力向外部世界学习,而且对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反应也非常敏感和在意。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百姓,一直在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如何评介中国。这种积极态度不仅反映了中国人的好学精神,更重要的还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不再是闭门造车。也正是因为内部的发展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内容,中国的和平崛起引来外部世界的一些苛刻非议甚至严重偏见也就是自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情绪化反应会有损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如每逢出现某些西方势力的不友好行为和小动作,中国通常的情况是必有反应。当然,对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国必须要有力还击。但如果对西方的每一种观点都要做出回应,这不仅显得中国没有包容性,而且在客观上也会导致负面的效果。中国作为一个责任大国而每每对西方少数人的诋毁做出反应,其效果会在西方成就了“敌人”的同时,也为西方媒体进一步诋毁中国提供了新的素材。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也正在加速融入世界,而展示责任中国的大国风范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本文就如何定义国际话语权以及中国如何在崛起过程中拓展国际话语权提出了新的思路。西方国家在现存的国际秩序领域里依然有巨大的传统影响力,包括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其表现在他们拥有话题设定(话语创新)优势、制定评判标准优势以及评议、裁决优势,反映了西方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控和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然而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其实力相对变得弱化。今天新兴国家已逐渐地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进入了中心地带,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特别是中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体,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与此同时,中国可能面临一个无法避免的现实:国际秩序一旦发生重大变化,就会对中国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此意义上,中国必须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而这也正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所在。
注释:
①Nina Hachigian,Michael Schiffer,Winny Chen,A Global Imperative: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US,August 2008.
②Ng Tze-wei,"China's voice loud and clear in new 'G5' Bloc",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ly 10,2008.
③Rosemary Foot,"The Chinese and President-elect Obama",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30 Issue 3,2008.
④Yu Hongyuan,"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Decision-making on Climate Change Polic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ume 1,Number 4,Oxford University,UK,2007,pp.497-523.
⑤朱立群、赵广成:《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J],《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8—25页。
⑥《胡锦涛在华盛顿20国领导人金融市场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http://www.cctv.com/default.shtml。
⑦Matt Burnett,"Politics: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w Frontier:EU-China Relations,University of Reading,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UK,2008.
⑧蔡丹:《全面解读“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12期,第110页。
⑨高飞:《公共外交的界定、形成条件及其作用》[J],《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106页。
⑩刘长乐:《争夺话语权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前提》,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
(1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4页。
(12)张幼文、伍贻康:《新棋局:参与全球经济的中国》[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83-87页。
(13)Yongnian Zheng,"China needs international outlook to be world leader",China Policy Institute,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K,Jul 1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