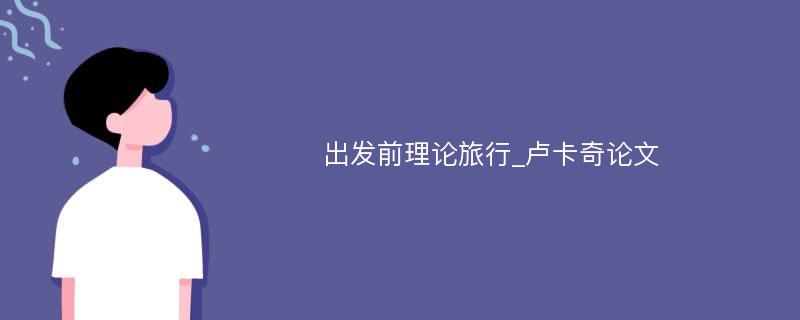
理论旅行再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出论文,理论论文,旅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状态下,理论跨越不同的边界(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广泛快速地流动,这已成为当代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女性主义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是其中的一支劲旅。我作为一个“旅行者”,多年来在国内外不同的时空地域对女性主义理论旅行的种种迹象进行着观察与思考,不免对下列问题产生了兴趣:这些理论和概念为什么会流动?它们是如何流动的?又如何被接受或拒绝的?谁参与和控制了这些理论的推广和再创造的过程?谁又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为什么某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概念在流动,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思想和概念则不流动?推而广之,在思想、文化等其他领域是否面临着同样的理论旅行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讨论的一个维度是将理论旅行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从阅读赛义德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同名之作《理论旅行》“出发”,借助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对“理论旅行”的批评与发展,对“理论旅行”的理论进行梳理;讨论的另一个维度是在观察理论旅行中的“路线”、“场所”和“旅行者”等方面,了解某些国外的理论如何“到达”不同的地方。借由这两个维度,探讨如何认识全球化大背景下知识生产中的有关问题。本文讨论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如何“重建旅行”,我对此的思考是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理论旅行,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它将在探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问题上,促进思考的变革和方法的创新。 一、出发 众所周知,中国的妇女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其受到国外(或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那么,女性主义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妇女研究?这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是如何被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这是国内外中国妇女研究领域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感兴趣和关注的方面。 说到妇女研究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这种思考关注的主要是国外的理论、概念如何为我所用。这样的思考往往把中国和西方看成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西方是理论生产的中心,而中国则处于边缘,或是被动地接受着外来的影响,或是主动地要把这些理论“中国化”、“本土化”。从全球来看,在有着被殖民历史的“东方”与“南方”,这种焦虑具有普遍性。在当代后殖民理论的冲击之下,“西方的”理论与方法,遭到了第三世界社会的质疑,因而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运动,例如,80年代台湾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的中国化”以及90年代中国内地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这些运动或许是来自理解本土的良善动机,或许是来自某种民族主义情绪,但目的的错置却往往使这些运动可能只能成为“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倒影。 回过头来看西方,所谓“西方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90年代初期,当我身处西方一段时间之后,便慢慢发现,我们在国内所接触的女性主义的理论,只不过是其众多女性主义的理论中极少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理论还留在西方的“家”里,根本就没出家门。例如,当时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已经达到了高潮,而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掀起浪花;社会性别(Gender)理论也讨论了多年,我们却基本上没听说过。也就是说,单是女性主义,就还有相当多的理论和概念并没有流传到中国。这就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理论和概念流动,而另外一些则不流动?是什么力量促使其流动或不流动?为什么我们往往将这“部分”的理论当成“全部”来照单全收?当然,这种状况与我们被封闭的太久有直接的原因,饥饿得太久了,真是有些饥不择食。另外,当我们的眼界局限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范围之内,往往就遮蔽了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与理论生产和流动的大图景。再进一步说,我们原有的认识问题的方法或许还不足以提供处理这些问题的思想手段。 从哪下手?怎么研究?爱德华·赛义德的文章《理论旅行》对于认识上述问题无疑是个出发之点。 (一)解读赛义德的“理论旅行” 在《理论旅行》这篇文章里,赛义德讨论的是文学领域的问题,他将“批评意识”引入了文学实践,强调创造性地借用、挪用理论,分析理论在国际环境中从一地向另一地的运动过程。虽然赛义德所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但他这种开放性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首先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启示,特别是“理论旅行”、“误读”与“批评”这几个关键概念。 1.理论旅行 赛义德认为,在文学和观念史这样的领域中没有内在的封闭界线,批评的流派、观念和理论可以在不同的人、情境、时空之间旅行。关于理论旅行的阶段,他是这样归纳的: 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宽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① 这里,赛义德使用的是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方法,他还以比较详尽的笔触展示了从卢卡奇、戈德曼到威廉斯之间的理论旅行过程。 卢卡奇是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参与者,在其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卢卡奇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物化现象。照他看来,诉诸理论就会对物化的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制度造成毁灭性威胁。无产阶级意识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对抗。因此,卢卡奇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 然而,在卢卡奇的入室弟子戈德曼那里,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却变成了“世界观”,变成了研究者的领地。尽管,戈德曼与卢卡奇的借鉴关系是很清楚的,普遍认为,戈德曼在《隐藏的上帝》(1955)一书中,对卢卡奇的理论做了最好的实际应用。但他们之间对于理论运用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卢卡奇是作为斗争(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参加者而写作的,戈德曼则是流落异乡巴黎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戈德曼对卢卡奇思想的整理使理论降格了,削弱了理论的重要性,把它驯服为适合巴黎的博士论文要求的东西。”②也就是说,在卢卡奇的理论从匈牙利穿越到巴黎的这段距离中,由于时空点的变化,接纳条件的不同,原本是革命的理论却变成了研究的素材。 接下来是雷蒙德·威廉斯(20世纪中晚期剑桥大学一位英国文学研究学者)对戈德曼理论的使用。赛义德认为,在当时的剑桥,对于研究文学的威廉斯来说,社会变革的理论对他毫无用处。正是戈德曼1970年对剑桥的造访,使剑桥认识了理论,并开始使用理论。通过戈德曼,威廉斯了解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这次对卢卡奇的修正,是将其人类解放总体性的思想变为一种革命的观念的形式。“不过,更有趣的是,因为剑桥不是革命的布达佩斯,因为威廉斯不是参加了战斗的卢卡奇,因为威廉斯是一个反思的批评家而不是献身的革命家——这一点尤为关键,所以他能看出一种始于解放人类的思想但最终成为自身陷阱的理论的界限。”③ 通过对这一段理论承传发展过程的梳理,赛义德总结出了理论旅行的两个要点:第一,当一种理论旅行到另一个时间、空间,该理论就失去了一些它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第二,“旅行”意味着该理论要发生与它在原来发生地不同的表现和机构化过程。赛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的概念,使我们看到理论不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顺着这种思路,我们就要关注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时空中旅行时失去了原有的哪些重要内涵,同样重要的是,当一种理论在失去了它原有的一些内涵之后,又在另一个时空中增添了哪些内涵。我认为,这后一点更为重要,它也往往是我们忽略的方面。 2.误读 对这一理论旅行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研究之后,赛义德阐述了“误读”的问题。如果说阅读就是一种解释,那么解释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所有的阅读不分高下都是误读。关键是赛义德提出,把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归结于误读,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如果照此办理,对于某一文本或理论,除了照抄照搬,便是创造性的误读,不存在任何中间的可能性。并且,远不止于此,赛义德还指出“提升到一般原则上讲,一切阅读皆误读的思想是要从根本上取消批评家的责任。即使批评家在严肃的意义上说阐释就是误释或借用必然涉及误读,那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恰恰相反: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④ 的确,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已看到太多的问题被判定为误读之后,便被搁置起来。误读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结论,而没有作为进一步的分析的起点。还以文学研究为例,有研究者以阅读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为例,指出这原本是一部尖刻的政治讽刺小说,但是当这部小说被译成中文之后,我们的阅读兴趣却集中在其中所描述的怪诞奇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不再理会它是一部严肃的政治讽刺小说的真实面貌,而把它变成了一本诙谐轻松的消遣读本⑤。在文学阅读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但问题是,虽然研究者们正确地看到了误读的这种现象,然而,如何能像赛义德那样再向前迈进一步,把误读置于一种具体历史情境之中,考察观念和理论如何从一情境向另一情境进行转移的过程,从而发现这些观念和理论在失去了它原有的一些内涵之后,又在另一个时空中增添了哪些内涵,并且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些误读的原因。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批评 赛义德在“理论旅行”中讨论了理论的局限性问题,“尤其是如果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的话,突破就会变成陷阱……观念一旦因其显而易见的效用和力量流布开来之后,就完全可能在它的旅行过程当中被简化,被编码,被制度化”。⑥有人或许认为这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看看我们在“全球设计,中国制造”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的低端地位,想想我们每天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被简化,被编码,被制度化”的现状,就会感到赛义德的批评入木三分。 如何挣脱这种局限性呢?赛义德认为,需要一种高于理论和驾驭理论的东西,那就是从批评的角度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无法包揽、封闭、预言它可能在其中有所用处的情景。赛义德是这样论述这种批评意识的: 我们可以说批评意识是一种空间的东西,一种将理论定位或安顿的度量能力,这样就把理论和批评意识区分开了。就是说,必须在时空中把握理论,它是作为时间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在时间中为时间而作用,并且向时间作出回应。结果,根据理论出现的后面的地方来度量先前的地方。批评意识就是对各种情境之间的差异的感觉和意识,同时也意识到任何体系或理论都不能穷尽它所出自或它被植入的情境。而且最重要的是,批评意识要感觉和意识到那些具体经验或与理论冲突的阐释对理论的抵抗和反动。我甚至要说,批评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对理论进行抵抗,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向社会、向人的需要和利益敞开,指向取自处于阐释领域之外或边际的日常生活现实的那些具体事例。⑦ 赛义德所讲的这种空间性的批判意识,强调的是“一种将理论定位或安顿的度量能力”,一种具有历史感的批评反思的能力。反思我们的理论研究现状,可能缺少的正是这种批评意识,这种能够捕捉到建立在具体经验之上的阐述对某些理论的抵抗(而不是盲目地拥抱)的能力。尽管赛义德是从文学批评的视域展开其讨论,但这种空间性的批评意识为后现代主义的“情景化”知识的发展做了铺垫。 赛义德的这些思想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然而,当我试图使用他的理论框架来观察女性主义的一些概念和知识如何在全球旅行时,发现‘理论旅行’的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复杂的过程。例如,西蒙·德·波伏瓦的《第二性》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女性主义著作,1949年在法国出版后,尽管引发了一些激烈评论和许多正面反响,但当时并没引起世界其他地区的思想革命。直到6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第二波”的到来,这本书的英文译本才面世,并被称为蕴涵了一种震撼世界的思想: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如Kate Millett、Ti-Grace Atkinson和Shulamith Firestone都将波伏娃的名字写在她们著作的扉页上以示致意。这一横越大西洋的联系将一部法国学术著作变成了一场更为广泛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⑧。那时,这部著作在中国几乎是无人知晓。又过了20年,《第二性》才旅行到中国大陆。它在中国的旅途又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例证使我想到了两个问题: 首先,理论在本质上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移动性?如果不是,那么何时何地、何人、何原因造成了理论的流动?简而言之,理论旅行的动因是什么?对此,赛义德似乎有所保留。相对来说,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专注于探讨某种理论或概念在学术上是如何被转换和接受的,使理论旅行似乎成为了一种“自动”的过程。然而,承认理论是旅行的,并不等于说理论必然是流动的,与将其看作是一种“自然”流动的东西是两回事。不然的话,为什么在上述历史中,被称为当代“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经过了几乎20年的时间才从法国流动到大西洋彼岸?而又过了20年才从太平洋彼岸旅行来到中国?更何况,还有诸多的理论根本就不流动呢?也就是说,关于理论旅行,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赛义德没有探究。 其次,虽然赛义德指出了批评的时空问题,但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时间问题,即在欧洲的范围内讨论理论的‘线性’旅行,而当旅行的路线复杂化之后,理论会发生何种变化?还以上述历史为例。当《第二性》理论旅行的路线跨出欧美的学术领域,进入广阔的社会运动领域——妇女解放运动,或进入更加广阔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进入中国大陆,理论和概念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换句话说,在这些不同的时空地域中,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文化是如何选择、接受、转换、应用(或拒绝)《第二性》这些理论的呢?尽管在他的研究中一再呼吁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赛义德的“理论旅行”对类似这样的问题没有涉及。 然而,在理论、知识飞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理论旅行的路线图不再可能是单一的、线性的。因此,理论在哪里以及如何产生,通过何人以及为了什么目的流动,这一切都成了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理论本身的质疑和颠覆也直接威胁到西方理论的霸权地位。要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进行了重新解读,并且提出了新的问题。 (二)解构理论 首先一个问题是,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中“理论”意味着什么?这对赛义德来说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不难看出,赛义德所讨论的理论概念来源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比较文学和哲学。正如阿加兹·艾哈麦德(Aijaz Ahmad)所指出的,赛义德的理论秉承的传统是:“(a)在欧洲/西方历史的起点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身份,并且通过它的思想和文本塑造了这一历史;(b)通过一套特定的信仰和价值观念,这一欧洲身份和思想的天衣无缝统一的历史从古代希腊开始延续到19世纪末甚至到20世纪,并将这种相同性本质化和强化;并且(c)这一历史内在于其伟大著作典籍之中,由此即可重建其传统。”⑨可见,在这一传统之上,赛义德的‘理论’是欧洲中心论的,并且他“……是将西方或欧洲作为一个知识生产者,东方作为那种知识的客体来谈论的。换句话说,他似乎固定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客体身份,也假定了两者之间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⑩艾哈麦德的批评是尖锐的,指出了赛义德的“理论”的局限性。在知识生产的格局中,西方是理论的生产者,东方只是被生产的对象。 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1989年发表的《关于旅行与理论的札记》是解构赛义德理论旅行的代表作。在解构理论方面,他比艾哈麦德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克利福德看来,理论已不在西方的这个“家园”(home)里了,或者说是具有特权的地方了。借用女性主义者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提出的“位置的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的思想,她指出,理论已被其他的种族、性别、具有文化差异的知识所在位置(location)的诉求所影响或打断。(11)克利福德看到了西方中心的理论已经开始“离家出走”,西方是理论的生产者、东方只是被生产的对象的知识生产的格局开始瓦解。 “位置的政治”问题何以变得如此重要?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深入了解一下艾德里安娜·里奇提出的这一思想。里奇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家。在访问了拉丁美洲之后,里奇看到美国政府在那些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给当地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她开始结合种族、阶级等方面的因素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政治问题,提出了“位置的政治”这一具有创建性的概念,其目的是要通过反思自身所处的“位置”,揭穿所谓西方中心的女性主义的假面。 里奇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在什么中心?(At the center of what?)她的答案是:这是一种西方自我为中心的,而且忘掉了我们的中心是把别人排挤到了边缘。因此,里奇指出,我们需要通过反思来取代这种普遍主义的假设,从而建立起新的女性主义。(12) 新的理论从哪里开始? 里奇提出,就从我们的身体(body)的碎片开始。特别要指出的是,里奇在这里强调的是“我的身体”(my body),而不是任何一个身体(the body)。身体变成了一个作为妇女来言说的场所和基础。由此出发,身体不再作为单个女性个体的神话,而是女性个体与广阔的女性主义政治的一种连接。 如何连接? “我的身体”一定是一个具体的东西,里奇就从她个人的身体开始,来讲述她这个位置的政治。里奇告诉我们,她具有一个白人、犹太人、同性恋的身体,例如,在她出生的年代,美国医院的产房被隔离为白人和黑人两个部分。当然,她是在医院的白人的产房里出生的,在她被界定为男女之前,就已经先被界定为白人(13)。种族与性别就这样通过身体连接了起来。于是,里奇就与早期的那种似乎是无面孔、无阶级、无种族的代表全部妇女的利益的女性主义划清了界限,她执意把妇女置于不同的阶级、种族、年龄和性向的范畴之中来讨论,让西方女性主义的“白人中产阶级”背景浮出水面。 如果每个人都提出“位置的政治”,那么会不会使理论变得见木不见林?里奇认为,理论就是要见木又见林,理论就如同云层一样,吸收大地上的水分然后又回落到大地上,如果没有大地的气息,对大地也就失去了意义。(14)作为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代表的先行者,里奇用“位置的政治”的理论不断消解白人女性主义中心意识,使每一种政治位置均有其知识生产的权利。这对瓦解西方是理论的生产者、东方只是生产的对象的神话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 赛义德一再告诫我们:理论永远不可能是完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过程。这话当然有理。然而,他所认同的理论的边界似乎没有超出欧美的范围,把突破这一范围的任务留给了后人。然而,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这种中心/边缘的关系一经打破,对于理论的理解便进入了新的阶段,各种位置都开始有了理论的诉求。于是,当理论冲破了欧美这一空间,进入全球领域跨国旅行时,我们如何看待理论?非西方中心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理论旅行和话语处于怎样一种关系?社会运动与话语实践的关系如何?这些赛义德未能给予答案的问题,在跨国实践活动中将由大家给出不同的答案。 既然理论已不是在西方的这个“家园”(home)里了,那么如何看待这些“离家出走”的理论的全球之旅呢? (三)重建旅行 进入全球化时代,理论旅行在学术知识生产中已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学者们在解构“理论”的同时,对“旅行”也进行了重建。旅行的概念、理论旅行的路线、旅行所到达的不同地点、理论旅行的载体等一系列问题,都进入了研究者批评的范围。 什么是旅行?这在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的框架中似乎是个不用解释的问题。然而,在批评赛义德欧洲中心的线性“理论旅行”观念的同时,一些研究者又进一步解构了“旅行”这一比喻象征。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看来,“旅行”还带有18、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传统旅行的意味。例如,克里福德提出,赛义德为什么用“理论旅行”命名,而不叫“理论流浪”或“理论迁移”、“理论的传播”?因为“旅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有图可循的运动。人们宁愿使用“旅行”一词,“而不顾它所含有的中产阶级‘文学的’意义,即长久以来一直与男性经验和美德相联系着的那些娱乐、休闲的空间活动。至少,‘旅行’一词指的是世俗性活动,它走的是公开的路线或人们常走的老路。不同的人员、阶级和性别是如何旅行的?他们产生出什么样的知识、故事和理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由此而开始”(15)。对克里福德来说,通过质疑传统意义上的“旅行”,将“旅行”的视野从欧洲中产阶级男性扩展到其他不同的人群,便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的讨论领域。 但是,克里福德虽然看到了旅行成员的范围的扩大,但却仍然将旅行的方式局限于“旅馆”这个范围内,例如,将“旅馆”比喻成“一个旅行者的必经之地”。对此,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又深挖了一步,指出:克里福德著作中所提到的“旅行”是由西方社会和政治权力中心决定和产生的;那么“抓住‘旅行’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抓住帝国主义的方法。………旅行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引起谈论中途、泪痕、中国移民登陆、强迫迁徙的日裔美国人,或无家可归者的悲惨景况的词语”。(16)胡克斯明确指出,中产阶级的旅行与大量的移民的流动说的不是一回事。借此,理论旅行分析中所忽略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权力/知识”的问题,被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提了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胡克斯的批评还揭示出了人们所忽视的“旅行”的物质层面的问题。 胡克斯的这些分析在跨国女性主义的研究里得到共鸣。跨国女性主义的理论开创者之一卡雷·卡普兰(Caren Kaplan)明确指出: 欧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批评实践对于这一跨国的物质语境认识较慢。批评家的主体位置(或用来批评的多重主体地位)没有受到极大的关注,不是被当做粗俗的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来处置,便是通过普世的欧洲中心话语取消了。理论和理论家的“旅行”既没有完全被认为是帝国主义遗产的一部分,也没有充分作为跨国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文化生产的政治的一部分来考虑。(17) 可以说,卡普兰与胡克斯异曲同工,她们抓住后现代主义中关于旅行的某些关键的比喻进行批评,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跨国实践的物质层面,从而提出跨国文化流动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也就是说,理论旅行和知识生产的实践既是一种物质的又是符号的。当我们研究理论旅行问题时,必须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不仅看到旅行的概念,而且要看到旅行的过程,看到理论是通过什么方式、何种媒介完成的旅行,并且要关注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例如,近年来,在跨国女性主义的理论旅行的话语中,“走私”(smuggling)、“理论空降”(theoretical parachutists)等概念的出现,便反映了这些研究的进展。前者是柏林墙拆毁之前东西德之间大量书籍的走私状况的真实写照;后者则反映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学术转型出现的矛盾和学术退化。(18) 理论旅行的路线如何展开?克利福德首先指出,赛义德的布达佩斯、巴黎、伦敦的理论旅行路线是线性的并且局限在欧洲,而理论旅行的四个“阶段”读起来像个太过熟悉的移民他国和文化传入的故事。克利福德还认为,这样的一个线性路线不能用来评判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理论旅行和理论家特有的反馈圈、带有矛盾情绪的借用和拒绝。进而,克利福德指出,“假如赛义德今日扩展他的‘理论旅行’,他一定会抓住这样的非线形的复杂组合形式。”(19)非线性的理论旅行路线终于成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20) 大量的研究表明,当今世界,理论旅行的路线走的都是“单向道”,即从西方、北方,旅行到东方和南方。然而,这些“地方”本身又是由复杂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所构成。因此,接下来问题是,当理论在不同的殖民地旅行时它会发生何种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如果说赛义德的模式可以用来说明理论从起点到达另一时空,中间未经过什么转折,而当代的理论旅行的模式却有相当部分是欧洲制造一美国认可一它国登陆。于是,这种经过多次“转机”的旅行便具有了值得注意新问题。例如,西方的理论在进入中国内地之前,首先要看其在美国学界的认可如何,如对法国女性主义的进口,就是由美国转道而来。经由美国后结构主义的炒作,丰富多彩的法国女性主义被削减到仅剩下克丽斯蒂娃、西苏、伊瑞格瑞三位学术明星,并带有了明显的美国“口音”,然后又转出口到世界各地。在这样的“转机”过程中,使在上世纪新妇女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许多法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在旅途中“遗失”了不少,并使其理论的政治和社会精神大打折扣。另外,从旅行到中国大陆的理论所走的路径来看,还有相当的部分是欧美认可-转道港台-沿海登陆-转销内地。例如,由于资料和语言的限制,很多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先由港台翻译成中文,再转道大陆。其中,自90年代之后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两个概念的翻译就受到港台女性主义的很大影响。 理论旅行的载体是什么?即翻译和文化翻译的问题,这既是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又是当今理论和概念跨国旅行中所不能被忽略的重要方面。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英语霸权的今天,“理论旅行”的复杂性还来自于翻译在理论旅行中的作用。“因为理论旅行的说法不仅通过赋予理论以充分的主体能动性而强调了理论(在他笔下也就是西方理论)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它完全忽视了翻译活动这个为理论旅行所必须依赖的交通工具本身。由于隐去了翻译这个重要媒体,理论的旅行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观念,以至于理论向哪里旅行(从西方向东方旅行或相反),为什么旅行(出于文化交流,帝国主义扩张,抑或殖民化),以及用什么语言翻译,翻译给哪些读者看,都似乎毫无不同”。(21)无疑,重现翻译在理论旅行中的作用问题,一方面将会揭示出理论旅行中语言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具体的理论和概念的跨文化翻译,看到该理论和概念在新的历史文化情景中是如何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或增添了新的意义。 打破了在知识生产上的这种中心/边缘的关系,理论的生产便成为一种过程。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成为了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于是,再看理论本土化的提法,虽然包含了力图创建本土知识的积极意义,但还是基本上把知识生产的工作划分成全球/本土、西方/中国,也就是说,还是用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的观点看问题,那么,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就容易假设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出产地,把自身放在一种被动的接受者的位置上,或是一种反对者的立场上。因此,我们要转变原有的认识角度,使研究的视域从理论本土化转向全球化知识生产的过程。看到这一过程具有时空地域(time,space,place)的特点。也就是说,全球化一定是在某一时间、空间和地点上进行的过程。那么全球就可被视为是一种建立在地域之上的东西,就如同地域的东西也是所谓全球的。于是,理论旅行就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分析全球化时代跨越不同时空地域知识生产的过程的方法,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从消极、被动的接受者,变为积极主动的知识生产者。 二、到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已经在中国全面登陆。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资本为动力,并与国家机器结盟,迅速地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生产空间。在此过程中,学术机构也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竞争的世外桃源。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竞争中,大学的研究与教学必须与应用的、商业的、工业的、政府等部门合作,争取更多的研究经费,整个评定系统均以研究经费的多寡定高低。“学术资本主义”(22)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流行通病。在这种状况下再谈理论旅行,便不能回避这种全球市场竞争的复杂局面。 首先,从知识生产上来看,要想挣脱自身所处的思想环境的束缚,就必须要借用外来的理论资源,这里不必一一细述其重要意义。关键是从哪里借用和如何借用?对此,赛义德曾经说过: 对欧美国家的学术刊物、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状况置之不理,没有一个阿拉伯或伊斯兰教学者可以负得起这个代价,倒过来却不是如此……结果是东方的学生仍然想坐在美国东方学者的脚下……这些人与他们美国和欧洲东方学导师之间的关系仍然处于一个“本土消息提供人”的角色。(23) 赛义德所焦虑的是阿拉伯世界70年代的状况,而这种局面现在却成为了我们面对的现实。 除此之外,中国大陆还具有本身的特色。不是说我们要和世界接轨吗?赶快接上就是了。于是,我们看到一轮又一轮的欧美理论被翻译引进,一位又一位欧美的“大师”(在国外没听谁叫他们“大师”?)被请来讲学。理论旅行的速度加快了不少。但很少有人提问:我们跟哪个世界接了轨?(欧美等于世界?)。我们为哪些理论开了绿灯?又有哪些理论被拒之门外?不可回避的现状是,在与世界(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第一世界)接轨的同时,又与第三世界(或东方、南方)“脱了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外,西方的理论仍是我们“进口”理论的主要部分。 其次,在西方、北方向东方、南方的理论旅行过程中,有一重要之点:东方、南方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理论话语。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理论/话语掮客”在国际基金会、学术界、NGO之间活动。这些不同的理论/话语掮客各自都有其各种各样的动因。例如,国内知识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专注于引进国外新的理论资源,这些人在理论旅行中充当了“旅行中介”或“掮客”的角色,成为当代知识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学术市场竞争的引导之下,有些“中介”“时刻保持着对欧美理论界任何风吹草动的警惕,并时刻准备着扑向猎物。”(24)他们既不愿(或不能)深入研究该理论的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情景;也没有考察该理论与我们自身的理论历史情景的关联。这样说可能有些以偏概全,实际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 从所接受的理论的内容方面看,有些人只对欧美理论界的某些“大师”和某些理论感兴趣。而对其他的理论置之不理。例如,在全球化讨论中,大多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主的理论,而对此进行尖锐批评的左翼理论,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大量研究却少之又少,结果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论调大行其道的局面。(25)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理论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却是为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最后,对于接受这些理论、从事知识生产的“大众”来说,所做的研究就是依托在某一思潮或主义,回避回答现实世界的问题。例如,在学院之内,经常所见的研究,是博导、硕导们先占据一个领域,然后令其学生围绕着该领域或某些思潮进行研究。由于缺乏问题意识,至多只是对某人的某些著作进行部分的翻译和简介,或对某种思潮进行评介。他们往往既缺乏对这些理论思潮与其产生之地社会背景的联系的分析,也没有对我们这块土地进行连接。对此,有人已提出了批评“只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上,把理论和学院知识生产作为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媒介与手段,更少有人追究当代流行理论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生产本身亦可视为历史和现实的复杂产物等问题”。(26)因此,当一轮又一轮的拥抱新理论之后,所剩下的只有既无理论创造,又无实际应用价值的学术垃圾。 回到女性主义的知识生产领域,如果给学术界引进的女性主义的知识画个图,就会发现我们所引进的理论大多是“白色”的(白人女性主义),即便是“白色”的女性主义也是以美国为主,欧洲、澳洲则少之又少(我们对北欧国家的“性别平等”的理论又有多少了解?)。于是,美国的某些女性主义便成了“普世性”的理论,如社会性别(gender)概念,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培训,已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概念之一。众多的黑人的、少数民族的、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理论,则被拒之门外,而这些理论对我们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密切的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只关注在“先进”国家的理论发展上,而对于我们周围的国家,亚洲地区的妇女/性别研究的了解甚少。有多少印度女性主义的研究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对菲律宾的妇女/性别问题又有多少了解?更别提在我们彼此之间建立有效的网络和合作研究了。 而在学院之外的妇女/性别研究及运动领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相当数量的国际项目“空投”到了偏远省份的贫困地区,另一方面,由于人力和资源的缺乏,“做(外来)项目”便成为该领域研究人员的唯一出路。许多研究者和活动家们不得不在外来的理念和当地的知识之间进行艰难的协调与谈判;在项目要求的田野调查、专业培训与深入分析研究的时间精力分派之间不断地作出选择。然而,也正是这些学院之外的妇女/性别研究及运动,在实践中不断对旅行的理论和概念提出质疑,例如,云南省的妇女/性别研究及运动这些年在全国领先,与大量的国外的理论及理论家们旅行到那里不无关系。然而,那里的研究者和活动家们却逐渐认识到:“理论学习很重要,但还要看到,如果想用已有的这些理论来诠释我们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和云南少数民族社区的状况时,我们常常显得无奈,‘套’不进去。或许,这正是我们想向某些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理论挑战的缘故”。(27)(她们的这些疑问和感慨又让我想到赛义德在“理论旅行”中讨论的理论的局限性问题,赛义德认为:“尤其是如果不加批评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的话,突破就会变成陷阱。……观念一旦因其显而易见的效用和力量流布开来之后,就完全可能在它的旅行过程当中被简化,被编码,被制度化”。(28) 经过了妇女/性别研究在中国30年来的发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理论是否已经真正装备好了在深入分析的层面上来探讨中国的性别平等问题?我感到,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之外,在近来诸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问题上,恐怕是缺失女性主义研究的身影和声音。这也说明,在全球化时代,性别理论的旅行速度大大超乎我们利用这些理论来处理自己的问题的能力。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了可替代的认识论:“没有全球的认知正义,就不会有全球的社会正义”。(29)换句话说,要想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知识生产,取得全球社会公正,关键任务在于发展一种替代的思维。这将是我对理论旅行的新思考的起点。在此起点上,如何发展一种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替代性的理论旅行,用来探讨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生产问题,下面几点是我对此的初步思考。(30) 一是理论旅行通常都是关注“旅行者”,即旅行的理论。替代性的理论旅行不仅仅讨论理论的旅行,它也同样关注理论接受地的人,以及当地人对这些外来理论的态度。他们对这些旅行来的理论是否欢迎、采纳和(或)质疑? 对理论接受地的人来说,应该关注的问题是:这些理论是在哪里生产的?从哪儿来?它与本地的地理—历史和知识生产的比例如何?当地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这些理论所经地区的差异,这些理论是如何被表达的?仅仅是用新的方式重述一遍还是要面对其理论的某种局限性? 二是大多数理论旅行著作处理的都是与话语有关的问题。替代性的理论旅行将包括对这些话语与物质条件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这就意味着,它不仅研究书面的翻译和理论,而且还包括与翻译随之而来的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理论旅行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浮出水面。 全球化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快速发展的技术交流和媒体己深深改变了理论旅行的条件(土壤)。正如克纳普(Knapp)所指出,“不反思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近的发展,就无法理解今天理论旅行的变化情况”。(31)随着知识和资讯变为高价值商品,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也被资本市场所高度统治,我们都面临压力去生产知识进行买卖。 随着项目基金的全球流动,“社会运动的市场化”(32)也跟着出现了。在这个市场中,各种运动和组织都把各自的观点、知识产品和技能拿来交易。资金流动的物质现实同样有着强有力的引导方向的作用。在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已从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中抽身而出,像许多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国际上的发展援助成为妇女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基金的组织该如何经营下去?没有研究经费将如何开展研究?摆在各地(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女性主义者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不受这些不平等的条件的影响,创造出“社会运动市场”中的平等政治关系? 三是替代性的理论旅行还将要探讨,在什么理论会旅行和什么理论不会旅行的背后,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一般来说,理论旅行关注的多是那些“旅行”的理论,而探讨那些没有旅行的理论其实也同样重要,这对于理解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理论旅行,以及更广泛深入地理解跨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总是有权力在促进一些理论旅行的同时阻碍另一些理论旅行。但是,具体地历史地分析这些状况之后,才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例如,在近20年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旅行地图中少了一样,那就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经过“文革”之后的政治转型,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被聚焦于经济增长的议程所取代,其中重要的部分是男女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此后妇女不再被看做是政治财富,而是被当做劳动力或经济负担。结果,中国妇女运动就不得不到处去寻找新的支持力量。我们看到,“社会性别”、“NGO”、“妇女组织”等话语成为90年代妇女参与政治的新语言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也愈加频繁地被提及,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与范围,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却在不断加剧,“性别平等”逐渐成为了一种空洞的口号。因此,如何从这些问题出发,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始新的旅程,这应该是替代性的理论旅行中的重要一环。 总之,通过探讨哪些理论会旅行和哪些理论不会旅行的背后权力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我们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更为积极的替代性的理论旅行。 注释: ①②③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147、150页。 ④⑥⑦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150-151、153页。 ⑤李政芳:《误读,文学文本的另类解读》,http://www.zkhy.cn/,2006年。 ⑧Braidotti,Rosi,"The exile,the nomad,and the migrant,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feminism",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1992,15(1),pp.7-9. ⑨⑩Ahmad,Aijaz,In Theor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Verso,London and New York,1992,pp.167,183.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关于旅行与理论的札记》,叶舒宪译,载《视界》2002年第8辑,第22-30页。 (12)(13)(14)Rich,Adrienne,"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in Adrienne Rich Blood,Bread and Poetry,Virago Press,London,1987,pp.210-231,215,214. (15)詹姆斯·克利福德:《关于旅行与理论的札记》,叶舒宪译,载《视界》2002年第8辑,第29页。 (16)hooks,bell,"Representations of whiteness in the black imagination",in bell hooks Black Looks,Race and Represntation,South End Press,Boston,1992,p.173. (17)Kaplan,Caren,Questions of Travel,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 and London,1996,p.103. (18)Knapp,Gudrun-Axeli,"Race,Class,Gender,Reclaiming Baggage in Fast Traveling Theories",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05,12(3),pp.249-265. (19)詹姆斯·克利福德:《关于旅行与理论的札记》,叶舒宪译,载《视界》2002年第8辑,第30页。 (20)果然,为了补救这一缺失,赛义德在1994年发表了《理论旅行的再考虑》(Travel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一文,加进了欧洲之外的理论旅行的路线,通过借用法农(Fanon)对卢卡奇等人批判性的接受的分析,对欧洲和非洲、殖民及后殖民主义等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21)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22)Slaughter,Sheila and Leslie,Larry L.,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23)Said,Edward,Orientalism,London:Penguin Books,1987,p.323. (24)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25)在2005-2007年,我在给管理专业研究生所上的公共课上,发现相当一部分学生持有这种观点。 (26)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 (27)赵捷:《我们的足迹——云南GAD小组于发展项目中的实践与反思》、《贴近真实的过程》,载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著《参与性发展中的社会性别足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25页,第320-335页。 (28)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51页。 (29)Santos,Boaventura de Sousa,The Rise of the Global Left: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Beyond.London:Zed.,2006,p.14. (30)关于“替代性的理论旅”,笔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有详细的论述,参见Min Dongchao,"Toward an Alternative Traveling Theory",in Signs,Spring 2014 (39),3,pp.584-592. (31)Knapp,Gudrun-Axeli,"Race,Class,Gender,Reclaiming Baggage in Fast Traveling Theories",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2005,12 (3),p.251. (32)Thayer,Millie,Making Transnational Feminism:Rural Women,NGO Activists,and Northern Donors in Brazil.New York:Routledge,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