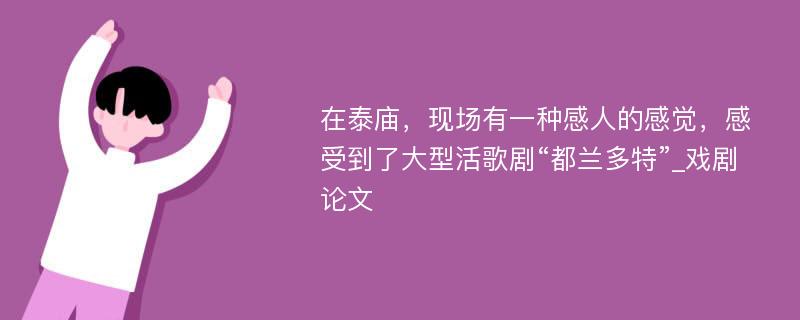
在太庙,这里有一个感动——临场感受大型实景歌剧《图兰朵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兰朵论文,太庙论文,实景论文,歌剧论文,有一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1998年9月3日(星期四)晚上19时30分
●地点:北京紫禁城太庙
●上演作品:[意]普契尼 《图兰朵特》
●指挥:祖宾·梅塔
●导演:张艺谋
●主要演员:(女高音,图兰朵特扮演者)乔瓦娜·卡索拉
(男高音,卡拉夫扮演者)谢尔盖·拉林
(女高音,柳儿扮演者)芭芭拉·弗里托利
●演奏:佛罗伦萨节日歌剧院管弦乐队和合唱队
●制作:佛罗伦萨节日歌剧院
●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执行制作: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瑞士历史实景歌剧公司
●承办:中演文化娱乐公司
●座位:1区8排8座
毫无疑问,由“临响”改为“临场”,仅仅一字之差,已然表明观/听的共同参与。说实话,在这场演出中,不仅有听觉和视觉的综合入境,更有历史的记忆在。
十分显然,这次实景演出,并非依傍高山流水的天然图景,也不同于前些时候的雅尼,借太庙缔造一个“文化广场”,实实在在,有一个人文景观在。于是,在尚未开演之前,我就生成一个强烈的感受,这是直接面对历史的一次敞开,尽管“今夜有人入睡”。
选择这样一个题材(据说发生在北京的一个古老故事),选择这样一个体裁(歌剧),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有着好传奇、擅听讲,并沉积持续着深厚戏剧传统的皇城内),几相合一,无疑,紫禁城太庙成了“唯一”。
以陈年已久的这座建筑物为背景,严格说,是真正的主体,足有三个普通舞台大小的跨度和两个以上普通舞台上下的高度。如此,“容积”,很自然,它便反客为主,成了这个演出版本的既定尺度,无论是普契尼的音响结构,梅塔的音乐指导,张艺谋的表演调度,以及其他创演者的工作平台,都必须以“太庙”的存在作为最后依据,音响要放大,人员要增加,色彩要绚丽,灯光要充足,现场要肃穆……,况且,不仅仅在尺寸,几乎要达到铺张。
有主创者们的精心策划,加上在场所有人的感情投入,可以肯定,在积淀着古老历史的沉甸甸的台基上,又融进了现代经世沧桑,尽管穿上“戏装”,则所有的创演人员和观听众,已然聚拢,并且,被套在一个只通天地的匣子里,共同叙述一个又遥远又在眼前的历史故事……就这样,在开场锣鼓声中,演出正式开始。
其实,故事并不复杂,尤其,对熟谙音律的爱乐者们来说,图兰朵特,可谓:案头存韵。不仅戏剧情节,人物角色,而且主题唱段,更何况,对中国观听众来讲,更有亲切感的是,中国民歌《茉莉花》曲调的整体贯穿。作为现场观/听,以下几方面似有新的经验在。
首先,表演舞台自始至终处在一种连贯的动作状态当中。每幕剧情开始之前,均由开场锣鼓“起兴”,不仅仅具肃静现场的预备功能,而且,在深层行为上,不乏有公开结构躯干的意义在。谈不上是十分标准的行为艺术,至少,随着每幕锣鼓手列队布局的变化,给人以一种逐渐入境的驱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注意到每当幕间休息的时候,观听众离座散场,舞台上却又有具戏剧角色的兵士列队进场,做些许动作之后,在下一幕启动之前退场,尽管,此举仅仅使舞台动作得以持续,然而,兴许其更有历史不断的意味。
与如此空前的场面相比,剧中角色显然变小了,或者说,有了相当程度的淡化,不仅在动作,甚至,连歌唱性很强的咏叹调在内,在整个演出过程当中,也似乎已不太引人注目,当然,这与出场演员的知名度,以及实际演唱水平(说实话,整场演出我始终未被这几位主要演员的歌声真正吸引过)也有一定的关系。相反,场面的频繁更替变换,包括人员、道具、布景等等,则逐渐成为观赏的主体。固然,如此的变化空间,并非原作提供,可猜测者,无疑,新版本的主创者所为。有人说,这样一种改编,时间看长了,难以摆脱“旅游文化”之嫌。这话不无道理,关键当然在于“适度”与否。不过,到目前为止,总算普契尼的音乐倒还不至于被吞没殆尽。因为,之所以被兴奋激动,场面之耀眼;之所以伤心感动,还是音乐者沁入。为此,并未真正吸引过我的那些主要演员,尤其是指挥大师梅塔的精湛技艺,实在是功不可没。曾经领略过梅塔风采的人,都不会怀疑他在调动音乐情绪方面的独到之处,不仅仅交响乐,哪怕是一首地方民歌,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并获得非常突出的效果。十分可惜,这次离他距离过远,好在,临响的效果不虚,不仅总体上平衡,局部也不乏弹性,尤其关键者,作为歌剧音乐来说,张弛的明显性,以及必要的适当得体,完全能够感受得到。
至于音响结构的现场效果,不用技术表明,在这种场合之中,音量的正常传递是无法实现的,或者说,不加以音量扩充的音响,对处在现场任何一个位置上的观听众来说,都是没有审美意义的,甚至连正常的感受意义也不会足以。因此,现场必须通过扩音设备,无论是乐队,还是合唱队,或者主要演员(看样子,声乐部分用的是随身袖珍麦克)。由此,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声音的保真度肯定要或多或少的打一些折扣,这一点倒是这部作品的音响结构还算是比较古典的(以协和性为主),因此,所缺尚可弥补,而不至于由于音响结构的不平衡,通过扩音设备的失真传递,变得面目全非。其次,是空间距离造成的时间差,由于场地面积大于普通剧场许多,因此,各个表演单位的相隔就要远一些,比如:指挥与舞台上主要演员的距离,舞台角色与合唱队的距离,原先可由指挥个人一统的局面,也因为其上下左右观照面的扩张,而带来诸多不便。其结果,乐队、合唱队之间,尤其是乐队和舞台演员之间,难免会在连接或者叠合的过程当中,出现不同音位之间的裂隙或空隙,并且,终究难以缝合或弥合,再加上传递上的空间距离,时间差在整个演出中,已然成为一个客观存在。所幸者还是,作品毕竟非现代样式类别,所以,哪怕十分明显的音位差别,也会被观听众的已有音响经验所还原。
就舞台直观而言,倒是不乏创意,不过,其创意的实现则有赖于通过已有经典的消解。比如,原本情节性甚强的戏剧场面,在此,有了非常意境化的处理,其结果,不仅造成乐舞分离,而且,还有情景间离。一个令我极其关注的场面是,一个颇具尚武精神意味的少女,穿戴血红的行头,以熟练的剑术翻腾在舞台中央,在她的周围,则是几十名全身白装素裹的宫女,排列成长长的一行,同时舞动水袖,有起伏,就像是一长道白绢织成的哀帘,覆盖在沉默的历史身躯之上。强烈的对比,一个和几十个,红与白,强和弱,剑与绢,从一道极具观赏的风景逐渐凝聚成一题难以推理的逻辑。在此,意境化的处理,其侵入性与渗透力远远甚于情节性戏剧场面。再比如,其色彩对比以及不同的寓意,以往领略过张艺谋电影作品的观众,不会不对他的色彩思维以及相关背景底色留下相当的印象,像《红高粱》当中的红色和田野底色,《菊豆》当中的黄色和染坊底色,《大红灯笼高高挂》当中的红色和深宅大院底色,等等。在此现场演出中,色彩再次令人注目,在太庙凝重而又沉甸的古老彩墨底色下,不断变换着不同的色彩:红色少女和白色少女,粉黄红三色花轿,蟒袍加身的金色宫服,有铜铁之感的士兵盔甲,跟随剧情的发展宫灯由绿而青再红的换色,以及与大舞台相映成趣的“台中台”,等等。甚至,把无关剧情的自己也拴在其中,不知有意无意,当张艺谋和他的合作伙伴们清一色地穿着黑衣最终走上舞台,接受观听众喝彩的时候,居然,与整个舞台的金碧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通过色彩而寓意,并且,在渐渐获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增加了具历史意义的人文含量。
进而,由此创意使然,仪式性极端强化的程序可谓结构框架。算是得益于先天赋予,选择太庙,必定有赖天圆地方之规,立一条座北朝南的中轴线,并以此设定阴阳和尊卑,于南北中轴音阳尊,处东西两厢者阴卑。诚然,这是古代的一个传统,归属于数术,但相应者,之后又合乎于人文道德,久而久之,成了一个程式,一个守则。由此规则,几乎所有的场面调动,都是左右对称,前后呼应。相比之下,几个剧情人物,反倒像是一个点缀,甚至一个背景。虽然,我时时盯着台上那几个角色,和他们极其有限的几个小动作,但毕竟还是借着几乎整体贯穿的场面大动作,而转换我的现场感受,就像在这样的音响传播空间,对合唱与乐队的关注,时常会多于对独唱和重唱部分,这种现象,也许在剧场歌剧演出当中,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从肯定的意义上说,仪式给予人的尊严性,以及所产生的感染力和慑服力,同样,也是难以抵御的。当女奴柳儿为主人而死去之后,与其说,人们的肃穆来自剧情,不如说,是场面的仪式感染更为直接:几个武士将她抬起(头南足北,绝对处在中轴线上),慢慢地走向太庙正殿之门(在此之前,仅仅供皇帝和公主图兰朵特及其随从进出,不可想象女奴能够登堂入家,这一点,显然已超越祭奠亡灵,以及安魂的剧情),随着音乐缓缓的哀恸之声,顿然,在两座移动楼阁的四周,落下了一条条刻有硕大“奠”字的垂幡,不仅仅仪式达到了高潮,而且,它本身所具备的形式力度,以及结合其他因素所产生的合力,完全出乎意料,人们为之震憾,连那两扇正在启开的太庙旧门,竟然也发出了吱吱的声响——历史,也被惊动……
就此折返音乐本身。作为经典作品,不管是批评,还是音乐史叙事,都已有大量涉及。但在现场,居然,我有一个发现,也许,是我少见多怪,或许,是以往片段听得太多了,也可能,即使听了也过于潦草,由中国民歌《茉莉花》经普契尼改编了的那个主题音调,在剧中几乎贯穿终始。与其他西方著名歌剧的经常剧目相比,比如:威尔第的《茶花女》,比才的《卡门》(这两剧在中国的上演率是最高的),很显然,就普通观听众而言,普契尼的歌剧作品,除了几个传世唱段为大家熟悉之外,其他方面可以说是比较陌生的,至少,这几个传世唱段,与《茶花女》的“饮酒歌”,《卡门》的“哈巴涅拉”相比,也是属于不容易上口的,说白了,就是富于歌唱性的旋律特点不强。因此,在这部作品当中,除了界内人士和音乐爱好者皆知的“今夜无人入睡”之外,就是女高音咏叹调,男女声二重唱,以及多人重唱,还算是有旋律轮廓在。其余者,即使不是宣叙调、咏叙调、朗诵调之类,也似乎只是在旋律轮廓周边徘徊。这样的情况,有作者的曲调结构样态,有当时的时尚品位影响,最主要的,当然还是风格使然,包括总体上的,也包括作者自己的。依我的歌剧音乐感受经验,应该说,普契尼是一个在歌剧领域当中,比较好地解决了声乐和器乐之间关系的作曲家。不管说是声乐的器乐比,还是说器乐的声乐化,都似乎不足以表明。但切切实实,在其总体结构过程当中,动机的个别显示,甚至仅仅暗示,乐句的平稳铺张,段落的有机衔接等等,都给人以一种动力不断,并有贯通预设的感受,说句不在行的话,他的音乐究竟如何成型?就在形成高潮的地方。进一步,他的音乐究竟又是怎样形成高潮?就在你感动的时候。果然,《茉莉花》主题音调的每一次出现,不仅形成音乐高潮,而且,正值内心感动之当口。虽然,作为结构贯穿,这个音调并不十分与其整体音乐风格相协调,但是,除了特定剧情可作弥补协调之工外,请注意他的配器方式,在一首本属纤细委婉并具曲折风格的中国民间小曲上,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油彩,不仅增加了原本音响的浑然性,而且,由于音响空间的相对扩张,使得原有的曲折风格,也似乎有了相当的平直性。如果说,原曲最具线条之阴柔,则改编之后,更有了力度之阳刚。如此而已,所谓与西洋风格不十分协调,也就有了可以靠拢,至少是远距离亲近的依托。当然,这个发现之所以在临场感受,也足以说明,在实景当中入境了。
作为临场感受实景歌剧,不可避免地还会有一个介入,这就是:非艺术的质料以及结构方式。或者说,除了人文质料以及结构方式之外,还有自然音响或其他动静,以及偶然事件的直接参与。虽然,这种介入更多是出于偶然,并非作者之结构预设,然而,毕竟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即时结构。遗憾的是,在此现场,多的只是人为的噪杂之声,诸如:说话走路电话铃声,缺的倒是自然之声,诸如:风声雷声……。不料,就在这音响与戏剧的结构当口,我看到了一只小鸟横空飞过,就像是一个插空,一个补白,还是通过自然,将人文化的裂隙和空隙再一次缝合和弥合了起来。
散场了,可还是有东西留在这里。不管日后人们将如何评价这个“太庙版本”和这一场演出,然而,在太庙,在紫禁城,至少,有一个感动在——不仅仅一个个曲调,普契尼的杰作;不仅仅一声声咏叹,男女角色的穿透力;不仅仅一招一式,梅塔的魔棍指点;不仅仅一个个场面,张艺谋的东方手笔;末了,还是一次次文化锁定:在北京,历史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今夜无人入睡,在一个最大的广场……
1998年9月4日
(写在燕东新源里)
标签:戏剧论文; 歌剧论文; 北京太庙论文; 艺术论文; 临场论文; 茉莉花论文; 普契尼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