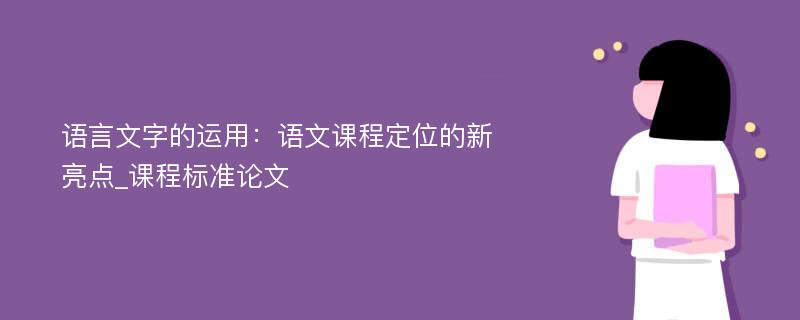
语言文字运用:语文课程定位的新亮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文字论文,新亮点论文,语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从词频分析说起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年版课程标准”)在课程特征定位上的一大亮点是:明确了语文课程的本体特征与学科功能——“语言文字运用”,并反复强调语文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此次修订稿中“语言文字运用”出现了8次之多。据笔者统计:导言中有4次,“课程性质”中有1次,“课程基本理念”中有2次,“课程设计思路”中有1次。
我们将2001年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2001年课程标准”)和2011年版课程标准中的三个关键词——“学习”、“运用”、“语言”进行检索统计,发现这三个词在课程标准中出现的次数分别由71、26、23次增长为118、48、43次,从词频上看几乎翻倍。可见,本次修订课标对“语言文字学习”的重视程度之高。
2001年课程标准的核心词是“学生”,这是当时注重语文教育人文性以及学生主体地位最有力的证明;而2011年版课程标准在保持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明显发育衍生出一些新的核心关键词,这就是“语文”、“学习”、“教学”、“发展”、“过程”等,这也是语文学科注重实践性、应用性的一个明证。那么,2011年版课程标准在定位和表述上的这种变化,有何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呢?
一、“语言文字”:语文学科课程的本体探寻
2011年版课程标准改动最大的是第一部分“前言”,而“前言”中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突出强调语文课程的“语文”内涵,尤其强调了“语言文字运用”这一本质特征。
语文设科一百多年来,关于“语文”本体的理解一直游移不定且极其混乱。语文学科的定位,从20世纪前50年的文言与白话、国语与国文、技术训练与精神训练等论争,到20世纪后50年的“文”与“道”之争、“工具性与思想性(人文性)的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比较明智的语文学人都坚持并坚守着语文学科的核心即“语言文字学习”这一学科基点,并且都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理解“语文”的含义,思考语文教学的路径。如“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叶圣陶),语文“可以解释是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解释成语言和文学”(吕叔湘),“语文这门学问主要是语言文字之学”(张志公)。
1963年教学大纲中提出“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这一重要论断。可是,各种社会思潮以及政治理念对语文的干预一直没有停止。“文革”时期,受到庸俗政治学的冲击,语文几乎成为政治思想斗争的工具,从课文的选编到语文课堂都充满了浓厚的阶级斗争气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恢复了1963年大纲的精神,但由于受到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影响,语文教育被应试教育抽空和榨干,语文学科失去了它最基本的灵性、精神和固有魅力;新世纪实施新课改以来,语文课程虽然一再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但由于矫枉过正,语文课程从教材到教学都弥漫着严重的“泛人文化”的“虚热症”,语文教材一律按“话题组元”,语文课堂上无边界的胡乱解读和拓展延伸使得语文本体迷失,导致语文教学效果下滑。
“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是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目标,这是语文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学科基点。王尚文先生说:“在基础教育中,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所有课程的特质在于它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根本宗旨。语文的本体就是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运用,语文教育必须走在‘语文’的路上,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就会走向自我消亡的悬崖。”[1]倪文锦先生认为:“从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百年历史来看,还没有哪个阶段的语文教育水平已经高到需要批判语文的工具性的程度,脱离或忽略语言工具性特点的语文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2]十年课改我们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的语文课程特点,但实际上是将“人文性”凌驾于“工具性”之上的,也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如今,我们再次找回“运用语言文字”这一学科基点,可以看作是对传统语文论争经验的再次确证,是十年课改一度迷失的语文本体的回归。
二、“语言文字运用”:语文课程定位的确证
长久以来,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都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这一次修订,关于“课程性质”的表述,作了如下修改: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程,应使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交流沟通,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提高思想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精神成长。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强调课程的目标和内容须聚焦于“语言文字运用”,突出“实践性”、“综合性”的特点。语文课程的内容十分丰富,语文教学可以因教师风格的差异而异彩纷呈,但是教学目标和内容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教学的种种举措和行为也都应该指向这个核心。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些背离核心目标的做法。有些教师在阅读教学中,往往会脱离课文的语言文字运用情况,讨论、评析作品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等问题。根据2011年版课程标准“教学建议”的要求,阅读教学可以从具体语言文字运用现象入手,通过对课文语言的品味、咀嚼,来探索文本的意蕴;也可以从整体阅读的感悟出发,到语言文字中找出依据。语文课程是一门学生学习如何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实践性课程。学习语文的功夫,首先应该花在对具体语言材料的积累、品味、感悟上,在语言材料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再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可能(学生已经具备的对语言文字运用现象抽象提升的条件),帮助学生认识语文运用规律。
开设语文课程的目的不是要让学生个个成为精通语言文字要素、结构、特点、规律之类专门学问的学者。语文课程目标不是落在关于语言、文字的知识系统和学科规律的理论知识上,课程内容不是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语用学、文字学、文章学、文学的知识拼盘,而是要让学生学会“运用”或者说“驾驭”语言文字这种工具,是要通过运用语言文字的范例和实践,学习如何在生活中、在本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学习中,并准备将来在不同工作领域里,运用好语言文字。语言最主要的功能是进行交流、传播信息以及传承和创造文化。语言作为一套为社会言语社团所共同拥有的符号,是社会言语活动的产物,语言文字是用来“表达交流”和“做事”的。语言文字运用是语文教育的本质特征。
何谓“语言文字运用”?指的就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听说读写的各种活动。在过去的教学大纲中曾经有过“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表述,2011年版课程标准中的“语言文字运用”,把“运用”一词的含义加以扩大,这里“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个表述中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1)“语言文字运用”是指向动态的言语实践活动的。学习语文课程不是学习那样一套僵死的语言符号系统,语言是来源于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学好。
(2)“语言文字运用”是超越学校教育、课堂学习的狭隘时空的,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相等。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它是社会生活的背景、资源和人类生活劳动创造的源泉。
(3)任何的语言活动都是有具体语境或活动场域的。语言在生活、工作、学习和文学艺术活动中的表现形态是不同的。在这里区分语言文字运用的不同场域,就等于承认了语言的功能化变体的存在,并暗示着语文教育的语言学观念从“静态语言观”向“动态语用观”转变。这也是语言学理论发展和世界语文课程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和进展。
关于“语文”课程的新定位,巢宗祺先生最近说过如下的话,基本代表了我们对语文本体的一个基本认识——
我们认为,开设这样一门课程,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学会运用本国的语言文字。说“语文”是“语言与文字”也好,是“语言与文学”也好,“语言与文章”也罢,其核心内容都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实用性的运用和艺术化的运用——为了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实际事务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为了表达对人、事、物、景的感受、体验和思考,运用语言文字,通过形象抒发自己的情怀。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在它的基本功能之外衍生出新的功能,产生大量的附加值。语文课程在它学习与教学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专门性功能的基础上,也会产生出其他的重要功能。在这具有多重功能的课程中,我们应该紧抓核心不偏离,争取综合效益不偏废。
这使我们联想到2001年新课改以来出现的“泛语文”、“非语文”、“去语文”倾向的语文教学。这种趋向表现为教材编撰上的“人文话题”组元方式,语文课堂文本解读在所谓的“多元解读”、“创造性阅读”名号下形成的无方向拓展的现象,脱离了文本本身和语言文字学习的中心任务而进行的所谓“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2011年版课程标准清晰地将语文定位为“语言文字运用”,无疑给飘飞不定的语文课程一根缆绳、一个锚杆或定海针。
三、语文课程的语言学基础及范式转型
任何母语学科都首先是学语言的。近百年语文教学中语言观的变化非常明显,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静态语言学到认知语言学再到功能语言学的变革。
静态语言学把语言当作纯粹的符号系统的“学得”,语言被看作是一套客观的、普适的、被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符号系统。字词的意义就是“字典义”,采用的教学方式是机械的行为主义的死记硬背和模仿训练,主张多读多写多训练。
到了认知语言学那里,语言被看作思维和大脑的机能,这种语言观使我们对学生的思维训练尤其重视,如概念、判断、推理、想象、联想以及各种言语图式的习得,因而运用信息加工原理,读写听说行为被看作信息的输入、内化加工、处理输出的过程,这种理论假设几乎仍是目前语文教学理论的主流。
随着语言学理论、社会认知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的进展,语文教学的语言观将可能转变为基于“功能语言学”和情境建构、社会认知、文化濡染的方向上来,这就是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成员共同建构协商的产物,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固有的,而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协商的产物。比如现在社会上的各种网络语言之所以能够流行并为大家采用,就在于它们在社会成员之间能达成共同的理解,比如“黑客”、“驴友”、“打酱油”、“囧”、“顶”、“被”、“给力”,都是网络时代语言急剧变化生灭汰选的结果。再就如短信、博客、微博、跟帖、电邮、网聊等新的文章体式的出现,也是言语社团在社会交流中协商定型的产物。
在功能语言学家看来,语言具有一种变化不停的“意义潜势”,以往的言语成品造就丰富着整个言语大海的存量和意义,每个人只能去这个大海中习得、濡染、领会。我们凭借语言,我们造就着语言,我们丰富着语言。语言的意义是由于某些人的语言被大家认可形成的,是整个言语社团或者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赋予的。
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教学考虑的是言语的目的、功能、文体、话题、语境等要素,同一个语言符号,在不同语言环境中意义是不同的。学习语言必须回到语境中去,揣摩原意,建构新意。语言是人类和社会文明的伟大馈赠,在我们手上传递、生长、创新。基于这样的语言观,语言教学就要考虑具体语境的还原、营造。可以这样说,静态语言学那里的语言是客观的,认知语言学那里的语言也是客观的,但考虑到了言语主体的作用,而功能语言学那里的语言成为言语主体和客观环境、文化、社会的一种综合建构。
如果说基于静态语言学的语言教学是一种“虚假语言”的教学,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教学是一种心理认知的语言教学,充分发挥语言和思维的作用,那么功能语言学的语言教学必须是具体的、情境的、对话交流、合作建构式的。因而,语文课程中的语言知识不应该是静态语言学上的客观意义,而是认知语言学的工具意义和功能语言学意义上的真实具体的意义。
这次语文课标修订的最大亮点就是强调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培养,这可以看做是我国课标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突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课标修订似乎预示着一个“以语用功能为主”的语文课程时代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