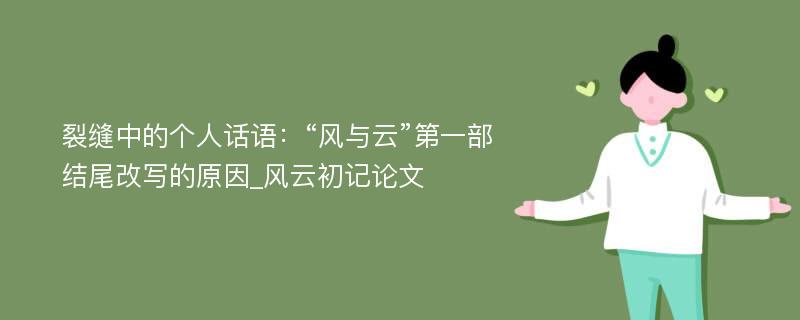
裂隙中的个人话语——《风云初记》尾声重写缘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裂隙论文,重写论文,缘由论文,尾声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7) 01—0018—04
孙犁创作《风云初记》前后历经12年之久。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写成第一集;1951年3月至1952年7月,完成第二集;1953年3月至1954年5月,第三集完成。后来孙犁病倒,直到1962年春病稍愈,编排章节并重写结尾。值得探究的是,《风云初记》初稿即第一、二、三集是在基本连贯的4年时间内完成,而定稿则在8年后二度创作而成,中间固然与1956年孙犁的大病有关,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在初稿距定稿的8年之间,《风云初记》仿佛如一个已经出世的婴儿独自成长,而8年之后,孙犁却突然如一位专制的母亲重新改变它的体形,为它安置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其实,这个重写的尾声的出现看似突然,实则必然。当然,它不是遵照故事的发展逻辑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叙述策略。在1962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孙犁之所以重写尾声、之所以选择“次要人物”李佩钟作为叙述对象显然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有密切的关系。用“光明的尾巴”的结构方式是孙犁战争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手法,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结尾却是一个特异的存在。1962年作者重写尾声时重点补叙了一个次要人物——女县长李佩钟的命运与归宿,并花了相当的笔墨解说其“烈士”身份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叙述策略。考察整部小说对李佩钟形象的塑造,可以发现在她身上凝聚着孙犁对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深切焦虑。而在重写的尾声中,李佩钟更成为孙犁在特殊年代倾泻知识分子个人话语言说冲动的载体,由此,这一人物形象也成了我们诠释孙犁缘何重写尾声的较好切入点。
《风云初记》以作者家乡滹沱河岸的两个村庄五龙堂和子午镇为中心,描写抗战初期冀中平原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错的复杂历史场景,共90章。在女性形象中,相比于贯穿全文始终的主要人物春儿,描写李佩钟的笔墨非常有限也非常集中,如第14章与高庆山的对话、第21至34章初任县长后抗日工作的开展,以及第39章、第52章、第75章中的简短出场等等,但在结尾,有关她的描述与议论却有5段文字。当然,笔墨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人物在作品及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有论者所言:“作者有意抑制对李佩钟的深入描绘,并没有转化成他对这个人物真正的冷漠;相反,在一些细节描写中,流露着他对李佩钟心灵和命运的真挚关怀。”[1]在重写的尾声中,因李佩钟的牺牲,作者有一段议论: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严重的年月里,残酷的环境里,不管她的性格带着多少缺点,内心里带着多少伤痛——别人不容易理解的伤痛,她究竟是决绝的从双重的封建家庭里走了出来,并在几次场合里,对她的公爹和亲生的父亲,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我们不应该求全责备。她参加了神圣的抗日战争,并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的生命。她究竟是属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队伍,是抗日战争中千百万烈士中的一个。
在这段文字里尽管孙犁竭力以温和的口吻试图对人物做一客观的价值评判,但两个“究竟”的着力辩解无意中流露出作者内心对笔下人物真切的关爱与怜惜。前一个“究竟”意在突出李佩钟阶级意识鲜明、阶级立场坚定以及成长过程中的自我磨炼。在此基础上,后一个“究竟”郑重认定其“优秀儿女”的政治属性与“烈士”荣誉的当之无愧。但颇具意味的是,小说前面诸多章节对李佩钟的形象只著一词——“俊俏”,尾声中却有丰富生动的详细描摹,如“她那苗细的高高的身影,她那长长的白嫩的脸庞,她那一双真挚多情的眼睛”等。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李佩钟抱有一种特殊的言说冲动与精神诉求。
孙犁塑造李佩钟这一人物形象显然怀有明显的企图。她或许是孙犁所有小说中思想最丰富、性格最复杂的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类,《光荣》中秀梅、《村歌》中双眉等热情能干的青年女干部;《荷花淀》、《嘱咐》中水生嫂等柔情似水的已婚妇女以及《秋千》中大娟等或出身或性格有争议的“问题女性”等等。并且,在具体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构成往往清新单一,但李佩钟形象却在糅合了以上三类女性形象的基本特征后,还冠以高学历、女县长与绅士女儿、地主儿媳妇、中央军专员妻子等复杂身份,显示孙犁开始有意突破战争美学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由对人物品德热情讴歌转而对人物命运的深沉关注,从人性的角度探触人物丰富的心灵空间。作为一名农村女干部,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悖的是,李佩钟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工作作风与抗战功绩,而是知识女性的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她“娇声嫩语”地说话,手枪像女学生的书包一样“随随便便挂在左肩”,忙里偷闲地养花,都显露出一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在作者对李佩钟日常化细节的精致刻画中,李佩钟与其说是一位农村妇女干部,不如说是一位情感丰富、趣味优雅的城市知识女性,而唯美、舒缓的叙述风格分明流露出叙述者那夹杂欣赏与怜爱的情感取向。
与孙犁以往小说中思想狭隘、作风偏激的女干部(如《村歌》中的王同志等)不同,李佩钟学养深厚且不骄不躁,作风干练又细致温和。曾有人指责孙犁将李佩钟写得“太娇嫩了”、“还远没有改造和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2]484。批评者显然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要求出发而忽视了人物性格衍变的逻辑。由救助会到抗日县政府的县长,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李佩钟的思想迅速地走向成熟,甚至成熟的步伐有些迈得过快。只是随着政治与工作上的日渐成熟,李佩钟的女性形象悄然退场,她深思熟虑的思维方式与坚定果断的工作作风酷似男性,如破路工作的顺利展开和成功捕获破坏分子等都充分展示革命干部的智慧与胆识。同时,在情感方面,她努力抑制自己对高庆山的满腹柔情,对秋儿则显示出女人少有的大度、豁达。可以说,如果没有出身问题的缺憾,李佩钟几乎是一个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又深受大众欢迎的完美的革命干部。而其出身问题则包括家庭出身与地主儿媳妇、反动军人妻子的多重身份,事实上,出身问题也没有困扰李佩钟很久,已出嫁的姑娘与娘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淡薄,而作为买办婚姻的受害者,文中并没有正面铺叙她与丈夫之间的情感纠葛,只在托春儿捎去离婚通知后有一段景物描写反衬她在过去婚姻中曾有的孤独与落寞。
按照现代女性人类学的观点,“女性”应包括“母性”、“妻性”和“女儿性”三种人格内涵。其中“母性”和“女儿性”属于本能的范畴,“妻性”属于文化的产物。而在李佩钟身上,“母性”、“妻性”的人格内涵本来就是残缺的,仅有的一点“女儿性”也随着抗日工作的展开而迅速消解。组织抗日县政府之后,审讯拒缴军鞋、殴打乡村干部的公公田大瞎子,拘捕破坏拆城工程的父亲李菊人,通知中央军专员丈夫田耀武离婚,照她婆婆的话说“天下新鲜事儿,都叫她行绝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佩钟不是作为一个本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而塑造,而更接近于“中性人”的性格气质与思想内涵,即是说,仅从叙述的表层而论,李佩钟作为一位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女干部形象并非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但从文本的深层结构而言,她却是风云时代知识分子生存言说的载体,在她身上凝聚着作者对知识分子以及自身命运的深切焦虑。
李佩钟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经历吻合众多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她由喜爱文学而“看了一些文艺书,对革命有了一些认识”,尔后抗日大潮将胆小的她“卷进来了”,换言之,她是由文学青年转变成革命青年,在进步思想的召唤下投身革命的,即“只在理性上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2]518,这样的成长经历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颇为典型。孙犁自己的经历就与之很相似。李佩钟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与言说方式集中体现在她与高庆山的关系上,确切地说,《风云初记》中李佩钟与高庆山不是作为情感关系的对象,而是作为两种身份——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阐释符码而存在。但他们的关系却时常滑出预设符码的意义限制。毋庸置疑,李佩钟对高庆山怀有爱慕之情,高庆山对她也心存好感。高庆山临行前那个夜晚月下听歌、吃饺子时的温馨和谐,黄昏送别时的无言伤感,都证明秋分对丈夫们会忘记家里女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换言之,倘若我们事先不知道高庆山有一个生性贤惠且思想积极的妻子秋分,他与李佩钟发展成革命夫妻的结局毫无疑问是合乎情理。当然,叙述者知道应当克制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因为宏大叙事的文本中不允许渲染私人化的“暧昧”情绪,只有时时勒住感情野马的缰绳,才不至于走到革命文学的悬崖而粉身碎骨。因此,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展开,李佩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意识模糊、思想情感软弱的共性渐渐“浮出历史地表”,于是,只有依靠以高庆山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力量,她才得以克服自身的弱点,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与救亡运动中成长起来。在初任县长审讯公爹时,李佩钟“脸上发烧”,“心里慌乱”,但看见高庆山“严肃地站着,静静地听着”,心里镇定下来;在破路、拆城等一系列民运工作中,对政策的疑虑与顾忌经过高庆山的开导豁然开朗,勇气倍增,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总之,依赖于高庆山工作上的悉心引导以及为评论家所讳饰的爱情魅力,李佩钟从柔弱走向坚强、从幼稚走向成熟。
但是,即便迅速“成长”的李佩钟还是不时遭到高庆山的严厉指正。因为高庆山在小说中是一位思想成熟、经得起各方面考验的工农干部。不消说题在匾额上的“人民政府”应换成“抗日县政府”的原则问题,就是大义灭亲严惩公爹却还是落得高庆山要“锻炼锻炼”的严肃批评,以至于吃完饺子后李佩钟郑重地向高庆山提出一个问题:“是你们老干部讨厌知识分子吗?”自然,面对严肃的原则性问题,孙犁采用了20世纪50年代革命题材小说惯有的手法,让高庆山以工农干部的姿态谆谆教导思想有待进步的知识分子李佩钟。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描绘两人对话时的神情,但我们可以想象高庆山的严肃和李佩钟的虔诚,在这里,李佩钟已经全然抛弃了原先“娇嫩”、“女学生”模样的“小资情调”,也不复拥有在丈夫、公爹及父母面前的自尊与骄傲,一如信徒承受神父教诲。从近代直到五四,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艺术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启蒙者或先驱者的角色。20世纪40年代以降,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逐步落实,知识分子启蒙者的崇高地位被予以倾覆,对“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成为现实生活与文学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众多的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叙述者往往将“精神上有许多不干净处”的知识分子与“最干净”的工农兵相对比,以后者的崇高、坚韧、圣洁映照前者的卑下、软弱与龌龊。在《风云初记》中,当李佩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形象出现在文本中时,她展现给读者的印象是生动的、丰富的、热情的,但当她面对如高庆山般“又红又专”的工农干部时,顿时“自愧弗如”,充满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副被规训、被教导俯就的卑微情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既是知识分子李佩钟的尴尬,也正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包括体制内作家孙犁自己正遭遇言说困境的重要表征。
据孙犁写给冉淮舟的信件,《风云初记》尾声重写完成的确切时间是 1962年2月24日,并且当时“尚觉满意”[3]73。从1956年大病以后,孙犁很少动笔,1957年至1961年之间5年中创作上一片空白。而1962年的情况截然不同, 除完成《风云初记》编排章节以及尾声重写外,孙犁仅这一年还写成17篇文章。正如渡边晴夫所言:“孙犁于1962年在创作上有一定的收获,当然与其身体健康恢复程度有关,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对其影响的结果。”[4] 即是说,1960年冬至1962年春之间再度缓和的时代气氛是直接触动孙犁重写尾声的重要因素,从而激发了孙犁蕴蓄已久的关涉知识分子的言说冲动。反之,如果1962年春的孙犁未曾受到中央文艺政策给予创作者“充分的自由”的有力鼓动,目睹有关尊重艺术规律精神的“文艺八条”的出台过程,其萌发重写《风云初记》尾声的创作意图及择定李佩钟为叙述对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历经50年代《婚姻》、《钟》、《村歌》以及成名作《荷花淀》等作品因“思想性薄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等“不良倾向”遭致的多次批伐,至20世纪60年代本性胆小、慎微的孙犁无论如何不敢再“心浮气盛”地信笔书写。
另一方面,作为体制内知名作家的孙犁,在择定知识分子李佩钟这一敏感人物展开言说时,他明白倘若听凭想象力的驰骋酣畅淋漓地书写她的性情将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本是一种讳莫如深不便言说的心痛。而论者及文学史家对孙犁未曾展开李佩钟这一复杂形象的深入开掘多有微词,也是忽视孙犁内心深处不便言说的苦衷而认定为刻画人物能力的问题。亲历某熟人被捕时“可能脸色都吓白了”的惊吓,“反胡风”、“反丁陈”事件的强烈刺激,都成为孙犁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所以,孙犁为知识分子李佩钟设计的是一个欲扬又贬颇具多重意味的结局。一方面,孙犁借烈士身份的英雄化叙事方式“美化”知识分子形象,即用拔高的方式凸显久为意识形态与工农干部贬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先进,用低回的语调倾诉久为“血统论”压抑的知识分子身份的郁闷,以至于写成后有“尚觉满意”的快慰。另一方面,孙犁深谙此“扬”有赖于彼“抑”的支撑才得以确立,唯有恪守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规范,作品与人物方可得到认同。在写于1962年4月1日,即重写尾声后写作的怀旧散文《清明随笔——忆邵子南同志》(4月5日发表于《天津日报》)中,孙犁批评友人邵子南“化大众”的主张:“片面地从文艺还要教育群众这个性能上着想,忽视了群众的斗争和生活,他们的才能和创造,才是文艺的真正源泉。”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大众化”的文艺立场,严肃的语调更似乎纯粹是站在旁人的角度对已逝友人做出评判。不过,随着叙事的推进,另一个孙犁总会像个顽皮的孩子偷偷从遮蔽的屏障后溜出来,向读者展露他的真实面孔。在邻近结尾时于徐徐忆旧中孙犁突来一笔:“今年春寒,写到这里,夜静更深,窗外的风雪,正在交织吼叫。”无论是先前对友人义正词严的批评还是结尾猛然闪现的象喻式景物描写都昭示孙犁对严峻现实的敏锐感知与清醒认识。
故此,孙犁作为一个间性主体使他在补叙李佩钟的命运时,被一种复杂矛盾的情绪所困扰。一方面,孙犁对李佩钟怀着同为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与深切眷恋,“烈士”就是一种有意彰显李佩钟先进革命意识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畅所欲言,更不能让其钟爱的李佩钟在新时代健康而快乐地继续活着,因为“以逝者之所长,补存者之不足”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她不够纯正的革命者身份的“缺陷”,从而获得以高庆山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情与认可。诚然,孙犁于心不忍又迫不得已的苦痛自不待言。李佩钟是他所有小说中学历最高、地位最高的知识女性,也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孤独、最凄凉的女性形象。尽管如此,1963年出版伊始李佩钟人物形象中那些“不够健康的感情”、“不适合革命要求的方面,和革命精神不相符合的方面”[2]519 依然遭到人们的批评与责难。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文学视做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认为政治阐释是所有阅读与阐释的绝对视野,因为“像文本一样,作者被视为一个交互作用的交点,意识形态、欲望和历史必然性在这里纵横交错。政治无意识作为这种诸层面的结合,仍然是使文本对历史开发的基本模式,因为作为欲望、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它的因素具有‘实际经历’的丰富性”[5]12。在历史形成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里,意识形态都以自己的某种方式影响或支配着文本生产的发展,同时,文本生产也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参与或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播撒,从而造成知识与权力、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关系中永远无法消释的矛盾。《风云初记》重写的尾声正是产生于这些矛盾挤兑的裂隙之中。
收稿日期:2006—03—20
收修日期2006—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