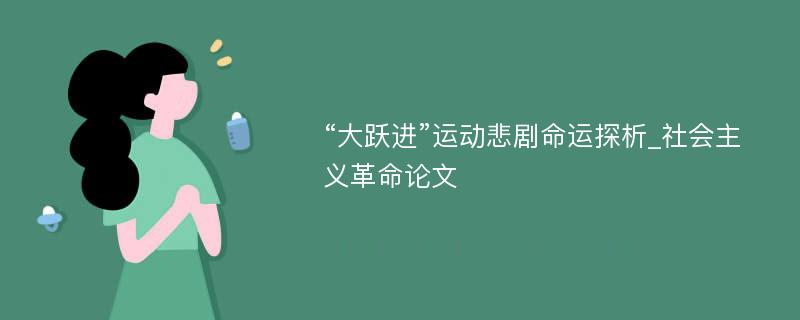
“大跃进”运动悲剧命运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悲剧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3)03-0048-06
“大跃进”运动是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悲剧性探索。这次探 索从理性的认识出发,最终却滑向非理性的歧途。其中的复杂原因和深刻教训应当给予 深入的探讨和总结。
一、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与“政治统帅经济”
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 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 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内主要矛 盾的变化,党和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生产力。顺着这一思路,毛泽 东在1957年上半年的一系列会议上讲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 建设。遗憾的是,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 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 的矛盾;在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 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就把社会主义革命结束的时限大大推迟了。
但到了1958年初,毛泽东的注意力又回到建设上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明确提出:“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 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1]这里所谓“技术革命”,可以理解 为经济建设的同义语。工作着重点转移思想的提出,说明反右派斗争尽管促使毛泽东提 出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并未使毛泽东离开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充满激情地说:“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 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1](P,350)难道能说毛泽东的这一番话不是出于理性的认 识吗?
那么主观上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后来为什么又走上了忽视乃至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非理性轨道了呢?
从指导思想上找原因,“政治统帅经济”或曰“政治挂帅”的思想在当时起了负面的 作用。
笼统地讲“政治统帅经济”或“政治挂帅”似乎并无不可。问题是在于这种提法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特定的内涵。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提出:“从1958年 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 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 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2]这段文字清楚地阐释了“政治统帅经济”或曰“政治挂 帅”的内涵。所谓“政治”概指“思想、政治革命”,它与“技术革命”即经济建设的 关系是统帅和士兵的关系、君与臣的关系。“政治挂帅”,也就是思想、政治革命挂帅 ,也就是阶级斗争挂帅,处在“君”的地位。中国有句古语叫“君为臣纲”,因此阶级 斗争也就成了其臣属——“技术革命”的纲。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概 源于此。
由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不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是阶级斗争挂帅,“大跃进” 运动不能不偏离理性的轨道。表现之一是过去搞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经 济建设,在各个领域大搞群众运动,尤其是发动全民大炼钢铁,场面极为壮观,几千万 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表现之二是把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毛泽东批评周恩 来、陈云的反冒进为右派所喜,为右派言论。认为冒进为左派所好,为革命精神;冒进 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 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由于把经济建设方针的分歧上纲为马克思主 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就使得主张反冒进者三缄其口,按照经 济规律办事、稳步前进、搞好综合平衡的思想受到排斥。表现之三是试图以阶级斗争推 动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做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号召拔“白旗”,插红旗,彻底批判一部分富 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试图以此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进一步鼓足 人们的革命干劲,从而带来经济建设的大跃进。
由此可见,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政治挂帅”与工作着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在 “大跃进”运动中同时并存,相互交织,又相互背离。这是导致“大跃进”运动走上违 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非理性轨道的根源。
二、“以苏为鉴”与回归革命经验
“大跃进”的发动,从主观上讲是为了超越苏联模式,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 度建设社会主义。对于这种愿望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一五”时期,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较多地搬用了苏联“老大哥”的经 验。这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问题。毛泽东对于照抄苏联模式很不满意,1955年底他就率 先提出要“以苏为鉴”。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存在问题的揭露,使毛泽 东进一步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 路,你还想走?”[1](P,23)从而正式向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党围绕这一任务提出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卓见。如“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 新经济政策”;“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的经济建设方针,等等。应当说,这些探索成果已经在一些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这 在当时苏联模式影响极其深广的年代,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1957年的反右斗争并没有使毛泽东放弃“以苏为鉴”的思考。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 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3]不幸的是,此后的“以苏为鉴”偏离了反右以 前的轨道,逐渐与回归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联系在一起。
对于回归革命经验的原因,胡乔木曾有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 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4]“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 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 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4](P,266)胡绳也与胡乔木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套办法有了无限崇高的威信,这 就很容易造成在自己没有新鲜的经验,别国的经验也不愿意照抄的情况下,回头来从民 主革命胜利的若干具体经验中寻求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且用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抽 象概念来解释这种经验。”[5]
上述解释讲到的因素——自己没有新经验、不愿照抄别国经验、旧有革命经验的惯性 作用——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但这些因素在反右之前业已存在,那时为什么不发生回归 革命经验的问题呢?
显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这就是反右斗争所引发的反对修正主义问题。1 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下决心反右的同时明确提出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11月 ,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需要同时反对教条主 义和修正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6]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一方面更加自觉地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尤其是维护“斯 大林制度”,另一方面又对斯大林时期采取的某些旨在刺激个人生产积极性的做法以及 赫鲁晓夫实行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些做法和措施是搞物质刺激,奖 金挂帅、利润挂帅,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渊薮。“以苏为鉴”,他迫切希望能找出一种不 同于苏联的依靠群众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来发展经济的新方法。而革命经验正好满足了 毛泽东的愿望。
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大跃进”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经验在建设年代的一次大 规模重演。各方面工作都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在激励机制方面突出“政治挂帅”, 在分配形式方面倡导恢复供给制,在领导体制方面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在“大 跃进”期间多次深情地谈到战争年代创造的这些经验,他对革命经验在建设时期的效用 充满信心,坚信回归革命经验将使中国经济比苏联发展得更快更好。然而,事实证明革 命经验在“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有许多是是负面的。它所体现的不是工业文明的科学 主义和经济理性,而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和浪漫激情。它背离了苏联经验中的专家治 厂、经济核算和科学管理等理性原则,代之以带有浓厚非理性色彩的“命令经济”做法 ,这不能不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提出“以苏为鉴”,旨在克服教条主义,使中国经济发展少走弯路,而回归中国革命 经验,则使经济发展走了更大的弯路。一个原本极富有创造性的命题,却造成了意想不 到的结果。历史和人们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与唯意志论
“大跃进”既然要开创一条别人都没有走过的新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就成为 必须。没有一种敢想敢说敢做的胆略和气魄,没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就不可能 走出一条新道路,干出一番新事业。毛泽东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深谙此理。因此, 在“大跃进”的发动过程中,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问题。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 独创精神。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 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在八大二次会议 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 威所吓倒。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要敢想 、敢说、敢做,不要被某些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手束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 人的创造性。要割掉奴隶尾巴,反掉贾桂作风。要敢于标新立异。不要怕教授,不要怕 马克思,不要迷信科学家。工业化并没有什么神秘。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在 5月18日和6月17日,毛泽东还先后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打倒奴隶 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批语。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和批语,当时曾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 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应当说,毛泽东的这些话基本上是正确甚至是精彩的,充分展现了 他作为全党领袖大胆探索、锐意开拓的宏大气魄。其主导思想在于激发全党同志和全国 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热情和意气风发、勇于创新的精神。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切地感受到了劳动人民身上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认为这是创出新路的宝贵资源。而开掘这种资源的方法就是“揭盖子”,打掉自 卑感,破除迷信,这样就可以使人民群众潜藏着的热情和智慧爆发出来,为社会主义建 设新道路的开辟贡献力量。能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种看法是非理性的吗?
然而,在“大跃进”运动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实际成果却大多是荒谬的, 非理性的。当时流行的口号是“破条件,创规律”,“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唯心主义的空气笼罩了中国的上空,全国进入了狂想蛮干 的年代。“农村为了放出高产‘卫星’”,大力推行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密植与深耕。 结果密不通气的秧苗成批发病死亡,深翻出来的生土根本种不了庄稼。工厂里的“技术 革新”也爆出了一个个类似于“永动机”式的发明创造大笑语。
严酷的事实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倡导者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 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实践中脱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演变成为忽视客观规律 ,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论。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群众的主观 能动性得到了空前的展示;提前结束的三大改造更是显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能量 。革命在一定时期内“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助长了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过分 崇信。在面对向自然界开战这一新的任务时,人们很容易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仍是最 重要的因素。只要有了革命热情和英勇精神,经过几年或者几十年苦战,搞几次大的会 战,就能够解决问题。
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想法。事实上,搞经济建设最重要的是认识 、掌握、遵循和利用经济规律。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大批干部由于过去长期从事政治 斗争和军事斗争,往往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对经济规律既不重视也不感兴趣,因 而在领导经济事务时常常感到不适应,受束缚,受压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 号一经提出,客观上使得这些干部借机摆脱那些经济规律、规章制度、条条框框的束缚 ,凭借主观想像进行所谓“创造”。更有甚者,以长官意志对群众进行瞎指挥,为了迎 合上级急于创新的愿望,可以毫不顾忌地进行“造假”。亩产万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 斤之类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当时的氛围下,如果谁对这类荒唐行为提出质 疑,就会被戴上“右倾保守”等的帽子。解放思想变成了胡思乱想,破除迷信变成了破 除科学。“大跃进”的悲剧命运就这样注定了。
四、“赶超战略”与“积极平衡论”
“大跃进”是我们党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赶超战略 ”是基于对形势正确考察的理性选择。
从国内情况看,一方面,革命的胜利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 人,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上“一穷二白”的严峻状况实在不 容乐观。毛泽东坦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 能造。”[7]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中国 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 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P,350)
从国际形势看,政治上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经济上社会主义却落后于资本主 义。西方大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强大的压力。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受 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政治孤立、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处境极为不利。
落后就要挨打,就会被开除“球籍”,这样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促使我们 党努力寻找改变落后状况的良策。这时,苏联的经验给我们党以启发。回顾历史,列宁 早在1917年就提出了“赶超”思想。他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 且超过发达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 的。”[8]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赶超”思想付诸实践,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集 中全国的资源全力实现工业化,使苏联仅用十年多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 ,其成就是巨大的。
前有列宁的教导,后有斯大林的示范,“赶超战略”就成为我们党的当然选择。而中 国革命胜利后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威力的崇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于先进生 产关系将带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心理预期,更使我们党增强了实现“赶超战略”的信心 。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党选择“赶超战略”绝非一时冲动,恰恰相反,这 一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理性的。但是,赶超战略后来走向了极端,目标实现的时 间一再提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定越高,空想色彩越来越浓厚。毛泽东先是在八 大二次会议期间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口号,不久 就认为赶超美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时间。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10万吨 ,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了一番。为了完成高指标,北 戴河会议后不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浪潮,据统计,参加大炼钢铁的人 力超过了1亿,也就是说,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6。一种理性的选择最终被非理性的狂 热所吞噬。
赶超战略之所以会走向反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积极平衡论 ”的提出。
由于赶超战略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 度,就有必要在一个时期内集中力量发展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对 它们实行倾斜政策。但是这种倾斜必须是适度的,以不破坏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原则, 否则就会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危害。遗憾的是,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八大确 定的“综合平衡”原则没有重视。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从哲学的角度指出:“我们的 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净是 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3](P,313-314)他主张要不断打破平衡才能使经 济获得更快发展。“大跃进”运动初起时,有些人就产生疑虑,担心国民经济的平衡遭 到破坏,会搞乱整个经济秩序,毛泽东不赞成这种观点,他在南宁会议上坚持认为,平 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如果一定要讲平衡,那么这种平衡 应该是革命的平衡,是积极的平衡,而不是消极的平衡,不是保守的平衡。这就是后来 被概括为“积极平衡论”的思想。据此,《人民日报》在2月28日发表社论,提倡积极 平衡,提出积极平衡就是提高落后指标和定额向先进看齐,“时时刻刻向旧的事物冲击 ,向旧的定额、旧的指标、旧的规章制度挑战。”[9]社论实际上否定了“八大”提出 的“综合平衡论”,认为那是“庸俗的平衡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明确 指出,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
“积极平衡论”过分强调了不平衡的作用,忽视了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只 强调平衡向不平衡的转化,忽略了转化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只强调转化的主观条件,忽 略了转化的客观条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来说,忽略客观条件的制约必然会导致致命的 后果。“积极平衡论”一经提出,既为计划工作处处留缺口,搞长线平衡,任意定高指 标找到了理由;又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加上片面 强调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结果造成了各生产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经 济比例失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又带来了商品奇缺、市场全面紧张的恶果。在付出沉 重的代价之后,毛泽东不得不承认:“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 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10]
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巨大反差使“大跃进”运动成为一场深刻的历史悲剧。悲剧固 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正确的先导。正是 在对“大跃进”的悲剧命运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化建设才有了改革开放新 时期的辉煌成就。
收稿日期:2002-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