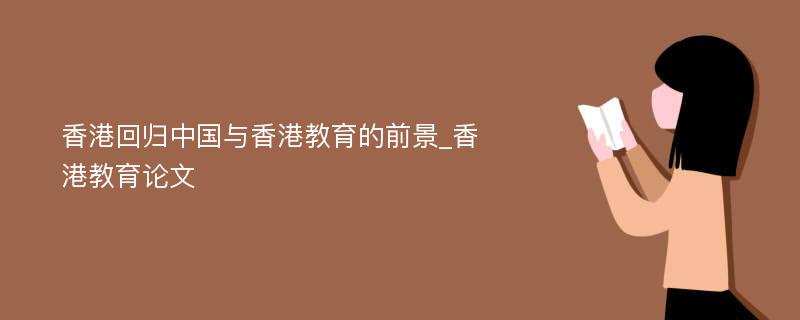
香港回归与香港教育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香港回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香港回归指日可待。在尚未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数年前,香港教育界已未雨绸缪地着手研究香港未来教育。其中香港大学副校长、香港政府许多咨询教育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教科文组织等机构顾问和负责人程介明教授从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维度地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对香港教育现状分析、未来构划以及从中体现的教育思想颇具灼见、富有启迪。限于篇幅,本刊择其一、二发表,以飨读者。(标题编者加)
1997后香港的教育怎么办?这不是三言两语、一个人的智慧可以解答的。正因为如此,研究1997后香港的教育显得更为迫切。
从现在的形势看,只有清晰地分析香港教育现状,才能胸有成竹地知道保存什么,去掉什么;只有将香港教育放在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回归后的教育趋势和如何为中国大陆乃至世界教育作出贡献才能明晰香港教育界当前该做什么?以及今后怎样持续稳定发展,以无愧于国际大都市称号。
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教育的应对
“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在理论上甚少有争论,即使是有争论,也往往限于政制方面。政客们甚少相信,政制不解决,其他努力都是枉然。其实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是由许多社会部门综合而成。教育领域,也将是“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
人们固然对政权及政制的交替与变化非常关注,但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切身的工作有何变化。愈是坚守本职岗位的,愈是如此。假如他们对于切身的变化无法预期,对即使是近期的变化也无法掌握,他们也就无法对“平稳过渡”产生信心。政制的变更如何,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次要的。因此,研究教育领域的“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刻不容缓。
“一国两制”是个多元概念,承认一个问题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解决方案,而多个方案之间,各各平等,不一定能以优劣、是非划分。教育制度,也是如此:若不承认“两制”内在的深刻由来与规律,勉强以优劣划分,或作政治判断,就难诚心地为两制共存而努力。
教育制度由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塑造而成,而且经过历史之演化而成。香港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又隶属于东亚文化体系;因此,香港的教育,多元之中含统一,竞争之中见公平;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后天与先天之间、严格与宽松之间、道德灌输与思想自由之间,都有其独特的平衡取向;逐渐形成一套柔合中西文化的教育思想体系,而有别于其他华人社会。认真研究并总结香港的这一制,是实行“一国两制”的重要前提。
香港的教育制度反映着这种教育思想体系。这个制度的优点缺点,必然会在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下有所反映。即使因外来因素或一时之政治行为而造成突变,也必然无法长久。在其他国度,不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教育改革,或无疾而终,或因紊乱而不可收拾,屡见不鲜。
因此,任何教育改革,必然以专业教师为主体,采取符合当时当地情况之途径,方会有效。也因此,教师专业权利之受尊重,不是为了教师本身的权力或权益,而是为了教育的健康发展。最近香港教育的发展,如专业教师参与决策之增加、教师公会之提出、以专业姿态出现的教育评议会,都循着这个方向。
专业教师主动参与教育政策的讨论与决定,是香港应引为自豪的。其参与程度,其他地方难与之匹比,虽然香港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港人治港”在政权的层面还会有许多争论。但是在政策的层面,就教育而言,还看不出有因政权移交而非大变不可的政策。因此,完全可以保存现有的架构与咨询机制,以保存决策过程中参与者与基层教育工作者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应该是“港人治港”在教育领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保存咨询机制,还牵涉到人选问题。目前的委任制度,在新的政制下必然会遇到挑战;但是完全的代表制度,又会全面改变咨询机构的参谋性质;因此必须从长计议。最近教育评议会提出的“政策议会”是教育界一个共议政策,求同存异的一种机制,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方向,又可以不代替行政决策,但同时也可以对各类咨询机构产生监督作用。教育界有长远的共商共议的传统,不同道也可以为谋,“政策议会”应该有相当好的基础。
“港人治港”,不能等到1997年7月。在此提出呼吁:
1.请各政策咨询委员会,以港人治港的主人翁姿态,关心并研究1997年政权交接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务使不致因外交争端而出现教育混乱;
2.请现任政府开放并鼓励各政策咨询委员会讨论研究1997后之教育政策;
3.请中国有关机构申明保存现有的教育政策咨询机制。
对教育界来说,建设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的香港,现在就开始了。
转变固有观念——在教育及文化上作出国际贡献
1994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中,香港的生产总值名列全球第19位。但这只是1992年数字,目前的情形实际更佳。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上就会期望她对其他国家作一点贡献。传统的西方列强,都设有专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机构,例如英国的ODA(海外发展专署)、加拿大的CIDA(加拿大国际发展组织)、瑞典的SIDA(瑞典国际发展专署)等等。这些国家都拥有一笔基金,专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发展项目而设。往往还设有专门与文化教育有关的机构,与其他国家交往。例如英国文化协会、瑞典的SERAC、德国的ADDA等等。这些传统的强国,都把援助发展中国家作为国策必要的环节。
这样的国策,当然与这些国家当年殖民地宗主国有关。但是今天,却起着结交国际朋友,争取国际影响,参与国际联合等作用。
近年来,这个俱乐部又多了一些新成员,例如以往偏安一隅的澳洲,近年就颇为活跃,积极参与互助发展中国家事务;日本和南韩,都努力想争取成为大的施主(donor)香港、新加坡也许是少有的例外。
以香港的经济状况来说,看来不能再长期保持一毛不拔的姿态。否则,生意也许还可做,香港却只能徘徊在国际大家庭的门外。从积极的角度看,香港的价值,完全在于她的国际地位;而参加到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也是其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上没有只取不予的事,国际地位也没有免费午餐,一心跻身强势经济行列,却对发展中国家不屑一顾,那只能在国际大家庭的门外徘徊。
笔者在多次国际论坛上提出的,北南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施受范式(Donor-Receipient Paradigm)。香港因其经济水平而被摒出受方名单;但香港又不是施主,因此在许多国际场合中,香港是被遗忘的一个地方。
但是香港若是简单地参加施主俱乐部,项多敬陪末座,也会染上施主们在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坏印象。从这一角度看,香港若真的要对国际大家庭作一点贡献,大可以不必走老牌列强的老路,而应创出自己特有的模式。
在教育及文化的领域作出贡献,是一个甚为可行的起点。以教育及文化作起点,有许多优点。首先是教育及文化的项目一般数额可大可小,丰俭随意,香港人买一个居住单位的钱,就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做许多教育或文化的大事。第二,教育及文化的项目,一般时间伸缩性大,可以在短期内完成很多。第三,教育及文化项目也可以教育本地的青少年,让他们不要以为世界就只有英、美、日、澳、加。第四,近年香港在教育及文化方面已经进入了不少国际网络,因此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有很好的基础。第五,香港并不拥有强势文化,因此不会被看作文化侵略。
关键不是钱、不是时间、也不是能力,而是整个社会的支持。教育及文化界应多作宣传,以引起社会的注意,让社会明白个中的道理,明白这也是香港前途关键的一着。
传媒的协助很重要。但教育及文化界一般唱低调,不喜欢也不善于营造新闻;但是各报章的教育文化版,由于记者或者编者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方面,失去了传媒推波助澜的作用。像前一阵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在港举行,正是宣传香港国际贡献的好机会。但是报章上登出来的,却是传媒乘机访问主持开幕的本地高官,内容则是本地一个热门话题,而著名的数学国际奥林匹克,却变成了某国际比赛。广东人的说法,真是“捉到鹿不懂脱角”。如此,如何当国际大都市。
社会上的意识也很重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建议增收外地研究生。近日读得学联的评论,担心会占据本地研究生就读机会。本地研究生是否会减少就读机会;本地研究生是鼓励其在本地还是往外地就读,外来研究生是否需要收一点费(或分类收费),都值得探讨的。但是总的方向,香港收一点外来研究生,不应只看成是为了增加本地教育的国际色彩,而也应该看成是香港对国际大家庭的一种贡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3年的估计,香港在外地就读受教育的近3.3万人(其中美国1.3万、英国6600多人、加拿大6800多人、澳洲5100多人),自己往外地去的多多益善,有人来香港则耿耿于怀(当然,香港学生往往是自己带钱去留学的)。接受外地学生,有许多外溢利益,不是斤斤计较学位、收费可以计算得出来。连研究生的门户都不敢开放,如何参加国际大家庭。
笔者正主持一个国际教育研究网络,下面联系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6个教育研究网络。这些网络都接受着发达国家的资助,但是他们说:“我们信任香港,因为香港对我们不会有野心;假如香港也能有些钱资助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哪怕是一点点,就可以使我们有所选择,打破传统施主的垄断!”
香港要成为国际一分子,就要摆脱孤岛心态,再不能一毛不拔。教育也不例外。
成功与抉择——香港教育的走向
21世纪,香港的教育怎样才算作了贡献?怎样才算真正有了进步,真正现代化?
科技的进步,相当多要向西方学,但教育的现代化却未必能给我们一个答案。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不能简单地搬用,必须谨慎地借用。那么香港教育要大步前进,应该向哪方面进取呢?笔者认为“成功与抉择”是香港教育发展的微观方向。
“成功”,是指让学生学会成功。香港社会重竞争,是讲究适应能力的社会,这是香港“东亚奇迹”的基点,我们没有理由随便抛弃。
事实上,不少西方的教育制度,在教育危机与失业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正在想方设法在教育中加进竞争与适应的因素。西方教育中一些成功例子,正是由于保存和发扬了学生个人的竞争能力,而不是相反。
在东亚教育圈中还有一套与竞争及适应相应的辩证哲理,如先苦后甜、勤能补拙,都是讲究调动人的能动性,以后天克服先天,以刻苦换取成功。这些哲理,在西方教育思想体系中甚少强调。但这些特征,可以是积极因素,也能成为消极因素。“竞争”可以积极地鼓励上进,也可以消极地制造挫败;“适应”可以令人灵活、机智,也可以变为盲目服从;“苦”可以使学生生活变得毫不愉快,制造灰色人生观;“勤”又可以变为无限量的榨取学习时间,使学生终日生活在压迫之中。
不能使消极、迷茫、失意、被动成为我们中小学的产品,更忌从幼稚园开始就在制造这样的未来成人。
要保存和发扬中国教育传统优势,必须使这些传统带上新的时代色彩。笔者认为,从哲理来说,是要在教师心中树立学生的个人价值,让学生看到自己的价值。从实践来说,则是让学生经历成功。
要使学生和教师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价值,都可以获得成功。学生能力千差万异,但总有自己的优势,总有可以成功的一面。要求学生学会竞争、适应,通过刻苦、勤奋,发扬自己的长处,获得“成功”。
这方面,值得介绍上海闸北八中的经验。这所“薄弱初中”,收的都是“差生”,类似香港的“第五组”学生。这所学校有针对性地去除学生的消极自我观念,强调学生的自我开发。难得的是,闸北八中至今仍然只收差生,至今仍然在非重点的拮据资源下生存。
与成功并列的,是“抉择”。要学生认识自己的价值,必须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权利,从政治角度看,是争取;从教育角度看,则是抉择。也就是给学生选择的机会。
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中,孩子从小依着大人定下的框框,规行矩步地生活。从入学、升学、婚姻到事业都受社会的摆布,个人要作重大抉择的机会少之又少,真正有抉择的时候也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社会变了,大人的框框再也缚不住孩子。但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跟上这种形势。学校仍然认为学生的生活完全可以由学校控制,由起床一直控制到学生上床睡觉;教师仍然以为教师是知识的唯一泉源,是价值观的唯裁判;家长仍然指望孩子们要乖、要听话、要循着大人为孩子铺的路走。这一切,都已经不切实际。孩子们有自己的另类世界,他们要在自己的世界中作出抉择,大人却一点也不给孩子们选择。这里并不是鼓吹西方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也不是主张极端的学生中心的教学模式。但是给孩子、学生予选择,却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也是可行的。给予选择,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自由放任与毫无选择之间,还有很宽阔的空间。选择,可以渗入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比如:
叫孩子做事的时候,是否只有一种做法?可不可让孩子有多种选择?
孩子问我问题的时候,是否只有一种答案?可不可给孩子一个以上的答案,让他选择?
孩子问怎么办时,是不是一定要给方案?可不可以引导孩子在多个方案中选择?
显然,要让孩子们抉择,家长教师要过两关:第一,比较平等地对待学生;第二,承认方案、答案都可以是多元的。从婴儿的父母到大学的教授,都可以让孩子、学生有一点抉择的经历。从教育观点看,关键不在于答案或方案是否正确,而在于孩子是否经历过抉择的训练。长年累月,经常经历抉择的孩子,与很少机会经历抉择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香港要民主、中国要民主,起点在教育,关键在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