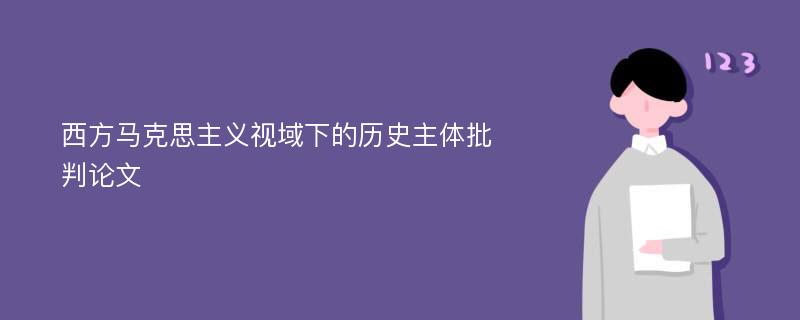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历史主体批判
李高荣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 正统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和阶级意识两个层面界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沿着上述两个层面推进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将经济基础与阶级意识两个分别对应为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在实践主体的探究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历史主体的问题上显示出更为多元的倾向:有对传统革命主体——工人阶级——的坚持,也有对其的扩展和补充——新工人阶级,更有对其的背离——消解工人阶级;在理论主体上,现实政治层面主体的退却,为思想理论主体的研究释放了空间,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中,他们在形成深刻理论洞见的同时,也使得主体玄学化、形而上学化,大量谈论人的抽象类本质,而忘记了实践中具体的个人,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摆脱普遍异化的具体策略。这是整个西方左派的总体困境。也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中应该极力避免的重大缺陷。
关键词: 实践主体;工人阶级;历史主体;理论主体
历史主体问题是关乎谁来改变历史的根本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无产)阶级是历史最重要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主体。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有着共同的客观利益基础,因而可以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401)列宁进一步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2](11)。尽管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但马克思也批评了不能仅仅从财产与收入的多少、从事的行业来区分阶级,“‘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3](343)。这即是说,阶级也是一个关系概念,反应的是基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与资产阶级针锋相对的政治主体范畴,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阶级属性,但同时他也承认工人阶级要从一般阶级上升为主体阶级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即从“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4](654)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阶级的界定本身就包含了两重视角:客观经济基础和主观意识形态。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阶级身份的建立,也就需要从现实革命实践的立场和阶级意识的培养两方面来进行。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5](547)随着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学者①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消失论”此起彼伏,尤其在东欧剧变后更是甚嚣尘上,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工人阶级不再是否定、对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力量,丧失了实践上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地位,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淡薄,日益被同化、融入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中,呼吁要重新寻找社会解放的主体[6]。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主体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消解的过程,对工人阶级的独特阶级意识的认识也体现出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完全抽象的谈论人的类本质再到消解其历史主体的典型特点。本文即从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两个维度将一些典型的代表性观点串联起来,以期从整体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观,并对这些认识进行总结和批判。
一、实践主体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的、整体的社会生活组织模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学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物质丰裕时代,信息化、工业化、后现代化是其基本特征。这一阶段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对阶级斗争的化解,对多元异质社会文化因素的包容,等等。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成“菱型”。尤其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来,整个西方社会思潮从对阶级主义的过渡张扬,转向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工人阶级的力量完全被分化,社会不再按照经济地位的高低来将所有的阶级划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阵营,整个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多元化。针对各种具体的、多样化的微观压迫而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等等,取代了传统无产阶级的革命。革命主体也从“阶级政治”转向“话语政治”和“身份政治”,更加强调多元分化,强调差异性和边缘化的话语力量,从“为了权力而斗争”到“为了承认而斗争”,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跟作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时消失了。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政治追求、消费观念等方面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逐渐趋同,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批判精神,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支柱,成为单向度的人。面对新时代新情况,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出于自己的立场对历史主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方案:有的继续高扬传统革命主体,有的提出应结合时代背景对其进行改造,也有认为应该完全跟随时代步伐消解革命主体②。
(一) 传统革命主体——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同角度对阶级、工人阶级进行了分析,主要是从不同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立场来划分阶级,指出对立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并对工人阶级赋予了革命主体的期望。但是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工人阶级的构成以及形成机制方面的探讨不足。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家E · P ·汤普森从工人阶级的国别史角度对阶级进行了考察,强调了文化等上层建筑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突破了经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视角的局限,对阶级概念和阶级形成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将阶级定义成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像病人躺在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那样让人随意塑造”[7](1)。在某种确定的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因相似的经历、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法律知识等感受到彼此之间存有共同利益时,阶级就出现了。汤普森阶级观点的形成融合了传统的生产关系、文化等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意识,对伍德的阶级理论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的大规模施工在我国不断展开,不但使人们的实际需求得到了满足,也使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路施工的质量,广大人民群众也渐渐重视软土路基施工的质量,鉴于此,相关施工技术人员应该深入了解路基的真实情况,不断优化、创新软土路基的施工技术,提升软土路基的施工质量。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认为目前对阶级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用阶级意识来定义阶级(卢卡奇、葛兰西等),一种是用生产关系来定义阶级。她认为第一种“在缺乏已形成的清晰可见的阶级自我意识时,则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展示阶级的影响;并且,对于宣称阶级概念只不过是在毫无历史证据的情况下从外部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驱动的理论构想的说法,他们也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8](79)。因此,她对第二种定义进行了详细准确的论述,从经济政治层面而非文化哲学层面来界定阶级的内涵,采取的是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列宁开辟的传统)。她首先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正面阐述了阶级包含的三个层面:①阶级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②阶级的形成需要“经历”③一个过程;③阶级形成后应该从阶级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她接下来在对“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NTS)的批评中再次阐发了自己的阶级理论。她否定了NTS对阶级的重新界定和划分标准,批评了查尔莫斯的“新小资产阶级”——商业雇员以及银行雇员、办公室文员和服务人员以及某些职业性群体等“新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她依据技术要素而非经济因素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模糊了阶级的客观基础,得出了无产阶级消失的结论。同时,也批评后马克思主义依赖变动的力量——跨阶级的联盟——通过“和平民主”来实现社会主义,如此存在差异化、缺乏统一阶级基础的主体只能是十分抽象随机的,后马克思主义极力强调“差异”,坚决拒绝“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以及阶级政治,只能在“去除了简单的、机械的,原始的决定论之后,能保存下来的就只有绝对的随机性。在实践中,它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历史纯粹是偶发的——或者就是没有历史,也没有决定性的历史条件、关系与过程”[9](75)。伍德在对各种消解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观点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批判高兹的“非工人非阶级的”、 批判拉克劳、默菲的“人民同盟”),坚决捍卫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全球化必然会导致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严重的贫富差距、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等,重申阶级斗争可以激发人们的斗争热情,时代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机遇。除此之外,她还讨论了阶级与国家的关系,认为国家只是在阶级社会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本质应该是一种形式的公共权力。这样,当阶级消亡的时候,国家仍然存在,因为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也需要某种代议形式,而非完全民主的自发形式。她还从民主与阶级的关系重新梳理了民主的定义,批评了拉克劳和默菲提出的未来社会是“多元”主体为“激进多元民主”而进行的斗争,而非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批评他们将民主定义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遮盖了民主最初的阶级意蕴。
由上可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主体的探索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这个时代是由资本带来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激烈的冲突,对传统阶级结构和个体价值的冲击和重构造就的。后现代主义从理论上对现代化所带来问题的反思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主体的重构提供了致思路径:如果说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那里,对主体的宣扬还带有实践的特征——历史语境中的主体,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续发展则完全偏离了这种中庸,走向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种致力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依据“实践理性”的要求,探索“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16](58)。然而讽刺的是,马克思说法国的实践哲学传入德国后成了思辨的玄学,而等到20世纪中期这一思潮再次回到法国时,法国的知识界却极力地将其发扬光大,全然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实践传统。
(二) 重建革命主体——从新工人阶级到消解工人阶级
但残酷的现实表明,这种虚构的、无阶级、无政党组织形式的自治主体运动到底能否成功地引导出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前景并不容乐观,正如“黄背心”运动已经渐趋冷却。即使西方左派如奈格里们对大众的反抗持有积极的乐观态度,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和历史主体仍旧在探索中,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仍旧困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主体观上尤为明显,缺乏可现实化的具体路径是其遭遇的巨大挑战。
马尔库塞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使得社会的各种对立面和矛盾不断地同化、彼此融合。然而事实上,“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11](8)。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日益丧失的情况下,“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对革命的意识占据统治地位。当然革命的意识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才会显示出来;但是和以前相反,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同化,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是扎根于基础,扎根于垄断的政治经济之中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一般地位和革命意识的发展是相对立的”[12](84)。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犹如一架巨大的机器,不再只是单方面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而是作为一个系统将任何摄入其中的个体都变成其中的一个零部件,人在机器里面被抽空了一切,丧失了主体性,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跟着这个机器一起运转。这里被革命的对象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而是要推翻这个冷冰冰的庞大体系;被解放的人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而是普遍的、抽象的、“异化的人”。让普遍的人摆脱异化的状态,这是全人类的命运。现实政治层面主体的退却,为思想理论主体的研究释放了空间,主体玄学化、形而上学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大量谈论人的抽象类本质了,其中谈论的最为深刻的是法国马克思主义。
一是反腐职责与保护地方经济的矛盾。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官权与商业资本的联合,并且腐败案件涉及的商业项目资金数额都较为庞大,若依照程序严惩腐败分子,则与腐败案件关联的商业项目必然随之枯萎,地方经济遭受损失。反之则是容忍腐败分子侵吞公共财产,扰乱市场秩序。在反腐工作与经济保护之间的价值选择成为阻碍反腐绩效的矛盾之一。二是价值与执行相脱节。在复杂的利益纷争下,公共部门所推崇的政治价值、管理价值等基本公共价值在官僚系统运行过程中容易走样,无法真正指导和落实到执行过程。
二、理论主体
虽然马克思一直都将现实的革命主体当作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但在马克思去世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和工人政党仍然存在,但他们丧失了独立的阶级意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者和意识形态的同谋。这一变化在卢卡奇、马尔库塞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都有描述。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卢卡奇,其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即是他有关历史主体的论述。在其早期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尤其重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培养和觉醒,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卢卡奇借用黑格尔的主客辩证法,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具有了阶级意识(类似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之后,才能将自己从历史的客体上升为历史的主体。这里的阶级意识不仅仅指那种局限在本阶级的局部利益和特殊地位里的自在意识,“它的阶级利益,它的阶级意识使它有可能根据这些利益来组织整个社会”[10](107),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超越了一个特定阶级的局限,上升为自为的阶级。作为对第二国际机械经济决定论的反叛,卢卡奇开辟了高扬阶级主体性的范式,从“物化”理论中突显了人的要素,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不能替代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作用。由于他借助黑格尔思辨哲学中的主体概念,因而使得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主体的界定,尽管卢卡奇后期在《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中从社会存在的本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关系——来理解历史主体,但他开启的这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60年代)的玄学正统,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发扬光大。
“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论先驱普兰查斯则用“新小资产阶级”取代了高兹的“新工人阶级”。他通过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且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看成一个阶级划分的决定因素,而非如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那样只是强调生产关系和经济要素,他追随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传统,将阶级看成是结构整体及其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归无产阶级;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包括从事第三产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工作人员和从事企业管理、科学研究的工作人员等,都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这些“新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相比,更多地从事脑力劳动(白领工人),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相比,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这个阶级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直接维护和支撑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在意识形态上,这些“新小资产阶级”为了避免自己变成无产阶级也反对资本主义,但更多地主张改良而非革命,崇尚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命运,强烈认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他们人数众多,占经济活动人口的半数以上,在劳资矛盾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社会背景下,“新小资产阶级”最终被划归到无产阶级中来,因此,工人阶级应该团结“新小资产阶级”组成“人民同盟”,共同反对垄断资本的统治。面对二战后的阶级分化,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有力地回击了当时的“阶级消亡论”,消解了“新中产阶级论”。当然,他捍卫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和革命主体的努力客观上造成了令人不安的后果:工人阶级队伍在缩小,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法国的存在主义者科耶夫将“他者”这个概念引入法国,使得法国哲学将大写的、抽象的主体的解放转换成试图摆脱绝对在场的“他者”对主体的限制和否定。正如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所断言的那样,“本人”在“他人”的注视下,由自为的存在变得不自由,由主体变成了对象。“他人表现为彻底否定我的经验……我对他而言不是主体,而是对象。”[13](290)法国马克思主义将主体的解放从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变成了抽象化的自我向一个绝对在场的大写他者的反抗。那个大写的他者(主要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既有的一切规章制度生活习惯)成为我的绝对的凌虐者,居于他人目光之下的主体是被阉割过的主体,为了获得解放必须对大写他者进行反抗,这正是战后青年一代的心声:不愿像父辈们那样循规蹈矩地按照资本主义的礼仪去过机械般的生活,反对一切权威对个人的压制,这一思潮爆发的顶点即是引发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而且生性浪漫的法国人与严谨克制、追求精神和心灵解放的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将身体作为反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首要场所,情欲化、感性化、肉身化的身体更纯粹,更能提供一种真实的自我感受,成为有可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场所:身体可以召唤出最为淳朴、未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污染的自我。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整个50—60年代,西方的造反运动很大一部分都围绕身体展开:性别平等、性解放、女权主义,直到今天的性取向运动等。当然,身体只是解放的起点,最终目的是连身体也要超越。
然而,如此具有革命反抗精神的存在主义主体,在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之后急转直下,阿尔都塞对主体的解构更是雪上加霜,他反对人道主义主张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认为这里的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抹杀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他认为不是“人”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中创造了历史,而是“群众通过阶级斗争创造了历史”。表面上看,阿尔都塞的主体似乎有种向无产阶级回归的趋势,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承认任何主体的存在,“历史是运动中的一个庞大的自然和人的系统,而历史的原动力是阶级斗争。历史是一种过程,而且是一种没有主体的过程”[14](62)。所谓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不断的询唤(interpellation)出个体的主体意识,是被建构出来的幻觉。“‘主体’不过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系统或者结构的诸多因素之一,‘主体’本身无力于去创造整个历史。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是一种‘多元决定的’辩证结构,而处于这个历史结构中具体的人,被笼括在这个结构的某一个节点上,与历史的节奏相伴随。这样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过是一种幻象,一种基于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构性产物,一旦我们夸大了处于‘多元决定’的结构中的‘人’的因素,自然就会陷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中去。”[15]这便是阿尔都塞的“无主体的主体性”内涵。
阿尔都塞对主体的消解被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们尽情发挥:福柯的“人死了”、罗兰·巴特“作者死了”,最近甚至出现了“读者死了”。但阿尔都塞的弟子阿兰·巴迪欧给出了不同于其老师的尝试,他用古希腊的哲学概念“一”与“杂多”来概括主体和历史,在历史变革的事件(原来历史结构中的例外)中,主体通过赋予社会杂多以全新的统一结构,促成了社会变革,这样的主体并不是普遍的,只是在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才出现,他们是那些真正面对事件、面对历史实现了主导自己的人。这些人也并非恒定是主体,他们只在某个特定的变革性的时刻,才作为主体出现。这里显然包含了“时势造英雄”(主体是在事件之后)和“英雄造时势”双重辩证的意味。他的主体不同于德里达的“幽灵”(完全外在于世界),也不同于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是一种尚未成型的状态,一个在当下不是主体的主体,潜存当下的未来主体,朗西埃的哑然主体和齐泽克的视差主体(parallax view)都是探寻此类主体的代表。
[1]Peter Skehan.Researching Pedagogic tasks:second language learning,teaching and testing[M].Pearson longman,2001:96.
大齿轮的齿形系数YFα=2.61,应力校正系数YSα=1.596;小齿轮的齿形系数YFα=2.19,应力校正系数YSα=1.783;分别对大小齿轮的(YFα·YSα)/[σF]进行计算,计算后小齿轮的(YFαYSα)/[σF]较大。
三、小结
2018年年末,法国掀起的“黄背心”运动似乎展示了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学者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大众(multitude)“反抗的权力”。即使不再存在大众掌权的可能性,但还是存在系统性地使造反运动保持开放的可能性,即能够长期并严重地给“资本的政府”制造麻烦,以迫使其退让出新的空间、资金给社会的福祉。西方左派激进分子的任务只能是打造全新的团结,以便滋养“反抗的权力”,这是大众能够变为阶级的唯一方式。奈格里和哈特这里所说的“大众”不同于“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等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体概念。“人民”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将多样化的个体概念通过民族国家化为同一性的整体,令个体具有同一身份;而“大众”是多元政治主体的联合,是对民族国家的反叛,产生于全球资本帝国时代。“群众”是无差别的单一主体,由群众组成的模糊集合体,更加具有统一的行动力。“大众”表现为许多且不可化约为统一的主体特征,更具异质性和多元性。“大众”不是工人阶级的新形态,而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它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也不是在一个个民族国家之内的,而是与帝国超地域盘剥和压迫关系相关联的各种不断重新设定和杂多的事件和个体构成的,是帝国时代的被奴役者,也是帝国时代新的革命主体,“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工作着的集合体并因此具有生产力”[18](14),是非同一性的革命主体。如同星丛般存在,帝国时代的无产阶级在传统理解中是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转变成一切直接或间接屈从全部帝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个人,使作为政治和经济范畴的无产阶级退缩为一种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人集合。哈特认为大众在无限空间里的流动性活动本身就能创造一种全新的时空,成为积极的独特的主体,摧毁了传统的边界,建立起全新的场域,在集体运动中显示出力量。很明显,奈格里和哈特希望通过拓展革命主体的内涵来扩大革命主体的战线,形成更具包容性、开放性的多元主体,以包容的姿态形成普遍的联合。“有无数个潜在的阶层共同构成了当代社会,这些阶层不仅基于经济状况的差异,而且还基于种族、民族、地域、性别、性以及其他特质的异质性。”[19](103)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玄学气质,更加注重理论层面的建构,即使他们也承认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现代实践论哲学。但他们所说的“实践”只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践,而不是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感性实践活动,这种缺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真正解决历史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虽然试图从领导权、阶级意识等主体层面来唤起阶级斗争的可能,或者唤醒大众在各种社会运动中的链接,但到目前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仍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之间摇摆不定。正如本·阿格尔所说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危机触发革命的决定论与政治和谐及阶级和解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悲观论之间不断交替的历史。”[17](15)也就是说,在各种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转换。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找不到一条如何改变资本主义的现实道路,更提不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现实的社会图景,只能在理论层面不断研究资本主义的现状,在资本主义内部提出各种改良方案:如民主社会主义、红绿联盟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缺陷: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理论尽管很好地解释了当今资本主义,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而言,实践主体远远没有理论主体在思维层面带来的深刻性那样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社会政治影响。
面对二战以来,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传统工人阶级的日益减少,工人阶级意识淡薄,被消费主义俘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认同,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衰退论”在西方大行其道,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高兹在这本书中解构了传统工人阶级概念,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身份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资本的产物,被资本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所同化,不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挑战。基于此,高兹先后提出了“新工人阶级”“非工人非阶级”等概念,他不是根据剥削关系而是根据劳动的技术过程来确定阶级的内涵的。“新工人阶级”是由专家、学者、学生、科层管理人员、白领工人、新型技术工人、知识分子、外籍劳工等组成的新中间阶级。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其革命的动力不是经济利益,而是通过创造性劳动克服被异化的状态来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反对总罢工,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随后他又提出应该告别工人阶级,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非工人非阶级”上。这些“非工人非阶级”群体阶级成分不明、政治身份模糊,主要包括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已经或将要失业或半失业者和所有当代社会生产的“多余者”。他们与传统工人的最大区别是:工作或者说劳动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和外在的强制,为了解放、扩大个人的自主领域而主张取消劳动本身。“新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非阶级”的区别是:前者主要是技术工人;后者多为失业者、半失业者和临时工,由于劳动的随机性和碎片化导致其更加缺乏阶级意识,所以他们在高兹看来都是社会变革的主体。
拉克劳、默菲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则将结构主义者普兰查斯的理论更加极端化——完全取消工人阶级。普兰查斯虽然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对阶级形成的重要性,将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看成是一个多元决定的结构,但是他也仍然承认经济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而拉克劳、默菲则完全采用了全新的概念和视角来解释阶级,拒绝经济—上层建筑的二分解读模式。他们认为,依据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收入水平等客观的物质经济条件来界定阶级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做法,只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共性,却无法看到同属工人群体身上存在的差异;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审美情绪等对身份的界定同样意义重大(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的“承认”理论对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强调身份的差异性、偶然性和异质性,主张话语政治和身份政治。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多种因素或解释性框架共同起作用,没有一种中介和解释性框架占据绝对优势,是话语连接实践的结果。他们主张政治去经济化、民主去阶级化、社会去中心化和话语化,通过“人民同盟”(取代工人阶级)实现多元激进民主(社会主义革命)。人民同盟不是由阶级构成的,而是由话语构成的,话语政治代替了意识形态。他们批评马克思之所以选定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是因为受“经济本质主义”的限制,需要取消用经济来定义阶级的本质主义倾向,打破工人阶级一贯在生产中进行斗争的作风,从而进行争夺话语霸权和激进的多元民主革命。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相对比较宽泛,既包括20世纪20-60年代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70年代以后以英美为重镇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还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倾向,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左翼思想家,例如高兹、奈格里等包括在内。学界对于某些人物能否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是有争议的,本文的宽泛选取只是想表达出整个西方左派的某些整体性的发展趋势,特此说明。
②本文在论述某种具体观点的代表人物时,只选取了少数几个典型,例如汤普森和伍德,属于支持传统革命主体的著名代表。考虑本文是从总体的角度给出思想发展的脉络,不能面面俱到,特此说明。
③“经历”指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对于自身相似经历(生产、剥削、斗争等)的“超空间”和“超时间”的感悟,形成阶级意识,激发出某种认同感。参见冯旺舟:《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
企业应当以经济效益审计作为中心,以审计任务而言,其不仅包括了企业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企业财务收支合法化情况,还包括了企业经济效益合乎规定情况。审计工作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了以下四点:其一,贯彻落实国家重大经济政策和企业总部决策部署,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情况;其二,企业所属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金收支以及财务运作方面的情况;其三,企业执行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各项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情况,各项管理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其四,执行董事会批准的重大经营方案以及计划、企业发展战略等情况。
where tl is the normalized frequency locked time, σt is the RMS jitter and P is power consumption.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列宁选集: 第4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姜辉.工人阶级还是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对西方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之关系的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2): 119−129.
[7]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 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吕薇洲, 刘海霞, 邢文增, 等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7.
[9]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新社会主义[M].尚庆飞,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 任立燕, 宏远,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11]H.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 译.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12]H.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3]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4]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M].杜章智, 沈起予, 译.台北: 远流出版有限公司, 1990.
[15]蓝江.从革命的无产阶级到事件中的“非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的嬗变历程[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41−48.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等,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18]安东尼奥•奈格里.超越帝国[M].李琨, 陆汉臻,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9]MICHAEL H, ANTONTO N, ANTONIO N.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M].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Criticism at historical ag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Marxism
LI Gaorong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Orthodox Marxism defines proletariat as a historical agent from the two levels of economic base and class consciousness.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class, western Marxism advances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agent along these two levels respectively.According the principle of unific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se two levels correspond to practical agent and theoretical agent respectively.On the practical agent, western Marxism shows the trend of much more multiplicity on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agent.Some theorists insist on the traditional revolutionary agent, that is, working class, others extend and supplement it, for example, with the new working class, and still others even deviate from it, such as, by abolishing working class.On the theoretical agent, they retreat from the practical and political agent and release a lot of spa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one,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discussion of humanistic Marxism and French Marxism.On the one hand, they get a lot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insights; on the other, they make the agent metaphysical as well.Western Marxism devotes itself to talking about the abstract class nature of human beings, but forgets the practical and concrete individual.They cannot fin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to get rid of the widespread alienation in practice, which is the biggest overall dilemma for the whole western leftists and the most serious disadvantage for our research on all kinds of branches of Western Marxism.
Key Words: practical agent; working class; new working class; theoretical agent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9)04−0144−07
DOI: 10.11817/j.issn.1672-3104.2019.04.017
收稿日期: 2018−12−26;
修回日期: 2019−05−15
基金项目: 2016年武汉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西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与融通研究”(118-413100003)
作者简介: 李高荣(1982—),女,湖北汉川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联系邮箱:ligaorong-0401@163.com
[编辑: 游玉佩]
标签:实践主体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历史主体论文; 理论主体论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