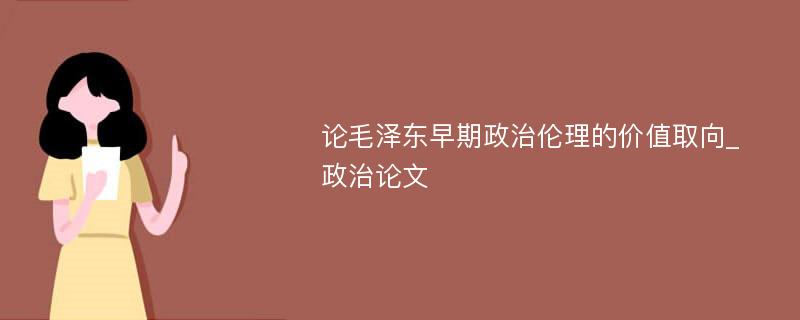
论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政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历史行程的演进,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思想文化特色愈益浓烈。今天我们可以对毛泽东作较为冷静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学界同仁对晚年毛泽东更多的是进行政治史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会发现,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其早期思想有一定的关连性。毛泽东晚年大权在握,人格化的国家权力使其早期思想有了一个宽广的社会试验场,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回到青年毛泽东。作为一种尝试,本文截取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这一具体层面,试对此做出一定的回答。
一
研究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首先就要对“政治伦理观”这一分析性概念加以界定。而理解这一概念,首先应从政治学说史和道德生活史的角度加以把握。近几年的研究,使我树立起这样一个牢固的观念,即政治是人的政治,描述和分析政治现象应当看到活生生的人,尤其应看到人之作为道德主体的活动对于政治过程的影响(注:参看拙文《主体论政治学的构思》,《社会科学报》1991年8月8日;《政治结构与道德人格——政治伦理学论纲》,《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营造人类最完善的道德生活,这一观念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已见端倪。柏拉图所向往的理想国蓝图的最高原则即是至善。亚里士多德则以“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为基本命题,阐明了一百五十八个雅典城邦的政体演变及相应的道德生活变迁史。他认为,“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中国儒家则主张以德治国,“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模式基本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走向。可以说,离开了人的道德生活史,人类的政治史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之求解,实是理解社会政治变迁的关键之一。在这一问题中,人的发展应是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主线。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有关人作为政治过程主体所具有的道德规定及其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便形成一定的政治伦理观。以人这一道德主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发展为主线,政治伦理观具体涉及到一定社会政治理想模式中的道德人格设计、相应的政治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结构对道德人格的影响,以及现实道德人格对社会政治结构的作用等方面。
这里采用政治伦理观的概念而不说伦理政治观,是因为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它应当是价值中立的,带有普遍适用性。伦理政治观是伦理型政治形态的观念表现,与法理政治观相对应。在这一观念体系中,伦理价值具有政治意义,伦理价值的选择直接转换为政治功用;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个道德判断就是政治清明直接赖于人的道德品格的完善。而政治伦理观本身则不带有价值取向,适合于任何政治体系的分析。本文也不用政治道德观,从研究主题看,如果单讲政治道德观,即关于政治道德规范的观点,则无法从整个社会宏观结构上透视毛泽东政治与伦理思想的特征及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尚无人研究,但关于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文献则为数不少。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和忧患意识使其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设计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政治伦理观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有一种直接适用性。
二
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从宇宙观的角度关于人文化特性的探求;从伦理学角度关于人的价值的思考;在对现实政治模式的批评和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展望中所揭示的道德人格规定。
(一)尚动求变、斗争造反:宇宙——人生——历史——社会大文化圈的求索
青年毛泽东很注重意志力的张扬,主张向“大本大源处”求索。这一价值理性层面的思索包含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历史观再到社会改造图式的一系列内在统一的环节,其贯穿始终的理性价值就是尚动求变、斗争造反。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动与斗”是青年毛泽东探索“大本大源”之宇宙观的核心观念(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青年毛泽东“宇宙真理”探索的动因在于立志,在于寻觅救国救民之路,是工具理性的寻觅促使其价值理性的求索;反过来,这一“宇宙真理”的求证,成为毛泽东人生观的指导,成为他立志改造社会的理性基础。青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人,其立志是一个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社会改造论的圆圈运动。在《第三札》中,青年毛泽东从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出发畅论立志:“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那么什么是“大本大源”呢?他认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而“志者,吾有见乎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决心“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
青年毛泽东向“大本大源处”探求,并不是寄冀宇宙本体论的理性思维,而是为其救国救民道路设计提供宇宙观基础。一开始,毛泽东就赋予宇宙观以实用理性的精神,而尚动求变,高扬斗争意识、造反精神则是在其思维空间中成为真正价值理性的东西,这既是对毛泽东个体文化性格的概括,同时又因其“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求索而带上一层普遍化色彩。这一价值取向从外在环境看,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非平衡格局所决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传统社会失去平衡稳定,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战祸迭起,内乱相乘,社会的无序和不安定作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尚动求变成为人们积极应付现实生活和改造环境的主要倾向。这一时代特点同样融入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视野。
青年毛泽东在哲学宇宙观的层面上把握求变尚动这一时代特征。他认为:“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正乎吾心而已。……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注:“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日,原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见《文稿》,第69页。)。这里所说的“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并非为某种外在目的(“营生”、“卫国”)服务,而是宇宙、人生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由宇宙本体论的探讨,进而联系到人的本性问题。青年毛泽东认为,“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的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注:“《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文稿》第218页。)。“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本源,一切外在的束缚、阻碍,都将被这“动”的本性所排除、摧毁。正因认为“动”是宇宙本体和人格本性,所以必然会对统一、安宁、稳定、秩序等世间现象表示怀疑、厌倦,提出挑战,高扬斗争意识和造反精神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理想道德人格。青年毛泽东认为圣人即是“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可以说,毛泽东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格发展,动与变的源泉在于“抵抗”,斗争,“抵抗”具有普遍性,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斗争抵抗,世界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遍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科伦布,洪水之对于禹,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注:“《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文稿》第181~182页。)。并以自然现象作喻:“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盖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盖增其怒号”(注:“《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文稿》第180~181页。)。正是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自身的差别因素之间的这种冲突、抵抗和斗争,给人以强烈的道德震撼,酣畅淋漓地展示出大禹、哥伦布、拿破仑那样的人格力量和巨大的创造潜能。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尚动求变的思想核心还在于对“人”的规定,对宇宙运动、斗争的说明是为了论证道德主体人格的斗争意识,造反精神。可以说,在紧张新奇的斗争中求平衡、求生存、求实现、求幸福,甚或是毛泽东整个一生基本的人生观念。1913年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写道:“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1917年,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注:转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高扬斗争意志既是毛泽东个人的人生信条,同时由尚动求变到斗争意志、造反精神的价值理性,又是一个宇宙——人生——社会——历史——文化的思维圆圈运动,是对人的意志力的张扬,从而青年毛泽东理想的道德人格设计便有了一个深厚的价值基础。
(二)个人本位与利他主义伦理价值的选择
“人”是青年毛泽东政治伦理观的核心,弄清他对人的价值的探求是理解其政治伦理观的关键。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吾以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既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这是毛泽东在1917~1918年的思想观点。彼时,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倡言伦理革命思想,新的民主主义价值观执时代之牛耳,“三纲五常”的传统道德一时受到猛烈的抨击。这对于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其影响是直接的。毛泽东由从前的“无我论”转向“精神之个人主义”。他力主“主观之道德律”,认为“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而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注:“《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文稿》第147~148页。)。即是说,道德并不是来自社会等任何外在标准、规范或律令,而只来自个体主观。所以由主观之道德律的界定,毛泽东又进一步肯定个人之价值,提出“精神之个人主义”的概念,他在《批注》中写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文稿》第151页。)。同时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明“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内涵:“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注:“《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载《文稿》第203页。)。其“精神之个人主义”的核心在于“实现自我”,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之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实现自我”包括身体与精神两个方面,这是人生最高目标,亦即是道德的自律。这种道德律令和人生境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并不同于传统伦理学讲的以“孔颜乐处”为标准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包含着体魄物质性内容在内的个体力量、意志、行为的完满实现。生物本能欲望、潜能的磨炼与个体意志力的张扬,主要在人的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来。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在人的价值,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极力抬高个人价值,要求重新肯定人的价值,提倡个性解放,其个人价值本位取向十分明显;一方面又受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谓个人主义实乃“精神之个人主义”,实际将其赋予了利他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然,青年毛泽东对三纲、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等压抑个性发展的外在权威的否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造反精神,但在价值归属上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内圣与力行相结合的伦理学说,从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出颜元、王夫之、顾炎武与陆王的合一(注:参阅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实践也证明,毛泽东关于个人价值本位的思想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带有浓烈实用理性色彩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倒是有着一贯的影响。毛泽东1919年11月就长沙女子赵王贞抗婚自杀于花轿中事发表一系列文章,也仅是对束缚女子婚姻自由的封建婚姻制度加以抨击,更多的是否定外在的权威。因此,青年毛泽东在个人价值问题上,其价值内核是利他主义;同时,在价值驱动过程中,又表现了鲜明地否定束缚个性发展的外在权威的人文主义倾向。
毛泽东“贵我”、“主观之道德律”、“精神之个人主义”思想,正说明在当时整个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崩溃时代,已经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客观规范;同时也体现了毛泽东“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传统观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正是英雄主义与反传统权威并存的思想倾向吗?“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一方面是圣贤的人格理想、救世主意识,一方面是力行哲学、平民精神,与“充分发达自己身体之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的“实现自我”正相吻合。所以,在青年毛泽东由内向外的思维路向中,作为认识客体的道德主体的人格理想同时也渗透了毛泽东作为认识主体所具有的文化特性和精神气质,最后这一人格理想要归于“经世致用”的救亡图存的探索中去,因之带有较多的工具理性色彩。
(三)圣贤精神与平民意识——“大同”理想图式中的道德人格
在早年的六年私塾生活中,毛泽东通过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和现实生活体察,确立了对贫苦农民朴素的道德同情心。青年毛泽东在走出乡关之后,有感于生灵涂炭而立志寻觅宇宙真理,从此便展开了圣贤精神与平民意识的交融。
如前所述,求得本源的宇宙行动观,实蕴含了进行哲学伦理学之社会改造的向上的人生观和圣贤治世的社会历史观。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立足于其宇宙行动观,以圣贤自许,表现了传统士大夫浓烈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认为天下生民各得“宇宙真理”,并非被动受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在这段感人肺腑的议论中,青年毛泽东不仅把本源同国家存亡、人民幸福联系起来而且认为本源存在于每个具体的国民心中,否则,本源即宇宙真理的价值就没有载体,本源的号召就没有回应。反过来,缺少或失却本源的人格,是没有自我的麻痹的人格。青年毛泽东寻求本源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重新塑造民族国家的新道德人格,其救亡图存的社会政治理想与道德人格追求本来就是合二而一的。在追求新人格的过程中,青年毛泽东偏重于“大气量人”——圣贤的理想道德人格。还是在《第三札》中,毛泽东充满激情地呼唤:“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
这样的“大气量人”,能够明究天人之际,精通古今之变,救济时势之危,并且集养身、进德、修业、建功于一体。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历史上的圣贤豪杰正是这一类人。早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毛泽东就认为:“人之为人,以圣贤为祈响”。在《第三札》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根据儒家的人格分类模式,把人划分为两类,即君子和小人,或圣贤和愚人,并明确把是否把握了大本大源作为区别标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他所说的圣人,必须是学而知之,并且有长期的自我更新和磨炼过程,圣人仅只是对本源有特殊领悟力的人,“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圣贤是“宇宙之我,精神之我”,融入宇宙的个人“大我”,自然是要以天下事为己任,这是他们个体人格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为此可以不惜牺牲肉体“小我”。从《讲堂录》中的“无我”境界到《批语》中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其中关于圣贤的人格价值实质上都是一致的。
青年毛泽东对于在苦海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曾寄以恻隐同情之心。这里他便赋予圣贤道德人格实现的路径:“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他认为圣贤君子的主体精神是在一种群体人伦关系中萌发的自我感觉,以及对自己的教化和创造能力的肯定,进而强化社会责任感,最后形成相应的道德行为。而“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君子救小人的过程,是创世的过程。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915年9月6日,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之代表,将其前者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注:“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载《文稿》第22页。)。巨夫伟人是圣贤君子的另一说法,和历史朝代的关系,即是代表者与附属品的关系,他们不仅是理想人格典范,而且是历史发展的标尺和动力。
青年毛泽东又从传教与办事两种职能将圣人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圣贤与豪杰,其道德人格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讲堂录》中,他记下了这样的话:“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破仑)翁,豪杰也,而非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注: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具体到政治发展过程,则毛泽东认为:“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在上者虽有贤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他明确地认识到,圣贤的道德人格典范与大众道德文化心理相结合,才可使政事长久。豪杰主事功,只是拥有权威的政治领袖,而圣贤则立功、明道、传教,是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并且圣贤亦可为事功,“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在这里,政治权力与道德教化的关系构成一对矛盾。在他看来,圣贤高于豪杰,本源高于权力,道德人格的价值大于政治权威的价值,观念的正确认识必然最终转化为实在的功效,方能治国平天下。晚年他对“四个伟大”的称呼,只喜欢和承认“伟大的导师”一句,并常说起自己早年做过教师工作之事,可见其圣贤精神价值取向。
毛泽东认为将传教与办事两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近世之曾国藩。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以维护纲常名教为号召,以礼治军,用兵讲求以静制动,后发制人,无不见出深厚的传统伦理根基。对此,青年毛泽东备加称颂:“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为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无满乎?”(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
圣贤精神的实质在于通过伦理教化,将“大本大源”贯彻于现实的大众道德人格,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人皆得为圣贤,使人类达到一个“大同”理想境界。他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入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自比以圣贤辈,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小人”、“愚人”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对未来“大同圣境”的理想社会模式表现出衷心的向往。其圣贤精神与平民意识并行不悖。当然偏向于前者。
圣贤传教,自应倡学,毛泽东是希望通过哲学、伦理学来改造现实社会,进而实现“大同圣域”、“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对此,张昆弟在191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述:“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哲学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注:转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民众,把民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具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人人皆为圣贤。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的思想有了急骤变化,其圣贤精神与平民意识的双重道德人格结构发生了偏转,由推崇圣贤转向寄希望于人民群众,并赋予其社会历史动力、政治道德主体的人格价值。青年毛泽东将民主的价值层面抛却,取其平民主义作为现实政治斗争的主动力。极其现实的政治功利主义,使毛泽东由“大本大源”求索的幻想转向寻求“民众大联合”的途径。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取向。
三
理解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必须将其放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行程中去考察。其中物器——制度——人心的文化逻辑进程论(庞朴)、中西文化冲撞反应论(费正清)、救亡与启营双重变奏论(李泽厚)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都不失为一种说明近代中国历史深层变动的理论模式。
就毛泽东早期政治伦理观而言,可以这样看,中西文化冲突是其时期背景,中国近代史是先进人物向西方求真理的过程,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宣传、理解,到底是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忧患意识和实用理性为底色的。救亡与启蒙是其时代主题,这一二重结构在毛泽东那里经常发生倾斜,因为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是一个更为紧迫现实的问题,思想启蒙往往服从于救亡图存甚或为其所取代。其“哲学、伦理学的改造”实不具有启蒙意义,有的只是为救国安邦之道而倡“人人内圣”,皆可为圣贤的大同圣域理想与现实倡学的急切心情。
深受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说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对中国的封建礼教、宗法政治制度和旧道德、旧思想有很多道义上的抨击;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针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以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认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89页,(下引该书仅注《文稿》及页码。)。有人曾用旅馆论来说明青年毛泽东在思想演进中受各种思潮影响的特点。这实际是他对各种救国工具的选择。他恰如住旅馆一样在不同的理论房间里留住过,随之又匆匆离去: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以及俄国的民粹主义等,这些西方思潮曾给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注:“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真正主导青年毛泽东政治伦理观价值取向的是传统典籍和古典小说中的“内圣外王”的忧患意识。
政治伦理观作为一种普遍适用性的分析概念,对毛泽东政治伦理观有一种直接适用性,这不仅因为其所表现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直接实现了政治伦理观逻辑主体——人的道德人格规定,还从文化结构上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内圣外王之道。青年毛泽东此前的论述不正与此相合吗?他以反传统斗士的姿态批判“吾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另一方面却又期望圣贤出世,以哲学伦理学来进行人心道德的改造,从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所走的正是内圣外王的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的路子。然而毛泽东又不与传统同流合污。他的造反精神不可谓不强,任何束缚他个性的外在权威,他都一概加以反对,从少年时与父亲的抗争,到对伦理纲常的批判,无一不表现出一种反传统意向,但着重反对的是外在的权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缺少彻底的批判。此前所说的三大取向,莫不如是。尚动求变,既受近代中国社会非平衡秩序的影响,更多地带有从孔子到康有为的历史循环论;斗争造反,则如前所说是反对外在的权威。由“无我论”的正宗传统儒学到中西合璧的“精神之个人主义”,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圣贤精神与平民意识则更多地带有内圣外王的儒家忧患意识。“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这是青年毛泽东对自我的评价,其极高处就是圣贤精神,就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其极卑处就是墨家精神,就是源于农家子弟的那种求实和勤苦的现实主义作风。在中西文化交汇的时代大潮中,青年毛泽东的政治伦理观确然是中西合璧而又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