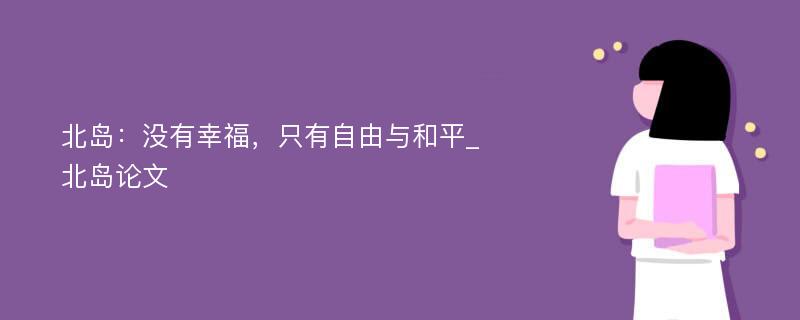
北岛: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岛论文,平静论文,幸福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被归入“朦胧诗”的一代诗人中,北岛从一开始就是最为耀眼的一个,但或许也因 此注定成为受成见侵害最深的一个。以他的早期作品为例:正如小说界迄今绝少有人提 到他初稿于1974年、发表于1978年的中篇小说《波动》——在我看来,无论在方法上带 有多少模仿的痕迹,这部小说在当代小说史上都应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一样,诗歌 界在大多情况下也只牢牢盯住他的《回答》、《宣告》或《迷途》等符合“朦胧诗”定 义的作品不放,充其量将视野扩展到《红帆船》、《习惯》等为数不多的爱情诗,而对 诸如《日子》、《一个青年诗人的肖像》等显示了别一种风格、别一种可能性的作品, 却基本上视若不见,就更不必说稍后像《触电》、《空间》那样既更深地触及生存的困 境,方法和风格上也更为精细,更具个人色彩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了。毫无疑问,这种象 征化、符号化,最终意识形态化的成见为某些一心要“打倒北岛”、“pass北岛”的后 起诗人提供了方便,其结果是使“北岛”这个名字在被加速度地经典化的同时,也被焊 死在人为设计的当代诗歌发展框架的某一点上,成了诗歌不断超越自身的一个证明,更 准确地说,一件祭品。或许在这些诗歌同志看来,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成见,并且相比之下是较小、较为无害的一种。来自另一向 度(国外汉学界的向度)而又与此对称的,可参见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先生的《何谓世界诗歌》(中文译文最早见载于上海民刊《异乡人》1992年春季号 ,已收入同一作者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迷楼》一书)和诗人欧阳江河为北岛诗集《 零度以上的风景》所写的序文《初醒时的孤独》(收入其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时更 名为《北岛诗的三种读法》,三联书店,2001)等文章。至于更大、为害也更烈的成见 ,这里不说也罢。需要指出的是,种种成见尽管各有所据,不可一概而论,但作为诗歌 态度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即都把诗看成了一种权力;这也就决定了成见持有者的共 同身份,即都是些“战争的客人们”。这一富于讽刺性的称谓出自北岛的《完整》一诗 ,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至为荒谬的场景:
琥珀里完整的火焰/战争的客人们/围着它取暖
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为“全球化”背景下多方合谋的一种诗歌“奇境”,或充满“后现 代”、“后殖民”意味的诗歌“奇观”?或者更彻底些:一道风景线?这道荒谬的风景线 肯定不为北岛所专属,却通过他显示得更加触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由于无从 读到他更新的作品,作为诗人的北岛对国内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越来越近于一个寓言,一 个因主人长期外出而赋闲的地址;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北岛:人们越来越习惯 像谈论一个明星那样谈论他的国际声名,谈论此起彼伏的他将要摘取诺奖桂冠或与之擦 肩而过的消息,以及种种与他有关的传闻、舆论、臆测、花絮,而不是他的诗。“北岛 的名字”,一位论者不无忧虑地写道,“在成为一个象征的同时也正在变成一个空洞的 能指”。他所忧虑的与其说是北岛的名字,不如说是那些播弄着这个名字的嘴巴,是在 播来弄去中被搅得乱七八糟、恶俗不堪的诗歌趣味和诗歌记忆——许多张大嘴巴,共用 一颗失忆的脑袋,还有什么比这更适合作为所谓“空洞的能指”的能指呢?就此而言, 最近发生的一件趣事不应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笑话,也可以被视为某种小小的 症候:春节期间,回国省亲的北岛应友人之邀去某地。当地一位据称“八十年代也写过 诗”的“诗爱者”听说后很兴奋:“北岛?我知道!”接着他开始热情洋溢地背诵他所认 为的北岛代表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汇聚了北岛迄今主要作品的《北岛诗歌集》去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 版,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诗集一印再印,总发行数已接近三万,就更值得庆贺。据 我所知,一部诗集而拥有如此高的印行数,近十年来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 。这是否表明北岛的诗又一次征服了读者?对此我宁可持更谨慎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次胜利:既是一个人和他的诗的胜利,也是有心向诗的读者们的胜利;既是 “缺席的权利”的胜利,也是“在场的权利”的胜利;既是时间的胜利;也是对时间的 胜利;最后,是把所有这些凝聚在一起,永远会逸出历史或人造的“琥珀”,而反复将 自己显示为生命/语言之“活火”的人性/诗歌本身的胜利!
北岛本人怎样看待自己作品的“还乡”是另一个问题。显然,这里需要的不是热情, 而是透彻的洞察力。他写于九十年代中期的《背景》一诗于此更像是某种预应式的,即 充分考虑了各种压力的表达。诗的基调是自我交谈性的,但起手一节却使用了斩钉截铁 的条件——论断句式:
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
孤立地看会觉得激愤、孤傲而突兀,只有领略了第二节交织着嘲谑和反讽、苍凉和豁 达混而不分的身世感,以及随后有关一个家庭宴会的半似调侃半似叹息的概括描述,才 能品出其中的复杂滋味。去年下半年我受《诗探索》的委托,通过E—mail对北岛进行 访谈时曾议及这首诗。在肯定“背景”、“重返”和“故乡”都具有多重涵义的前提下 ,我的问题是:假如“重返”成了错位,你会失望吗?他的回答令我感到,他和他的诗 其实从未脱离过母语语境:
……这是个悖论。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是不可能的 ,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但回家之路是 没有的。这甚至说不上是失望,而是在人生荒谬前的困惑与迷失。
我不知道对应地去读写于稍晚的《远景》一诗是否合适?在这首诗中,乡愁和风、言说 和道路互为隐喻,而威胁来自道路尽头那只“扮装成夜”的“历史的走狗”。诗的结尾 饱含忧郁,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北岛,一个有点“老派”,但很可能也更加本真的北 岛:
夜的背后/有无边的粮食/伤心的爱人
“无边的粮食”、“伤心的爱人”在这里都具有终极事物的性质。认为它们的被遮蔽 构成了北岛写作或继续写作的理由是过于简单化了;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发现令 他忧郁的理由,令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荒谬一直保有极度敏感的理由,令他认同“诗是忧 郁的载体”(西班牙诗人马查多语),并致力于使写作成为对荒谬的持续揭示的理由。而 同样的理由或许也正是他的诗吸引我们一读再读的理由。
和“荒谬”一样,“忧郁”肯定也是北岛写作最重要的根词之一。在前面提到的访谈 中,“忧郁的载体”不仅被北岛标举为他一直在寻找的诗学方向,而且被用来表述他在 长期漂泊中对母语的感受(在布罗斯基所比喻的“剑、盾和宇宙舱”外,他又加上了“ 伤口”),甚至被用作他反思新诗传统的“动力和缺憾”的内在尺度(见《诗探索》2003 年第4期)。这是否意味着他同时也提供了一把钥匙,据此可以更方便地打开他的诗歌之 门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总也有人站在他诗的门前抱怨“不好懂”。那就让我们一起 来试试如何?不过要小心,警惕由此又形成一种新的成见。多年前北岛曾把诗自我定义 为“危险的平衡”,对他的新老读者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应该始终记取的提示。
不妨把北岛的散文也视为一个平衡的因素。北岛开始写散文是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事, “还乡”却早于他的诗;虽不像诗那样成规模建制,但也足够集中(初见于《天涯》, 近年则先后在《读书》、《书城》等杂志辟有专栏)。散文中的北岛当然还是诗人北岛 ,却更为从容洒脱,富有情趣,其风格上的明显标志是突出和放大了在他的诗中往往隐 藏得过深的幽默(一个幽默的北岛是必要的,他在令人感到亲切的同时也令人安心)。借 此我想特别推荐刊载于2003年《收获》第六期上的《他乡的天空》一文,而他自今年一 月号起在同一刊物上开辟的“世纪金链”专栏(已有《洛尔加: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见载)可能更值得关注。“金链”在这里意味着:一个人的诗歌史、他的精神谱系和他 “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
多年的漂泊游历之后,北岛定居美国,现携女儿和新婚的妻子一起生活在加州戴维斯 。从前年起可以不时回国,探视年迈而多病的父母(他的父亲已于去年过世——愿老人 家的在天之灵安息)。他曾先后获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阿 格那国际诗歌奖;曾获著名的古根海姆奖学金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但正如他所认可的,母语才是他“惟一的现实”。在美国他像普通人一样生活,除为一 份文学杂志操心外,每年还要到大学里教两个月的书,以维持生计。在一篇访问记中他 这样描述自己目前的生活日程:“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 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相带看,算是休息。”他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诗来概括这一切: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2004年2月9日天通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