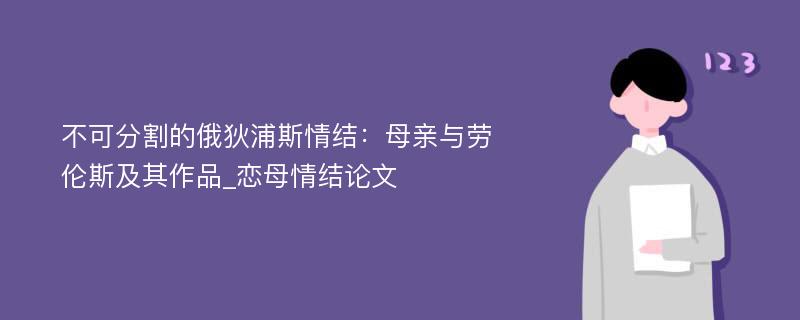
解不开的俄狄浦斯情结——母亲与劳伦斯及其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伦斯论文,情结论文,解不开论文,母亲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劳伦斯 俄狄浦斯情结 母亲
一生颠沛流离,充满波折的D.H.劳伦斯命途多舛、英年早逝,四十五岁时生命便划上了句号。然而,这位多才多艺的英伦才子却将自己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英国文学的史册里,世界文学史的殿堂里也闪耀着其作品的光辉。除了10部长篇和4部中篇小说外, 劳伦斯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游记、戏剧、文学评论以及数量达千首的诗集和四卷本的书信集。然而,真正使劳伦斯立足文坛、一举成名的是其第三部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儿子与情人》总是被评论界视为劳伦斯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艺术风格的转折点。”〔1〕《儿子与情人》之所获得如此巨大成功,与劳伦斯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 日出生在英国南部的诺丁汉郡。父亲是一位煤矿工人,终日如牛负重地劳作于矿井下。父亲性情暴燥,没有文化,结婚以后,脾气越发乖戾,经常在酗酒之后打骂妻儿。劳伦斯的母亲是一位性格温柔的小学教员,有着较好的文化修养,对矿工的生活格调始终不能接受,希冀过上一种较为文雅的生活。母亲的这种企望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尤其是劳伦斯。因为在长兄恩尼斯特死后,劳伦斯便成了母亲的心肝宝贝。柔弱多病的劳伦斯幼时与其他男孩很少来往,母亲单独教他认字、读书、吟诗作画,把跻身上流社会的希望完全倾注在劳伦斯身上。劳伦斯聪颖好学,深得母亲的宠爱。耳目所及多为母亲的言行,母亲的生活方式深深地熏染了劳伦斯。因此,劳伦斯对母亲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对父亲则表现出厌恶和仇视。这一切对劳伦斯本人及其日后的作品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此,劳伦斯青梅竹马的女友和恋人杰西·钱伯斯以及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劳伦斯均有记载,劳伦斯本人对此也坦然承认。
1910年,劳伦斯太太(D.H.劳伦斯的母亲)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劳伦斯终日守在母亲身旁。在母亲葬礼的前一天,钱伯斯去看劳伦斯。俩人在熟悉的小径上边走边谈,劳伦斯哽咽着告诉钱伯斯:“你知道——我爱母亲。”钱伯斯说:“我知道你爱她。”但劳伦斯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直象一个情人一样爱着她。这就是我不能爱你的原因。”钱伯斯对此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她很清楚,“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她母亲赢得了他的爱,赢得了他全部发自内心的柔情,而没有这种柔情,‘爱’仅仅是一种嘲弄。劳伦斯毫不保留地把他全部给了母亲,实际上他已没有爱情给任何其他人。”〔2〕钱伯斯认为, 在劳伦斯心目中母亲必须至高无上,为了那种至高无上的缘故,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在《不是我,而是风》中曾记下了劳伦斯对她说过的话:“假如我母亲还活着,我就不会爱你,她不会让我离开她的。”无须他人指证,劳伦斯本人坦然承认。1910年在致雷切尔·A ·泰勒的信中劳伦斯写道:“我们母子相互情深意笃,情似夫妻,爱胜母子。我们相互无所不知,这种本能的相知达到了极至,致使我在某些方面失常。”〔3〕这儿所说的“某些方面失常”即是指日后与异性朋友的关系,说得具体一点,即是指与女友钱伯斯的关系。母子之情有如一堵无形的高墙横立在劳伦斯与钱伯斯之间,使他们感到若即若离,无法逾越这屏障,去实现完整的自我。劳伦斯的亲身经历使其体验到,如果母子的垂直关系太强,儿子与情人的左右水平关系可能被窒杀。这一切均充分地反映在其成名作《儿子与情人》之中。
《儿子与情人》是一部自传色彩浓郁的小说。小说本身恰似一个“俄狄浦斯情结”故事,是作者早期生活的真实写照。
小说以19世纪中叶作者家乡诺丁汉群、德贝郡一带煤矿与水乡阡陌纵横交叉的地带为背景,描绘了一幅煤矿工人家庭的生活图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英格兰蔚蓝的天空被林立的烟囱涂上浓黑的阴霾,秀美的田园被灰色的井架扯得支离破碎,乡间的宁静被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人的灵魂被机械文明扭曲,自然天性遭到窒息。小说中的煤矿工人毛瑞尔(生活中的劳伦斯之父)终日在黑暗、潮湿的坑道里干着非人的苦工,每时每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婚后的毛瑞尔与妻子葛楚(生活中的劳伦斯之母)不睦,变得越发粗暴蛮横。忧愁和疲劳只有酒才能暂时排解,怒气和怨恨只有酗酒后打骂妻儿才能发泄。于是,从矿井到酒馆,从地下挖煤到家里打骂妻儿成了他特定的生活方式。而妻子则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维持着贫困的家庭生活,抚养幼小的子女,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毛瑞尔太太少女时代的美梦,绝望之余葛楚便把全部的爱和希望倾注在保罗(生活中的劳伦斯)身上。葛楚企图以对儿子的爱来填补由于对丈夫的失意和绝望而造成的感情的真空,试图从儿子身上得到她本来应从丈夫身上得到的爱。于是,母子两人的关系发展到了情深意笃、如漆似胶的程度。他们相互倾吐内心的隐衷,共享生活中的忧乐,谁也离不开对方,这种超越正常母子之爱的情感在毛瑞尔工伤住院时达到了高潮,保罗竟然高兴的扮演父亲的角色,情不自禁地喊道:“我现在是一家之主了!”他巴不得父亲早点死去,与母亲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葛楚对保罗的超乎寻常的爱还表现在这种爱与其他女性对保罗的感情冰炭难容。葛楚看到米丽安(生活中的杰西·钱伯斯)与保罗过往甚密,便醋意大发,生怕米丽安会占据保罗的整个灵魂。因此,对儿子喊道:“她(指米丽安)不给我留下一点位置,一点也不留。”年已20岁的保罗,感情上完全处在母亲的控制之下。下面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保罗已陷入对母亲的爱而不能自拔:
“你还没有遇到相当的姑娘。”
“只要你健在,我永远不可能遇到相当的姑娘”,保罗说。
在米丽安热烈地追求保罗期间,葛楚曾醋意十足地对保罗说:“难道就没人跟你说话了吗……哦,我懂了,我老了,所以应该靠边站,跟你没关系了。你只要我服侍你——此外你就只有米丽安了”。
为了击退米丽安的进攻,永远占有儿子的感情,葛楚几乎在向儿子海誓山盟了:
“我从未——保罗,你知道吗——我从未有过丈夫。真的,从来也没有过。”保罗轻轻抚着母亲的头发,吻着她的头颈。
“我不爱她,妈妈,”保罗柔声地说。他低下头来,难过地将脸埋在母亲的肩上。母亲长久地、热烈的吻着他。
其情之真,其意之切,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关于这一情节,劳伦斯本人也曾在致出版商的信中作了如下说明:
“……当儿子长大起来时,她(葛楚)挑选他们作为情人,首先是最大的儿子,随后是第二个儿子。这些儿子由于与母亲之间的爱的推动而来到人间,并且一直受到这种力量的推动。然而,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们却失去了恋爱的能力,因为母亲作为他们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了他们……这些年轻人一旦与女子接触便趋向分裂。”〔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劳伦斯早年的生活经历已被完整地记录在小说之中。浏览一下劳伦斯的传记便会发现,作者的早期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俄狄浦斯情结”式的活生生的记录,而他的这部小说则是基于这种个人经验,只不过加了一个艺术虚构和典型概括罢了。
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式的生活经历是否因为母亲的去世而就此终止了对劳伦斯本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呢?许多研究劳伦斯的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但笔者认为不然。母亲去世之后,劳伦斯对她的迷恋依然存在,其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对其本人,还是对其作品仍未消逝,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对此,钱伯斯感受最深在《一份私人档案》中她写道:“我们又在一起了,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分开,但是他母亲的禁令比她在世时更加有力。我开始意识到不管劳伦斯怎样接近我,他都会产生一种对他母亲不忠的感觉。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契约,某种协定。这种协约通常不可言传,而正因为不可言传,它显得更有约束力。这个契约把我明白无误地排斥出了某个特定的位置,而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我才能真正帮助他。我们回到了以前那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但是由于环境变了,这种处境比以前残酷一千倍。”在钱伯斯看来,母亲去世后的“劳伦斯就象一只无舵的小船,疾风中的一片树叶”。此后很久,在谈到母亲时,劳伦斯仍有一种飘忽不定毫无着落的感觉。他认为与亲人失去了联系,必须在纷繁奇妙的大千世界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而这奇妙的世界却突然间变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令人不寒而粟。请看劳伦斯是如何将恋母之情、丧母之痛见诸于笔端的:
我心上的人儿长眠九泉,
她的脸儿朝上对着我的脸;
难舍的吻别使她启开樱唇,
她与我同将人生之路走完。〔5〕
字字含真情,句句寓实意,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母亲的去世使劳伦斯寸断肝肠,多年之后依然难忘。在1928年出版的《诗集》的前言中劳伦斯写道:“自从母亲去世,我周围的世界便开始崩溃,原先五彩缤纷的美好世界逐渐化为乌有,直到我自己也几乎要崩溃了……”母亲去世已18年了,但劳伦斯仍然六神无主地罩在一片阴影之中,足见儿子对母亲爱之深,情之切,也足见母亲在儿子心目中的位置。在此后的作品中莉迪亚·劳伦斯(作者的母亲)的形象总是魂牵梦绕反复出现,《儿子与情人》的寿床上安睡的是她,母亲赞歌中长眠的也是她,她那安息的形象成了他作品中女性的主导形象。请看《儿子与情人》中的毛瑞尔太太:
“她被抬起半躺在床上,床单从他跷起的脚上向上伸展,象一片洁白的,起伏的雪,一切是那么安静。她象一个酣睡的少女躺在那里。他手中拿着蜡烛向她俯下身去。她犹如一个在睡眠中梦见情人的姑娘……她显得青春焕发,额头高高的,白白的,似乎生活从未碰过它。……她会醒来的,会睁开眼帘的。她依然和他在一起。他俯下身热烈地吻她。但他的嘴唇碰到的是一片冰凉。他心情恐怖地咬了咬嘴唇。”
在劳伦斯笔下,毛瑞尔太太的形象放射出女性的光芒,空旷的房子里她的尸体静卧在寿床上。在世时,保罗不能将母亲所渴求的爱全部给她,死后,只能以吻作为补偿。为此,保罗感到震惊,感到遗憾。因为他看到死去的母亲似乎又返老还童了,和年轻时一样美丽漂亮。尽管有点冷漠,她依然在作年轻的梦。然而保罗又感到恐怖,因为他热烈地吻她时,嘴唇碰到的是一片冰凉,她没有醒来。
在劳伦斯笔下,毛瑞尔太太成了睡美人。保罗之吻既表示他与母亲诀别时依依难舍之情,也表示他对长期抑制的强烈母爱的深深答谢。然而,与格林笔下睡美人所不同的是,确已死去的毛瑞尔太太没能象儿子所下意识地渴望的那样,深情一吻唤醒长眠的母亲。作品中的保罗为此感到遗憾,生活中的劳伦斯更是为此抱恨终生。
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劳伦斯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总是频频出现。如果说在前期作品中塑造母亲的艺术形象是为了忏悔对母亲犯下的荒唐的罪过,那么后期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则是为了摆脱萦绕在心头的母亲形象,发泄对母亲的束缚、苛求及偏见的怨恨。因此,在《儿子与情人》之后的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成书于1924年的中篇小说《公主》中的主人公便是个突出的典型。劳伦斯笔下的这位主人公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貌倾国倾城。然而她却极端高傲,情欲淡漠、茫然恍惚、麻木不仁,在极度沉寂中度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息尚存的“睡美人”,她是毛瑞尔太太残酷形象的再现。她那拱形的鼻子犹如一幅高傲而古老的佛罗伦萨派画像,这象征着劳伦斯母亲那令人难忘的特征——那幅形状别致的鹰钩鼻。公主那昏昏欲睡的样子令郁郁不乐的罗梅罗着迷。公主在酣睡,梦幻中外面在下雪,雪透过房脊落在她的身上,轻柔地,自由自在地飘落下来,她就被活埋在雪中。然而,罗梅罗哪里知道厄运已在劫难逃,结果这位发疯的公主在与罗梅罗云雨一番之后,罗梅罗便被带去杀掉了。
沉睡的女人失去正常的机能是劳伦斯中后期作品的主题。在《虹》中,是斯克列本斯基使厄秀拉意识到“源泉的不朽”,但厄秀拉却很快看到了热恋之下潜伏着的冰冷的裂缝:斯克列本斯基甘愿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为英国政府在印度效力卖命,而厄秀拉则与斯克列本斯基代表的势力誓不两立。因此致使厄秀拉最终变得严厉、冷漠,拒绝斯克列本斯基徒有肉体而没有精神的爱,两人关系最终破裂。《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中的康斯坦斯·恰特里有时很象厄秀拉,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英格兰,如同一个“睡美人”,只有当阳物王子的“猛烈撞击”到来时才会再生。诸如此类的“睡美人”均对男人构成威胁。劳伦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冷漠可恶难以接近的女人面前,男人所受的折磨自身就是一种毫无结果的麻痹与死亡”。〔6〕为了阻止这种情况, 在《骑马离去的女人》中,劳伦斯故意让被符咒镇压住的女子经常遭受暴力的袭击,所以故事中沉睡的女人被当作吸血鬼而遭利刃穿心。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母亲的形象在劳伦斯的笔下发生了变化,由最初的可敬可爱逐渐变得可恶甚至可恨。这种变化与作者生活中的关键时刻——母亲的去世,自己的病重,与钱伯斯分道扬镳以及与弗丽达结婚——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重要的经历促使劳伦斯一遍又一遍地改写《儿子与情人》,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使“俄狄浦斯情结”贯穿其作品的始终。劳伦斯最终虽然意识到并承认他母亲错了,但仍难以彻底摆脱“俄狄浦斯情结”式的生活经历对其产生的影响。直至去世前不久,劳伦斯在《魂归西天》一诗中还写道:
快回到我的身边,
结束那离别的思念,
眼下你已成了寡妇……
你已摆脱男人的重负,
快回到我身边……
回来吧,母亲,我的情人,
是我送你归天。
只有我清楚你的贞洁,
何处是家园。
无人注目的贞洁,
我的心肝。
魂将归西天,依然忘不了对母亲的依恋,情切切,意绵绵,母亲对劳伦斯的影响可见一斑。
注释:
〔1〕Novel,A Forum on Fiction,Spring,1994,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Jessie Chambers :D.H.Lawrencee ,A Personal Rec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3〕《劳伦斯书信集》第一卷,P69。
〔4〕The Letters of D.H.Lawrence,ed,Aldous Huxley ( Heinemann,1932)PP.78—79.
〔5〕〔6〕Complete Poem 198 &411(中文为笔者自译)
〔7〕Judith Farr:D.H.Lawrence's Mother As Sleeping Beauty:The "Still Queen "of His poems and Fie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