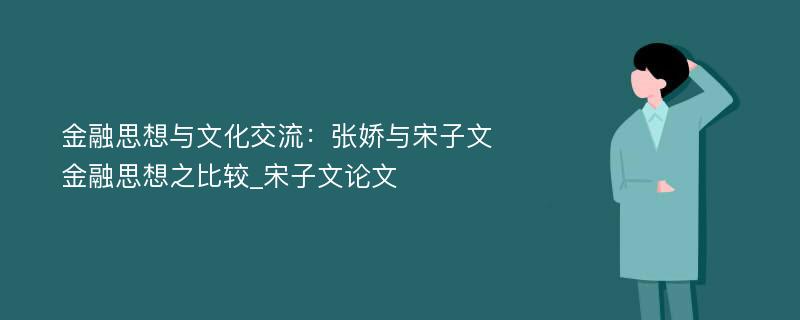
金融理念与文化交流——张嘉璈与宋子文金融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文化交流论文,理念论文,思想论文,张嘉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嘉璈曾被称为金融界“四大名旦”,宋子文则被列入“四大家族”,两人作为赫赫有名的金融巨头,他们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分歧,并且反复较量。同时,他们又拥有不少共识,并且多次携手,其复杂关系引起了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笔者认为仅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概括他们的共识与分歧并不全面,本文尝试变换观察视角,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并从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同流派和理念的不同影响的角度,对两人的斗争与合作进行分析,以期有所裨益。
一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幼时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北京高等工业学校,18岁负笈东渡,进日本庆应大学留学。1913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主持中行至1935年。后又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部长。
宋子文(1894-1971)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1912年起先后进入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3年,担任广东革命政府中央银行筹备员,后任中央银行行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1934年,组建中国建设银行,1935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在从事金融事业的过程中,张、宋两人曾发生过尖锐的斗争。南京政府完成“中国统一”之前,张嘉璈是北方政府国家银行的主持人,宋子文是南方政府中国银行的负责者,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例如,1923年,宋子文曾呈请孙中山查封了中国银行在广州的房地产。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宋子文代表中央银行,张嘉璈则代表着已经改组为商业银行的中国银行,两人的较量进入了新阶段。1927年,国民政府设立财政监理局,派人检查“中行”帐目,张嘉璈严词拒绝;1928年,宋子文建议改组中国银行为国家银行,张嘉璈再次拒绝,只同意“中行”改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以后,宋子文多次要求提高“中行”官股比例,而张嘉璈则努力加强“中行”商业银行的地位;一直到1935年,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登上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宝座,张嘉璈无可奈何地辞去总经理的职务……这些冲突掺杂着政治的因素,也反映着两人不同的金融理念。
(一)服务工商与服务政府
张嘉璈认为服务工商是银行的天职。他多次宣称:“力谋以低利资金,扶助大小工商,藉以图物价低廉,生产发达,出口增加。”“欲发展国际贸易,非发展国内贸易,非辅助工商业不可。”[1](P8-10)基于这一认识,他不惜重金,扶持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纺织大王张謇、面粉大王荣宗敬、火柴大王刘鸿生都曾得到“中行”的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宋子文认为服务政府是银行的宗旨之一。他起草的广州政府《中央银行条例》规定,除了收受各类的存款外,该行还经营国库证券,买卖政府担保之票证。代政府募集债款,发行货币,代理金库,代政府创办经营各项固有实业。南京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他宣称:“中央银行乃代为国家做事,非以营业为目的。”[2],抱着“为国家做事”的宗旨,宋子文运用金融手段支持北伐进军,也支持国民党军进剿工农红军。
(二)依靠商股与凭借权力
张嘉璈坚持银行应运用私人资本的力量,加强私人资本的地位。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商股在中国银行股金中的比例。1917年11月,他修改《中国银行则例》,鼓励扩充商股,并亲自四处招募商股,使中国银行股金官商各半变为商强官弱。1921年,在张嘉璈的主持下,“中行”继续扩充资本,规定商股尽先认购,终于使商股比例达到99.75%。正是在商股中不断扩充的基础上,张嘉璈改组“中行”董事会,改变了银行负责人随时局变化而更迭的先例,使总裁和董事会掌握了银行的经营权,也圆了自己建立中国最大商业银行的梦。
相比之下,宋子文更多地依靠政权力量推行自己的主张。这种倾向在1923年查封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的行动中已露端倪,接着,强制流通央行货币,强制以央行货币为交税纳赋、报解公款的唯一货币,强制取缔外币流通等一系列行动使“凭借权力”逐步升级。南京政府建立后,宋子文以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的身分更频繁地运用政权力量,他命令将广东央行的规定推广到全国,他命令向“央行”以外的银行征收银行券收益税和发行税;他还命令将关税、盐税的保管权收归“央行”。宋子文终于在政权力量的支持下确立了“央行”国家银行的地位。
(三)经营生意与统率金融
张嘉璈从事金融业的信条是:银行是“生意”。他曾专门撰文阐述这一思想:“我们银行是做生意……出卖的是‘信用’和‘服务’……离开了‘生意’二字就没有银行。”[3],张嘉璈视银行为生意,自然以追求利润为重,不惜开罪政府;以服务工商为重,不愿官股干预;强调顾客为上帝,不仅重视豪商大贾,也关注平民百姓。
宋子文则认为银行的职责是统率金融。他公开申明中央银行的三项任务:(1)辅助政府整理和统一币制;(2)统一全国之金库;(3)调剂全国之金融。宋子文坚持:“国家必须有强力之国家银行,中国历来金融制度缺点极多,即无完备之国家银行之故。”[4]为了统一金融,宋子文设新税,输官股,派官僚,千方百计限制其它银行的发展;为了统率金融,宋子文运用权力,统一货币,筹措资金想方设法加强“央行”的领导地位。
不同货币金融理念驱使着张、宋二人的行为。张嘉璈以发展商业银行为理想,呕心沥血将中国银行这一大清帝国和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银行改造成最大的商业银行。宋子文以建立中央银行为己任,绞尽脑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终于完成了四行二局为核心的金融垄断网。
二
在反复较量的同时,张、宋二人也曾有过十分相似的举动,也曾携手做过耐人寻味的事情。在相似与携手的背后则包含着大量共识。
(一)银行必须保持独立
张嘉璈直到晚年旅居美国,仍然坚持“银行是银行,国库是国库。”[5](P49)坚持自己一生信奉的银行独立的宗旨。宋子文也同意这一观点,在就任南京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时,他便宣告:“中央银行握全国最高之金融权,其地位应超然立于政治之外。”[6]
为保持银行独立,张嘉璈任“中行”副总裁之始便建议总行负责人不应随政局变化而更迭。宋子文受命组织中央银行便将行址选在上海,而远离政治中心南京。两人还不约而同地抵制向政府过度垫款,张嘉璈制定的《中国银行则例》明确规定限制对政府垫款,并且采用收缩京钞与停止为政府垫款同时并进的方法,抵制了原来“中行”的垫款。宋子文制定的广东政府《中央银行条例》也明确规定:政府不得向银行任意支借现款,如贷款予政府,必须有相应之抵押品。
其实,1934年宋子文被迫辞去“央行”总裁职务,正是因为他不愿随意向政府垫款。1935年,张嘉璈被排挤出“中行”,同样是因为他不愿唯政府马首是瞻。
(二)银行必须保持信用
张嘉璈视信用为银行的“根本”。他说:“银行亦商店一种,出卖的是‘信用’和‘服务’。”[7]宋子文同样重视信用。也曾多次宣称“维持信用,即所以巩固本行基础”[3]。“货币流通,全恃信用。”[8]
为保持银行信用,张、宋二人一致主张应有充分的准备金。张嘉璈在“中行”上任伊始,便着手筹措足够准备金,并且规定不经一定的手续,任何人不得动用。鉴于当时军阀横行,为保护准备金的安全,树立纸币信用,“中行”将准备金集中于天津、上海、汉口三地。宋子文同样是在刚刚上任广州“央行”行长之时,便提议将造币厂的余利等资金按月拨交“央行”以备付息还本。
张、宋二人一致反对滥发纸币,张嘉璈在北京处理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解决原来“中行”滥发的不兑现京钞,为此,他殚精竭虑历时五年才大功告成,为此张嘉璈对滥发纸币,深恶痛绝。宋子文也深知滥发纸币损害信用,他曾经表示“本行(央行)发行纸币,惟有十足准备,决不敢超出定额”[9]。
为了保持银行信用,张、宋二人一致反对随意停兑停付。张嘉璈正是因为抵制北洋政府停兑令而在金融界崭露头角的。1916年,“中行”为政府过度垫款,造成危机,政府竟然下令“中行”、“交行”各地机构停止兑付,张嘉璈认为停兑则“丧失信用”,“必然沦入破产命运”[10](P222-223)。他勇敢地组织股东联合会,坚持“照旧兑钞付存”,终于顶住了北洋政府的压力,保住了“中行”上海分行的信用。宋子文有着同样的经历。1925年廖仲恺遇刺身亡,广州人心浮动,发生挤兑风潮,宋子文不仅照样兑付,而且延长营业时间,平息了风潮,维护了广东“央行”的信用。也正是在这次风潮中,张嘉璈的“中行”向宋子文主持的“央行”伸出了友谊之手,借予“央行”现金50万元。
(三)银行必须支持经济建设
张嘉璈在支持工商的同时,尤为重视运用金融手段支持铁路建设。宋子文也重视支持经济建设,在他主持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章程中便宣布:“本公司以协助并联合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他组织扶持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11],在这一原则下,张、宋二人实现了第二次握手,为中国经济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为什么张、宋二人会有如此激烈的斗争,又会有如此密切的配合?众多论者已从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分析,但却忽视了不同金融货币理论的深刻影响。
在救亡图存学习西方口号的感召下,中国涌动起留学热潮,满怀豪情的莘莘学子们学科学、学民主,也开始采集先进的货币金融理论成果。张、宋二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跨出国门进入了与中国大相径庭的经济文化环境,接受了与中国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金融货币理论,信用是银行的基础,服务是银行的手段,银行拥有自身运行的规律,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等近代银行的基本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脑海。
从中外交流的角度观察,不难看出,张嘉璈与宋子文重独立、重信用、重经济的观点,正是世界金融货币理论在中国银行家头脑中的折射,张、宋共识的源头正是他们在留学过程中获取的新知识。张嘉璈与宋子文反对过度垫款,反对滥发纸币,反对随意停兑的行动,正是近代金融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张、宋的合作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丰硕成果。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张、宋二人留学于不同国度,所接受的货币金融理论也不尽相同。张嘉璈1906年东渡扶桑,那时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于1872年颁布《国立银行条例》,建立了四家国立银行,但其性质并不明确,直到1882年,日本通过《银行条例》,以日本银行为中央银行,其它国立银行改为商业银行。无论是商业银行的出现,还是中央银行的建立,日本均晚于欧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使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有矛盾不如欧美那样尖锐。银行体系建立较晚,使日本银行券发行,票据交换,最后贷款人等矛盾不如欧美那样广泛和激烈。因此,日本经济学界尚未来得及对欧美已经十分突出的新矛盾进行系统的解释,传统的自由贸易和稳定通货方案仍占统治地位。
这时来到日本的张嘉璈不仅在西方古典金融财政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尚欠发达的日本经济,所有这些,奠定了他立志建立服务社会的商业银行的思想基础。以后,张嘉璈多次走出国门,足迹遍布欧亚拉美,进一步丰富了货币金融的思想,但服务社会的初衷未改。他那以利润为目的,以生意为宗旨的思想正是商业银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以经营资产和负债为手段的反映;他的服务社会、服务工商的观念,正是商业银行信用中介、支付中介、信用创造、金融服务职能的反映。正是基于上述观念,张嘉璈身为北京政府国家银行的副总裁却千方百计使银行向商业化发展,并多次抵制了宋子文加入官股、增加官权的主张,甚至不惜与国家权力相抗衡。
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第一,资本集中和生产垄断也名列世界前茅。这些推动了金融体系的深刻变化。自从1782年北美银行成立以后,美国银行逐步扩展,至1816年增为246家。南北战争后发展更为迅速,由于监管不力,弊端显露,金融恐慌一浪紧接一浪,1873年、1884年、1893年、1901年、1907年都发生了金融危机。尤其是在1907年的金融风潮中,纽约国民银行无法应付各地银行提款,被迫停止兑付,危机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一时间,怨声载道,引起各界的强烈不满[12](P13)。
美国一批经济学家开始积极寻找新理论和方法,他们中有些人,例如制度派,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的某些缺点,认为古典的自发调节论已经过时,主张政府应在经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应对私有经济,包括金融领域进行干预调节,甚至打出了“计划资本主义”[13](P191-193)的牌子。现实与理论促进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变革,美国早在1791年便设立了国家银行——第一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1912年,美国开始建立联邦储备制度,1913年,联邦储备条例通过,中央银行制度正式建立。
恰逢此时,宋子文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就读,而后又在摩根财团的花旗银行实习,危机的阴影,新学派的药方,新制度的手段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建立中国名符其实的中央银行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他那服务政府,运用权力的思想正是中央银行执行国家货币政策,建立金融权威职责的体现;他那监督限制金融的行动反映着执行中央银行职能的愿望;他要求改组“中行”“交行”的活动包含着加强“央行”调控能力的动机。尽管由于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使之不是那么纯洁。
留学的经历把相同和不相同的货币金融理论像种子一样植入了张、宋二人的心田,北洋军阀的腐败刺激了张嘉璈金融自由的理想;四大家族的权势催化了宋子文金融监控的愿望。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雨露使张、宋二人心中的理念萌芽出色彩斑斓的嫩叶。张、宋分歧的源头是世界金融货币理论的不同流派。
事实证明,张嘉璈、宋子文的“共识与分歧”正是建立于他们在中外交流中汲取世界金融理念的“共识与分歧”之上。
四
张嘉璈与宋子文之间的斗争与合作,分歧与共识,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一)相反相成,传播了系统的近代货币银行知识
近代银行与旧式钱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现象,当近代中国迫切需要更新观念,新金融机构服务于社会时,人们仅仅从外资银行那里得到了一麟半爪的知识,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新形势下产生的关于不同类型银行的服务、调节、管理职能的知识,不同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功用的知识,中国人更是知之甚少,因此,最早的华资银行——通商银行,只能实行“办事以汇丰为准”的原则,只能聘请英国的”洋大班”掌握经营权。为扭转这种情况,张嘉璈、宋子文等为代表的金融专业的留学生,把传播近代金融知识当作自己的历史使命。
1917年,张嘉璈创办了民国最早的金融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介绍国内外金融组织及管理经验,研究中国财政金融问题。此外,该刊还编辑出版《银行年鉴》及相关专业资料。这个刊物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从初创时的700份,发展到抗日战争时的2万份,行销全国及海外,坚持30余年,共出版1635期。张嘉璈担任“中行”副总裁时,特意成立经济研究室,聘请英国专家主持,研究室发行《中行月刊》、《金融统计月报》,并定期发布《中国银行营业报告》。这些都为传播近代金融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子文的理论建树较少,但他参与制定的广州《中央银行条例》、上海《中央银行条例》、《银行注册章程》、《银行法》以及他在许多重大场合的讲话和报告也在潜移默化地传播着金融知识。
毋庸讳言:张嘉璈阐述的主要是商业银行知识,宋子文宣传的主要是中央银行的原则,两人突出了不同的银行理念。单个考察,两人的介绍不免失之偏颇,但是,他们彼此互相补充则构成了比较完整全面的理论体系。
(二)异途同归,锻造了中国银行业的脊梁
张、宋学成回国之时,中国银行业还很稚嫩,至1911年,仅有华资银行16家。商业银行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银行难以完成稳定货币调节金融的任务。面对此情此景,张、宋二人为发展中国银行业,惨淡经营,功勋卓著。
张嘉璈从1913年进入“中行”到1935年被迫离任,艰苦奋斗22年,把先进的金融知识与“中行”的实践相结合。提出服务社会、顾客为上帝的口号;改革内部管理,健全会计制度;把一个残破不全、危机四伏的中国银行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银行。1928年至1931年,“中国银行”存放款超过中央、交通两大银行的总和。1934年存款总额达到5.4669亿元,各项贷款达4.1195亿元。1936年,“中行”在国内分支机构194处,海外机构9处,特约代理店96家[1](P8-10),真正成为中国金融界的擎天一柱。
宋子文从1924年开始,数建中央银行,在他主持下,上海“央行”规模不断扩大,从1928年至1933年,资产总额增加近10倍,存款增加近17倍,货币发行增加60倍,分支机构遍布大江南北,共计有分行6个,支行9个,以及相当数量的办事处、代办处。并在纽约、柏林、日内瓦、伦敦、巴黎设立代理处[14]。在他主持下,中央银行的职能不断强化,“中行”、“交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逐步被置于他的控制、监督之下,“央行”统率金融的地位正在确立。
张、宋二人主持的“中行”和“央行”几乎履行了各类银行的全部职责,从不同的支点支撑着中国金融的半壁江山。
(三)相得益彰,推动了社会进步
张、宋二人不仅在金融业扬鞭跃马,而且为其它的进步事业增砖加瓦。
他们曾相互支持,反对军阀,谋求祖国的统一。1925年,廖仲凯被刺,宋子文主持的“央行”风雨飘摇,张嘉璈主持的“中行”慷慨解囊,助“央行”一臂之力,使之渡过难关,以后,名为北洋政府国家银行的“中行”多次秘密接济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军,先后在赣县、南昌、上海,多次给予贷款。宋子文也投桃报李电令北伐军各部“加意维护中国银行”。两人同舟共济,密切配合,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力尽绵薄。
他们曾相互配合,支援经济建设,谋求祖国的富强。在他们努力下,1936年5月,引进英国贷款100万镑,扩建沪杭甬铁路。1936年2月,引进德国资金800万元,修建玉萍铁路。1936年12月,引进法国经费1300万元,修建成渝铁路。除铁路之外,他们还共同向西京电厂、首都电厂、成金煤矿、陕西同官煤矿、建川煤矿等工矿企业投资。两人协手并肩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
张嘉璈与宋子文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的关系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他们产生共识的基础之一是对世界文化主流的认同,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则是各种流派的不同影响。无论共识,还是分歧,都体现着留学生作为文化交流载体的价值,都从不同侧面满足社会的需要,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标签:宋子文论文; 中行论文; 银行论文; 央行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中国人民银行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信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