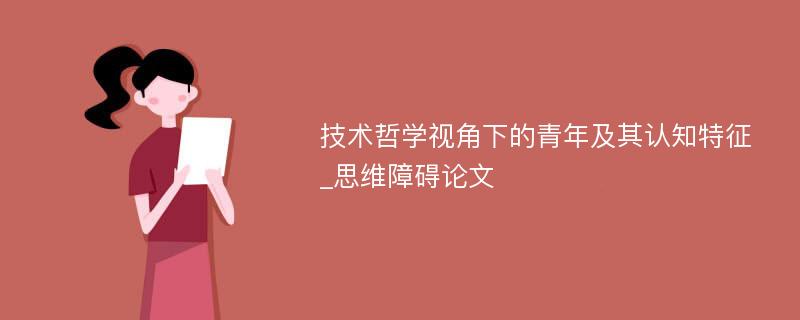
技术哲学视野中的青年及其认知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视野论文,特征论文,哲学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哲学的对象是人与技术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展开为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人对技术的价值评价,也包括技术对人的多维建构,尤其是技术的变迁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知方式的深刻影响。如果这里的“人”进一步具体化为“青年”,那么技术哲学的上述视野无疑为我们更丰富地把握青年及其当代认知特征开启一扇新的窗户。
一、青年与技术的亲和:一种本体论视角
当技术与人的关系具体化为技术与青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发现,青年与技术,尤其是青年与新技术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青年较之人类的任何其他年龄群体,都更容易与新技术相融合,这既表现为他们是发明新技术的主力军,也体现为他们是接收和使用新技术的先行者,从而较之其他年龄群体来说,他们是与新技术的亲和性最强的一个群体。
一方面,从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来说,青年通常在相关群体中占据最大的比重,从而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力军,成为历次技术革命的最主要的推动者。据统计,在前三次技术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的184人中,其平均年龄为33.9岁,其中22~44岁之间者最多,而29~35岁为最高区间[1]。从当前正在我国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来说,有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青年已成为推动我国IT业快速发展的现实的积极的推动力量,成为IT从业人员的绝对主体;近年来在我们的企业技术发展中有重大和突出贡献的研究开发人员中,35岁以下青年所占的平均比例为72.8%;企业近年来参加技术攻关的人员中,35岁以下青年所占的平均比例为79.0%;在IT企业近年来有重大和突出贡献的人员中,35岁以下青年所占比例日益提高[2]。如果IT业是当前“青春产业”的标志,那么更一般地说,新技术时代就是青年的时代,新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事业更多的是一种青春事业,这一点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相类似,例如标志现代科学革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一系列重大发现中,做出重要贡献者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的物理学家,所以被称为“男孩的物理学”(boy's physics)。这无疑是因为青年是人生中精力最充沛、头脑反应最敏锐、最少保守思想、最具开拓性的时期。
另一方面,从新技术的接收和使用来说,青年较之其他群体更能适应新技术。美国学者戴维斯(Fred D.Davis)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指出,影响技术被接受的主要因素有两个:①感知的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反映某种技术的使用者在使用该技术时认为它对他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②感知的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反映他使用该技术的容易程度,或认为它能为自己省事减少用心费神的程度。用户的感知易用性越高,其使用态度倾向越积极;同时用户的感知易用性越高,其感知有用性也越大[3]。可以说,无论从技术的感知有用性还是感知易用性,青年群体都会优于其他群体,所以任何新技术的“能手”、“标兵”多是青年,这也是青年的“可塑性”所决定的:他们对外界变化的顺应性强,由此也决定了他们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极强,从而能够最先掌握和熟练使用新技术,并成为新技术的主导使用群体。以互联网为例,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3年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的主体是29岁及以下的年轻群体,这个网民群体占到中国网民的58.2%;再就是,作为青年重要群体的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大专以上学历人群上网比例接近饱和[4],也就是说,在青年学生中,几乎无人不上网、无人不使用当代信息技术。进一步看,网络技术也是不断翻新的,目前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4.57亿,而“80后”、“90后”大学生作为网络新一代,是网络新技术和新应用的最先体验者。如果关注我们的身边还不难发现:在更新的移动互联网——手机网民中,绝大多数也是青年人;最新的手机(如智能手机)在青年中拥有最大的消费群体;最新的网络工具(从微博到微信等)在青年中最流行……而年龄越大,对上述新的网络技术通常越不敏感,其身上的“旧技术痕迹”就越深重,因为人到中年后其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会逐渐变弱,到了老年阶段后因顺应能力的衰减而对新技术常常陷入一种拒斥或恐惧的态度。
青年期也是人生中最肯学习的时期,从而青年也是最有可能接受到新技术、新科学知识教育的群体,这也决定了他们可以迅速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无论从精力上,还是记忆力和适应力上,或是知识文化背景上,青年对新技术的适应和掌握的速度和程度往往都是其他年龄群体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信息时代,他们最能在赛博空间中“开发”和熟练使用电脑和网络的新功能,所以他们更能做到对互联网了如指掌。看到他们敲击键盘时手指如飞,浏览网页时信手拈来,操弄手机时眼花缭乱,不能不让成年人感到自愧不如。因此,从这个方面讲,技术进步对青年是有利的,新技术是每一个时代给予青年的最好礼物,由此也决定了青年与新技术的天然联系和亲密感。
青年的创造力与技术发展的新陈代谢也是本质上契合的。青年代表未来,也代表技术发展的趋势,从而代表新技术的生命力。新技术对青年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年龄群体,因此青年对新技术常常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些也决定了在技术悲观者与乐观者的分界中,青年大多是技术乐观者,大多肯定技术进步的意义。澳大利亚科学技术理事会的研究表明:87%的青年人认为由于科学的成就能够克服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69%的青年人对利用科学达到社会提出的目标的前景作出了肯定的评估[5]。所以德国学者克路斯认为:“研究表明,成年人与被调查的青年并不完全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技术。例如,从总体上看,更为年轻的一代对技术的兴趣往往比其前一代的兴趣更为浓厚;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青年和技术共同分享着同一个无与伦比的荣誉,它们都被人们看成是社会未来的希望和寄托。”[6]
青年与技术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也形成了关于青年特征的一种本体论视角:其一,人际间“代沟”的形成是与技术的变迁密不可分的,当我们用“汽车轮子上的一代”、“电视机旁的一代”再到“互联网一代”来描述代际差异时,就可以看到它们都是由技术时代造就的;其二,代际的技术特征通常是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或者说技术代沟生成于该技术占时代性统治地位时所影响的那一代年轻人,一旦他们受到该技术的影响,在其身体和心智世界中就会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迹,直至成为中年和老年,都仍然被归属到那种技术所塑造的“**一代”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性的代际差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这也正是青年与新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必然要展现的一个侧面。
二、技术大于自然:青年认知的一般特点
技术与青年的上述本体论关系如果引向一种认识的分析,则可以发现青年身上普遍具有的并且在当代尤为鲜明的一种认知特征:技术大于自然。
何谓“技术大于自然”?“技术”和“自然”是具有对照性关系的两个范畴。从技术的“人工性”和自然的“非人工性”来说,技术就是非自然的东西,而自然就是非技术的东西。基于这样的理解,所谓认识中的“技术大于自然”,就是指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技术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于超过了“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东西。
技术与人的认识具有紧密的联系,作为媒介的信息技术更是具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是决定认识的关系,这是因为信息技术所决定的“信息的呈现方式直接影响人们对它(世界——引者注)的感知和理解”[7],或者说触动了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正如加拿大学者塞尔日·普鲁(Serge Proulx)所说:“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8];或如同法国学者西卡尔所说,“从达·芬奇的放大镜到‘探索者号’的精密仪器,从文艺复兴时代有着丰富的实物插图,但是读者有限的基础读本,到在卫星电视上通过大量传播图像所形成的视觉世界化,视觉机器管治着我们的视觉认知。它们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汲取什么”[9]。
由于技术与青年之间具有一种较之其他群体更密切的关系,也由于青年具有对新技术的更强的天然亲和性,或者说新技术对青年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年龄群体,使得青年在自己的认识活动中借助和使用技术的内在趋向也更强,于是当新技术造就新的认识方式时,无疑也最先是在青年身上实现的。作为新技术的领航者,青年与技术的亲和性,也容易走向过度依赖技术,极易造成一种在青年群体中的总体性认识论特征,这就是“技术大于自然”。
青年中的技术大于自然,其根基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极易生产这一倾向。“只要我们考察一下技术对青年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受到技术渗透的地方,都有青年人把自己的精力花在享用具体的技术上面:整天沉溺于玩各种电视电子游戏的青年人;以玩自行车或模型铁路装置为乐的青年人;以看电视来消磨时光的青年人;整日醉心于玩计算机的青年人……在目前的情况下,青年的直觉需求就是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年对计算机怀有如此浓厚而持久的兴趣。”[10]所以,各个技术时代,都可以看到“沉溺”当时的主导技术的青年人,他们的那段人生,借用今天“数字化生存”的说法,就是一种“技术化生存”,就是当时所呈现出来的在生活方式上的“技术大于自然”。
在电子信息时代的今天,这种技术大于自然的生活方式,使得年轻人看上去如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所说的完全是个“新的人种”:他们不是把电脑视为科技,而是与生俱来拥有的东西,用它去玩电动、传简讯、与多重平台进行多种操作;他们可以在脸书(像QQ)之类的同学网分享生活点滴,在YouTube上相互取悦,在博客空间里进行哲学沉思,在维基百科上贡献智慧,在飞客上创作最前卫的艺术,然后汇编档案,还常常在同时做到这么多的事情;他们使用新的技术成为习惯,而习惯成自然,技术不再被当做外来的东西,而是自己的自然的东西,技术成为新的自然[11]。为此法国科学院院士热拉尔·贝里认为:如果“老一代在晚年才看到数字化的到来,往往对其抱有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对年轻人来说,信息技术只是先于他们而存在的现实的一部分,与大海、高山和自行车等没有什么不同”[12]。当数字技术成为“新的自然”时,就使得“技术大于自然”走向一种更彻底的状态:技术创造自然,甚至技术决定自然。
技术大于自然的生活方式必然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从而导致一种相应的认知特征,其中最主要和大量的就表现为认识对象上的技术大于自然。
当认识对象上出现技术大于自然时,人的认识就越来越多地不是面对自然或面对直接对象的认识,而是面对虚拟实在的认识;他们认识的来源抑或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多的是技术手段,而不是从亲身在场、亲临其境、直接接触对象中去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人工的东西对他们的吸引力强于自然的东西,于是来自技术设备的人工的信息也强于来自现实世界的自然信息,使得他们整日眼不离屏:从手机屏到电脑屏再到电视屏,而这些都是技术显现中的电子显现。这种主要面对技术显现获得信息的方式,正是当今青年的主导性认识方式。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的青年比他们的父辈来说,有更多的时间是在网上度过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工作、学习之外,今天的大学生群体中平均每天花费3~5个小时在互联网上的比例最大,占40%,在5~7个小时的比例占15.2%,此外分别有5.1%和2.3%的大学生的非工作学习上网时间在7~9个小时和9个小时以上[13]。如果工作和学习也是网上进行的,则他们在网上度过的时间就更多,甚至可以说除了睡眠和休息,许多年轻的网迷一天的大多数时间可能都是在“阅读”各种屏幕中度过的:他(她)经常是查完短信查微信,查完微信看微博,看完微博溜新闻,然后就是看视频、玩游戏、网上聊天……这些“项目”被不知疲倦地轮番进行,加总其观看屏幕的时间,恐怕远远大于观察“现实世界”的时间。
今天,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得青年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更多地从网络中学习。即使课堂学习,也有网上课堂、远程教育、在线学习(e-Learning)、移动学习(m-Learning)、泛在学习(u-Learning)等,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s)使得学习可以无处不在,但这也使得“社会场景越来越由电子媒介交流所组成”[14],使得青年学生们所看到的事物都是透过某种技术手段呈现出来的,各种影像、视频、广告等视觉产品通过技术的复制手段制作出来并通过技术性多媒体来观看。当“技术性的观视”成为视觉文化最重要的识读手段时,一些青年学生就有了“一切源于技术”的观念或认知习惯,他们习惯于从技术系统中获知,从机器设备中求解问题,从网络中交友,从虚拟实在中建构理想,甚至想要知道“外面的天气怎样”时,也不是向窗外一看去获知,而是在从网上或QQ对话中查信息或问网友;当要想知道“去……怎么走”时,通常不在出发前或行路中当场询问别人,而是在网上查询或从GPS上寻找。就是说,电子屏幕中的技术显现几乎构成了他们的全部认识对象和信息来源,他们为电子信息所全面包围;或者说技术性显现而非自然显现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视觉和听觉空间,成为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于是,由技术性显现建构出来的虚拟世界几乎完全淹没了由自然事物构成的现实世界,或者以对虚拟世界的认同来否定对现实世界的感觉。
其实,从电视时代开始,青年就出现了在信息摄取的方式上技术大于自然的倾向,那时“对青年人来说,观看电视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与他们的父母相比,青年人的许多闲暇时间都花在观看电视和录像上;第二,电视,尤其是录像,使年轻人可以不受各种限制地观察现实生活,从而体验到不受父母和机构直接控制的另一种潜在的未来时空境界”。于是,“年轻一代的观众可以跨越老一代观众的语言障碍——主要是英语,从而通过外国传播网来获取信息”[15]。可以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种在认识对象上的技术大于自然在青年的身上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化的趋势。
作为一种认识论结果,技术大于自然在青年的身上则表现为“尽信网”,它是印刷时代“尽信书”的一种翻版。由于今天的青年人接触最多的是网络,他们最熟悉的信息获取方式就是网络,他们获取信息能力的强项就是网络搜索,从而形成了“有问题,找网络”的问题求解路径;只要在网上,他们便感到“无所不知”,而一旦离开了网络,则会感到“一无所知”;网络成为他们的“摇知树”,只要“摇一摇”(即“搜一搜”),就会要什么有什么。网络成为无穷无尽的知识和信息的源泉,从而在他们的“认识的来源”上十分明显地具有“技术性资源多于自然性资源”的特征。
技术大于自然的认知方式,对于青年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极大地扩展其认识对象和范围,使得过去受到物理限制而不能获取的信息和对象,变得可以信手拈来;可以使青年们的眼界开阔、信息灵通、思维活跃、知识丰富……但是,这一方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无论是认识对象还是信息来源,都出现了普遍的“二手化”抑或“间接化”,使得知识的可靠性基础、真理的证实方式都被严重地技术化,成为一种由技术宰制的认知活动。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李普曼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媒介提供的信息了解身外世界,但大众传播媒介并不是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通过对新闻和信息选择、加工、重构后向人们提示环境。这样的环境如果是被有意歪曲事实后形成的,则会使我们不能了解真相而停留于人工的技术性视觉表象之中,从而与“自然”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
技术大于自然还表现在认识的手段上,青年更趋向于运用技术工具而不是自然天成的人脑去进行信息的加工和处理。例如,利用互联网和搜索引擎来记忆,而不是用自己的大脑来记忆,“互联网把记忆全球化了。记住某一信息的最好方法不再一定是用心记忆,而是知道如何在网络上借助搜索引擎找到它”[16]。又如,用计算机或计算器来计算,而不是用“心”去计算。借助技术工具可以克服作为自然手段的大脑的许多局限,使得信息的储存量、信息处理的速度和精度等得到极大的提高。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就是人的一些相应的能力出现衰退。例如,过去的青年中出现过心算奇才——史丰收,而今天有谁听说过新的史丰收?不仅如此,青年学生的一般计算能力也因为使用计算器而出现下降,一份关于计算器对青少年运算能力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学生普遍反应脱离了计算器后,运算的准确性下降;计算器的使用也影响了思考的灵活性,青年学生如果一味地使用计算器,他们只会简单、机械地把数据输入求解,没有去思考如何快捷、简洁地解决问题,缺少了这方面的训练,这就等于失去了提高运算能力的有效途径;使用计算器对思考的严密性也产生影响,使用计算器时,一般都会省去运算过程,这对学生的数学思维、数学素质的提高非常不利。还有,过多、过滥地使用计算器,学生就会不愿花时间进行思考,做规范的运算,从而草率从事,久而久之,思考没有条理、混乱,运算逐渐生疏,而且养成了粗心、马虎的不良习惯,缺乏意志和毅力的磨炼。计算器的过多使用同时也造成了有些学生只习惯于单向、单层次的运算,习惯于顺向计算,不习惯于多向、多层次的运算,更不习惯于逆向运算。总之,计算器的使用削弱了学生的运算能力,影响了学生数学素质的提高[17]。
可见,技术大于自然既是青年在认知活动的优势,也是其劣势,且常常是优势转化为劣势,这就需要合理评价和有限发挥这一特征,而不是无限度扩展这一认知特征;作为青年人,也必须在这一点上保持警醒,寻找尽可能多的机会“回到自然”,否则自然(既包括外在的自然对象也包括自身的自然能力)就会在“技术的汪洋”中消失殆尽。
三、碎片化与图像化:网络时代的青年思维意象
青年身上所具有的技术大于自然的认知特征,使得技术发展所引起的人类思维方式的变迁,或者说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人类认知特征的巨变,常常首先是在青年的身上呈现出来;于是,当代信息技术使我们进入网络时代后所形成的一些新的具体认知特征,也必然率先集中地体现在青年身上。如果“老一代”还保留了因使用过去的技术而形成的思维认知“传统”,那么今天的青年一代正在使这些传统真正地成为“历史”,而使得因为使用网络和计算机所形成的“认知景观”鲜明地呈现出来,这也是所谓代际特征的认识论表现。
从技术塑造人的关系来看,青年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就被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其《技艺与文明》一书中,就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被拘役于时间的人。由于深受当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今天的青年被称为“互联网的一代”,或“IT一代”,其思维认识特征具有明显的信息技术特征,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活跃、发散性中的碎片化、多媒体显现中的图像化。
当今的信息技术,使青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多更快地获取信息,但同时他们又被目不暇接的信息造就了一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和思维。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尔在他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害我们的大脑》一书中,介绍了许多关于互联网的使用如何改变人们思维习惯和认知特点的看法。例如他看到,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这就是所谓“支离破碎的浏览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互联网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它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状态”,于是出现了所谓的“碎片化”;碎片化使我们的思维无法再“深刻”下去,因为显然,我们不再拥有保持深刻所需要的注意力:“必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一个最大的悖论是: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互联网所做的似乎就是把我们的专注和思考能力撕成碎片,抛到一边。无论上网还是不上网,我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互联网传播信息的方式,即通过快速移动的粒子流来传播信息;以前,我戴着潜水呼吸器,在文字的海洋中缓缓前进。现在,我就像一个摩托快艇手,贴着水面呼啸而过……他们上网越多,阅读长篇文章就越难集中注意力。有些人担心自己正在患上慢性注意力分散症……于是,“我再也读不了《战争与和平》了,我已经丧失了通读长篇文章的能力。甚至就连三四段以上的博文,我都觉得内容太多,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来,只能走马观花地一瞥而过”[18]。阅读的碎片化导致的是思维的跳跃性,这是“当代青年”的思维认知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一项研究显示:现今的大学生在阅读习惯上有以下明显的特点:第一,思维的广阔性,思想活跃,兴趣广泛,但兴趣中心容易转移,也容易“跟风”阅读,有盲目性。第二,解读信息呈现平面化和“碎片化”的倾向,不完整和不够系统。这是由于“快餐式”阅读方式所导致的。现今的不少学生不再像以往的大学生那样专注于读大部头的原著经典和喜欢看深入解析性的文章,而是讲究阅读的“短、平、快”感受,即喜欢读一些信息量较大的时新杂志刊物,读一些短小活泼的小材料,读只需平面信息链接、不需深入剖析的时文评议和社会动态,读轻松、好玩、有刺激的书刊,而不大喜欢看理论类书刊,等等[19]。于是,青年一代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但又缺少深度;可以说,这正是网络造就了青年的这些认知特点。
由于网络阅读也是一种多媒体阅读,当信息采用多媒体来显现时,采用图像方式的生动而直观的显现就成为易事。由于对图像的数字化摄取、计算机制作以及电子显现的极大便捷性,使得网络空间中的图像元素越来越多进而趋向于占据主导性地位,出现文字网页不敌视频网页的格局,电子文化由此而日益成为图像文化,而图像文化似乎也成了多媒体文化的代名词,图像化也就成为深受当代信息技术影响的青年人的又一个明显的认知特点,他们也因此被称为“读图一代”。
较之文字来说,图像可以更直观传达信息,一目了然,所见即所得,读图需要的知识储备更少,所以视频传播可以使“受众”在轻松愉快中获取信息;而且,图像传播所表达的内容可以非常丰富,甚至一图胜千言,传达出语言文字所传达不出来的意义。这源于图像的易读、轻松而感性的先天优势,较之文字来说更为青年所喜闻乐见。
但是,又必须看到,由于图像传播借助多媒体显现而具有的强势地位,使得文字的传播效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处于了相对的弱势,以至于形成了所谓的“图像霸权”,甚至使当代社会面临着“景象的高度堆积”、“拟像”的遮天蔽日,“在这里,图像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图像文明’。这里的现实成了图像暗淡的倒影……几乎无法区分现实和虚幻”[20]。当文字描述在强大的图像霸权面前黯然失色、苍白无力时,一些文学作品就只有在改编成电视或电影后才能“走红”,一些经典著作只有变成《图说***》的方式后才能畅销;而在文配图的作品中,文字完全沦为了图像的陪衬。图像使人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直观形象的表层内容,如果疏于文字,则会渐渐远离内在的形式规则和浓厚的理性文化;图像往往造成对感官刺激的依赖,形成放纵和宣泄的浮躁思维方式,而对话语符号的把握,则需要反复咀嚼的深度思考,形成紧张严谨的思辨模式,后者无疑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所不能缺少的。长期满足于读图的轻松,不仅会导致思维的懒惰,还会使得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都可能出现“符号厌恶症”,最后造成抽象思维和对文字理解能力的下降,使得我们不得不担忧“读图一代”有可能再回到仅有或主要靠“形象思维”的时代。
四、结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青年与技术具有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所包含的是种种“双重性”,例如,新技术为青年使用时,他们既可因过度使用诸如互联网和手机之类的新技术而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也会因此而获得其他年龄群体无法获得的益处[21];再如本文所分析的技术对青年认知发展的双重性:他们的认知长处和短处都与这种特殊性有关。其长处在于,新技术如果加在精力旺盛、求知欲强的青年身上,青年就会如虎添翼,其认知能力和信息量飞速增长;此时新技术的特征与青年的认知特征是互惠的,青年的一些积极的认识特征本身就是源于技术的进步,例如新技术的拓展性就使得青年在认识上的创新性具有了技术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在青年对新技术过分依赖乃至走向沉溺后,则会使“技术大于自然”被推向极端,例如在今天的一部分青年身上,电子屏幕仿佛具有无穷大的魔力,将他们牢牢地吸引在它的一旁,使其失去了阅读自然之书、生活之书、社会之书的兴趣。海德格尔曾经深刻地指出了技术具有遮蔽自然的一面,这可视为人类认识史的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的率先承担者往往就是青年,将这个主题发挥到极致的往往也是青年。当青年生活于这样的环境时,当青年还充当着引领这一认识方式的角色时,所意味的就不仅仅是技术大于自然,还可能是“技术吞没自然”。
技术造就了人的新进化,也导致了人的一些能力的逐渐退化。新技术越强大,它具有的“替代”人的功能就越发达,人就越可能将自己的“自然能力”移交给技术,而自己则变得不再具有这样的“自然能力”,这也是技术大于自然进而“吞没自然”的特征,而青年对于新技术的青睐一旦变为依赖之后,自己的“自然性”也可能“率先”丢失。
基于此,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青年与技术的关系就需要有更合理的调整,其对新技术的追求当然要保持,同时,也要避免对新技术尤其是某种单一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沉溺,需要“博采”各种技术之长,来辅助自己的全面发展;也要不时地“放下”技术,与各种维度的“自然”保持亲密的接触,使自身的“自然性”在强大的“技术性”面前能够存在和得以显现;还需要在自己的认知世界中,尤其是当代信息技术辅助的认知活动中,让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达成一种有机的交融,而不是用前者完全吞并了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