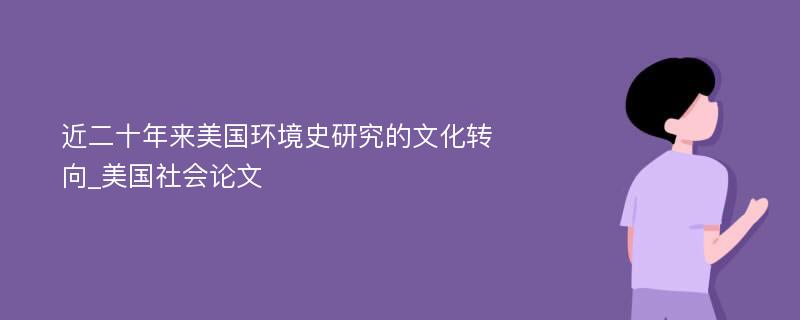
近二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近二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环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重点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美国环境史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注重物质层面的分析转向注重社会层面的分析;从强调生态环境变迁及自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转向强调不同社会群体与自然交往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从以生态和经济变迁为中心转向着重于社会和文化分析;从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转向运用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分析工具。总之,环境史越来越接近社会文化史。这一范式转换,被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理查德·怀特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①时至今日,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明显的趋势,文化转向被研究者广为接受。文化转向在使环境史走向主流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原有的一些特色。文化转向直接关涉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在环境史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议。现对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文化转向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兴起背景及其利弊得失予以评述。②
一、文化转向及其主要表现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主要是指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它将自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加以探讨,并强调将种族、性别、阶级、族裔作为分析工具引入环境史研究,侧重探讨人类历史上不同人群的自然观念及其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理查德·怀特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史最主要的变化“或许可被称为文化转向”,主要表现为“在早期环境史研究中不见踪影的文本、故事、叙事,受到了关注,同时,研究重点从荒野转向了人工景观”。③怀特提出“人工景观”(Hybrid Landscape),实际上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的边界模糊,文化观念在环境变迁中发挥着影响。
早在1990年的一场学术讨论中,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就已初露端倪。《美国历史杂志》1990年第4期刊发了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地球的变迁:论史学研究的农业生态视角》以及围绕该文的一组评论文章。④这组文章出自美国最知名的六位环境史学者之手,在环境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沃斯特提出,环境史要重视农业生产,以自然环境、经济活动和生态变迁为研究中心。虽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理查德·怀特、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都认可农业生产在环境史研究中具有的重要性,但他们认为环境史应该大力加强对城市的研究,重视社会分层和思想文化的作用。在克罗农看来,人们在选择食物时会受文化观念的影响,食物“也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建构”。怀特也认为,在农业生产中,文化观念可以发挥与生产方式同样重要的作用。克罗农提出要将环境史研究的领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指出环境史研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没有从不同群体的角度入手,探究社会分层对环境变迁的意义”,环境史应充分探讨不同社会集团及其互动对环境变迁的影响。⑤而麦茜特则倡导在环境史研究中采用“性别分析”。⑥沃斯特在当期发表的回应文章《超越文化视角》一文中,担心文化分析将削弱环境史研究的特色。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会使环境史沦为社会史”,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特色将丧失殆尽。⑦
直至今日,这场争论仍以某种方式继续着。从1990年以来,以沃斯特为代表的一方依然坚持环境史研究要以生态变迁为中心,大体可称为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分析学派”;以克罗农、怀特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大力拓展社会分层和文化分析,可称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分析学派”。⑧
在克罗农和怀特这两位领军人物及其支持者的大力推动下,文化转向已经成为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1990年在《美国历史杂志》参与讨论环境史的六位学者中,克罗农、怀特、麦茜特和斯蒂芬·派因(Stephen J.Pyne)均对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表示赞同,成为此后推动环境史文化转向的先锋。他们总体上以四种形式推进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一是重视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研究,将种族、阶级和性别作为环境史的分析工具;二是通过社会文化建构模糊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突出文化的作用;三是以生态学中的混沌理论为基础,扩大相对主义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影响;四是将环境史视为讲故事的艺术,强调史学研究的主观性。在这些合力推进环境史文化转向的学者中,克罗农和怀特功不可没,两人的有关著述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而使文化转向渐成燎原之势。
在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克罗农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学者,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开辟道路,推动环境史的繁荣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推动环境史研究从荒野和农村转向城市,带动了城市环境史尤其是城乡关系史的研究。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⑨是一部公认的杰作,该书考察了1833-1893年芝加哥发展为美国第二大都市的历程,通过追踪芝加哥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商品流动,揭示了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生态和社会变迁。该书将城乡视为一个整体,在农业史与城市史之间搭建了桥梁,将城乡关系纳入了环境史研究的范畴。其二,克罗农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叙事引入环境史研究,⑩对环境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发起了挑战。他通过对比两部关于美国尘暴重灾区(Dust Bowl)的历史著作,表明历史研究的主观性。(11)克罗农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破除环境史研究中“衰败论”的叙述模式(declensionist narratives),激励公众要对环保更有信心。(12)其三,克罗农解构了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荒野神话。所谓荒野,是指纯粹的自然,是指那些未曾受人侵扰、应该予以保留而不进行开发的地方,20世纪下半叶,这种“荒野”神话越来越流行。克罗农则将荒野(自然)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并以家园取代荒野作为环境史叙述的中心,由此减少既往环境史研究中关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争论。(13)在克罗农的带动下,文化分析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日益流行。
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美国西部史和环境史学家,怀特通过批判环保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他率先明确提出“文化转向”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源于其多年来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印第安人的一些观察和思考。他的研究表明,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带来了剧烈的环境变化,这种观点是对传统看法——印第安人没有改变环境——的直接修正。这种观点虽然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似乎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但实际上它挑战了环境保护主义以及受其影响至深的美国环境史研究。环保主义者“大多把人类在自然中的创造性工作等同于破坏”,“把自然当作人类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很少把它视为人类谋生和工作的所在。环保主义者将过去理想化、借古讽今的倾向也较为明显,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印第安人塑造成生态圣徒。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环保运动和自然的这种褊狭理解,严重制约了环境史研究的范围。而怀特在文化转向方面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剖析环保运动的错误倾向及其消极影响。在《你是环保主义者还是要为生存而劳动:工作与自然》(1995)一文中,怀特对自然进行了解构,指出自然实际上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人类的劳动“将自然与人类联系起来”,模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劳动应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起点”。(14)在1996年出版的一部有关哥伦比亚河的著作中,怀特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怀特将劳动从单纯的人类劳动,推延到自然万物所有涉及能量凝结与消耗的活动,用劳动和能量流动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连接起来。在怀特看来,在环境史研究中,人类与自然彼此融合,既不存在脱离人类的自然界,也不存在脱离自然界的人类。怀特打破了环境史学界对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解,有利于推进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但这种理解也消解了自然本身,自然不再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所有的景观都成了人工景观。
除文化建构之外,阶级、种族和性别分析在环境史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也是文化转向的另外一个主要表现。在推动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方面,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和安德鲁·赫尔利(Andrew Hurley)无疑具有开拓之功。
戈特利布是一位城市和环境政策专家,他于1993年出版的《呼唤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演变》一书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自然和环保运动的理解,对推动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本书出版之前,环境史学者在追溯环保运动时,只局限于吉福特·平肖倡导的资源保护运动和约翰·缪尔领导的荒野保护运动,环境史学者所理解的自然都位于城市之外,与市民的生活无关;反污染运动似乎是在战后才突然出现的;环保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仿佛也只有白人男性。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完全颠覆了上述观念,提供了一种对自然和环保运动的全新理解,有力地推动了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戈特利布认为自然存在于“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同时,环保运动是应对工业和城市巨变而出现的一场遍及城乡的社会运动,它不仅关注荒野保护以及自然资源的明智利用和有效管理,而且也致力于反对污染,维护公众的身心健康。另外,该书把环保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将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分别探讨性别、族裔、阶级因素在环保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戈特利布认为,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了环保运动的历史演变,而且关系到当前环保运动应如何定位。(15)该书在环境史学界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将环境史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城市,促进了社会文化分析在环境史领域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安德鲁·赫尔利是一位以环境史研究成名后来却与该领域渐行渐远的城市史学者。他的《环境不公: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及美国工业污染》(1995)一书是环境史与社会史融合的典范。该书从多个方面推动了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他明确提出,环境史学者要关心环境权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社会上广泛存在,而且主要以“阶级、种族、性别和族裔”为界限。因此,他提出要“将环境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16)用社会分层的分析方法来探求环境变化。其次,他明确提出,“以社会平等作为环境变化的衡量标准”。传统上,“生态平衡”往往用于衡量环境变化,但在赫尔利看来,这一标准暗含着一些前提:生态平衡在人类干预之前一直存在;生态失衡是人为干预的结果,人类干预越多,环境就越糟糕。但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根本就不存在平衡状态。传统标准因为过于主观而存在不足。赫尔利认为,“如果从社会平等的角度,以不同社会群体所受的影响来衡量环境变化,环境史学者的研究将会更加客观。”(17)再次,他也不认可环境史研究中的“衰败论”叙事模式,而对人类未来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环保运动已经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进步,城市人口比以前更长寿,人类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在发生积极变化。赫尔利主张将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为挑战而不是被迫承受的恶果加以叙述。《环境不公: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及美国工业污染》一书成功融合了环境史和社会史,被广泛列为环境史课程的必读书目。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史与社会史融合的迹象日渐明显,环境史研究中大量出现了有色人种、劳工、妇女的身影。环境史与社会史的广泛融合,促进了黑人环境史、劳工环境史、妇女环境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黑人环境史是环境史学者所开展的有关“种族、族裔与环境”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环境史学者所关注的种族主要限于印第安人,此后则转向了以黑人为代表的少数族裔。(18)斯图尔特(Mart Stewart)、普罗克特(Nicholas Proctor)及赫尔利等学者分别探讨了黑人作为奴隶、分成佃农和劳工在田间、林地和工厂的经历。他们三人被认为是黑人环境史这一新兴领域的开拓者。(19)在他们的带动下,有关黑人的环境史成果快速增加,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拥抱风雨:美国黑人与环境史》这本文集,该文集以种族、族裔、性别和阶级为分析工具,探讨了黑人对自然环境的感知和利用,涉及奴隶制、内战后种族隔离、战后民权和环境正义运动三个阶段,是融合环境史和社会史的一部力作。
劳工环境史是环境史及劳工史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广泛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劳工史和环境史存在互通之处。劳工史研究的先驱康芒斯(John Commons)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强调环境的作用,并从环境的角度解释20世纪美国劳工运动的低迷状态。(20)另外,劳工史的研究主题目前已经从劳工领袖、劳工组织和工人运动转向劳工生活状况本身,大量涉及工人住处和工作场所的环境卫生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劳工和阶级的环境史成果不断涌现。阶级分析目前已被用于探讨“奴隶制与佃农、工业化、荒野保护与自然保护、劳工与环境保护主义”等主题。(21)
妇女环境史则将性别分析、妇女史和环境史糅合在一起。妇女环境史的兴起,离不开社会性别史和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的20多年间,麦茜特几乎是独自一人,努力将性别分析带入环境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分析开始受到更多环境史学者的关注。尽管如此,性别分析明显少于种族、阶级分析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妇女环境史仍然处于“萌芽状态”。(22)而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性别和美国环境史”方面的研究到现在几乎还没有开始。(23)
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史学者的倡导和重视。1996年,社会史专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在《人为的不平等:社会史和环境史》一文中提出,“社会史和环境史从根本上是可以兼容的,而且可以互为促进”。在他看来,社会史和环境史有三个共同点:它们所关注的都是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对象,所运用的新史料都可适用于统计分析,它们的兴起都与社会运动相关,都要表达一定的道德和政治诉求。他通过分析多部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著作,表明这两个领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交叉。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史必然是环境史,而环境史也必然是社会史”。(24)英国社会史学者斯蒂芬·莫斯利(Stephen Mosley)也倡导社会史和环境史的融合。莫斯利提到,这一融合还很缓慢,两个领域的学者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环境史不应该“回避种族歧视、性别关系、阶级冲突、族裔差异等棘手问题”。(25)环境与认同、环境正义与消费等主题可以在这两个领域中建立联系,努力促使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成为社会史优先考虑的主题。
近20年来,文化转向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追随,在年轻一辈的环境史学者的作品中有明显体现。文化转向可以从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中得以反映。对美国环境史学会专业期刊有关文化转向的文章和书评的统计结果表明,在1995年以前,很少有文章的标题包含“种族”、“阶级”与“性别”这几个涉及文化转向的关键词,它们在全文检索中出现的频率也很低。但从1996年以后,这些术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笔者通过检索相关数据库后发现,在1978-1989年间,《环境评论》没有登载过全文同时含有这三个关键词的文章,但在1990-1995年间,这类文章为6篇,而在1996-2012年间则达到了52篇。(26)如果在全文中检索“社会史”、“非裔”、“西班牙裔”,得到的结果也很类似。这些术语出现频率的普遍上升,可以反映出文化转向这一新兴趋势。
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也可以从不同时期梳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综述文章和著作中得以反映。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为环境史学者所采用。怀特在1985年指出,当时还很少有环境史学者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这种研究刚刚开始,还显得非常零散。(27)他在2001年评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变化时,对文化转向有所提及。(28)哈尔·罗斯曼(Hal Rothman)在1993-2002年间担任《环境史》杂志主编,他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运用种族、阶级与性别分析方法的一些环境史成果。(29)J.唐纳德·休斯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在提纲挈领地梳理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时,也专门提到环境史学界有关城市环境史、环境正义、妇女与环境等方面的大量成果。(30)在道格拉斯·萨科曼(Douglas C.Sackman)主编的《美国环境史研究指南》(2010)这部工具书里,“种族”、“阶级”、“性别”与“文化转向”各被单列一章加以详细探讨,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跃然纸上。
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既是顺应社会现实的结果,也是史学发展新动向在环境史领域的反映,与环境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又有密切关联。环境正义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促使环境史学界开始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反映了社会史及新文化史对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冲击和影响。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与环境史学者早期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合理都联系在一起。
环境史对种族、劳工、女性问题的重视,与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有直接关系。环境正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有色人种、劳工阶层争取平等环境权益、保护家园免受污染的运动。自战后以来,不断剧增的有毒有害废弃物对美国民众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但有毒有害垃圾处理设施在选址时往往会倾向于有色人种及贫困劳工居住的社区。这些弱势群体因此饱受污染的困扰,并承受着更多的健康威胁。环境正义运动的宗旨就是要争取平等公民权利,因此得到了民权组织、劳工组织、妇女组织等众多团体的声援和支持。在环境正义运动的推动下,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11日签署了第12898号行政命令,责成联邦政府各部门切实采取行动,保障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口能享有平等的环境权益。
环境正义运动对环境史研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重新塑造美国的主流环保运动这一形式进行的。首先,环境正义运动为主流环保运动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以富裕白人为主要社会基础的美国环保组织,致力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河流山川的保护,而对有色人种和劳工阶层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视而不见,以致被扣上种族主义组织的帽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保护弱势群体的环境权益被纳入主流环保组织的议事日程。其次,环境正义运动扩展了人们对环境的理解。环境并不只存在于乡间野外,同时存在于城市、郊区的各个角落,存在于人们生活的社区、工作及娱乐场所。再次,环境正义运动表明,少数族裔、劳工阶层非常重视环境问题,他们是环保斗争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环保运动的发展史足以表明,环保组织如果仅拘泥于环保本身而不关心社会正义,就会因孤掌难鸣而难有大的作为。环保组织只有将保护环境与维护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与民权、劳工、妇女等组织广泛结盟,才能扩大社会基础,把环保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为推动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现实动力,环保运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对环境史领域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些环境史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环保运动的新发展为环境史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在1995年发表的《平等、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史》一文中,梅洛西就呼吁环境史学者要重视种族问题,重视环境正义运动所提出的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相关的环境平等;环境的文化建构;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冲突。(31)而麦茜特的《种族主义的阴影:种族和环境史》一文,则结合美国环保先驱的有关著述,指出了环保组织的种族偏见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她认为,环境史学者应该正视这些问题,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研究美国历史上的环境正义问题。(32)在这些学者的倡导下,美国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上有关“种族、族裔与环境”的小组讨论逐渐增多,1995年拉斯维加斯的会议上达到4场。而此前这种讨论很少,有关该主题的小组讨论直到1989年才首次出现,且只有一场;1991年有两场;1993年的学术研讨会则没有出现类似主题的小组讨论。(33)
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环境史领域的折射。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动以及战后以来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战后,有色人种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增加,黑人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9.9%上升到1999年的12.8%,而拉美裔人口则从1970年的4.4%上升至1999年的11.5%。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有色种族向中心城市聚集,比如在1988年,美国西部和北部98%的黑人都住在都市区。(34)从战后以来,高校向女性、有色人种和平民子弟敞开了大门。1948-1988年,高校女生的比例从28.8%增至54%。(35)大学生中有色人种的比例也在提高,1960年为6.4%,(36)1990年为20.1%,1997年高达26.8%。(37)低收入家庭高中毕业生能上大学的比例,从1971年的26.1%增至1985年的40.2%,1993年则达到50.4%。(38)女性、有色人种和平民子弟在高校学生和教师中的比例逐步提高,这些群体在文化领域的影响日渐扩大。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其在中心城市的聚居,以及文化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少数族裔的族群认同和政治意识日渐增强,有色人种争取文化认同、争取平等权益的热情更趋高涨,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兴起。多元文化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实践。它要求的不仅是尊重有色种族的文化和传统,“而且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将种族平等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这已经超越了文化的范畴而成为直接的政治诉求。(39)多元文化主义对包括环境史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强烈冲击,促进了以弱势群体为研究重点的新美国史学的兴起,并推动了少数族裔研究和性别研究中心在大学的广泛建立。
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突出不同群体对美国历史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学界对劳工、妇女、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的关注,部分就是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这些群体在环保运动兴起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开始逐步得到承认。妇女在探索与保护自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成为诺伍德的《来自地球的灵感:美国妇女与自然》、沙夫主编的《性别视野下的自然》、赖利的《妇女与自然:拯救“荒凉”的西部》等著作探索的共同主题。(40)杜波依斯(William Du Bois)、布克·华盛顿(Booker Washington)等多位黑人领袖的环境观念也得到了探讨。(41)劳工运动和劳工领袖对环保运动的贡献也成为环境史学者研究的课题,已有的研究表明,现代环保运动的领袖除了广为人知的利奥波德、布劳尔(Brower David)、卡逊等人之外,还应该包括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西泽·查维斯(Cesar Chavez)、阿诺德·米勒(Arnold Miller)等劳工领袖。另外,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早期环境史研究中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
环境史将种族、性别和阶级作为分析工具,显然受到了社会史的影响。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史在国际史坛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是西方史学在战后最明显的发展转向。社会史关注平民百姓,主张自下而上看历史。率先研究社会史的那批学者,大多属于美国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将撰写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视为重建其所在群体历史记忆的契机,为那些默默无闻的民众代言。这批研究人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不断壮大。1978年社会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数量是1958年的4倍,社会史超越政治史从而成为历史学的显学。(42)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对2003年春季收集的8861名会员年度登记表的统计显示,社会史是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领域,是1369人的首选研究领域。其次为文化史(1148人)、政治史(1033人)、妇女史(997人)、非裔美国人史(940人),环境史为300多人。(43)社会史讲述被边缘化的小人物的故事,常常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进步史观,对人文社会科学所标榜的客观、科学和理性不以为然。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使社会史受到右翼人士的嫉恨和攻击,而被指斥为含沙射影地攻击美国现有的体制,是在故意矮化美国历史。受社会史的影响,种族、阶级和性别已经成为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而且环境史不仅关注弱势人群,也总是为底层民众鸣不平并为他们代言,环境史研究的道德伦理诉求又有所增强。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明显受到了新文化史的影响。(44)新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战后西方史学继社会史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史学转型。新文化史广泛应用文化建构、话语分析、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的叙述等方法开展研究。新文化史背离了长期以来历史学的科学化取向,主张向历史学的人文化取向回归。新文化史反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经济决定论或社会结构决定论,强调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化史学者看来,“文化与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之间有一种不分轩轾、相互依赖的关系”,“精神与物质之间,没有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而是相辅相成的”。在新文化史的推动下,历史学从向经济学和社会学靠拢,转向朝着人类学和文学靠拢。(45)新文化史反对社会史研究中枯燥的数据统计和计量分析,注重叙述的文采和技巧。新文化史也接受了人类学中所蕴含的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所有文化都有存在的价值,各种文化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新文化史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指导,将所有的知识都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新文化史既是对社会史的反驳,也是对社会史的继承和发展,它坚持社会史“自下而上”的治史宗旨,将视野投向了占人口多数、但在历史上默默无声的芸芸众生,重视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大众文化及其日常生活。新文化史作为一场席卷整个欧美史坛的史学思潮,对环境史这一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环境史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自然观念的变化,人们不再相信自然本身的精巧平衡及和谐有序,而认为自然本身就是混乱无序的;(46)纯粹的自然、神圣的荒野都不存在,而只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在环境史著作中,生态破坏也被视为一种文化建构而被生态变迁所取代。上述种种理解,虽然有利于克服早期环境史著述中衰败论的叙事模式,但也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还与该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遭遇的发展瓶颈有关。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花结果,多本著作深受学界好评并荣获嘉奖,环境史在史学界已经赢得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环境史研究也面临诸多困境,在80年代中后期跌入低谷。《环境评论》没有充足的稿源,学会会员的登记情况也不太理想,甚至连每两年一度的美国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也难以为继,学会的一些负责人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担心学会和刊物是否能够支撑下去。(47)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史学界整体上对自然和环保运动存在褊狭理解甚至误解。自然往往被认为与文化对立,只存在于乡间野外,而不存在于城市。与此同时,环保运动虽然在百余年前兴起之际,便将“效率、平等与美丽”作为其关心的三大议题,但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它实际上偏重于资源保护和自然保护,而污染对弱势群体身心健康的威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受其影响,环境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依然主要局限于研究荒野保护与自然保护的历史,而很少涉及城市,也很少论及少数族裔等普通民众。同时,受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90年代之前的环境史研究存在明显的道德伦理诉求,美化过去、批判现在和怀疑将来的悲观倾向也不罕见。而正是在环境史遭遇如此困境的情况下,克罗农将“第二自然”的概念引入了环境史研究,并对流行的“荒野”神话进行了解构。而怀特为解构自然和环保运动也做了一些努力。在他们的笔下,第一自然不过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人们所接触的自然,实际上都是“第二自然”,是经过文化改造后的产物,存在于人们居住、工作和娱乐的每一个地方。可以说,文化转向为90年代以来环境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文化转向之所以受到美国环境史学界的普遍欢迎,与诸多环境史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也存在一定关联。美国多数环境史学者在历史系工作,普遍缺乏自然科学的专业训练,很难自如地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面对知识结构的缺陷和环境史研究所提出的挑战,一些学者在努力提高自身的自然科学素养,但也有一些学者以后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为理论武器,把自然和科学知识视为一种文化建构,实质上是要向科学的权威发起挑战。尽管科学存在一些问题,但自然科学知识对环境史学者了解自然界如何运行是至关重要的,环境史学者要想写出一流的作品,就必须尊重科学,并将科学作为研究的重要参考。正如沃斯特所言:“尽管我批评科学的某些方面,尽管我知道科学总在变化,并不精确,而且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能以科学为指导。”(48)
三、文化转向的利弊得失
文化转向作为近20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明显趋势,带来了环境史研究的繁荣,环境史开始融入并影响美国史学的主流。但文化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环境史研究的特色。随着文化转向的深入,其弱点日益突出,生态分析亦将受到相应的重视。文化分析和生态分析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范式,虽然各有侧重,但彼此之间也有诸多共通之处,可以相互促进和补充,从而将环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环境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克服美国早期环境史研究暴露出来的一些缺陷,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促进了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并推动环境史融于并引导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转向从多个方面推动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
首先,文化转向有利于环境史摆脱生态学整体意识的消极影响。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科学,生态学自始就成为环境史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49)在生物学的分类系统中,人作为一个物种,隶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人被视为生物学基本分类中最小的研究单位来加以对待。生态学很少关注个体的差异或不同,用这种方法探讨个体和个性就会充满风险。(50)受生态学的影响,环境史也秉持整体论。整体论倾向于把人类的内部差别缩小,或者把一个群体视为整体,而难以分辨人类社会及各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冲突。环境史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往往忽视社会分层和权力关系,与整体论的影响不无关系。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问世的一些著作,诸如《自然与美国人》、《美国的人与自然》,虽然冠以美国人的标题,但这些作品中的美国人实际上是指白人男性。(51)在承认整体论影响环境史研究的同时,也不应过分夸大其影响。实际上,许多环境史学者对社会分层有明确的认识,其作品中并不乏平民百姓,但他们有意淡化社会差异,乃是因为他们要保持环境史研究的特色。沃斯特说,当年写作《尘暴》一书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大平原地区存在的社会差异,同样的灾难对不同的人群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他并未给予种族和文化过多的关注,以免分散对生态和经济等基本问题的注意力。(52)
其次,文化转向也有利于环境史摆脱环境保护主义的消极影响。环境史是环保运动的产儿,这个领域的许多先驱,比如纳什(Roderick Nash)、奥佩(John Opie)、福莱德(Susan Flader)、麦茜特、克罗农等人都是著名的环保人士。“绝大多数环境史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环保主义者”,认同环境保护主义的基本主张,环境史也因而打上了环境保护主义的深深烙印。(53)其一,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专业刊物《环境评论》将教育公众作为其办刊的宗旨之一,以扩大环境保护主义的影响,这种取向损害了刊物的学术性。其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主流环保运动“白人精英主义取向”的影响,环境史重视对荒野的研究而忽视对城市弱势群体的研究。而激进环保主义将环保与文明对立起来的倾向,在环境史领域也有所体现。其三,环境史往往采用三部曲的“衰败论”叙事结构:原本丰饶的自然资源,在白人开发和破坏之后,变得日益稀缺贫瘠。(54)在80年代中后期,民间环保人士因为觉得在美国环境史学会难有作为而相继退出,从而削弱了环境保护主义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环境评论》更名为《环境史评论》之后,随着刊物制度建设的加强,学术质量稳步提高。从90年代以来,早期环境史著述中经常出现的“环境破坏”等字眼已逐渐被“环境变迁”所取代,人类也不再只是以“自然的破坏者”的面目出现,早期环境史著述中的悲观情绪也明显减少,一批振奋人心的环境史著作相继问世。还有学者认为,环境史三部曲的传统叙事结构——“丰饶、破坏、贫瘠”——并不完整,还应该加入“修复”这一环节。(55)文化转向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影响,有利于环境史被学界和公众广泛接受。
再次,文化转向使环境史“自下而上”的视角不仅深入地球本身,而且更加贴近平民百姓。这样一种新的视角,使环境史研究能另辟蹊径,推陈出新。环保运动史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但社会文化分析却为重新撰写美国环保运动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在以往的著述中,资源保护主义者总被认为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他们着眼于美国长远的公共利益,破除地方阻力,在美国中西部推行资源保护。90年代以来,一些环境史学者采用阶级分析和种族分析方法,却对这段历史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沃伦(Louis S.Warren)在《猎手的游戏》一书中指出,资源保护主义者经常运用自己的权势,剥夺当地人民的财产,而且强迫当地人民接受有损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而雅各比(Karl Jacoby)在《破坏自然的罪行》一书中则认为,资源保护主义者运用他们所能掌握的司法力量,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56)卡顿德(Ted Cattonde)、斯彭斯(Mark Spence)的作品讲述了印第安人在国家公园建立过程中被剥夺土地的悲惨经历。这两本著作都表明,尽管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原住民,但掌握话语权的权势集团却把印第安人的家园定义为荒野,以便为驱逐印第安人寻找依据。这些著作使人们对资源保护运动有了全新的认识。另外,通过采用种族、阶级和性别研究方法,环保运动被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时期,而不再被认为兴起于二战以后,其原因也比塞缪尔·海斯所说的追求“生活质量”远为复杂。由于文化分析的应用,环境正义运动的历史有望被改写。
复次,文化转向为环境史研究挖掘出了大量的新资料,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课题。由于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旧史料又有了新的价值,过去很少利用的史料也被大量发掘出来,为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创造了条件。不妨以劳工环境史为例。美国劳工运动历史悠久,劳工史料比比皆是。比如,位于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韦恩州立大学就藏有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卡车司机工会、美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国际产业工人协会等系列档案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会议纪要、演讲稿、劳工通讯、报纸期刊剪报等正式文件,而且还包括手稿、日记、回忆录、访谈、个人通信等个人资料。这些浩如烟海的珍贵史料,目前还很少为环境史学者所问津。这些史料的挖掘,将为劳工环境史研究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可以用来梳理劳工参与环保运动的历程,阐述劳工领袖对环保运动的贡献,比较不同劳工组织对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拓展和深化对劳工与环境问题的研究。(57)
最后,文化转向有利于增强史学界对环境史的认同,使该领域从史学的边缘逐渐向主流靠拢。克罗斯比的经历实际上可以反映史学界对环境史态度的变化。克罗斯比以其关于哥伦布交换的研究而誉满天下,但他的这一作品在70年代被认为稀奇古怪而难以出版,他在历史系也谋不到教职。克罗斯比在历史系所受的冷遇,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环境史以前在史学界所受的排斥。直到1986年《生态帝国主义》出版后,克罗斯比才开始到历史系工作。在90年代之前,环境史常常难以为外界所理解和接受。但到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环境史在美国史学界已经颇具声势。迄今为止,四本环境史著作荣获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已有五位环境史学家当选为国家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其中两人分别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AH)和美国历史学会(AHA)的主席。《环境史》的引用率在美国史学杂志中排名第三,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哥伦布大交换”已经成为大学世界史教材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而大多数美国史教材至少也会提到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和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近年来,甚至连一些保守的高校历史系也开始聘用环境史学者。环境史当前在美国史学界的影响,也许可以从美国史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美国历史学会的2012年年会窥见一斑。该年会的主题“生命、地方和故事”与环境史直接相关,而获得2012年度历史学终身成就奖的三位学者中,包括克罗斯比和沃斯特两位环境史学者。而2013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六位主席团成员中,包括克罗农和约翰·麦克尼尔这两位环境史学者。考虑到文化转向所带来的繁荣,也许不必对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过于担心。怀特指出,“那种认为文化转向会导致环境史偏离自然这一核心而变得越来越抽象和虚无的看法,实际上是非常滑稽的”,正如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不可能完全客观一样,非人类世界也不可能在文化中消失。(58)
文化转向造就了当前环境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它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和社会差异,削弱了生态和经济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弱化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加剧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
文化转向削弱了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及跨学科研究的特色。环境史将自然引入历史,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自然因素,包括空气、水源、土地、各种生物、自然资源和能源,都能发挥作用。环境史重视各种自然因素的作用,而不是把自然仅作为人类历史的背景。环境史学者如果过多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因素及这些因素背后的权力关系,那么环境史的特点就不复存在。(59)正如侯文蕙教授所担忧的,“环境史若是把它的研究中心放在族群、人种和性别方面……那环境史将何以复存?”(60)安德鲁·赫尔利指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虽然可以帮助环境史成为主流,但若因此而使环境史的特色丧失殆尽,将得不偿失。(61)文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为哲学基础,对科学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削弱科学在环境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文化转向导致了环境史与科学的疏远和隔离,削弱了环境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紧密联系。
文化转向还导致了环境史研究的碎化。环境史学者通过运用种族、阶级、性别等分析工具,使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但由于往往将种族、阶级、性别因素孤立开来,而不是置于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复杂网络之中,因此很难对这些社会分层因素的影响做出全面准确的估计。同时,微观研究常常因为缺乏广阔的历史视野和一定的理论关照,而难以通过局部或个案研究体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克罗斯比认为应该更关注“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那些层面”,他和沃斯特都认为,“如果我们太拘泥于细节”,而忽略了“自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帝国主义的影响、地球的命运”等重大问题,环境史著作就不会给“关心这些重大问题的公众提供多大帮助”。(62)如此一来,环境史的魅力就会削弱,离社会公众越来越远。
文化转向可能会给环境史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或许可从克罗农的《关于荒野的困惑》一文所引起的激烈反应窥见一斑。该文将荒野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对美国环保运动过分重视荒野、忽略底层民众的利益这一不足进行了反思。克罗农写作此文时既是知名的环境史学者,又是活跃的民间环保人士,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荒野协会等著名环保组织还担任一定的职务。在一定程度上,克罗农是从一个热爱环保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面对环保运动所遭遇的一些现实困境,抱着促进环保运动的初衷,来写这篇文章和主编《各抒己见》这本论文集的。长期以来,荒野一直被环保主义者视为神圣崇高和个人自由的代名词,保护荒野成为环保运动的内在精神动力。由于荒野总是被等同于无人的区域,人类的利益在环保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环保主义者那里处于次要地位。主流环保运动坚持生态中心、忽视社会公正的整体倾向,激进环保主义反人类、反文明的立场,削弱了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从而助长了反环保势力的抬头。克罗农撰写此文,其主旨就是要批判这种错误但却非常流行的自然观念,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矛盾,扩大环保运动的社会基础。克罗农力图瓦解荒野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以人们身边、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家园取而代之,从而使环保能朝“既可持续又人性化”的方向发展。(63)克罗农没有想到的是,此文的发表得到了反环保势力的欢呼,而招致了部分环保主义者和环境史学者的强烈谴责。《关于荒野的困惑》一文在《环境史》杂志发表之时,在同一期杂志上还登载了三篇由知名学者所写的评论文章,其中两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塞缪尔·海斯提出,克罗农对荒野的建构,是脱离环保运动实际的冥思苦想,带有强烈的个人和社会情绪。(64)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则认为,应把福柯作为文本加以解构,抑制后现代主义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如果我们采用福柯的社会建构,我们最终可能不得不放弃环境史本身”。(65)克罗农在同一期发表了回应文章,对被触怒的读者表示歉意,并提到,“该文若被用来反对荒野保护,我会深感后悔”。(66)克罗农的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强烈反响,(67)或许可以促使环境史学者冷静思考:文化转向可能会把环境史带往何方?
正是基于文化转向对环境史研究的不利影响,以沃斯特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文化转向一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对种族和文化的过多关注,分散了环境史学家对生态和经济等根本因素的注意力。而如果不将“进化、经济和生态”置于其研究中心,忽略自然及其影响,环境史领域就不可能提出独特的创见。沃斯特的上述主张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实际上,他的每本书里都有许多小人物的身影,带有悲天悯人的浓厚气息,他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同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但是,他坚持认为,以自然为中心是环境史研究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方向,舍此就会损害环境史学科的长远发展。(68)
沃斯特对文化转向的担忧,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文化分析或轻视文化因素。他在第一本专著《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就把生态学思想视为社会文化建构加以阐述。在他看来,生态学并非“一种独立的客观真理”,可以独立于文化之外如实反映自然本身,生态学的发展一直“与内涵更为丰富的文化变革相联系”,生态学是“由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理由,按照不同的方式定义的”。(69)而《尘暴》一书则将尘暴重灾区的形成主要归咎于资本主义文化。在《自然的财富》一书里,沃斯特以“反对唯物论的唯物主义者”来概括他的哲学立场,他说:“我希望引导人们注意自然世界的物质现实”,“但仅从物质层面加以解释也不够,自然的文化史和文化的生态史是同样重要的”。(70)沃斯特的这些论断也适用于他对文化转向的批评,这种批评不是要对其加以否定,而只是强调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因为片面强调文化层面而忽视从生态和经济层面探讨环境变迁。在沃斯特的研究中,资本主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但资本主义既被他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又被视为一种思想文化,他总是从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开展环境史研究。
相对于美国环境史学者对文化转向的热衷而言,欧洲同行显得比较冷静。这可以从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专业刊物《环境与历史》上反映出来。在1996-2007年间,标题含“种族”、“族裔”、“阶级”、“性别”等任何一个词的文章,在《环境与历史》上仅为3篇,而在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专业期刊《环境史》上则达到了35篇,其中包括论文14篇,书评21篇。(71)欧洲学者对文化转向的默然,与他们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欧洲资深的环境史学者大多有自然科学的专业背景,而且也不在历史系工作。欧洲的环境史学者往往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坚持以研究生态变迁为中心,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大量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欧洲环境史研究的这种风格,受到了一些美国学者的称赞,对坚守生态分析的那些学者也是一种鼓舞。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南希·兰斯顿(Nancy Langston)、埃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亚当·罗姆(Adam Rome),实际上依然一如既往地坚守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分析模式,并逐渐成为美国环境史领域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也融入了文化分析。麦克尼尔在《太阳下的新事物》中就指出,“环境变化通常总是对有些人有利而不利于另外一些人”,在对环境变化的好坏进行评价时,就不能不依据“将谁的利益置于其他人之上”,麦克尼尔在书中就多次谈到了发展对不同人群的截然不同的影响。(72)兰斯顿关于马卢尔保护区(Malheur Refuge)的那本著作,就是从不同人群关于该地的记忆和故事讲起的。而亚当·罗姆在探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的环境改革和战后环保运动时就直接运用了性别分析。(73)文化分析实际上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史研究,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继文化转向之后,美国环境史研究在未来或许又会出现一种新转向。这种新转向也许将是环境史的“科学转向”或“生态转向”的重新开始,以矫正文化转向过犹不及的消极影响。这一转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为进化和协同进化(coevolution)研究热的兴起。埃德蒙德·拉塞尔作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强调人类作为影响其他物种进化的重要力量,突出人为进化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重视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相互适应而共同进化。(74)拉塞尔以其在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而声誉鹊起,在2013年加盟堪萨斯大学,接替沃斯特担任该校的霍尔杰出讲席教授。进化研究热将有力推动生态分析在环境史领域的复兴。
四、结论
近20年来,在以克罗农、怀特、戈特利布和赫尔利为首的一批学者的推动下,文化转向已经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最明显的趋势之一,社会文化分析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在这种新的范式下,自然既被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又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自然与文化的边界非常模糊;自然是变动不居的,而非稳定有序的。与此同时,种族、阶级和性别分析被广泛应用于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加快了与社会史融合的步伐。
文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它受到了一些质疑,但仍然得到了环境史学界的普遍认可,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环境史的文化转向,既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现实的变化,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发展,又体现了新文化史对整个史学领域的冲击和影响。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可以折射出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揭示环境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种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环境问题既然与社会问题紧密相连,环境史就不能脱离社会史,不能脱离社会分层和权力关系而抽象地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
文化转向虽然削弱了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的研究特色,但它在整体上仍然有利于环境史的发展,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与生态分析范式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其一,它们都将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反对将两者进行二元区分;其二,它们都承认思想文化的作用,只是对影响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其三,它们都致力于推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是价值取向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各有侧重,它们都反对极端的价值取向。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两大范式,文化分析和生态分析侧重于环境史研究的不同层面。实际上,这两种分析模式从环境史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只是在90年代以前,生态分析模式主导了美国的环境史研究。(75)近年来,文化分析蔚为大观,或许可以视为对生态分析模式的一种矫正或平衡。实际上,文化分析和生态分析各有利弊,彼此可以取长补短,在具体研究中应协调配合使用,而不要顾此失彼,更没必要将二者对立起来。生态分析和文化分析或许将成为环境史的两翼,彼此协调,从而促进环境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两位匿名审稿人以及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马克·赫西(Mark Hersey)、俞金尧、孙群郎、侯深等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R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Historian,vol.66,no.3(September 2004).
②在美国学者中,只有理查德·怀特曾就此撰文,但比较简略;英国学者彼特·科茨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趋势。参见Peter Coates,"Emerging from the Wilderness(or,from Redwoods to Bananas):Rec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America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10,no.4(Nov.2004),pp.412-416.国内迄今尚无相关论述,但有学者注意到环境史与社会史存在关联。(参见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页;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5—151页;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44页)
③R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558.
④Donald Worster,"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p.1087-1106.
⑤William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p.1124-1129; Richard White,"Environmental History,Ecology,and Meaning,"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1113.
⑥Carolyn Merchant,"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p.1117-1121.
⑦Donald Worster,"Seeing beyond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6,no.4(March 1990),p.1144.
⑧“生态分析学派”和“文化分析学派”是笔者所归纳的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两种主要流派,实际上并没有美国学者做这种区分,但在环境史的有关著述中“环境分析”、“生态分析”、“文化分析”等术语并不罕见。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同于传统的“环境思想史”,主要在于采用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分析工具。在沃斯特看来,这一新动向的准确表达应为多元文化转向而非文化转向。(Mark Harvey,"Interview:Donald Worster,"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3,no.1(Jan.2008),p.145)
⑨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New York:W.W.Norton,1991,pp.xvi-xvii.
⑩William Cronon,"A Place for Stories:Nature,History,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78,no.4(Mar.1992),pp.1347-1376.
(11)Donald Worster,Dust Bowl: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aul Bonnifield,The Dust Bowl:Men,Dirt,and Depression,Albuquerque,NM.: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79.这两本著作的叙事风格和结论截然不同:沃斯特将尘暴重灾区的形成视为逐利的资本主义文化所导致的人为的生态灾难,当地人民既是灾难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而博尼菲尔德则将大平原地区的这段经历视为人类战胜自然灾难的英雄史诗。
(12)William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ol.17,no.3(Fall 1993),pp.2-22.“衰败论”的主要观点是: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恶化。早期环境史作品多以生态灾难为主题,或多或少存在“衰败论”的倾向,其中尤以沃斯特的《尘暴》一书最为典型。
(13)William Cronon,ed.,Uncommon Ground: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5,pp.69-90.
(14)Richard White,"'Are You an Environmentalist or Do You Work for a Living?':Work and Nature," in William Cronon,ed.,Uncommon Ground: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pp.171-183.
(15)Robert Gottlieb,Forcing the Spr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2,p.9.
(16)Andrew Hurley,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Class,Race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Gary,Indiana,1945-1980,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5,Preface,p.xiii.
(17)高国荣:《关注城市与环境的公共史学家:安德鲁·赫尔利教授访谈录》,《北大史学》第1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8)在1996年之前,《环境评论》和《环境史评论》上刊登的标题中含有“印第安人”的论文和书评共计9篇,但标题含“非裔”、“拉美裔”和“亚裔”上述三词任意一个的论文和书评却只有1篇。从1996年以后,这一局面明显改变,从1996-2009年,标题中含“印第安人”的论文和书评共计6篇,但标题含“非裔”、“拉美裔”和“亚裔”上述三词任意一个的论文和书评已达到7篇,其中5篇与黑人有关。相关数据为笔者于2013年1月20日检索JSTOR数据库所得。
(19)Dianne D.Glave and Mark Stoll,eds.,"To Love the Wind and the Rain":African American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p.6.
(20)Gunther Peck,"The Nature of Labor:Fault Lines and Common Ground in Environmental and Labor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1,no.2(April 2006),p.215.
(21)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Malden,Mass.:Blackwell,2010,p.149.
(22)Virginia Scharff,"Are Earth Girls Easy?:Ecofeminism,Women's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vol.7,no.2(Summer 1995),pp.165-170.
(23)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p.117.
(24)Alan Taylor,"Unnatural Inequalitie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no.4(Oct.1996),pp.8-16.艾伦·泰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社会史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作品曾获班克罗夫特奖和普利策奖。
(25)Stephen Mosley,"Common Ground:Integrating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39,no.3(Spring 2006),p.920.
(26)相关数据为笔者于2013年1月10-15日检索JSTOR数据库和Oxford Journals数据库所得。检索词分别为:种族(race)、阶级(class)、性别(gender or women,female.feminist)。
(27)Richard White,"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4,no.3(Aug.1985),pp.334-335.
(28)Richard White,"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70,no.1(Feb.2001),pp.108-109.
(29)Hal Rothman,"Conceptualizing the Real: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vol.54,no.3(Sep.2002),pp.493-496.
(30)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46页。
(31)Martin V.Melosi,"Equity,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ol.19,no.3(Autumn 1995),p.14.
(32)Carolyn Merchant,"Shades of Darkness:Rac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8,no.3(July 2003),p.381.
(33)Martin V.Melosi,"Equity,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p.3.美国环境史学会学术研讨会于1982年首次举行,从1987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从2000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
(34)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120 edit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0,p.12,Table 11;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Social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Bureau of the Census,Hispanic Americans Today,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3,pp.2-6.
(35)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00,NCES2000-034,Washington,D.C.,2001,p.20,Table 17.
(36)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1981(102 edition),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1,p.159,Table 267.
(37)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00,NCES2000-034,p.315,Table 208.
(38)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1996,NCES 96-304,Washington,D.C.,1997,p.52.
(39)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40)Vera Norwood,Made from This Earth:American Women and Natur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 Virginia Scharff,Seeing Nature through Gende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3; Glenda Riley,Women and Nature:Saving the "Wild" Wes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41)Kimberly K.Smith,Afric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Thought:Foundations,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7.
(42)林·亨特:《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3)"Social History Tops Members' Interests," OAH Newsletter,vol.31,no.4(November 2003),p.18会员登记表列出了51个史学专业领域,会员从中圈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最多不超过5个。该图表的文字说明没有单独列出将环境史作为专业领域的具体人数。
(44)Richard White,"Environmental History: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 p.104.
(45)王晴佳:《新史学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46)Donald Worster,"The Ecology of Order and Chaos," in Char Miller and Hal Rothman,eds.,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Pittsburgh,PA: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7,p.5.
(47)Thomas R.Cox,"A Tale of Two Journals:Fifty Year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ts Predecessors,"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3,no.1(January 2008),pp.23-24.
(48)Donald Worster,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reface,p.ix.
(49)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50)John Opie,"Environmental History: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in Kendall E.Bailes,ed.,Environmental History: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27.
(51)Hans Huth,Nature and the American:Three Centuries of Changing Attitude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57; Arthur A.Ekirch,Jr.,Man and Nature in Americ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52)Donald Worster,Dust Bowl: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p.247.
(53)William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2-22.
(54)Alan Taylor,"'Wasty Ways':Stories of Americ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3,no.3(July 1998),p.292.
(55)Marcus Hall,"Repairing Mountains:Restoration,Ecology,and Wilder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Utah,"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6,no.4(Oct.2001),p.584.
(56)Louis S.Warren,The Hunter's Game:Poachers and Conservationists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Karl Jacoby,Crimes Against Nature:Squatters,Poachers,Thieves,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57)Chad Montrie,"Class," in 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156-159.
(58)Richard White,"From Wilderness to Hybrid Landscapes:The Cultural Tur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564.
(59)Ellen Stroud,"Does Nature Always Matter? Following Dirt through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2003),p.76.
(60)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61)高国荣:《关注城市与环境的公共史学家:安德鲁·赫尔利教授访谈录》,《北大史学》第17辑。
(62)Donald Worster,"Seeing beyond Culture," p.1143.
(63)William Cronon,ed.,Uncommon Ground: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p.26.
(64)Samuel P.Hays,"The Trouble with Bill Cronon's wilderness,"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no.1(Jan.1996),p.30.
(65)Michael P.Cohen,"Resistance to Wilderness,"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no.1(Jan.1996),p.34.
(66)William Cronon,"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A Response,"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no.1(Jan.1996),p.47.
(67)有关这篇文章的更多争论,还可以参考Char Miller,"An Open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54,no.3(Aug.1985),pp.72-74.实际上,克罗农本人并不认可海斯和科恩的批评意见,他认为,对环保运动和环境史的不断反省和自我批判,尽管非常艰难,但有利于环保运动和环境史的长远发展。时至今日,更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接受克罗农的观点。
(68)Mark Harvey,"Interview:Donald Worster," p.145.
(69)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10、14页。
(70)Donald Worster,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Preface,p.ix.
(71)相关数据为笔者于2013年1月18日检索JSTOR数据库所得。
(72)John McNeill,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New York:Norton,2000,Preface,p.xxv.
(73)Nancy Langston,Where Land and Water Meet:A Western Landscape Transformed,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3; Adam Rome,"'Give Earth a Chance':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Sixtie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90,no.2(Sep.2003),pp.525-554; Adam Rome,"'Political Hermaphrodites':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 in Progressive America," Environmental History,vol.11,no.3(July 2006),pp.440-463.
(74)Edmund Russell,Evolutionary History:Uniting History and Biology to Understand Life on Ear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p.2-3.
(75)Douglas Cazaux Sackman,ed.,A Companion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Introduction,p.x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