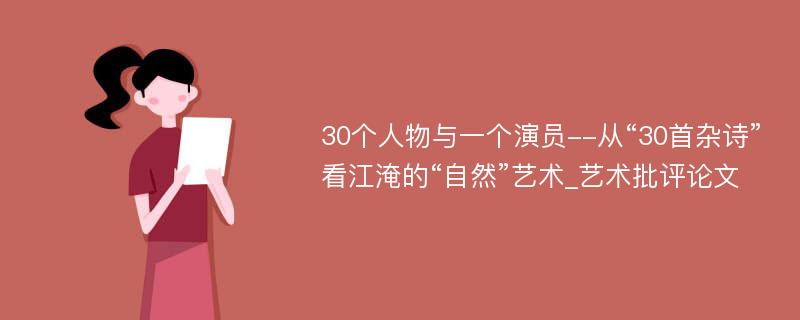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色论文,演员论文,角色论文,艺术论文,杂体诗三十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1-0001-10
一、《杂体诗三十首》的双重属性
在多个意义上,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都可以说是“多”与“一”的对立统一体。首先,从命题方式来看,《杂体诗三十首》是其总题,笼罩众篇,而其下的三十首诗又自有标题,各自独立。其次,从结构形式来看,正如诗题中之“杂”字所示,这三十篇诗作主题不同,风格各异,但这些诗篇又是按照时代的顺序和诗史的逻辑,排列组合为一个整体,脉络清楚,目的明确。具体说来,江淹有意通过对历史上30家五言诗人的选择和模拟,来表达个人对五言诗史的“品藻”观点,并与当时论家展开“商榷”。这也就是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所说的:“五言之兴,谅非夐古。但关西邺下,即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敩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①再次,从生成方式来看,尽管这组诗所拟学的对象,包括从两汉到南朝的三十家诗人,其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多年,而其模拟者从头到尾却只有一个江淹。如果把每一篇拟学比喻作一次对古人角色的扮演,那么,《杂体诗三十首》就有如三十个角色,而其演员却只有江淹一个人。要之,《杂体诗三十首》是特殊的组诗,总杂而一致,江淹是贯穿众“多”角色客体中的惟“一”演员主体。
明确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杂体诗三十首》很有意义。例如,曾经有学者认为:“萧统将《杂体诗三十首》全部录入《文选》,占入选江诗的绝大部分,可见对其艺术是深为首肯的。”②确实,《文选》一书选录了不少组诗,就入选总数而言,《杂体诗三十首》亦是首屈一指。阮籍五言《咏怀诗》82篇,其总篇数是《杂体诗三十首》的一倍多,但《文选》卷23只选录17首,入选比例只有大约21%,比江淹这组诗的100%低多了。这一现象似乎可以说明《文选》编者对《杂体诗三十首》情有独钟。但是,实质上,这是因为《杂体诗三十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若有所取舍,必然陷于鲁莽灭裂,有负江淹“品藻渊流”之苦心,影响对其五言诗史观的理解。换句话说,《文选》编者此举隐含着对这三十首诗的整体性的强调。最近几年,有不少论文以《杂体诗三十首》为据,研究江淹的文学观点③,其暗含的前提亦是对这种整体性的承认与关注。
总之,《杂体诗三十首》具有诗歌创作和诗史批评的两种属性。作为诗史批评,江淹的选择和模拟都受到既往诗史的限制,不能自由发挥。作为诗歌创作,即使是拟古诗,也势必体现拟者亦即“演员”的主体性,有意无意地呈现作者的艺术个性。以往我们似乎过于强调这组诗作为拟古诗的被动属性,而忽略其作为江淹创作的主动属性,而江淹作为创作者的主体身份,也同时被淡化了。
二、《杂体诗三十首》中的所谓“芜词累句”
从创作角度研究《杂体诗三十首》,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观点将其作为江淹的代表作,认为它体现了江淹“善于摹拟”的特点,以南朝钟嵘、宋人严羽、清人施补华为代表。钟嵘《诗品》最早提出这样的看法:“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所谓“诗体总杂”,《杂体诗三十首》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亦称“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独拟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汉耳”④。显然,严羽赞同钟嵘的看法。施补华对江淹拟古的评价更高:“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杂拟三十首,尤可为后人拟古之法。”⑤另一种看法虽然承认江淹拟古颇有功力,却批评这类诗没有个性面目,终非本色,以元人陈绎曾、清人潘德舆、刘熙载等人为代表。陈绎曾认为江淹虽然“善观古作,曲尽心手之妙”,但毕竟依附古人,不能“自立”⑥。潘德舆也对江淹虽有“一世隽才”,却不能“自抒怀抱,乃为赝古之作”而感到遗憾⑦。刘熙载则批评江文通诗“虽长于摹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⑧。
双方褒贬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充分肯定江淹拟古之“似”与“肖”⑨。这是《杂体诗三十首》评价中的主流观点,其声音之宏亮,影响之深远,致使一些非主流的尖锐批评被掩盖,甚至被屏蔽。在非主流的批评中,清代诗人兼文选学家汪师韩的说法听来格外刺耳。在《诗学纂闻》中,汪师韩批评“江文通《杂拟》三十首,自谓无乖商榷。后人每效为之。观其词句多有可议”;“三十首中,芜词累句居其半”⑩。换句话说,江淹拟古非但未必全似古人,而且多有瑕疵。汪师韩指摘江淹这一组诗存在23处诗病,其举证涉及30首诗中的16首。在我看来,虽然汪师韩的举证并未穷尽江诗所存在的问题,但其评语大多一箭中的,并非虚诬苛责,哗众取宠,很值得我们重视。至于这些例证中究竟有何意涵,更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从现象上看,这些诗病基本上属于技法层面,尤其集中在字法和句法方面,可以概括为凑韵趁韵、词意晦涩、词语生造等三大类。下面就按照这个顺序,将汪师韩所举例证分类排列如下(11):
第一,凑韵趁韵之例:
1.《陈思王赠友》云:“日夕望青阁”,以青楼为青阁,岂非凑韵?
2.又(《陈思王赠友》)云:“辞义丽金雘。”易金玉为金雘,亦凑韵也。
3.《刘文学感遇》云:“橘柚在南国,因君为羽翼。”以羽翼说树,为就韵故耳。
4.又(《孙廷尉杂述》)云:“传火乃薪草。”用《庄子》为薪火传之语,而草字凑韵。
5.《陶征君田居》云:“稚子候檐隙。”易候门为候檐隙,语病。
6.《谢临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晰。”初晰即初阳之谓,故以对晨霞,然无解于趁韵。
第二,词意晦涩之例:
1.《魏文帝游宴》云:“渊鱼犹伏蒲。”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易出听为伏蒲则意晦。
2.《王侍中怀德》云:“严风吹若茎。”《文选注》以若茎为若木,斯可笑矣。然如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尔也。
3.《嵇中散言志》云:“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下句不知其指。
4.《张黄门苦雨》云:“水鹳巢层甍。”注云:“巢层甍未详。”按:此不过谓水鸟入居人屋,不必有本也,而词则支缀。
5.又(《谢光禄郊游》)云:“烟驾可辞金。”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羡也。然词拙而晦。
第三,词语生造之例:
1.《潘黄门述哀》云:“徘徊泣松铭。”松是松楸,铭是志铭,二字相连,则词不贯。
2.《郭弘农游仙》云:“隐沦驻精魄”,此用《江赋》:“纳隐沦之列真,挺异人之精魄。”即郭璞语也。合作一句则乖隔。
3.又(《郭弘农游仙》)云:“矫掌望烟客。”烟客二字,后人爱其鲜新,当时则生造矣。
4.《孙廷尉杂述》云:“凭轩咏尧老。”尧及老子也,然不伦矣。
5.又(《孙廷尉杂述》)云:“南山有绮皓。”绮里季特四皓之一,何独摘举?
6.《颜特进侍宴》云:“瑶光正神县”,赤县、神州,岂可摘取神县二字。
7.又(《颜特进侍宴》)云:“山云备卿霭,池卉具灵变。”因改灵芝为灵变,遂并卿云亦改卿霭。
8.又(《颜特进侍宴》)云:“巡华过盈瑱。”以盈尺之玉为盈瑱,用对兼金,拙劣。
9.《谢法曹赠别》云:“觌子杳未僝,款睇在何辰?”意本浅而故为拙滞。
10.《王征君养疾》云:“水碧验未黜,金膏灵讵缁?”未黜、讵缁,拙滞。
11.《袁太尉从驾》云:“云旆象汉徙。”汉徙谓如天汉之转,亦支缀矣。
12.《谢光禄郊游》云:“徙乐逗江阴”,乐者行乐也,加徙字则拙。(12)
需要说明的是:分作这样三类主要是出于论析的方便。尽管汪师韩举证时已经点明某一例子的问题类型,但实际上,这三类往往彼此联系,密不可分。例如,汪师韩举为趁韵之例的“初晰”一词,其实就是江淹生造之词,故亦有生涩之嫌。又如,“伏蒲”(今本多作“伏浦”)一词之所以“意晦”,也是因为江淹生造此词,自我作古。再如,将商山四皓中的绮里季特别挑出来,拼合成“绮皓”,恐怕也不无趁韵的嫌疑。如果没有前文“南山”的引导,读者理解此句恐怕也有困难。
趁韵、凑韵之病的诗病,通常应该是浅学所犯,江淹这样的诗文高手为什么也会蹈此覆辙呢?对江淹来说,押韵并不是一件难事,何况诗中所选多非险窄之韵。以“南山有绮皓”一句为例,写作“商山有四皓”即可谐韵。问题是这种平易的句法不符合江淹追求用字奇崛生涩的修辞习惯。因此,他不惜将常见的“商山”改为不经见的“南山”,又通过词语的剪裁拼合,锻造出“绮皓”这一新词。好为雕琢锻造,这一作风贯穿于江淹各体文章创作之中,可说是江淹诗文的重要特色。前人早有论及,如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江醴陵集题辞》称江淹“诗文新丽顿挫”(13),毛先舒《诗辩坻》卷2称“江郎流丽中带蹇涩”(14)。所谓“顿挫”,即指其用笔雕炼,时涉蹇涩。许裢《六朝文絮》卷1更具体指江淹《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琢采秀削,别开奥窒。昔人讥其句句生涩,余谓醴陵佳处,即在生涩上”(15)。至于如《别赋》中“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恨赋》中“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之类的雕琢例子,更是众所皆知,不必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日积月累,这种手法已经成为江淹创作的积习,即使在拟古这种“有限制的写作”(16)活动中,他也不自觉地露出习惯性的动作。因此,汪师韩所举各例,与其说是“多有可议”的“芜词累句”,不如说是江淹在拟古中情不自禁的本色表现。在“角色扮演”中,他不经意地流露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由此联想到清人孙月峰对《杂体诗三十首》的批评。孙氏谓《班婕妤咏扇》“比班稍着色相”;谓《陈思王赠友》“较陈思不甚似,彼气雄,此骨秀;彼素质,此铅华”;谓《刘文学感遇》“刘以质率胜,此稍作意”(17);诸如此类的例子甚多,实质上正体现了江淹在字词琢磨方面的着力与着意,体现了江淹字词修辞的“本色”。
三、字法、词法及句法中的江淹特色
客观地说,琢字造语并非绝不可为,关键在于把握好分寸。恰到好处者,足以使人“爱其鲜新”,稍有过失者,则不免让人产生“生造”、“乖隔”、语词“不贯”的感觉。江淹老于琢字造语,手法往往相当高明。如《休上人别怨》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句,即是琢字成功之例。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2将此句与魏文帝诗句“朝与佳人期,日久殊未来”以及谢灵运诗句“园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相比较,充分肯定江淹后来居上,“愈衍愈工巧”,并且认为,从这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魏、宋、梁体自别”(18)。
窃以为,“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不仅反映了梁朝的风格,其琢字造句更体现了江淹的个人特色。“合”是江淹诗赋中常用的字眼,略举数例为证:
再逢绿草合,重见翠云生。(《从建平王游纪南城》)
岁采合云光,平原秋色来。(《岁铜雀台》)
玄云合而为冻,黄烟起而成雪。(《思北归赋》)
见红草之交生,眺碧树之四合。(《江上之山赋》)
在江淹之前,古典文献中虽然也有“雷动云合”、“云合景从”、“义兵云合”之类的词语,但都是在比喻意义上使用,并不着力于物色的描摹。惟独一篇古乐府中有“黄云暮四合,高鸟各分飞”的句子,笔法与江淹诗相近(19),而琢字造句之功力,却与江淹相去甚远。“日暮碧云合”一句带有明显的江淹特色,只是因为休上人与江淹年代相近,亦有近于“梁体”的特点,故后人对此句没有异议,甚至长时间误认为惠休之秀句而加以吟咏发挥(20)。
模拟年代较近的诗人,并不一定就比年代较远的诗人容易。年代久远,诗人诗作经过历史淘汰,其风格特点亦往往已有定评,较易凝聚共识。故江淹模拟汉魏晋诸家,只须化用前人词句,或者借用前人意象,有所依傍,突出甚至放大其特点(21),即可在形貌上逼肖原作。年代较近,对其人自然更加亲切熟悉,对其诗个性的把握却可能各持一端,难臻一致。《杂体诗三十首》中,自《袁太尉从驾》以下四家,与江淹年代相近。江淹对其个性的彰显似有不足,甚至让人有四篇如出一手的强烈感觉。大体上,所模拟的诗家年代越近,江淹个人的面目就越是突出。清人方伯海曾高度评价《颜特进侍宴》一篇,以为“上半矞皇典重,得颜作之瑜,下半晦涩滞闷,得颜作之瑕”(22)。模拟之中不择瑕瑜,一一肖之,似乎形神兼备,已臻极致。实际上,此篇中生涩词句特多,不似颜氏之雍雅典重,直是江氏之劲崛蹇涩。例如上半篇的“神县”一词,据《文选》李善注,此词是摘取“神州”、“赤县”二词中各一字捏合而成,意指中国。在江淹之前,此词未见于文献,可以确定是江淹的原创,也突出体现了江淹琢字锻词之法(23)。又如下半篇“巡华过盈瑱”一句,亦颇受后人疵议。“巡华”、“盈瑱”等词语乍看高深莫测,不知所云,其实只是生造之词,并无出典,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之中,才比较容易理解。
在句法方面,《杂体诗三十首》也带着鲜明的江淹特色,即好用虚字构句,好用散文化句法。毛先舒曾批评《孙廷尉杂述》中“浪迹无妍蚩,然后君子道”二句殊欠锤炼,“一经拈出,涉笔可憎”(24)。对这类以虚词串接前后两句的散文化做法,前人多有评说,见仁见智(25)。汉魏诗歌偶有用散文化句式者,然皆一气浑成,句法高古。江淹颇喜用此种句法,其中亦有佳者,如《古离别》“远与君别者,乃至雁门关”,句法不失高古;又如《李都尉从军》中的“而我在万里”,《刘太尉伤乱》中的“虽无六奇术,冀与张韩遇”,《陶征君田居》中的“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而”、“虽”二字联接上下,气势顺畅自然。但也有不太成功者,如《嵇中散言志》“曰余不师训”用在篇首,单纯以发语词足句,颇嫌枯槁。《孙廷尉杂述》中,除毛先舒所举之例外,还有“寂动苟有源,因谓殇子夭”,亦失之粗质。反观江淹其他诗作,在这一方面亦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如《悼室人十首》其四:“驾言出游衍,冀以涤心胸。复值烟雨散,清阴带山浓。”虚字承接,前后照应,句法逶迤多变。又如《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虚字关联而兼流水句法,仍然不失清劲。至于《感春冰遥和谢中书》中的“揽洲之宿莽”与《效阮公诗十五首》之九中的“人道则不然”,则不免疲沓松散。总之,这种句法与其说是江淹拟学古人,不如说乃出于其个性癖好,故其所施不限于拟汉魏诸诗,而广泛用于各代诗家。
以助词尤其是语气助词入诗,较难生色,尽管前人有成功之例,如阮籍《咏怀诗》:“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哉”字在句尾加重咏叹语气,妙手天成。江淹效而仿之,其《效阮公诗十五首》第七:“高阳邈已远,伫立谁语哉?”《休上人怨别》:“西北秋风至,楚客心悠哉!”依仿阮籍之迹明显,但境界高下立判,并不成功。至于句中使用语气助词,则易使句法散缓软沓,往往得不偿失。魏晋诗人已有此类试验,如刘琨《重赠卢谌》即有“吾衰久矣夫,何其不梦周”、“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之句(26),虽然就前后文而言尚称气盛言宜,但终究不足为训,不可轻易效颦。不过,江淹对此似乎情有独钟。其《刘太尉伤乱》中已有“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许征君自序》中有“去矣从所欲”、“至哉操斤客”,《谢仆射游览》亦有“信矣劳物化”,皆失之粗朴。至于其他诗篇,如《步桐岩》云:“客子畏霜雪,忧至竟悠哉!”《就谢主簿宿》诗云:“怅哉心神晚。”《感春冰遥和谢中书》诗云:“此焉空守贞。”又云:“怅哉望佳人。”更不惮屡次为之。当然,其他齐梁诗人亦有以虚字入诗者,如谢朓在其名篇《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即有这样的句子:“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27)但其频率远不及江淹。在上述诸例中,好用语助的句法与其说是阮籍、刘琨、许询、谢混、惠休的共同特点,不如说是江淹句法习惯的潜移默化。
四、语气、口吻、意象及风格中的江淹本色
一首诗的风格呈现,一个诗人的风格形成,取决于很多因素,不仅复杂,而且微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拟古诗中,字词使用或修辞把握方面一个小小的偏差,就会造成风格的背离,导致拟诗与被拟诗之间韵味或意境的明显不同。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很多,语气和口吻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两个。语气指的是以什么样的声气语调来发言,口吻指的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角色来发言。在诗文作品中,这两者都取决于作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因此又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文选》卷20王粲《公宴诗》结尾六句云:“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据李善注,此诗乃王粲侍曹操宴时所作,“贤主人”指魏太祖曹操。考虑到公宴的特殊场合,“贤主人”这个称呼应该说是适当的。《杂体诗三十首》中的《王侍中怀德》,明显受到王粲此篇的影响,特别是诗的后半段:
贤主降嘉赏,金貂服玄缨。侍宴出河曲,飞盖游邺城。朝露竟几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笃惠义,柯叶终不倾。福履既所绥,千载垂令名。
表面上,这里的“贤主”与王粲诗中的“贤主人”一样,都是指魏太祖曹操,但由于江诗以“怀德”为主题,侍宴的背景已淡化,“贤主”的称呼显得亲近有馀,而尊崇不足,难怪清人洪若皋感觉这不大符合王粲的口吻:“仲宣无此响亮,不称圣君,而称贤主,亦无此气骨,令仲宣读之,当自汗颜。”(28)江诗最后四句以君子自比,其口气不仅略显质直,述志之时,也显得太过自信。这其实是江淹代拟发言时语气口吻失当的表现。
无独有偶。《潘黄门述哀》也有与《王侍中怀德》类似的口吻问题。尽管江淹此诗的标目是“述哀”而不是“悼亡”(29),尽管“述哀”所涵盖的题材空间要比“悼亡”大,但江淹此诗乃以潘岳《悼亡诗》三首为模拟对象,是毋庸置疑的。潘诗三首分别从春夏之间、夏秋之间和岁聿云暮三个时间段,通过时间的推移,来表达哀情的深沉与持久(30)。由于《杂体诗三十首》体例的限制,江淹只能写一首,以少总多,不易应对。总体上,江淹善写哀情,其情感体验与笔力堪与潘岳媲美,但是,《潘黄门述哀》所使用的一个称呼,暴露了江淹与潘岳的不同:“美人归重泉,凄怆无终毕。”“美人”一词,今存潘岳集中未见。对于潘岳来说,这至少不是熟悉的常用词,他未必愿意这样称呼亡妻。在《悼亡诗》中,潘岳对亡妻的称呼是更加亲密的“之子”:“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江淹改“之子”为“美人”,这一用词不经意间透露了他个人的称谓习惯。两字之别,意味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
在传统用法中,“美人”一般不是指作者的原配夫人,而是或指歌儿舞女,或是虚化的象征用法。自楚辞开创了中国文学的香草美人传统以来,后一用法更为常见。江淹诗赋中爱用“美人”一词,如《别赋》中的“燕赵歌兮伤美人”,《学梁王兔园赋》中的“美人不见”,《咏美人春游》诗中的“不知谁家子”,皆不出此二义,显然都不是夫妻间的称谓。《潘黄门述哀》中的“美人”之称谓表明,江淹似乎以第三者的旁观身份来发言,忘记自己正在拟学或“扮演”潘岳。此外,这一首诗后半“尔无帝女灵”一句,以“旦为朝云,暮为行雨”的巫山神女比喻潘岳的亡妻,非但比拟不伦,而且完全没有夫妻间应有的那种感觉。它所描写的与其说是潘岳的悲悼,不如说是江淹的哀情。江淹另有《悼室人十首》,恰好可以印证。此诗为悼念其亡妻而作,诗中称亡妻为“佳人”,与江氏习惯的“美人”相近,而与潘岳的“之子”相远。此诗“后二首以神女作衬托,表示哀思和祝愿”(31),与《潘黄门述哀》“尔无帝女灵”相互呼应,更说明江淹虽然披着潘岳的外衣,却在说自己的话。
如果说,语气与口吻关涉到拟古或扮演之中语言使用的身份感和分寸感,那么,拟古诗中意象的择取,就好比戏剧扮演中服装道具的选用,对诗歌风格的影响更加显著,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潘黄门述哀》诗云:“驾言出远山,徘徊泣松铭。”其思路显然源自《悼亡诗》:“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纡轸。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对读之后,可以看出江淹不及潘岳含蓄。不过,在炼字方面,江淹比潘岳用力,故而生造出“松铭”一词,用来指“松下之碑碣”(32)。众所周知,魏晋时代严禁立碑铭,少数达官权贵死后欲立碑,也要经过特许,一般人无缘享受那样的哀荣。潘岳亡妻坟墓之上很可能植有松楸,却不可能有碑碣。自东晋末年以迄南朝,碑禁不止,取代碑而出现的墓志铭在丧葬中使用越来越多,但墓志铭埋在地下,非“松铭”一词所指(33)。江淹颇善碑志文写作,传世文集中尚有《齐故安陆昭王碑》、《豫章文宪王碑》、《太尉王俭碑》等碑文,学潘之时,遂油然联想到墓上的碑碣。但是,即使在江淹之时,有资格立碑的也只是勋贵名臣,而非一般平民百姓。总之,以“徘徊泣松铭”描写潘岳在亡妻墓上的形象,纯粹出自南朝人江淹的想像,西晋人潘岳是不会这么写的。只能说“松铭”一句是画蛇添足。
刘祯《赠从弟》一题共三首,其第二首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此诗主题出自《论语·子罕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江淹拟刘祯一篇,选择“感遇”为主题,其章法结构则全仿《赠从弟》第二首:
苍苍山中桂,团圆霜露色。霜露一何紧,桂枝生自直。橘柚在南国,因君为羽翼。谬蒙圣主私,托身文墨职。丹采既已过,敢不自雕饰。华月照方池,列坐金殿侧。微臣固受赐,鸿恩良未测。
虽然《赠从弟》三首的主题并不是“感遇”,但是,应该说,以“感遇”来概括刘祯诗歌的主题,还是比较准确的。不过,在内容与形式,或者说形貌与精神两方面,江淹拟诗与刘祯原作有明显的距离。从内容上看,“敢不自雕饰”一句述怀过于直露,而结尾两句的口吻更将抒情主人公的姿态放得太低。从形式上看,刘祯诗中所写的风中劲松,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意象,造成的视觉及心理冲击力都很强。江淹不敢照搬松树意象,而以“山中桂”取代“山上松”。桂之与松,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一物之异,其意涵却大不相同。桂这一意象与楚辞文学传统有着深厚的联系,江淹创作受到这一传统的显著影响,集中有《刘仆射东山集学骚》、《应谢主簿骚体》、《山中楚辞》等作品可以为证。其诗赋作品中亦喜用“桂”的意象,例如:
山中如未夕,无使桂叶伤。(《侍始安王石头》)
桂枝空命折,烟气坐自惊。(《仙阳亭》)
山中有杂桂,玉沥乃人斟。(《惜晚春应刘秘书》)
爱桂枝而不见,怅浮云之离居。(《去故乡赋》)
在江淹的心目中,桂/桂枝是故乡与自我的象征。反观现存刘祯集,桂字未曾出现过一次。江淹以“山中桂”的意象植入《刘文学感遇》,使此诗之口吻及风格皆不类刘祯,而像江淹的自我述怀。
在语气与口吻把握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对古人的理解,这又可分为理解其人与理解其诗两个方面。以诗而论,一位诗人往往有不止一种风格,江淹拟作之时固然可以择善而从,但有时也因为乱花迷眼,莫衷一是,在诗作中闪现其摇摆不定的心态。例如《刘文学感遇》一首,前四句写山中桂枝,至少句调上颇类刘祯原作;第五句到第十句转向写橘柚,与前文没有必然联系。十一、十二两句,似乎又接近刘祯诗的另一个典型主题“公宴”,结尾两句再从公宴过渡到感遇主题,显得杂乱无章。就主题把握和结构安排来说,这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刘祯诗歌有不止一种声音、不止一个主题,都给江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干扰了江淹的表达。
以人而论,既要懂得透,又要说得清,就更为复杂了。咏史为左思诗之突出特色,应该不难理解。江淹拟作《左太冲咏史》,没有把握好以情贯串典实这一核心,颇伤冗散。“左之《咏史》,大抵宾主相形。此作既以卫、霍诸公形容仲蔚,乃复以韩、梅发端,不已赘乎?太冲本诗虽用事错杂,而指趣了然。此则徒仿其体,不复能文从字顺矣。”(34)表面上,这似乎只是理解方面的问题,实质上与表达不精确也有关系。又如刘琨。他矢志扶持晋室,恢复中原,其《重赠卢谌》虽然有“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的嗟叹,但全诗表达的是他不甘失败的顽强意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江淹《刘太尉伤乱》拟作中则云:“功名惜未立,玄鬓已改素”,“时或苟有会,治乱惟冥数。”透露的则是一种认命的无奈。江淹忘了自己在扮演刘琨,因而不自觉地表达出一己的感慨,与《重赠卢谌》等诗中凸显出来的刘琨形象颇有距离。这不是刘琨对时局的看法,而完全是江淹的声音。再如《郭弘农游仙》一首,江淹只得其游仙之表,而未得其慷慨之里,故所作“太浓太实,却不似景纯”(35)。究其原因,即是因为其“仿作多在修辞技巧的貌似,而不在精神性情的把握”(36)。钟嵘《诗品》明确说,郭璞《游仙诗》“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填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而《郭弘农游仙》表达的正是江淹的“列仙之趣”,不是郭璞的“坎壈咏怀”。
《杂体诗三十首》中最为人注意的一首是《陶征君田居》。一方面,前人多称其逼肖陶诗,宋时俗本甚至将此诗编入《陶渊明集》,“东坡亦因其误和之”(37)。清人沈德潜《古诗源》卷13赞江淹此诗“得彭泽之清逸矣”。连一向比较挑剔的何焯也称江淹“拟陶能得其自然”(38)。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其大醇小疵,如清人贺贻孙谓:“江文通《拟陶征君》一首,非不酷似,然皆有意为之。如富贵人家园林,时效竹篱茅舍,闻鸡犬吠声,以为胜绝,而繁华之意不除。若陶诗则如桃源异境,鸡犬桑麻,非复人间,究竟不异人间。”(39)孙月峰谓:“句法尽相似,但总看觉色过浓妍耳。”(40)这两家的批评主要着眼于词采修辞,颇为有见,但所论犹有未尽。
《陶征君田居》诗云: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闇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
此诗的成功之处,在于兼取陶氏诗文,尤其是大量借用《归去来兮辞》中的文句,以营造与陶渊明文本逼肖的风格氛围。首句中的“东皋”,取自《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第五句“日暮巾柴车”,出自《归去来兮辞》“或巾柴车”;第八句“稚子候檐隙”出自《归去来兮辞》“稚子候门”。至于化自陶诗的句子,更不必一一列举。例如“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二句,即自陶诗“虽欲挥手归,浊酒聊自持”点化而来,故外形酷似。但是,若细味此诗,其口吻大似旁观者的客观陈述,明显流露出江淹的主体性。其“破绽”主要有三:
首先,“倦”字很不妥当。《陶渊明集》中“倦”字凡两见,一次见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另一次见于《归去来兮辞》:“鸟倦飞而知还。”无论是诗中的行役疲劳,还是赋中的赋归咏叹,这两个例子中“倦”字明显都是表达陶渊明对于宦途的厌倦,表达心灵的疲倦,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江淹诗中所用的“倦”字不仅不合陶渊明的一惯用法,也凸显了陶渊明对于躬耕陇亩生活的不堪。当然,这表达了江淹对陶渊明的理解,它塑造的是江淹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并影响了全诗的风格。
其次,陶渊明《和刘柴桑》诗云:“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这里的“归人”明确是第三人称。江淹事事拟学,但“归人”一句却暴露了他的旁观者立场,模糊了他正在“饰演”的陶渊明的角色身份。因此,尽管这两句是由“依依墟里烟”和“稚子候门”等拼装而成,却显得与陶渊明的口吻格格不入。
再次,除了篇首、篇中的这两个破绽,“开径望三益”可以说是篇终的另一个瑕疵。前人已经敏锐地察觉,“‘开径望三益’,此一句为不类”(41)。李善引《论语》注此句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则此句之意,在盼望益友之到来,此意良善,但是与陶渊明诗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颇异其趣。陶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读山海经》其一:“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这些诗句中所塑造的陶渊明的形象,是处穷巷之中而不改其乐的隐士,他并不着意期望友人之过访,故一任三径之就荒,而自掩白日之荆扉。陶诗研究史上,有过著名的“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的争论(42),至今莫衷一是。无论如何,我以为,《陶征君田居》中的这个“望”字太着意,它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陶诗的风格,甚至歪曲了陶渊明的形象。归根到底,它表现的是江淹的本色。
五、结语
这篇文章的目的,似乎是要揭发江淹拟古的疵病,彰显其学人之“不似”,其实是要揭示其拟古的特点,要突出其为己之“似”。如果说,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是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那么,本文的重点就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43)。
郭绍虞说过:“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与后人学古优孟衣冠者不同。”(44)在拟古中,江淹不仅深入体会古人字词章法方面的特点,而且吸取其创作经验,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发挥。谢灵运诗赋描摹山水景色,爱用“带”字,如《白石岩下径行田》:“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仅《山居赋》一篇,即有多处用例:“室、壁带溪,曾、孤临江”;“岂伊临溪而傍沼,乃抱阜而带山”;“枇杷林檎,带谷映渚”(45)。反观江淹《谢临川游山》,其中“桐林带晨露,石壁映初晰”二句,以“带”对“映”,与《山居赋》如出一辙。而《悼室人十首》其四亦有:“复值烟雨散,清阴带山浓。”《秋至怀归》亦云:“楚关带秦陇,荆云冠吴烟。”《从萧骠骑新帝垒》也有:“云色被江出,烟光带海浮。”可见江淹从谢灵运学得字法,不仅用于模拟谢诗,亦用于自家的诗歌创作。对于江淹,拟古与自作似相反而相成,实殊途而同归。
注释:
①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序》,[明]胡之骥注,李长路、赵威点校:《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6页。本文引证江淹作品,除另有说明者外,皆据此本。
②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校注》“前言”,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页。
③例如陈德长《论江淹的拟古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孙津华《试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及其序对钟嵘的影响》(《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王丰先《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与钟嵘〈诗品〉关系考辨》(《甘肃高师学报》2005年第3期);郑虹霓《从江淹拟古诗看其文学观》(《阜阳师院学报》2005年第4期);母美春《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④[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91页。清人冯班《冯氏纠谬》则与严羽反调:“江淹所拟,《从军》一篇最合。”
⑤[清]施补华:《岘佣说诗》,《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77页。
⑥[元]陈绎曾:《诗谱》,[清]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31页。
⑦[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9,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⑧[清]刘熙载:《艺概》卷2《诗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⑨郑虹霓曾从文献学与写作学两个角度,论述江淹拟古逼真的创作技巧,见其《江淹拟古诗新审视——从文献学与写作学角度考察》,《阜阳师院学报》2003年第4期。
⑩[清]汪师韩:《诗学纂闻》,《清诗话》,第456、457页。
(11)以下23个例证,皆为汪师韩所举,见其《诗学纂闻》“江文通《杂体诗》拙句”条,《清诗话》,第456-457页。按:笔者并不完全同意汪师韩的意见,例如汪氏谓《刘文学感遇》“橘柚在南国,因君为羽翼”二句“以羽翼说树,为就韵故耳”。今按《古诗》:“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人傥欲我知,因君为羽翼。”江诗全本此诗之意,以橘柚拟人,未为可非。窃以为此乃汪氏误解,不能视作江诗趁韵之例。
(12)按:此句“乐”当作“药”。胡克家《文选考异》云:“茶陵本云:乐,五臣作药。袁本作药,云善作药。案各本所见皆非也。下有‘丹泉术’‘紫芳心’之云,此言药无疑。袁本载五臣翰注云:‘徙药,行药也。’又载善注:‘徙乐,行乐也。’茶陵但载善‘徙乐,行乐也’,五臣删此一句,当是正文善自作‘药’,与五臣不异。其五臣之注为全袭善语,传写误善正文及注作‘乐’,据之作校语者不辨,尤亦同其误也。鲍明远有《行药至城东桥》诗,在二十二卷。”黄侃《文选平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7页亦作此说。汪师韩虽未校正此讹字,但认为江氏改行作徒、“加徙字则拙”的提法并没有错。
(13)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18页。
(14)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1983年。
(15)[清]许梿编,黎经诰笺注:《六朝文絮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6)林文月语,见其《拟古·自序》,台北:洪范书店,1993年,第2页。
(17)[清]于光华编:《评注昭明文选》卷7,台北:学海出版社,1981年。
(18)[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9)参看[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又[宋]王琳撰:《野客丛书》卷20“规仿古诗意”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20)这种误解在唐宋时代尤为盛行。《野客丛书》卷12:“《遁斋闲览》云:《文选》有江淹拟汤惠休诗曰:‘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仆谓此误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韦庄诗曰:‘千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许浑《送僧南归诗》曰:‘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秋思长。’曰:‘汤师不可问,江上碧云深。’权德舆《赠惠上人诗》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云。’孟郊《送清远上人诗》曰:‘诗夸碧云句,道证青莲心。’张祜《赠高闲上人诗》曰:‘道心黄檗老,诗思碧云秋。’雪窦诗曰:‘碧云流水是诗家。’曰:‘汤惠休词岂易闻,暮风吹断碧溪云。’此等语皆以为汤诗用,惟韦苏州《赠皎上人诗》曰:‘愿以碧云思,方君怨别词。’似不失本意。吴曾《漫录》但引乐天与唐上人对答二诗为证,岂止此耶?”
(21)如谢惠连诗,当时有“谢惠连体”之说,其特点之一是使用蝉联格连接各章,《谢法曹赠别》中即有意放大此一特点。关于谢惠连体,参看王运熙:《谢惠连体与西洲曲》(《江海学刊》1991年第1期);拙撰《世族与六朝文学》(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22)[清]于光华编:《评注昭明文选》卷7。
(23)在南北朝文献中,除了时代稍晚的《魏书》中见有两个用例之外,其余未见使用。似乎到了唐宋时代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裴灌《唐嵩岳少林寺碑》有“孤标神县”的句子,宋祁《和登山城望京邑》亦云:“山川不可见,葱郁望神县。”其句法劲崛,显然都受到江淹的影响。
(24)《诗辩坻》卷2。
(25)例如汉《刘熊碑》铭诗中有“有君臣然后有父子”一句,后代或褒或贬,意见不一。参看拙撰《刘熊碑新考》,载《古刻新诠》,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3-14页。
(26)《文选》卷25。按:刘氏原作颇有“累句”,除文中所举外,还有“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等。相比之下,江淹《刘太尉伤乱》句法老到,较胜原作。
(27)[南朝齐]谢朓著,曹融南校注:《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28)[清]洪若皋辑评:《梁昭明文选越裁》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总集类,第28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8页。
(29)尤本误改为“悼亡”,误,胡克家《文选考异》卷6已指明。
(30)诗见《文选》卷23。
(31)《江淹集校注》,第68页。按:《悼室人》“前八首写对亡妻的四时悼念之情”,其结构倒是与《悼亡诗》三首相同。
(32)黄侃平点,黄焯编次:《文选平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按:“松铭”一词亦是江淹首创。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有些袭用者受江淹此诗之影响,倾向用此词于悼念女性死者的诗文之中,如[宋]范成大《姚夫人挽歌词》、《故太夫人章氏挽词》,见《石湖居士诗集》卷20、卷32,《四部丛刊》本。
(33)参看拙撰《墓志文体起源新论》,《学术研究》2005年第6期。
(34)[清]何焯撰,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9页。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9亦谓江淹“拟左记室诗,只是数史中典故”。
(35)孙月峰语,见[清]于光华编:《评注昭明文选》卷7。
(36)游志诚:《江淹〈杂拟〉三十首反映的文类学》,载《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228页。
(37)韩子苍语,见[宋]蔡正孙编:《诗林广记》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939页。
(39)[清]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本。
(40)见[清]于光华编:《评注昭明文选》卷7。
(41)《诗林广记》卷1记韩子苍称引张子西语。
(42)此一争论由来已久,牵涉面甚广,较为晚近也较全面的讨论,参看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43)《杂体诗三十首》在题材选择方面亦体现江淹本色,陈恩维《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已有论述,故本文不赘。
(44)[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第191页。
(45)[南朝宋]谢灵运著,顾绍柏集注:《谢灵运集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年,第126、452、454、4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