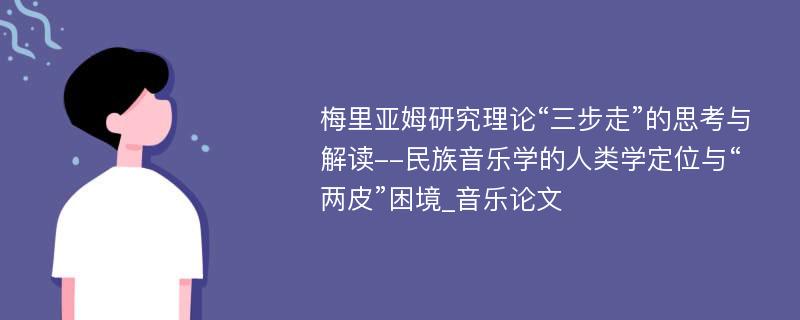
对梅里亚姆研究理论“三步骤”的思考与解读——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与“两张皮”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民族音乐论文,取向论文,困境论文,梅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1)02-0007-08
笔者关注民族音乐学,读书有心得,试作札记一篇。①
一、问题的提出
在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中,几位关键的先生及著作影响了该学科的发展,美国音乐人类学家Alan P.梅里亚姆即其一。梅里亚姆属人类学取向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他率先提出“在文化中研究音乐”(study music in culture,1960),后又说“音乐作为文化研究”(study music as culture,1973)。②由此,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被推至学术前台,受到重视,并构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取向。然而,音乐载体的声音性特征及其显在性如何与文化关联,以及如何协调和阐释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对民族音乐学来说既是新课题,也是新挑战。声音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兼顾与平衡,一直是该学科前行中不断探索和追寻的目标,由此也形成该研究取向最富张力和最具吸引力的特色之一。
针对文化中的音乐,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具体的维度,即音乐(声音)研究与文化(语境及意义与价值)研究。然而,因其研究取向与研究手段不尽一致,二者互动关系脱节,出现了强化语境研究而疏于音乐研究的倾向,此类情形国内外常有闻见。对此,M·胡德早有示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乐。”C·西格亦云,民族音乐学当是:“对人类音乐的整体研究,包括音乐本身和音乐与外围关系的研究。”J·H·K·恩克迪亚也提醒关注文化者:上下文语境的描述应该只是促进探索音乐的意义的工具,而不是学科研究的目的。③国内曹本冶也注意到“以人类学为取向的学者,在学科定位上靠拢人类学、疏远音乐学”,导致“轻音乐体系、重文化上下关联等取向上的侧重”④。对于音乐研究的弱化,赵塔里木亦深为担忧:“现在国内很多音乐学专业的论文,也写得和民族学论文一样……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应该有的独特价值何在?”⑤简单说,这里的问题是“音乐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离,即人们常说的“两张皮”问题。
这种情况何以出现?是学习者的自身问题,还是潜在的学科方法问题,抑或是其他更根本性的危机?本文尝试做些讨论,并谈点初浅的认识。
二、民族音乐学研究“三步骤”
民族音乐学发展中的重大理论转向始自梅里亚姆,1964年,他发表《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为其理论奠定基石;⑥其后,多次撰文重申其理论模式,以推动民族音乐学研究。
在《民族音乐学定义》一文中,梅里亚姆专文解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三步骤⑦,即:1.在田野中搜集材料;2.记谱和分析;3.把分析结果放到相关背景中去讨论。简单说,即音乐民族志、记谱与分析和相关文化研究。对此,笔者的理解是:第一步在第一时空中确定研究对象,以获取事实资源,操作以为音乐民族志;第二步对所确立对象的音响部分进行音乐学式的描写和解析,用记谱确立音乐的书面形态及其运用乐谱分析获得其艺术含义;第三步文化角度的研究,以人类学立场、视野与价值目标,联系文化背景、文明渊源、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诠释,以彰显其文化意义。
从此程式看出,3个阶段采用了不同的研究策略,但其研究理念并不具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会给研究结果带来什么?下面是笔者的考察与分析。
梅里亚姆明确将民族音乐学研究旨趣定位在:“在文化中研究音乐”或“音乐作为文化研究”。故研究起点由“田野”始,以“文化”终,音乐居其间。田野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第一步,所究对象在文化中存在,故音乐当受文化的全面观照。该出发点这种文化上的“一体性”使其田野工作不单局限于音乐,在对音乐与文化事象的搜集、记录和描述并不加以特别的区分和分离。田野工作“一体性”原则是与其研究主旨相吻合的。研究第二步:记谱和分析。该步骤的工作目标是对所采集的音乐声响用乐谱进行描写及其音乐分析。这一步骤涉及两点:其一,对音乐声响进行符码化操作是不与自身文化语境相联系的独立操作;其二,记录与分析音乐音响的手段,其基础是以西方记谱法和术语系统为其“元语言”的。实际上,待第二步工作结束,音乐分析的结果已形成,而此时文化研究还尚未展开。⑧一个潜在的事实是,乐谱的西方内涵和术语操作已经在逻辑和时序上获得了优先权,并在文化研究介入前,已成功地将音乐与它相关的文化进行了剥离,即不经意间已被“艺术化”。实际上,该步骤已落入西方音乐学研究的窠臼。第三步骤,对已被“音乐学”意义判定的“音乐形态”加以文化视角的考察,以便找到和说明这些“音乐形态”(已非“音乐现象”)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维系背景及其文化价值与意义。这样的三步骤研究,实质已成为“拼接”,即将“音乐学”意义上的音乐存在拼接到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文化存在的讨论上。这种讨论其实就是对“音乐”声响的“音高系”和“时间系”等“音乐学”意义上的物理特性,附会以文化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民俗的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说明,以解释“音乐学”意义上的音乐声响存在的文化因由。
梅里亚姆对“三步骤”的阐述,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让人徒增“重此轻彼”的疑惑。在讲第一步骤时,洋洋洒洒6个方面,可谓详尽⑨,讲第三步骤时,亦以荷斯科维兹(Herskovits)《原始黑人心理中的弗洛伊德机械论》文章实例详加阐述,以强调“音乐处于文化之中”当是研究的一种普遍思路和方法。⑩然令人费解的是,梅氏对研究第二步骤一笔带过,不做申论,只寥寥三句:
民族音乐学调查的第二个阶段,或称为实验室阶段,我们在这里暂不讨论。在这个阶段中,调查者转向记谱工作,对他已经在采风中记录下来的材料进行结构分析。当然,对该项研究来说最基本的,是要确立一种分类法。(11)
如何记谱,又怎样分析?这里“不讨论”。只是提到一个目标:“一种分类法”。什么分类法,怎样建立?也没说。留下的事实是:梅氏人类学取向的音乐“记谱与分析”没一点具体内容。(12)研究中这第二步,本同样关键,不想梅氏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了。这三个步骤极不对称,有何暗示吗?
即便是因梅氏“疏忽”,这些晦暗不明仍有些蹊跷。(13)然细察下,即可注意到该研究模式的明显疏漏,那就是:梅氏没能将“音乐作为文化研究”理念在他的3个步骤中一以贯之。可以明确的是,他在第一、第三步与第二步中使用的标准不一(使用了双重标准)。第一步骤将音乐作为文化整体认知的对象加以考察(音乐民族志),第三步骤讨论音乐的意义亦是通过社会-文化系统加以分析的,而第二步骤研究则是将音乐与文化相割裂,在文化尚未到位情况下,以音乐学“元理论”为前提而单独加以研究(记谱与分析)。梅氏既然没有明确说出他“音乐研究”的“新法”,那么留给这个第二步骤的唯剩“旧法”,“记谱与分析”工作只好沿用西方音乐学的共性分析原则与模式,不会有局内人主位立场的文化预设。(14)按笔者理解,梅里亚姆“声音-概念-行为”之“三元”研究模式,在“概念”与“行为”范畴的理论阐释上贯彻了“文化”主导的思想,而在“声音”研究这一环节中,却并没能将其理论意图切实地贯彻下去。这不由得怀疑他所倡导的“三元”研究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能否真正实现。据此追问,梅里亚姆研究模式是否真解决了音乐文化的分析?当然,可能是因他意外离世,未来得及拿出该理论完整的“记谱与分析”模式。但事实的结果是,直到梅里亚姆离世,他并没有提供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独特的“记谱与分析”模式。可否作此联系:至少在我国大陆目前民族音乐学研究实际中,“音乐研究”与“文化研究”未能取得统一的“两张皮”现象与此有关。这是否是梅氏理论自身的问题?是否与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的研究方法不完善相关呢?尽管在梅氏前后,不少民族音乐学家为此做出大量努力,探索与进展不断(15),但该问题在梅氏理论中的存在,是否说明现有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理论在音乐分析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呢?
三、音乐分析与音乐文化
然而无论如何,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取向和价值毋庸置疑。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先回到梅里亚姆“在文化中研究音乐”和“音乐作为文化研究”的这个起点,以此考察人类学取向的音乐“记谱与分析”问题。梅氏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在音乐研究中考虑到了文化的地位和潜在能量,它打开了理解和认识音乐的文化性质的另一扇大门。梅氏理论提供了认识音乐与其文化环境的深刻联系的视角。考虑音乐与文化的关联是梅氏人类学取向的理论内核,而这恰恰是以往西方音乐学理论体系所忽视和遗漏的。笔者曾撰文谈到:“在欧洲传统的音乐学(体系音乐学)研究观念中,只有两种对象才是音乐实在(或音乐本体),才能成为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由此可以纳入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这两种对象是:声音与观念。”(16)梅氏“声音-概念-行为”的“三元”模式,曹本冶用“思想-行为”方式与之对应;即“思想”对应梅氏“概念”,而“行为”(细分为“过程”与“结果”)对应梅氏的“行为”与“声音”。曹氏试图用“过程”与“结果”揭示出梅氏“行为”与“声音”深层上的关联,可加深对梅氏“三元”模式本质的理解。(17)按此可知,音乐是外部(行为)与内部(声响)的关联,是文化视角与音乐视角的一统。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人类学取向的音乐“记谱与分析”问题,当可引入“声音景观”概念。按通常理解,乐谱被认为是音乐的符号记录和音乐的一种书面文本,它所记录的是被人们称作为音乐的东西,谱面上的符号即可转达音乐的含意。然而,与音乐一样,乐谱也与特定文化相联系,背后潜藏着特定的文化观念。通常,民族音乐学的音乐记谱方式与西方记谱法在观念上有所关联(18),它的内核是对音乐声音的物理学抽象的标识,所描述的对象是声音物理量的四种要素及其延伸系列。它最基本的理念一面是将这些物理量与音乐等量齐观并赋予其意义,而另一面则是抽去声音在社会文化时空中特殊的含义。就乐谱所提供的实际信息来说,它所能反映的只是声音的那些容易被符码化的物理计量:频率(音高)、时长(时值)、振幅(强弱)、振动式样(音色),以及被“音乐学”知识体系所认定并赋予其“音乐”含义的那些元素,如音阶、调式、节拍、旋律、和声、动机、乐节、乐句、乐段、曲式等。可见,记谱方式即内含着文化的价值表达。至于后一步“分析”工作,更是绝不可简单地看做是“客观”描写,或是在就这些单纯的“物理量”作技术上的符码转移工作。其实,音乐分析,即使不考虑局内人主位立场,也有该音乐所处文明阶段和文化模式方面的考量。客观的分析,实际上也摆脱不了分析者主位判断的因素。(19)
“记谱和分析”潜藏更深的东西也不应被忽略,如:1.现行乐谱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什么;2.乐谱分析先在的立场与预设;3.民族音乐学文化视野中音乐的范围与内涵等等。(20)西方记谱法是跨越了语言、地域、宗教或民族界限的一种普适性的话语模式。实际上,由这种乐谱所提供的音乐指示或指标是它事先规定的(21),即音乐声音的物理表达以及音乐声音的形式化表达。就仅乐谱来说,音乐经它一记录,不经意间音乐中一些表达被凸显,而另一些特别的文化表达则可能被过滤掉。(22)那些被过滤掉的文化表达中的差异性的东西,可能正是不同文化中最富特色的声音景观和最核心的文化精髓。
另外,将音乐作为纯粹的聆听而诉诸听觉,也是一种文化约定,是欧洲音乐历史过程的产物。听赏问题本身,在西方直到19世纪才成为一个学术的问题,而此前这种明确的观念并不存在。(23)在西方音乐史中,与纯粹聆听相对应的社会生态是音乐会式的“独立型音乐”。这种音乐在欧洲只是晚至19世纪才最终占据主流。而此前的音乐,主要是某种兼涉视觉因素的“社交型音乐”。(24)德国音乐社会学家贝塞勒发现了西方艺术音乐与听赏的深刻关系:由于听赏的发现,使西方音乐更加坚定了其纯粹音响形式的文化取向。西方音乐声音的形式化过程及与聆听方式变化间的对应关系,使人们看到了西方音乐形式化背后因纯粹聆听方式而被强化的另一层社会动因。(25)同时也暗示,以纯粹声音方式来理解音乐,与西方乐谱重记声音物理形态的文化取向大致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从梅氏“文化中的音乐”出发考察音乐现象,并以“过程”、“结果”一统视角观察音乐的“记谱与分析”,会更强调整体性地关注音乐。在此:音乐不仅仅是音乐(声音),联系其文化环境,它更是一种“景观”。这里,引入“声音景观”的概念,可以扩展对“文化中音乐”的记录与描写空间。“声音景观”(soundscape),美国谢勒梅将之释义为:“一种音乐文化特有的背景、声音与意义。”(26)将音乐视为“声音景观”,那么,它的范围与内涵就不再单一。至少,它不再仅是单纯的声音事象本身,而是与文化相关联的多方位的一种“声音”的“景致”。“声音景观”这一概念将音乐看成是一种景象,这种景象是一个全景,包括前景与景深。由此,不仅音乐主体(音响载体)仍得到强调,而且其中景(乐器、奏法与唱法等)、背景(文化关联物及其意识)也纳入其中,而且被推至前台,使其与音乐合为一体。(27)汤亚汀将谢勒梅“景观三分模式”与梅氏“三元”框架理论相对应,以强调这两种理论的内在一致性。(28)如此一来,音乐就应该从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一是“声音景观”,即人声、乐器、乐曲等;二是“音乐(文化)景观”,它并非是单一声响(听觉)层面的事象,而是一个景观复合体,包括以声音源为中心向外辐射至其他的文化景观,诸如演奏者、表演时空、仪式场面及其器物、参与者及其介入状况等等。尤其是后者,其文化属性可以不诉诸听觉,也不与访谈性的语言和文字相类,而以瞬息的过程状况存在,其“可视性”特征突出。(29)其实,当今民族音乐学,摄影与录像已成为研究的支柱性手段,原因即在于此。面对“声音景观”,民族音乐学如何记录与描写?笔者以为,“声音景观”最根本的特点是声音-文化的复合。显然,它不是由单一的乐谱所能容纳得了的。因此,音乐民族志描写必须体现其“复合”性特点,仅仅使用乐谱的声音记录远远不够。在此,Regula Burchkardt Qureshi博士的研究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他在1987年撰写《音乐之声和背景输入:一个音乐分析的表演模式》一文,将“场面”录像而不是单以“音乐”声响来作为描写框架。他提供的“图谱”,除乐谱外,还包括演奏者表演中行为和在场观众及其行为反响。该“图谱”容纳了三组信息:1.乐谱(音乐的声音)信息;2.表演者(演奏或演唱行为及仪式过程)信息;3.观众(精神状况与对音乐的反映和演出场面的气氛)信息。(30)在这三组信息中,如果说显在的音乐形式为乐谱所记录的话,那么,其他非显在的音乐隐性信息:演出者与仪式、观众与场面、气氛与精神氛围等也都得到了平行地记录。这即是围绕“声音中心”而展开而延伸至相关文化信息的综录,这其中既有音乐声音,也有非音乐声音的相关文化事项的对应描写。或许,这类“图录”在取向上更趋近于梅里亚姆“在文化中研究音乐”和“音乐作为文化研究”的含义。
“声音景观”具有一般文化的重要特征,比如连续的、在场不在场的、显在的和隐性的并无限延展的等性质。这些文化属性使得文化中音乐的内涵更加丰富多样。丰富性增加,文化描写泛化的危险也随之增加。鉴于此,笔者以为,把握“声音景观”,必须有“度”。所以,可考虑:以“音乐”现场乐音源为中心来拓展“景观”描述,包括前述如演奏者、表演时空、仪式场合及其器物、参与者和介入状况等(31)。“文化中音乐”描写的重点,是将“乐谱”与“整个场面的文化状况”合成在同一个时空坐标上,以便研究者能够全面了解和把握“文化中音乐”的脉络和构成。为了使文化描写进入音乐的空间,进而与音乐描写共存于一个空间,以显现音乐与文化的关联,上述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乐谱描写与文化描写的“接轨”,即以乐谱为坐标,在其下作平行的文化描写。因乐谱(音乐)按时序演进,所以以时间为坐标,将文化描写与时间同步。当然,音乐与文化的关联极为多样与复杂,它可以是外显关系,也可以是内隐关系。外显关系,如表演过程、仪式场合,观众同步参与等在“声音景观”中可以在场。而内隐关系,如观念、民俗制度、潜在法则等却不在“声音景观”中,即它们并不在场(即不外显于表演的现场)。这种不在场本身即意味着它与音乐的联系是另一种方式,它不与乐谱描写共存亦不为怪。再者,内隐部分作为一种通道,通向的是外部最广阔的文化空间。因此,就音乐描写说,自不必去考虑。笔者以为,“文化中的音乐”,其语义并非单指文化本身,而是包含三层关联:即还兼指文化中的音乐及文化与音乐二者的关系。所以最为重要的是,音乐民族志要体现这三层关系并描写出相互关联的管道。这种管道是音乐迈向文化的起点,也是文化影响音乐的结点。
由此,反观目前的“记谱与分析”,可注意其中的两点问题:一是将内涵丰富的“声音景观”仅仅看作是“声音”,相应地只将声音物理量变化当作记录和分析的对象;二是将“声音”记谱与分析同文化记录与分析从空间维度上加以拆解与阻隔,使“音乐”记录与研究同“文化”记录与研究不处在同一个时空坐标和研究平台上,造成了“音乐”与“文化”实际上的分裂。同时,“记谱与分析”在先,而文化分析在后的研究过程,使二者的信息与研究不互递、不相交和不重合。造成音乐研究只能回到音乐学的轨道,只能向“内转”,去分析和讨论音乐自身的声音要素,而无法迈向“文化中音乐”的研究。反之,文化研究也相类,难以找到与音乐最有效的契合点,从而导致一味无针对性地或模棱两可地泛泛谈论文化区域、民俗、语言、观念等的相关性。
我们对此应保持警醒,在接受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给我们带来的鼓舞的同时,也沉思高歌迈进背后的隐忧。
四、小结
今天,颇具里程碑式意义的《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发表已过去近半个世纪,尽管民族音乐学研究日趋精进,但梅里亚姆人类学取向的研究,至今仍是民族音乐学中的一面旗帜,其前瞻性的学理仍是该学科的一笔财富。回溯梅氏经典,重温那两句方向性的引领:“在文化中研究音乐”和“音乐作为文化研究”仍能给人启示,助人识辨方向。
笔者以为,梅里亚姆给民族音乐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资源,但他却没来得及提供一个整体的、与之匹配并具有操作性的研究方法。梅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定义》中方法论的缺失,反映出该学科取向所存在致命短板和潜在危机。正因民族音乐学没能完成本学科自己的音乐“记谱与分析”方法,从而造成“音乐”与“文化”研究的脱节。(32)“两张皮”的现状足以使该学科自身深处尴尬和饱受质疑的不利局面之中。
其实,梅氏音乐人类学理论颇具前沿性,突出价值体现在两点:一是它扩展了音乐的范围;二是它扩充了音乐的意义。这两点形成了“民族音乐学”对音乐本质的不同理解,由此与原“音乐学”在学科上形成价值分野,其意义十分显要。然现实的不足是,梅氏理论的真正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更没有在实际研究中得到完全的贯彻和落实,令人深感遗憾。梅氏所说“文化中的音乐”是想表明,音乐不应只被框定在声音的形态范围,也不应只囿于“艺术”的藩篱之中,而他的“声音-概念-行为”“三元”理论框架,是想在总体上将音乐纳入到“文化”考察的范畴之中。梅氏理解与音乐学理解的差别是,尽管音乐学也有相类似的对象与领域,但它们却是处在各自不相连属的分支学科或视域中,如声音(在记谱法、乐理、作曲等领域中探究)、概念(在乐理、和声、复调、曲式、音乐美学、音乐史学等领域中研究)、行为(在器乐与声乐教学法中研讨),(33)其研究主旨仍趋向以形态学为核心。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学科的价值取向与范畴。除此外,梅氏认为,就音乐范围讲,音乐不只是存在于自身的声音范围之内,音乐自身的界定亦是由文化确定的。以声音为表征的“音乐”,还与其社会文化事项密切相关。(34)所以,民族音乐学需要从文化角度来考察“音乐”更本质的方面,如何谓音乐,音乐存在的方式与状况、理由与来源,以及外部文化如何使“作为文化的音乐”成为了“音乐”等。在“意义”方面,“在文化中研究音乐”或“音乐作为文化研究”的提法,实际上是将“音乐”(原以艺术音乐为尺度与准绳的约定)的意义做了扩充。梅氏恢复了音乐与社会生活的生动联系,并重新找回被“艺术”剥夺已久的那份已失落了的权利。音乐学中的音乐,是以审美为唯一对象的存在物,它的“声音形式”在“审美”上具有充足的意义,而挤掉了音乐所兼具的其他功能,音乐意义被限定在以审美为取向的纯粹精神范畴之内。由此一来,音乐实际上被压缩了与生活和精神空间的对位,同时也挤压了自身的时空自在。真实的情况是,世界上各文化区域的音乐存在远远多于仅具审美意义的音乐的存在。民族音乐学所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的真实的自为的音乐存在。由此可以说,民族音乐学客观上也恢复和重建了音乐的意义领域。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获得对音乐更完整的透析和理解,民族音乐学自身不仅要在观念取向上,而且也要在理论方法上取得更高度的统整性。民族音乐学在迈向未来的途中,当务之急是必须重建它自己研究中的全面的整体性的方法论!
到此,回头再回味梅氏这个理论“模式”——以“田野”始,以“文化”终,“音乐”居其间。出发点与归属都是文化,居其间的音乐有何意味?它的存在意味着什么?这一境况中的音乐,会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并与其前后具有不相连属的意义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它会是一种什么意义的存在:它不就是“文化中的音乐”?!于是,依稀之中可辨出:梅氏三步骤,它本是一个文化学架构!并非一个音乐学架构!(35)由此,梅氏不愿直说的潜在之意,于此昭然若揭!!如果说20世纪之前,音乐早已成为了一门艺术(其典型代表即西方的“艺术音乐”),已经超拔远离了民俗生活而进入了另一个范畴(36),那么,尚存留于民俗文化中的音乐当属“文化”中的现象而非“艺术”中的现象。梅里亚姆要完成的是另一件工作,他要恢复“艺术音乐”之外的“音乐”的真貌,这本是一件人类学的工作。这里可以对应上他后来留下的那句话:“音乐就是文化!!”这才是梅里亚姆的真实想法,也即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的真正性质:面对的是音乐,指向的是文化。
由此,笔者对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理论“模式”:“声音-概念-行为”的解读是,该人类学取向“模式”想表达的本意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音乐,不是“艺术”中的音乐,而是“文化”中的音乐,由此,也就不是“音乐学”的对象,而是“人类学”的对象。(37)
注释:
①本文是在2010年10月中国音乐学院“庆祝董维松教授80华诞暨中国传统音乐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对于民族音乐学,笔者不类,但因曾偶为董师授徒,20余年来一直保持对该学科的高度关注,近来又集中阅读了梅里亚姆《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布莱金《人的音乐性》,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曹本冶编《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陈铭道《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及所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等一批著述,偶有心得。借为“董先生80华诞祝寿”暨“研讨会”之机,忝冒于此,奉上局外人点滴心得,以谢师授之恩。行外之见,有隔靴搔痒之感,难为周全,还望指正。
②梅里亚姆前后两种说法尽管有别;1975年,他甚至还说过“Music is culture”(音乐就是文化),但他想表达“音乐与文化”内在关系的立场则一以贯之。该英文的汉语表达采自曹本冶。见《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民族音乐学”》,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③此三条材料均转引自曹本冶《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民族音乐学”》,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5页。
④同上,第11页。
⑤赵塔里木:《民族音乐学:本土语境中的学科建构问题》,载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⑥实际上,《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一书因其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的体系性建构需要,要解决的是方向性和基础性的大问题,即要梳理该理论取向与其外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要说明该取向自身的学术理论以及其理论自洽的内在逻辑等问题,故梅氏放弃了该书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全面的讨论。在该书中,他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虽然我们无意在这里详述民族音乐的记谱和音乐分析,但是对一些问题必须加以考虑。”(见穆谦“学位论文”译文打印本,第56-57页)
⑦梅氏《民族音乐学定义》一文专谈该取向“方法”,似对此问题稍有弥补。本文即以该文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梅里亚姆对“三步骤”全面的解说,详见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⑧此分析结果,指向是音乐声响的物理属性的音高系和时间系等音乐学分类与表达,它所体现的是“音乐学”所提供的价值参照及其音乐意义。而待后续第三步“文化研究”开始时,已完成分析的“音乐”实际上是以准西方的文化身份加入其“文化建构”的。
⑨其实,第一步骤中这六点内容已在《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出现,即所考察的对象包括6个方面:1.音乐的物质文化;2.关注歌词研究;3.音乐类别;4.音乐家;5.音乐的文化用途与功能;6.音乐作为文化创造行为。(见该书第50-52页)
⑩见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定义》,载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页。
(11)同上书,第8页。
(12)尽管梅氏希望澄清这两者(笔者注:音乐学取向与人类学取向)是学科必须兼有的取向和着重点,二者缺一不可。(见《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民族音乐学”》,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但此处情况似乎表明,这仍旧是人类学取向的研究最初所存在的问题。北美民族音乐学家Regula Burchkardt Qureshi博士指出,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方法(如梅里亚姆等)的研究:“最初聚焦于音乐的使用和功能上,并未将音乐本身纳入到分析计划中。他们既没有分析音乐声音,也没有按照完全地将背景研究排除在外的西方标准来分析。”(《音乐之声和背景输入:一个音乐分析的表演模式》,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页)曹本冶亦认为:“对于音乐本体的形态记录和分析……被北美学界人类学视野取向的学者们所忽略。”(《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民族音乐学”》,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13)其实,梅氏忽略音乐“记谱与分析”的原因,他在《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一书中有所暗示,即该问题现在还得不到解决。他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问题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实验室的分析者具有将音乐的声音转写到书面的正确方法,但是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民族音乐学家们一致同意,书面转写的最终目的在于得到一首歌曲的准确面貌,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揭示形态和风格的要素。然而,对于达到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以及记录声音细节所必需的精确程度现在还没有定论。”(穆谦译打印本,第59页)
(14)这是在“记谱与分析”步骤梅氏没有提出具体的操作理论前提下的可能情况。也就是说,该取向的这一研究步骤没有像前后的其他两个步骤那样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梅氏在音乐的“记谱与分析”中没有提出具体的理论与方法。他可能有意回避了该问题。从题目看,梅氏该文主旨当有说明与构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模式的意图,然而在阐述时,他又避而不谈“记谱与分析”这一重要环节。笔者匪夷所思,只好做如此的理解:或许他并不认为这里的记谱和分析与人们普遍使用的记谱和分析有需要指出的特别之处,或有需要重新建构的必要;或许他还没有找到(或还在酝酿)与他该理论取向一致而有效的研究方法。
(15)梅氏前后,这方面的尝试和专门研究不少,许多学者一直在为记谱及其分析方法的丰富与完善而努力,如M·胡德在《民族音乐学家》中对三种记谱法的讨论;B·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研究:29个问题及概念》中的专门研究;(参见《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民族音乐学的记谱问题》,载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5页;47-73页)当今的北美学者R·B·Qureshi:《音乐之声和背景输入:一个音乐分析的表演模式》;(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386页)还有早期的霍恩博斯特尔(E·M.von Hornbositel)、巴托克(B·Bartok)以及M·赫尔顿(M·Herndon)等人所做的尝试。在音乐的声音记录和分析上,比较音乐学有重要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这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可以好好总结与发展(笔者以为,比较音乐学在这一领域所做的贡献是突出的)。人类学取向与音乐学取向的民族音乐学,其实,撇开其取向看,其研究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因音乐学取向看重音乐,故发展出一套“记谱与分析”方法,而人类学取向因侧重文化阐释,故对“记谱与分析”方法有所忽略,并非在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质上有何不同。
(16)参见拙著《音乐表演学科建设如何可能——从音乐学、知识和表演角度的审视》(载《中国音乐》2008年3期,第11页)。笔者进而申论:“在西方传统的音乐学观念中,表演只是声音产生前的活动,它既不属于声音,也不属于观念。尽管声音是表演的伴随物,但表演毕竟不是声音本身。而且,音乐在表演中产生后,便脱离表演而独立成为了一种实在,这种实在属于声音范畴,而不在表演之列。这种认识的必然结果是把表演与声音加以分离,由此,割断了表演与声音的联系。另一方面,表演的各种奏法、唱法虽是历史和文化观念的产物,但它还并不是观念本身,所以也不能归入音乐体系的研究范畴,由此又割断了表演与历史文化观念的联系。就这样,表演在体系音乐学范畴中没有了立锥之地。”
(17)曹氏的这种对应,对于理解“音乐行为”是有好处的。但梅氏所言的行为,还涉及到不同视域和层面的广泛内涵。正如他所说:“在音乐的产生和组织方面,我们可以分出四种主要行为:它们包括身体行为、关于乐音的言语行为、音乐的创造者和对音乐有所反映的听众双方的社会行为以及使音乐家有能力创造出适当的音乐的学习行为。”见《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穆谦译打印本),第95页。
(18)B·内特尔明确指出:“西方音乐通常所采用的记谱法不合民族音乐学的需求。”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方法通常是在西方记谱法的基础上添加标志性符号来记录西方音乐不常见到的音乐现象。”(见《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载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C·西格进一步讲道:“我们从其他音乐中挑选出某些与西方艺术音乐记谱法中我们熟知的构造物相似的构造物,并把它们写下来,而忽略了我们没有对应符号的一切其他构造物。”(转引自梅里亚姆:《音乐的人类学研究》穆谦译打印本,第60页)B·内特尔和C·西格的论述即对西方记谱法有所警惕。他们警惕什么呢?警惕的是西方记谱法的潜在文化规定。B·内特尔所说“在西方记谱法的基础上添加标志性符号”的目的,是用它们“来记录西方音乐不常见到的音乐现象”,也就是说,非西方音乐中的有些现象,西方记谱法是不予反映的,如果不添加新符号,这些现象就不能被这种乐谱所反映。C·西格的话更明白,按西方记谱法操作,实际上是在做一种选择,即选择那些与西方记谱法符号相对应的声音构造物,西方记谱法符号之外的声音现象是被排拒的。
(19)记得1984年,董维松老师给笔者等学生上“戏曲音乐”课时,曾放眉户剧《梁秋燕》中[软月调]开头过门(共24小节),要求学生按直感判断调式,结果各有不同。后来他以此为例,写成文章《从律学的角度再谈“苦音”的音阶及其调式》发表在《音乐研究》1987年第1期上。这种类似情形在B·内特尔看来,即是有先在或主观的音乐观念渗入其中:“作为一个研究者,在记谱时他必须先对音乐体系的特性有一定的了解。就是说,他在录音之前已经从听觉上对音乐进行过分析。用记谱法记录音乐之后,他还得进一步分析。”(见《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载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0)对于该问题,B·内特尔在对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过总结,他明确了五大问题:“1.表述性记谱与描述性记谱之间的区分;2.音乐思维的构成特性;3.两种记谱的关系:记谱是局外人利用记谱法对音乐所进行的描述,还是某种文化自身为了表达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所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4.人和机器的角色与作用;5.记谱应该是学科的统一的技术,是否可以根据某种特殊观察的需要而发展特殊的技术。”(见《民族音乐学的历史与民族音乐学家的工作》,载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1)C·西格对记谱有深入研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区分了“表述性记谱”与“描述性记谱”两种不同性质的记谱。(参见张伯瑜编译:《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7-74页)现代的西方五线谱,是作曲家创作的工具,本质上是供演奏(唱)记录乐曲用的。也就是说,它本质是“表述性”而非“描述性”的。这就说明它内含着西方艺术音乐的文化约定。许多文化性的约定并不在乐谱的符码中,比如五线谱中音、音高、节奏、调式、和弦等符号的含义并不在符号之中,而在“乐理”、“和声学”、“曲式学”、“音乐美学”和“器乐”、“声乐”等训练过程以及艺术音乐整个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导向之中。
(22)这里以阿兰·洛马克斯名著《民歌风格与文化》为例来谈谈这个问题。该著述中罗列了37个分析指标(见陈铭道《西方民族音乐学十讲》第90-94页),以说明这些音乐的社会与文化特征。尽管这里提到的37个指标不是记谱法本身而是分析指标,但它们的背后与西方记谱法相关。如上所述,西方记谱法是在“声音四要素”基础上的“描写”,然后再以“音乐学”的知识体系加以识别。笔者据西方记谱法内涵将这37个指标还原,即可注意到与记谱指标基本重合,并存在对应关系:1.声乐部分领唱与合唱(声部:音高系);2.乐队与唱队关系(声部:音高系);3.乐队中自身关系(声部:音高系);4.合唱组织(声部:音高系);5.合唱与领唱的音准(音高系);6.合唱与领唱的节奏(时值系);7.乐队的组织(声部与节奏系);8.乐队及领奏的音准配合(音高系);9.乐队及领奏的节奏配合(时值系);10.歌词部分(文学系);11.声乐演唱部分的节奏(时值系);12.声乐部分的节奏组织(时值系);13.乐队的节奏(时值系);14.乐队的节奏组织(时值系);15.旋律型(音高系);16.旋律的曲式(时值系);17.乐句的长度(时值系);18.乐句的数量(时值系);19.终止的位置(音高系);20.旋律音域(音高系);21.平均音程大小(音高系);22.声乐的多声类型(音高、时值系);23.装饰音(音高系);24.速度(时值系);25.音量(强弱系);26.声乐部分的节奏(时值系);27.乐队的节奏(时值系);28.滑音(音高系);29.多音(词曲关系);30.颤音(音高系);31.喉音与装饰音(特殊系:唱法);32.声音的位置(特殊系:唱法);33.声音的宽度与张力(特殊系:唱法);34.鼻音(特殊系:唱法);35.刺耳(音色系);36.重音(强弱系);37.共鸣(音色系)。由此观之,该37个分析指标背后的理据乃是西方记谱法的音乐观念。所谓音乐风格分析的主体,依旧是音高、时值、音强、音色四个核心要素的声音指标。当然,其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分析指标,即“唱法”。此为西方记谱法所不予以关注和记录的声音系列。这里有趣的是,为何这一指标西方记谱法不予以考虑?其根源涉及到西方记谱法的文化体系。西方记谱法不记唱法,并非唱法与声音无关,而是西方艺术音乐另有约定,而其声音特色不用记谱法来标识。唱法所涉及的声音品质是西方声乐传授过程中教师的事,他们将该文化认可的声音,如西方艺术音乐的Bel canto作为他们的声音标准,这种标准已被潜在的认可。这是一种没有鼻音、而有丰富共鸣和均匀泛音的“美”的声音。由于有了这个前提,西方记谱法可以不用去记录声乐声音的这类品质。也就是说,记谱法不记录唱法特质的音色(器乐声音亦然)。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记谱法依然有其存在的文化前提。也在此意义上,阿兰·洛马克斯为了能区别他所记录的歌唱声音与西方的歌唱声音的不同,所以必须加以特殊标记,否则就无法让人知晓这种唱法所形成的特殊音色。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了上述洛马克斯提供的这一特殊系,难道非西方文化中音乐的声音就再无可以作为音乐的声音的其他特殊品质了吗?
(23)也就是说,在此前音乐是否为听觉所独揽,是否只可属于聆听,其理解当与今天有别。贝塞勒:《近代音乐听赏问题》:“怎样听赏音乐,这在19世纪时成了一个学术问题。”(载[德]克奈夫等:《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页)也即19世纪以前,即使是西方的艺术音乐,亦并非以纯粹聆听的方式存在。那么,其他非欧地区文化中的音乐与人的关系,更不一定是以纯粹聆听的方式相联系。
(24)贝塞勒:《近代音乐听赏问题》:“例如,在欧洲以外的节日、庆典、神秘的招神除鬼仪式时,在基督教的祈祷和祭祀庆典时,在全世界的集体劳动、集会和舞蹈时,在欧洲,又比如与宫廷抒情诗、小型歌舞表演歌曲的演唱,与大学里的音乐爱好者团体、男声合唱团和歌咏运动有关的场合,就是这样。这些都是‘社交型音乐’,它们具有大量几乎不会被忽视的‘形象’。而很晚以后才形成的‘独立型’音乐,只是到了19世纪才获得了胜利。”载[德]克奈夫等:《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25)贝塞勒:《近代音乐听赏问题》,载[德]克奈夫等:《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26)2000年,民族音乐学家K·K.谢梅勒运用“声音景观”概念对音乐进行了讨论。见汤亚汀:《音乐的流动景观与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读谢勒梅新著〈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音乐艺术》2001年第4期,第92页。
(27)由此,“声音景观”(soundscape)或可改作“音乐景观”(musikscape),可能更能体现其针对性。
(28)汤亚汀解释说:“这里的‘背景’,谢氏在文中定义为‘表演地点’和‘表演者与听众的行为’,‘声音’则是指‘音色,音高,音值,音强’,‘意义’即音乐本身的含义及对表演者与听众生活的含义。谢氏的景观三分模式,大致相当于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1964)的‘概念—乐音—行为’三分模式。只是前者用‘背景’加强了后者‘行为’中所缺的‘表演地点’(venue或place),并用‘声音’涵盖了‘乐音’,即去掉了sound前的修饰语musical(音乐的)。对表演地点的强调,在跨文化研究中有重要意义。”(《音乐的流动景观与家门口的民族音乐学——读谢勒梅新著〈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音乐艺术》2001年第4期,第92页)无论是梅氏“三元”理论框架还是谢氏“景观”三分模式,不容忽视的是,民族音乐学近来的取向一直是解读文化,一直是在将潜藏于幕后缄默的文化推举至可观瞻与识读的台前,以共筑音乐的意义。
(29)这主要包括音乐的演出场合与仪式性程序的行为过程和场面。这些时间性的行为过程与场面恰好是摄影和摄像所记录的对象。其最佳民族志手段当包括影像与画面。
(30)见该文图3的“录像图示”,载《大音(第二卷):音乐学·“音乐”之间的对话》,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页。
(31)参与者(或观众)指与音乐表演群体相对的参与群体(观众)。参与群体如何描写,或是否须描述,可作深入研讨。也就是说,“声音景观”外延如何限定,得做进一步探究。
(32)当然,这里肯定存在是否真正学好、用好该学科已有的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但就学科自身讲,仅是借用音乐学的“记谱与分析”方法,毕竟难以担当与完成民族音乐学自身的学科使命。
(33)我国学者于润洋注意到“音乐学”学科细分导致的认知割裂化倾向,而倡导“音乐学分析”。他尝试将音乐形式分析、音乐史与社会学分析统整到“美学”中去。他音乐学分析的经典案例《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音乐研究》1993年第1、2期)和《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即是从这一考虑与视角出发的研究。实际上学科与视野分离的情况,如“音乐形式”与“音乐内容”二分的争论在音乐学内部就长期存在。这也表明了音乐学的“音乐分析”中也是存在音乐形态与其文化属性方面的内在矛盾的。它表明欧洲音乐学学科理论体系自身亦有潜藏其中的深刻的学理和价值危机!(该问题拟另文专论)
(34)由于研究者同他研究的音乐可能不属同一文化体系,于是,什么是“音乐”也成为研究的前提和研究的问题。这里似乎遇到了“鸡与蛋”需要同时面对的问题。因而,文化也就成为了考察和确定音声范围和意义的基础和条件,并成为了音乐研究者所审视和考察的对象。
(35)这里以“文化学”与“音乐学”并举,想指出的是:梅氏理论属于文化研究而非音乐研究,归根结底,该模式是一个人类学的研究框架,而非音乐学(即非音乐学知识体系范围内)的研究框架。
(36)尽管仍称之为“音乐”,但它已是音乐中一类性质和意义都不相同的范畴及样式,与存在于民俗中的并不一样。
(37)所以,他才有意回避并不讨论音乐的“记谱与分析”,的确,他还没来得及将作为非“艺术”的音乐的形态的性质以及它的文化意义等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弄清楚并最终定性,也就没能提出他的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的音乐“记谱与分析”模式。也正由于此,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继续思考的空间和一条尚需探索的道路。如果说,梅氏“模式”本身就不是一个音乐学范畴的东西,它并没有开发出一个适于其音乐分析的模式,那我们又怎么可能用此理论“模式”将“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清楚呢?由此看来,“两张皮”的困境就是一个必然!
有鉴于此,当应对此悬而未决的问题再做积极的理论开拓,这是由民族音乐学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上的各种民族的音乐文化。它面对的是多元与多样,它要求世界所有的不同的音乐文化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这些多样化的经验必然是建立在多样性的认识和阐释基础之上的。真正有价值的经验是面对本土资源,能够从具体文化的存在和现象出发的事实描述和理论阐释。民族音乐学必须发展自己的研究理论包括“记谱与分析”理论。这也就为不同地区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前提和条件。由此,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应该积极参与到本土化的研究中去,因为我们就在其中。理论创新,本土的资源,当是最好的机会和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