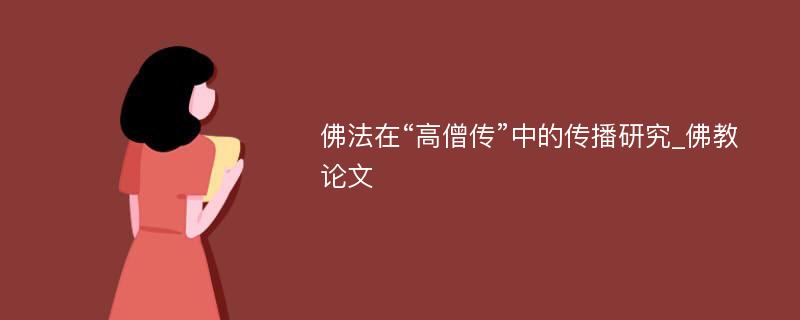
《高僧传》弘法起信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僧论文,起信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梁释慧皎在《高僧传》(注:本文工作本为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自序中说:其记载“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终于梁天监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载。”[1](P.524)按此期正为佛法东传最为重要的滥觞阶段,故从《高僧传》辑录出关于弘法起信之材料若干,并稍加整理,以窥早期佛法的传布与影响。
系年第一
系年者,意在明其次序。系年之法,以起信事件发生之年为定:如《卷十二·诵经·晋并州竺慧达》据原文“西晋将末,建兴元年”[1](P.478)可定;若无明确记载则参以本事先后之文:如《卷一·译经上·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支谦)》据起信事前之文记载当在吴赤乌年间[1](PP.15-18);若仍乏考则参以本传先后之文:如《卷一·译经上·汉雒阳安清》据传文起信事在汉灵帝之末[1](PP.5-6);最下参以本传标题之文:如《卷一·译经上·魏吴武昌维祗难(法立 法巨)》起信事在维祗难东来之前,故根据标题推断在三国年间[1](P21)。以标序为首,其次年代:凡北方诸条均依慧皎本传所系之朝代为准,如《卷九·神异下·宋伪魏长安释昙始》其起信事在北魏拓跋焘时而系于宋元嘉年间[1](PP.385-386),其次卷科,其次传别,其次页码,其次起信大略,总成一表如下:
标序
年代 卷科
传别
页码
起信大略
1
东汉灵帝之末
卷一译经上
汉雒阳安清
5-6
明三世之有征
2
吴赤乌年间
卷一译经上
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支谦) 15-18
江左大法遂兴
3
吴末
卷一译经上
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支谦) 5-18
以开其心
4
三国年间卷一译经上
魏吴武昌维祗难(法立 法巨)
21
于佛法大生信乐
5
西晋惠帝年间
卷一译经上
晋长安帛远(帛法祚 卫士度)
26
白黑宗禀几千人
6
西晋永嘉前
卷四义解一
晋剡东仰山竺法潜(竺法友 竺法蕴 康
156
味道者数盈五百
法识 竺法济)
7
西晋永嘉年间
卷九神异下
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慧持) 372-373
莫不 邪改信
8
西晋建兴元年
卷十三兴福
晋并州竺慧达
478
归心者众矣
9
东晋咸和年间
卷九神异上
晋邺中竺佛图澄(道近)
345-352
中州胡晋皆奉佛
10 东晋咸和年间
卷一译经上
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支谦) 15-18
由此信敬
11 东晋咸康年间
卷五义解二
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王嘉)
178
道俗欣慕
12 东晋简文年间
卷五义解二
晋京师瓦官寺竺法汰(昙壹 昙贰)193
三吴负 至者千数
13 东晋孝武年间
卷五义解二
晋泰山昆仑岩竺僧朗(支僧敦)190-191
称善无极
14 东晋孝武年间
卷五义解二
晋荆州长沙寺释昙翼(僧卫) 198-199
道俗奔赴
15 东晋孝武年间
卷五义解二
晋荆州长沙寺释法遇
201
劝业者甚众
16 东晋孝武年间
卷五义解二
晋荆州上明释昙徽202
咸致敬印手菩萨
17 东晋太元元年
卷六义解三
晋庐山释慧远
213
望风遥集
18 东晋太元年间
卷六义解三
晋庐山释慧永(僧融)
232
归心者众矣
19 东晋太元年间
卷九神异下
晋长安涉公 373-374
士庶皆投身接足
20 东晋太元末年
卷九神异下
宋伪魏长安释昙始
385-386
高句骊闻道之始
21 东晋元兴年间
卷九神异下
晋西平释昙霍
375
因之事佛者甚众
22 东晋义熙年间
卷六义解三
晋新阳释法安
235
改神庙,留安立寺
23 东晋义熙年间
卷六义解三
晋彭城郡释道融
241-242
像运再兴
24 东晋义熙年间
卷六义解三
晋长安释僧
244
远近归德
25 东晋宋之交
卷七义解四
宋京师彭城寺释僧弼
270
大化江表
26 宋武帝年间
卷七义解四
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僧馥 法业)264
使荆楚之民 邪归
正者,十有其半
27 宋元嘉前卷四义解一
晋剡岘葛山竺法崇(道宝)171
少时,化洽湘土
28 宋元嘉年间
卷三译经下
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阿那摩低) 131-134
通才硕学师事焉
29 宋元嘉年间
卷三译经下
宋京师奉诚寺僧伽跋摩
119
倾于京邑
30 宋元嘉年间
卷三译经下
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 121-122
望风成化
31 宋元嘉年间
卷七义解四
宋京师东安寺释慧岩(法智)
263
声布楚郢
32 宋元嘉年间
卷七义解四
宋京师兴皇寺释道猛(道坚 慧鸾 慧敷
296
大化江西,学人成列
道明)
33 宋元嘉年间
卷八义解五
齐山阴法华山释慧基(僧行 慧旭 道恢
324
士庶归依,利养纷集
慧永 慧深 法洪)
34 宋元嘉年间
卷九神异下
宋伪魏长安释昙始
385-386
顶礼足下,悔其 失
35 宋元嘉年间
卷十三唱导
齐兴福寺释慧芬
514-515
梁楚之间奉其化
36 宋孝建年间
卷三译经下
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阿那摩低)
134
四远道俗,咸敬异焉
37 宋大明年间
卷七义解四
宋蜀武担寺释道往(普明 道誾) 284
咸发净心
38 宋孝武年间
卷十一明律
宋京师庄严寺释僧璩
431
道俗归依
39 梁天监前卷十二诵经
梁富阳齐坚寺释道琳
474
众皆服其征感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高僧传》所载之高僧弘法起信事迹主要集中在东晋及南朝宋两个时期,详言之:东汉一条,三国三条,西晋五条,东晋十五条,晋宋之交一条,南朝宋十三条,梁一条。其中,三国三条中吴独占其二;西晋五条中永嘉占三;而孝武、太元及义熙几乎瓜分了东晋起信事载,分别为四条、四条及三条;同时元嘉亦占南朝宋条数大半,有九条之多。依照此表可以大体推定以下几点:其一,高僧在灵帝末年已有弘法起信事迹,说明东汉末期佛教早已东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虽详辨佛教何时传入,而未对何时佛教开始产生广泛影响有足够的重视,颇显欠缺。其二,佛教传布并产生较大反响是从三国后期逐渐开始,至西晋时全面展开,又至东晋及南朝宋时高僧们弘法起信之努力业已达到最高点,波澜壮阔、蔚为壮观,这说明当时佛教在东土还未完全站稳脚跟,正奋力拚搏,竭力弘教。其三,至于南朝齐梁时高僧所矻矻以求的当务之急已经不再是弘法起信,其所关注的焦点稍稍他移了,佛教似乎在中土有了身份,占了势力。其四,起信事件又主要集中在晋宋的几个时段(东晋孝武、太元、义熙及宋元嘉),这可能与本朝重臣及名士对佛教的态度有着莫大关系。(注:《世说新语》中此类记载颇多,萧登福所撰《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五章“两晋名僧名士相交游及佛教之发展”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可参考。)
地域第二
地域问题在古史研究中特别重要,人世沧桑,渺茫无稽,而地域虽有沿革、有变迁,却故地犹存、大体可考。对起信行迹的考查,必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佛教早期传布时的诸多问题,故单独加以讨论。再造地域表如下:
故地
今地 影响范围
标序
吴建业江苏南京
江左大法遂兴
2
东晋京师
江苏南京
三吴负盖至者千数 12
宋京师江苏南京
京师远近,冠盖相望
28
宋京师江苏南京
四众殷盛,倾于京邑
29
宋京师江苏南京
于是敬以为师,令子弟悉从受戒
35
宋京师江苏南京
四远道俗,咸敬而异焉
36
宋京师江苏南京
道俗归依,车轨相接
38
西晋松江
江苏苏州南 吴中士庶嗟其灵异,归心者众矣
8
宋三吴③
江苏苏州,浙江湖州、绍兴
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余人
33
宋县 浙江宁波东 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
30
梁富阳浙江富阳
众皆服其征感,富阳人始家家立圣僧坐以饭之 39
宋寿春安徽寿县北 于是大化江西,学人成列 32
宋熟 安徽和县北 梁楚之间,悉奉其化
35
东晋长沙
湖南长沙
道俗奔赴,车马轰填
14
东晋长沙
湖南长沙
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劝业者甚众
15
宋湘洲湖南长沙
少时,化洽湘土 27
宋长沙湖南长沙
门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 30
宋楚郢湖北江陵、武汉
训诱经戒,大化江表
25
宋荆州湖北江陵
使夫荆楚之民 邪归正者,十有其半 26
宋江陵湖北江陵
于是声布楚郢,誉洽京吴 31
东晋上明
湖北宜都东 于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萨 16
东晋阳新④
湖北武昌南 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
22
东晋庐山
江西庐山
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
17
风遥集
东晋庐山
江西庐山
白黑闻之,归心者众矣
18
宋成都四川成都
行途瞻仰,咸发净心
37
南凉西平
青海西宁
国人既蒙其祐,咸称曰大师,出入街巷,百姓并 21
迎为之礼
西晋长安
陕西西安西 白黑宗禀,几且千人5
前秦长安
陕西西安西 奉为国神,士庶皆投身接足 19
后秦长安
陕西西安西 婆罗门心愧悔伏,顶礼融足 23
后秦长安
陕西西安西 于是美声遐布,远近归德 24
北魏长安
陕西西安西 大弘佛法,盛迄于今
34
后汉雒阳
河南洛阳
远近闻知,莫不悲恸,明三世之有征也1
西晋洛阳
河南洛阳
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 6
后赵邺中
河南安阳
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
9
北魏武邑
河北武邑
名实既符,道俗欣慕
11
前秦泰山
山东泰山
百姓咨嗟,称善无极
13
后燕辽东
辽宁辽阳
盖高句骊闻道之始也
20
(注:③“三吴”所指地区说法不一,今从《水经注·卷四十》载:“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则“三吴”当为今江苏苏州,浙江湖州、绍兴等地,其他说法可参看《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三吴”条。)
(注:④校注本正文作“新阳”,而汤氏校记云:“《冥祥记》作阳新县”,查《晋书·地理志上》“新阳”乃西晋时天水郡属县,此时已为东晋,显误;又据《晋书·地理志下》“阳新”属武昌郡,本传又载武昌太守向其索借铜钟云云,则可证明其与武昌之关系,故应从《冥祥记》为“阳新”。)
表中地域考定方法大体与表一相通,以起信发生地为“故地”,不依本传传名所列地域。其中起信事件地域不明者参考本传上下文而定,不可考定者暂缺,第二列为与故地相对应之“今地”(注:主要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册》第三、第四分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故地若为州郡,其与现今行政区域不能匹配,则用与其时州郡治所对应的今地予以表示。),第三列备录佛法化洽之范围,最末注明在表一中的标序,以资校覈。
从地域表中可以得出诸多推论:其一,长江流域及其南方所披弘化要远过于北方,这可以从起信地域的广度(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青海)以及起信事件的数量(南:25;北:13)的南北对比中看出,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高僧们在南方起信布法的成绩要高于北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汉末魏晋以来南方相对于北方较为安定,故而“避乱过江”[1](P.156)、“避地东下”[1](P.201);或是南方自古以来为南蛮、巫楚之地,而北方乃中原故邦,前者民风久好怪诞神奇、幽冥鬼魅,后者却浸染礼教甚深、熏陶儒学弥久,故南方比北方易于接纳佛教(注: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十七章和第二十一章对此有详论,可参看。),且与道教的传布也有着很深关系(详见总论第四);或是著者释慧皎本属南朝,对南方高僧行迹比较熟悉的缘故;亦有可能上述诸端兼而有之。其二,起信地往往出现在重镇(如古南京、古苏州、古长沙、古江陵、古西安、古洛阳、古成都),这大概说明高僧们弘法起信时主要是走城市辐射农村的路线,更加便利于其接触世家望族,接受来自上层的惠顾,特别是统治者的服膺将大大促进起信事业的拓展;也可凭借重镇的交通优势,将佛法的影响力最大程度地辐射出去;亦可见当时在穷乡僻壤传教布道是很困难的,或根本难以推行。其三,就整个弘法起信地域的范围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青海总十三省),可谓斜贯中土、化洽南北,说明至迟在南朝梁前弘法高僧们已将大法传布到了东土绝大部分地域,并有了大量的起信事迹(详事迹第三)。其四,高句骊从辽阳得道,反映出佛教继续向东传布的趋势和高僧向域外弘法的意识。
事迹第三
释教西来,与中土人情世俗必然有诸多扞格难通之处,而要使得佛法渗入民众、为其接受,就必须依靠高僧们的不懈努力。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序》中也说:“道由人弘,法待缘显,有道无人,雅文存而莫悟,有法无缘,虽并世而弗闻。”[2](P1)通过对其众多事迹的考查,或许对认识佛教史的诸多问题有所帮助。高僧们弘法起信的众多事迹可粗分为八类:
其一,显神异。此类在起信事中占有较大比重,有十八处之多,又可详分为以下几种:获舍利,三处(在表一中的标序为2、14、30,此下皆同);延佛像,三处(8、14、17);咒验灵,三处(4、9、36);晓幽事,两处(9、21);虎不食,两处(22、34);验报应(1)、经僻火(7)、刀不伤(34)、耐饥饿(21)、现神迹(39),各一处。
其二,倡法理。共十六处,颇为可观,也可再分为:为王侯讲学,四处(11、12、29、36);游击宣教,四处(20、24、25、33);论辩弘教,三处(23、31、35);通透典籍宣扬佛理,三处(5、6、32);精舍讲习,两处(5、16)。
其三,创寺庙。共六处(13、14、26、27、30、37)。
其四,弥灾祸。共四处,其中除虎灾两处(13、22),祈雨救旱灾两处(9、19)。
其五,示惩戒。共四处,其中施于帝王两处(3、34),自我责罚一处(15),施于冒犯高僧者一处(18)。
其六,施救护。共三处,其中挽救王室成员两处(3、9),救护佛家弟子一处(39)。
其七,自标高。共三处,其中得贵胄推崇一处(24),硕儒求教一处(36),律行无疵一处(38)。
其八,呈尊像。共两处,其中即崖镌像一处(37),图写安形一处(16)。
从以上所列几类中,可以看出高僧们在弘法起信时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根据各类分布情况的差异,亦能推断出以下几点:其一,起信手段主要集中在“显神异”和“倡法理”上,这似乎从鬼神幽怪的虚幻角度和渊深细密的学术角度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东土民众的思维习惯和信仰趋向;其二,就整个起信手段而言,因有实际验用而激发士庶皈依佛法的起信类别和事件数量,要远远高于因佛法渊宏以及高僧崇拜而使得众人笃信不二的相关类别和数量,前者占了八类起信手段中的一半(显神异、弥灾祸、示惩戒和施救护,数量也有二十九处之多),而后者只占两类(倡法理和自标高,数量只有十九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佛教之所以能在当时兴起,主要依靠的并非其精深严密、三乘四谛的玄妙佛理和超凡脱俗、遥不可及的高僧魅力,而是显而易见、立竿成影的通灵施惠,这与当时道教蓬然兴起的缘由或许有相通之处(注:赵夏竹《汉末三国时代的疾疫、社会与文学》(《中国典籍与文化》,总3日期)曾指出道教兴起与三国时代瘟疫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功利色彩如此之强大大冲淡了宗教本身所标志的神圣和虔诚。汤用彤曾经指出魏晋佛法兴盛的原因有四端:一因法术煽惑、一因清谈助兴、一因外胡支持、一因道安尽力[3](PP.133-135),若从上述分析看来汤氏论述基本公允,但后两因似乎有所牵强。其三,高僧能够有意识的创建寺庙,规划长期弘法的蓝图,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布,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寒门子弟入读研习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造就了所谓“士大夫佛学”与其时玄学清谈冲击和揉杂的特有现象,这又反过来加速了佛教的化洽。陈垣曾于1932年北平辅仁社夏令会讲时提到佛教能传布中国的三点原因:能利用文学、能利用美术及能利用园林[4](PP.65-72),其言园林也已提及佛寺却未述及其弘法起信之功用,而通观其“三因说”立论的材料大率出于唐宋,不知陈氏所谓“传布”为何回避魏晋之“传入”,只是稍有言及而已,相形之下,汤氏“四因”说较之胜出。
如果从起信对象的角度来看,犹有可说者:其一,对权贵,高僧们可谓软硬兼施、恩威并重,软者获舍利、延佛像、咒验灵;硬者示惩戒,恩者施救护、弥灾祸,威者倡法理、自标高。对半信半疑者(如孙权、石勒及耨檀等),高僧知道其“不远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1](P346),便显出神异,从而取信;对倾慕者(如刘义康、姚兴等人),便炫耀起佛法的精深宏大,畅谈法理、悠游典藏,无得而逾之,便越发崇敬、笃信不疑了;对冥顽不灵者(如孙皓、拓跋焘),毫不手软,甚至使秽佛者孙皓“举身大肿,阴会尤痛,叫呼彻天”[1](P17),然后又妙手回春,受戒病瘳,慧皎曰:“唯叙报应近事,以开其心”,可谓得之[1](P18),若能得到实权者的青睐,起信事业自然会顺利得多,效果将明显得多。其二,对士和庶,比较复杂。在起信载文中,“士庶”连出者有六次(8、19、22、29、30、33),结合原文细揣其义当是对一般民众的泛指(注:又提到“士女”(12、16),意思似乎与前者相近。),起信手段包括创寺庙、弥灾祸、倡法理、显神异、呈尊像;提到士大夫三次(17、24、36),起信手段为显神异、倡法理、自标高;提到“道俗”连出者(注:又提到“黑白”两次(12、16),《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合订本)“黑白”词条下第四个注解为:道俗。而又有“白黑”者三次(5、18、37),意思与前者相仿,字序颠倒而已。《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收录释慧琳《白黑论》,其中“白学先生”崇奉儒学,“黑学道士”宗述佛法,与上述“黑白”之意稍稍不同。)共七次(11、13、14、15、28、30),根据起信载文理应是僧众和俗人的合称,所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此推测高僧们对俗众的起信方法是倡法理、显神异、示惩戒;其他含有广泛民众意思的起信对象,还包括“众”三次(15、35、39),“民”一次(26),“百姓”两次(13、21),其起信手段主要有创寺庙、倡法理、显神异、施救护、示惩戒。可以看出,高僧们对士与庶实际上都采用功利刺激和学理引导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弘法起信,然而对前者明显偏重于学理上的传教和启发,而对待普通民众则更多采取了显示现报的起信方法,侧重于对高僧法力、释教神奇的夸耀,从而诱其信服。其三,对持异教观念者,高僧们毫不懈怠、各显神通,有的妙示神异、金针度人(4),有的大兴土木、创建寺宇引渡众生(30),有的执定大法、抗言明辩(23);而对黄老教徒,除了炫耀自己的法力(8)外,更是厉用罚治,严惩不贷(34),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威慑了倾慕于异教而敌对佛家的士庶们。
总论第四
以上三篇,各执一端,未能综观融会、互补发明,现汇合三篇,冀有所得。整个起信事件大体可粗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汉末至于西晋建兴元年为发轫阶段。起信地主要集中在河南洛阳(1、6)及江南之南京(2)、苏州(8)南北两大区域,且分别在汉末(1)和孙吴(2)时就有高僧在洛阳和南京布教,然后再于西晋时向陕西西安(5)和三吴(8)拓展,这就大体有了两条弘法的行进路线:一条由南京向南,一条由洛阳向西抵西安;而起信手法主要为显神异(1、2、4、7、8)和倡法理(5、6),这说明其时佛教初入,士庶颇感陌生,故多用法术神力来吸引众生,同时辅以渊深佛理对前者的拔高激发起高层士族对其的关注(可参看事迹第三的相关论述),从而为佛法能在上层和下层思想空间内迅速打开局面打好基础,并且倡法理也是在显神异有了影响的情况下而采用的:如在洛阳,于汉末时通过验报应(1)起信,到了西晋永嘉前便开始讲法华、大品(6)传法施教了。
第二期,从东晋咸和年间到宋元嘉年间为鼎盛期。在入南朝之前第一期的两条线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南京一线萎缩逡巡、盘桓不进(12);而洛阳西安一线却蓬蓬勃勃、北上南下。首看北路,先从洛阳至安阳(9),到河北武邑(11),达山东泰山(13),远及辽宁辽阳(20);次看南路,先大化两湖流域(14、15、16、22),并向东抵江西庐山(17、18)。而直到宋元嘉年间第一期的南京一线才向南向西稍有推进,前者只到浙江宁波东(30),后者也仅至安徽寿县(32)、和县(35);与此同时原洛阳西安一线也失去了狂飙迅猛的突进劲头,只是巩固既得地盘:陕西西安(34)、湖南长沙(27、30)、湖北江陵(25、26、31);其中北路安阳至辽阳一线,起信手段主要是稍重于宣扬佛教精义的倡法理(11、20)、创寺庙(13),但也兼用炫耀法力的显神异(9)、弥灾祸(13),而反观南路两湖至庐山一线,则绝少倚重倡法理(16)、创寺庙(14),主要采取显神异(14、17、22)、示惩戒(15、18),梁启超“南方尚理解、北方重迷信”的推断[5](P9)显与史实乖舛。从此可以看出,在高僧拓展弘法空间的初期,所采用的起信手段应是针对南北地域文化的不同而精心挑选的,或者说其想广布佛法就不得不入乡随俗、合潮同流,这又可与地域第二中的相关推测互证发明:第一期南京一线之所以畏止不前,大异于洛阳西安一线的开枝散叶,这是由于在第一期高僧们更看重洛阳和长安的政治意义,大都云集于此,所以一旦有变,便会四散开去,将原先集聚收拢的高僧集团拆解,从而开辟了由此而兴的弘法起信大业之鼎盛时期,而南京却无法拥有如此庞大的高僧群体,这也可解释为何其即使作为东晋都城也不能与前者延伸规模相侔的疑问了;入南朝后,几条弘法路线基本上不再探进或只是稍有延伸(32、35),这大概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主要行政区域都已被高僧囊括,其他深山老林、鬼谷幽径不具备太大的弘法意义的缘故,另一方面已布教的地区也不够巩固:如东晋时婆罗门挑战,遂使释道融雄辩救法(23),异教蓬起、多有缺失,高僧必然要回防固守、重夺失地,也就无暇他顾了,如拓跋焘毁法,始有释昙始力挽狂澜(34);稷下自古乃方士云集之地,秦始皇慕仙敬神求不死之药即受其蛊惑,汉末遂有太平道孳生渐起,佛教虽在其入华初期亦被视为一种道术、僧人被称为道人(注:僧人亦被称为道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凡称道人者皆为高僧,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道人”条对此有详说,可参看。),但必然会受到前者的抵制,故而于此不易大展宏图;同样五斗米教占据的巴蜀地区直到第三期才始见高僧起信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注:李文才《〈高僧传〉所见部分东晋南朝巴蜀地区僧人事迹及推论》(《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对此有详论,可参看。至于中国早期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冲突和关系,可参看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五章“佛教之弘传与道教”及萧登福《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附录《佛教初期发展及佛道二教交流》。),故而汤用彤认为黄老方术盛行之地亦利于早期佛法传布是值得商榷的[3](PP.56-59)。
第三期,从宋孝建年间到梁天监前为成熟期。弘法地域微有扩展,西南至四川成都(37),东南至浙江富阳(39)。其不振缘由除了第二期相关分析外,似乎亦与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有关,而相较于此期间《高僧传》对其他事件的载录,起信事迹可谓微乎其微,南朝齐竟不书一条,梁也仅存唯一,同时起信手段也偏重于自标高(36、38)、创寺庙(37)、呈尊像(37),稍有弥灾祸(39)、显神迹(39),可说明民众对佛法已经有了认识。此时弘法起信似乎已不再成为高僧们的当务之急,佛教影响基本渗入了中土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自身在东土的宗教席位(可证系年第一之推论)。
历来谈论中国佛教史者,大多津津于何时何地佛法东披的问题,殊少对佛法如何在中土确立信仰及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注: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综述。),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也只是讨论了四世纪到六世纪的起信问题[6](PP.375-378),殊不知更为重要的是二世纪至四世纪前后这段时间,且亦未能对《高僧传》有足够的重视,而《高僧传》作为成书最早、内容最富、保存最好的佛家史传(注:可参汤一介《高僧传·绪论》,史学大师如钱穆、陈垣都对《高僧传》极其重视,汤用彤更以《高僧传》为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门径,陈寅恪亦对《高僧传》颇下功夫作有读书札记若干。)自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笔者对此久有兴趣,遂详阅全传、略有所得,又不自量力、草创成篇:作系年第一,明其时序;地域第二,晓其路径;事迹第三,显其作为;总论第四,推定三期。昔日钱穆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举吹灭康氏伪经谬说,仅凭一部《汉书》,后人嗟叹不已、传为佳话,笔者心慕久矣,今撰此篇,聊表谨敬先贤之意。
